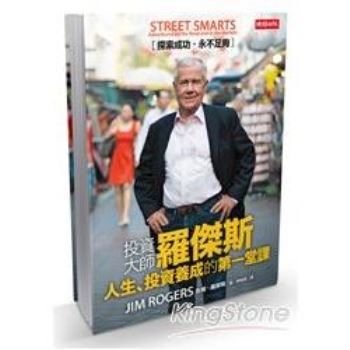第一章.青年投資人的畫像
事無永恆,變化永存
我家鄉戴摩波里斯(Demopolis)位居阿拉巴馬州坎布雷克(Canebrake)地區中心,正好是黑戰士河與湯比比河匯流處。
戴摩波里斯是馬倫哥郡(Marengo County)最大的城市,坐落在喬治亞、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三州歷史上號稱黑土地帶的中心。會叫做黑土地帶,是因為大地上鋪滿厚厚一層肥沃草原黑土,近兩百年前,這些黑土滋養了龐大的棉花田作物,解放黑奴之後,有些棉花田還繼續生存,但是沒有一座棉花田能夠熬過棉籽象鼻蟲的摧殘。
我還是小男孩時,每次要跟朋友出門釣魚,就是在這塊土地上挖掘魚餌。美洲鯰魚無所不吃,不只吃蚯蚓,牠會咬住任何聞到的東西,而且不論什麼東西的味道幾乎都聞得到。在炎熱的夏天,挖蚯蚓比抓蟋蟀還容易,那一年我八歲,和大我約十個月的堂哥韋德在我家後院挖蚯蚓,當時他說了一句我當時聽不懂、但直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的話。
他說:「如果我們繼續挖下去,最後會挖到中國。」當時我已經是個熱愛研究的人,不會不知道地球是圓的,但是我查看地球儀後才了解,和阿拉巴馬州方向相反的地球另一邊,橫亙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龐大的陸塊,如果我們有足夠的精力繼續挖掘,一定會滿身汙泥、全身濕透的鑽出中國地面。
幾十年過去了,今天我終於定居在中國的大門口,兩位金髮碧眼小美女女兒的普通話,說得比英語還流利。我怎麼變成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是跟挖掘有關的另一個故事,這樣的挖掘可能沒有這麼辛苦,卻同樣費力;是我無盡無止、親身深入體驗世界運作、發掘真實故事,完全靠自己探索的結果。
我花五年時間環遊世界兩次,一次是騎機車,另一次是駕駛汽車,讓我了解一百多個國家的變化。對我來說,不是坐在安樂椅上了解歷史和歷史的影響,而是要親自探險。這樣做帶給我個人與物質極大的報酬,而且無可避免的引導我來到新加坡:一個遠離窮鄉僻壤阿拉巴馬州、馬來半島南端華人前哨站的國度。
如果歷史能夠確定什麼事情的話,一定是希臘人所說「事無永恆、變化永存」,最早說這句話的人是西元前六世紀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斯( Heraclitus),他警告我們,一個人不可能踏進同樣的河水兩次。預測變化的能力是評估人生成就的標準,我搬到新加坡,是為了因應世界處於歷史性變化、世界大勢急劇改變、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沒落、亞洲相應崛起的認知。
我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寫這本書,世界各國大部分政客都希望你相信這場危機為時短暫,告訴你情勢一定會轉變。我不會質疑這一點,只是要告訴你,在你有生之年,情勢不太可能永遠轉變。很多國家積欠的驚人債務會導致人類生活與工作方式的重大改變,很多舊的制度、傳統、政黨、政府、文化,甚至國家都會沒落、崩潰或是完全消失,就像政經重大動盪時代總是會發生的情形一樣。
例如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在二○○八年崩潰時已經經營幾十年了,同年倒閉的金融服務業者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營業已經超過一個半世紀。這些歷史悠久的全球企業不支倒地,證明美國很多制度正面臨情勢變化,哈佛、普林斯頓,和史丹佛等大學或許並不自知,卻可能正走向破產之途。博物館、醫院和我們知道與深愛的其他機構正走向困境,我們會在未來的金融或經濟巨變中,看到很多這種機構消失。
有些人說我危言聳聽,說我是現代專門預測凶事的烏鴉嘴卡珊德拉(Cassandra)。但是我在未來的情勢中,看不到半點值得驚慌、甚至值得驚異的地方。改變的大風已經吹起,從中國的方向吹來,而且是以可預測的方式吹來。我們所看到的情形一切如常,歷史正在翻轉熟悉的一頁。
在整個人類史上,這種轉型時刻都會為有心人提供大好良機,因此我對未來的很多事情極為樂觀。如果你在十九世紀開始之時夠精明,會前往倫敦;如果你在二十世紀開始之時很精明,會打包搬到紐約;如果你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時很精明,會前進亞洲。
一百年後,變化的循環可能轉到任何地方—第一個千禧年結束時,所有的聰明人都搬到科多華(Cordoba),伊斯蘭教統治西班牙期間的繁華都會、當時歐洲的知識中心以及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待續)二○○七年我搬到亞洲,更重要的是,我把小孩也帶來這裡。在她們有生之年,通曉亞洲是創造成就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各國,精通中文會變成像今天精通英文一樣重要。一九二○,三○年代,世界權力和影響力從英國移轉到美國,金融危機和施政不當導致英國加速喪失領導地位,很多人要到二、三十年後,才注意到這一點。現在世界權力和影響力正由美國移轉到亞洲,同樣的力量讓美國加速失去領導地位。
轉向亞洲的風潮在第二次歷史性大變動的時刻出現,在金融海嘯嚴重期間,世界面臨擺脫金融的情勢,也面臨擺脫金融業者作為繁榮來源的循環性變化。整個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期間由金融家負責主導,也有很多期間由實質財貨的生產者,包括農民、礦工、能源供應業者、伐木工人負責主導。二十世紀的五○、六○和七○年代,在大多頭市場開始前,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區是默默無聞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會再度打回原形,搬運資金的專家正在沒落,聖經舊約《約書亞記》中所說「劈柴挑水的人」即將繼承這個世界。
省思造成變化的歷史力量、擁抱事無恒常的簡單假設之際,我不由得欣賞西方文明另一位偉大思想家愛因斯坦的說法:「只有兩件事情無窮無盡,就是宇宙和人類的愚蠢,而且我對前者是否無窮無盡,還不是這麼肯定。」
我們別忘了特洛伊城的公主卡珊德拉,她警告大家,不要把希臘人留下的木馬拖進城裡時,其實是自找麻煩,要是我們記不得這件事的其他特點,我們應該會記得她的預言正確無誤。
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大家了解,我們怎麼會走到今天這種地步,個人要怎麼自我教育,以便為未來做準備。我會跟你分享我一輩子從事金融、投資與冒險之旅所得到的見解,跟你分享我成長之際所學到的教訓,說明我從黑土地帶的泥土出發,走到地球另一邊這個東南亞城市國家的終生之旅中,怎麼把整個世界當成我家後院的經驗。
凡事沒有「夠了」這回事
我的市場探險之旅始於一九六四年春季,當時我是耶魯大學四年級學生,我發現自己非常像幾年前前進長春籐盟校一樣,跌跌撞撞的闖進華爾街。
我念高中時,熱心參加同濟會俱樂部(Key Club)的會務,同濟會俱樂部是由學生領導的服務組織,隸屬到一九七六年還只限制男性參加的國際同濟會(Kiwanis International)。
戴摩波里斯同濟會俱樂部會員資格是了不得的大事,因為本地的支持者決定一年只允許五位少年入會。我擔任會長那一年,戴摩波里斯同濟會俱樂部贏得世界小城鎮最優秀同濟會俱樂部的殊榮。當時耶魯大學每年發給一位國際同濟會俱樂部會員四年的獎學金,也因為這項獎學金我才認識耶魯大學,如果不是同濟會俱樂部的關係,我根本不會申請耶魯大學的入學資格。
除了耶魯大學,我滿心希望就讀也是唯一申請的是田納西州西瓦尼(Sewanee)的南方大學,這所大學跟美國新教聖公會關係密切,是一所文科大學。我寄出申請書後不久,就接到西瓦尼方面寄來的同意書。一直到四月或五月,家父寄給西瓦尼要求的五十美元接受費之後相當久,我才收到耶魯大學寄來的厚厚信封,通知我耶魯大學已經接受我這個學生,而且發給我一年兩千美元的同濟會俱樂部獎學金。
我嚇壞了。
我才十七歲,對耶魯大學一無所知,只知道這所大學設在康乃逖克州的紐海文(New Haven)。然而,家父、家母經驗豐富,知道耶魯大學接受我這個學生的重大意義。他倆都是大學畢業生,在奧克拉荷馬州大學認識,兩人當時都是優等生。家父主修石油工程,家母主修文科。對他們來說,我上耶魯大學是相當非同小可。我記得家父說過:「我們有點擔心送你到北部這座自由主義堡壘。」但事實上,他和家母都樂不可支。家父的欣喜後來略為降低,因為他無法索回寄到西瓦尼的五十美元。在一九六○年的戴摩波里斯,五十美元是一筆大錢,今天仍然是一筆大錢,但是當時五十美元的價值大約是今天的七倍之多。
我是家中五兄弟的老大,也是高中畢業班不到五十位畢業生的其中一位,於是我對所有人表露出因幸運而產生的過度自傲,就像本地人所說的,裝出大狗的樣子,但是自我膨脹的意識注定很短命。我慢慢的明白:唉,唉,我現在得去上耶魯了。我突然覺得很害怕,因為整個情勢遠遠超出自己的理解範圍。我不禁問道:我現在要做什麼?(待續)那年夏天,我搭火車到波士頓參加同濟會俱樂部大會,在紐海文下車後前往耶魯大學的招生辦公室,我希望知道他們為什麼接受我這個學生,希望問這個問題後,自己可以知道將來會是什麼樣子,也能了解他們對我有什麼期望。招生主任抽出我的卷宗說:「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你看,你以全校第一名成績畢業,很多科都得到一百分,平均成績接近一百。」
我心想:對,但那是在戴摩波里斯,唉,天啊,這些傢伙認為我很聰明,認為我懂得不少東西。
我就在覺得全無準備、無法跟美國東北部著名預校學生競爭的情況下,來到耶魯,但我抱著比別人更認真的決心,準備努力用功。記得有次老師要考試,一位同班同學說他要花五小時準備:「這次考試值得花五小時準備。」我發現他的想法很奇怪,我的方法是儘量努力用功,直到了解這一科目為止,然後再多用功一番,確保萬無一失。這是我處理所有事情的方法,是胞弟和我從父母身上學到的紀律:「凡事沒有『夠了』這回事」,不管任務是什麼,你就是要不斷用功、不斷努力,或不斷的研究。
當時上耶魯所需的學費和食宿費一共兩千三百美元,我有兩千美元獎學金,所以一開始就少了三百美元,而且還沒有算書籍費和其他固定開支,於是每星期我到學校餐廳打工幾小時,上大學期間也兼做校園裡的差事。
青年期工作經驗帶來的好處,是可以計算的。除了能學習金錢價值,也能幫助自己培養認同;學習財務管理時,你會獲得明確的自主性。我從小就開始自力更生,六歲時家父教我﹁錢不是長在樹上﹂的道理,堅持要我自己出錢買棒球手套,於是我到五金行挑了標價四美元的手套,然後每星期六付給老闆布拉斯威爾(Cruse Braswell)十五美分,一直到付完全部金額。多年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引用某大學的研究告訴我,要預測成年之後生活是否幸福,最重要的單一指標是青少年時期做過有報酬的工作。
總之,我的耶魯生活過得很愉快。我主修歷史,還以舵手的身分參加划船賽,大二、大三當選校隊選手,四年級時沒有擔任舵手。我甚至涉入演藝事業,得到幾次重要的戲份,其中一部電影由一九六一年從耶魯畢業的貝德漢(John Badham)導演。你可以想像,要是他的《周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用我當主角,這部電影應該會更紅!雖然我十分喜愛演藝事業,卻沒有過度深入,原因跟我大四時不當舵手一樣。我把時間花在學業上,這樣的紀律也得到回報,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卻能夠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但我像很多大學畢業生一樣,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
哈佛商學院、法學院和耶魯法學院都接受我的入學申請,但是我也申請進入醫學院,因為希望得到更多選擇的興奮之情。然而我真正的希望是到處旅行,我從小就愛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的《匹克威克遊記》(The 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俱樂部的紳士和他們的漫遊冒險,在我漫遊欲望的發展中,可能扮演了某種角色。雖然我才二十一歲,卻對自己有足夠的了解,知道光是離開家園就是我教育當中重要的一環;我的情況是,離開阿拉巴馬州的農村,到一千六百公里外去上康乃逖克州的長春藤大學。
這段經驗讓我大開眼界,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就像吉卜齡(Rudyard Kipling)在《英國國旗》(The English Flag)這首詩中所寫:「只了解英國的人,又能對英國了解多少呢?」
置身在很多耶魯學生當中,總是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已經到外國旅行過。我總是一心一意想要多了解、多看看這個世界。
我因為急於擴大眼界,申請了好幾種留學國外的獎學金,徵才人員在耶魯校園出現前,我已經收到一份由耶魯大學核發、到牛津大學巴里歐學院(Balliol College)研讀政治經濟哲學的學術獎學金。這是我出國旅行的機會,也提供我延後兩年決定自己一輩子要做什麼工作的附帶好處(而且私底下,我懷抱著美妙的幻想,希望在傳奇性的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划船賽中擔任舵手)。我急於啟程,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暑期的工作。(待續)多明尼克公司(Dominick & Dominick Inc.)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未上市投資公司之一,也是大力在耶魯大學徵才的公司。這家公司具有貴族氣息、專用白人、偏愛耶魯等長春藤大學校友,也是求才企業在校園設攤徵才時,我安排好要面談的幾家公司之一。
我跟別的公司面談毫無結果,卻跟多明尼克負責求才的卡其歐帝(Joe Cacciotti)相談甚歡,他在紐約布朗克斯街頭出生、卻設法進入哈佛大學;我在阿拉巴馬州窮鄉僻壤長大、卻設法進了耶魯大學。我們有很多共同的看法,只有一個明顯的例外:多明尼克要找專職員工。
「我不能接受你們的專職工作」,我告訴他:「但是我非常樂意在暑假期間為你們效勞。」多明尼克在一八七○年創立,是紐約股票交易所早期的會員,他們每年春季在耶魯大學設攤求才,但不找暑期打工者。因此我認為是卡其歐帝的大力推薦,公司才對我破例。一九六四年夏天,我開始在華爾街工作。
那年下半年我前往牛津大學時,已經清楚知道自己這輩子要做什麼工作。
那年夏天找到自己的前途
到華爾街工作之前,我對華爾街所知道的就是它位在紐約某個地方,一九二九年曾經發生慘劇,但我不知道股票和債券有什麼不同,更不知道不同的地方是什麼。我對外匯或商品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市場上的銅價會起起伏伏。
我在多明尼克工作的第一個暑假是待在研究部門,回答經紀商打電報來問的問題,例如通用汽車公司是否會配發股息,如果配發的話,會配發多少錢?我熱心的挖掘資訊,也在交易檯旁幫忙,看著他們為沒有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股票,進行所謂的「造市」,也就是在那斯達克( NASDAQ)成立前買賣上櫃股票。我學到很多跟市場實際交易有關的知識。
我記得公司的資深合夥人問我念哪個學校,我回答是耶魯大學畢業生。他說:「那好,因為我們不希望用太多紅腹龜或老虎男孩。」他指的分別是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既然有機會見到他,我就抓住機會,問他對上商學院的意見,他說:「他們無法教你有用的東西,你到這裡放空一次黃豆,學到的會遠比在那裡浪費兩年所學還要多。」
那年夏天我過得很刺激,我用自己從沒用過的眼光觀察世界。突然間,我對歷史和時事所下的功夫不再只是理論學習,而是變成具有實際價值的努力。我急於了解世界的熱情派上了用場,因為主修歷史的關係,我發現研究市場怎麼受世界大勢影響這件事十分迷人,但是真正讓我這一輩子首次銘記在心的是:整個人類史,市場用極為可以預測的方式,左右世界大勢。
我學到每一件事情都有息息相關的道理,學到智利的革命會影響銅價,進而影響全世界的電價與房價,影響每一樣東西的價格,衝擊每一個人,包括影響西班牙托雷多(Toledo)的屋主。我也學到,如果你可以預測智利會爆發革命,就可以賺很多錢,過很好的日子。
那年夏天我找到自己的前途。在華爾街,別人真的會發錢給我,也是我發揮探索天性的地方,如果我做得不錯,他們會發給我優渥的待遇。在華爾街,我會拿錢做所有愛做的事情。這是我在多明尼克兩個暑假中的第一個,當時我立刻就知道,離開牛津大學之後不會去上法學研究所、不會上商學研究所,我會儘快回到華爾街工作。(待續)第二章 純真的留學生涯
要發財就去當農夫
我的演講讓與會的巴里歐學院學生感覺困惑,他們像我一樣深知,從我當年在牛津念書以來,全球情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改變後的情勢又變回原狀,尤其是金融勢力的崛起。
我在牛津第二年時,經濟學導師貝克曼(Wilfred Beckerman)教授對我說:「這裡沒有人像你一樣,大部分人完全不關心股市。倫敦金融區毫不重要,跟世界經濟毫無關係,跟英國經濟更沒有干係,根本沒有人關心英國股市。」
一九六○年代,巴里歐學院的大部分教授都是社會主義信徒,對於擔任政府顧問的學者來說,自由市場毫無意義。一九六四年我到牛津大學時,倫敦金融區備受忽略,最好、最聰明的巴里歐學院學生都在公家機關和學術界追求職業生涯,只有白癡才會到倫敦金融區找工作。
我的經濟學導師說的對,倫敦金融區和當時的華爾街一樣,都是一片荒涼。
二○一○年我回牛津演講時,情勢已經明顯改變,倫敦再度變成全球金融中心,事實上,還是世界上極為重要的金融中心。聽我演講的巴里歐學院學生屬於另一代的學生,都渴望在投資銀行界尋找事業生涯,從他們的樣子來看,其中很多人一定已經在自己的宿舍經營避險基金。
他們告訴我,他們希望做我做過的事情,他們問我應該閱讀什麼東西。我說,要讀哲學、歷史。他們說,不對、不對,他們希望到倫敦金融區工作、希望發財。我回答,如果是這樣應該避開倫敦金融區,因為那裡很快就會再度變成沒落荒涼的地方。我告訴他們,金融完了,應該改念農業,我建議他們,如果希望發財應該去當農夫。
二○一三年,單是美國每年畢業的管理碩士就超過二十萬人,一九五八年,每年只有五千位而已;其他國家每年還培養幾十萬個管理碩士(一九五八年時,其他國家沒有製造半個管理碩士。)未來幾十年內,企管學位會變的毫無價值,只是浪費時間和金錢,現在金融業積欠了驚人的債務,這種情形和先前截然不同,各種新的控制、管制和稅負會使金融變得比較昂貴,政府像一九三○年代一樣,對金融業者愈來愈不滿。
所有管理碩士的精明做法應該是去拿農業和礦業學位。今天念公共關係的學生比學農的人多;念體育或運動管理的人比學礦業工程的人多。但是將來農業會變成遠比金融業報酬高的部門。很快的,證券營業員會變成開計程車的司機(比較精明的營業員會開拖拉機,以便為農民工作)農民會開著藍寶堅尼(Lamborghini)超級跑車。
﹝仍然生產汽車的藍寶堅尼起初是生產拖拉機的公司。一九四八年,藍寶堅尼(Ferruccio Lamborghini)創立拖拉機公司,利用剩餘的汽車引擎和殘存的軍用廢料,生產最早一批拖拉機,變成義大利規模較大的農業機械製造商。他在一九六三年創設藍寶堅尼汽車公司,我總是聽說,他會創立汽車公司,是因為他去找法拉利(Enzo Ferrari),希望買一輛汽車,但是法拉利先生輕蔑的說,他不希望別人看到拖拉機司機開他的名車。需要是發明之母,藍寶堅尼因此自行生產汽車。﹞
我們目前處在世界性長期商品多頭市場中,在一九七○年代的商品與農產品多頭市場中,食物價格急劇上漲,庫存大量增加,到一九八○年代,世界食物庫存增加到大約占消費量的三五%,可能是有史以來最高紀錄,食物價格最後因此崩盤。例如,砂糖價格從一九七四年的每磅六十六美分,跌倒一九八七年的每磅二美分。世界各地的農民都因此受苦受難,美國的農民也一樣,尼爾遜︵Willie Nelson︶之類的音樂家舉辦救農音樂會。以經濟的一個部門來說,農業部門當時的景象很淒慘,美國每一個未來的農民都努力爭取管理碩士學位,轉進華爾街工作,那裡是資金所在的地方,是重大事件發生的地方。
除非價格漲到種植食物有利可圖的地步,否則不會有人願意取代世界上正在老化和死亡的農民。價格一定要上漲,而且一定會上漲。近年來,世界食物消耗量超過產量,食物庫存量在一九八 年代升到極高的水準,現在卻已經降到歷史低點,大約占消費量的一四%。全世界已經(○) 面臨嚴重的糧食短缺,食物價格正在上漲,就算你滿腹怨言,如果食物價格不再大漲,我們都會碰到過去從來沒有碰過的事情:食物會變成無價之寶。(待續)目前的商品多頭市場始於一九九九年,到本書寫作時為止,已經延續了十四年,商品多頭市場像所有的多頭市場一樣,最後都會形成泡沫。大家在雞尾酒會上告訴你,他們在黃豆上賺了多少錢時,就是應該出場的時候。但是這波多頭市場還有好幾年壽命。
如果世界經濟好轉,經濟成長會刺激商品和原物料的需求,商品、原料和天然資源會有優異的表現,如果經濟沒有好轉,這些東西也會有優異的表現,因為政府的行動已經證明雖然不應該這樣做,卻會繼續印更多鈔票,印鈔票總是會導致白銀、稻米、能源和其他實質資產之類的商品價格上漲,因為投資人會設法自保,以免受到貨幣貶值之害。
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了,後文會另行探討。
二○一○年,我在巴里歐學院演講時,對台下那群決心到金融界服務的學生解釋得很清楚:身為投資人,研究哲學與歷史對我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我告訴他們:「你必須深刻了解自己,如果希望人生有什麼成就、如果希望了解真相,你就必須學會以更深入、更深遠的水準思考。」學習哲學協助我發展這些技巧,學習哲學訓練我獨立思考、協助我脫出既有框架思考。哲學教我獨立評估情勢,檢驗每一個觀念、每一個﹁事實﹂;教我放大眼界,看看少了什麼東西。今天有極多的人陷入傳統的思考方式,因為反映大家的共同見解、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用國家、文化或宗教觀念限制自己的思考過程,會比較容易,也比較安全。要用與眾不同的方式思考很難,哲學會教你如何思考,在這種過程中,還會教你如何懷疑。
如果我們從歷史中沒有學到什麼教訓,至少學到下面這一點:今天看來似乎無可置疑的東西,明天看來會大不相同,最穩定、最可以預測的社會,都會經歷重大動盪。一九一四年,中歐閃亮明珠的奧匈帝國幅員廣大,是國際財富中心,當時維也納股票交易所大約有四千個會員,四年之內,奧匈帝國完全消失。你可以隨便挑選一年,然後往後退十年或十五年,例如挑選世界普遍恢復和平、繁榮和穩定的一九二五年,想一想,一九三五年的情勢如何?一九四○年又如何?你可以從過去五十年中,挑選每個十年中的第一年,從一九六○、一九七○一直到二○○○年中挑選,在每一個十年開始之初存在的凡俗之見,在隨後的十年或十五年中都徹底破滅。
第三章 自立自強
以熱情投入工作
我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進入華爾街,事後證明,這十年是股市史上最可怕的十年。
一九七○年道瓊工業指數崩盤的程度,是一九三○年代以來最慘的一次,我在三家不同的公司當了幾年分析師,在那一年進入安諾布雷許洛德公司(Arnhold and S. Bleichroeder)服務。
這家公司歷史悠久,是由能力高強的德裔猶太人經營的投資公司﹝馮布雷許洛德(Gerson von Bleichroeder)曾經當過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銀行家。﹞一九三七年,納粹黨崛起,這家公司把業務遷移到紐約經營,我就是在他們規模不大的家族經營公司裡開始大展所長。
華爾街讓人覺得美妙和興奮的地方就是情勢總是不斷變化,你必須時時保持領先,重大行動從來沒有停頓過,就像成交量與時間結合的四度空間謎團。每天上工都會發現有人在你之前移動了棋子:有人去世、發生暴動或戰爭、氣候狀況改變,無論如何,就是情勢不斷變化。
投資行為缺少其他行為的韻律,因此始終不斷的考驗你。如果你設計一款汽車,生產和銷售的時間是可以預測的,市場不是接受就是拒絕,整個計畫有一段生命週期。但投資沒有一樣東西會靜止不動,這點使投資變成持續不斷的挑戰… …你可以隨心所欲的把投資稱為一種遊戲、一種戰鬥… …
我熱愛投資過程的每一分鐘,覺得如魚得水。我全天候工作,有時候一週工作七天。
我熱愛股市,甚至偶爾希望股市週末不休市。還記得自己在一週之內,到十個城市去拜
訪十家公司,卻從不覺得花太多時間做這種事。(待續)在華爾街要努力工作是既定的事實,但是能成功的人卻很少,很多人在多頭市場時賺了很多錢,但是在正常狀況要賺很多錢比較難,要在空頭市場賺錢更難,大部分人因此都退出這一行,堅持和堅忍不拔是繼續生存絕對必要的條件,但是趨勢判斷一樣重要。
要在華爾街成功,你必須特別謹慎。挑中一塊大石頭時,誰知道有什麼東西會跑出來,可能引發什麼問題?此外,你必須多疑。翻轉一塊大石頭後,你聽到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正確,都反映政府、公司或個人缺乏知識或扭曲資訊。你不能相信任何人的任何話,每一件事都必須自行研究、證明,你必須動用每一種消息來源。可能有一百個人走進會議室,同時聽到相同的資訊,但是只有三、四人走出去後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我開始在華爾街工作時,非常少人投資股票,在一九六○年代,個人、退休基金與校產基金之類的機構投資人,主要投資標的是債券(外匯和商品呢?華爾街沒有幾個人能夠正確拼對這兩個英文字。)一九六○年代末期,福特基金會發表一份報告,認為股票是適當的投資標的,股息和資本利得加在一起,使股票變成像債券一樣有吸引力。因為福特基金會信用卓著,很多投資人根據他們的報告採取行動進場,從此股市開闢了新天地。
今天的管理碩士根本無法想像,幾十年前的普通股還是不普遍的投資,但是整個情勢一直要到一九八○年代的多頭市場開始後,才出現重大變化,今天幾乎所有投資機構都把大部分的資金投入股票。一九六四年我入行時,紐約股票交易所熱絡的日子裡,一天的成交量是三百萬股。今天一筆交易量就有三百萬股,而且可能在早餐前、交易所開市前就完成交易。今天,每星期的成交量大約五十億股,還另加那斯達克(NASDAQ)成交約五十億股。
我從念牛津大學開始,就對國際投資興趣盎然。當時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觀察世界其他國家的情勢。一九六八年我退伍時,若是談到投資丹麥貨幣克朗之類的話題,身邊的人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年齡比我大、精明又有經驗的人都目瞪口呆,好像他們不知道丹麥在哪裡一樣,更不知道丹麥有很好的機會。當時華爾街只有兩家小公司專門從事外國投資,安諾布雷許洛德是其中一家,另一家是卡爾馬克斯(Carl Marks & Co.)。
安諾布雷許洛德找我跟公司副總裁索羅斯(George Soros)合作。索羅斯一直在找一位聰明的年輕人,而我正希望換工作,有人便介紹我們認識,我們也一拍即合。他跟我一樣擁有相同的國際觀,大我約十二歲,在匈牙利長大,到英國念書和工作直到二十五、六歲才移民美國,他擁有國際投資背景,因此我們是很好的組合。我們在安諾布雷許洛德管理雙鷹避險基金(Bleichroeder Fund),利用國內外的大好良機,卻因為業界的技術性變化,也就是新管制法規的限制,我們被迫脫離安諾布雷許洛德自行獨立經營,但該公司繼續擔任我們的主要經紀商。
我們找了一間小小的辦公室,成立量子基金(Quantum Fund),這檔基金是複雜的海外避險基金(Hedge Fund,又稱:對沖基金),專攻不受利息均一稅影響的外國投資,基金在荷屬安地列斯群島註冊。我們買進和放空世界任何地方的股票、商品、外匯和債券。我們投資別人不投資的地方、利用全球各地沒有人利用的市場。我不眠不休的工作,盡最大的力量,精通全世界資本、商品、原料和資訊的流動。
到一九七四年,全世界只剩下幾檔避險基金存活下來,不過從一開始,避險基金的檔數就不多,因為華爾街已經變成非常難以賺錢的地方,大部分避險基金都停止營業。
連少數還存活的避險基金,投資重點主要都放在美國,我們是唯一的國際型避險基金。
理論上,避險基金業者都是聰明人,但是當時沒有人投資外國,當時只有少數人能夠在地圖上指出比利時,更不用說投資比利時了。
最早的避險基金是瓊斯(Alfred Winslow Jones)在一九四九年創立的,我們開始經營自己的基金時,他的避險基金還在營業(瓊斯到今天還活著),他的基金在一九五○、六○年代經營得非常成功,我們利用的報酬結構是瓊斯想出來的,當時其他人也運用相同的結構。
事無永恆,變化永存
我家鄉戴摩波里斯(Demopolis)位居阿拉巴馬州坎布雷克(Canebrake)地區中心,正好是黑戰士河與湯比比河匯流處。
戴摩波里斯是馬倫哥郡(Marengo County)最大的城市,坐落在喬治亞、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三州歷史上號稱黑土地帶的中心。會叫做黑土地帶,是因為大地上鋪滿厚厚一層肥沃草原黑土,近兩百年前,這些黑土滋養了龐大的棉花田作物,解放黑奴之後,有些棉花田還繼續生存,但是沒有一座棉花田能夠熬過棉籽象鼻蟲的摧殘。
我還是小男孩時,每次要跟朋友出門釣魚,就是在這塊土地上挖掘魚餌。美洲鯰魚無所不吃,不只吃蚯蚓,牠會咬住任何聞到的東西,而且不論什麼東西的味道幾乎都聞得到。在炎熱的夏天,挖蚯蚓比抓蟋蟀還容易,那一年我八歲,和大我約十個月的堂哥韋德在我家後院挖蚯蚓,當時他說了一句我當時聽不懂、但直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的話。
他說:「如果我們繼續挖下去,最後會挖到中國。」當時我已經是個熱愛研究的人,不會不知道地球是圓的,但是我查看地球儀後才了解,和阿拉巴馬州方向相反的地球另一邊,橫亙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龐大的陸塊,如果我們有足夠的精力繼續挖掘,一定會滿身汙泥、全身濕透的鑽出中國地面。
幾十年過去了,今天我終於定居在中國的大門口,兩位金髮碧眼小美女女兒的普通話,說得比英語還流利。我怎麼變成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是跟挖掘有關的另一個故事,這樣的挖掘可能沒有這麼辛苦,卻同樣費力;是我無盡無止、親身深入體驗世界運作、發掘真實故事,完全靠自己探索的結果。
我花五年時間環遊世界兩次,一次是騎機車,另一次是駕駛汽車,讓我了解一百多個國家的變化。對我來說,不是坐在安樂椅上了解歷史和歷史的影響,而是要親自探險。這樣做帶給我個人與物質極大的報酬,而且無可避免的引導我來到新加坡:一個遠離窮鄉僻壤阿拉巴馬州、馬來半島南端華人前哨站的國度。
如果歷史能夠確定什麼事情的話,一定是希臘人所說「事無永恆、變化永存」,最早說這句話的人是西元前六世紀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斯( Heraclitus),他警告我們,一個人不可能踏進同樣的河水兩次。預測變化的能力是評估人生成就的標準,我搬到新加坡,是為了因應世界處於歷史性變化、世界大勢急劇改變、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沒落、亞洲相應崛起的認知。
我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寫這本書,世界各國大部分政客都希望你相信這場危機為時短暫,告訴你情勢一定會轉變。我不會質疑這一點,只是要告訴你,在你有生之年,情勢不太可能永遠轉變。很多國家積欠的驚人債務會導致人類生活與工作方式的重大改變,很多舊的制度、傳統、政黨、政府、文化,甚至國家都會沒落、崩潰或是完全消失,就像政經重大動盪時代總是會發生的情形一樣。
例如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在二○○八年崩潰時已經經營幾十年了,同年倒閉的金融服務業者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營業已經超過一個半世紀。這些歷史悠久的全球企業不支倒地,證明美國很多制度正面臨情勢變化,哈佛、普林斯頓,和史丹佛等大學或許並不自知,卻可能正走向破產之途。博物館、醫院和我們知道與深愛的其他機構正走向困境,我們會在未來的金融或經濟巨變中,看到很多這種機構消失。
有些人說我危言聳聽,說我是現代專門預測凶事的烏鴉嘴卡珊德拉(Cassandra)。但是我在未來的情勢中,看不到半點值得驚慌、甚至值得驚異的地方。改變的大風已經吹起,從中國的方向吹來,而且是以可預測的方式吹來。我們所看到的情形一切如常,歷史正在翻轉熟悉的一頁。
在整個人類史上,這種轉型時刻都會為有心人提供大好良機,因此我對未來的很多事情極為樂觀。如果你在十九世紀開始之時夠精明,會前往倫敦;如果你在二十世紀開始之時很精明,會打包搬到紐約;如果你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時很精明,會前進亞洲。
一百年後,變化的循環可能轉到任何地方—第一個千禧年結束時,所有的聰明人都搬到科多華(Cordoba),伊斯蘭教統治西班牙期間的繁華都會、當時歐洲的知識中心以及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待續)二○○七年我搬到亞洲,更重要的是,我把小孩也帶來這裡。在她們有生之年,通曉亞洲是創造成就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各國,精通中文會變成像今天精通英文一樣重要。一九二○,三○年代,世界權力和影響力從英國移轉到美國,金融危機和施政不當導致英國加速喪失領導地位,很多人要到二、三十年後,才注意到這一點。現在世界權力和影響力正由美國移轉到亞洲,同樣的力量讓美國加速失去領導地位。
轉向亞洲的風潮在第二次歷史性大變動的時刻出現,在金融海嘯嚴重期間,世界面臨擺脫金融的情勢,也面臨擺脫金融業者作為繁榮來源的循環性變化。整個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期間由金融家負責主導,也有很多期間由實質財貨的生產者,包括農民、礦工、能源供應業者、伐木工人負責主導。二十世紀的五○、六○和七○年代,在大多頭市場開始前,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區是默默無聞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會再度打回原形,搬運資金的專家正在沒落,聖經舊約《約書亞記》中所說「劈柴挑水的人」即將繼承這個世界。
省思造成變化的歷史力量、擁抱事無恒常的簡單假設之際,我不由得欣賞西方文明另一位偉大思想家愛因斯坦的說法:「只有兩件事情無窮無盡,就是宇宙和人類的愚蠢,而且我對前者是否無窮無盡,還不是這麼肯定。」
我們別忘了特洛伊城的公主卡珊德拉,她警告大家,不要把希臘人留下的木馬拖進城裡時,其實是自找麻煩,要是我們記不得這件事的其他特點,我們應該會記得她的預言正確無誤。
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大家了解,我們怎麼會走到今天這種地步,個人要怎麼自我教育,以便為未來做準備。我會跟你分享我一輩子從事金融、投資與冒險之旅所得到的見解,跟你分享我成長之際所學到的教訓,說明我從黑土地帶的泥土出發,走到地球另一邊這個東南亞城市國家的終生之旅中,怎麼把整個世界當成我家後院的經驗。
凡事沒有「夠了」這回事
我的市場探險之旅始於一九六四年春季,當時我是耶魯大學四年級學生,我發現自己非常像幾年前前進長春籐盟校一樣,跌跌撞撞的闖進華爾街。
我念高中時,熱心參加同濟會俱樂部(Key Club)的會務,同濟會俱樂部是由學生領導的服務組織,隸屬到一九七六年還只限制男性參加的國際同濟會(Kiwanis International)。
戴摩波里斯同濟會俱樂部會員資格是了不得的大事,因為本地的支持者決定一年只允許五位少年入會。我擔任會長那一年,戴摩波里斯同濟會俱樂部贏得世界小城鎮最優秀同濟會俱樂部的殊榮。當時耶魯大學每年發給一位國際同濟會俱樂部會員四年的獎學金,也因為這項獎學金我才認識耶魯大學,如果不是同濟會俱樂部的關係,我根本不會申請耶魯大學的入學資格。
除了耶魯大學,我滿心希望就讀也是唯一申請的是田納西州西瓦尼(Sewanee)的南方大學,這所大學跟美國新教聖公會關係密切,是一所文科大學。我寄出申請書後不久,就接到西瓦尼方面寄來的同意書。一直到四月或五月,家父寄給西瓦尼要求的五十美元接受費之後相當久,我才收到耶魯大學寄來的厚厚信封,通知我耶魯大學已經接受我這個學生,而且發給我一年兩千美元的同濟會俱樂部獎學金。
我嚇壞了。
我才十七歲,對耶魯大學一無所知,只知道這所大學設在康乃逖克州的紐海文(New Haven)。然而,家父、家母經驗豐富,知道耶魯大學接受我這個學生的重大意義。他倆都是大學畢業生,在奧克拉荷馬州大學認識,兩人當時都是優等生。家父主修石油工程,家母主修文科。對他們來說,我上耶魯大學是相當非同小可。我記得家父說過:「我們有點擔心送你到北部這座自由主義堡壘。」但事實上,他和家母都樂不可支。家父的欣喜後來略為降低,因為他無法索回寄到西瓦尼的五十美元。在一九六○年的戴摩波里斯,五十美元是一筆大錢,今天仍然是一筆大錢,但是當時五十美元的價值大約是今天的七倍之多。
我是家中五兄弟的老大,也是高中畢業班不到五十位畢業生的其中一位,於是我對所有人表露出因幸運而產生的過度自傲,就像本地人所說的,裝出大狗的樣子,但是自我膨脹的意識注定很短命。我慢慢的明白:唉,唉,我現在得去上耶魯了。我突然覺得很害怕,因為整個情勢遠遠超出自己的理解範圍。我不禁問道:我現在要做什麼?(待續)那年夏天,我搭火車到波士頓參加同濟會俱樂部大會,在紐海文下車後前往耶魯大學的招生辦公室,我希望知道他們為什麼接受我這個學生,希望問這個問題後,自己可以知道將來會是什麼樣子,也能了解他們對我有什麼期望。招生主任抽出我的卷宗說:「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你看,你以全校第一名成績畢業,很多科都得到一百分,平均成績接近一百。」
我心想:對,但那是在戴摩波里斯,唉,天啊,這些傢伙認為我很聰明,認為我懂得不少東西。
我就在覺得全無準備、無法跟美國東北部著名預校學生競爭的情況下,來到耶魯,但我抱著比別人更認真的決心,準備努力用功。記得有次老師要考試,一位同班同學說他要花五小時準備:「這次考試值得花五小時準備。」我發現他的想法很奇怪,我的方法是儘量努力用功,直到了解這一科目為止,然後再多用功一番,確保萬無一失。這是我處理所有事情的方法,是胞弟和我從父母身上學到的紀律:「凡事沒有『夠了』這回事」,不管任務是什麼,你就是要不斷用功、不斷努力,或不斷的研究。
當時上耶魯所需的學費和食宿費一共兩千三百美元,我有兩千美元獎學金,所以一開始就少了三百美元,而且還沒有算書籍費和其他固定開支,於是每星期我到學校餐廳打工幾小時,上大學期間也兼做校園裡的差事。
青年期工作經驗帶來的好處,是可以計算的。除了能學習金錢價值,也能幫助自己培養認同;學習財務管理時,你會獲得明確的自主性。我從小就開始自力更生,六歲時家父教我﹁錢不是長在樹上﹂的道理,堅持要我自己出錢買棒球手套,於是我到五金行挑了標價四美元的手套,然後每星期六付給老闆布拉斯威爾(Cruse Braswell)十五美分,一直到付完全部金額。多年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引用某大學的研究告訴我,要預測成年之後生活是否幸福,最重要的單一指標是青少年時期做過有報酬的工作。
總之,我的耶魯生活過得很愉快。我主修歷史,還以舵手的身分參加划船賽,大二、大三當選校隊選手,四年級時沒有擔任舵手。我甚至涉入演藝事業,得到幾次重要的戲份,其中一部電影由一九六一年從耶魯畢業的貝德漢(John Badham)導演。你可以想像,要是他的《周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用我當主角,這部電影應該會更紅!雖然我十分喜愛演藝事業,卻沒有過度深入,原因跟我大四時不當舵手一樣。我把時間花在學業上,這樣的紀律也得到回報,我沒有比別人聰明,卻能夠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但我像很多大學畢業生一樣,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
哈佛商學院、法學院和耶魯法學院都接受我的入學申請,但是我也申請進入醫學院,因為希望得到更多選擇的興奮之情。然而我真正的希望是到處旅行,我從小就愛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的《匹克威克遊記》(The 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俱樂部的紳士和他們的漫遊冒險,在我漫遊欲望的發展中,可能扮演了某種角色。雖然我才二十一歲,卻對自己有足夠的了解,知道光是離開家園就是我教育當中重要的一環;我的情況是,離開阿拉巴馬州的農村,到一千六百公里外去上康乃逖克州的長春藤大學。
這段經驗讓我大開眼界,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就像吉卜齡(Rudyard Kipling)在《英國國旗》(The English Flag)這首詩中所寫:「只了解英國的人,又能對英國了解多少呢?」
置身在很多耶魯學生當中,總是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已經到外國旅行過。我總是一心一意想要多了解、多看看這個世界。
我因為急於擴大眼界,申請了好幾種留學國外的獎學金,徵才人員在耶魯校園出現前,我已經收到一份由耶魯大學核發、到牛津大學巴里歐學院(Balliol College)研讀政治經濟哲學的學術獎學金。這是我出國旅行的機會,也提供我延後兩年決定自己一輩子要做什麼工作的附帶好處(而且私底下,我懷抱著美妙的幻想,希望在傳奇性的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划船賽中擔任舵手)。我急於啟程,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暑期的工作。(待續)多明尼克公司(Dominick & Dominick Inc.)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未上市投資公司之一,也是大力在耶魯大學徵才的公司。這家公司具有貴族氣息、專用白人、偏愛耶魯等長春藤大學校友,也是求才企業在校園設攤徵才時,我安排好要面談的幾家公司之一。
我跟別的公司面談毫無結果,卻跟多明尼克負責求才的卡其歐帝(Joe Cacciotti)相談甚歡,他在紐約布朗克斯街頭出生、卻設法進入哈佛大學;我在阿拉巴馬州窮鄉僻壤長大、卻設法進了耶魯大學。我們有很多共同的看法,只有一個明顯的例外:多明尼克要找專職員工。
「我不能接受你們的專職工作」,我告訴他:「但是我非常樂意在暑假期間為你們效勞。」多明尼克在一八七○年創立,是紐約股票交易所早期的會員,他們每年春季在耶魯大學設攤求才,但不找暑期打工者。因此我認為是卡其歐帝的大力推薦,公司才對我破例。一九六四年夏天,我開始在華爾街工作。
那年下半年我前往牛津大學時,已經清楚知道自己這輩子要做什麼工作。
那年夏天找到自己的前途
到華爾街工作之前,我對華爾街所知道的就是它位在紐約某個地方,一九二九年曾經發生慘劇,但我不知道股票和債券有什麼不同,更不知道不同的地方是什麼。我對外匯或商品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市場上的銅價會起起伏伏。
我在多明尼克工作的第一個暑假是待在研究部門,回答經紀商打電報來問的問題,例如通用汽車公司是否會配發股息,如果配發的話,會配發多少錢?我熱心的挖掘資訊,也在交易檯旁幫忙,看著他們為沒有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股票,進行所謂的「造市」,也就是在那斯達克( NASDAQ)成立前買賣上櫃股票。我學到很多跟市場實際交易有關的知識。
我記得公司的資深合夥人問我念哪個學校,我回答是耶魯大學畢業生。他說:「那好,因為我們不希望用太多紅腹龜或老虎男孩。」他指的分別是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既然有機會見到他,我就抓住機會,問他對上商學院的意見,他說:「他們無法教你有用的東西,你到這裡放空一次黃豆,學到的會遠比在那裡浪費兩年所學還要多。」
那年夏天我過得很刺激,我用自己從沒用過的眼光觀察世界。突然間,我對歷史和時事所下的功夫不再只是理論學習,而是變成具有實際價值的努力。我急於了解世界的熱情派上了用場,因為主修歷史的關係,我發現研究市場怎麼受世界大勢影響這件事十分迷人,但是真正讓我這一輩子首次銘記在心的是:整個人類史,市場用極為可以預測的方式,左右世界大勢。
我學到每一件事情都有息息相關的道理,學到智利的革命會影響銅價,進而影響全世界的電價與房價,影響每一樣東西的價格,衝擊每一個人,包括影響西班牙托雷多(Toledo)的屋主。我也學到,如果你可以預測智利會爆發革命,就可以賺很多錢,過很好的日子。
那年夏天我找到自己的前途。在華爾街,別人真的會發錢給我,也是我發揮探索天性的地方,如果我做得不錯,他們會發給我優渥的待遇。在華爾街,我會拿錢做所有愛做的事情。這是我在多明尼克兩個暑假中的第一個,當時我立刻就知道,離開牛津大學之後不會去上法學研究所、不會上商學研究所,我會儘快回到華爾街工作。(待續)第二章 純真的留學生涯
要發財就去當農夫
我的演講讓與會的巴里歐學院學生感覺困惑,他們像我一樣深知,從我當年在牛津念書以來,全球情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改變後的情勢又變回原狀,尤其是金融勢力的崛起。
我在牛津第二年時,經濟學導師貝克曼(Wilfred Beckerman)教授對我說:「這裡沒有人像你一樣,大部分人完全不關心股市。倫敦金融區毫不重要,跟世界經濟毫無關係,跟英國經濟更沒有干係,根本沒有人關心英國股市。」
一九六○年代,巴里歐學院的大部分教授都是社會主義信徒,對於擔任政府顧問的學者來說,自由市場毫無意義。一九六四年我到牛津大學時,倫敦金融區備受忽略,最好、最聰明的巴里歐學院學生都在公家機關和學術界追求職業生涯,只有白癡才會到倫敦金融區找工作。
我的經濟學導師說的對,倫敦金融區和當時的華爾街一樣,都是一片荒涼。
二○一○年我回牛津演講時,情勢已經明顯改變,倫敦再度變成全球金融中心,事實上,還是世界上極為重要的金融中心。聽我演講的巴里歐學院學生屬於另一代的學生,都渴望在投資銀行界尋找事業生涯,從他們的樣子來看,其中很多人一定已經在自己的宿舍經營避險基金。
他們告訴我,他們希望做我做過的事情,他們問我應該閱讀什麼東西。我說,要讀哲學、歷史。他們說,不對、不對,他們希望到倫敦金融區工作、希望發財。我回答,如果是這樣應該避開倫敦金融區,因為那裡很快就會再度變成沒落荒涼的地方。我告訴他們,金融完了,應該改念農業,我建議他們,如果希望發財應該去當農夫。
二○一三年,單是美國每年畢業的管理碩士就超過二十萬人,一九五八年,每年只有五千位而已;其他國家每年還培養幾十萬個管理碩士(一九五八年時,其他國家沒有製造半個管理碩士。)未來幾十年內,企管學位會變的毫無價值,只是浪費時間和金錢,現在金融業積欠了驚人的債務,這種情形和先前截然不同,各種新的控制、管制和稅負會使金融變得比較昂貴,政府像一九三○年代一樣,對金融業者愈來愈不滿。
所有管理碩士的精明做法應該是去拿農業和礦業學位。今天念公共關係的學生比學農的人多;念體育或運動管理的人比學礦業工程的人多。但是將來農業會變成遠比金融業報酬高的部門。很快的,證券營業員會變成開計程車的司機(比較精明的營業員會開拖拉機,以便為農民工作)農民會開著藍寶堅尼(Lamborghini)超級跑車。
﹝仍然生產汽車的藍寶堅尼起初是生產拖拉機的公司。一九四八年,藍寶堅尼(Ferruccio Lamborghini)創立拖拉機公司,利用剩餘的汽車引擎和殘存的軍用廢料,生產最早一批拖拉機,變成義大利規模較大的農業機械製造商。他在一九六三年創設藍寶堅尼汽車公司,我總是聽說,他會創立汽車公司,是因為他去找法拉利(Enzo Ferrari),希望買一輛汽車,但是法拉利先生輕蔑的說,他不希望別人看到拖拉機司機開他的名車。需要是發明之母,藍寶堅尼因此自行生產汽車。﹞
我們目前處在世界性長期商品多頭市場中,在一九七○年代的商品與農產品多頭市場中,食物價格急劇上漲,庫存大量增加,到一九八○年代,世界食物庫存增加到大約占消費量的三五%,可能是有史以來最高紀錄,食物價格最後因此崩盤。例如,砂糖價格從一九七四年的每磅六十六美分,跌倒一九八七年的每磅二美分。世界各地的農民都因此受苦受難,美國的農民也一樣,尼爾遜︵Willie Nelson︶之類的音樂家舉辦救農音樂會。以經濟的一個部門來說,農業部門當時的景象很淒慘,美國每一個未來的農民都努力爭取管理碩士學位,轉進華爾街工作,那裡是資金所在的地方,是重大事件發生的地方。
除非價格漲到種植食物有利可圖的地步,否則不會有人願意取代世界上正在老化和死亡的農民。價格一定要上漲,而且一定會上漲。近年來,世界食物消耗量超過產量,食物庫存量在一九八 年代升到極高的水準,現在卻已經降到歷史低點,大約占消費量的一四%。全世界已經(○) 面臨嚴重的糧食短缺,食物價格正在上漲,就算你滿腹怨言,如果食物價格不再大漲,我們都會碰到過去從來沒有碰過的事情:食物會變成無價之寶。(待續)目前的商品多頭市場始於一九九九年,到本書寫作時為止,已經延續了十四年,商品多頭市場像所有的多頭市場一樣,最後都會形成泡沫。大家在雞尾酒會上告訴你,他們在黃豆上賺了多少錢時,就是應該出場的時候。但是這波多頭市場還有好幾年壽命。
如果世界經濟好轉,經濟成長會刺激商品和原物料的需求,商品、原料和天然資源會有優異的表現,如果經濟沒有好轉,這些東西也會有優異的表現,因為政府的行動已經證明雖然不應該這樣做,卻會繼續印更多鈔票,印鈔票總是會導致白銀、稻米、能源和其他實質資產之類的商品價格上漲,因為投資人會設法自保,以免受到貨幣貶值之害。
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了,後文會另行探討。
二○一○年,我在巴里歐學院演講時,對台下那群決心到金融界服務的學生解釋得很清楚:身為投資人,研究哲學與歷史對我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我告訴他們:「你必須深刻了解自己,如果希望人生有什麼成就、如果希望了解真相,你就必須學會以更深入、更深遠的水準思考。」學習哲學協助我發展這些技巧,學習哲學訓練我獨立思考、協助我脫出既有框架思考。哲學教我獨立評估情勢,檢驗每一個觀念、每一個﹁事實﹂;教我放大眼界,看看少了什麼東西。今天有極多的人陷入傳統的思考方式,因為反映大家的共同見解、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用國家、文化或宗教觀念限制自己的思考過程,會比較容易,也比較安全。要用與眾不同的方式思考很難,哲學會教你如何思考,在這種過程中,還會教你如何懷疑。
如果我們從歷史中沒有學到什麼教訓,至少學到下面這一點:今天看來似乎無可置疑的東西,明天看來會大不相同,最穩定、最可以預測的社會,都會經歷重大動盪。一九一四年,中歐閃亮明珠的奧匈帝國幅員廣大,是國際財富中心,當時維也納股票交易所大約有四千個會員,四年之內,奧匈帝國完全消失。你可以隨便挑選一年,然後往後退十年或十五年,例如挑選世界普遍恢復和平、繁榮和穩定的一九二五年,想一想,一九三五年的情勢如何?一九四○年又如何?你可以從過去五十年中,挑選每個十年中的第一年,從一九六○、一九七○一直到二○○○年中挑選,在每一個十年開始之初存在的凡俗之見,在隨後的十年或十五年中都徹底破滅。
第三章 自立自強
以熱情投入工作
我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進入華爾街,事後證明,這十年是股市史上最可怕的十年。
一九七○年道瓊工業指數崩盤的程度,是一九三○年代以來最慘的一次,我在三家不同的公司當了幾年分析師,在那一年進入安諾布雷許洛德公司(Arnhold and S. Bleichroeder)服務。
這家公司歷史悠久,是由能力高強的德裔猶太人經營的投資公司﹝馮布雷許洛德(Gerson von Bleichroeder)曾經當過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銀行家。﹞一九三七年,納粹黨崛起,這家公司把業務遷移到紐約經營,我就是在他們規模不大的家族經營公司裡開始大展所長。
華爾街讓人覺得美妙和興奮的地方就是情勢總是不斷變化,你必須時時保持領先,重大行動從來沒有停頓過,就像成交量與時間結合的四度空間謎團。每天上工都會發現有人在你之前移動了棋子:有人去世、發生暴動或戰爭、氣候狀況改變,無論如何,就是情勢不斷變化。
投資行為缺少其他行為的韻律,因此始終不斷的考驗你。如果你設計一款汽車,生產和銷售的時間是可以預測的,市場不是接受就是拒絕,整個計畫有一段生命週期。但投資沒有一樣東西會靜止不動,這點使投資變成持續不斷的挑戰… …你可以隨心所欲的把投資稱為一種遊戲、一種戰鬥… …
我熱愛投資過程的每一分鐘,覺得如魚得水。我全天候工作,有時候一週工作七天。
我熱愛股市,甚至偶爾希望股市週末不休市。還記得自己在一週之內,到十個城市去拜
訪十家公司,卻從不覺得花太多時間做這種事。(待續)在華爾街要努力工作是既定的事實,但是能成功的人卻很少,很多人在多頭市場時賺了很多錢,但是在正常狀況要賺很多錢比較難,要在空頭市場賺錢更難,大部分人因此都退出這一行,堅持和堅忍不拔是繼續生存絕對必要的條件,但是趨勢判斷一樣重要。
要在華爾街成功,你必須特別謹慎。挑中一塊大石頭時,誰知道有什麼東西會跑出來,可能引發什麼問題?此外,你必須多疑。翻轉一塊大石頭後,你聽到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正確,都反映政府、公司或個人缺乏知識或扭曲資訊。你不能相信任何人的任何話,每一件事都必須自行研究、證明,你必須動用每一種消息來源。可能有一百個人走進會議室,同時聽到相同的資訊,但是只有三、四人走出去後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我開始在華爾街工作時,非常少人投資股票,在一九六○年代,個人、退休基金與校產基金之類的機構投資人,主要投資標的是債券(外匯和商品呢?華爾街沒有幾個人能夠正確拼對這兩個英文字。)一九六○年代末期,福特基金會發表一份報告,認為股票是適當的投資標的,股息和資本利得加在一起,使股票變成像債券一樣有吸引力。因為福特基金會信用卓著,很多投資人根據他們的報告採取行動進場,從此股市開闢了新天地。
今天的管理碩士根本無法想像,幾十年前的普通股還是不普遍的投資,但是整個情勢一直要到一九八○年代的多頭市場開始後,才出現重大變化,今天幾乎所有投資機構都把大部分的資金投入股票。一九六四年我入行時,紐約股票交易所熱絡的日子裡,一天的成交量是三百萬股。今天一筆交易量就有三百萬股,而且可能在早餐前、交易所開市前就完成交易。今天,每星期的成交量大約五十億股,還另加那斯達克(NASDAQ)成交約五十億股。
我從念牛津大學開始,就對國際投資興趣盎然。當時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觀察世界其他國家的情勢。一九六八年我退伍時,若是談到投資丹麥貨幣克朗之類的話題,身邊的人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年齡比我大、精明又有經驗的人都目瞪口呆,好像他們不知道丹麥在哪裡一樣,更不知道丹麥有很好的機會。當時華爾街只有兩家小公司專門從事外國投資,安諾布雷許洛德是其中一家,另一家是卡爾馬克斯(Carl Marks & Co.)。
安諾布雷許洛德找我跟公司副總裁索羅斯(George Soros)合作。索羅斯一直在找一位聰明的年輕人,而我正希望換工作,有人便介紹我們認識,我們也一拍即合。他跟我一樣擁有相同的國際觀,大我約十二歲,在匈牙利長大,到英國念書和工作直到二十五、六歲才移民美國,他擁有國際投資背景,因此我們是很好的組合。我們在安諾布雷許洛德管理雙鷹避險基金(Bleichroeder Fund),利用國內外的大好良機,卻因為業界的技術性變化,也就是新管制法規的限制,我們被迫脫離安諾布雷許洛德自行獨立經營,但該公司繼續擔任我們的主要經紀商。
我們找了一間小小的辦公室,成立量子基金(Quantum Fund),這檔基金是複雜的海外避險基金(Hedge Fund,又稱:對沖基金),專攻不受利息均一稅影響的外國投資,基金在荷屬安地列斯群島註冊。我們買進和放空世界任何地方的股票、商品、外匯和債券。我們投資別人不投資的地方、利用全球各地沒有人利用的市場。我不眠不休的工作,盡最大的力量,精通全世界資本、商品、原料和資訊的流動。
到一九七四年,全世界只剩下幾檔避險基金存活下來,不過從一開始,避險基金的檔數就不多,因為華爾街已經變成非常難以賺錢的地方,大部分避險基金都停止營業。
連少數還存活的避險基金,投資重點主要都放在美國,我們是唯一的國際型避險基金。
理論上,避險基金業者都是聰明人,但是當時沒有人投資外國,當時只有少數人能夠在地圖上指出比利時,更不用說投資比利時了。
最早的避險基金是瓊斯(Alfred Winslow Jones)在一九四九年創立的,我們開始經營自己的基金時,他的避險基金還在營業(瓊斯到今天還活著),他的基金在一九五○、六○年代經營得非常成功,我們利用的報酬結構是瓊斯想出來的,當時其他人也運用相同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