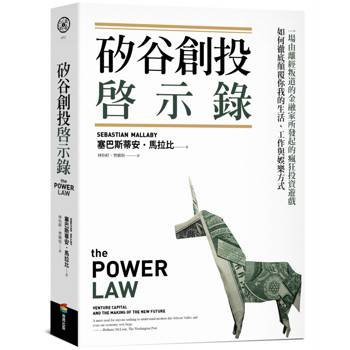給Google的資金,沒有交換條件
1998年8月某天,兩位史丹佛大學博士生坐在帕羅奧圖某處的門廊上。他們正為開發瀏覽網路的新方式籌措資金,就像3年前的雅虎一樣。不過當時雅虎創辦人向紅杉資本募得100萬元,交出公司三分之一股權,而接下來的發展則非常不一樣。
這兩位博士生分別是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賴利.佩吉(Larry Page),他們初露頭角的公司叫做Google。表面上,他們的創業前途黯淡,市面上已經有其他17間提供網路搜尋服務的公司。不過自信滿滿的布林和佩吉相信他們的技術能壓倒對手,因此他們在門廊上等待一位著名的矽谷工程師安迪.貝托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
不久之後,貝托斯海姆駕著一輛銀色保時捷抵達,他本人風度翩翩,頭髮蓬鬆飄逸,講話帶著微微的德國口音。布林和佩吉向他示範搜尋引擎後,貝托斯海姆越發感興趣。Google系統會查詢有多少其他網站連結到某一網站,據此為網站進行排序,因此顯示的搜尋結果相關程度比對手更高。貝托斯海姆立刻發現其系統借用學術界的機制:引用次數是判斷論文聲望的標準。
貝托斯海姆不是創業投資人,不過他成立2間公司,手邊有資金可以運用。1982年,他共同創立昇陽電腦,大獲成功。之後又創立網路公司Granite Systems,貝托斯海姆是該公司的主要股東,後來公司以2.2億元出售給思科。貝托斯海姆喜歡運用自己的財富來資助工程師同行,隨處花個幾十萬對他的銀行餘額沒什麼影響。
1980年代後期,網路發展初期的創業家約翰.利朵(John Little)經過貝托斯海姆的辦公室。利朵也是電腦科學家,兩人是在昇陽電腦的啤酒派對上認識的。
貝托斯海姆問道:「近來如何?」
利朵回答不太好,他的新創公司共同創辦人打算辭職,而買下他的股份需要一筆錢。利朵沒有這筆錢。
你需要多少?貝托斯海姆問道。
利朵表示:「我不知道,大概9萬吧。」
貝托斯海姆拿出支票簿,開了一張9萬元的支票給他。動作之迅速,利朵根本還沒意會到他在做什麼。利朵事後表示:「他拿出支票簿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要幹嘛。我從來沒看過有人就這麼掏出錢來,沒有交換條件。」貝托斯海姆沒有表示他希望用這筆錢買進利朵公司的多少股份,利朵回憶道:「安迪不太在意這些。那之後,大概1年1次吧,我們可能在烤肉會上碰到彼此,就會向對方提到要把那筆投資白紙黑字寫下來,可是我們都很忙。」
最後,到了1996年,利朵向專業的創業投資人(Accel的亞瑟.派特森)募得將近600萬元,這時必須明確把誰擁有多少股份記錄下來了,貝托斯海姆衝動的慷慨之舉換得利朵公司的1%股份。在網路欣欣向榮的那段時期,利朵的公司Portal Software業績驚人,因此貝托斯海姆9萬元支票的報酬大概比他共同創立昇陽電腦的獲利還要高。
現在,貝托斯海姆坐在帕羅奧圖一處門廊上與Google創辦人閒聊,他準備故技重施。他看得出Google創辦人沒有商業企劃書,他們堅定拒絕採用橫幅廣告或彈出式廣告這兩種網站營利的標準作法。不過看到布林和佩吉示範他們的搜尋引擎,貝托斯海姆明白他們具有軟體優勢;此外,他也對這兩位年輕人頗有好感。他們充滿好奇心、擇善固執、性情平和,和他自己在史丹佛大學研讀電腦科學時沒什麼不同。
貝托斯海姆跑回他的保時捷車上拿東西,他興高采烈地表示:「我們還可以討論幾個問題,我先開張支票給你們。」,接著交給布林和佩吉一張10萬元的支票,抬頭是「Google公司」。
布林和佩吉表示他們還沒成立公司,沒有可以存入支票的銀行帳戶。
貝托斯海姆輕快地表示:「那等你們成立公司,就存進去吧。」接著就開著保時捷揚長而去,沒有指明他希望用這筆錢購入Google多少股份。他事後表示:「我興奮極了,只想著不能錯過。」
--------------------------
貝托斯海姆的隨興投資標誌著新型態技術投資的出現,重要性堪比2年前孫正義開出的1億元支票。1990年代中期以前,半退休的科技業主管偶爾也會從事投資。舉例來說,麥克.馬庫拉資助並輔導剛起步的蘋果公司;米奇.卡普爾為GO和UUNET提供資金與建議。不過要到1990年代中後段、科技市場的繁榮時期,這種「天使投資」才真正開始成為一股勢力。多虧初次公開發行帶來的財富,矽谷的百萬富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天使投資成為這個菁英族群的新消遣,就像醫美手術在好萊塢一樣的稀鬆平常。1998年,貝托斯海姆資助Google的同一年,活躍的天使投資人朗恩.康威(Ron Conway)甚至籌募3,000萬元的基金來強化個人投資,而「機構天使」或「超級天使」成為矽谷新創公司引擎的最新汽缸。一夕之間,創辦者有了傳統創業投資人之外的新選擇,就像孫正義所的成長資金提供了公開上市之外的選項。進行第一輪募資時,創業家只需要認識幾位成功前輩就行了。貝托斯海姆獨特的投資風格後來幾乎變成常態。
布林和佩吉尤其善用這種新模式。一開始,他們找上印度裔科技主管蘭姆.西里蘭(Ram Shriram),西里蘭後來靠著將自己的新創公司出售給亞馬遜而發跡。起初,西里蘭幫忙介紹幾間可能有意收購Google技術的大型搜尋公司,不過後來沒有出現像樣的合作案,因此西里蘭提議資助這兩位博士生,前提是他們能找到其他天使投資人合資。布林和佩吉很快就成功拉攏貝托斯海姆及其Granite Systems的共同創辦人,還有一位史丹佛大學教授大衛.薛瑞頓(David Cheriton)。幾個月後,亞馬遜創辦人傑夫.貝佐斯造訪灣區露營度假,在西里蘭家遇到布林和佩吉兩人。貝佐斯也想要入股,他後來表示:「我愛上賴利和謝爾蓋的才華。」
至1998年底,布林和佩吉已向4位天使投資人募得100萬元,比雅虎自紅杉資本募到的資金還多。不過他們沒有與任何一位創業投資人交涉,交出的公司股權更不到十分之一,也不必同意創業投資人訂定的績效目標和監管。貝佐斯和貝托斯海姆等天使投資人全心專注於自己的公司,無暇對布林和佩吉指手畫腳。於是,一如約翰.利朵所說,Google創辦人得以「就這麼募到錢,沒有交換條件」。自由資本的舊有觀念邁入全新層次,人類歷史中,年輕發明家從未如此備受禮遇。
雖然Google創辦人避免與創業投資人交涉,不過當時正是創投產業欣欣向榮的時期。1998年,創業投資人籌措的資金達到創紀錄的300億元,與孫正義投資雅虎的1995年相比翻了3倍。1999年成長更為猛烈:創投合夥公司握有560億元資金;美國的創投合夥企業數量達750間(10年前大約只有400間)。矽谷似乎瀰漫著創造財富所激發的腎上腺素,至少對創業投資人來說是如此。
這樣的蓬勃發展令傳統創業投資人稍感不安。一位老前輩回憶道:「顯然我們身處泡沫之中。我們認知中打造基本價值的措施都遭到懲罰,而偏差行為卻獲得獎賞。」雅虎所帶動的趨勢(先行者因氣勢壯盛而獲得資金)顯然衝過了頭:在許多案例中,創造氣勢的是資金本身,眾多網路公司根本賺不到利潤。不論市場上揚的態勢有多瘋狂,創投前輩也無力抵制。不像避險基金,即便預期泡沫化也能運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或其他機制來獲利,創業投資人想要賺錢就只能打賭價值不斷上升。他們的業務很單純,那就是購買新創公司的股權,而且除了付出水漲船高的價格外別無他法。除了獲利機制以外,避險基金和創業投資還有心理方面的差異。避險基金從業人員基本上各自獨立。當交易員路易斯.培根(Louis Bacon)於1990年代買下一座私人島嶼時,人們打趣說他原本就住在孤島上,因為他本來就是隱藏在一排排螢幕之後的神祕人物,隱居避世。不過創業投資人是另一個極端,他們的辦公室相鄰,彼此會在新創公司的董事會上相遇,互相談論後續的投資事宜。不論在地理和心理上,創投從業人員緊緊相依。由於他們仰賴人脈網絡,因此即便只是提起泡沫化的可能性也代價高昂,公開質疑瘋狂情勢的投資人只會掃大家的興。
一般情況下,股市能夠制衡創投產業的泡沫熱潮。創業投資人知道,新創公司尋求上市時將面臨更嚴厲的裁判,股民不太會為了別人的夢想掏出錢來,譴責公司或做空其股票時更不會手下留情。這對創投行為有一定的約束作用,防止創業投資人對私人公司的估價過高,以致公開發行股票後無法獲利退場。不過到了1990年代後期,股市不再具有約束效果。CNBC等財經電視頻道在1990年代後半的收視人數翻了3倍,新一代的股票新手受到節目中財經話題的驅使,大量買進網路股。心明眼亮的避險基金投資人做空這股熱潮,反而蒙受嚴重虧損,直到他們由空轉多,於是進一步推動股市的上漲氣勢。華爾街人士指出,乘冪定律思維的普及,可能是大眾對於科技股抱持狂熱態度的原因。摩根史坦利投資長喬瑟夫.佩羅拉(Joseph Perella)驚嘆道:「美國資本主義出現根本的變化,基本上大眾的態度是:『我要買進每一家公司的股票,就算虧了19次,只要第20次碰上雅虎,那就值得了。』」
由於股市也全心接納乘冪定律的邏輯,創業投資人再也不受制衡。私人投資協議的估價越來越高,新創公司籌到的資金也越來越多。1997年,線上零售商Webvan在徒有概念、根本還不算是一間公司的情況下,就向標竿創投和紅杉資本募得700萬元。1998年,Webvan又向軟銀募得3,500萬元,用於建立公司的第一間經銷中心。1999年,經銷中心還未開始營運,Webvan又成功說服投資人投入令人瞠目結舌的3.48億元。到這時,根據創投投機者的評估,雖然公司仍持續虧損,Webvan的帳面估價已超過40億元。簡而言之,Webvan就像是打了類固醇的GO,展開一場創業投資漫天喊價之旅。不過,由於股市一樣亢奮,創業投資人並不是唯一的罪魁禍首。Webvan於1999年秋天初次公開發行,成績亮眼,公司市值飆破110億元。如果股票市場投資人願意高估公司價值,創業投資的狂熱也算是情有可原。
1998年8月某天,兩位史丹佛大學博士生坐在帕羅奧圖某處的門廊上。他們正為開發瀏覽網路的新方式籌措資金,就像3年前的雅虎一樣。不過當時雅虎創辦人向紅杉資本募得100萬元,交出公司三分之一股權,而接下來的發展則非常不一樣。
這兩位博士生分別是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賴利.佩吉(Larry Page),他們初露頭角的公司叫做Google。表面上,他們的創業前途黯淡,市面上已經有其他17間提供網路搜尋服務的公司。不過自信滿滿的布林和佩吉相信他們的技術能壓倒對手,因此他們在門廊上等待一位著名的矽谷工程師安迪.貝托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
不久之後,貝托斯海姆駕著一輛銀色保時捷抵達,他本人風度翩翩,頭髮蓬鬆飄逸,講話帶著微微的德國口音。布林和佩吉向他示範搜尋引擎後,貝托斯海姆越發感興趣。Google系統會查詢有多少其他網站連結到某一網站,據此為網站進行排序,因此顯示的搜尋結果相關程度比對手更高。貝托斯海姆立刻發現其系統借用學術界的機制:引用次數是判斷論文聲望的標準。
貝托斯海姆不是創業投資人,不過他成立2間公司,手邊有資金可以運用。1982年,他共同創立昇陽電腦,大獲成功。之後又創立網路公司Granite Systems,貝托斯海姆是該公司的主要股東,後來公司以2.2億元出售給思科。貝托斯海姆喜歡運用自己的財富來資助工程師同行,隨處花個幾十萬對他的銀行餘額沒什麼影響。
1980年代後期,網路發展初期的創業家約翰.利朵(John Little)經過貝托斯海姆的辦公室。利朵也是電腦科學家,兩人是在昇陽電腦的啤酒派對上認識的。
貝托斯海姆問道:「近來如何?」
利朵回答不太好,他的新創公司共同創辦人打算辭職,而買下他的股份需要一筆錢。利朵沒有這筆錢。
你需要多少?貝托斯海姆問道。
利朵表示:「我不知道,大概9萬吧。」
貝托斯海姆拿出支票簿,開了一張9萬元的支票給他。動作之迅速,利朵根本還沒意會到他在做什麼。利朵事後表示:「他拿出支票簿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要幹嘛。我從來沒看過有人就這麼掏出錢來,沒有交換條件。」貝托斯海姆沒有表示他希望用這筆錢買進利朵公司的多少股份,利朵回憶道:「安迪不太在意這些。那之後,大概1年1次吧,我們可能在烤肉會上碰到彼此,就會向對方提到要把那筆投資白紙黑字寫下來,可是我們都很忙。」
最後,到了1996年,利朵向專業的創業投資人(Accel的亞瑟.派特森)募得將近600萬元,這時必須明確把誰擁有多少股份記錄下來了,貝托斯海姆衝動的慷慨之舉換得利朵公司的1%股份。在網路欣欣向榮的那段時期,利朵的公司Portal Software業績驚人,因此貝托斯海姆9萬元支票的報酬大概比他共同創立昇陽電腦的獲利還要高。
現在,貝托斯海姆坐在帕羅奧圖一處門廊上與Google創辦人閒聊,他準備故技重施。他看得出Google創辦人沒有商業企劃書,他們堅定拒絕採用橫幅廣告或彈出式廣告這兩種網站營利的標準作法。不過看到布林和佩吉示範他們的搜尋引擎,貝托斯海姆明白他們具有軟體優勢;此外,他也對這兩位年輕人頗有好感。他們充滿好奇心、擇善固執、性情平和,和他自己在史丹佛大學研讀電腦科學時沒什麼不同。
貝托斯海姆跑回他的保時捷車上拿東西,他興高采烈地表示:「我們還可以討論幾個問題,我先開張支票給你們。」,接著交給布林和佩吉一張10萬元的支票,抬頭是「Google公司」。
布林和佩吉表示他們還沒成立公司,沒有可以存入支票的銀行帳戶。
貝托斯海姆輕快地表示:「那等你們成立公司,就存進去吧。」接著就開著保時捷揚長而去,沒有指明他希望用這筆錢購入Google多少股份。他事後表示:「我興奮極了,只想著不能錯過。」
--------------------------
貝托斯海姆的隨興投資標誌著新型態技術投資的出現,重要性堪比2年前孫正義開出的1億元支票。1990年代中期以前,半退休的科技業主管偶爾也會從事投資。舉例來說,麥克.馬庫拉資助並輔導剛起步的蘋果公司;米奇.卡普爾為GO和UUNET提供資金與建議。不過要到1990年代中後段、科技市場的繁榮時期,這種「天使投資」才真正開始成為一股勢力。多虧初次公開發行帶來的財富,矽谷的百萬富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天使投資成為這個菁英族群的新消遣,就像醫美手術在好萊塢一樣的稀鬆平常。1998年,貝托斯海姆資助Google的同一年,活躍的天使投資人朗恩.康威(Ron Conway)甚至籌募3,000萬元的基金來強化個人投資,而「機構天使」或「超級天使」成為矽谷新創公司引擎的最新汽缸。一夕之間,創辦者有了傳統創業投資人之外的新選擇,就像孫正義所的成長資金提供了公開上市之外的選項。進行第一輪募資時,創業家只需要認識幾位成功前輩就行了。貝托斯海姆獨特的投資風格後來幾乎變成常態。
布林和佩吉尤其善用這種新模式。一開始,他們找上印度裔科技主管蘭姆.西里蘭(Ram Shriram),西里蘭後來靠著將自己的新創公司出售給亞馬遜而發跡。起初,西里蘭幫忙介紹幾間可能有意收購Google技術的大型搜尋公司,不過後來沒有出現像樣的合作案,因此西里蘭提議資助這兩位博士生,前提是他們能找到其他天使投資人合資。布林和佩吉很快就成功拉攏貝托斯海姆及其Granite Systems的共同創辦人,還有一位史丹佛大學教授大衛.薛瑞頓(David Cheriton)。幾個月後,亞馬遜創辦人傑夫.貝佐斯造訪灣區露營度假,在西里蘭家遇到布林和佩吉兩人。貝佐斯也想要入股,他後來表示:「我愛上賴利和謝爾蓋的才華。」
至1998年底,布林和佩吉已向4位天使投資人募得100萬元,比雅虎自紅杉資本募到的資金還多。不過他們沒有與任何一位創業投資人交涉,交出的公司股權更不到十分之一,也不必同意創業投資人訂定的績效目標和監管。貝佐斯和貝托斯海姆等天使投資人全心專注於自己的公司,無暇對布林和佩吉指手畫腳。於是,一如約翰.利朵所說,Google創辦人得以「就這麼募到錢,沒有交換條件」。自由資本的舊有觀念邁入全新層次,人類歷史中,年輕發明家從未如此備受禮遇。
雖然Google創辦人避免與創業投資人交涉,不過當時正是創投產業欣欣向榮的時期。1998年,創業投資人籌措的資金達到創紀錄的300億元,與孫正義投資雅虎的1995年相比翻了3倍。1999年成長更為猛烈:創投合夥公司握有560億元資金;美國的創投合夥企業數量達750間(10年前大約只有400間)。矽谷似乎瀰漫著創造財富所激發的腎上腺素,至少對創業投資人來說是如此。
這樣的蓬勃發展令傳統創業投資人稍感不安。一位老前輩回憶道:「顯然我們身處泡沫之中。我們認知中打造基本價值的措施都遭到懲罰,而偏差行為卻獲得獎賞。」雅虎所帶動的趨勢(先行者因氣勢壯盛而獲得資金)顯然衝過了頭:在許多案例中,創造氣勢的是資金本身,眾多網路公司根本賺不到利潤。不論市場上揚的態勢有多瘋狂,創投前輩也無力抵制。不像避險基金,即便預期泡沫化也能運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或其他機制來獲利,創業投資人想要賺錢就只能打賭價值不斷上升。他們的業務很單純,那就是購買新創公司的股權,而且除了付出水漲船高的價格外別無他法。除了獲利機制以外,避險基金和創業投資還有心理方面的差異。避險基金從業人員基本上各自獨立。當交易員路易斯.培根(Louis Bacon)於1990年代買下一座私人島嶼時,人們打趣說他原本就住在孤島上,因為他本來就是隱藏在一排排螢幕之後的神祕人物,隱居避世。不過創業投資人是另一個極端,他們的辦公室相鄰,彼此會在新創公司的董事會上相遇,互相談論後續的投資事宜。不論在地理和心理上,創投從業人員緊緊相依。由於他們仰賴人脈網絡,因此即便只是提起泡沫化的可能性也代價高昂,公開質疑瘋狂情勢的投資人只會掃大家的興。
一般情況下,股市能夠制衡創投產業的泡沫熱潮。創業投資人知道,新創公司尋求上市時將面臨更嚴厲的裁判,股民不太會為了別人的夢想掏出錢來,譴責公司或做空其股票時更不會手下留情。這對創投行為有一定的約束作用,防止創業投資人對私人公司的估價過高,以致公開發行股票後無法獲利退場。不過到了1990年代後期,股市不再具有約束效果。CNBC等財經電視頻道在1990年代後半的收視人數翻了3倍,新一代的股票新手受到節目中財經話題的驅使,大量買進網路股。心明眼亮的避險基金投資人做空這股熱潮,反而蒙受嚴重虧損,直到他們由空轉多,於是進一步推動股市的上漲氣勢。華爾街人士指出,乘冪定律思維的普及,可能是大眾對於科技股抱持狂熱態度的原因。摩根史坦利投資長喬瑟夫.佩羅拉(Joseph Perella)驚嘆道:「美國資本主義出現根本的變化,基本上大眾的態度是:『我要買進每一家公司的股票,就算虧了19次,只要第20次碰上雅虎,那就值得了。』」
由於股市也全心接納乘冪定律的邏輯,創業投資人再也不受制衡。私人投資協議的估價越來越高,新創公司籌到的資金也越來越多。1997年,線上零售商Webvan在徒有概念、根本還不算是一間公司的情況下,就向標竿創投和紅杉資本募得700萬元。1998年,Webvan又向軟銀募得3,500萬元,用於建立公司的第一間經銷中心。1999年,經銷中心還未開始營運,Webvan又成功說服投資人投入令人瞠目結舌的3.48億元。到這時,根據創投投機者的評估,雖然公司仍持續虧損,Webvan的帳面估價已超過40億元。簡而言之,Webvan就像是打了類固醇的GO,展開一場創業投資漫天喊價之旅。不過,由於股市一樣亢奮,創業投資人並不是唯一的罪魁禍首。Webvan於1999年秋天初次公開發行,成績亮眼,公司市值飆破110億元。如果股票市場投資人願意高估公司價值,創業投資的狂熱也算是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