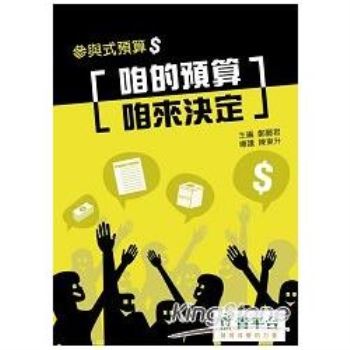第一篇、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神話與現實/萬毓澤老師
第一節 從巴西的「民主聖地」說起
「參與式民主」的重要闡釋者、政治理論學者 Carole Pateman 在經典著作《參與和民主理論》(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中,曾這樣闡述參與式民主的核心論點:「在參與式的理論中,『參與』意謂(平等地)參與決策過程,而『政治平等』意謂擁有平等的權力來決定決策的結果」;「在參與式民主理論中,『參與』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而且是最廣義的教育,包括心理的面向,以及實踐民主技巧及民主程序」(Pateman, 1970: 43, 42)。參與式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多不勝數、各有特色,但近年來引人注目的「參與式預算」,似乎頗能符合 Pateman 的描述。
「參與式預算」晚近已在都市治理、發展研究、民主理論等領域中成為熱門關鍵字。舉幾個例子:2005 年,英國成立了半官方的「參與式預算小組」(Participatory Budgeting Unit),由民間的慈善團體「教會扶貧行動」(Church Action on Poverty)和官方的社區暨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共同推動,至今已在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進行約 150 個試點;2007 年,世界銀行出版了參與式預算的調查報告;參與式預算的國際會議也於 2010 年首度召開。不管是左的、右的、激進的、保守的政府與團體,似乎都能從「參與式預算」中各取所需。時至今日,同以「參與式預算」為名的方案或計畫,目標、內容可能南轅北轍,民眾「參與」的程度也可能有雲泥之別。但無論如何,如果要理解參與式預算,為當前不同的參與式預算實踐模式定位,似乎很難不追本溯源,回到參與式預算的發源地: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的首府愉港(Porto
Alegre)。
巴西工人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PT)1988 年在愉港取得執政權,1989 年起在該地推動參與式預算(葡萄牙文為 orçamento participativo,簡稱 OP)。愉港的參與式預算,是一系列由下而上匯集公民意見的決策過程。在過程中,公民透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參與公共預算的決策和控制,不僅逐步將資源轉移至公共服務項目和較貧窮的社區,還促成了各種基層社區組織的蓬勃發展。在審議過程中,市政府公開所有預算,包括人員費用、公共債務、基本服務、投資、發展等,並組織各種會議,協助公民參與討論。
實施六、七年後,1996 年的聯合國人居會議(United Nations Habitat Conference)將愉港的參與式預算選為全世界都市治理的「最佳實踐」之一,也從此成為全世界「進步」或「左翼」都市治理的典範。
那麼,為什麼是愉港?
愉港可說是巴西的「民主聖地」,長期扮演「反對都市」(oppositional city)的角色。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初期,中間偏左的巴西勞動黨(Partido Trabalhista Brasileiro,PTB)在愉港建立了深厚的基礎。3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61 年 8 月,軍方策動政變,南大河州州長 Leonel Brizola(先前曾任愉港市長)在州長官邸內指揮反抗,在各地成立準軍事組織「民主抵抗委員會」( C o m i t ê d e R e s i s t ê n c i a Democrática),並宣布愉港將捍衛民主,直到最後一刻。後來,在 1964 年到 1985 年的軍事戒嚴時期,愉港的反對力量始終存在,並且在民主化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1985 年,各州首府市長恢復民選,愉港的勝選者為巴西民主勞動黨的 Alceu Collares。1988 年,政治上更為激進的工人黨在地方選舉中大有斬獲,選上 36 名市長,包括 3 個州的首府,愉港也在其中。自 1988 年起,工人黨在愉港連續選上四屆市長,共執政了 16 年;代表「另類全球化」、「全球正義運動」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前三屆、第五屆也都在愉港召開(2001-2003 年、2005 年),第五屆的與會人士還共同發表了〈愉港宣言〉,提出十二項涵蓋「經濟措施」、「和平與正義」及「民主」的行動綱領。總之,在工人黨的治理、進步社會力量的推波助瀾下,推動鼓勵民眾參與的預算改革,似乎是水到渠成。即使 2005 年後愉港不再由工人黨執政,參與式預算依然健在,成為「不可逆」的民主成就。四位研究參與式預算的重要學者將這段過程總結如下:
在愉港,1988 年工人黨選舉獲勝後,出現了「機會之窗」,從而使參與式預算逐漸成形。但是,推動新的參與式過程的,不只是新上任的左翼地方政府;公民社會,尤其是社區協會,也要求更多的共同決策權。這是一種務實的變革,而不是學術或政治計畫的應用。……工人黨在掌權 16 年後,於 2004 年失去市長職位,但由於參與式預算的制度化程度已經很深,故新政府也不敢廢除之(Sintomer and Herzberg, 2012:8,中譯略有修改)。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我們在第三節、第四節會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節 從巴西的「民主聖地」說起
「參與式民主」的重要闡釋者、政治理論學者 Carole Pateman 在經典著作《參與和民主理論》(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中,曾這樣闡述參與式民主的核心論點:「在參與式的理論中,『參與』意謂(平等地)參與決策過程,而『政治平等』意謂擁有平等的權力來決定決策的結果」;「在參與式民主理論中,『參與』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而且是最廣義的教育,包括心理的面向,以及實踐民主技巧及民主程序」(Pateman, 1970: 43, 42)。參與式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多不勝數、各有特色,但近年來引人注目的「參與式預算」,似乎頗能符合 Pateman 的描述。
「參與式預算」晚近已在都市治理、發展研究、民主理論等領域中成為熱門關鍵字。舉幾個例子:2005 年,英國成立了半官方的「參與式預算小組」(Participatory Budgeting Unit),由民間的慈善團體「教會扶貧行動」(Church Action on Poverty)和官方的社區暨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共同推動,至今已在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進行約 150 個試點;2007 年,世界銀行出版了參與式預算的調查報告;參與式預算的國際會議也於 2010 年首度召開。不管是左的、右的、激進的、保守的政府與團體,似乎都能從「參與式預算」中各取所需。時至今日,同以「參與式預算」為名的方案或計畫,目標、內容可能南轅北轍,民眾「參與」的程度也可能有雲泥之別。但無論如何,如果要理解參與式預算,為當前不同的參與式預算實踐模式定位,似乎很難不追本溯源,回到參與式預算的發源地: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的首府愉港(Porto
Alegre)。
巴西工人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PT)1988 年在愉港取得執政權,1989 年起在該地推動參與式預算(葡萄牙文為 orçamento participativo,簡稱 OP)。愉港的參與式預算,是一系列由下而上匯集公民意見的決策過程。在過程中,公民透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參與公共預算的決策和控制,不僅逐步將資源轉移至公共服務項目和較貧窮的社區,還促成了各種基層社區組織的蓬勃發展。在審議過程中,市政府公開所有預算,包括人員費用、公共債務、基本服務、投資、發展等,並組織各種會議,協助公民參與討論。
實施六、七年後,1996 年的聯合國人居會議(United Nations Habitat Conference)將愉港的參與式預算選為全世界都市治理的「最佳實踐」之一,也從此成為全世界「進步」或「左翼」都市治理的典範。
那麼,為什麼是愉港?
愉港可說是巴西的「民主聖地」,長期扮演「反對都市」(oppositional city)的角色。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初期,中間偏左的巴西勞動黨(Partido Trabalhista Brasileiro,PTB)在愉港建立了深厚的基礎。3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61 年 8 月,軍方策動政變,南大河州州長 Leonel Brizola(先前曾任愉港市長)在州長官邸內指揮反抗,在各地成立準軍事組織「民主抵抗委員會」( C o m i t ê d e R e s i s t ê n c i a Democrática),並宣布愉港將捍衛民主,直到最後一刻。後來,在 1964 年到 1985 年的軍事戒嚴時期,愉港的反對力量始終存在,並且在民主化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1985 年,各州首府市長恢復民選,愉港的勝選者為巴西民主勞動黨的 Alceu Collares。1988 年,政治上更為激進的工人黨在地方選舉中大有斬獲,選上 36 名市長,包括 3 個州的首府,愉港也在其中。自 1988 年起,工人黨在愉港連續選上四屆市長,共執政了 16 年;代表「另類全球化」、「全球正義運動」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前三屆、第五屆也都在愉港召開(2001-2003 年、2005 年),第五屆的與會人士還共同發表了〈愉港宣言〉,提出十二項涵蓋「經濟措施」、「和平與正義」及「民主」的行動綱領。總之,在工人黨的治理、進步社會力量的推波助瀾下,推動鼓勵民眾參與的預算改革,似乎是水到渠成。即使 2005 年後愉港不再由工人黨執政,參與式預算依然健在,成為「不可逆」的民主成就。四位研究參與式預算的重要學者將這段過程總結如下:
在愉港,1988 年工人黨選舉獲勝後,出現了「機會之窗」,從而使參與式預算逐漸成形。但是,推動新的參與式過程的,不只是新上任的左翼地方政府;公民社會,尤其是社區協會,也要求更多的共同決策權。這是一種務實的變革,而不是學術或政治計畫的應用。……工人黨在掌權 16 年後,於 2004 年失去市長職位,但由於參與式預算的制度化程度已經很深,故新政府也不敢廢除之(Sintomer and Herzberg, 2012:8,中譯略有修改)。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我們在第三節、第四節會討論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