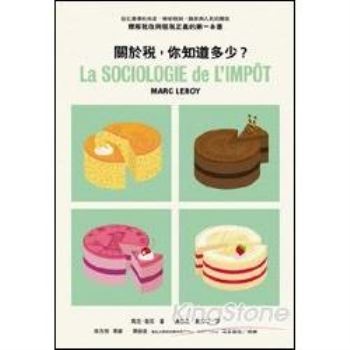中文版序 財稅制度做為一種與市場運作有關的特殊公共行動的型態,不僅是一個經濟議題,更有重要的政治和社會意涵。稅制一方面是輔助公共政策的一種手段,例如用以加惠某些企業、特定職業類別或經濟產業等等,同時它本身也是公共政策的一個項目,例如我們會討論如何調整稅制來達成所得重分配或是支應政府公共支出。 跳脫稅制複雜的技術層面,財稅社會學關心的是如何經由社會面和政治面的探討以及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分析與財稅制度相關的現象。因此,不論對學術研究者、公民大眾、或是決定政策的人而言,財稅社會學都具有重要性。財稅社會學觀察與稅相關的各種政府行為程序,不僅探討財稅國家之於公民的正當性何在,也對社會正義的問題提出省思。此外,財稅社會學的研究也將實證調查的資料化為理論,提出能解釋廣泛現象的模型。 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歐洲,財稅社會學實為理解社會種種演進和變化的重要研究取徑。這門學問對於公共政策和社會科學研究都有重大意義,例如:財稅改革和社會變遷彼此相關,稅政實務的操作則可延伸出官僚制度治理理論(尤其在商業治理方面),大眾對稅的觀感涉及公共政策的正當性,稅賦的負擔應放在社會正義的具體脈絡下研究,逃漏稅現象則可援引偏差行為社會學來探討何以公共政策的功能失去正當性,抗稅行動則是一種反映政治制度運轉失靈的集體行動。此外,在研究納稅人如何決定服從或違反納稅義務時,財稅社會學提出超越功效主義的利益(self-interest)模型的新理性模型,例如財稅社會學提出「自願攤派性質的稅」(l’impot-contribution)的觀點,以描繪公民認為納稅就是貢獻稅金給他認為正當的公共政策的現象,不論他是否會從該政策中得到利益。此時,納稅人的決策便是建立在其政治價值觀和具體的論理邏輯(即認知理性而非利益計算)上。 國家、權力、和公共政策都是財稅社會學關注的課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歐洲現代國家的誕生也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相應產生的穩定稅制有密切關連。由經濟全球化所遭遇的危機對各國政府造成的衝擊,也可以明顯看到財稅制度的政治意涵是不容忽視的。然而究竟稅是基於服從政治權威的義務,還是基於同意政策正當性而提供的納捐?兩種論點總是爭論不休,而欲化解兩造間的紛爭,亦即稅是一種強制(例如出於戰爭或市場危機等等),或是一種在稅的各項功能之間做出的政治性選擇,唯有倚賴民主體制下公民的自律意識。此外,公共事務的決策也是一項研究重點,包括制度改革、財稅聯邦主義與地方政府間的關係、官僚體制的變革、左右派對抗及其他意識型態造成的影響……等等。 稅法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也是財稅社會學的研究主題。例如研究財稅稽查使我們注意到逃漏稅的官方認定基準背後的許多社會機制運作,也使我們注意到各國間不同的行政管理型態等等。 同時,財稅社會學也是一種超越了狹義理性選擇理論(指功效主義)侷限的經濟社會學。其關注財稅國家和經濟之間的各種關係,特別是在面對不景氣時國家介入經濟活動的策略。 如果完全從社會的角度來建立理論,稅制的相關現象應該被解釋為一種社會程序(processus)的產物。然而,儘管與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相關的文獻汗牛充棟,針對稅的社會科學研究即便對個人或公共政策而言都有具體的貢獻,卻仍有待深入耕耘。財稅社會學的理論模型,採用的資料來源包括官方資料、本身的研究成果、與財稅心理學、金融史、經濟心理學(la psychologie economique)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之上。歷史研究、認知研究、以及功能論等研究方法對財稅社會學尤為重要。 歷經草創時期,財政社會學在各國及不同時期的發展程度不一。其能否成為受重視的研究領域,端視各國政府及社會的態度是否可以邁過需求面的進入門檻,並克服以法律學者與經濟學者為主軸,過度強調專業技術知識的供給面障礙。從縱向的觀點來看,國家干涉主義的演進似乎與此一研究領域的發展有關,雖然兩種現象在時間上並不完全重疊。 在一九七○年代的經濟危機下,國家干涉主義受到強烈的批評。批評的聲浪持續不斷,更受到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全球化的觀點所支持。公共選擇學派就主張反對徵稅主義,這和他們主張限縮政府社福經費的立場是相互配套的。新馬克思主義也藉由公共財政危機的分析對徵稅的正當性再次提出質疑。 一九九○年之後,財稅社會學的面貌有所改變。在經濟全球化的脈絡下,是否應該進一步限縮國家權力成為辯論的焦點。以利益為核心的功效主義,其主導地位受到強調實證方法的經濟心理學所挑戰。新的研究顯示,若財稅國家被認為是正當的,納稅人同時也是一個樂於實踐公民身份支付稅金的人。財稅社會學研究的日益充實,一方面來自研究領域的拓廣,例如研究地方分權政策(decentralisation)、發展中國家、前蘇聯成員國……等等,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其它不同學科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