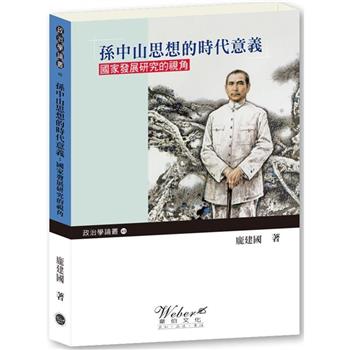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前言
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認為,人類的思想乃是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該思想著落的時代環境背景,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影響或制約,反映著思想建構者特定的歷史處境或社會位置。 孫中山(1866-1925)建立其思想體系的時代距今已近百年,百年來,不僅人類社會產生巨大變化,人類知識更是突飛猛進,孫中山思想到了今天還能夠經得起時代考驗,具有時代意義嗎?這是本書開宗明義想要嘗試回答的問題。
本書作者對於前述問題的基本看法是,雖然孫中山思想是特定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反映著孫中山在特定時代環境下,對於中國發展建設問題的思考,不過,由於孫中山思想本質上的一些特性,使得孫中山思想比較經得起社會變遷的考驗,即使在時代環境變化、人類知識進步之餘,仍然能夠經得起檢驗,展現其歷久彌新的時代意義。這種時代意義的展現,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發展理論演進的情形,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一些趨勢,看得更清楚。
依據前述思維,本書的敍事結構或章節安排如下。首先,從孫中山建構其思想體系的時代環境談起。其次,從意識形態思維方法比較研究的角度(特別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比較),來說明孫中山思想的特性。接著,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發展研究興起的緣由。然後,介紹國家發展研究領域中主要的理論派別,陳明其與孫中山思想相互會通或彼此扞格之處,並以海峽兩岸的發展經驗來檢驗這些說法的長短高下。最後,以意識形態和國家發展關係的分析探討,以及海峽兩岸發展經驗的整體省思,作為結語。
貳、現代性的擴散與回應
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其他革命方略所構成,並以三民主義為理論核心的孫中山思想,從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來看,乃是一套整體性的國家發展理論(the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雖然孫中山建構其思想體系的時空背景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當代國家發展理論則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兩者對應的時空背景並不相同。但是,若將視野拉長放大,其實兩者都可以擺在現代性擴散和回應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
儘管有著不同的體會或界定,學者們大多同意,現代性是伴隨十八和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而來的人類社會組織型態和生活方式的變遷。這種社會變遷揉和了工業革命之前和之後,歐洲人在思想觀念、社會制度和工藝技術上出現的一些歷史現象和演化趨勢,像城市興起(十一到十三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十四到十五世紀)、海外探險和殖民主義(十五到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十四到二十一世紀)、宗教改革(十六世紀)、民族國家(十五到十七世紀)、民主革命(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十七世紀)、和啟蒙運動(十八世紀)等等(黃瑞祺,2001:38-51)。
金耀基(2004:53)認為,啟蒙運動把這種社會大轉型提升到意識層次,建構出一種以理性為基礎,包含自由、民主、公正、人權等價值的文明形態或國家發展方案,可稱之為「啟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或者,採用Jurgen Habermas(1981)的用語,稱之為「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現代性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而具有突破性的生產力和向外蔓延的競爭力,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強勢文明。從制度安排層面來理解現代性,它主要表現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社會形構與人群關係。從社會變遷脈絡來理解現代性,它呈現出下列趨勢:首先,在社會經濟面向上,是都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和科技進步;其次,在政治面向上,是民主政體的建立和維繫;再者,在文化面向上,是世俗化和理性化;最後,在人類群體關係上,是建立民族國家。
Jurgen Habermas(1981)將這一套組織型態和生活方式視為歐洲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社會不斷在追求且尚未完成的方案。Anthony Giddens(1990)認為,這套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模式(modes of social life or organization)大約十七世紀之時從歐洲生成,然後,隨著時間演進不斷向外蔓延,至今已擴及大多數的人類社會,但仍然保有其主要的特性,尚未成為過去。
從上述現代性形成的概括析論出發,我們發現,孫中山思想基本上就是一套回應現代性對中國的挑戰,並追求中國之現代性的國家發展方案。以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來說,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問題的烘托和對應的三個主義的標舉,就是回應現代性挑戰和處理國家發展問題的論述。1904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即指出: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他旋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孫文,1989,第二冊:256)。
這段話所描繪的觀察和前述現代性形成的背景可說是若合符節。值得注意的是,形成現代性的各項質素彼此之間雖然有著某些歷史脈絡的關聯性,或者社會形構的親和性(affinity),但卻非邏輯演繹上環環相扣的必然關係,而是特定歷史社會情境下的輻湊聚合。所以,在擴張的過程中,隨著被影響地區自然和人文條件的差異,現代性的各項質素會遭遇不同程度的迎拒,會出現不同速度的進展,不同深淺的影響,和不同樣貌的組合,因而使得回應現代性擴散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之路,呈現不同的路徑和速度。同時,除了發源地的歐洲之外,現代性在擴張的過程中,也分化出另外一些推波助瀾的據點,像美國、俄國和日本,並且各自展現出本身的現代性特質和現代化路徑,而有所謂「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呈現。 那麼,中國的現代性該如何建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該如何開拓?顯然,這就是孫中山思想要探索的大哉問。
參、探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
從歷史脈絡來觀察,現代性在歐洲成形之後,就以強勢文明的姿態開始向外擴張,並在十九世紀的中葉開始挑戰東方的古老文明國度─中國。中國與西方近代文明的接觸,本可追溯到明朝末年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之交。西元1583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入居廣東肇慶,開啟了西方文明來到中國的先河。隨後,同樣也是義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的艾儒略(Giulio Aleni)和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也分別在1613年和1623年到中國傳教,他們將歐洲天文、數學和地理方面的知識帶進了東方的古老文明。 明朝覆亡,清朝繼起,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主的西方學者仍然絡繹來到中國,並且得到順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重用。後來,由於耶穌會傳教方式改變,並且介入清廷皇位之爭,導致雍正皇帝把康熙皇帝所延攬的大量歐洲學者驅逐淨盡,開始了清朝的閉關自守政策,斷絕了中國學界與西方交往的機會,也使得中西文化交流一度中斷了兩百年(梁啟超,1975:18-19)。在這一段期間裡,缺少外來文明刺激的中國文明逐漸落後給現代性形成中的歐洲文明。
黃仁宇(2006)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認為,明神宗缺乏數字管理的庸碌施政,顯示出由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文明已經呈現出耗弱僵滯的情形,為日後無力因應西方文明的挑戰寫下註腳。但是,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進行交流的期間,中國仍然扮演強有力的角色。當清廷發現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對於中國傳統的人生觀和倫理規範構成挑戰,同時還夾纒著某些政治目的,因而決定加以驅逐之時,西方只能悄然退出。直到中英鴉片戰爭發生之前,西方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俄國等國家都曾嘗試侵入中國,但都無法得逞。此一時期,歐洲的現代性還在醞釀孵化的階段,尚未經歷工業革命的洗禮而塑形摶成。
然而,當十九世紀西潮再度拍打東方古老大陸的邊岸之時,以現代性為主要內涵的西方文明已經經歷了工業革命的洗禮,不再以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謂「陌生的宗教」(strange religion)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人面前,而是以「陌生的技器」(strange technology)的面目來敲叩中華帝國的大門(金耀基,1977:1)。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艦隊的炮火轟開了中國閉關的大門,劃下了中西文明對壘強弱異勢的分水嶺,現代性的挑戰成為有意救亡圖存的中國志士仁人必須面對的大變局。從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和李鴻章等人所推動的洋務運動(或稱自強運動),到康有為和梁啟超主張的變法維新,到孫中山所領導的倒滿革命,再到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中國大致依循著器物技能層次、制度層次和思想行為層次的順序,逐步接受了現代性的洗禮(金耀基,1978:183;殷海光,1988)。不過,此一過程並不順遂,甚至於可說是充滿了挫折困頓。
由「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中間經歷了中西文化「體」、「用」上的爭執,變法維新的嘗試,倒滿革命的實現,到新文化運動的呼籲,中國知識界對現代性挑戰的因應態度和理解模式漸次蛻變。從器物技術的學習,到政法制度的仿效,再到思想觀念的爭執和價值理想的批判,中國接受現代性洗禮的現代化之路,不僅荊棘叢生,而且路線紛歧(張朋園,1975)。
從同盟會時期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先後盛行於中國知識圈的西方學說,有淵源於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Montesquieu)、彌勒(John Stuart Mill)、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民主思想;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和杜威(John Dewey)到中國講學,所傳授的邏輯理論和實用主義;有脫胎於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物種起源說,並由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進一步演繹,強調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有以克魯包特金(Peter Kropotkin)的《互助論》(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有以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存在主義思想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有柏格森(Henry Bergson)強調創造和進化不會互相排斥的「創造進化論」;以及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王德昭,1975:182-183)。
在百家爭鳴的中國思想界,面對歐洲現代性和其支流或變體(如俄國和日本之現代性)的洶湧來勢,為了挽救國運的衰蹇、重振民族的生機,曾經有許多志士仁人提出他們的分析判斷和因應方案。在這些努力當中,本書作者認為,能夠憑藉融貫中西的學養, 豐富的海外閱歷,秉持高瞻遠矚的視野,提出理性務實的洞見,為中國的發展建設擘畫出最佳藍圖方案的人,就是孫中山。
不過,有如本節前言提到的,孫中山建立其思想體系的時代距今已有百年,百年來,不僅人類社會產生巨大變化,人類知識更是突飛猛進,孫中山思想到了今天還能夠經得起時代考驗,具有時代意義嗎?本書作者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說,雖然時空背景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國家發展的研究更積累了大量的知識,孫中山思想仍然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甚至於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再來審視孫中山思想,更可以看出孫中山思想的歷久彌新。而孫中山思想之所以能夠經得起時代考驗,展現歷久彌新的意涵,主要在於這套思想體系具有一些可大可久的特性,以下略加申論。
第二節 孫中山思想的特性
從意識形態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本書作者認為,孫中山思想具有三個可大可久的思想建構特性,就是「博大平正」、「調和持中」、以及「彈性開放」,以下分別論列。
壹、博大平正的特性
首先,談到博大平正。過去,從正面態度評價孫中山思想的人,常有孫中山思想「博大精深」的說法,對此,本文作者認為,唐君毅(1976:74)的評語:「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並不以精深見長,但在晚清,與他人相比,則顯然最平正博大,所以才為人們所歸往」,值得參考。另外,徐復觀在談論他對於孫中山思想的體認時表示: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並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發揮了思想上的綜合能力,所以能概括三百年來的政治、社會思想。而是在他的天下為公的「人格之全」中把握到了「天下之全」;由天下之全以指陳天下的需要與其遠景。這是由「天下的實存」來決定思想,而不是以思想去決定「天下的實存」。因此,僅從「知識系統」、「思想系統」等思辨的方向,不能把握到三民主義的真切地意義;而只能從「天下之全」、「人類之全」的真實存在中,才可以加以把握(徐復觀,1971a:150)。
不過,這並不意味孫中山的思想是膚淺或零散的。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另一巨擘,與康有為一起領導立憲派的梁啟超就認為,革命派的孫中山雖然不是個專門做學問的學者,但「眼光極敏銳」(梁啟超,1975:30),並且在與孫中山初識交往之時,受孫中山之影響,幾至脫離康有為的陣營(張朋園,1969:208)。如此眼光敏銳、深具說服力的人,在建構本身的思想體系時,決不至於停留在過於膚淺和片斷的層次。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是,由於孫中山是當時中國思想界極少數直接受英美教育出身的成員,沒有英文的語言障礙,所以,他可以直接涉獵以英文表述的現代性主流思想。同時,孫中山也是同一時代的政治人物中,海外天地接觸最廣,閱歷和體會最深的一位,所以,他可以比同一時代的政治家更廣泛深入地理解現代性。另外,孫中山一生交往的朋友和一起革命的同志,有許多人是當時中國和西方思想界的精英。在中國方面,例如何啟、容閎、鄭觀應、王韜、章太炎、李石曾和歐陽竟無等人,或者與孫中山先生曾經友好相善,或者與孫中山先生有過思想學問上的切磋(唐君毅,1976:79-80;胡秋原,1977:32-33)。在歐美學者方面,孫中山先生除了在倫敦蒙難後駐留英國的期間,與英國思想界的精英,尤其是費邊社的成員,多所往來之外(羅香林,1952:81-84),也曾和美國的杜威討論「知難行易」的問題(孫文,1989,第一冊:381),並和英國的加爾根(Archibald Ross Colquhoun)談論革命方略(孫文,1989,第一冊:391)。
再者,當革命派和立憲派透過《民報》與《新民叢報》論辯中國的改革之路時,孫中山與康有為、梁啟超在路線爭執上的理論交鋒,使得孫中山有機會從康、梁的論述中,獲取豐富本身思想體系的養分。當時,胡漢民、汪精衛、劉光漢等人依循著孫中山的指點,和梁啟超辯詰對話(張朋園,1969:208)。後來,則有戴季陶、吳稚暉、廖仲愷、邵元冲、朱執信、蔡元培、蔣夢麟、和王寵惠等人,服膺並且為文闡釋孫中山思想。
無論是和革命派同志的切磋,或者是和立憲派對手的辯難,乃至於辛亥革命之後對國家建設大業挫折的反省,都必然會促使孫中山將思想觸角延伸到一定的深度,並尋求本身論點的貫通。不過,若從孫中山所遺留之著作和言論資料來看,孫中山思想的確較少深遂精密的論證,最少,和馬克思與恩格思的論著相比,孫中山的論述不夠嚴密通貫。 究其原因,第一,是因為他的完整寫作計畫未能實現;第二,則是因為他希望普及國家建設的理念到俗民大眾。
就第一個原因來說,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演講本發行之時,於「自序」中說道:
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烱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敍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孫文,1989,第一冊:1)。
就第二個原因來說,鄒魯記述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時的一段故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又有一次,總理講民權主義,裡面有一段,我看了不很明白,特意拿了原稿去見總理。我報告來意之後就請他再講一遍。但是總理拿了原稿,問我從什麼地方起,到什麼地方止。我指出後,總理不待思索,立即把這一段全部塗掉。我不明用意,惶急起來請示總理。總理說:「不要這一段」。我問:「為什麼不要?」總理說:「三民主義的學理雖然非常深奧,却要使凡識字的人,個個都能看得懂。這樣,我的主義才能普及民眾,然後始能望其實現。假使你都看不清楚,那末看不懂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全部刪去。」很多人批評三民主義的文字太淺顯,並且還有建議修改的,知道總理這一段話,當然可以恍然大悟,明白三民主義的文字為什麼淺顯的理由了(鄒魯,1967:325)。
同樣的例子,也曾出現在其他場合。例如,孫中山先生在演講〈民生主義〉第二講的時候就說:
民生主義這個問題,如果要從學理上詳細來講,就是講十天或二十天也講不完全。況且這種學理,現在還是沒有定論的,所以單就學理來講,不但是虛耗很多時間,恐怕講演理論,越講越難明白;所以我今天先把學理暫且放下不說,專拿辦法來講(孫文,1989,第一冊:145)。
所以,作為國家發展建設的理論依據,孫中山思想的長處並不在於蘊含了精深謹嚴的論證,而是如唐君毅所說,展現出「博大平正」的特色。透過寬廣的視野,孫中山周全地掌握了現代性蔓延擴張下,人類世界發展變化的主要脈動和後進國家發展建設所面對的主要問題,析理出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癥結所在,並且提出平實可行的因應方案。
以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來說,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問題的烘托,就是反映現代性挑戰和處理國家發展問題很好的一個分析架構,對當時中國乃至於戰後新興國家在發展建設中所遭遇到的問題,有頗為平實貼切的掌握,充分展現了博大平正的視野。相對而言,馬克思對於現代性的回應採取了歷史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的詮釋與對策,將整個人類歷史的動力歸結到社會結構「下層建築」的物質生產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以三民主義的分析架構來說,就是將文化傳承與人群關係的民族問題,建立與維繫民主政體的民權問題,都視為經濟層面民生問題的附屬議題,沒有獨立析論的價值。以如此的分析架構來處理現代性的生成和演進,其引申出來的對策,當然就只有共產革命一途。所有其他社會變遷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解析中,都可以在邁向共產社會的道路上迎刃而解。
馬克思從唯物論的立場來解釋人類歷史的進程,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統攝工業革命洗禮後現代性的演進,並從階級對立和貧富懸殊來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再以共產社會來號召響往平等境界人士的支持獻身,的確有著思維邏輯上通貫的特色。不過,在孫中山思想的分析架構中,「平等」只是理想社會境界的終極價值之一,在平等之外,還有「自由」與「博愛」。孫中山不同意馬克思將自由和博愛附屬在平等的價值目標之下,化約到經濟或物質的單一軸線上。政治的民主化,或者用孫中山在〈民權主義〉演講中的說法,民權的爭取和普及,本身就是自由、平等與博愛的落實,就牽涉到不平等、假平等和真平等的分辨。所以,國家發展無法只用物質境遇來規劃,必須分成民生、民權和民族的三條脈絡,同時重視平等、自由、和博愛的發揚,朝向「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境界邁進(孫文,1989,第一冊:67-88)。
換句話說,孫中山對於現代性的理解,是將其視為一個綜合性的文明形態,其中有著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個主要發展脈絡,這三個脈絡固然有其相互影響的關聯,如胡漢民所體認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1951),但仍然有其各自分立的運作邏輯。以人類社會的後續演進為鑑,特別是戰後台灣的發展經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瓦解,以及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肆虐,我們不能不說,博大平正的特性使得孫中山思想展現出跨時代的生命力。
貳、調和持中的特性
其次,談到調和持中。博大平正的特性使得孫中山思想對於現代性的理解和回應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對於這種特性,不同立場的評論者會有不同的評價。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從批判的立場評論孫中山思想,認為它是一部折衷主義的作品,混成的大雜燴之作。其中,在民族主義部份,一方面肯定中國的文化傳統,另一方也接納列寧的反帝國主義思想;在民權主義部份,孟德斯鳩主張三權分立的《法意》,和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格言並列;在民生主義部份,享利‧喬治的土地改革主張,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中國的大同思想攜手同行。白吉爾引用孫中山的說法:「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它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然後認為,這種實用主義的拼貼作法使得孫中山思想經常出現首尾不一的情形(白吉爾著,溫洽溢譯,2010:369)。
在肯定孫中山救國救民的理想與熱誠,承認孫中山具有跨文化的溝通與傳播能力的同時,白吉爾批評三民主義不如馬克思主義,或者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來得縝密,認為其既無原創性且缺乏知識上的嚴謹度,所以,論斷孫中山不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白吉爾著,溫洽溢譯,2010:15-17)。
但是,本書作者認為,孫中山思想的兼容並蓄絕非毫無章法的拼貼,其融會各家說法所秉持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理性務實的中庸之道,因而使得孫中山思想具有調和持中的特性。蔡元培(1965)在闡述孫中山思想的時候,就特別強調三民主義的「中和性」,他認為,孫中山思想比歐美的政治道理突出的地方,就在於他受到中國中和的民族性與中和的歷史事實的影響,把中庸的精神貫注到他的理論體系裡去,因而展現出中道溫和的特性,在國家的發展建設上,不走過左或過右的激進路線。
面對現代性的挑戰,當中國的知識界陷入中西文化的體用論辯和全盤取捨的爭執之時,孫中山已經看出執兩用中、截長補短的可能性。所以,當他鼓勵國人學習西方文明之所長,希望迎頭趕上之時,並不認為中國因此必須走上全盤西化之路,而是主張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他接受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但認為中國傳統中的考試和監察制度可以補三權之不足。他嚮往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要求在選舉權之外,還應賦予人民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以充分掌控執政者的去留和政策的興廢,但也強調權能區分,希望給予執政者足夠的運作空間,以建立有能的政府。他反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經濟發展路線,但也不接受共產主義沒收私人財產、消滅資產階級的作法,而是主張防微杜漸和適度的政府干預。這種調和持中的精神,在孫中山的言論和著作中隨處都可以感受得到。
調和持中的特性,使得孫中山思想在剖析問題和提出辦法時,或許不如左右兩側的思想潮流,如共產主義和放任資本主義,來得犀利明快,但也避免了激進思想潮流對社會歷史情境的過當反應和誤入歧途。相較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諸多全盤去留(totalistic)的反傳統思想,以及整體包裹(holistic)的思考模式,孫中山是以相對持平的態度涵詠於現代性和中國文化傳統之間。透過兼容並蓄的思維架構,理性務實地在中西文化之間斟酌取捨,融會出他所期許的中國現代性藍圖和現代化道路。
參、彈性開放的特性
最後,談到彈性開放。由於接受英美教育和醫學的訓練,孫中山的思想具有比較濃厚的英美學術風格,重視經驗事實和科學方法,不同於歐陸學術風格的偏重理念思辨和體系建構。有如徐復觀(1971b:156)的評論,如果我們把思想分成以思辨為主的和以體驗為主的兩種類型的話,孫中山思想顯然比較貼近以體驗為主的類型,並不強調體系哲學般的思想建構。王爾敏(2011b:14;2011c:257)不贊成將三民主義體系化、哲學化,而主張將三民主義當作政治學來解讀,也是同樣的意思。本書作者的體會是,孫中山的思想體系或許不如黑格爾或馬克思等人的思想體系般,形式嚴密通貫,內容繁複深奧,可以形成一套首尾一貫的體系性論述。但是,綜觀現代性擴散的既有經驗,扣緊後進國家的發展條件,從多數人的平常人性出發,孫中山的思想因而更貼近於人類社會的實際需求,更容易接合現實與理想,也比較不會蹈入把觀念遊戲強加於現世人生的陷阱。
由於採取偏向英美經驗主義傳統的認知途徑,所以,孫中山比較能夠抱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在思想體系的建構上保持開放的態度,避免獨斷的傾向(崔垂言,1979:444)。他雖然對於人類知識的發展深具信心,但也明白指出,人類所知有限,尤其在人文社會領域更有待努力。當馬克思和其門徒宣稱不同於前此的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乃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能夠預知歷史演進的規律,指陳人類社會的共同前景的時候,孫中山在〈孫文學說〉的著作中,討論「知行關係」時說:「然而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為尤多也」(孫文,1989,第一冊:401);同時,在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的時候說:「惟現在社會主義尚未若數理、天文學成為完全科學,故現在進行,尚無一定標準,將來苟能成為科學一種,則研究措施更易著手」(孫文,1989,第三冊:98)。
基於前述立場,孫中山先生很清楚任何社會學理的研究或國家發展方案的規劃,都會受到時空背景和人類既有知識的限制,所以,他並不認為他所創建的三民主義或國家建設理論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他在《三民主義》演講本發行的序言中,就囑咐後繼者要「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孫文,1989,第一冊:1)。這種立論態度,使得孫中山思想呈現出頗為彈性開放的特性,給予後繼者相當寬廣的詮釋和修正空間。
肆、對闡述孫中山思想時代意義的基本看法
由於具有前述博大平正、調和持中、與彈性開放的特性,孫中山思想因而能夠展現出跨越時空的生命力。但是,有如本章一開始就提到的,這套學說畢竟是一個世紀之前的產物,百年來,人類世界已經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知識,孫中山思想能否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又如何彰顯其時代意義?
本書作者的看法是,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義不僅植基於其具有跨時空生命力的思想特性,也有賴於後繼者結合時空變化與知識進展的闡揚。有如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學說為放任資本主義的論述開啟了源頭,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著當代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經濟思潮;以及馬克思的學說雖然經歷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衝擊,卻仍然被左派學者用來針砭放任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流弊; 同樣的,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義也需要後繼者能夠「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
本書作者認為,從學科分類和定位的角度來觀察,孫中山思想基本上是一套國家建設與發展的論述,所以,闡揚孫中山思想時代意義的較佳作法之一,是讓孫中山思想和當代的國家發展學說進行對話,相互印證。本書採取孫中山析論國家發展問題的基本分析架構,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三條分析脈絡,來鋪陳本書的章節(但基於論述脈絡起承轉合的考量,先談民生主義,後談民權主義,再談民族主義),分別介紹與該分析脈絡有關之國家發展相關理論,指陳這些理論的長短高下,發掘其與孫中山思想會通或扞格之處,並以海峽兩岸分治之後的發展經驗,作為檢驗理論高下或說服力強弱的依據,從中烘托出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前言
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認為,人類的思想乃是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該思想著落的時代環境背景,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影響或制約,反映著思想建構者特定的歷史處境或社會位置。 孫中山(1866-1925)建立其思想體系的時代距今已近百年,百年來,不僅人類社會產生巨大變化,人類知識更是突飛猛進,孫中山思想到了今天還能夠經得起時代考驗,具有時代意義嗎?這是本書開宗明義想要嘗試回答的問題。
本書作者對於前述問題的基本看法是,雖然孫中山思想是特定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反映著孫中山在特定時代環境下,對於中國發展建設問題的思考,不過,由於孫中山思想本質上的一些特性,使得孫中山思想比較經得起社會變遷的考驗,即使在時代環境變化、人類知識進步之餘,仍然能夠經得起檢驗,展現其歷久彌新的時代意義。這種時代意義的展現,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發展理論演進的情形,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一些趨勢,看得更清楚。
依據前述思維,本書的敍事結構或章節安排如下。首先,從孫中山建構其思想體系的時代環境談起。其次,從意識形態思維方法比較研究的角度(特別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比較),來說明孫中山思想的特性。接著,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發展研究興起的緣由。然後,介紹國家發展研究領域中主要的理論派別,陳明其與孫中山思想相互會通或彼此扞格之處,並以海峽兩岸的發展經驗來檢驗這些說法的長短高下。最後,以意識形態和國家發展關係的分析探討,以及海峽兩岸發展經驗的整體省思,作為結語。
貳、現代性的擴散與回應
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其他革命方略所構成,並以三民主義為理論核心的孫中山思想,從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來看,乃是一套整體性的國家發展理論(the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雖然孫中山建構其思想體系的時空背景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當代國家發展理論則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兩者對應的時空背景並不相同。但是,若將視野拉長放大,其實兩者都可以擺在現代性擴散和回應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
儘管有著不同的體會或界定,學者們大多同意,現代性是伴隨十八和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而來的人類社會組織型態和生活方式的變遷。這種社會變遷揉和了工業革命之前和之後,歐洲人在思想觀念、社會制度和工藝技術上出現的一些歷史現象和演化趨勢,像城市興起(十一到十三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十四到十五世紀)、海外探險和殖民主義(十五到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十四到二十一世紀)、宗教改革(十六世紀)、民族國家(十五到十七世紀)、民主革命(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十七世紀)、和啟蒙運動(十八世紀)等等(黃瑞祺,2001:38-51)。
金耀基(2004:53)認為,啟蒙運動把這種社會大轉型提升到意識層次,建構出一種以理性為基礎,包含自由、民主、公正、人權等價值的文明形態或國家發展方案,可稱之為「啟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或者,採用Jurgen Habermas(1981)的用語,稱之為「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現代性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而具有突破性的生產力和向外蔓延的競爭力,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強勢文明。從制度安排層面來理解現代性,它主要表現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社會形構與人群關係。從社會變遷脈絡來理解現代性,它呈現出下列趨勢:首先,在社會經濟面向上,是都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和科技進步;其次,在政治面向上,是民主政體的建立和維繫;再者,在文化面向上,是世俗化和理性化;最後,在人類群體關係上,是建立民族國家。
Jurgen Habermas(1981)將這一套組織型態和生活方式視為歐洲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社會不斷在追求且尚未完成的方案。Anthony Giddens(1990)認為,這套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模式(modes of social life or organization)大約十七世紀之時從歐洲生成,然後,隨著時間演進不斷向外蔓延,至今已擴及大多數的人類社會,但仍然保有其主要的特性,尚未成為過去。
從上述現代性形成的概括析論出發,我們發現,孫中山思想基本上就是一套回應現代性對中國的挑戰,並追求中國之現代性的國家發展方案。以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來說,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問題的烘托和對應的三個主義的標舉,就是回應現代性挑戰和處理國家發展問題的論述。1904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即指出: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他旋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孫文,1989,第二冊:256)。
這段話所描繪的觀察和前述現代性形成的背景可說是若合符節。值得注意的是,形成現代性的各項質素彼此之間雖然有著某些歷史脈絡的關聯性,或者社會形構的親和性(affinity),但卻非邏輯演繹上環環相扣的必然關係,而是特定歷史社會情境下的輻湊聚合。所以,在擴張的過程中,隨著被影響地區自然和人文條件的差異,現代性的各項質素會遭遇不同程度的迎拒,會出現不同速度的進展,不同深淺的影響,和不同樣貌的組合,因而使得回應現代性擴散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之路,呈現不同的路徑和速度。同時,除了發源地的歐洲之外,現代性在擴張的過程中,也分化出另外一些推波助瀾的據點,像美國、俄國和日本,並且各自展現出本身的現代性特質和現代化路徑,而有所謂「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呈現。 那麼,中國的現代性該如何建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該如何開拓?顯然,這就是孫中山思想要探索的大哉問。
參、探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
從歷史脈絡來觀察,現代性在歐洲成形之後,就以強勢文明的姿態開始向外擴張,並在十九世紀的中葉開始挑戰東方的古老文明國度─中國。中國與西方近代文明的接觸,本可追溯到明朝末年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之交。西元1583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入居廣東肇慶,開啟了西方文明來到中國的先河。隨後,同樣也是義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的艾儒略(Giulio Aleni)和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也分別在1613年和1623年到中國傳教,他們將歐洲天文、數學和地理方面的知識帶進了東方的古老文明。 明朝覆亡,清朝繼起,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主的西方學者仍然絡繹來到中國,並且得到順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重用。後來,由於耶穌會傳教方式改變,並且介入清廷皇位之爭,導致雍正皇帝把康熙皇帝所延攬的大量歐洲學者驅逐淨盡,開始了清朝的閉關自守政策,斷絕了中國學界與西方交往的機會,也使得中西文化交流一度中斷了兩百年(梁啟超,1975:18-19)。在這一段期間裡,缺少外來文明刺激的中國文明逐漸落後給現代性形成中的歐洲文明。
黃仁宇(2006)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認為,明神宗缺乏數字管理的庸碌施政,顯示出由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文明已經呈現出耗弱僵滯的情形,為日後無力因應西方文明的挑戰寫下註腳。但是,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進行交流的期間,中國仍然扮演強有力的角色。當清廷發現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對於中國傳統的人生觀和倫理規範構成挑戰,同時還夾纒著某些政治目的,因而決定加以驅逐之時,西方只能悄然退出。直到中英鴉片戰爭發生之前,西方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俄國等國家都曾嘗試侵入中國,但都無法得逞。此一時期,歐洲的現代性還在醞釀孵化的階段,尚未經歷工業革命的洗禮而塑形摶成。
然而,當十九世紀西潮再度拍打東方古老大陸的邊岸之時,以現代性為主要內涵的西方文明已經經歷了工業革命的洗禮,不再以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謂「陌生的宗教」(strange religion)的姿態出現在中國人面前,而是以「陌生的技器」(strange technology)的面目來敲叩中華帝國的大門(金耀基,1977:1)。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艦隊的炮火轟開了中國閉關的大門,劃下了中西文明對壘強弱異勢的分水嶺,現代性的挑戰成為有意救亡圖存的中國志士仁人必須面對的大變局。從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和李鴻章等人所推動的洋務運動(或稱自強運動),到康有為和梁啟超主張的變法維新,到孫中山所領導的倒滿革命,再到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中國大致依循著器物技能層次、制度層次和思想行為層次的順序,逐步接受了現代性的洗禮(金耀基,1978:183;殷海光,1988)。不過,此一過程並不順遂,甚至於可說是充滿了挫折困頓。
由「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中間經歷了中西文化「體」、「用」上的爭執,變法維新的嘗試,倒滿革命的實現,到新文化運動的呼籲,中國知識界對現代性挑戰的因應態度和理解模式漸次蛻變。從器物技術的學習,到政法制度的仿效,再到思想觀念的爭執和價值理想的批判,中國接受現代性洗禮的現代化之路,不僅荊棘叢生,而且路線紛歧(張朋園,1975)。
從同盟會時期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先後盛行於中國知識圈的西方學說,有淵源於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Montesquieu)、彌勒(John Stuart Mill)、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民主思想;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和杜威(John Dewey)到中國講學,所傳授的邏輯理論和實用主義;有脫胎於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物種起源說,並由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進一步演繹,強調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有以克魯包特金(Peter Kropotkin)的《互助論》(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有以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存在主義思想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有柏格森(Henry Bergson)強調創造和進化不會互相排斥的「創造進化論」;以及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王德昭,1975:182-183)。
在百家爭鳴的中國思想界,面對歐洲現代性和其支流或變體(如俄國和日本之現代性)的洶湧來勢,為了挽救國運的衰蹇、重振民族的生機,曾經有許多志士仁人提出他們的分析判斷和因應方案。在這些努力當中,本書作者認為,能夠憑藉融貫中西的學養, 豐富的海外閱歷,秉持高瞻遠矚的視野,提出理性務實的洞見,為中國的發展建設擘畫出最佳藍圖方案的人,就是孫中山。
不過,有如本節前言提到的,孫中山建立其思想體系的時代距今已有百年,百年來,不僅人類社會產生巨大變化,人類知識更是突飛猛進,孫中山思想到了今天還能夠經得起時代考驗,具有時代意義嗎?本書作者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說,雖然時空背景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國家發展的研究更積累了大量的知識,孫中山思想仍然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甚至於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再來審視孫中山思想,更可以看出孫中山思想的歷久彌新。而孫中山思想之所以能夠經得起時代考驗,展現歷久彌新的意涵,主要在於這套思想體系具有一些可大可久的特性,以下略加申論。
第二節 孫中山思想的特性
從意識形態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本書作者認為,孫中山思想具有三個可大可久的思想建構特性,就是「博大平正」、「調和持中」、以及「彈性開放」,以下分別論列。
壹、博大平正的特性
首先,談到博大平正。過去,從正面態度評價孫中山思想的人,常有孫中山思想「博大精深」的說法,對此,本文作者認為,唐君毅(1976:74)的評語:「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並不以精深見長,但在晚清,與他人相比,則顯然最平正博大,所以才為人們所歸往」,值得參考。另外,徐復觀在談論他對於孫中山思想的體認時表示: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並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發揮了思想上的綜合能力,所以能概括三百年來的政治、社會思想。而是在他的天下為公的「人格之全」中把握到了「天下之全」;由天下之全以指陳天下的需要與其遠景。這是由「天下的實存」來決定思想,而不是以思想去決定「天下的實存」。因此,僅從「知識系統」、「思想系統」等思辨的方向,不能把握到三民主義的真切地意義;而只能從「天下之全」、「人類之全」的真實存在中,才可以加以把握(徐復觀,1971a:150)。
不過,這並不意味孫中山的思想是膚淺或零散的。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另一巨擘,與康有為一起領導立憲派的梁啟超就認為,革命派的孫中山雖然不是個專門做學問的學者,但「眼光極敏銳」(梁啟超,1975:30),並且在與孫中山初識交往之時,受孫中山之影響,幾至脫離康有為的陣營(張朋園,1969:208)。如此眼光敏銳、深具說服力的人,在建構本身的思想體系時,決不至於停留在過於膚淺和片斷的層次。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是,由於孫中山是當時中國思想界極少數直接受英美教育出身的成員,沒有英文的語言障礙,所以,他可以直接涉獵以英文表述的現代性主流思想。同時,孫中山也是同一時代的政治人物中,海外天地接觸最廣,閱歷和體會最深的一位,所以,他可以比同一時代的政治家更廣泛深入地理解現代性。另外,孫中山一生交往的朋友和一起革命的同志,有許多人是當時中國和西方思想界的精英。在中國方面,例如何啟、容閎、鄭觀應、王韜、章太炎、李石曾和歐陽竟無等人,或者與孫中山先生曾經友好相善,或者與孫中山先生有過思想學問上的切磋(唐君毅,1976:79-80;胡秋原,1977:32-33)。在歐美學者方面,孫中山先生除了在倫敦蒙難後駐留英國的期間,與英國思想界的精英,尤其是費邊社的成員,多所往來之外(羅香林,1952:81-84),也曾和美國的杜威討論「知難行易」的問題(孫文,1989,第一冊:381),並和英國的加爾根(Archibald Ross Colquhoun)談論革命方略(孫文,1989,第一冊:391)。
再者,當革命派和立憲派透過《民報》與《新民叢報》論辯中國的改革之路時,孫中山與康有為、梁啟超在路線爭執上的理論交鋒,使得孫中山有機會從康、梁的論述中,獲取豐富本身思想體系的養分。當時,胡漢民、汪精衛、劉光漢等人依循著孫中山的指點,和梁啟超辯詰對話(張朋園,1969:208)。後來,則有戴季陶、吳稚暉、廖仲愷、邵元冲、朱執信、蔡元培、蔣夢麟、和王寵惠等人,服膺並且為文闡釋孫中山思想。
無論是和革命派同志的切磋,或者是和立憲派對手的辯難,乃至於辛亥革命之後對國家建設大業挫折的反省,都必然會促使孫中山將思想觸角延伸到一定的深度,並尋求本身論點的貫通。不過,若從孫中山所遺留之著作和言論資料來看,孫中山思想的確較少深遂精密的論證,最少,和馬克思與恩格思的論著相比,孫中山的論述不夠嚴密通貫。 究其原因,第一,是因為他的完整寫作計畫未能實現;第二,則是因為他希望普及國家建設的理念到俗民大眾。
就第一個原因來說,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演講本發行之時,於「自序」中說道:
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烱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敍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孫文,1989,第一冊:1)。
就第二個原因來說,鄒魯記述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時的一段故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又有一次,總理講民權主義,裡面有一段,我看了不很明白,特意拿了原稿去見總理。我報告來意之後就請他再講一遍。但是總理拿了原稿,問我從什麼地方起,到什麼地方止。我指出後,總理不待思索,立即把這一段全部塗掉。我不明用意,惶急起來請示總理。總理說:「不要這一段」。我問:「為什麼不要?」總理說:「三民主義的學理雖然非常深奧,却要使凡識字的人,個個都能看得懂。這樣,我的主義才能普及民眾,然後始能望其實現。假使你都看不清楚,那末看不懂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全部刪去。」很多人批評三民主義的文字太淺顯,並且還有建議修改的,知道總理這一段話,當然可以恍然大悟,明白三民主義的文字為什麼淺顯的理由了(鄒魯,1967:325)。
同樣的例子,也曾出現在其他場合。例如,孫中山先生在演講〈民生主義〉第二講的時候就說:
民生主義這個問題,如果要從學理上詳細來講,就是講十天或二十天也講不完全。況且這種學理,現在還是沒有定論的,所以單就學理來講,不但是虛耗很多時間,恐怕講演理論,越講越難明白;所以我今天先把學理暫且放下不說,專拿辦法來講(孫文,1989,第一冊:145)。
所以,作為國家發展建設的理論依據,孫中山思想的長處並不在於蘊含了精深謹嚴的論證,而是如唐君毅所說,展現出「博大平正」的特色。透過寬廣的視野,孫中山周全地掌握了現代性蔓延擴張下,人類世界發展變化的主要脈動和後進國家發展建設所面對的主要問題,析理出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癥結所在,並且提出平實可行的因應方案。
以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來說,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問題的烘托,就是反映現代性挑戰和處理國家發展問題很好的一個分析架構,對當時中國乃至於戰後新興國家在發展建設中所遭遇到的問題,有頗為平實貼切的掌握,充分展現了博大平正的視野。相對而言,馬克思對於現代性的回應採取了歷史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的詮釋與對策,將整個人類歷史的動力歸結到社會結構「下層建築」的物質生產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以三民主義的分析架構來說,就是將文化傳承與人群關係的民族問題,建立與維繫民主政體的民權問題,都視為經濟層面民生問題的附屬議題,沒有獨立析論的價值。以如此的分析架構來處理現代性的生成和演進,其引申出來的對策,當然就只有共產革命一途。所有其他社會變遷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解析中,都可以在邁向共產社會的道路上迎刃而解。
馬克思從唯物論的立場來解釋人類歷史的進程,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統攝工業革命洗禮後現代性的演進,並從階級對立和貧富懸殊來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再以共產社會來號召響往平等境界人士的支持獻身,的確有著思維邏輯上通貫的特色。不過,在孫中山思想的分析架構中,「平等」只是理想社會境界的終極價值之一,在平等之外,還有「自由」與「博愛」。孫中山不同意馬克思將自由和博愛附屬在平等的價值目標之下,化約到經濟或物質的單一軸線上。政治的民主化,或者用孫中山在〈民權主義〉演講中的說法,民權的爭取和普及,本身就是自由、平等與博愛的落實,就牽涉到不平等、假平等和真平等的分辨。所以,國家發展無法只用物質境遇來規劃,必須分成民生、民權和民族的三條脈絡,同時重視平等、自由、和博愛的發揚,朝向「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境界邁進(孫文,1989,第一冊:67-88)。
換句話說,孫中山對於現代性的理解,是將其視為一個綜合性的文明形態,其中有著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個主要發展脈絡,這三個脈絡固然有其相互影響的關聯,如胡漢民所體認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1951),但仍然有其各自分立的運作邏輯。以人類社會的後續演進為鑑,特別是戰後台灣的發展經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瓦解,以及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肆虐,我們不能不說,博大平正的特性使得孫中山思想展現出跨時代的生命力。
貳、調和持中的特性
其次,談到調和持中。博大平正的特性使得孫中山思想對於現代性的理解和回應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對於這種特性,不同立場的評論者會有不同的評價。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從批判的立場評論孫中山思想,認為它是一部折衷主義的作品,混成的大雜燴之作。其中,在民族主義部份,一方面肯定中國的文化傳統,另一方也接納列寧的反帝國主義思想;在民權主義部份,孟德斯鳩主張三權分立的《法意》,和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格言並列;在民生主義部份,享利‧喬治的土地改革主張,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中國的大同思想攜手同行。白吉爾引用孫中山的說法:「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它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然後認為,這種實用主義的拼貼作法使得孫中山思想經常出現首尾不一的情形(白吉爾著,溫洽溢譯,2010:369)。
在肯定孫中山救國救民的理想與熱誠,承認孫中山具有跨文化的溝通與傳播能力的同時,白吉爾批評三民主義不如馬克思主義,或者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來得縝密,認為其既無原創性且缺乏知識上的嚴謹度,所以,論斷孫中山不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白吉爾著,溫洽溢譯,2010:15-17)。
但是,本書作者認為,孫中山思想的兼容並蓄絕非毫無章法的拼貼,其融會各家說法所秉持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理性務實的中庸之道,因而使得孫中山思想具有調和持中的特性。蔡元培(1965)在闡述孫中山思想的時候,就特別強調三民主義的「中和性」,他認為,孫中山思想比歐美的政治道理突出的地方,就在於他受到中國中和的民族性與中和的歷史事實的影響,把中庸的精神貫注到他的理論體系裡去,因而展現出中道溫和的特性,在國家的發展建設上,不走過左或過右的激進路線。
面對現代性的挑戰,當中國的知識界陷入中西文化的體用論辯和全盤取捨的爭執之時,孫中山已經看出執兩用中、截長補短的可能性。所以,當他鼓勵國人學習西方文明之所長,希望迎頭趕上之時,並不認為中國因此必須走上全盤西化之路,而是主張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他接受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但認為中國傳統中的考試和監察制度可以補三權之不足。他嚮往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要求在選舉權之外,還應賦予人民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以充分掌控執政者的去留和政策的興廢,但也強調權能區分,希望給予執政者足夠的運作空間,以建立有能的政府。他反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經濟發展路線,但也不接受共產主義沒收私人財產、消滅資產階級的作法,而是主張防微杜漸和適度的政府干預。這種調和持中的精神,在孫中山的言論和著作中隨處都可以感受得到。
調和持中的特性,使得孫中山思想在剖析問題和提出辦法時,或許不如左右兩側的思想潮流,如共產主義和放任資本主義,來得犀利明快,但也避免了激進思想潮流對社會歷史情境的過當反應和誤入歧途。相較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諸多全盤去留(totalistic)的反傳統思想,以及整體包裹(holistic)的思考模式,孫中山是以相對持平的態度涵詠於現代性和中國文化傳統之間。透過兼容並蓄的思維架構,理性務實地在中西文化之間斟酌取捨,融會出他所期許的中國現代性藍圖和現代化道路。
參、彈性開放的特性
最後,談到彈性開放。由於接受英美教育和醫學的訓練,孫中山的思想具有比較濃厚的英美學術風格,重視經驗事實和科學方法,不同於歐陸學術風格的偏重理念思辨和體系建構。有如徐復觀(1971b:156)的評論,如果我們把思想分成以思辨為主的和以體驗為主的兩種類型的話,孫中山思想顯然比較貼近以體驗為主的類型,並不強調體系哲學般的思想建構。王爾敏(2011b:14;2011c:257)不贊成將三民主義體系化、哲學化,而主張將三民主義當作政治學來解讀,也是同樣的意思。本書作者的體會是,孫中山的思想體系或許不如黑格爾或馬克思等人的思想體系般,形式嚴密通貫,內容繁複深奧,可以形成一套首尾一貫的體系性論述。但是,綜觀現代性擴散的既有經驗,扣緊後進國家的發展條件,從多數人的平常人性出發,孫中山的思想因而更貼近於人類社會的實際需求,更容易接合現實與理想,也比較不會蹈入把觀念遊戲強加於現世人生的陷阱。
由於採取偏向英美經驗主義傳統的認知途徑,所以,孫中山比較能夠抱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在思想體系的建構上保持開放的態度,避免獨斷的傾向(崔垂言,1979:444)。他雖然對於人類知識的發展深具信心,但也明白指出,人類所知有限,尤其在人文社會領域更有待努力。當馬克思和其門徒宣稱不同於前此的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乃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能夠預知歷史演進的規律,指陳人類社會的共同前景的時候,孫中山在〈孫文學說〉的著作中,討論「知行關係」時說:「然而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為尤多也」(孫文,1989,第一冊:401);同時,在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的時候說:「惟現在社會主義尚未若數理、天文學成為完全科學,故現在進行,尚無一定標準,將來苟能成為科學一種,則研究措施更易著手」(孫文,1989,第三冊:98)。
基於前述立場,孫中山先生很清楚任何社會學理的研究或國家發展方案的規劃,都會受到時空背景和人類既有知識的限制,所以,他並不認為他所創建的三民主義或國家建設理論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他在《三民主義》演講本發行的序言中,就囑咐後繼者要「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孫文,1989,第一冊:1)。這種立論態度,使得孫中山思想呈現出頗為彈性開放的特性,給予後繼者相當寬廣的詮釋和修正空間。
肆、對闡述孫中山思想時代意義的基本看法
由於具有前述博大平正、調和持中、與彈性開放的特性,孫中山思想因而能夠展現出跨越時空的生命力。但是,有如本章一開始就提到的,這套學說畢竟是一個世紀之前的產物,百年來,人類世界已經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也產生了許多新的知識,孫中山思想能否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又如何彰顯其時代意義?
本書作者的看法是,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義不僅植基於其具有跨時空生命力的思想特性,也有賴於後繼者結合時空變化與知識進展的闡揚。有如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學說為放任資本主義的論述開啟了源頭,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著當代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經濟思潮;以及馬克思的學說雖然經歷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衝擊,卻仍然被左派學者用來針砭放任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流弊; 同樣的,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義也需要後繼者能夠「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
本書作者認為,從學科分類和定位的角度來觀察,孫中山思想基本上是一套國家建設與發展的論述,所以,闡揚孫中山思想時代意義的較佳作法之一,是讓孫中山思想和當代的國家發展學說進行對話,相互印證。本書採取孫中山析論國家發展問題的基本分析架構,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三條分析脈絡,來鋪陳本書的章節(但基於論述脈絡起承轉合的考量,先談民生主義,後談民權主義,再談民族主義),分別介紹與該分析脈絡有關之國家發展相關理論,指陳這些理論的長短高下,發掘其與孫中山思想會通或扞格之處,並以海峽兩岸分治之後的發展經驗,作為檢驗理論高下或說服力強弱的依據,從中烘托出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