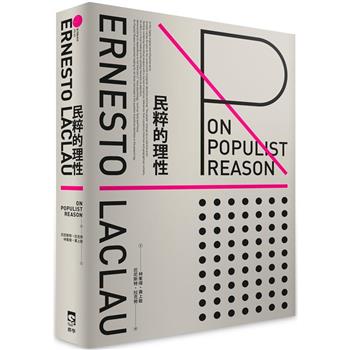第一章 民粹主義:曖昧與弔詭
上述論證也適用於「意識型態」與「運動」兩者之間的區分,這個區辨是米諾格文章中另個關鍵──他想藉由這組區分警告我們,研究社會運動時,要提防不要「落入意識型態」的圈套。雖說如此,我們又要如何將「意識型態」與「運動」嚴格區分開來?此外,這組區分會讓我們清楚地回想起另一組更古老的區分:人們腦袋裡的觀念,與他們所參與的行動。只不過,這組古老區分也不太站得住腳。從維根斯坦以來,我們便知道,語言遊戲涵蓋了語言的交流以及語言鑲嵌於其中的行動,同時言說行動(speech act)理論也以嶄新的方式,看待論述序列如何構成社會制度生活。正是在此意義下,珊妲.慕孚與我才把論述(discourse)定義成結構化的總體(structured totalities),它同時接合了語言與非語言的各種元素。由此可見,將意識型態與運動區分開來,既是無望之舉,也顯得無甚用處──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否確立出某些論述序列,並指出社會的力量與運動如何透過它們,施展出完整的政治操演。
顯然,我之所以質疑米諾格的區分,是因為那些區分不過是反映出民粹主義文獻的一種廣泛態度,另個原因則是,我嘗試顛覆既有的分析視角:我不願一開始就從政治理性的角度著眼,那種作法試圖突顯出民粹主義欠缺的諸多成分──將它看成模糊、意識型態上空泛、反智主義,或短暫的現象──同時,我還打算利用一般化的修辭(我們之後會稱這種修辭為「霸權」)來擴大解釋模型,亦即延伸理性的定義,好讓民粹主義能看起來很特殊,卻又是政治生活的結構化所存在的一種可能性。把民粹主義僅僅當成異常、偏差或操弄的眾多取徑,與我所採用的分析策略,可說是完全不相容。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沃斯利的文章令人尤其耳目一新。在〈民粹主義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pulism)一文,沃斯利的論證雖然止於描述性的說明,尚未嘗試在概念上釐清民粹主義概念的特殊性,但他發出的不滿之聲,即使仍很粗略,在我看來卻甚為完備。其中有三點很具前瞻性。
1. 他不再執著於單純的概念內容分析,轉而處理諸概念在特定文化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亦即這些概念是如何隨著文化脈絡轉變其用途,同時也改變它們的知識內容。
『這意味著,情況與我們所知相反。當一些概念被吸收到某些綿延不斷的文化脈絡中,而該脈絡有別於那些概念誕生乃至於茁壯的原生脈絡時,這些概念就具備了不同的社會學意義,因為他們會被吸納到新的行動框架中,進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使用;且不只是這樣,這些概念本身的內容也會受到修整,因為它們勢必需要和其他心理裝置(psychic furniture)接合,心理裝置是指:既有的「利害關係」(interest)、認知元素或結構,或是有效力的行為傾向等等,這些心理裝置皆屬於接受概念的環境之一部分。由此可知,原初的概念在上述過程中必然面臨修整,最終轉變成為不同的概念。』
上述論證著實重要。我們的任務與其說是進行不同概念體系之間,概念本身的比較,不如說是深究這些概念體系的操演面向。舉例來說,民粹主義擁有相對簡單且空泛的意識型態,雖然這往往預示著某種對菁英主義的鄙視,但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卻是,那些簡化與空泛化的過程如何操演出來,換言之,這兩種過程表現出何種社會理性。
2. 沃斯利不把民粹主義視為某種類型的組織或意識型態,並將它與其他類型的意識型態做比較(例如,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反之,他把民粹主義看做政治文化的某個維度,它總是持續存在於各種運動之中,即使這些運動擁有著不同的意識型態符號:
『民粹主義這個症候群……它可以表現出的樣態,遠遠超乎特定政策、意識型態體系或政體(民主、極權…),所能給定的形式或脈絡。這意味著我們最好將民粹主義看做是廣泛政治文化的一個面向,而非某種全面性的意識型態或組織。當然,我們還是可以建立各種民粹主義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s),而可能還是有特定政治文化與結構案例,比較貼近這些類型,例如那些早已被標定為「民粹主義」的現象。』
此一分析步驟是關鍵所在。倘若沃斯利的論證正確──我認為正是如此──那麼嘗試找出民粹主義所包含的普遍屬性,顯然是一種瘋狂之舉:如我們所見,既有文獻不斷試圖指認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雖然最終是找到了,但人們很快就發現,這些所謂的「民粹主義」運動,彼此的社會基礎卻南轅北轍。換個角度來說,倘若研究者嘗試避免上述的困境,僅僅把民粹主義當作某個可以跨越意識型態與社會差異的維度(dimension),那麼研究者的責任,便是如何標示出這個維度的內涵──這一點是沃斯利尚未做到的,至少,他還沒能提出那麼有效且令人信服的分析。
3. 上述兩點既使得沃斯利有別於古典的研究取徑,也讓他得以採取其他幾個有效的分析步驟。此處我僅僅指出兩點。一是對於第三世界民粹主義的分析:「相較於已開發國家,以社會經濟面向所界定出的階級,在第三世界並不是關鍵的社會實存(entity)。……所以說,階級鬥爭是個不甚重要的概念」。
當然,對於沃斯利來說,即使他未給出自己的看法,上述的論證所涉及到的確實是第三世界的意識型態。只是,列寧在分析俄國農民時,曾指出社會經濟區隔與社會政治連帶之間是重疊的,對於這種重疊現象與其適用的範圍,沃斯利則持批評立場,由此可見他拒斥第三世界民粹主義運動所標榜的階級鬥爭,同時藉由田野資料他也說明了其中乃存在著「虛假意識」,甚至指出將階級鬥爭視為政治動員的普遍綱領是有實際困難的。
我想要提及的第二點則是,沃斯利盡力避免以下這種化約論的廉價作法,也就是把操弄的虛假面向,當作民粹主義的必要成分。如他所說,
『分析民粹主義若要看起來更加引人入勝,……我們可以修改一下希爾斯對民粹主義的定義,民粹主義除了包含「虛假參與」(譬如政治煽動,或「電視治國」),也包含真正且有效的大眾參與,這兩種參與必須要區別清楚。於是乎,「民粹主義」這個概念既關乎人民與領袖之間的「直接」交流(當此等交流發生在較為複雜且規模更廣大的社會中,神秘化與象徵化,勢必將取得主導地位),在更廣泛的情況下,也涉及普遍的大眾參與(包括虛假參與)。』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讓我們在分析民粹主義時,能夠消除某些必然出現且帶有倫理色彩的指控──這些指控如我們所知道的,常常根植於看似「客觀」的分析之中。
找尋替代取徑
我們已快速回顧過相關文獻,雖說顯然並不完整。接下來我們將採取不一樣的視角,以便避開既有研究的死胡同。為了達成此一任務,我們首先會質疑──有時甚至會翻轉──民粹主義研究所立基的若干預設,並探究這些論述如何害分析走進死路。以下先考慮兩個基本的要點:
1. 首先,我們應當反問自己,民粹主義之所以(幾乎)無法定義,是否是因為既有文獻在從概念上理解民粹主義時,就讓民粹主義政治邏輯內含的某種理性,在分析之前(a priori,或譯先驗)就被排除。我認為這種狀況是存在的。倘若我們僅僅把民粹主義描繪成「模糊不清」、「意義不精確」、「知識上貧瘠」、「暫時性」的現象、充斥「操弄」程序……那麼,我們就無法從正面角度界定民粹主義的特殊本質(differentia specifica)。反觀既有文獻,它們好像只是為了區分「政治行動中可以理解且符合理性」的部分,以及「與之對立」的部分:民粹主義遂被當成非理性、無法定義的現象。一旦採取它們這種分析策略,「何謂民粹主義」的問題就會被另一個問題取代,亦即,「民粹主義究竟能套用於何種意識型態或社會現實?」由於它們已經排除所有內含於民粹主義之中的理性,所以解釋項完全只能存在於被解釋項之外。然而,在套用分類範疇時,還是必須假定存在著某種外部關連,才能證明這樣的套用合理,因此上述的問題通常又會被第三種說法所取代:「民粹主義是哪種社會實在或情境的表現?」論證到達了這種地步,民粹主義將無疑地被認定成附帶現象。對這樣的取徑來說,民粹主義的形式根本不需要額外解釋──「為什麼某些政治替代方案或目標,非得採取民粹主義這種手段,才能表現出來?」──這類提問根本不會成立。大家就只會談民粹主義表現出何種社會內容(例如,階級或其他社會部門的利益),而對於這種表現形式為何是必需的,大家仍然不清楚。此時,我們所身處的情況和馬克思描繪的一種關係很相似,那就是價值理論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角色:古典政治經濟學有能力指出,勞動是價值的實質(substance),它卻無法解釋,這個隱藏在底下的實質,為何必須藉由諸多等價物所形成的交換形式,方能表現出自身?至此,人們通常只剩下一些前文回顧過的、不太可靠的選項:要麼,把民粹主義限縮成它的其中一種歷史變體;要麼,試著提出一體適用(general)的定義,而該定義卻往往顯得過於狹隘。在後者的狀況中,文獻作者們通常會弄巧成拙,轉而採取前述的那種作法:在「民粹主義」這個標籤之下列出一堆頗不相關的運動,卻沒有詳細說明民粹主義是什麼。
2. 為了不要用貶抑的方式看待民粹主義,我們的第一步亦不在於否認幾個用來描繪民粹主義的分類範疇,諸如「模糊」、「意義不精確」等等,而是在承認這些分類範疇的表面意義之餘,也要駁斥它們所根植的偏見。換言之,我們不會將「模糊」的民粹主義直接與成熟的政治邏輯對立起來,後者意指精確程度很高的制度性決策之治理,反之,首先倒應當追問自己一系列不同於現有文獻的基本問題:「民粹主義論述之所以如此模糊,是否是因為社會現實本身在某些情況下也如此模糊與不確定?」假設情況真是如此,「那麼與其說民粹主義是一種拙劣的政治或意識型態上的操作,不如說它可能是某種擁有自身理性的操演行動,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模糊正是建構重要政治意義的前提?」最後,「民粹主義真的僅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產物,來自於不成熟的社會行動者,而最終將遭遇到被取代的命運,還是說,長久以來它都是政治行動的某個面向,無可避免地浮現在所有的政治論述之中(程度可能有別),一方面顛覆所謂「成熟」之意識型態,另一方面也把它們變得更複雜?」以下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
研究者常認定民粹主義「簡化」了政治空間,並且利用僵硬的二分法(dichotomy),取代政治差異與政治決策所形成的複雜組合,並且,這個二分法的兩端往往在定義上並不精確。舉例來說,1945年,裴隆將軍採取民族主義的立場,並宣稱阿根廷面臨布雷登與裴隆二選一的局面(布雷登時任美國駐阿根廷大使)。後來的發展正如我們所知,這種把兩個人物當成對立選項的特徵,也藉由別種二分法,出現在不同論述中,例如,人民對抗寡頭、勞苦大眾對抗剝削者等等。我們會發現,無論是這些二分法,還是那些構成政治-意識型態疆界的二分法,皆發揮了簡化政治空間的效果(所有的社會奇異性〔singularity〕都會揀取二分法中任何一端,圍繞著它,進行集結),而所有二分法所包含的兩個端點也必然是意義不精確的(如若不然,二分法就無法涵蓋所有特殊性,自然也無法重組它們)。只不過,情況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到,會不會正是由於簡化、詞彙意義不精確的〔運作〕邏輯,才讓政治行動得以成形?設想有個架空的世界,其中政治完全遭到行政取代,為了處理特殊化的差異而發起的政治工程即使零散,卻足以消弭諸多敵對式二分法,只有在這種世界中,「意義不精確」或「簡化」才真正可能在公共領域之中被抹消。但這例子恰恰告訴我們,民粹主義這樣的標籤將反過來凸顯出,這種政治邏輯就是「政治」的必要成分。
如我們所知,另一種忽視民粹主義的作法,是「只把它當作修辭」。然而,也如同前文所述,我們能夠利用非修辭性的方式來描繪社會現實,但任何比喻的運用絕不可能僅止於妝點社會現實,因此比喻的運用可以被視作構成政治身分的一種邏輯。讓我們以隱喻為例子進行說明。我們知道,基於類比的原則,隱喻能建立起詞彙之間的替換關係。於此,就像我說過的,不同的身分或利益常會依循著二分法的結構,環繞著二元對立的其中一端,作為等同的差異(equivalential differences)來進行重組。例如,「人民」當中存在著不同群體,而每個群體碰到的糟糕處境並不一樣,但只有在他們面對「寡頭」之時,這些壞事才被視為等同嚴重。而這就相當於說,不同經驗唯有在面對寡頭權力時,才會彼此類比。然而,如果它不僅是一種比喻上的累加呢?無疑,當制度化程度較高的論述逐漸被建立起來,上述這種等同關係便會面臨到被拆解的命運,而在拆解等同性的過程中,人們仍舊會運用修辭工具,只是種類不同罷了。因此,這些工具絕不只是修辭而已,它們所根植的邏輯,事實上主宰著所有政治空間的構成與解組。
上述論證也適用於「意識型態」與「運動」兩者之間的區分,這個區辨是米諾格文章中另個關鍵──他想藉由這組區分警告我們,研究社會運動時,要提防不要「落入意識型態」的圈套。雖說如此,我們又要如何將「意識型態」與「運動」嚴格區分開來?此外,這組區分會讓我們清楚地回想起另一組更古老的區分:人們腦袋裡的觀念,與他們所參與的行動。只不過,這組古老區分也不太站得住腳。從維根斯坦以來,我們便知道,語言遊戲涵蓋了語言的交流以及語言鑲嵌於其中的行動,同時言說行動(speech act)理論也以嶄新的方式,看待論述序列如何構成社會制度生活。正是在此意義下,珊妲.慕孚與我才把論述(discourse)定義成結構化的總體(structured totalities),它同時接合了語言與非語言的各種元素。由此可見,將意識型態與運動區分開來,既是無望之舉,也顯得無甚用處──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否確立出某些論述序列,並指出社會的力量與運動如何透過它們,施展出完整的政治操演。
顯然,我之所以質疑米諾格的區分,是因為那些區分不過是反映出民粹主義文獻的一種廣泛態度,另個原因則是,我嘗試顛覆既有的分析視角:我不願一開始就從政治理性的角度著眼,那種作法試圖突顯出民粹主義欠缺的諸多成分──將它看成模糊、意識型態上空泛、反智主義,或短暫的現象──同時,我還打算利用一般化的修辭(我們之後會稱這種修辭為「霸權」)來擴大解釋模型,亦即延伸理性的定義,好讓民粹主義能看起來很特殊,卻又是政治生活的結構化所存在的一種可能性。把民粹主義僅僅當成異常、偏差或操弄的眾多取徑,與我所採用的分析策略,可說是完全不相容。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沃斯利的文章令人尤其耳目一新。在〈民粹主義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pulism)一文,沃斯利的論證雖然止於描述性的說明,尚未嘗試在概念上釐清民粹主義概念的特殊性,但他發出的不滿之聲,即使仍很粗略,在我看來卻甚為完備。其中有三點很具前瞻性。
1. 他不再執著於單純的概念內容分析,轉而處理諸概念在特定文化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亦即這些概念是如何隨著文化脈絡轉變其用途,同時也改變它們的知識內容。
『這意味著,情況與我們所知相反。當一些概念被吸收到某些綿延不斷的文化脈絡中,而該脈絡有別於那些概念誕生乃至於茁壯的原生脈絡時,這些概念就具備了不同的社會學意義,因為他們會被吸納到新的行動框架中,進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使用;且不只是這樣,這些概念本身的內容也會受到修整,因為它們勢必需要和其他心理裝置(psychic furniture)接合,心理裝置是指:既有的「利害關係」(interest)、認知元素或結構,或是有效力的行為傾向等等,這些心理裝置皆屬於接受概念的環境之一部分。由此可知,原初的概念在上述過程中必然面臨修整,最終轉變成為不同的概念。』
上述論證著實重要。我們的任務與其說是進行不同概念體系之間,概念本身的比較,不如說是深究這些概念體系的操演面向。舉例來說,民粹主義擁有相對簡單且空泛的意識型態,雖然這往往預示著某種對菁英主義的鄙視,但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卻是,那些簡化與空泛化的過程如何操演出來,換言之,這兩種過程表現出何種社會理性。
2. 沃斯利不把民粹主義視為某種類型的組織或意識型態,並將它與其他類型的意識型態做比較(例如,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反之,他把民粹主義看做政治文化的某個維度,它總是持續存在於各種運動之中,即使這些運動擁有著不同的意識型態符號:
『民粹主義這個症候群……它可以表現出的樣態,遠遠超乎特定政策、意識型態體系或政體(民主、極權…),所能給定的形式或脈絡。這意味著我們最好將民粹主義看做是廣泛政治文化的一個面向,而非某種全面性的意識型態或組織。當然,我們還是可以建立各種民粹主義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s),而可能還是有特定政治文化與結構案例,比較貼近這些類型,例如那些早已被標定為「民粹主義」的現象。』
此一分析步驟是關鍵所在。倘若沃斯利的論證正確──我認為正是如此──那麼嘗試找出民粹主義所包含的普遍屬性,顯然是一種瘋狂之舉:如我們所見,既有文獻不斷試圖指認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雖然最終是找到了,但人們很快就發現,這些所謂的「民粹主義」運動,彼此的社會基礎卻南轅北轍。換個角度來說,倘若研究者嘗試避免上述的困境,僅僅把民粹主義當作某個可以跨越意識型態與社會差異的維度(dimension),那麼研究者的責任,便是如何標示出這個維度的內涵──這一點是沃斯利尚未做到的,至少,他還沒能提出那麼有效且令人信服的分析。
3. 上述兩點既使得沃斯利有別於古典的研究取徑,也讓他得以採取其他幾個有效的分析步驟。此處我僅僅指出兩點。一是對於第三世界民粹主義的分析:「相較於已開發國家,以社會經濟面向所界定出的階級,在第三世界並不是關鍵的社會實存(entity)。……所以說,階級鬥爭是個不甚重要的概念」。
當然,對於沃斯利來說,即使他未給出自己的看法,上述的論證所涉及到的確實是第三世界的意識型態。只是,列寧在分析俄國農民時,曾指出社會經濟區隔與社會政治連帶之間是重疊的,對於這種重疊現象與其適用的範圍,沃斯利則持批評立場,由此可見他拒斥第三世界民粹主義運動所標榜的階級鬥爭,同時藉由田野資料他也說明了其中乃存在著「虛假意識」,甚至指出將階級鬥爭視為政治動員的普遍綱領是有實際困難的。
我想要提及的第二點則是,沃斯利盡力避免以下這種化約論的廉價作法,也就是把操弄的虛假面向,當作民粹主義的必要成分。如他所說,
『分析民粹主義若要看起來更加引人入勝,……我們可以修改一下希爾斯對民粹主義的定義,民粹主義除了包含「虛假參與」(譬如政治煽動,或「電視治國」),也包含真正且有效的大眾參與,這兩種參與必須要區別清楚。於是乎,「民粹主義」這個概念既關乎人民與領袖之間的「直接」交流(當此等交流發生在較為複雜且規模更廣大的社會中,神秘化與象徵化,勢必將取得主導地位),在更廣泛的情況下,也涉及普遍的大眾參與(包括虛假參與)。』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讓我們在分析民粹主義時,能夠消除某些必然出現且帶有倫理色彩的指控──這些指控如我們所知道的,常常根植於看似「客觀」的分析之中。
找尋替代取徑
我們已快速回顧過相關文獻,雖說顯然並不完整。接下來我們將採取不一樣的視角,以便避開既有研究的死胡同。為了達成此一任務,我們首先會質疑──有時甚至會翻轉──民粹主義研究所立基的若干預設,並探究這些論述如何害分析走進死路。以下先考慮兩個基本的要點:
1. 首先,我們應當反問自己,民粹主義之所以(幾乎)無法定義,是否是因為既有文獻在從概念上理解民粹主義時,就讓民粹主義政治邏輯內含的某種理性,在分析之前(a priori,或譯先驗)就被排除。我認為這種狀況是存在的。倘若我們僅僅把民粹主義描繪成「模糊不清」、「意義不精確」、「知識上貧瘠」、「暫時性」的現象、充斥「操弄」程序……那麼,我們就無法從正面角度界定民粹主義的特殊本質(differentia specifica)。反觀既有文獻,它們好像只是為了區分「政治行動中可以理解且符合理性」的部分,以及「與之對立」的部分:民粹主義遂被當成非理性、無法定義的現象。一旦採取它們這種分析策略,「何謂民粹主義」的問題就會被另一個問題取代,亦即,「民粹主義究竟能套用於何種意識型態或社會現實?」由於它們已經排除所有內含於民粹主義之中的理性,所以解釋項完全只能存在於被解釋項之外。然而,在套用分類範疇時,還是必須假定存在著某種外部關連,才能證明這樣的套用合理,因此上述的問題通常又會被第三種說法所取代:「民粹主義是哪種社會實在或情境的表現?」論證到達了這種地步,民粹主義將無疑地被認定成附帶現象。對這樣的取徑來說,民粹主義的形式根本不需要額外解釋──「為什麼某些政治替代方案或目標,非得採取民粹主義這種手段,才能表現出來?」──這類提問根本不會成立。大家就只會談民粹主義表現出何種社會內容(例如,階級或其他社會部門的利益),而對於這種表現形式為何是必需的,大家仍然不清楚。此時,我們所身處的情況和馬克思描繪的一種關係很相似,那就是價值理論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角色:古典政治經濟學有能力指出,勞動是價值的實質(substance),它卻無法解釋,這個隱藏在底下的實質,為何必須藉由諸多等價物所形成的交換形式,方能表現出自身?至此,人們通常只剩下一些前文回顧過的、不太可靠的選項:要麼,把民粹主義限縮成它的其中一種歷史變體;要麼,試著提出一體適用(general)的定義,而該定義卻往往顯得過於狹隘。在後者的狀況中,文獻作者們通常會弄巧成拙,轉而採取前述的那種作法:在「民粹主義」這個標籤之下列出一堆頗不相關的運動,卻沒有詳細說明民粹主義是什麼。
2. 為了不要用貶抑的方式看待民粹主義,我們的第一步亦不在於否認幾個用來描繪民粹主義的分類範疇,諸如「模糊」、「意義不精確」等等,而是在承認這些分類範疇的表面意義之餘,也要駁斥它們所根植的偏見。換言之,我們不會將「模糊」的民粹主義直接與成熟的政治邏輯對立起來,後者意指精確程度很高的制度性決策之治理,反之,首先倒應當追問自己一系列不同於現有文獻的基本問題:「民粹主義論述之所以如此模糊,是否是因為社會現實本身在某些情況下也如此模糊與不確定?」假設情況真是如此,「那麼與其說民粹主義是一種拙劣的政治或意識型態上的操作,不如說它可能是某種擁有自身理性的操演行動,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模糊正是建構重要政治意義的前提?」最後,「民粹主義真的僅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產物,來自於不成熟的社會行動者,而最終將遭遇到被取代的命運,還是說,長久以來它都是政治行動的某個面向,無可避免地浮現在所有的政治論述之中(程度可能有別),一方面顛覆所謂「成熟」之意識型態,另一方面也把它們變得更複雜?」以下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
研究者常認定民粹主義「簡化」了政治空間,並且利用僵硬的二分法(dichotomy),取代政治差異與政治決策所形成的複雜組合,並且,這個二分法的兩端往往在定義上並不精確。舉例來說,1945年,裴隆將軍採取民族主義的立場,並宣稱阿根廷面臨布雷登與裴隆二選一的局面(布雷登時任美國駐阿根廷大使)。後來的發展正如我們所知,這種把兩個人物當成對立選項的特徵,也藉由別種二分法,出現在不同論述中,例如,人民對抗寡頭、勞苦大眾對抗剝削者等等。我們會發現,無論是這些二分法,還是那些構成政治-意識型態疆界的二分法,皆發揮了簡化政治空間的效果(所有的社會奇異性〔singularity〕都會揀取二分法中任何一端,圍繞著它,進行集結),而所有二分法所包含的兩個端點也必然是意義不精確的(如若不然,二分法就無法涵蓋所有特殊性,自然也無法重組它們)。只不過,情況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到,會不會正是由於簡化、詞彙意義不精確的〔運作〕邏輯,才讓政治行動得以成形?設想有個架空的世界,其中政治完全遭到行政取代,為了處理特殊化的差異而發起的政治工程即使零散,卻足以消弭諸多敵對式二分法,只有在這種世界中,「意義不精確」或「簡化」才真正可能在公共領域之中被抹消。但這例子恰恰告訴我們,民粹主義這樣的標籤將反過來凸顯出,這種政治邏輯就是「政治」的必要成分。
如我們所知,另一種忽視民粹主義的作法,是「只把它當作修辭」。然而,也如同前文所述,我們能夠利用非修辭性的方式來描繪社會現實,但任何比喻的運用絕不可能僅止於妝點社會現實,因此比喻的運用可以被視作構成政治身分的一種邏輯。讓我們以隱喻為例子進行說明。我們知道,基於類比的原則,隱喻能建立起詞彙之間的替換關係。於此,就像我說過的,不同的身分或利益常會依循著二分法的結構,環繞著二元對立的其中一端,作為等同的差異(equivalential differences)來進行重組。例如,「人民」當中存在著不同群體,而每個群體碰到的糟糕處境並不一樣,但只有在他們面對「寡頭」之時,這些壞事才被視為等同嚴重。而這就相當於說,不同經驗唯有在面對寡頭權力時,才會彼此類比。然而,如果它不僅是一種比喻上的累加呢?無疑,當制度化程度較高的論述逐漸被建立起來,上述這種等同關係便會面臨到被拆解的命運,而在拆解等同性的過程中,人們仍舊會運用修辭工具,只是種類不同罷了。因此,這些工具絕不只是修辭而已,它們所根植的邏輯,事實上主宰著所有政治空間的構成與解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