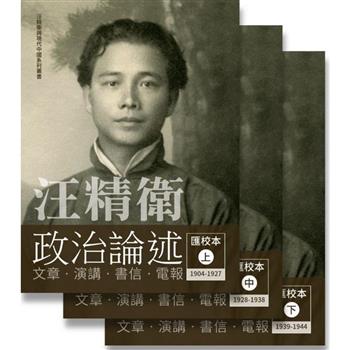舉一個例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曾仲鳴先生彌留的時候,有鄭重而簡單的兩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曾先生對於國事的主張與我相同,因為主張相同,常在一處,所以此次不免於死。曾先生之死,為國而死、為對於國事的主張而死。他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一息尚存,為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經應該更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何況這主張的實現,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
我因發表〈艷電〉被目為主和,主和是我對於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麼?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日舉一個例罷。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址: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
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書長:張羣
秘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上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中國當局。其條件為
(一)內蒙自治;
(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鑛產開發,仍繼續辦理;
(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
(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
(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
(六)關稅改善問題;
(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
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好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
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高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瀟、徐次辰,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傍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擔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的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
(一)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
但尚有兩點,須請陶大使報告德國政府:
(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為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
(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為戰勝國,以為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
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
蔣委員長說:「可以。」
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
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
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
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為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
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為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為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
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為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及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註一 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是蔣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銘。當時國府表面上由南京遷往重慶,實際上在武漢辦公。蔣主席因軍事指揮,留在南京。故國防會議,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註二 外交部長王寵惠亦為常務委員之一,是日因感冒請假,故由次長徐謨列席。且徐次長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報告之必要。
附註三 徐次長報告所說,墨三,是顧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瀟,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看了以上的報告,則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國防最高會議函中所說:「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內容具如此。
此外還有證據沒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質尚未過去,為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調停之事,則已成過去,故不妨舉出來作一個例。
於此,便會發生以下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為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已經認為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
對於以上三個疑問.我不欲答覆。但對於和戰大計,卻不能不再為國民一言。
有人說道:「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此話不通。國家之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時,則和。和之可不可,視其條件而定。條件而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不可和;條件而不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可以和。「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言猶在耳,試問主和有何不可?
有人說道:「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為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為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卻以之為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而抗戰。以抗戰為對內統一手段,我絕對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有人說道:「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刻搗亂。」我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
有人說道:「國際並不盼望我們和。」我以為和與戰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立於主動的地位、以運用外交求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決不應該俛仰隨人。何況現時除第三國際外,並沒有其他國家反對我們和。
如上所述已經明瞭,還有鄭重聲明的。甲午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庚子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這是說起來就難過的,我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大戰而後吐氣;大戰之後,德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今日而後吐氣。這是說起來就得意的,我也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因為這樣的循環報復,無有已時,決非長治久安之道。我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
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要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長百年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這種看法,兩國人都有懷疑的,然而也都有確信的。尤其二十個月的苦戰,日本的消耗,不為不大;中國的犧牲,不為不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怵於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捨嗎?我希望大家本着獨立、不屈不撓的精神幹去。和平建議之第一個犧牲者曾仲鳴先生,已將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們,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而前進。
末了,我還有幾句話。當二月中旬,重慶曾派中央委員某君來給我護照,俾我出國。我託他轉致幾句話:
其一,我不離重慶,〈艷電〉不能發出。然當此危難之時,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我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要主張得蒙採納,個人不成問題。
其二、聞得國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國際調停,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並行。如此,則我以在野之身從傍協助,亦不為無補。
其三、如果國民政府始終不下決心,任這局面僵下去,我雖離國,也會回來。
以上幾句話,定然是構成三月二十一日事變之原因。所可惜者,曾仲鳴先生比我年青,卻齎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為重慶方面所采納;終有一日,為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采納,則我可以無憾。
出處:
• 汪精衛,〈舉一個例〉,《時代文選》第二期(1939年),頁3-6。
• 中山樵夫編,《汪兆銘言論集》(東京:三省堂,1939年),頁39-49。
• 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上卷(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1940年),頁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