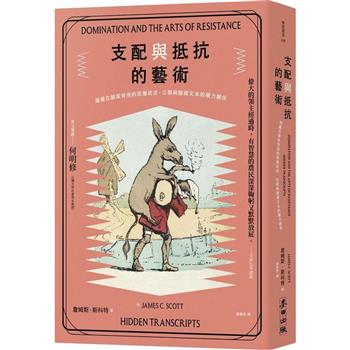偉大的領主經過時,有智慧的農民深深鞠躬又默默放屁。──衣索比亞諺語
前言
這本書背後的概念是從我在一座馬來(Malay)村莊的研究成果發展而來,我長期靠著我有些遲鈍的腦袋試圖理解那裡的階級關係。關於土地交易、工資率、社會名聲和技術變遷等議題,我聽見許多分歧的言論。單就這點而言,考慮到不同村民的利益互相衝突,從他們口中得到相異的敘述並不太意外。比較令我困擾的是,即使是同一位村民,偶爾也會講出自相矛盾的言論!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意識到儘管這樣的矛盾可能出現在任何人身上,但尤其常見於比較貧窮、經濟依賴程度最高的村民。經濟依賴的因素和貧窮同樣重要,因為有幾位經濟相當自主的窮人所表達的意見始終如一且獨立。
此外,這些矛盾帶有某種情境邏輯。當我把議題限縮在階級關係──這是我探討的諸多議題之一──窮人似乎會在富人面前說一套,和窮人在一起時又說另一套。富人同樣也會對窮人說某些話,而在自己人面前又改變說法。這是最粗略的區分方法;許多更細緻的區別則要取決於談話群體的具體組成,當然還有討論的議題,才能顯現出來。不久,我就發現自己開始運用這樣的社會邏輯,來尋找或創造某些情境,好讓我能夠核對不同的論述,並且可說是藉由三角交叉檢證,進入未經探索的領域。這個方法的成效足以達成我為數不多的目標,而研究成果載錄在《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一書,特別是在第兩百八十四至二百八十九頁的段落。
一旦我開始更加適應馬來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是如何影響論述,不久我便發現自己也會在那些在某些重要層面權力比我大的人面前字斟句酌。而我觀察到,當我必須忍住不脫口說出某些不夠審慎的回應,我往往也能找到某些對象讓我暢所欲言。這種受到壓抑的言論背後似乎有某種近乎身體性的壓力存在。在罕見的某些場合,我的怒氣或憤慨戰勝我的謹慎理智時,儘管反擊可能會招致危險,我卻會感到興高采烈。直到當時,我才完整體會到,為何我可能無法完全根據表面去判斷比我更弱勢的人們的公開行為。
這些關於權力關係與論述的觀察絕非我所原創。這是數百萬人日常民間智慧的基本要素,這些人睜開眼睛的多數時間都身處在受權力壓迫的情境之中,一次不得體的舉止或一句錯話都可能帶來可怕的後果。我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更有系統、甚至近乎固執地去探究這個概念,看看它在關於權力、霸權、抵抗和從屬的議題上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我在組織這本書時的工作假設是,弱勢無力和依賴程度最為嚴峻的情況將會是可以辨識的。因此,許多我在書中提出的證據是援引自關於奴隸、農奴和種姓從屬的研究,而我所設定的前提是,論述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會最鮮明地顯現在我所謂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落差最為嚴重之處。而在較為隱晦的情況下,我也加入了關於父權支配、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甚至是監獄和戰俘營等全控機構的證據。
這本書不像我在那座小型馬來村莊所做的研究那般,是嚴實、偶然、具組織性且奠基於歷史的分析。這本書兼容並蓄且概要的寫作方式違背了許多後現代主義著作的準則。不過,書中依然存在與後現代主義契合的部分,那就是我確信沒有任何社會位置或分析立場,能夠去判斷一段文本或論述的真值(truth value)。儘管我確實認為嚴實且梳理脈絡的著述是構成理論的命脈,但我也相信,當我們聚焦在結構性的相似之處,跨越文化和歷史時期的比較仍然有其價值。
因此,本書採用的分析策略始於一項前提──結構上類似的支配形式都會具有某種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在奴隸、農奴和種姓從屬的案例中,這些相似性十分明確。每個例子都代表著從某群從屬人口身上佔用勞力、財貨和服務的制度化部署。在形式上,這些支配形式下的從屬群體沒有任何政治或公民權利,他們的地位在出生時便已經底定。就算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但在原則上社會流動遭到杜絕。將這類支配正當化的意識形態包括尊卑之分的形式假設,這些假設相應表現在控制階層間公開接觸的特定儀式或禮節上。儘管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主人和奴隸、地主和農奴、高種姓印度教徒(Hindu)和賤民之間的關係都是個人統治的形式,提供上位者專橫獨斷、為所欲為的極大自由。這些關係之中總是會帶有個人恐怖的元素──個人恐怖可能會以任意毆打、性暴行、辱罵和公開羞辱等形式展現。舉例來說,某個奴隸或許足夠幸運逃過這類的惡劣對待,但她肯定知道這些事情可能發生在她身上,這樣的認知滲透進整段關係之中。最後,儘管如此,身處如此大規模支配結構之中的從屬者,在支配者直接控制的範圍外,仍然擁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而原則上,正是在這類隱蔽的情境下,人們才可能發展出對支配的共同批判。
對於我所希望提出的論點來說,我剛所描述的結構相似性是分析的核心。我絕對不是想要主張奴隸、農奴、賤民、被殖民者和被征服的種族都共同擁有不可改變的特性。那種本質論的主張站不住腳。然而,我真正想要主張的是,如果能夠證明支配結構是以類似的方式運作,那麼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往往會引發類似的抵抗反應和模式。因此,奴隸和農奴通常不敢針對他們的從屬地位提出異議。然而,他們有可能秘密創造並捍衛出一個社會空間,在其中得以說出他們私下對權力關係的官方文本所抱持的異議。這種社會空間的具體形式(例如語言掩飾、儀式符碼、小酒館、集市、奴隸宗教的「僻靜所」〔hush-arbor〕[1])或表達其異議的特定內容(例如希望某位先知歸返、透過巫術的儀式攻擊、頌揚盜匪英雄和反抗烈士),與正在討論的行為者所特有的文化歷史一樣獨一無二。為了描述某些廣泛的模式,我刻意忽略每種從屬形式的鮮明特殊性──比如說加勒比海地區(Caribbean)和北美洲奴隸制度的差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農奴制度的差異、俄羅斯和法國農奴制度的差異、區域差異等等。我在本書中勾勒的廣泛模式,唯有將之穩固置入以歷史為基礎和特定文化的背景中,才能建立其終極價值。
觀察本書所選擇探討的結構,就能明顯看出我特別重視尊嚴和自主的議題,但這些議題一般都被認為比物質剝削次要。奴隸制度、農奴制度、種姓制度、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經常會導致貶低、辱罵和侵犯身體的做法和慣例,而這些作為似乎在其受害者的隱藏文本中佔據了一大部分。一如我們將在後文所見,這類壓迫的形式拒絕給予從屬者一般的負面互欺(negative reciprocity)空間:以巴掌還巴掌,以辱罵還辱罵。即使是對當代勞動階級而言,在描述剝削時,藐視尊嚴和密切管控工作的部分,似乎至少與對工作和薪酬較狹隘的關注同樣顯著。
我更廣泛的目的是要建議,我們或許可以如何更成功地解讀、詮釋和理解從屬群體往往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當無權者在掌權者面前經常必須採取策略性的姿態,而掌權者可能傾向過度渲染他們的聲望和優勢時,我們如何研究權力關係?如果我們以表面價值來理解這一切,便面臨了一種風險,將可能只是策略的表象誤解為事情全貌。反之,我試圖證明另一種揭露矛盾、緊張和固有可能性的權力研究有其道理。每個從屬群體都從其苦難中創造出「隱藏文本」,體現在支配者背後訴說的對權力的批判。對掌權者而言,他們也發展出一種隱藏文本,體現關於他們的統治無法公開承認的實踐和主張。比較弱勢者和掌權者的隱藏文本,以及比較兩者的隱藏文本和權力關係的公開文本,可以讓我們以嶄新的方式理解對支配的抵抗。
在開頭頗具文學性地引用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後,我試圖說明支配的過程如何產生一套霸權的公開行為,以及一套無法在掌權者面前言說的檯面下論述。與此同時,我探討了展現支配和同意背後的霸權目的,並探問這類的行為是表演給哪些人看的。這樣的研究接著讓我們理解,為何就連嚴實爬梳歷史和文獻證據的著述,在描述權力關係時也傾向採用霸權敘述。我認為,在缺乏實際反叛的情況下,無權的群體協力鞏固霸權表象將能利己。
唯有透過比較表象和在受權力壓迫情境之外的從屬者論述,我們才能知曉這些表象的意義。因為意識形態的抵抗在不受直接監控的情況下最能蓬勃發展,本書將我們帶領檢視這類抵抗得以萌芽的社會性場域。
若說要解密權力關係,取決於能否完整獲取從屬群體多少有些秘密的論述,那麼研究古今權力的學者都將面臨僵局。不過,事實上隱藏文本通常會公開表述──儘管是以有所掩飾的形式呈現──因此我們無須絕望。根據這些原則,我提議我們如何能夠將無權者的謠言、八卦、民間故事、歌曲、姿態、笑話和戲劇詮釋為載體,透過這些和許多其他途徑,他們影射批判權力,同時躲藏在匿名或認定他們行為無害的認知背後。這些掩蓋意識形態違抗的模式多少可以類比在我經驗中所認知的農民和奴隸行為模式,他們會有所掩飾地努力阻撓掌權者在物質上佔用他們的勞動力、生產和財產:例如盜獵、故意拖延、偷竊、裝糊塗、脫逃等作為。整體而言,這些不服從的方式可以適切地稱作無權者的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
最後,我認為隱藏文本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那些往往是人們記憶以來頭一遭,隱藏文本被直接公開表述來違抗權力的罕見政治激情時刻。
第一章、官方說法背後
要在暴君面前說出自由的話語令我不寒而慄。──尤里比底斯(Euripides)《酒神女信徒》(The Bacchae)的合唱團主唱者
工人和工匠儘管是他們主人的僕人,但卻能靠著聽命行事來擺脫。然而暴君看著那些在他身旁的人,苦苦哀求他施恩;他們不僅必須執行他的命令,還必須照他希望他們(思考)的方式思考,而且為了滿足他,甚至要時常預測他的想法。僅僅服從他是不夠的,他們也必須要取悅他,他們效勞他時必須折磨虐待自己,甚至自殺;而且……他們必須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喜好,違背他們的意願,擺脫他們天生的性情。他們必須謹慎觀察他的話語、聲調、眼神,甚至是點頭。他們必須無眼、無腳、無手,全心全意警戒關注,以刺探他的心意,發掘他的想法。這樣的生活快樂嗎?這還稱得上是生活嗎?──拉波哀西(ESTIENNE DE LA BOETIE)的《自願奴役論》(A 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
最強烈的仇恨是源自恐懼,迫使人沉默無語,讓憤怒變成積極的報復意圖,幻想憎惡的對象毀滅就像某種隱祕的復仇儀式,受迫害者藉此秘密地發洩他們的怒氣。──喬治・艾略特的《丹尼爾・德隆達》(Daniel Deronda)
如果「向權勢說出真相」這個說法聽起來仍太過理想化,甚至在現代民主國家也不例外,那麼肯定是因為鮮少有人實行。弱勢者在掌權者面前掩飾真實想法並不令人意外。這種情形無所不在。事實上,甚至普遍到導致在許多情況下,那類行使的權力曲解「權力」的原意到幾乎無法辨認的地步。多數人認定的正常社交需要我們例行寒暄,笑臉迎人,儘管我們對對方可能懷抱著和外在表現不一致的看法。就這點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體現在儀節和禮貌上的社會習俗力量要求我們經常犧牲坦率直言,以換取和我們的熟人建立圓滑的關係。我們謹慎周到的行為可能也帶有策略性的層面:我們矯飾自我的這個對象可能會以某種方式傷害或幫助我們。喬治・艾略特聲稱「如果沒有一點演技,就什麼事也做不了」,或許並不誇張。
在後文中,我們所關注的比較不是出於客套的演技,而是從古至今絕大多數人被迫養成的演技。我指的是那些受到精細且系統性的社會從屬形式支配的人,所必須實行的公開表演:受雇主支配的工人、受地主支配的租戶或佃農、受領主支配的農奴、受主人支配的奴隸、受婆羅門(Brahmin)支配的賤民、受優勢種族支配的從屬種族成員。除了極罕見但意義重大的例外,從屬者的公開表演出於審慎、恐懼和討好的渴望,往往被形塑成迎合掌權者的期望。我將使用「公開文本」一詞來簡述從屬者和支配者之間的公開互動。(注1)公開文本儘管不一定會誤導人,但不可能說明權力關係的全貌。這種文本經常會符合雙方的利益,心照不宣地共同促成失實的表述。一名法國佃農老迪耶儂(Old Tiennon)的口述歷史幾乎涵蓋了十九世紀的歷史,描述著審慎且令人誤解的服從:「他(曾解雇他父親的地主)在從拉庫赫(Le Craux)前往梅耶(Meillers)途中,會稍事停留和我說話,而我強迫自己要表現出友好的樣子,儘管我內心相當鄙視他。」
老迪耶儂很自豪自己不像他笨拙又不幸的父親,他已經學會「生活必備的裝糊塗技能」。從美國南方傳出的奴隸敘事也一再提到欺騙的必要性:
我努力表現,讓自己不要被白人居民討厭,畢竟我深知他們的權力,以及他們對有色人種的敵意。……第一,我從不展示我所擁有的少數財產或金錢,而是方方面面都盡可能穿得像奴隸的樣子。第二,我從不表現得像我實際上的那麼聰明。無論是自由民或奴隸,這是所有南方的有色人種都認定,若要保全自己的舒適和安全尤其必須遵守的原則。
當從屬群體的一個關鍵生存技巧是在權力壓迫的情況下管理對外呈現的印象,他們行為的表演面向也會被支配群體中觀察力較敏銳的成員注意到。農場主瑪麗・切斯納特(Mary Chesnut)發現,每當白人在討論內戰前線最新消息時,她的奴隸都會異常沉默,她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在隱藏某些事情:「他們戴著黑色的面具到處走動,沒有一絲情緒的漣漪;但遇上除了戰爭以外的所有話題,他們都是所有種族中最熱烈討論的。現在迪克(Dick)就像一尊非常莊嚴的埃及獅身人面像,高深莫測地沉默不語。」
在此我要冒險提出一項粗略廣泛的歸納,我將在後文嚴格地具體描述:支配者和從屬者之間的權力落差愈大,權力行使時愈專橫,從屬者的公開文本就會愈符合刻板印象的慣常型態。換句話說,權力愈具威脅性,面具就愈厚。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想像到各式各樣的情境,從地位和權力對等的朋友關係,到另一個極端的集中營,受害者的公開文本帶有對死亡的恐懼。我們接下來要關注的絕大多數系統性從屬的歷史案例,都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
(未完)
[1] 譯注:僻靜所英文又作hush harbor或bush harbor,是美國內戰前時期非裔奴隸所發展出的簡易設施,他們會在遠離奴隸主活動範圍的樹林中搭建簡陋棚屋,以便聚會和進行融合非洲傳統和基督宗教的信仰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