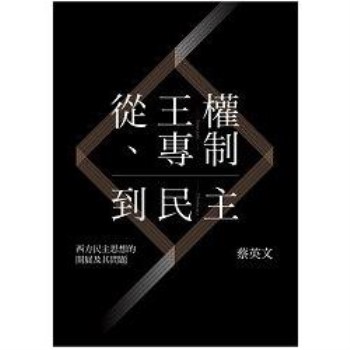第二章 古典共和思想中的公民政治共同體: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的解釋
一、引言
古希臘城邦與羅馬共和雖有體制上的不同(前者是民主城邦,後者是貴族的共和)但在本質上乃是由公民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koinonia politike)也可稱之為公民社會(civilis societies)。如我們所熟悉的,亞里斯多德在闡釋此概念時,界定人的本質在於過政治的生活(phusin zoon politikon),並且區分 polis(城邦的公共生活)與 oikos(家業的管理),把政治視為「公共之善」(res publica)的具體落實,以及明確表述「公民之德」。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在古羅馬共和時期,因為「羅馬法」的實踐而有了新的概念內涵。古羅馬共和思想雖然承襲亞里斯多德的「公民的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可是更強調法律的權威;同時,公民身份之認定不只是在於公共事務之參與,更是指稱「法律社會的成員」。這些成員(或所有的公民)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以及受法律的保護。簡言之,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之概念上賦予更明確的法律人(legalis homo)的意義。(J‧ A‧ Pocock,1992/1995: 36-37)
如何較詳細地闡釋古典共和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的概念的轉變?針對這個問題,本章闡述西塞羅的公民社會(civilis societatis)與共和國(civitas 或 respublica)的觀念,而說明古典共和之「政治共同體」呈現「人民的權益」(res populi)與法治的含意。古典共和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理念是跟當時的民主城邦與貴族共和的實際經驗有關,是故,在闡述他們的理念之前,簡要說明民主城邦與貴族共和的特徵。
二、古雅典城邦的民主與古羅馬共和的貴族政體
古雅典城邦,經歷了索倫(Solon)在西元前594年,以及克萊吉尼斯(Cleisthenes)在508年(或507年)的政治與社會改革,而形成(或者說創造了)民主制。不論其歷史的機緣與這些改革的方案,古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表現下列的特質:民主城邦是由公民所構成的共同體,公民身份是有其限定(譬如婦女與外邦人,奴隸皆不得成為公民)。公民皆有責任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擔任執政官。因此從法律的制訂、司法的審查,城市的公共政策的審議與執行皆由公民承擔。這種民主的城邦,引用卡斯托利亞底斯(Corelius Castoriadis)的話,即是由公民集體構成的自我建制(the self-institution of the collectivity)。這種自我建制呈現動態性格,但這種動態乃受其憲法的主導,也由公民的知識與理念的傳播所支援與推促,就如雅典公民所言,法律既然由我們所制訂,也可以由我們改變(Castoriadis, 1996: 122)
古希臘創造出民主,其概念語詞乃結合「人民」(demos)與「治理」(kratos,也意指力量、智能、意志與作為)。就此而言,民主意指人民的作為、權力與治理。在古希臘的政治中,人民乃指特定疆域(如城邦)的居民,它與「貴族」(aristori,或謂「寡頭」)相對立。除此之外,人民也指實行民主的城邦的所有公民。在此,值得提示的是,民主的概念也跟其他兩個概念語詞相關,一是「表達言論的平等權利」(isegoria),另一則是「參與法律的制訂與接受司法的平等權利」(isonomy),這兩個概念語詞的使用,乃先於「民主」的概念,它意指公民的平等地位(Vidal-Naquet, 1996: 109)。在民主政體中,所謂「政治」乃是指公民集體的參與、審議、判斷與行動,這一切作為的正當性不須援引超越性的論證(如上帝的權能或天意),也非來自一人或少數及獨制的權力(如君主制與寡頭制的權力),而是純粹由人民(公民)本身的作為。因此,如維多‧拿奎德(Pierre Vidal-Naquet)所言,「民主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政治是可能的,而政治就其定義而言,乃是所有公民的事務」。(ibid‧: 111)相對而言,古羅馬從西元前509年,當貴族推翻王制,至西元前27年屋大維稱帝,其間所形成的「共和制」並非如古雅典城邦的民主制,而是「寡頭制」(oligarchic regime,或可譯為「貴族制」),主導政治的不是平民大眾,而是社會上有名望,且擁有龐大財富與扈從(clients)的家族。這些貴族掌握元老院作為他們治理平民大眾的重要機構,體現政治的權威(autorita)。儘管共和的平民大眾沒有資格參與公共或政治事務的權利,但貴族深知其權威必須來自人民的支持,他們的政治事功,榮耀必須贏取人民的讚許與信賴。因此,羅馬共和的政府,在理念上,乃是「權威在元老院,權力在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貴族與平民雖相互倚賴,但亦彼此衝突,甚至鬥爭。平民欲擠身於公民階層,進入元老院,必須透過顯赫的事功與財富的累積,以及由此得到社會的聲望。在西元前第四世紀公民經由所謂「社會等級的鬥爭」(struggle of the orders),取得抗衡執政權威的權利,而得以自組議會(plebeian assembly),以及自選其行政長官(tribunes)。就此,元老院的權威必須受到人民議會及監察官的制衡。(Rosenstein, 1999: 374)。
然而,古羅馬共和並非民主制,其主要的因素在於政治權力與權威跟社會的名望與財富糾葛一起,無法如古雅典城邦一樣,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公共空間,容許自由公民審議與決斷政治事務。共和雖有公共討論的場所(forum),但是羅馬人民不是透過政治參與的途徑,發揮其影響力,而是運用街頭抗議、騷動,甚至暴亂的方式表達政治的不滿。除此之外,羅馬共和的行政長官雖經由公民的選任,但他們不是人民的代表,因此,沒有責任實現人民的願望(Yakobson, 1999: 391)。共和體制因元老院的權威以及注重法治而得以維繫其穩定性,但由於掌握元老院的貴族來自社會的望族以及財富的累積,致使政治權力、權威的行使與社會的實力相結合,排除了人民的政治參與。除此之外,貴族內部派系的傾軋、鬥爭造成元老院決策權的癱瘓,無法有效地因應內外的問題與危機。因元老院制度的失靈,解決內外的政治與軍事事務而只能循經制度外的途徑,決斷權最後則由軍事強人所掌控,在共和體制喪失其正當性的處境中,從貴族門第出身的軍事強人的干政,以及平民大眾的要求,將共和制推向皇權帝制(principte)。以上述的政治體系為背景,本章試著闡釋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的政治共同體理論。三、亞里斯多德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的理念
依照亞里斯多德的解釋,任何共同體(koinõnia)的形成必須預設其成員可以共享、溝通與參與的共同事務,以及共同的結合紐帶。就城邦的共同體而言,亞氏基於目的論與自然演化的觀點,闡釋它乃是從家庭、農村公社演化成的,最具廣延性(comprehensive)、自足性(autarky)的結社形式。另一方面,如果說任何結社皆是建立在「善」之目的的條件上,那麼,依照亞氏的觀點,城邦的政治共同體乃是人之「最高善」的實現。
城邦的政治共同體既是一廣延性與自足性的結社型態,那麼,它必然包含各種自發自願結合的結社團體(如農業的、技術工藝的團體),這些結社團體,相對於城邦的政治共同體而言,是部分的,無法成就自足的條件。這種「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取決於一個社群之「善」的本質意義,譬如,大學作為一個追求「知識」之善的目的而形成的共同體,「知識」遂成為此共同體生活的「界線」(a limit),組成此共同體的「部分」(如校務的行政管理)成為達此目的之「輔助性」的設置。城邦政治共同體既然代表「最高善」的實現,那麼,這「最高善」所指為何?
「善」,在個人與結社的層面上,指「良好的生活」與「人的卓越秀異」(human excellence)。從一普遍的意義來說,它可以意指人的實踐(praxis)與構成社群的倫理,如公道、正義,或者是友誼,當然,它亦包含實質性的福祇,如健康、利益與優厚的物質生活狀況等。亞氏在思考政治共同體的「最高善」的意義時,著重於倫理之善的組合關係,其理由在於政治共同體既是一廣延的、整全與自足的社群,它的「至善」必須包容與超越其組成之「部分」的個別與特殊的「善」,而得以滿足此條件的「至善」就必須是倫理性的「善」。這也是為什麼亞氏強調「正義」(不論是數學式的,或幾何學式的分配正義)乃是政治共同體構成的基本條件的理由。
城邦的政治共同體,乃是在一種憲政下由公民所構成的共同體。在界定「公民身分」時,亞氏排除了宗族血緣與地緣的關係;其次,否定從事勞動生產與製造業者(包含外邦人和商人)的公民身分。在這裡不討論古希臘城邦公民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就「公民身分」的理論解釋而言,所謂公民乃指「享有參與政治事務,以及身兼行政與司法職司的權益。依照我們的定義,享有這些權益者才有資格成為城邦之公民。一般而言,一個城邦乃是像這樣具有自足生活的成員所構成。從是觀之,公民是指擁有產業,得以免除勞動與工作,而享有閒暇、具有能力參與城邦公共事務的『統治階級』(politeuma)。他們在上軌道的城邦中,是平等且彼此相似,也就是說,他們具有同質性的生活方式,能表現公共德行(civic virtue)。他們自由合作,彼此相互治理,能達成一個共同體『共善』之目的。」(1985‧: 1227 b7-16~1332 b12-41)。
政治共同體具有政治的屬性(the political),在此,亞氏所使用的「政治」(politikos)一詞具有如下的含意:政治表示公民(polites)對於城邦公共事務的關心,以及增進公共福祉的作為,這乃是「政治屬性」(politiké)的基本意義。除此之外,政治亦表示「治理」(the ruling)的意涵,它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指城邦的「統治階層」(politeuma)依照法律(通常是指習慣法)的規約,處理城邦的公共事務;另一方面,指公民彼此之間的關係乃是建立在道德倫理的聯繫。再者,「政治體制」(politeia)這個名詞亦含有城邦之憲政構成的意義,以及表示亞氏所說的擷取寡頭政體(oligarchy)與民主制(democracy)的長處而形成的理想政體(polity)。
不論及亞氏對政治體制的類型之論述,他的公民政治實踐的理念,其論證的主題在於公民的政治實踐並非技術性的專家政治──如我們現在所稱的「科技官僚」的行政管理──而是指公民參與政治實務時,言行的具體表達,以及彼此之間言行之溝通、分享。他所關切的是公民「合作共事」(act in concord),以增進與實現城邦的共同福祉。
亞氏在闡述此公民政治實踐的理念時,提示了人的本質或意向的觀點,就如同一般所論的,亞氏肯定人為「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以及「具言說與行動能力的存有」(zoon logos ekon)。相對於現代的「個人主義」,此觀念強調人相互結社的傾向,而非孤立單獨的個體存在。同時,「理性言說」(logos)是指「公民在市集或公共場域」(agora)的言辯、溝通,以及經由此過程,對於公共議題有一種釐清,以鄂蘭的用語,即是「透過言辯,解釋、論述我們生活之共同世界的種種事物」,它所指的不是一種「理性計算」,或者也不是如歐克秀所指的「依照一項不證自明的原理作獨白式(monological)的推論與證明」(Oakefshott, 1991: 84-85),語言的表明與溝通,乃是一種彰顯與釐清。
亞氏以古希臘城邦的政治社會經驗,建立了「政治共同體」 (koinõnia politiké)的理念,在其中,他闡釋公民身份與德行的意義,肯定政治共同體的道德倫理性格;另一方面,他塑造出人的「公共或政治人格」和「理性言辯溝通」的存有,這些均構成了「公民共和主義」思想之濫觴。羅馬共和時期的西塞羅承續了這些理念,提出了政治共同體的構成基礎。筆者依據他的 De Re Publica(《論共和》)與 De Legibus(《論法律》)為本,說明其公民社會的理念。
一、引言
古希臘城邦與羅馬共和雖有體制上的不同(前者是民主城邦,後者是貴族的共和)但在本質上乃是由公民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koinonia politike)也可稱之為公民社會(civilis societies)。如我們所熟悉的,亞里斯多德在闡釋此概念時,界定人的本質在於過政治的生活(phusin zoon politikon),並且區分 polis(城邦的公共生活)與 oikos(家業的管理),把政治視為「公共之善」(res publica)的具體落實,以及明確表述「公民之德」。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在古羅馬共和時期,因為「羅馬法」的實踐而有了新的概念內涵。古羅馬共和思想雖然承襲亞里斯多德的「公民的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可是更強調法律的權威;同時,公民身份之認定不只是在於公共事務之參與,更是指稱「法律社會的成員」。這些成員(或所有的公民)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以及受法律的保護。簡言之,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之概念上賦予更明確的法律人(legalis homo)的意義。(J‧ A‧ Pocock,1992/1995: 36-37)
如何較詳細地闡釋古典共和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的概念的轉變?針對這個問題,本章闡述西塞羅的公民社會(civilis societatis)與共和國(civitas 或 respublica)的觀念,而說明古典共和之「政治共同體」呈現「人民的權益」(res populi)與法治的含意。古典共和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理念是跟當時的民主城邦與貴族共和的實際經驗有關,是故,在闡述他們的理念之前,簡要說明民主城邦與貴族共和的特徵。
二、古雅典城邦的民主與古羅馬共和的貴族政體
古雅典城邦,經歷了索倫(Solon)在西元前594年,以及克萊吉尼斯(Cleisthenes)在508年(或507年)的政治與社會改革,而形成(或者說創造了)民主制。不論其歷史的機緣與這些改革的方案,古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表現下列的特質:民主城邦是由公民所構成的共同體,公民身份是有其限定(譬如婦女與外邦人,奴隸皆不得成為公民)。公民皆有責任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擔任執政官。因此從法律的制訂、司法的審查,城市的公共政策的審議與執行皆由公民承擔。這種民主的城邦,引用卡斯托利亞底斯(Corelius Castoriadis)的話,即是由公民集體構成的自我建制(the self-institution of the collectivity)。這種自我建制呈現動態性格,但這種動態乃受其憲法的主導,也由公民的知識與理念的傳播所支援與推促,就如雅典公民所言,法律既然由我們所制訂,也可以由我們改變(Castoriadis, 1996: 122)
古希臘創造出民主,其概念語詞乃結合「人民」(demos)與「治理」(kratos,也意指力量、智能、意志與作為)。就此而言,民主意指人民的作為、權力與治理。在古希臘的政治中,人民乃指特定疆域(如城邦)的居民,它與「貴族」(aristori,或謂「寡頭」)相對立。除此之外,人民也指實行民主的城邦的所有公民。在此,值得提示的是,民主的概念也跟其他兩個概念語詞相關,一是「表達言論的平等權利」(isegoria),另一則是「參與法律的制訂與接受司法的平等權利」(isonomy),這兩個概念語詞的使用,乃先於「民主」的概念,它意指公民的平等地位(Vidal-Naquet, 1996: 109)。在民主政體中,所謂「政治」乃是指公民集體的參與、審議、判斷與行動,這一切作為的正當性不須援引超越性的論證(如上帝的權能或天意),也非來自一人或少數及獨制的權力(如君主制與寡頭制的權力),而是純粹由人民(公民)本身的作為。因此,如維多‧拿奎德(Pierre Vidal-Naquet)所言,「民主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政治是可能的,而政治就其定義而言,乃是所有公民的事務」。(ibid‧: 111)相對而言,古羅馬從西元前509年,當貴族推翻王制,至西元前27年屋大維稱帝,其間所形成的「共和制」並非如古雅典城邦的民主制,而是「寡頭制」(oligarchic regime,或可譯為「貴族制」),主導政治的不是平民大眾,而是社會上有名望,且擁有龐大財富與扈從(clients)的家族。這些貴族掌握元老院作為他們治理平民大眾的重要機構,體現政治的權威(autorita)。儘管共和的平民大眾沒有資格參與公共或政治事務的權利,但貴族深知其權威必須來自人民的支持,他們的政治事功,榮耀必須贏取人民的讚許與信賴。因此,羅馬共和的政府,在理念上,乃是「權威在元老院,權力在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貴族與平民雖相互倚賴,但亦彼此衝突,甚至鬥爭。平民欲擠身於公民階層,進入元老院,必須透過顯赫的事功與財富的累積,以及由此得到社會的聲望。在西元前第四世紀公民經由所謂「社會等級的鬥爭」(struggle of the orders),取得抗衡執政權威的權利,而得以自組議會(plebeian assembly),以及自選其行政長官(tribunes)。就此,元老院的權威必須受到人民議會及監察官的制衡。(Rosenstein, 1999: 374)。
然而,古羅馬共和並非民主制,其主要的因素在於政治權力與權威跟社會的名望與財富糾葛一起,無法如古雅典城邦一樣,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公共空間,容許自由公民審議與決斷政治事務。共和雖有公共討論的場所(forum),但是羅馬人民不是透過政治參與的途徑,發揮其影響力,而是運用街頭抗議、騷動,甚至暴亂的方式表達政治的不滿。除此之外,羅馬共和的行政長官雖經由公民的選任,但他們不是人民的代表,因此,沒有責任實現人民的願望(Yakobson, 1999: 391)。共和體制因元老院的權威以及注重法治而得以維繫其穩定性,但由於掌握元老院的貴族來自社會的望族以及財富的累積,致使政治權力、權威的行使與社會的實力相結合,排除了人民的政治參與。除此之外,貴族內部派系的傾軋、鬥爭造成元老院決策權的癱瘓,無法有效地因應內外的問題與危機。因元老院制度的失靈,解決內外的政治與軍事事務而只能循經制度外的途徑,決斷權最後則由軍事強人所掌控,在共和體制喪失其正當性的處境中,從貴族門第出身的軍事強人的干政,以及平民大眾的要求,將共和制推向皇權帝制(principte)。以上述的政治體系為背景,本章試著闡釋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的政治共同體理論。三、亞里斯多德的公民政治共同體的理念
依照亞里斯多德的解釋,任何共同體(koinõnia)的形成必須預設其成員可以共享、溝通與參與的共同事務,以及共同的結合紐帶。就城邦的共同體而言,亞氏基於目的論與自然演化的觀點,闡釋它乃是從家庭、農村公社演化成的,最具廣延性(comprehensive)、自足性(autarky)的結社形式。另一方面,如果說任何結社皆是建立在「善」之目的的條件上,那麼,依照亞氏的觀點,城邦的政治共同體乃是人之「最高善」的實現。
城邦的政治共同體既是一廣延性與自足性的結社型態,那麼,它必然包含各種自發自願結合的結社團體(如農業的、技術工藝的團體),這些結社團體,相對於城邦的政治共同體而言,是部分的,無法成就自足的條件。這種「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取決於一個社群之「善」的本質意義,譬如,大學作為一個追求「知識」之善的目的而形成的共同體,「知識」遂成為此共同體生活的「界線」(a limit),組成此共同體的「部分」(如校務的行政管理)成為達此目的之「輔助性」的設置。城邦政治共同體既然代表「最高善」的實現,那麼,這「最高善」所指為何?
「善」,在個人與結社的層面上,指「良好的生活」與「人的卓越秀異」(human excellence)。從一普遍的意義來說,它可以意指人的實踐(praxis)與構成社群的倫理,如公道、正義,或者是友誼,當然,它亦包含實質性的福祇,如健康、利益與優厚的物質生活狀況等。亞氏在思考政治共同體的「最高善」的意義時,著重於倫理之善的組合關係,其理由在於政治共同體既是一廣延的、整全與自足的社群,它的「至善」必須包容與超越其組成之「部分」的個別與特殊的「善」,而得以滿足此條件的「至善」就必須是倫理性的「善」。這也是為什麼亞氏強調「正義」(不論是數學式的,或幾何學式的分配正義)乃是政治共同體構成的基本條件的理由。
城邦的政治共同體,乃是在一種憲政下由公民所構成的共同體。在界定「公民身分」時,亞氏排除了宗族血緣與地緣的關係;其次,否定從事勞動生產與製造業者(包含外邦人和商人)的公民身分。在這裡不討論古希臘城邦公民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就「公民身分」的理論解釋而言,所謂公民乃指「享有參與政治事務,以及身兼行政與司法職司的權益。依照我們的定義,享有這些權益者才有資格成為城邦之公民。一般而言,一個城邦乃是像這樣具有自足生活的成員所構成。從是觀之,公民是指擁有產業,得以免除勞動與工作,而享有閒暇、具有能力參與城邦公共事務的『統治階級』(politeuma)。他們在上軌道的城邦中,是平等且彼此相似,也就是說,他們具有同質性的生活方式,能表現公共德行(civic virtue)。他們自由合作,彼此相互治理,能達成一個共同體『共善』之目的。」(1985‧: 1227 b7-16~1332 b12-41)。
政治共同體具有政治的屬性(the political),在此,亞氏所使用的「政治」(politikos)一詞具有如下的含意:政治表示公民(polites)對於城邦公共事務的關心,以及增進公共福祉的作為,這乃是「政治屬性」(politiké)的基本意義。除此之外,政治亦表示「治理」(the ruling)的意涵,它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指城邦的「統治階層」(politeuma)依照法律(通常是指習慣法)的規約,處理城邦的公共事務;另一方面,指公民彼此之間的關係乃是建立在道德倫理的聯繫。再者,「政治體制」(politeia)這個名詞亦含有城邦之憲政構成的意義,以及表示亞氏所說的擷取寡頭政體(oligarchy)與民主制(democracy)的長處而形成的理想政體(polity)。
不論及亞氏對政治體制的類型之論述,他的公民政治實踐的理念,其論證的主題在於公民的政治實踐並非技術性的專家政治──如我們現在所稱的「科技官僚」的行政管理──而是指公民參與政治實務時,言行的具體表達,以及彼此之間言行之溝通、分享。他所關切的是公民「合作共事」(act in concord),以增進與實現城邦的共同福祉。
亞氏在闡述此公民政治實踐的理念時,提示了人的本質或意向的觀點,就如同一般所論的,亞氏肯定人為「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以及「具言說與行動能力的存有」(zoon logos ekon)。相對於現代的「個人主義」,此觀念強調人相互結社的傾向,而非孤立單獨的個體存在。同時,「理性言說」(logos)是指「公民在市集或公共場域」(agora)的言辯、溝通,以及經由此過程,對於公共議題有一種釐清,以鄂蘭的用語,即是「透過言辯,解釋、論述我們生活之共同世界的種種事物」,它所指的不是一種「理性計算」,或者也不是如歐克秀所指的「依照一項不證自明的原理作獨白式(monological)的推論與證明」(Oakefshott, 1991: 84-85),語言的表明與溝通,乃是一種彰顯與釐清。
亞氏以古希臘城邦的政治社會經驗,建立了「政治共同體」 (koinõnia politiké)的理念,在其中,他闡釋公民身份與德行的意義,肯定政治共同體的道德倫理性格;另一方面,他塑造出人的「公共或政治人格」和「理性言辯溝通」的存有,這些均構成了「公民共和主義」思想之濫觴。羅馬共和時期的西塞羅承續了這些理念,提出了政治共同體的構成基礎。筆者依據他的 De Re Publica(《論共和》)與 De Legibus(《論法律》)為本,說明其公民社會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