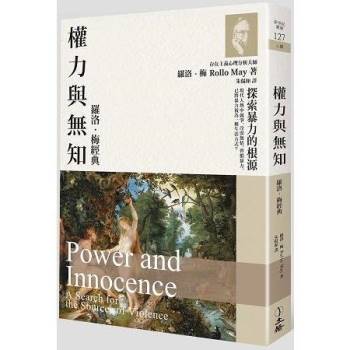瘋狂與無能
Madness and Powerlessness
找到生命,便找到權力的意志(will to pow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權力是一切生物的根本。尤其是人類,數十億年前被拋到這荒瘠的地球表面上,期待存活,也必須求生;他們在每次與天地人群的競爭中,都必須運用權力並面對挑戰的勢力。雖然人類自始以來就感到不安,被局限與脆弱摧折、被疾病侵擾,最終被死亡擊倒,但是卻反而因此肯定了自己的創造力。文明就是這樣的成果之一。
我不把權力看成是用來屈辱他人或用到敵人身上的字詞,而是把它當成對生命過程的基本面向的描述。它與生命本身不能劃上等號;人類存在的內涵遠甚於此──諸如好奇、關愛與創意等,也許在一般情況下的確與權力有關,但其本身卻不應被稱為權力。但是,如果我們忽略權力這個因素,像平日那樣反抗濫用權力造成的毀滅性後果的話,我們便會失去做人的基本價值。
請承認我們個人是無能的──我們無法影響他人,我們無足輕重,我們父母一生信奉不渝的價值對我們毫無意義,我們像奧登(W. H. Auden)筆下「『無名的他者』」那樣,對他人和自己都不值一文──真是情何以堪。過去四十年來,關於個人能力與潛能的言論是這樣地多,但是對於個人具有在心理與政治上改變現況能力的信心卻是少得可憐。這類言談至少有一部分是基於補償心理所顯現的症狀,因為我們不安地發覺到自己的權力喪失了。
因此,在人類認為以按鈕的方式便可將地球毀滅的過渡年代裡,有人會提議人類放棄此一恐怖的實驗,是可以理解的。克拉克醫師(Dr. Kenneth B. Clark)在美國心理學會會長的就職典禮中論證說: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中,要信任個人的心情與選擇,是太危險的事了。……我們不再能掌控當權者,因此必須靠鎮定劑來控制我們的領袖。」慮及克拉克熟知紐約哈林區及黑人族裔的無力感才有此提議的背景,我們可以同情他的絕望論調。但是我們不能不了解,當化學藥物立意要治療當代人的侵略性,並發展其「合群」人格時,卻發現藥物的使用與人格的萎靡以及個人責任感的消失,是息息相關的,讀來怎不令人沈痛。這樣的改變實際上意味著人性正逐漸喪失。無能與冷漠乃是孕生暴力的溫床。沒錯,因為侵略性一向被提升到暴力的層次,所以人們會對它感到害怕或不喜歡,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是,無能的狀態會造成冷漠,也會因上述根除侵略性的計劃而產生;它是暴力的源頭。當我們使人們無能為力時,我們正鼓動而非控制了暴力。我們社會中的暴力行為,大多是出自那些試圖建立自尊、護衛自我形象,或想顯現自己份量的人。不論這些動機有多偏差,是如何被誤用,或是其展現多具破壞性,它們仍舊是人際需求的正向呈現。我們不能漠視的事實是,儘管要導正這些需求十分困難,但是它們的確具有建設性的潛能。暴力不是出於權能的過剩,而是來自無能。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猶太人,德國哲學大師海德格的學生,兩人亦曾發生戀情)說得好:暴力是無能的表現。
無能的腐化
多年前當我開始心理治療師的生涯時,無能與精神病的關係便讓我印象深刻。心理治療師可以在精神受困者的身上,看到極端的行為以及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經驗。這佐證了弗登堡(Edgar Z. Friedenberg)所說的話:「一切的軟弱都會腐化,無能則會帶來絕對的腐化。」
普莉西拉(Priscilla)這位年輕的音樂家,是我最早的案主之一。根據為她做羅氏墨漬測驗(Rorschach,譯註:由當事人對墨水點繪圖形的解釋,以判斷其性格)的人員所述,她的「一隻腳落在精神分裂症的領域,另一隻腳則踩在香蕉皮上(譯註:表示岌岌可危)。」在我和她會談的那些時段,她會長篇大套、巨細靡遺地比較從紐沃克(Newark)開出的火車的音符顏色,和從紐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開出的火車的音符顏色有何不同。我對她所說的內容大多毫無頭緒──這點她也知道。但是她似乎就需要有我這麼一位肯傾聽、願意試著去了解她的人,不管我懂了沒。她也是一位矜持自重、具有幽默感的女士,這些特質後來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但是,她從不生氣。無論是對我、對她父母或對任何人,都是如此。她的自尊薄弱模糊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樣。有一次,和她同屬一個合唱團的年輕人,邀請她一起去參加一個音樂會。她接受了。但是第二天,一股頓生的自我懷疑促使她打電話給對方說:「如果你不願意,就不用帶我去。」她自信不足,不覺得有人會想要和她一起去參加音樂會。她在八、九歲的時候,曾經和一位比她年紀稍長的男孩玩足球;他用力撞得使她受了傷。其他孩子可能會向對方吼叫,或打架、哭鬧、不願再玩;這些反應不論好壞,都是因應的方式。但是普莉西拉完全沒用這些方法;她只是坐在地上看著男孩,靜靜地想說,他不應該這麼用力撞她。
當她在財務上或性事上被利用時,她完全不會防衛自己,不知道該如何說「不」,因為沒有足夠的憤怒支持她說不。隨著她無法生氣這件事而來的後果,就是一種深沈的無能經驗,以及幾乎無法在人際關係中去影響他人的處境。
但是,這樣的人有著完全不同的一面,這一點我在爾後與許多邊緣性病患的共處經驗中已經獲得確認。普莉西拉的夢不是裝在袋子裡的屍塊,就是血腥與戰爭──簡言之,她的意識生活有多馴良,她的夢就有多暴力。
後來我經常反思無能與瘋狂之間的關係,部分原因也是這位年輕女士的緣故。在此我要刻意強調瘋狂(mad)這字眼的雙重意義:其一是個人的憤怒已達暴力程度的感受;其二是傳統精神醫學對精神病的觀點。這二者之間有其關連,而且這兩種語義的使用將引導我們進入問題的核心。
我們知道,精神病患的共同特徵就是「無能」,這造成了他們的持續焦慮,而焦慮又與他們的軟弱互為因果。病患牢不可破地認定自己是無足輕重的,並且認為這是與生俱來的,在人生歷程中,常常用卑微可憐的姿態去獲取那一丁點的首肯。某位青春期的少女在正午時分來找我諮商時,竟然穿了一件有著篷篷裙的夜禮服,這可能是她最漂亮的衣服之一,她以此表示對我的注目與關心有多在意,但卻沒有覺察到這樣多麼時地不宜。當普莉西拉無法再以這種生活方式過下去時,她的內在便會「垮掉」,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態,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普莉西拉夢裡的暴力現在成了她清醒時的生活內容。當事人似乎完全瘋了,這就是為什麼數百年來精神病會被稱為瘋病的原因。當事人會對所有人都很生氣,包括自己在內,她會威脅或試圖自殺,割腕後將血塗抹在醫院的門上,以戲劇性的手法凸顯出自己對醫護人員的需求。她對自己和所投射的人公開地施行暴力。
我們在其他案主身上也看到同樣的舉動。在描述本身精神分裂症的自傳體小說《未曾許諾的玫瑰花園》中記載著,女主角漢娜.格林(Hannah Green)是在十六歲時被送到栗樹屋療養院的。她是馴良安靜性格的典範,從來不曾發怒。只要她有需要,就會退入自己私密精神世界的神話中,和裡頭的神話角色談話。治療她的精神醫師瑞奇曼尊重漢娜的個人神話,並保證只要漢娜需要,就不會剝奪她的神話。但是當瑞奇曼去歐洲的那個夏天,醫院指派了一位比較年輕的醫師治療漢娜。他樂觀而勇氣十足地衝入漢娜的神話世界,並搗毀了它。結果慘不忍睹。暴力一旦迸發,漢娜便在療養院裡火燒自己和隨身的衣物,要為自己烙印下一輩子的傷疤。這位年輕醫生所犯的錯誤在於,不能體會神話對於漢娜存在的意義。關鍵不是神話在理論上的對錯問題,而是它對漢娜發揮的功能。這位沈靜的病患看似不具侵略性,卻從馴良的一端擺盪到公然暴力的另一端去。
這看起來感覺像是針對醫院照顧人員所施展的權力,但它是一個虛假的權力(pseudo-power),是軟弱無能的表現。如今我們可以說她「瘋了」,意思是她不符合我們社會既定的標準,也就是她沒有穿戴上所有社會皆偏好的馴良「臉面」。被壓抑的怒氣與忿懟,若與因無能而生的持續恐懼相結合,終將導致暴力,了解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在瘋狂的虛假權力背後看到的景象,往往是人們奮力求取某種意義感,以及某種改變現況和建立自尊的方法。我在為普莉西拉進行治療期間,她收到家鄉寄來的一份報紙,報導說她的村子有一位男人自殺了。她對我說:「如果村裡有人認得他的話,他便不會自殺了。」請注意,她不是說「如果他認得某人的話」,而是「如果有人認得他的話」。我相信她在告訴我,只要我繼續陪著她,她便不會以暴力結束生命。然而她也說出了為人所需的至寶──必須有人傾聽、認同和了解。如此人們才會認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他的生命與其他人的一樣重要;也才會給他某種方向感,讓他在這個原本無意義的世界找到一個立足點。
當普莉西拉能對我生氣時,值得大書特書,因為那時我將知道,她在這個廣闊的世界,已經開始懂得在人我交往中保護自己了。更重要的是,她敢於活出自己豐沛的能量,做一個既有原味又討人喜愛的人。
瘋狂與社會
我們在普莉西拉身上看到的消極──瘋狂模式,與已屬當代男女嚴重問題的社會暴力之間,有什麼樣的關連呢?
我有一位朋友,既不是處於被分析的狀況,也不是精神病患;以下是他和太太吵架之後,所感受到那種暴怒之情的自白:
這樣的憤怒和暫時的精神病有多接近啊!當我沿著那條看似遙無止盡的街道走時,我無法思考;我感到暈眩迷亂。但這種模糊困惑只是外在的──在心裡,我是極有精神的,對每個念頭和感受都能敏銳地覺察,彷彿自己置身在一個光明透亮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非常逼真。我唯一的困擾是,這種內在的清醒和外在世界可說毫無關連。
說到我與外在世界的聯繫,我略感羞赧──羞赧而且無力抗拒。如果有人嘲弄我,或突然極為需要我(譬如說街上發生了車禍),我將無法反應。如果我有所回應,就必須顯露出我的「瘋狂」;它會一股腦兒地爆裂開來。
街道是陌生的;雖然人們一如往常在路上走著,但是街道看起來卻空蕩蕩的。我對那些街道覺得生疏(雖然我曾見過它們千百次)。
我像酒醉般地走著,抬起腿來,又刻意地放了下來。我走進一家餐廳,很怕出納小姐認不得我──我的膚色不一樣了──或者她會以為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她確實認得我,也如往常般友善)。我走進男生廁所,不帶任何情緒地讀著如廁區上方的塗鴉。我仍舊害怕有人會要我做什麼或侵略我,而我卻無法抵抗。我回到座位上,盯著餐廳盡頭的窗子往外看。我覺得與世界只有模糊的關連。食物送上來了;我對於吃或品嚐食物沒太大興趣;我只是糊里糊塗地完成動作。
我試著回想我們爭吵的細節,卻徒勞無功──只有兩三件事非常清楚地浮現出來;其餘的則是一團亂。我只吃了一點點。
侍者走了過來,他是一位中年的中國人,他對我說:「我覺得你想太多了。」他指指自己的前額。「你有困難嗎?」我笑著點點頭。他繼續說:「近來人人都有麻煩事。」他的話有種奇異的舒緩作用。他搖著頭走開。這是我對外在世界的第一次突圍。它使我大笑起來,對我有莫大的幫助。
我了解,當這種狀態漫長地持續下去,人們會做出傷害自己的事情來,例如站到車子前面等著被撞。他們會這麼做多半是因為對周遭的真實世界欠缺覺察。他們也會出於報復而這麼做,或拿出一把槍來殺人。
陷入這種暴怒情緒中的經驗,與歷史記載中的「瘋狂」經驗,相去不遠了。例如,以下是一位哈林區的年輕黑人所陳述的「瘋狂」意義:
那些白人條子,他們有種可惡的虐待本性。……哈林區不需要他們!……他們引起的暴力比任何人都多。……當我們無法回家而在街頭跳舞時,就來了個條子,追趕著每個人。他瘋了。我的意思是他真的瘋了!……他又氣又瘋地跑到這附近來。
這位黑人說的是,警察的「瘋狂」與哈林區的暴力是有關連的。警察是否以誘發暴力反應的方式激怒自己,來維護他所認定的法律與秩序呢?這是否是人們選擇當警察的原因之一呢?難道他只要緊抓住被文化認可的精神病,並以此和保守的社會現狀站在同一陣線,就可以使他在值勤時,合法地攜帶警棍和警槍發洩暴力嗎?
犯罪學教授托赫(Hans Toch)在《暴力人》(Violent Men)一書中的逐字報告,可以讓我們更仔細地來考量這些問題。譬如,托赫相信:
黑人小孩與白人警察──他們的驕傲、恐懼、孤立、需要自我肯定,特別是需要被尊重──有著奇異的相似性;雙方都是受害者,都是囚犯,受制於日益升高卻不是由他們造成的衝突。根據他們自己的報告顯示,警察覺得他們必須維護「法律與秩序」,而且把此舉和他們個人的自尊與男子氣概劃上等號。警察長久以來從「法律與秩序」的概念,在自己內心中投射延伸出一場證明自己有無能力的戰爭來。某位接到家庭糾紛報案的警官,看到一位坐在車內的黑人,他認為對方可以為這件口角之爭提供相關的線索:
警官叫黑人走到車外。黑人回答說:「你不能叫我這麼做。我是在私有的領域裡。」警官的報告說,這黑人看起來很討厭,他的「態度讓我很煩」。
黑人最後出來到車外,但是雙手一直插在防水夾克的口袋內。此舉仍舊讓警官很討厭,於是叫黑人把手拿出來。由於黑人一再拒絕配合,警官於是叫來另一名警察,他們一起迫使黑人把手伸出口袋。
警察認為這是蔑視權威,是不可原諒的。他必須不計代價地伸張警察的權威。……(「我覺得黑人將手從口袋伸出來,是絕對必要的。……我們抓住他時,他便開始惡言相向。……我們逮捕他,並讓他坐上巡邏車後座,他恐嚇說要小便在座位上,並在玻璃窗上又踢又搥的。」)
在此案例中,這個黑人認為,做為白人政府武力,以及整個黑人族群敵人的警察,任意地羞辱了他。他確實沒錯,因為警察必須恐嚇黑人來維持權威。二者都是「暴力人」。事件中制服警察的藍色勢力與黑人的黑色勢力,乃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各自都為保護自我形象,保護自己做為「人」的感覺而不遺餘力。只是因為警察代表法律執行者,而且佩了警徽和警槍,所以特別具有優勢。警力中的「暴力人」,托赫寫道,是「有本事把人際互動提升到爆炸性情勢的專家」。「嫌犯」通常會覺得自己處於極為不利的位置;他的「決鬥」對手以警徽和警槍為掩護,以至於「嫌犯」往往會挑釁警官要他拿下警徽,以「男人對男人」的方式來解決彼此的歧異。
Madness and Powerlessness
找到生命,便找到權力的意志(will to pow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權力是一切生物的根本。尤其是人類,數十億年前被拋到這荒瘠的地球表面上,期待存活,也必須求生;他們在每次與天地人群的競爭中,都必須運用權力並面對挑戰的勢力。雖然人類自始以來就感到不安,被局限與脆弱摧折、被疾病侵擾,最終被死亡擊倒,但是卻反而因此肯定了自己的創造力。文明就是這樣的成果之一。
我不把權力看成是用來屈辱他人或用到敵人身上的字詞,而是把它當成對生命過程的基本面向的描述。它與生命本身不能劃上等號;人類存在的內涵遠甚於此──諸如好奇、關愛與創意等,也許在一般情況下的確與權力有關,但其本身卻不應被稱為權力。但是,如果我們忽略權力這個因素,像平日那樣反抗濫用權力造成的毀滅性後果的話,我們便會失去做人的基本價值。
請承認我們個人是無能的──我們無法影響他人,我們無足輕重,我們父母一生信奉不渝的價值對我們毫無意義,我們像奧登(W. H. Auden)筆下「『無名的他者』」那樣,對他人和自己都不值一文──真是情何以堪。過去四十年來,關於個人能力與潛能的言論是這樣地多,但是對於個人具有在心理與政治上改變現況能力的信心卻是少得可憐。這類言談至少有一部分是基於補償心理所顯現的症狀,因為我們不安地發覺到自己的權力喪失了。
因此,在人類認為以按鈕的方式便可將地球毀滅的過渡年代裡,有人會提議人類放棄此一恐怖的實驗,是可以理解的。克拉克醫師(Dr. Kenneth B. Clark)在美國心理學會會長的就職典禮中論證說: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中,要信任個人的心情與選擇,是太危險的事了。……我們不再能掌控當權者,因此必須靠鎮定劑來控制我們的領袖。」慮及克拉克熟知紐約哈林區及黑人族裔的無力感才有此提議的背景,我們可以同情他的絕望論調。但是我們不能不了解,當化學藥物立意要治療當代人的侵略性,並發展其「合群」人格時,卻發現藥物的使用與人格的萎靡以及個人責任感的消失,是息息相關的,讀來怎不令人沈痛。這樣的改變實際上意味著人性正逐漸喪失。無能與冷漠乃是孕生暴力的溫床。沒錯,因為侵略性一向被提升到暴力的層次,所以人們會對它感到害怕或不喜歡,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是,無能的狀態會造成冷漠,也會因上述根除侵略性的計劃而產生;它是暴力的源頭。當我們使人們無能為力時,我們正鼓動而非控制了暴力。我們社會中的暴力行為,大多是出自那些試圖建立自尊、護衛自我形象,或想顯現自己份量的人。不論這些動機有多偏差,是如何被誤用,或是其展現多具破壞性,它們仍舊是人際需求的正向呈現。我們不能漠視的事實是,儘管要導正這些需求十分困難,但是它們的確具有建設性的潛能。暴力不是出於權能的過剩,而是來自無能。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猶太人,德國哲學大師海德格的學生,兩人亦曾發生戀情)說得好:暴力是無能的表現。
無能的腐化
多年前當我開始心理治療師的生涯時,無能與精神病的關係便讓我印象深刻。心理治療師可以在精神受困者的身上,看到極端的行為以及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經驗。這佐證了弗登堡(Edgar Z. Friedenberg)所說的話:「一切的軟弱都會腐化,無能則會帶來絕對的腐化。」
普莉西拉(Priscilla)這位年輕的音樂家,是我最早的案主之一。根據為她做羅氏墨漬測驗(Rorschach,譯註:由當事人對墨水點繪圖形的解釋,以判斷其性格)的人員所述,她的「一隻腳落在精神分裂症的領域,另一隻腳則踩在香蕉皮上(譯註:表示岌岌可危)。」在我和她會談的那些時段,她會長篇大套、巨細靡遺地比較從紐沃克(Newark)開出的火車的音符顏色,和從紐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開出的火車的音符顏色有何不同。我對她所說的內容大多毫無頭緒──這點她也知道。但是她似乎就需要有我這麼一位肯傾聽、願意試著去了解她的人,不管我懂了沒。她也是一位矜持自重、具有幽默感的女士,這些特質後來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但是,她從不生氣。無論是對我、對她父母或對任何人,都是如此。她的自尊薄弱模糊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樣。有一次,和她同屬一個合唱團的年輕人,邀請她一起去參加一個音樂會。她接受了。但是第二天,一股頓生的自我懷疑促使她打電話給對方說:「如果你不願意,就不用帶我去。」她自信不足,不覺得有人會想要和她一起去參加音樂會。她在八、九歲的時候,曾經和一位比她年紀稍長的男孩玩足球;他用力撞得使她受了傷。其他孩子可能會向對方吼叫,或打架、哭鬧、不願再玩;這些反應不論好壞,都是因應的方式。但是普莉西拉完全沒用這些方法;她只是坐在地上看著男孩,靜靜地想說,他不應該這麼用力撞她。
當她在財務上或性事上被利用時,她完全不會防衛自己,不知道該如何說「不」,因為沒有足夠的憤怒支持她說不。隨著她無法生氣這件事而來的後果,就是一種深沈的無能經驗,以及幾乎無法在人際關係中去影響他人的處境。
但是,這樣的人有著完全不同的一面,這一點我在爾後與許多邊緣性病患的共處經驗中已經獲得確認。普莉西拉的夢不是裝在袋子裡的屍塊,就是血腥與戰爭──簡言之,她的意識生活有多馴良,她的夢就有多暴力。
後來我經常反思無能與瘋狂之間的關係,部分原因也是這位年輕女士的緣故。在此我要刻意強調瘋狂(mad)這字眼的雙重意義:其一是個人的憤怒已達暴力程度的感受;其二是傳統精神醫學對精神病的觀點。這二者之間有其關連,而且這兩種語義的使用將引導我們進入問題的核心。
我們知道,精神病患的共同特徵就是「無能」,這造成了他們的持續焦慮,而焦慮又與他們的軟弱互為因果。病患牢不可破地認定自己是無足輕重的,並且認為這是與生俱來的,在人生歷程中,常常用卑微可憐的姿態去獲取那一丁點的首肯。某位青春期的少女在正午時分來找我諮商時,竟然穿了一件有著篷篷裙的夜禮服,這可能是她最漂亮的衣服之一,她以此表示對我的注目與關心有多在意,但卻沒有覺察到這樣多麼時地不宜。當普莉西拉無法再以這種生活方式過下去時,她的內在便會「垮掉」,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態,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普莉西拉夢裡的暴力現在成了她清醒時的生活內容。當事人似乎完全瘋了,這就是為什麼數百年來精神病會被稱為瘋病的原因。當事人會對所有人都很生氣,包括自己在內,她會威脅或試圖自殺,割腕後將血塗抹在醫院的門上,以戲劇性的手法凸顯出自己對醫護人員的需求。她對自己和所投射的人公開地施行暴力。
我們在其他案主身上也看到同樣的舉動。在描述本身精神分裂症的自傳體小說《未曾許諾的玫瑰花園》中記載著,女主角漢娜.格林(Hannah Green)是在十六歲時被送到栗樹屋療養院的。她是馴良安靜性格的典範,從來不曾發怒。只要她有需要,就會退入自己私密精神世界的神話中,和裡頭的神話角色談話。治療她的精神醫師瑞奇曼尊重漢娜的個人神話,並保證只要漢娜需要,就不會剝奪她的神話。但是當瑞奇曼去歐洲的那個夏天,醫院指派了一位比較年輕的醫師治療漢娜。他樂觀而勇氣十足地衝入漢娜的神話世界,並搗毀了它。結果慘不忍睹。暴力一旦迸發,漢娜便在療養院裡火燒自己和隨身的衣物,要為自己烙印下一輩子的傷疤。這位年輕醫生所犯的錯誤在於,不能體會神話對於漢娜存在的意義。關鍵不是神話在理論上的對錯問題,而是它對漢娜發揮的功能。這位沈靜的病患看似不具侵略性,卻從馴良的一端擺盪到公然暴力的另一端去。
這看起來感覺像是針對醫院照顧人員所施展的權力,但它是一個虛假的權力(pseudo-power),是軟弱無能的表現。如今我們可以說她「瘋了」,意思是她不符合我們社會既定的標準,也就是她沒有穿戴上所有社會皆偏好的馴良「臉面」。被壓抑的怒氣與忿懟,若與因無能而生的持續恐懼相結合,終將導致暴力,了解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在瘋狂的虛假權力背後看到的景象,往往是人們奮力求取某種意義感,以及某種改變現況和建立自尊的方法。我在為普莉西拉進行治療期間,她收到家鄉寄來的一份報紙,報導說她的村子有一位男人自殺了。她對我說:「如果村裡有人認得他的話,他便不會自殺了。」請注意,她不是說「如果他認得某人的話」,而是「如果有人認得他的話」。我相信她在告訴我,只要我繼續陪著她,她便不會以暴力結束生命。然而她也說出了為人所需的至寶──必須有人傾聽、認同和了解。如此人們才會認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他的生命與其他人的一樣重要;也才會給他某種方向感,讓他在這個原本無意義的世界找到一個立足點。
當普莉西拉能對我生氣時,值得大書特書,因為那時我將知道,她在這個廣闊的世界,已經開始懂得在人我交往中保護自己了。更重要的是,她敢於活出自己豐沛的能量,做一個既有原味又討人喜愛的人。
瘋狂與社會
我們在普莉西拉身上看到的消極──瘋狂模式,與已屬當代男女嚴重問題的社會暴力之間,有什麼樣的關連呢?
我有一位朋友,既不是處於被分析的狀況,也不是精神病患;以下是他和太太吵架之後,所感受到那種暴怒之情的自白:
這樣的憤怒和暫時的精神病有多接近啊!當我沿著那條看似遙無止盡的街道走時,我無法思考;我感到暈眩迷亂。但這種模糊困惑只是外在的──在心裡,我是極有精神的,對每個念頭和感受都能敏銳地覺察,彷彿自己置身在一個光明透亮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非常逼真。我唯一的困擾是,這種內在的清醒和外在世界可說毫無關連。
說到我與外在世界的聯繫,我略感羞赧──羞赧而且無力抗拒。如果有人嘲弄我,或突然極為需要我(譬如說街上發生了車禍),我將無法反應。如果我有所回應,就必須顯露出我的「瘋狂」;它會一股腦兒地爆裂開來。
街道是陌生的;雖然人們一如往常在路上走著,但是街道看起來卻空蕩蕩的。我對那些街道覺得生疏(雖然我曾見過它們千百次)。
我像酒醉般地走著,抬起腿來,又刻意地放了下來。我走進一家餐廳,很怕出納小姐認不得我──我的膚色不一樣了──或者她會以為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她確實認得我,也如往常般友善)。我走進男生廁所,不帶任何情緒地讀著如廁區上方的塗鴉。我仍舊害怕有人會要我做什麼或侵略我,而我卻無法抵抗。我回到座位上,盯著餐廳盡頭的窗子往外看。我覺得與世界只有模糊的關連。食物送上來了;我對於吃或品嚐食物沒太大興趣;我只是糊里糊塗地完成動作。
我試著回想我們爭吵的細節,卻徒勞無功──只有兩三件事非常清楚地浮現出來;其餘的則是一團亂。我只吃了一點點。
侍者走了過來,他是一位中年的中國人,他對我說:「我覺得你想太多了。」他指指自己的前額。「你有困難嗎?」我笑著點點頭。他繼續說:「近來人人都有麻煩事。」他的話有種奇異的舒緩作用。他搖著頭走開。這是我對外在世界的第一次突圍。它使我大笑起來,對我有莫大的幫助。
我了解,當這種狀態漫長地持續下去,人們會做出傷害自己的事情來,例如站到車子前面等著被撞。他們會這麼做多半是因為對周遭的真實世界欠缺覺察。他們也會出於報復而這麼做,或拿出一把槍來殺人。
陷入這種暴怒情緒中的經驗,與歷史記載中的「瘋狂」經驗,相去不遠了。例如,以下是一位哈林區的年輕黑人所陳述的「瘋狂」意義:
那些白人條子,他們有種可惡的虐待本性。……哈林區不需要他們!……他們引起的暴力比任何人都多。……當我們無法回家而在街頭跳舞時,就來了個條子,追趕著每個人。他瘋了。我的意思是他真的瘋了!……他又氣又瘋地跑到這附近來。
這位黑人說的是,警察的「瘋狂」與哈林區的暴力是有關連的。警察是否以誘發暴力反應的方式激怒自己,來維護他所認定的法律與秩序呢?這是否是人們選擇當警察的原因之一呢?難道他只要緊抓住被文化認可的精神病,並以此和保守的社會現狀站在同一陣線,就可以使他在值勤時,合法地攜帶警棍和警槍發洩暴力嗎?
犯罪學教授托赫(Hans Toch)在《暴力人》(Violent Men)一書中的逐字報告,可以讓我們更仔細地來考量這些問題。譬如,托赫相信:
黑人小孩與白人警察──他們的驕傲、恐懼、孤立、需要自我肯定,特別是需要被尊重──有著奇異的相似性;雙方都是受害者,都是囚犯,受制於日益升高卻不是由他們造成的衝突。根據他們自己的報告顯示,警察覺得他們必須維護「法律與秩序」,而且把此舉和他們個人的自尊與男子氣概劃上等號。警察長久以來從「法律與秩序」的概念,在自己內心中投射延伸出一場證明自己有無能力的戰爭來。某位接到家庭糾紛報案的警官,看到一位坐在車內的黑人,他認為對方可以為這件口角之爭提供相關的線索:
警官叫黑人走到車外。黑人回答說:「你不能叫我這麼做。我是在私有的領域裡。」警官的報告說,這黑人看起來很討厭,他的「態度讓我很煩」。
黑人最後出來到車外,但是雙手一直插在防水夾克的口袋內。此舉仍舊讓警官很討厭,於是叫黑人把手拿出來。由於黑人一再拒絕配合,警官於是叫來另一名警察,他們一起迫使黑人把手伸出口袋。
警察認為這是蔑視權威,是不可原諒的。他必須不計代價地伸張警察的權威。……(「我覺得黑人將手從口袋伸出來,是絕對必要的。……我們抓住他時,他便開始惡言相向。……我們逮捕他,並讓他坐上巡邏車後座,他恐嚇說要小便在座位上,並在玻璃窗上又踢又搥的。」)
在此案例中,這個黑人認為,做為白人政府武力,以及整個黑人族群敵人的警察,任意地羞辱了他。他確實沒錯,因為警察必須恐嚇黑人來維持權威。二者都是「暴力人」。事件中制服警察的藍色勢力與黑人的黑色勢力,乃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各自都為保護自我形象,保護自己做為「人」的感覺而不遺餘力。只是因為警察代表法律執行者,而且佩了警徽和警槍,所以特別具有優勢。警力中的「暴力人」,托赫寫道,是「有本事把人際互動提升到爆炸性情勢的專家」。「嫌犯」通常會覺得自己處於極為不利的位置;他的「決鬥」對手以警徽和警槍為掩護,以至於「嫌犯」往往會挑釁警官要他拿下警徽,以「男人對男人」的方式來解決彼此的歧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