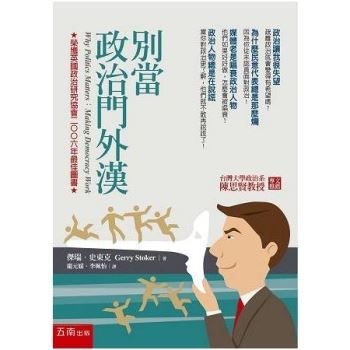第一篇 大眾民主政治:勝利與失望
第一章 民主的勝利?
「一九九七年夏季,我接受日本某大報訪問,請我說出一件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大事。這個問題可不簡單,必須仔細思考,因為過去一百年來發生不少大事…不過這個問題也難不倒我,我認為民主政治崛起是二十世紀的頭號大事,並不是說其他事情就不重要,我只是認為在遙遠的將來,大家回頭看看二十世紀,一定會認為很難不把民主政治崛起,成為全世界最成功最受歡迎的政治制度,視為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阿馬帝亞.森(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阿馬帝亞.森認為民主政治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最大成就,當然二十世紀值得稱頌的大事還有很多,包括世界各國經濟福利提升,以及人類的太空之旅,不過筆者認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大成就仍然是建立民主制度。二十世紀末,全球掀起民主化浪潮,如今政治活動多半出現在公民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公民得以透過民主程序與民主機構表達意見、行使權力以及參與決策。本章介紹民主政治如何成為廣受歡迎的制度,進而影響人類社會的集體決策。另外探討民主政治的本質,筆者認為民主制度應該受到保護,並舉例說明這不僅是西方國家思想,也符合普世價值。本章接著探討民主政治普及的過程,在結尾提出多民族國家的「黑暗面」,民主政治的觀點遭到扭曲,淪為「種族淨化」的藉口。儘管如此,本章還是要總結:民主萬歲。
民主政治的本質
大眾民主政治保障所有達到法定年齡公民的投票權,是二十世紀初幾十年才出現的新治理制度,不過民主政治的概念至少在兩千多年前希臘城邦時代就已經出現,最近幾十年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治理制度。
我們把民主政治定義為符合以下三項條件的政治制度:
●普選權,亦即所有達到法定年齡的公民都有選舉權
●透過定期、自由的競爭性選舉選出的政府
●人民享有各項政治權利,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
即使以這麼寬鬆的標準來看,一九〇〇年還是沒有一個國家有資格稱為「民主國家」,因為當時沒有一國舉辦普選。到了一九五〇年,全球三分之一左右的國家大致符合這三項條件。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全球掀起民主化巨浪,民主國家數量增至全球三分之二左右。民主政治如今已經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治理制度,享有絕佳地位。
實行民主政治是許多領袖以及全體人民奮鬥的結果,一九九〇年代南非總統曼德拉的故事相信許多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在艱困環境中為民主奮鬥的故事。一九八〇年代,波蘭以及其他東歐國家歷經長期努力,終於實現民主政治。在這之前,二十世紀初延續了上個世紀的女性投票權運動,結果芬蘭拔得頭籌,於一九〇六年首度給予女性普選權。
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民主化浪潮是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最明顯的是英國、法國與其他西方強權殖民時代結束。第二個因素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西歐國家獨裁政權垮台。第三個因素是前蘇聯(FSU)瓦解,以及前蘇聯在中歐與東歐(CEE)的衛星國解放。第四個因素是民主政治在拉丁美洲與亞洲重新崛起。
經濟發展改變了社會階級、族群以及女性的地位,也等於改變了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原動力,南韓、台灣、巴西與墨西哥的經驗就是明證。在某些例子,獨裁政權拿不出經濟成績,必須承受「民主政治比較會拼經濟」的挑戰。重點在於民主轉型要能順利成功,執政菁英與新崛起的政治勢力之間必須妥協。歐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某些國家的經驗就是例子。
關於民主化的辯論或多或少有些改變。傳統觀點偏向討論國家架構與國家領導人能否提供適合民主政治發展的環境與條件,通常假設民主政治是一種獨特的治理制度,需要良性的環境才能發展成熟。近來討論的重點已經變成全球因素與國際因素。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間開始倡導民主政治的大業。美國與歐盟(EU)也一致推崇民主政治是正確的道路,值得其他國家採納,雖然美國與歐盟也不是一直都提倡民主政治。最後,有國際上巨大的壓力主張人權與民主政治是基本權利,推廣民主政治已經是國際社會重量級國家明白宣示的目標。
民主政治是普世價值
究竟何謂「民主政治」?我們應該一開始就明確界定民主政治,先前提到民主政治是過濾社會決策的一套程序與機構。民主政治是一套治理制度,也就是社會進行集體決策的制度,需要自由、公正與競爭的選舉,透過普選選出政府領導人,選舉結果也應該受到全民尊重。民主政治也應尊重人民的各項自由與基本權利,要能貫徹正義,尊重法治,人民要能自由交換意見,新聞與意見的流通應該不受審查。民主政治即使要做到這些多數人眼中的基本要求,都需要整個社會付出許多。
有人認為民主政治絕不只是前面形容的一些社會決策。本書採用的民主政治觀點強烈偏向所謂的「現實主義陣營」,重點放在決策的作業制度,而非遙不可及的夢想。這個模型提倡平等主義,強調人民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受到的保障也平等,而非堅稱廣義的經濟平等或社會平等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筆者認為民主政治最終還是需要人民深入參與,不是只有投票選出政治領導人而已,重點在於人民參與政治的能力,以及人民影響政策辯論與結果的能力。民主政治與民主治理不同,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受決策影響的人民都有權表達意見。至於人民的權限應該有多大,以及人民對民主治理制度應該有哪些期待,都是本書一再討論的主題,在第九章會特別詳述。
目前要強調的是關於民主政治還有其他論述,其中不少比筆者更強調直接參與的重要,並且強烈主張必須先建立平等環境,民主政治才能蓬勃發展。的確,在各國民主化的進程當中,人民對於民主政治能帶來哪些好處以及民主政治的意義難免看法不一。這些不同的意見也是靈感與紛爭的來源,如果民主政治最後沒有成功,這些不同的意見就會變成失望,比方說在某些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化進程與其他變遷(如市場經濟)同時發生,像南非就是一邊進行民主化,一邊建立後種族隔離社會。如果民主政治無法支援經濟發展或更平等的社會,就會失去正當性以及人民的支持。這些議題在本書都會討論,本書稍後要討論的還包括在大多數民主國家,更多人民參與政治、重振政治的機率。
有人認為民主政治完全是西方的概念。有些西方政治人物的確宣稱民主政治是西方的產物,不過這種說法有待商榷。有些受到西方強國掌握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就大力稱讚西式民主是一種良性治理制度,不過不能因為這樣就認定民主政治只不過是西方出口貨。
民主政治應該是一種普世價值,如同諾貝爾獎得主阿馬帝亞.森所言:
「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社會環境,都有一些席捲社會的思想,躍升成為普遍的規則,就好像是電腦程式的「隱含值」一樣,除非有人否定,否則大家都不會質疑。雖然並非全世界都實行民主政治,也不是全世界都接受民主政治,但全球人民普遍認為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一種普世權利。」
民主政治並不是因為大家都認同才成為普世價值,的確,任何一種普遍得到認可的價值都很容易變成「媽媽經與做菜經」之類的空泛觀念,沒有人會反對。可是民主政治比媽媽經、做菜經複雜得多。民主政治是歷經千辛萬苦才得以實現,也贏得世人的尊敬。民主政治之所以成為普世價值,是因為「世界各國的人民都能體會民主政治的價值」。
不過還是有評論者主張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因為文化因素或實際上根本無法實行民主政治。哈佛大學教授山繆.杭廷頓主張世界現在來到前所未有的階段,面臨文明之間的基本衝突,西方對抗其他地區。西方的勢力與優勢是對立的來源,不過根本原因還是價值衝突。諸如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法治等「西方」價值在伊斯蘭文化、儒家文化等非西方文化很難引起共鳴。根據這位哈佛大學教授所言,現實情況就是「現代民主政府是西方的產物,會出現在非西方社會通常是西方殖民主義以及西方勢力強加於上的結果。」用沒那麼學術的口吻來說就是「阿拉伯人與非洲人就是不喜歡民主政治。」
杭廷頓認為西方運用勢力達到目的引起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憎恨,這話也許沒錯,西方過於倉促的將商業帝國主義以及政治帝國主義套用在思想與商品上,埋下對立的禍根。他認為民主政治是西方的禁臠,這點不見得對。民主政治在西方國家之外的地方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西方的殖民或干預,根本就是不了解歷史。光是印度人與南非人就可以澄清他們國家的民主政治絕對不是西方的功勞。杭汀頓在一九九三年發表文章探討文明之間的衝突,後來的情況就如同先前提到,民主政治在伊斯蘭地區、儒家地區以及非洲與拉丁美洲大為盛行,絕對不是西方才有民主政治。
筆者反對「文明之間的衝突」的理論有一個基本原因,這種想法假設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文明的思想與行為都是同質。但是就像阿馬帝亞.森所言,「世界上多數文化都有多元特質」,所以主張西方思想顯示「西方一千多年來對民主政治的堅持,又以各種非西方傳統(每一種都是一個整體)對抗西方思想是大錯特錯。」伊斯蘭傳統以及其他傳統其實也允許民主政治,西方思想也不見得都認同民主政治。與民主政治分庭抗禮的獨裁主義也是西方思想的核心,也曾經在西方歷史出現。
民主政治能吸引這麼多人,主要原因有三。如同阿馬帝亞.森所言,民主政治具備內在性、功能性與建設性的特質,所以能夠吸引人。民主政治的內在價值相信願意與他人共同決策是人性的一部分,這個內在價值也得到政治哲學家大加讚揚。參與社區政治活動能讓我們的人生更為全面,也獲得表達意見的機會。
有些人會認同內在特質的理論,有些人則不認同。這種想法看待政治似乎太過浪漫,甚至有點模糊,筆者需要看到更為實際的觀點才能認同。除非能達到某些目的,否則一般人能一直支持一個程序(如民主政治)多久?要推銷民主政治,最好告訴人民「民主政治能帶給你心之所欲」。由此就能看出民主政治的功能性有多重要。不過宣傳政治的市場性要特別小心,民主政治不能保證你的生活幸福快樂,卻能降低災難降臨在你頭上的機會。一項研究顯示「民主機構與身體健康之間可能有很大的關係,民主國家的人民平均壽命也較長。阿馬帝亞.森能贏得諾貝爾獎,部分原因在於他證明了嚴重飢荒不會發生在民主國家,近來的飢荒發生在伊索比亞與索馬利亞兩個獨裁國家,另外歷史上的幾次大飢荒,如一九三〇年代蘇聯的大飢荒,以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飢荒都是發生在獨裁政權。證據擺在眼前,一清二楚,阿瑪蒂亞.森的解釋也一針見血:
「如果真的有心預防飢荒,一定可以做到。民主國家的政府要面臨選舉的壓力,還要面對在野黨與獨立報紙媒體的批評,想偷懶不做也沒辦法。」
諸事順利的時候,人民可能不會想起民主政治的功能價值。一旦出了問題(早晚一定會出問題),人民就會需要民主政治,因為政府的行事決策只要有考慮人民的福祉,就能在民主政治中得到好處。民主政治也提供了一個機制,確保政府只能得到某些好處。
最後,民主政治的確能為棘手的問題與挑戰找尋出路,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設性價值。我們面臨的難題大部分能用開放對話解決,透過開放對話,人民可以分享想法、學習以及思考問題,公開討論議題能帶來截然不同的效果。有些審議民主學家認為政治必須完全透明,但是政治有時是透過打迷糊仗完成。政治用不同的方式解讀同一件事情,讓意見相左的人民得以攜手向前,可說是功德無量。我們不願意承認,但是民主政治必須仰賴「詭辯之詞」與檯面下交易,人民往往無法立即得到滿足,還要用一些模糊的手段讓所有方面都能宣稱自己是贏家,就算落敗也能保住尊嚴。
由此可見民主政治的確堪稱普世價值,民主政治不是西方特有的治理方式,而是全球人民最認同的決策制度。民主政治以不同的方式發揮功能,在許多混亂與妥協中達到目的。民主政治有不少侷限,發揮的作用也有限,卻是最近幾十年全球多數國家的共同選擇,下一節將詳細討論這一點。
第一章 民主的勝利?
「一九九七年夏季,我接受日本某大報訪問,請我說出一件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大事。這個問題可不簡單,必須仔細思考,因為過去一百年來發生不少大事…不過這個問題也難不倒我,我認為民主政治崛起是二十世紀的頭號大事,並不是說其他事情就不重要,我只是認為在遙遠的將來,大家回頭看看二十世紀,一定會認為很難不把民主政治崛起,成為全世界最成功最受歡迎的政治制度,視為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阿馬帝亞.森(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阿馬帝亞.森認為民主政治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最大成就,當然二十世紀值得稱頌的大事還有很多,包括世界各國經濟福利提升,以及人類的太空之旅,不過筆者認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大成就仍然是建立民主制度。二十世紀末,全球掀起民主化浪潮,如今政治活動多半出現在公民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公民得以透過民主程序與民主機構表達意見、行使權力以及參與決策。本章介紹民主政治如何成為廣受歡迎的制度,進而影響人類社會的集體決策。另外探討民主政治的本質,筆者認為民主制度應該受到保護,並舉例說明這不僅是西方國家思想,也符合普世價值。本章接著探討民主政治普及的過程,在結尾提出多民族國家的「黑暗面」,民主政治的觀點遭到扭曲,淪為「種族淨化」的藉口。儘管如此,本章還是要總結:民主萬歲。
民主政治的本質
大眾民主政治保障所有達到法定年齡公民的投票權,是二十世紀初幾十年才出現的新治理制度,不過民主政治的概念至少在兩千多年前希臘城邦時代就已經出現,最近幾十年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治理制度。
我們把民主政治定義為符合以下三項條件的政治制度:
●普選權,亦即所有達到法定年齡的公民都有選舉權
●透過定期、自由的競爭性選舉選出的政府
●人民享有各項政治權利,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
即使以這麼寬鬆的標準來看,一九〇〇年還是沒有一個國家有資格稱為「民主國家」,因為當時沒有一國舉辦普選。到了一九五〇年,全球三分之一左右的國家大致符合這三項條件。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全球掀起民主化巨浪,民主國家數量增至全球三分之二左右。民主政治如今已經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治理制度,享有絕佳地位。
實行民主政治是許多領袖以及全體人民奮鬥的結果,一九九〇年代南非總統曼德拉的故事相信許多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在艱困環境中為民主奮鬥的故事。一九八〇年代,波蘭以及其他東歐國家歷經長期努力,終於實現民主政治。在這之前,二十世紀初延續了上個世紀的女性投票權運動,結果芬蘭拔得頭籌,於一九〇六年首度給予女性普選權。
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民主化浪潮是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最明顯的是英國、法國與其他西方強權殖民時代結束。第二個因素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西歐國家獨裁政權垮台。第三個因素是前蘇聯(FSU)瓦解,以及前蘇聯在中歐與東歐(CEE)的衛星國解放。第四個因素是民主政治在拉丁美洲與亞洲重新崛起。
經濟發展改變了社會階級、族群以及女性的地位,也等於改變了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原動力,南韓、台灣、巴西與墨西哥的經驗就是明證。在某些例子,獨裁政權拿不出經濟成績,必須承受「民主政治比較會拼經濟」的挑戰。重點在於民主轉型要能順利成功,執政菁英與新崛起的政治勢力之間必須妥協。歐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某些國家的經驗就是例子。
關於民主化的辯論或多或少有些改變。傳統觀點偏向討論國家架構與國家領導人能否提供適合民主政治發展的環境與條件,通常假設民主政治是一種獨特的治理制度,需要良性的環境才能發展成熟。近來討論的重點已經變成全球因素與國際因素。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間開始倡導民主政治的大業。美國與歐盟(EU)也一致推崇民主政治是正確的道路,值得其他國家採納,雖然美國與歐盟也不是一直都提倡民主政治。最後,有國際上巨大的壓力主張人權與民主政治是基本權利,推廣民主政治已經是國際社會重量級國家明白宣示的目標。
民主政治是普世價值
究竟何謂「民主政治」?我們應該一開始就明確界定民主政治,先前提到民主政治是過濾社會決策的一套程序與機構。民主政治是一套治理制度,也就是社會進行集體決策的制度,需要自由、公正與競爭的選舉,透過普選選出政府領導人,選舉結果也應該受到全民尊重。民主政治也應尊重人民的各項自由與基本權利,要能貫徹正義,尊重法治,人民要能自由交換意見,新聞與意見的流通應該不受審查。民主政治即使要做到這些多數人眼中的基本要求,都需要整個社會付出許多。
有人認為民主政治絕不只是前面形容的一些社會決策。本書採用的民主政治觀點強烈偏向所謂的「現實主義陣營」,重點放在決策的作業制度,而非遙不可及的夢想。這個模型提倡平等主義,強調人民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受到的保障也平等,而非堅稱廣義的經濟平等或社會平等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筆者認為民主政治最終還是需要人民深入參與,不是只有投票選出政治領導人而已,重點在於人民參與政治的能力,以及人民影響政策辯論與結果的能力。民主政治與民主治理不同,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受決策影響的人民都有權表達意見。至於人民的權限應該有多大,以及人民對民主治理制度應該有哪些期待,都是本書一再討論的主題,在第九章會特別詳述。
目前要強調的是關於民主政治還有其他論述,其中不少比筆者更強調直接參與的重要,並且強烈主張必須先建立平等環境,民主政治才能蓬勃發展。的確,在各國民主化的進程當中,人民對於民主政治能帶來哪些好處以及民主政治的意義難免看法不一。這些不同的意見也是靈感與紛爭的來源,如果民主政治最後沒有成功,這些不同的意見就會變成失望,比方說在某些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化進程與其他變遷(如市場經濟)同時發生,像南非就是一邊進行民主化,一邊建立後種族隔離社會。如果民主政治無法支援經濟發展或更平等的社會,就會失去正當性以及人民的支持。這些議題在本書都會討論,本書稍後要討論的還包括在大多數民主國家,更多人民參與政治、重振政治的機率。
有人認為民主政治完全是西方的概念。有些西方政治人物的確宣稱民主政治是西方的產物,不過這種說法有待商榷。有些受到西方強國掌握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就大力稱讚西式民主是一種良性治理制度,不過不能因為這樣就認定民主政治只不過是西方出口貨。
民主政治應該是一種普世價值,如同諾貝爾獎得主阿馬帝亞.森所言:
「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社會環境,都有一些席捲社會的思想,躍升成為普遍的規則,就好像是電腦程式的「隱含值」一樣,除非有人否定,否則大家都不會質疑。雖然並非全世界都實行民主政治,也不是全世界都接受民主政治,但全球人民普遍認為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一種普世權利。」
民主政治並不是因為大家都認同才成為普世價值,的確,任何一種普遍得到認可的價值都很容易變成「媽媽經與做菜經」之類的空泛觀念,沒有人會反對。可是民主政治比媽媽經、做菜經複雜得多。民主政治是歷經千辛萬苦才得以實現,也贏得世人的尊敬。民主政治之所以成為普世價值,是因為「世界各國的人民都能體會民主政治的價值」。
不過還是有評論者主張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因為文化因素或實際上根本無法實行民主政治。哈佛大學教授山繆.杭廷頓主張世界現在來到前所未有的階段,面臨文明之間的基本衝突,西方對抗其他地區。西方的勢力與優勢是對立的來源,不過根本原因還是價值衝突。諸如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法治等「西方」價值在伊斯蘭文化、儒家文化等非西方文化很難引起共鳴。根據這位哈佛大學教授所言,現實情況就是「現代民主政府是西方的產物,會出現在非西方社會通常是西方殖民主義以及西方勢力強加於上的結果。」用沒那麼學術的口吻來說就是「阿拉伯人與非洲人就是不喜歡民主政治。」
杭廷頓認為西方運用勢力達到目的引起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憎恨,這話也許沒錯,西方過於倉促的將商業帝國主義以及政治帝國主義套用在思想與商品上,埋下對立的禍根。他認為民主政治是西方的禁臠,這點不見得對。民主政治在西方國家之外的地方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西方的殖民或干預,根本就是不了解歷史。光是印度人與南非人就可以澄清他們國家的民主政治絕對不是西方的功勞。杭汀頓在一九九三年發表文章探討文明之間的衝突,後來的情況就如同先前提到,民主政治在伊斯蘭地區、儒家地區以及非洲與拉丁美洲大為盛行,絕對不是西方才有民主政治。
筆者反對「文明之間的衝突」的理論有一個基本原因,這種想法假設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文明的思想與行為都是同質。但是就像阿馬帝亞.森所言,「世界上多數文化都有多元特質」,所以主張西方思想顯示「西方一千多年來對民主政治的堅持,又以各種非西方傳統(每一種都是一個整體)對抗西方思想是大錯特錯。」伊斯蘭傳統以及其他傳統其實也允許民主政治,西方思想也不見得都認同民主政治。與民主政治分庭抗禮的獨裁主義也是西方思想的核心,也曾經在西方歷史出現。
民主政治能吸引這麼多人,主要原因有三。如同阿馬帝亞.森所言,民主政治具備內在性、功能性與建設性的特質,所以能夠吸引人。民主政治的內在價值相信願意與他人共同決策是人性的一部分,這個內在價值也得到政治哲學家大加讚揚。參與社區政治活動能讓我們的人生更為全面,也獲得表達意見的機會。
有些人會認同內在特質的理論,有些人則不認同。這種想法看待政治似乎太過浪漫,甚至有點模糊,筆者需要看到更為實際的觀點才能認同。除非能達到某些目的,否則一般人能一直支持一個程序(如民主政治)多久?要推銷民主政治,最好告訴人民「民主政治能帶給你心之所欲」。由此就能看出民主政治的功能性有多重要。不過宣傳政治的市場性要特別小心,民主政治不能保證你的生活幸福快樂,卻能降低災難降臨在你頭上的機會。一項研究顯示「民主機構與身體健康之間可能有很大的關係,民主國家的人民平均壽命也較長。阿馬帝亞.森能贏得諾貝爾獎,部分原因在於他證明了嚴重飢荒不會發生在民主國家,近來的飢荒發生在伊索比亞與索馬利亞兩個獨裁國家,另外歷史上的幾次大飢荒,如一九三〇年代蘇聯的大飢荒,以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飢荒都是發生在獨裁政權。證據擺在眼前,一清二楚,阿瑪蒂亞.森的解釋也一針見血:
「如果真的有心預防飢荒,一定可以做到。民主國家的政府要面臨選舉的壓力,還要面對在野黨與獨立報紙媒體的批評,想偷懶不做也沒辦法。」
諸事順利的時候,人民可能不會想起民主政治的功能價值。一旦出了問題(早晚一定會出問題),人民就會需要民主政治,因為政府的行事決策只要有考慮人民的福祉,就能在民主政治中得到好處。民主政治也提供了一個機制,確保政府只能得到某些好處。
最後,民主政治的確能為棘手的問題與挑戰找尋出路,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設性價值。我們面臨的難題大部分能用開放對話解決,透過開放對話,人民可以分享想法、學習以及思考問題,公開討論議題能帶來截然不同的效果。有些審議民主學家認為政治必須完全透明,但是政治有時是透過打迷糊仗完成。政治用不同的方式解讀同一件事情,讓意見相左的人民得以攜手向前,可說是功德無量。我們不願意承認,但是民主政治必須仰賴「詭辯之詞」與檯面下交易,人民往往無法立即得到滿足,還要用一些模糊的手段讓所有方面都能宣稱自己是贏家,就算落敗也能保住尊嚴。
由此可見民主政治的確堪稱普世價值,民主政治不是西方特有的治理方式,而是全球人民最認同的決策制度。民主政治以不同的方式發揮功能,在許多混亂與妥協中達到目的。民主政治有不少侷限,發揮的作用也有限,卻是最近幾十年全球多數國家的共同選擇,下一節將詳細討論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