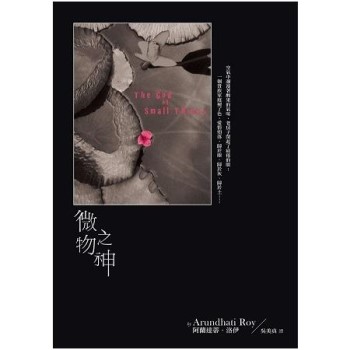天堂果菜醃製廠
阿耶門連的五月是一個炎熱、陰沉沉的月份。白日長而潮溼,河流縮小。黑烏鴉貪婪地吃著靜止、布滿灰塵的綠色芒果樹上那些鮮艷的果實。紅白蕉成熟了,菠蘿蜜脹裂開來。放浪形骸的青蠅在溢滿果香的空氣中,空茫茫地嗡嗡鳴叫著,然後撞在明亮的窗玻璃上,一命嗚呼,肥胖的身體在陽光下顯得不知所措。
夜,澄澈無雲,但瀰漫著懶散的情緒和沉重的期待。
但是到了六月,西南季風吹來。有三個月,風刮著,雨下著,偶爾刺眼、閃爍的太陽才露一下面,而興奮的孩子則趁機大玩一番。鄉間一片恣肆的綠,當插在地上作為籬笆的樹薯枝幹生根且開花時,界限變模糊了。磚牆出現綠苔,胡椒的藤蔓蜿蜒爬上電線桿,野生爬藤植物迸出鋁紅土岸,爬過淹水的道路,船在市集來回穿梭,而小魚兒出現在公共工程部於公路製造的坑洞積水裡。
當瑞海兒回到阿耶門連時,正下著雨,銀繩般斜斜的雨猛擊著鬆散的地面,像炮彈似地將泥土翻起。山上老房子陡陡的山形屋頂低垂下來,像是一頂拉得低低的帽子。布滿苔痕的牆已經鬆動了,而且因地面往上滲出的溼氣而微微膨脹。荒蕪、長滿野草的花園,充滿了小生命的耳語和疾行。矮樹叢中,一隻蛇鼠靠在一塊閃亮的石頭上摩擦身子。滿懷希望的黃色牛蛙在多浮渣的水塘巡行,想尋找配偶。一隻溼淋淋的貓鼬掠過散布著樹葉的車道。
房子本身看起來空蕩蕩的,門和窗都上了鎖。前陽臺光禿禿的沒有任何裝設,但是那輛有鍍鉻尾翼的天藍色普利茅斯仍停在外面;而在屋內,寶寶克加瑪仍然活著。
她是瑞海兒的姑婆,她外公的妹妹。她的真名是娜華蜜——娜華蜜。伊培,但是每個人都叫她寶寶,長到夠當姑媽的年紀時,她變成了寶寶克加瑪。然而,瑞海兒不是來看她的,孫姪女和姑婆都不曾對這件事懷著任何幻想。瑞海兒是來看她的哥哥艾斯沙的。他們是異卵雙胞胎,醫生稱他們為「雙胚子」,這是由兩個分開,但同時受精的卵生成的。艾斯沙——艾斯沙本,比瑞海兒早十八分鐘出生。
艾斯沙和瑞海兒不甚相像,向來都是如此。即使當他們還是手臂細瘦、胸部扁平、飽受寄生蟲折磨、梳著貓王式飛機頭的孩子時,帶著誇張微笑的親戚,或經常來到阿耶門連房子求捐獻的敘利亞正教主教,也不曾像問其他雙胞胎那樣地問他們「誰是誰」,或「哪位是哪位」。混淆藏在更深入、更隱密的地方。
在早先那未定形的幾年,當記憶才剛剛開始,當生命充滿了開始,沒有結束,而一切都是永恆時,艾斯沙本和瑞海兒認為:在一起時,他們是「我」;分開時,他們是「我們」。彷彿他們是罕見的一對暹邏雙胞胎,身體分開,但本性卻相連。
現在,在這些年後,瑞海兒仍記得,她曾在一個晚上醒來,因艾斯沙的一個滑稽的夢而吃吃地笑著。
她甚至有其他她無權擁有的記憶。
例如,雖然她沒有在場,但是她記得在阿布希拉許戲院裡,賣柳橙和檸檬飲料的人對艾斯沙做了些什麼。她記得在前往馬德拉斯的馬德拉斯郵車上,艾斯沙所吃的番茄三明治的味道。
而這些只是瑣屑的事情。
不管怎樣,現在她認為艾斯沙和瑞海兒是「他們」,因為分開時,這兩個人不再是以前的「他們」,或他們曾經想像過的「他們」。
曾經。
現在,他們的生命有了一個尺寸和形式。艾斯沙有他自己的尺寸和形式,瑞海兒也有她自己的尺寸和形式。
邊緣、邊界、分界線和界限,在他們個別的地平線上出現,就像一群侏儒——有著長長的影子,在「模糊的末端」巡視的小矮人。柔和的半月形眼袋在他們的眼下形成了,現在他們和阿慕死時一樣大。三十一歲。
不算老。
也不算年輕。
一個可以活著,也可以死去的年齡。
他們幾乎是在公車上出生的,艾斯沙和瑞海兒。他們的父親開車載他們的母親阿慕到席隆的醫院生產,但這輛車子在阿薩姆一條蜿蜒的茶莊道路上故障了。他們丟下那輛車子,揮旗讓一輛擁擠的州交通部的公車停下來。坐在車上的乘客帶著一種窮人對於較富裕的人所懷有的奇怪憐憫讓位給他們,或者,他們這樣做只是因為看到阿慕奇大的肚子。在剩下的旅程中,艾斯沙和瑞海兒的父親必須抱住他們母親的肚子(以及肚子裡的他們),以免肚子搖搖晃晃。這是在他們離婚,而阿慕回到克洛拉居住之前。艾斯沙認為,倘使他們在公車上出生,那麼他們這一生將可免費搭公車。不知他們從哪裡得知這類事情,或者如何得知這類事情。但是有幾年時間,這對雙胞胎對於他們的父母懷著一種隱約的不滿,因為父母毀掉了他們終生免費搭公車的權利。
他們也相信,倘使他們在過斑馬線時被車子撞死了,那麼政府會負擔他們的葬禮費用。他們十分肯定地認為,斑馬線就是為了這目的而存在的。免費的葬禮。當然了,阿耶門連沒有這種可以讓人被車撞死的斑馬線,甚至科塔亞姆——離此最近的一個鎮——也沒有。但是當他們坐兩個小時的車子去科沁時,曾在途中,從車窗看到了一些這樣的斑馬線。
政府從來沒有負擔蘇菲默爾的葬禮費用,因為她不是在斑馬線上被撞死的。她的葬禮是在阿耶門連的一間剛上漆的老教堂舉行的。她是艾斯沙和瑞海兒的表姊,也就是恰克舅舅的女兒。她從英國來拜訪他們。當她死時,艾斯沙和瑞海兒七歲,而蘇菲默爾快九歲了。她躺在一個孩子專用的小棺材裡。
有緞子襯裡。
黃銅把手閃閃發光。
她穿著克林普蘭黃色喇叭褲,髮上繫著緞帶,手裡拿著她喜愛的英國製時髦帥氣的袋子。她的面孔蒼白,而且布滿皺紋,就像洗衣者的一根在水裡泡了太久的拇指。教友們聚集在棺材四周,漆成黃色的教堂因憂傷的歌唱聲,而像喉嚨那樣膨脹著。留著卷曲鬍鬚的神父搖動著掛在鏈子上的乳香缽,而且不曾像一般星期日那樣對著嬰兒微笑。
祭壇上的長蠟燭彎曲了,但短蠟燭沒有彎曲。
葬禮上有一個佯稱是遠房親戚的老婦人,沒有人認識她,但她常常於葬禮中出現在屍體旁。一個對於葬禮上了癮的婦人?一個潛在的戀屍癖者?她將古龍水倒在一小塊生棉之上,然後帶著虔誠的模樣和溫和的挑戰神情,拿這塊生棉輕拭蘇菲默爾的額頭。蘇菲默爾聞到了古龍水和棺木的味道。
瑪格麗特克加瑪(蘇菲默爾的英國籍母親)不讓蘇非的生父——恰克,將手臂搭在她身上安慰她。這一家人擠成一團站著。瑪格麗特克加瑪、恰克、寶寶克加瑪,以及她旁邊的嫂嫂瑪瑪奇——艾斯沙、瑞海兒的外婆以及蘇菲默爾的奶奶。瑪瑪奇幾乎看不見了,到屋外時,總是戴著墨鏡。她的眼淚從鏡片後滴下來,沿著她的顎部抖動著,就像屋頂邊的雨滴。她穿著那件乾爽、白裡透灰的紗麗,顯得瘦小而病懨懨。恰克是瑪瑪奇的獨生子,她自己的悲傷令她難過,而他的悲傷則將她擊垮了。
雖然他們容許阿慕、艾斯沙和瑞海兒參加葬禮,但是,他們叫這三人站在一旁,不能和其他家人在一起。沒有人看他們。
教堂裡非常熱,白星海芋花的白色邊緣起皺、卷曲。一隻蜜蜂死在棺材裡的一朵花裡。阿慕的手顫抖著,手中的讚美詩集也跟著顫抖。她的皮膚是冰冷的,艾斯沙靠著她站,幾乎還在睡夢中,疼痛的眼睛閃爍如玻璃,燃燒的臉頰貼在阿慕拿著讚美詩集那顫抖、赤裸的手臂上。
但是瑞海兒卻十分清醒,保持高度的警覺,而且因為正和「真實的生命」戰鬥著,而變得精疲力盡和脆弱。
她注意到蘇菲默爾醒來參加她自己的葬禮。她讓瑞海兒看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是黃色教堂剛剛上漆的高圓頂,瑞海兒以前不曾從裡面觀看它。它被漆成藍色,像天堂那樣,有飄浮的雲朵和颼颼作響、白煙尾巴與雲朵交叉的小噴射機。的確(我們必須說),躺在棺材裡往上看,比站在教堂座席中,被憂傷的臀部和讚美詩集包圍,更容易注意到這些東西。
瑞海兒想到有人費力地拿著刷子、稀釋劑和一罐罐的油漆爬到那兒,白色的油漆用來畫雲,藍色的油漆用來畫天堂,銀色的油漆用來畫飛機。她想像他爬到那兒,某個像維魯沙的男人,光著身子,閃閃發光,坐在一塊木板上,懸吊在教堂高圓頂中的鷹架上,在藍色的教堂天空畫銀色的噴射機。
她想到如果繩子斷裂了,會發生什麼事情。她想像他像一顆黑色的星星那般,從他自己創造的天空掉落下來,支離破碎地躺在發燙的教堂地板上,黑色的血像祕密般,從頭顱流出來。
那時,艾斯沙和瑞海兒已經知道這個世界有將人擊碎的其他方式。他們已經熟悉那氣味,令人噁心的香味,就像微風中即將凋謝的玫瑰的味道。
蘇菲默爾讓瑞海兒看的第二樣東西,是那隻蝙蝠寶寶。在追悼儀式中,瑞海兒看著一隻黑色的小蝙蝠用牠那溫柔緊貼的卷爪,爬上寶寶克加瑪那件葬禮時穿的昂貴紗麗。當牠爬到她的紗麗和上衣之間,爬上她那團似有愁容的脂肪,爬上她赤裸的腰身時,她大聲尖叫,拿她的讚美詩集擊打空氣。教堂內的人停止歌唱,紛紛問「什麼事?怎麼了?」然後蝙蝠颼颼地旋飛,紗麗啪噠啪噠地翻動。
神色憂傷的神父用戴金戒的手指將卷曲的鬍鬚清理乾淨,彷彿幾隻隱密的蜘蛛突然在那兒結了網。
小蝙蝠往上飛入天空,變成一架噴射機,一架白煙尾巴沒有和雲交叉的噴射機。
只有瑞海兒注意到蘇菲默爾在棺材裡祕密地翻筋斗。
憂傷的歌唱聲又響起了,他們將那首憂傷的詩歌唱了兩遍,而黃色的教堂再次像喉嚨般因歌聲而膨脹著。…
【更多精彩內容請翻閱本書】
阿耶門連的五月是一個炎熱、陰沉沉的月份。白日長而潮溼,河流縮小。黑烏鴉貪婪地吃著靜止、布滿灰塵的綠色芒果樹上那些鮮艷的果實。紅白蕉成熟了,菠蘿蜜脹裂開來。放浪形骸的青蠅在溢滿果香的空氣中,空茫茫地嗡嗡鳴叫著,然後撞在明亮的窗玻璃上,一命嗚呼,肥胖的身體在陽光下顯得不知所措。
夜,澄澈無雲,但瀰漫著懶散的情緒和沉重的期待。
但是到了六月,西南季風吹來。有三個月,風刮著,雨下著,偶爾刺眼、閃爍的太陽才露一下面,而興奮的孩子則趁機大玩一番。鄉間一片恣肆的綠,當插在地上作為籬笆的樹薯枝幹生根且開花時,界限變模糊了。磚牆出現綠苔,胡椒的藤蔓蜿蜒爬上電線桿,野生爬藤植物迸出鋁紅土岸,爬過淹水的道路,船在市集來回穿梭,而小魚兒出現在公共工程部於公路製造的坑洞積水裡。
當瑞海兒回到阿耶門連時,正下著雨,銀繩般斜斜的雨猛擊著鬆散的地面,像炮彈似地將泥土翻起。山上老房子陡陡的山形屋頂低垂下來,像是一頂拉得低低的帽子。布滿苔痕的牆已經鬆動了,而且因地面往上滲出的溼氣而微微膨脹。荒蕪、長滿野草的花園,充滿了小生命的耳語和疾行。矮樹叢中,一隻蛇鼠靠在一塊閃亮的石頭上摩擦身子。滿懷希望的黃色牛蛙在多浮渣的水塘巡行,想尋找配偶。一隻溼淋淋的貓鼬掠過散布著樹葉的車道。
房子本身看起來空蕩蕩的,門和窗都上了鎖。前陽臺光禿禿的沒有任何裝設,但是那輛有鍍鉻尾翼的天藍色普利茅斯仍停在外面;而在屋內,寶寶克加瑪仍然活著。
她是瑞海兒的姑婆,她外公的妹妹。她的真名是娜華蜜——娜華蜜。伊培,但是每個人都叫她寶寶,長到夠當姑媽的年紀時,她變成了寶寶克加瑪。然而,瑞海兒不是來看她的,孫姪女和姑婆都不曾對這件事懷著任何幻想。瑞海兒是來看她的哥哥艾斯沙的。他們是異卵雙胞胎,醫生稱他們為「雙胚子」,這是由兩個分開,但同時受精的卵生成的。艾斯沙——艾斯沙本,比瑞海兒早十八分鐘出生。
艾斯沙和瑞海兒不甚相像,向來都是如此。即使當他們還是手臂細瘦、胸部扁平、飽受寄生蟲折磨、梳著貓王式飛機頭的孩子時,帶著誇張微笑的親戚,或經常來到阿耶門連房子求捐獻的敘利亞正教主教,也不曾像問其他雙胞胎那樣地問他們「誰是誰」,或「哪位是哪位」。混淆藏在更深入、更隱密的地方。
在早先那未定形的幾年,當記憶才剛剛開始,當生命充滿了開始,沒有結束,而一切都是永恆時,艾斯沙本和瑞海兒認為:在一起時,他們是「我」;分開時,他們是「我們」。彷彿他們是罕見的一對暹邏雙胞胎,身體分開,但本性卻相連。
現在,在這些年後,瑞海兒仍記得,她曾在一個晚上醒來,因艾斯沙的一個滑稽的夢而吃吃地笑著。
她甚至有其他她無權擁有的記憶。
例如,雖然她沒有在場,但是她記得在阿布希拉許戲院裡,賣柳橙和檸檬飲料的人對艾斯沙做了些什麼。她記得在前往馬德拉斯的馬德拉斯郵車上,艾斯沙所吃的番茄三明治的味道。
而這些只是瑣屑的事情。
不管怎樣,現在她認為艾斯沙和瑞海兒是「他們」,因為分開時,這兩個人不再是以前的「他們」,或他們曾經想像過的「他們」。
曾經。
現在,他們的生命有了一個尺寸和形式。艾斯沙有他自己的尺寸和形式,瑞海兒也有她自己的尺寸和形式。
邊緣、邊界、分界線和界限,在他們個別的地平線上出現,就像一群侏儒——有著長長的影子,在「模糊的末端」巡視的小矮人。柔和的半月形眼袋在他們的眼下形成了,現在他們和阿慕死時一樣大。三十一歲。
不算老。
也不算年輕。
一個可以活著,也可以死去的年齡。
他們幾乎是在公車上出生的,艾斯沙和瑞海兒。他們的父親開車載他們的母親阿慕到席隆的醫院生產,但這輛車子在阿薩姆一條蜿蜒的茶莊道路上故障了。他們丟下那輛車子,揮旗讓一輛擁擠的州交通部的公車停下來。坐在車上的乘客帶著一種窮人對於較富裕的人所懷有的奇怪憐憫讓位給他們,或者,他們這樣做只是因為看到阿慕奇大的肚子。在剩下的旅程中,艾斯沙和瑞海兒的父親必須抱住他們母親的肚子(以及肚子裡的他們),以免肚子搖搖晃晃。這是在他們離婚,而阿慕回到克洛拉居住之前。艾斯沙認為,倘使他們在公車上出生,那麼他們這一生將可免費搭公車。不知他們從哪裡得知這類事情,或者如何得知這類事情。但是有幾年時間,這對雙胞胎對於他們的父母懷著一種隱約的不滿,因為父母毀掉了他們終生免費搭公車的權利。
他們也相信,倘使他們在過斑馬線時被車子撞死了,那麼政府會負擔他們的葬禮費用。他們十分肯定地認為,斑馬線就是為了這目的而存在的。免費的葬禮。當然了,阿耶門連沒有這種可以讓人被車撞死的斑馬線,甚至科塔亞姆——離此最近的一個鎮——也沒有。但是當他們坐兩個小時的車子去科沁時,曾在途中,從車窗看到了一些這樣的斑馬線。
政府從來沒有負擔蘇菲默爾的葬禮費用,因為她不是在斑馬線上被撞死的。她的葬禮是在阿耶門連的一間剛上漆的老教堂舉行的。她是艾斯沙和瑞海兒的表姊,也就是恰克舅舅的女兒。她從英國來拜訪他們。當她死時,艾斯沙和瑞海兒七歲,而蘇菲默爾快九歲了。她躺在一個孩子專用的小棺材裡。
有緞子襯裡。
黃銅把手閃閃發光。
她穿著克林普蘭黃色喇叭褲,髮上繫著緞帶,手裡拿著她喜愛的英國製時髦帥氣的袋子。她的面孔蒼白,而且布滿皺紋,就像洗衣者的一根在水裡泡了太久的拇指。教友們聚集在棺材四周,漆成黃色的教堂因憂傷的歌唱聲,而像喉嚨那樣膨脹著。留著卷曲鬍鬚的神父搖動著掛在鏈子上的乳香缽,而且不曾像一般星期日那樣對著嬰兒微笑。
祭壇上的長蠟燭彎曲了,但短蠟燭沒有彎曲。
葬禮上有一個佯稱是遠房親戚的老婦人,沒有人認識她,但她常常於葬禮中出現在屍體旁。一個對於葬禮上了癮的婦人?一個潛在的戀屍癖者?她將古龍水倒在一小塊生棉之上,然後帶著虔誠的模樣和溫和的挑戰神情,拿這塊生棉輕拭蘇菲默爾的額頭。蘇菲默爾聞到了古龍水和棺木的味道。
瑪格麗特克加瑪(蘇菲默爾的英國籍母親)不讓蘇非的生父——恰克,將手臂搭在她身上安慰她。這一家人擠成一團站著。瑪格麗特克加瑪、恰克、寶寶克加瑪,以及她旁邊的嫂嫂瑪瑪奇——艾斯沙、瑞海兒的外婆以及蘇菲默爾的奶奶。瑪瑪奇幾乎看不見了,到屋外時,總是戴著墨鏡。她的眼淚從鏡片後滴下來,沿著她的顎部抖動著,就像屋頂邊的雨滴。她穿著那件乾爽、白裡透灰的紗麗,顯得瘦小而病懨懨。恰克是瑪瑪奇的獨生子,她自己的悲傷令她難過,而他的悲傷則將她擊垮了。
雖然他們容許阿慕、艾斯沙和瑞海兒參加葬禮,但是,他們叫這三人站在一旁,不能和其他家人在一起。沒有人看他們。
教堂裡非常熱,白星海芋花的白色邊緣起皺、卷曲。一隻蜜蜂死在棺材裡的一朵花裡。阿慕的手顫抖著,手中的讚美詩集也跟著顫抖。她的皮膚是冰冷的,艾斯沙靠著她站,幾乎還在睡夢中,疼痛的眼睛閃爍如玻璃,燃燒的臉頰貼在阿慕拿著讚美詩集那顫抖、赤裸的手臂上。
但是瑞海兒卻十分清醒,保持高度的警覺,而且因為正和「真實的生命」戰鬥著,而變得精疲力盡和脆弱。
她注意到蘇菲默爾醒來參加她自己的葬禮。她讓瑞海兒看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是黃色教堂剛剛上漆的高圓頂,瑞海兒以前不曾從裡面觀看它。它被漆成藍色,像天堂那樣,有飄浮的雲朵和颼颼作響、白煙尾巴與雲朵交叉的小噴射機。的確(我們必須說),躺在棺材裡往上看,比站在教堂座席中,被憂傷的臀部和讚美詩集包圍,更容易注意到這些東西。
瑞海兒想到有人費力地拿著刷子、稀釋劑和一罐罐的油漆爬到那兒,白色的油漆用來畫雲,藍色的油漆用來畫天堂,銀色的油漆用來畫飛機。她想像他爬到那兒,某個像維魯沙的男人,光著身子,閃閃發光,坐在一塊木板上,懸吊在教堂高圓頂中的鷹架上,在藍色的教堂天空畫銀色的噴射機。
她想到如果繩子斷裂了,會發生什麼事情。她想像他像一顆黑色的星星那般,從他自己創造的天空掉落下來,支離破碎地躺在發燙的教堂地板上,黑色的血像祕密般,從頭顱流出來。
那時,艾斯沙和瑞海兒已經知道這個世界有將人擊碎的其他方式。他們已經熟悉那氣味,令人噁心的香味,就像微風中即將凋謝的玫瑰的味道。
蘇菲默爾讓瑞海兒看的第二樣東西,是那隻蝙蝠寶寶。在追悼儀式中,瑞海兒看著一隻黑色的小蝙蝠用牠那溫柔緊貼的卷爪,爬上寶寶克加瑪那件葬禮時穿的昂貴紗麗。當牠爬到她的紗麗和上衣之間,爬上她那團似有愁容的脂肪,爬上她赤裸的腰身時,她大聲尖叫,拿她的讚美詩集擊打空氣。教堂內的人停止歌唱,紛紛問「什麼事?怎麼了?」然後蝙蝠颼颼地旋飛,紗麗啪噠啪噠地翻動。
神色憂傷的神父用戴金戒的手指將卷曲的鬍鬚清理乾淨,彷彿幾隻隱密的蜘蛛突然在那兒結了網。
小蝙蝠往上飛入天空,變成一架噴射機,一架白煙尾巴沒有和雲交叉的噴射機。
只有瑞海兒注意到蘇菲默爾在棺材裡祕密地翻筋斗。
憂傷的歌唱聲又響起了,他們將那首憂傷的詩歌唱了兩遍,而黃色的教堂再次像喉嚨般因歌聲而膨脹著。…
【更多精彩內容請翻閱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