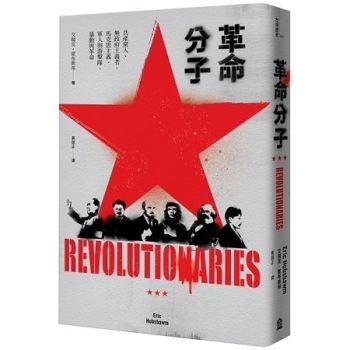知識分子與階級鬥爭(摘文)
也因為這樣,在西方國家的新興革命精神,幾乎都歸知識分子,以及其中邊緣的中產階級(例如具創造力的藝術家),或承認富裕社會的成就,而很正確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該社會缺陷上的年輕中產階級們所專有。先不管像黑人這類不難理解其不滿情緒的特殊少數,典型的革命分子應該是個出身中產階級的年輕人(通常都是學生),而且,他也很想與勞工運動中的左派、社會主義者或共產黨人,劃清界線。即使是像法國的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與義大利一九六九年「熾烈的秋天」,當兩種運動結合在一起,也只有學生才會一腳踢翻資本主義;至於勞工,不論多麼好戰,仍舊在資本主義裡面埋頭苦幹。
我已經說過,一九六○年代後期的這種局面,是短暫的,就像一九一四年以前一樣。這段時期的西方世界,似乎不單是帶著一個對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新解釋,進入一個全新的科技資本主義(有時會被誤稱為「後工業社會」)的境界之中,更明確地說,它是進入了另一段長期的經濟危機。革命運動想要起來對抗的,不是一個「經濟奇蹟」的環境,而是一種經濟上的難題。現在估計其可能引發的基進化政治的數量與種類多寡,還嫌太早。誠然,值得留意的是,在最近一次類似的局面中,右派基進分子比左派的獲利更多。迄今,革命風潮在工業國家中最戲劇性的象徵,仍是在景氣的高峰下,亦即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所開展的那些。如果真要給個預言,一定會覺得光是社會的分崩離析與經濟的萎靡不振兩個因素加起來,就要比各工業國家在兩次大戰之間所發生的任何事故更具爆炸性,除了德國可能是個例外。不過傳統的那種社會革命絕對不是其唯一的,或最可能會產生的結果。
然而,在新興的革命精神,與兩次大戰間的我們這一代的革命精神之間,仍有一個主要的差異。我們曾經擁有過希望,它也許是錯誤的;以及一個可供選擇的社會具體典型:社會主義。今天,這種對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及蘇聯的信仰,已經大幅度消逝了──而且也沒被什麼別的給取代。因為,雖然新興的革命分子正汲汲尋找足以效忠的可能模式或是中心,但是較小的、地方性的革命政權,古巴、北越、北韓之類的,甚至連中國,都無法提供像蘇聯在我們這一時代所給予的相同的東西。在我們觀念中最早浮現的,是一種全盤否定既存社會的仇視與烏托邦,兩者的結合。另外,同樣地,強而有力的革命運動形式,也就是有紀律的群眾政黨,在新興革命分子中也失去了分量。後者似乎寧可以小型的部眾,或接近無政府主義式、結構鬆散的自由派分子集團方式來活動,而不想遵循馬克思主義者的傳統。這一切在歷史上似乎都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它在革命激情與有效的革命行動之間所製造的鴻溝,看來要比我年輕的時代嚴重得多。我舉出這些差異點,心中並無絲毫的快意,也沒有貶抑新興革命分子的意思。擁有一個革命運動,總比什麼都沒有來得強。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能擁有的革命運動,而且我們得盡己所能好好地做。唯一不變的事實是,我們還有很多要學習、或是要重新學習的地方。
最後,讓我改來談談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的角色這個問題。換言之,不是為何他們有些人會變成革命分子,而是作為社會中一個階層的他們,會有什麼樣的政治態度,以及他們這種行動,又將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幾乎用不著我說,這兩個問題是或將會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當然是知識分子,但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的德國知識分子,其數量與所占的比例卻相當少,應該說根本微不足道。我這一代的共產黨學生,在大戰前夕的五萬名大學生裡,僅占相當少數,我猜,最多的時候也不會超過四到五百人;在牛津與劍橋,儘管還不到鳳毛鱗角的地步,但即使是較大的社會主義俱樂部,也只屬於少數人。雖然,在我們這群極少數中,有時會有比例上足以自豪的、最優秀學生。這項事實的確引人側目,但這並不影響一九三九年以前,極大部分的西歐學生都不屬於左派、更甭說是革命派的這個事實。不過,在像南斯拉夫這樣的國家,或許還是有大部分的學生是屬於左派或革命派的吧。
另外,即使我們能夠聲稱,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是富有革命精神的(一般說來,或許在第三世界的年輕知識分子的確容易如此),我們也不能自動就把他們的態度或政治行為,與其他革命力量的態度與政治行為相提並論。就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吧,學生在一八四八年革命裡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但在俾斯麥的時代,這些富有革命精神的自由派分子跑到哪裡去了?再者,在一九○五年的俄國革命中,學生(包括中學生)是極端出色的一群,但是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呢?我們只能說,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不過,這與布爾什維克,以及所有其他反對勢力的群眾政黨領導集團,幾乎清一色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這個事實,並不相抵觸。再舉第三個,而且或許是相當地方性與很快就會消失的例子。今日,英國學生團體整體來說所占的政治位置,很有可能比勞工集團來得更左。但是,就在此時此刻,勞工群眾實施工廠行動的戰鬥性與奮不顧身的精神,要比「大罷工」(編按:一九一六年)之後的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明顯時,學生的集體政治活動卻可能比過去三年內的任何時期都更處於低潮。這兩種集團顯然沒有採取相同的路線,遵循相同的方向,藉著相同的力量與動機來運動。
那麼,我們要如何形容在今天的工業國家中,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知識分子呢?首先,他們在今天,是如此一個不能再被輕易歸類為中產階級的特殊變項集團。他們的數量更多了,因為科技的成長與經濟制度中第三部門(包括管理與溝通)的擴張,對他們的需求較過去增大了不少。他們在技術上被無產階級化了,因為他們之中有大多數都不再是「自由業」或私人企業家,而成了領薪的受雇者;即使對其中大多數的中產階級來說,這也是事實。藉由特殊的舉止態度、特有的消費需求,以及特別的興趣,我們可以辨認出他們來,而生意人也正是如此向他們訴求著。例如,他們讀的是《衛報》而不是《每日電訊報》,而且,他們對訴求地位象徵的商品買賣,像是挑剔某種型式範疇的東西之類的活動,相當無動於衷。今天,在西方國家的中心裡,這個階層中的大多數(或至少是其中屬於某種職業形態的人)在政治上或許是偏左的,不過,可能也僅止於此了。在英國,閱讀《衛報》-《觀察家週報》的專業階級形態,在政治的分野上站在同一邊,而閱讀《每日電訊報》的中產階級形態,則屬於另一邊。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國,階級鬥爭的陣線,則穿越了中產階級的核心地帶。在總罷工裡,搞研究與發展型的、實驗室裡的,與設計部門和公共關係的,都傾向和勞動者一起走上街頭,而且常常是勇猛善戰的。然而企管人員、行政人員、銷售員等,卻仍都和管理階層站在一起。
曾經有人說,今天的知識分子,有部分是屬於一種「新興的」勞動階級,在某種意義下也稱得上是十九世紀在英國舉足輕重,屬於「智力工匠」中技術純熟、自信十足,並且在技術上屬於最獨立的勞工貴族之現代翻版。更有人認為,作為一批領薪水的專業人才,他們個人或整個階級的經濟財富,與私人企業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密切的關係,簡單來說,他們有能力判斷私人企業的缺陷所在。確實,有人認為他們與那些在商場上運疇帷幄的人至少一樣聰明,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至少讓他們對該企業的政策與經濟制度有個同樣宏觀的認識。他們並不喜歡把自己的活動囿限在薪資啦、工作環境啦,這些細微末節的瑣事,而比較樂意去檢視經營與政策上的改變。
這些論點主要是來自像阿蘭.圖賴訥、與索格.馬勒這類法國的社會學者,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他們的主張並沒有說新興的「勞工貴族」比老勞工貴族更像一股革命的力量。他們是說它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改良力量,只有當我們正視社會中有一種徐緩、和平,但根本的轉型,它才算得上具有革命精神的。不過,這樣的一種轉型是否可能,或即使可能,能否被視為一種革命,還是個棘手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新興勞動階級」的主張者認為,這在實際上只不過是新費邊主義者的答案,穿上了馬克思主義術語的外衣而已,它們是絕對不會被所有左派接受的。現在,最佳的手段,就是將他們視為與他們那些勞工貴族的老前輩相同的穩健改良主義者。他們在職業上的興趣,或許會使他們略微傾向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因為這種社會主義不致於威脅到他們頗為優越的地位;而且,他們對左派的志向,通常也可能比對自己的職業興趣更遠大,畢竟,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曾度過學生時代。但是他們對社會變遷的基本態度是,而且或許必然是:在既存的體制所能做的,要比做一個革命者所能做的多得多,這包括他們的孩子,以及他們的想像。就算對他們自己來說,這也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除了那些邊緣團體譬如等同於老式手搖紡織機織工之類的中產階層,其職業已經被技術的進步搞到無用武之地—像老式的藝術創作者,作家等等,知識分子中會對現狀表現出完全否定態度的,主要就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了。他們包含了那些被教育來從事智力工作的人,儘管我們總是搞不清楚他們的反叛性與教育體系之間到底有什麼關聯。
這些中產階層年輕成員的社會經驗相當有限,儘管或許在今天已經比他們父母那個時代豐富多了。這些經驗中有大部分是被來自家庭、學校或學院,具有類似背景的同儕團體經驗調合出來的,愈年輕的愈是如此。(一般所謂的「青年文化」是指跨越了社會差異,結合同一年齡青年的團體,這是膚淺或商業化的,甚至是既膚淺又商業化的概念。類似的服飾、髮型、娛樂的形態與社會習俗,並不代表會有相同的政治行為,這一點在學生群中的好戰分子企圖動員年輕工人時,就常常會發現到。一個不具混雜性的「青年文化」單獨型,究竟有幾分屬實,仍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它不單純是關於中產階級年輕人的評論所說的,一種舊的或新的「代溝」,一種對長輩的反叛,或不管有無理由,對教育制度的不滿。它可能會和過去常常發生的一樣,反映出一種對社會應加以重視之問題的懇切批評,不管它的形成是否欠缺統整性。
青年革命精神中最有用的組織化形式,就是學生組織。(有些國家還包括中等學校的學生。)因此,評估這種學生革命精神的性格與可能性,是相當重要的。當然,它的政治功能是雙重的。它既是一個為其本身權利的運動,也就是說,作為一種基於年齡或為教育制度拔擢進入的人群團體而存在,而且,也是成人政治世界活躍分子與領袖的後援基地。第一種功能在目前較為明顯,但第二種則在歷史上較引人側目。烏爾姆街高等師範學校在十九世紀末政治上的顯赫聲名,並不是由於該校當時對社會主義者的同情以及該校學生支持德雷福運動所致,而是這些學生中某些人在之後的職業所造成的,例如饒勒斯、萊昂.布魯姆與愛德華.赫里歐等人。
關於青年/學生運動,通常可以作出兩個普遍性的觀察。第一個相當濫調陳腔但卻十分明顯,就是這樣的運動本質上難以持久與延續。作為一個青年、或學生,不過是進入成年且自力更生階段的前奏曲;它本身並非一種職業。與獨身生活不同,它甚至不是一個藉由個人的力量就能實現的計畫。這段時間是能夠延長的,儘管當前流行一種說法,把每個度過最初二十年的人當作徘徊在中年邊緣,企圖縮短這段時間。不過,它遲早必須結束。是以,青年或學生的政治性運動,無法與那些成員能夠留在其中一輩子的運動相提並論,例如勞工運動(他們其中大部分都要一直幹到退休為止),或婦女運動、黑人運動;這些人從出生到死亡都隸屬於其各自的範疇。不過,永遠都會有青年、也永遠都會有學生,以他們為基礎的運動格局自然也就永遠存在。而且因為這二者今日在人口中占了相當高的比例,所以很容易就會變成至少是潛在性的群眾運動,但其成員每隔幾年便會來一次大換血,則是百分之百無可避免的了。另外,更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種運動愈是自限於難以持久的判準,也就是說,自限於衡量他們與成年人之間有多大的差距,也就愈難保持行動、組織,甚或計畫與意識形態的持續性,這與其氛圍的延續或是每個新世代都面對類似問題的事實,正好形成了對比。這在過去對革命青年來說不算什麼問題,主要是因為他們普遍將自己的運動視同成年人的運動,而且也通常義正辭嚴地拒絕被歸類為青年運動;他們的目光,也總是集中在成年人的地位。目前這種將「青年文化」劃分出來的流行趨勢,或許能讓這種運動潛在的數量更大,但也使得它更加起伏不定。
其次,在過去五十年可以看到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就是高等教育在所有國家可說是史無前例地擴張,同時帶來了三種影響:容納這些新生的教育設施由於對這種蜂擁狀況毫無準備,以致產生嚴重的疲態;在完全欠缺家庭知識與傳統的準備下就進入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的第一代學生,大量地出現;同時,就經濟方面來說,知識分子已經有一種潛在的生產過剩現象。基於種種原因,這個的確難以抑制的擴張,現在已經放緩了腳步,而高等教育的模式也或多或少基進地更張了其結構,不過可不能將其錯認為因應一九六○年代後期爆發的學生騷亂之結果。因為,它同時又製造了各式各樣的騷亂與緊張。
在這些處境之下,學生騷亂的存在實不足為奇,儘管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低度發展世界中重要的部門裡,它是以社會革命(典型地無政府化,或馬克思主義化)運動,而非基進右翼運動的形式存在。這和兩次大戰間,在歐洲大部分地區裡多數政治化學生的性格沒什麼兩樣。這是布爾喬亞社會,與對它的傳統式選擇二者的危機症候,它告訴那些不知所措的較低收入中產階級(許多新鮮人是來自其中,以及屬於這個階級),學生行動主義的典型方式,就是採取某種極端左傾的態度。
然而,這並不保證這樣的學生騷亂會維持一種嚴重而且繼續性的狀態,更不必期待它會成為一種有效的革命性政治力量。因為,如果這批新生中的大部分人,將來會被吸納進一個日趨擴張的經濟制度,與一個穩健的社會,那它可能就無法保證了。舉個極端的例子吧,有一批六萬人左右的秘魯大學生(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只有大約四千之數),是家庭中的第一代,他們通常屬於土著印第安人,或是西班牙與美洲混血的較低收入中產階級,或富農。他們典型的極端左傾態度就是:會對一個全新、茫然不知所措的生活方式有某種程度的接受。不過無論如何,因為他們其中有大部分仍然很容易就會被中產階級的職務所吸收,所以,這種態度很少會持續到畢業之後。因此一個流行的笑話就說,他們像是在服兵役似的「服他們義務的革命役」。要判斷他們是否會與一九二○年代那一小撮學生為美洲人民革命聯盟和共產黨所做的那樣,製造出一個大型的成人政治領袖集團,還嫌太早。不過,看來是沒什麼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