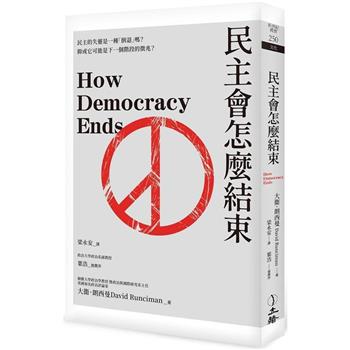想像那不可想像者
∕大衛.朗西曼
沒有什麼是地久天長。總有一天,民主制度會走入歷史。包括曾經在一九八九年宣布「歷史的終結」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內,沒有人相信民主制度的優點足以讓它永遠存在。直至最近期,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都認為民主的終結會是很久以後的事。他們並不預期這種事會在他們有生之年發生。極少有人想過,它也許會在他們眼前發生。
不過,在進入二十一世紀還不到二十年的今日,以下這個問題卻幾乎憑空而至:民主制度就是以這個樣子壽終正寢的嗎?
就像許多人一樣,我是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借哲學的術語來說,川普的當選看似是民主政治的歸謬法:任何能夠產生這麼荒謬結論的過程必然是哪裡出了差錯。如果川普就是答案,那我們就不再是在問正確的問題。事情還不只是出在川普本人。他的當選只是越來越不穩定、互不信任和互不寬容的過熱政治氣候的一種表徵。不只在美國,民主在很多國家都開始看起來像是精神錯亂。
應該開門見山的是,我並不相信川普入主白宮代表著民主的壽終正寢。美國的民主制度是設計來抵抗各種顛簸,而川普在競選期間的奇言怪行並未超出這些制度的容忍範圍。更有可能,他的政府是相對率由舊章而不是做些驚世駭俗的事。不過,川普入主白宮還是構成了一個直接的挑戰: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民主的失靈意味著什麼?在什麼情況下,行之已久的民主制度會活不下去?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些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但又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們的政治想像力被過時的民主失靈意象纏住。我們被困在了二十世紀。每次試圖想像民主瓦解的後果,我們就會乞靈於一九三○年代或一九七○年代的畫面:當時坦克會出現在街頭,獨裁者會口沫橫飛呼籲全國上下齊心,暴力和鎮壓會尾隨而至。川普的當選讓很多人拿他和過去的暴君相提並論。這些人警告我們,不要以為歷史不會重演。但另一種危險要怎麼辦?會不會,正當我們尋找民主失靈的熟悉訊號時,我們的民主正在以一些我們不熟悉方式出毛病?我驚覺這才是更大的威脅。我不認為我們有多大機會倒退回一九三○年代的情況。我們不是處於第二次法西斯主義、暴力和世界大戰的前夜。我們的社會和那個時候大相逕庭(富裕太多、年長太多和網絡化太多),而我們對那個時候出了什麼毛病的集體歷史知識也堅定不移。所以,當民主終結,它採取的形式有可能會讓我們大吃一驚。我們甚至可能會因為望錯地方,對它的發生不知不覺。
當代政治科學很少談論民主制度也許會以哪些新的方式失靈,因為它關注的是另一個不同的問題:民主制度一開始是怎樣站穩腳步?這種取向是可以瞭解的。在民主向全世界散播的過程中,它常常是進兩步、退一步。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也許實驗性地建立起民主制度,接著發生政變或軍事接管,然後又設法再來一遍。這樣的事從智利到南韓到肯亞都發生過。政治學的一個核心疑問是:到底是什麼導致民主固定下來。這根本上是一個信任的問題:那些在某次選舉結果中失去什麼的人必須相信忍耐到下一次選舉是值得的。富人必須相信窮人不會拿走他們的錢。士兵必須相信平民不會拿走他們的武器。但這種信賴常常會崩潰,這時民主就會垮台。
所以,政治科學家傾向於把民主的失靈視為一種「倒退」,是退回到能夠對民主制度建立長久信任之前的時期。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老是喜歡用從前民主失靈的事例來照明當前可能出了什麼差錯。我們假定民主的結束會把我們帶回起點。
我打算在本書提供一個不同的角度。在那些人們對民主的信賴已經難以動搖的社會,民主的失靈會是什麼樣子?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問題是,當我們對民主的制度安排已經變得非常信任,以致在它們失去作用卻察覺不到時,民主還能維持多久?我說的這些制度安排除了定期選舉(它仍然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還包括民主立法、獨立法庭和出版自由。這一切都可以繼續運作卻沒有做到它們應該做的事。民主空心化的危險在於它會讓我們有一種錯誤的安全感。我們也許會繼續信賴它,向它尋求拯救——哪怕我們又會對它的無力回應呼求感到滿心憤怒。民主制度可以在完好無缺的情況下失靈。
我的分析看起來會和常常被人談及的一點相左:西方社會對民主政治和政治家已經失去了信任。不錯,現在很多選民都不喜歡也不信任他們選出來的代表,而且程度是歷來之最。但失去信任感不會讓人揭竿起義反對民主,只會讓他們在絕望中認命。民主是可以在這種失望中存活很久的。這樣的民主會怎樣收場是一個問題,也是我嘗試回答的問題。但這種民主的下場不會是回到一九三○年代。
我們不應該採取布頓(Benjamin Button)的歷史觀,即不應該認為老舊的事物有可能再次年輕起來。歷史不會走回頭路。不錯,當代西方民主的行為看來呼應著我們歷史上一些最黑暗的時刻:任何人只要看見示威者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蒂鎮舉著納粹萬字旗示威,然後又聽到美國總統表示示威者和反示威者應該各打五十大板,都會原諒那些擔心歷史重演的人。不過,不管這一類事件有多麼猙獰,它們都不是回返一些我們認為早已留在了後頭的東西的先驅。我們確實已經把二十世紀留在了後頭。我們有需要另立一個參考架構。
所以,容我提供另一個類比。這個類比並不是沒有瑕疵,但我希望它可以幫助讀者對本書的論證有一個直觀性的掌握。西方的民主制度正經歷一場中年危機。我這樣說並不是低估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嚴重性,因為中年危機的後果一樣可以很嚴重,甚至會死人。西方民主的中年危機是一場全幅度的危機。中年危機的症狀包括表現出一個人更年輕時的行為。不過,如果假定研究年輕人的行為就可以理解中年危機,便是一個錯誤。
當一個可憐兮兮的中年男人出於衝動而買了一輛摩托車來騎,可以是很危險的。如果他真的不走運,摩托車最後有可能會化為一團火球。不過,這種危險和一個十七歲的毛頭小子買一輛摩托車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更有可能,它只是讓人尷尬:中年危機的摩托車被騎過幾次後便遭到冷落,閒置在街頭的停車格。它也有可能會被賣掉。危機將會需要以別的方法解決——假如它有可能解決的話。美國的民主正是處於可憐兮兮的中年階段,而川普是它的摩托車。它一樣有可能會化為一團火球。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危機會持續,需要以別的方法解決——假如它有可能解決的話。
我知道用這種方式來談論民主的危機也許帶有自我放縱味道,特別因為我是個好命的中年白種男人。以我的方式說話是世界上很多人負擔不起的奢侈。這些是第一世界的問題。民主的危機是真實的,但又有一點開玩笑的味道。這正是為什麼會那麼難以知道它也許會怎樣終結。
不是在人生的開始或結束階段,而是在中間階段經驗一場危機,意味著同時被向前拉和向後拉。把我們向前拉的是我們對更好情況的願望。把我們向後拉的是不願意放開一種和我們在一起已經很久的東西的心理。這種不情願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民主制度一直把我們伺候得很好。現代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在於它有能力帶給社會長期福祉,以及讓每個公民能夠表達心聲。很容易看出來為什麼我們不願意放棄它,至少目前還不願意。然後,選擇也許不單單是介乎於民主制度的整個套裝組合和某些反民主的替代方案的套裝組合之間。有可能是那些讓民主制度如此具吸引力的元素會繼續運作,但不再是一起運作。套裝組合開始瓦解。當一個人開始解體,我們有時會說他是散了開來。當今民主制度看來就是散了開來。但這並不表示它不可修復。目前還不至於。
然則,是哪些因素讓民主當前所面對的危機不同於它過去碰到的那些,不同於它在更年輕時碰到的那些?我相信有三個基本差異。首先,現在的政治暴力在規模上和性格上都不同於早前的世代。西方民主國家基本上都是一些太平社會,而這表示我們最強烈的破壞性衝動是表現在其他方面。政治暴力當然依舊存在,但是它潛行在我們政治的邊緣和我們想像力的幽深處,從不會走到舞台的中心。它是本故事中的幽靈。第二,大災難的威脅已經改變。災難的前景一度有一種刺激行動的效果,但現在卻傾向於窒息行動。我們在自身的恐懼面前僵住。第三是資訊科技的革命徹底改變了民主制度必須賴以運作的條件。我們變得依賴一些我們要不是控制不了就是並不完全理解的溝通形式和資訊分享形式。我們的民主制度的這些特徵,全都和它的年紀變得更長的事實相一致。
我用三大主題來組織本書: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我會從政變談起(它是民主失靈的標準指標),探問對民主的軍事接管在今日是不是還有實際可能性。如果這種可能性不存在,民主又是怎樣可能不必動用武力而被顛覆?我們有意識到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嗎?陰謀論的擴散是我們越來越不確定真正威脅何在的症狀。政變需要陰謀是因為它必須由一小群人祕密策劃,否則就無法實現。因為沒有了這些人,我們便只剩下陰謀論。
接著我會探討大災難的風險。當一切都分崩離析,民主制度當然一定會倒下。核子戰爭、災難性氣候變遷、恐怖主義的生化攻擊、殺人機器人的出現,這些全都可以讓民主政治完蛋,不過卻是我們最不用擔心的。因為如果真的發生了恐怖大災難,那麼存活下來的人將汲汲於求生,無暇改變。不過,在面對這些威脅時,我們發現自己被猶豫不決麻痺癱瘓的風險有多大?
再下來我會討論科技接管的可能性。智慧機器人還不會那麼快出現。但低層次的準智慧機器正漸漸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我們現在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擁有更大效率的科技,受到一些比現代政治史任何階段都更少責任感的大企業控制。我們會不會連再見都不說一聲,就把民主責任拱手讓給這些新力量?
最後,我會探討這個問題:用更好的制度取代民主制度這種說法通不通?中年危機可能確實是我們有需要做出改變的徵兆。既然我們陷在了車轍裡,為什麼不和讓我們如此悲慘的東西一刀兩斷?邱吉爾說過,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不計其他所有不斷被試驗過的政府形式的話。他這番話是在一九四七年說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之後,真的是沒有出現過更好的系統?我回顧了其中一些替代方案,包括二十一世紀的極權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的無政府主義。
在結論處,我考慮了民主的故事也許會怎樣結束。在我看來,它不會只有單一個終點。有鑑於它們有不同的預期壽命,世界不同國家的民主制度繼續會追隨不同的道路。美國民主挺得過川普不代表土耳其的民主挺得過艾爾多安(Erdogan)。即使民主在部分歐洲地區失靈,它未嘗不可能在非洲繁榮茁壯。發生在西方民主的事情不必然會決定其他地區民主的命運。但西方民主仍然是民主進步的旗艦級模型。它的失靈對於政治的未來有著巨大意涵。
除非世界末日先來到,否則不管發生什麼事,民主的死亡都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死亡。當代美國的民主經驗位於我要講述的民主故事的核心,但這個故事有必要放在其他時代和地點的民主經驗去理解。雖然我力主應該離開我們當前對一九三○年代的固著,但並不是暗示歷史不重要。正好相反:我們對於過去少數創傷時刻的執著,有可能會讓我們看不見可以從很多其他歷史時期得到的教訓。因為,我們從一八九○年代可以學到的並不少於從一九三○年代。但我會往回走得更遠:回到一六五○年代和古代世界的民主。我們需要以歷史來幫助我們擺脫對即時背景故事的不健康固著。那是對中年危機的一種療法。
未來將會不同於過去。過去比我們以為的要長。美國並不是全世界。不過,即時的美國過去卻是我的開始之處:我會從川普的總統就職典禮談起。那不是民主的終結,不過卻是開始思考民主終結也許意味著什麼的適當時刻。
(全文未完)
∕大衛.朗西曼
沒有什麼是地久天長。總有一天,民主制度會走入歷史。包括曾經在一九八九年宣布「歷史的終結」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內,沒有人相信民主制度的優點足以讓它永遠存在。直至最近期,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都認為民主的終結會是很久以後的事。他們並不預期這種事會在他們有生之年發生。極少有人想過,它也許會在他們眼前發生。
不過,在進入二十一世紀還不到二十年的今日,以下這個問題卻幾乎憑空而至:民主制度就是以這個樣子壽終正寢的嗎?
就像許多人一樣,我是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借哲學的術語來說,川普的當選看似是民主政治的歸謬法:任何能夠產生這麼荒謬結論的過程必然是哪裡出了差錯。如果川普就是答案,那我們就不再是在問正確的問題。事情還不只是出在川普本人。他的當選只是越來越不穩定、互不信任和互不寬容的過熱政治氣候的一種表徵。不只在美國,民主在很多國家都開始看起來像是精神錯亂。
應該開門見山的是,我並不相信川普入主白宮代表著民主的壽終正寢。美國的民主制度是設計來抵抗各種顛簸,而川普在競選期間的奇言怪行並未超出這些制度的容忍範圍。更有可能,他的政府是相對率由舊章而不是做些驚世駭俗的事。不過,川普入主白宮還是構成了一個直接的挑戰: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民主的失靈意味著什麼?在什麼情況下,行之已久的民主制度會活不下去?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些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但又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們的政治想像力被過時的民主失靈意象纏住。我們被困在了二十世紀。每次試圖想像民主瓦解的後果,我們就會乞靈於一九三○年代或一九七○年代的畫面:當時坦克會出現在街頭,獨裁者會口沫橫飛呼籲全國上下齊心,暴力和鎮壓會尾隨而至。川普的當選讓很多人拿他和過去的暴君相提並論。這些人警告我們,不要以為歷史不會重演。但另一種危險要怎麼辦?會不會,正當我們尋找民主失靈的熟悉訊號時,我們的民主正在以一些我們不熟悉方式出毛病?我驚覺這才是更大的威脅。我不認為我們有多大機會倒退回一九三○年代的情況。我們不是處於第二次法西斯主義、暴力和世界大戰的前夜。我們的社會和那個時候大相逕庭(富裕太多、年長太多和網絡化太多),而我們對那個時候出了什麼毛病的集體歷史知識也堅定不移。所以,當民主終結,它採取的形式有可能會讓我們大吃一驚。我們甚至可能會因為望錯地方,對它的發生不知不覺。
當代政治科學很少談論民主制度也許會以哪些新的方式失靈,因為它關注的是另一個不同的問題:民主制度一開始是怎樣站穩腳步?這種取向是可以瞭解的。在民主向全世界散播的過程中,它常常是進兩步、退一步。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也許實驗性地建立起民主制度,接著發生政變或軍事接管,然後又設法再來一遍。這樣的事從智利到南韓到肯亞都發生過。政治學的一個核心疑問是:到底是什麼導致民主固定下來。這根本上是一個信任的問題:那些在某次選舉結果中失去什麼的人必須相信忍耐到下一次選舉是值得的。富人必須相信窮人不會拿走他們的錢。士兵必須相信平民不會拿走他們的武器。但這種信賴常常會崩潰,這時民主就會垮台。
所以,政治科學家傾向於把民主的失靈視為一種「倒退」,是退回到能夠對民主制度建立長久信任之前的時期。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老是喜歡用從前民主失靈的事例來照明當前可能出了什麼差錯。我們假定民主的結束會把我們帶回起點。
我打算在本書提供一個不同的角度。在那些人們對民主的信賴已經難以動搖的社會,民主的失靈會是什麼樣子?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問題是,當我們對民主的制度安排已經變得非常信任,以致在它們失去作用卻察覺不到時,民主還能維持多久?我說的這些制度安排除了定期選舉(它仍然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還包括民主立法、獨立法庭和出版自由。這一切都可以繼續運作卻沒有做到它們應該做的事。民主空心化的危險在於它會讓我們有一種錯誤的安全感。我們也許會繼續信賴它,向它尋求拯救——哪怕我們又會對它的無力回應呼求感到滿心憤怒。民主制度可以在完好無缺的情況下失靈。
我的分析看起來會和常常被人談及的一點相左:西方社會對民主政治和政治家已經失去了信任。不錯,現在很多選民都不喜歡也不信任他們選出來的代表,而且程度是歷來之最。但失去信任感不會讓人揭竿起義反對民主,只會讓他們在絕望中認命。民主是可以在這種失望中存活很久的。這樣的民主會怎樣收場是一個問題,也是我嘗試回答的問題。但這種民主的下場不會是回到一九三○年代。
我們不應該採取布頓(Benjamin Button)的歷史觀,即不應該認為老舊的事物有可能再次年輕起來。歷史不會走回頭路。不錯,當代西方民主的行為看來呼應著我們歷史上一些最黑暗的時刻:任何人只要看見示威者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蒂鎮舉著納粹萬字旗示威,然後又聽到美國總統表示示威者和反示威者應該各打五十大板,都會原諒那些擔心歷史重演的人。不過,不管這一類事件有多麼猙獰,它們都不是回返一些我們認為早已留在了後頭的東西的先驅。我們確實已經把二十世紀留在了後頭。我們有需要另立一個參考架構。
所以,容我提供另一個類比。這個類比並不是沒有瑕疵,但我希望它可以幫助讀者對本書的論證有一個直觀性的掌握。西方的民主制度正經歷一場中年危機。我這樣說並不是低估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嚴重性,因為中年危機的後果一樣可以很嚴重,甚至會死人。西方民主的中年危機是一場全幅度的危機。中年危機的症狀包括表現出一個人更年輕時的行為。不過,如果假定研究年輕人的行為就可以理解中年危機,便是一個錯誤。
當一個可憐兮兮的中年男人出於衝動而買了一輛摩托車來騎,可以是很危險的。如果他真的不走運,摩托車最後有可能會化為一團火球。不過,這種危險和一個十七歲的毛頭小子買一輛摩托車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更有可能,它只是讓人尷尬:中年危機的摩托車被騎過幾次後便遭到冷落,閒置在街頭的停車格。它也有可能會被賣掉。危機將會需要以別的方法解決——假如它有可能解決的話。美國的民主正是處於可憐兮兮的中年階段,而川普是它的摩托車。它一樣有可能會化為一團火球。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危機會持續,需要以別的方法解決——假如它有可能解決的話。
我知道用這種方式來談論民主的危機也許帶有自我放縱味道,特別因為我是個好命的中年白種男人。以我的方式說話是世界上很多人負擔不起的奢侈。這些是第一世界的問題。民主的危機是真實的,但又有一點開玩笑的味道。這正是為什麼會那麼難以知道它也許會怎樣終結。
不是在人生的開始或結束階段,而是在中間階段經驗一場危機,意味著同時被向前拉和向後拉。把我們向前拉的是我們對更好情況的願望。把我們向後拉的是不願意放開一種和我們在一起已經很久的東西的心理。這種不情願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民主制度一直把我們伺候得很好。現代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在於它有能力帶給社會長期福祉,以及讓每個公民能夠表達心聲。很容易看出來為什麼我們不願意放棄它,至少目前還不願意。然後,選擇也許不單單是介乎於民主制度的整個套裝組合和某些反民主的替代方案的套裝組合之間。有可能是那些讓民主制度如此具吸引力的元素會繼續運作,但不再是一起運作。套裝組合開始瓦解。當一個人開始解體,我們有時會說他是散了開來。當今民主制度看來就是散了開來。但這並不表示它不可修復。目前還不至於。
然則,是哪些因素讓民主當前所面對的危機不同於它過去碰到的那些,不同於它在更年輕時碰到的那些?我相信有三個基本差異。首先,現在的政治暴力在規模上和性格上都不同於早前的世代。西方民主國家基本上都是一些太平社會,而這表示我們最強烈的破壞性衝動是表現在其他方面。政治暴力當然依舊存在,但是它潛行在我們政治的邊緣和我們想像力的幽深處,從不會走到舞台的中心。它是本故事中的幽靈。第二,大災難的威脅已經改變。災難的前景一度有一種刺激行動的效果,但現在卻傾向於窒息行動。我們在自身的恐懼面前僵住。第三是資訊科技的革命徹底改變了民主制度必須賴以運作的條件。我們變得依賴一些我們要不是控制不了就是並不完全理解的溝通形式和資訊分享形式。我們的民主制度的這些特徵,全都和它的年紀變得更長的事實相一致。
我用三大主題來組織本書: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我會從政變談起(它是民主失靈的標準指標),探問對民主的軍事接管在今日是不是還有實際可能性。如果這種可能性不存在,民主又是怎樣可能不必動用武力而被顛覆?我們有意識到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嗎?陰謀論的擴散是我們越來越不確定真正威脅何在的症狀。政變需要陰謀是因為它必須由一小群人祕密策劃,否則就無法實現。因為沒有了這些人,我們便只剩下陰謀論。
接著我會探討大災難的風險。當一切都分崩離析,民主制度當然一定會倒下。核子戰爭、災難性氣候變遷、恐怖主義的生化攻擊、殺人機器人的出現,這些全都可以讓民主政治完蛋,不過卻是我們最不用擔心的。因為如果真的發生了恐怖大災難,那麼存活下來的人將汲汲於求生,無暇改變。不過,在面對這些威脅時,我們發現自己被猶豫不決麻痺癱瘓的風險有多大?
再下來我會討論科技接管的可能性。智慧機器人還不會那麼快出現。但低層次的準智慧機器正漸漸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我們現在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擁有更大效率的科技,受到一些比現代政治史任何階段都更少責任感的大企業控制。我們會不會連再見都不說一聲,就把民主責任拱手讓給這些新力量?
最後,我會探討這個問題:用更好的制度取代民主制度這種說法通不通?中年危機可能確實是我們有需要做出改變的徵兆。既然我們陷在了車轍裡,為什麼不和讓我們如此悲慘的東西一刀兩斷?邱吉爾說過,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不計其他所有不斷被試驗過的政府形式的話。他這番話是在一九四七年說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之後,真的是沒有出現過更好的系統?我回顧了其中一些替代方案,包括二十一世紀的極權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的無政府主義。
在結論處,我考慮了民主的故事也許會怎樣結束。在我看來,它不會只有單一個終點。有鑑於它們有不同的預期壽命,世界不同國家的民主制度繼續會追隨不同的道路。美國民主挺得過川普不代表土耳其的民主挺得過艾爾多安(Erdogan)。即使民主在部分歐洲地區失靈,它未嘗不可能在非洲繁榮茁壯。發生在西方民主的事情不必然會決定其他地區民主的命運。但西方民主仍然是民主進步的旗艦級模型。它的失靈對於政治的未來有著巨大意涵。
除非世界末日先來到,否則不管發生什麼事,民主的死亡都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死亡。當代美國的民主經驗位於我要講述的民主故事的核心,但這個故事有必要放在其他時代和地點的民主經驗去理解。雖然我力主應該離開我們當前對一九三○年代的固著,但並不是暗示歷史不重要。正好相反:我們對於過去少數創傷時刻的執著,有可能會讓我們看不見可以從很多其他歷史時期得到的教訓。因為,我們從一八九○年代可以學到的並不少於從一九三○年代。但我會往回走得更遠:回到一六五○年代和古代世界的民主。我們需要以歷史來幫助我們擺脫對即時背景故事的不健康固著。那是對中年危機的一種療法。
未來將會不同於過去。過去比我們以為的要長。美國並不是全世界。不過,即時的美國過去卻是我的開始之處:我會從川普的總統就職典禮談起。那不是民主的終結,不過卻是開始思考民主終結也許意味著什麼的適當時刻。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