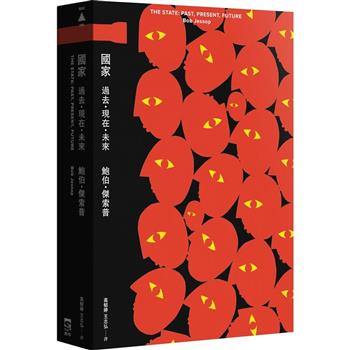第九章 自由主義民主、例外國家與新常態
脆弱國家、失敗國家與流氓國家
隨著能力配置、國家經理人投射權力至國家多重界線外的能力,以及盛行的挑戰,國家的力量會有大幅變化──實際上,在極端的案例裡,國家可能分崩離析,或展現其他經常被稱為「國家失敗」的徵兆。所有國家都會在某些方面失敗,常態政府則是從失敗中學習並適應失敗的重要機制。與此對比,「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面臨反覆出現的國家失敗時,缺乏重新發明或重新定位其活動以維持國內政策之「常態政治服務」的能力。「失敗國家」的論述經常是作為國家間際及國內政策的一環,藉此污名化某些體制。這種說法在掠奪式國家(predatory states)的例子裡可能有其合理依據,這些國家的官員仰賴特定階級,或一般人口的剩餘或其他資源「過活」,卻沒有確保擴大再生產的條件。這種現象的其他名稱有「竊盜統治」(kleptocracy)和「吸血鬼國家」(vampire state)。明智地混合善治(good governance)和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在這類狀況裡經常是推薦的做法,卻非普世皆然的萬靈丹。有外加壓力或外來干預的其他案例顯示,轉型的首要決定因素是內部國家能力和內部力量平衡(受到外來因素修正)。儘管「善治」政策有某些成就(如盧安達),但嚴重且持續失敗的例子也所在多有(如阿富汗、辛巴威、前比屬剛果)。
同樣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標籤可以用來誹謗某些國家,它們的行動在霸權或支配國家──特別是美國──看來,會威脅既有的國際秩序。美國國務院以四項標準辨識這類國家:(1)它們是威權體制;(2)它們支持恐怖主義;(3)它們企圖增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4)它們在本國犯下嚴重的侵犯人權罪刑。2000年時,國務院將官方論述裡的「流氓國家」替換成「受關切國家」(states of concern)。雖然有些「流氓國家」同時也是「失敗國家」,但其他則是強大又易脆的例外國家(例如北韓、緬甸)。流氓國家的標籤已經招致反霸權的批判回應,指出美國本身多年來就是最糟糕的流氓國家。這類指控與反控顯示,「失敗」和「流氓」國家這類詞彙具有高度爭議性──但這並不表示該宣稱的有效性無法經由特定標準來檢驗。還有個類似標籤是「賤民國家」(pariah state),這個詞適用於那些在本國侵犯人權,但未威脅世界和平的國家(如緬甸、辛巴威)。
威權國家主義
波拿巴主義和凱撒主義之類的概念,是十九世紀歐洲政治論述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們與民主體制一起,提供探索政治權威和民眾意志之間關係的焦點。這個主題持續至二十世紀,圍繞著獨裁和極權主義而展開,尤其在戰間期。威權主義統治命題的再次復甦,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尤其是在冷戰脈絡下,偕同國民安全國家的崛起──以及戰後大西洋福特主義模式成長危機之後,而大西洋福特主義乃結合了繁榮前景與對於普涵型政黨和擴張福利國家的強力支持。
有幾種重要說法都指出,「威權」統治形式是成熟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且不只出現於原始積累時期和晚期發展階段,或是依賴型與邊陲資本主義。此處的例子有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指出的強官僚國家趨勢──不論其形式是威權或極權──這是在經濟危機脈絡下,伴隨國家資本主義的萌生而發展。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這些理論家主張,這種國家形式與組織化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或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聯,其意識形態權力愈來愈仰賴大眾媒體,而且若非將勞工運動整合入政治支持,就是作為鞏固極權統治的手法而粉碎它。
在戰後理論家之間,人們或許會提起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晚期資本主義公共領域衰頹主張。其他例子還有赫希(Joachim Hirsch)指出的戰後福特主義脈絡下,安全國家(Sicherheitsstaat)(security state)的崛起;各種有關「強國家」(starker Staat)(strong state)、「軍武國家」(garrison state)、「友善法西斯主義」(friendly fascism)等傾向的主張。這類論證通常關切的是先進歐洲與北美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就目前國家主義與發展型國家同化的狀態而言,邊陲資本主義彰顯的國家主義議題甚至更為嚴峻(例如凱末爾的土耳其、李光耀的新加坡)。除了這些較「常態」的發展型國家主義形式,我們還發現例外的「發展型」國家(例如,南韓和臺灣發展型國家的早期階段,它們有獨裁體制主導的強大國家安全體制──在資本分支間的分歧與人民壓力升高導致的民主化發生之前)。
進入戰後時期不久,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即形容美國這個國家是由「常規國家階序」(regular state hierarchy)組成的拼裝體,它既依法治行動,也有監測並控管常規國家的更隱蔽「安全階序」(security hierarchy),限制著民主的影響力,並藉由培養對國內外敵人的懼怕而激發保護需求。更晚近,圖納德(Ola Tunander)發展並調整了蕭爾(Martin Shaw)的西方集團國家(western conglomerate state)概念,主張美國帝國(the US Reich)已然將西方國家(他也稱為西方勢力範圍〔western Großraum〕)一分為二:一系列在法治下運作的常規民主或公眾國民國家;以及,隱蔽的跨國安全國家,它可否決自身決策,並藉著將特定活動建構為國家或國際安全的根本威脅而「安全化」常規政治,在某些案例子中更訴諸恐怖主義來合理化軍事政變或政變企圖。
更晚近,安全階序或安全國家的想法,也反映在對「深層國家」(deep state)的更多關注。「深層國家」一詞是土耳其的發明(土耳其的對應字眼是derin devlet),指由情報服務、軍事、安全、司法和組織性犯罪內部的高層人士構成的系統。類似的網絡已經出現在埃及和烏克蘭、西班牙和哥倫比亞、義大利和以色列,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對於以這些角度撰寫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內幕爆料書的洛夫格倫(Mike Lofgren)而言,深層國家是個「政府元素與部分金融與產業高層結盟的混合體,無須參照被治理者經正式政治過程表達的同意,仍能有效治理美國」。
同樣道理,林西(Jason Lindsey)區分了淺層國家(shallow state)與暗黑國家(dark state)。淺層國家是國家的公眾面貌──它構成政治場景的前臺:演講、選舉、政黨政治及類似產物;相對的,深層國家愈來愈脫離了公眾的凝視(或謂「公然隱身」),其網絡包括了官員、私人公司、媒體管道、智庫、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以及其他關注資本需求而非日常生活需求的力量。事實上,它愈來愈隱身於新自由主義的庇護下,也通過新自由主義實踐來隱身: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主權消蝕的迷思──這遮掩了許多藉由公共-私人劃界而交扣資本和國家利益的方式。基進記者恩格哈特(Tom Engelhardt)稱其為美國政府除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門」;於他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更加不受箝制且無可課責,在祕密面紗背後運作的華盛頓中心。
普蘭札斯除了分析平行權力網絡和例外體制中作為硬核的「掩體」的角色,也主張此前曾是例外且暫時的政治秩序特徵,正愈來愈在他稱為威權國家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型態裡常態化。因為隨著世界市場更加整合,其矛盾也變得普遍化,而其危機傾向也益發明顯。這使得移置或延遲危機愈來愈困難,它們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恆常特徵。於是,隨著它們編納進入與官方國家系統平行運作的恆久結構裡,明顯的「例外」特徵便與資本主義型國家的「常態」特徵共存,並修正了後者。這個過程蘊含著常態與例外結構持續的共生和功能交錯,置於國家機器與主導政黨的制高點控制下。
於是,普蘭札斯主張,資本主義型國家如今「永久(permanent)且結構性的特徵,就是政治危機與國家危機之共通元素的獨特尖銳化(sharpening)」。這反映出1970年代已然顯現的,當代資本主義的長期結構性經濟危機,及這項危機如何凝縮於正在裂解干預型國家之社會基礎的各種政治與意識形態危機,譬如資產階級與新舊小資產階級的傳統聯盟的解組;工會和其他從屬群體的普通成員愈來愈好戰;伴隨著過往的「次要」戰線上的新社會運動成長而出現的意識形態危機;以及權力集團內部的矛盾,隨著國際化對各資本分支之間關係的衝擊而加劇(。這些徵候反映了大西洋福特主義危機,但類似徵候也可見於1990年代與本世紀頭二十年的出口導向知識經濟體,以及新自由主義金融主導經濟體。再者,由於當前的世界市場比1970年代中期整合程度更高,相較於普蘭札斯的預想,危機傾向已變得更具有多重形態、多重尺度,以及更多中心,而且由更多的分歧、物質與理念利益,以及認同所驅動。
雖然普蘭札斯分析中的細節反映的是他寫作當時的局勢,但他對新浮現的資本主義型國家之「常態」形式的描述,頗有先見之明。他將「威權國家主義」的基本發展傾向,形容為「對所有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加強國家控制,結合政治民主制度的劇烈衰退,以及對所謂『形式』自由施以嚴苛且形式多重的限制」。更具體地說,威權國家主義的元素,以及它們對代議制民主的意涵是:
•權力從立法移轉到行政與管理系統,而且實質權力集中於後者,從而封鎖來自被視為人民代表之政黨與議會的明確影響。實際上,政治愈來愈集中在總統或首相的職員辦公室。占據行政頂點的這個辦公室,儼然是純粹人格化的總統-首相系統。不存在將專制權力集中於他(或她)手上的真正波拿巴主義獨裁者;反之,此處尋求的是奇魅型的門面人物,他能對政治的複雜性提出有意義的策略方向──不論是面對支配階級,或是以更偏公民決定的風格,面對人民大眾。人格主義(personalism)實際上是許多矛盾壓力的濃縮,其致力於重新平衡仍以矛盾形式顯現於行政體系中的衝突力量與民眾利益。
•立法、行政與司法的加速融合,並伴隨法治的衰退。議會和政黨如今是權力極為有限的單純選舉「登記室」──其代理者很可能轉由競選資助者、遊說者,以及當代政治旋轉門中的潛在未來雇主「擁有」。因此,成為國家政策發展主要位址的,是由政治執行者引導的國家行政體系。這些變化使掌權的政黨(或是「政府的自然政黨」,對比於註定扮演永久反對角色的政黨)轉變成為單一(或雙頭壟斷〔duopolistic〕)型的威權大眾政黨(authoritarian mass party),比起直接闡述及代表人民的利益與對國家的要求,其任務更關乎以公民表決(plebiscitary)的方式去動員民眾支持國家政策。這使得行政大幅政治化,在官僚階序與統一的正式門面底下,冒著行政片斷化的風險。此一趨勢的存在得到卡茨與梅爾(Katz and Mair)的佐證,他們分析政黨菁英策略的轉換,以及政黨競爭的變化動態,如何導致「擔任公職政黨」的優勢,卻以草根成員和全國政黨執行委員為代價(也參見第三章)。
•作為與行政體系進行政治對話的優先管道,以及組織霸權的主要力量,政黨的這種功能衰退了。掌權的政黨也發生了改變,「它們嘗試參與,也確實參與了政府,遵照既有整體國家制度有機地固定且預期的常規輪替模式(而且不只是遵照憲政)」。壟斷資本發現愈來愈難透過議會政黨去組織自身的霸權,因而將遊說行動集中於行政,政黨與權力集團之間的代表性紐帶遂變得更為鬆散(。於是,政黨不再能完成它們在政策制定(環繞著共同政黨綱領而妥協和結盟)或政治正當化(通過選舉競爭來贏取國民-人民的授權)上的傳統功能。如今,它們只不過是官方決策的輸送帶,也僅在它們選擇宣揚的官方政策面向上有些差別。政治正當化也在行政單位的主導下,經由基於公投和操縱性技巧的管道來調整方向,並透過大眾媒體擴大宣揚。
•平行的權力網絡成長,它們與正式國家組織交錯,並且在其各種活動裡占有決策分量。更精確地說,威權國家主義意味著行政部門、占支配地位的「國家政黨」(擔任從國家到人民,而非人民到國家的輸送帶),以及一種新的反民主意識形態的角色提升。這進一步侵蝕了大眾在政治決策裡已然受限的參與,嚴重弱化了政黨系統的有機運作(即使仍有許多政黨完好無缺地繼續存在),也消磨了民主政治論述的活力。於是,威權-國家主義形式持續穿透所有社會生活領域時,遇到的阻礙漸少──我們或可補充,當這種穿透是以(國家)安全和反恐戰爭之名來合理化時,尤為顯著。甚且,普蘭札斯實際上就宣稱,若說得誇張一些,那麼,「所有的當代權力都為威權國家主義所用」。
事實上,普蘭札斯指出國家行政活動會持續遭逢自身政治結構與運作的內在限制時,有稍微撤回這項主張。行政體系的小團體、派別和派系的內部分歧,以及階級衝突和矛盾在國家系統內的再生產,是這些限制尤為鮮明之處。於是,我們必須探問,行政體系如何克服這些張力,方能有效為了壟斷資本的利益而行動。例外國家透過與行政體系明顯有別的政治機器(例如法西斯政黨、軍隊或政治警察)而達致此一目的。在代議制民主的常態形式裡,同樣目的則是透過位居中央行政機器之外,多元政黨系統的有機運作而達成。
隨之浮現的問題是,這種有機運作如何可能在威權國家主義底下實現。普蘭札斯指出,這是藉由將占支配地位的大眾政黨轉型成為支配性國家政黨。如今,這個政黨的功能是以行政核心之政治委員身分而行動的平行網絡,它與位居要津的公務員一同發展出物質與意識形態的利益共同體,將國家呈現給大眾,而非反過來。它也將國家意識形態傳遞給人民群眾,並強化威權國家主義的公民決議正當性(plebiscitary legitimation)。如此高度統一且結構化的大眾政黨,最有可能長期發展而期間沒有執政輪替發生。同樣的功能也可能由單一的跨黨「中心」實行,而這個中心主導了執政黨的輪替。
「國家行政以勢不可擋之姿崛起」之現象,被普蘭札斯關聯至國家日益上升的經濟角色,但他的論點必須受到政治情境的修正。原因是,他的說法仍然是以1970年代的局勢為特色,只是,我們可以重塑他的理論,以吻合當前的新自由主義體制轉變、務實(pragmatic)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調整,以及外部強加的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政策。
脆弱國家、失敗國家與流氓國家
隨著能力配置、國家經理人投射權力至國家多重界線外的能力,以及盛行的挑戰,國家的力量會有大幅變化──實際上,在極端的案例裡,國家可能分崩離析,或展現其他經常被稱為「國家失敗」的徵兆。所有國家都會在某些方面失敗,常態政府則是從失敗中學習並適應失敗的重要機制。與此對比,「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面臨反覆出現的國家失敗時,缺乏重新發明或重新定位其活動以維持國內政策之「常態政治服務」的能力。「失敗國家」的論述經常是作為國家間際及國內政策的一環,藉此污名化某些體制。這種說法在掠奪式國家(predatory states)的例子裡可能有其合理依據,這些國家的官員仰賴特定階級,或一般人口的剩餘或其他資源「過活」,卻沒有確保擴大再生產的條件。這種現象的其他名稱有「竊盜統治」(kleptocracy)和「吸血鬼國家」(vampire state)。明智地混合善治(good governance)和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在這類狀況裡經常是推薦的做法,卻非普世皆然的萬靈丹。有外加壓力或外來干預的其他案例顯示,轉型的首要決定因素是內部國家能力和內部力量平衡(受到外來因素修正)。儘管「善治」政策有某些成就(如盧安達),但嚴重且持續失敗的例子也所在多有(如阿富汗、辛巴威、前比屬剛果)。
同樣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標籤可以用來誹謗某些國家,它們的行動在霸權或支配國家──特別是美國──看來,會威脅既有的國際秩序。美國國務院以四項標準辨識這類國家:(1)它們是威權體制;(2)它們支持恐怖主義;(3)它們企圖增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4)它們在本國犯下嚴重的侵犯人權罪刑。2000年時,國務院將官方論述裡的「流氓國家」替換成「受關切國家」(states of concern)。雖然有些「流氓國家」同時也是「失敗國家」,但其他則是強大又易脆的例外國家(例如北韓、緬甸)。流氓國家的標籤已經招致反霸權的批判回應,指出美國本身多年來就是最糟糕的流氓國家。這類指控與反控顯示,「失敗」和「流氓」國家這類詞彙具有高度爭議性──但這並不表示該宣稱的有效性無法經由特定標準來檢驗。還有個類似標籤是「賤民國家」(pariah state),這個詞適用於那些在本國侵犯人權,但未威脅世界和平的國家(如緬甸、辛巴威)。
威權國家主義
波拿巴主義和凱撒主義之類的概念,是十九世紀歐洲政治論述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們與民主體制一起,提供探索政治權威和民眾意志之間關係的焦點。這個主題持續至二十世紀,圍繞著獨裁和極權主義而展開,尤其在戰間期。威權主義統治命題的再次復甦,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尤其是在冷戰脈絡下,偕同國民安全國家的崛起──以及戰後大西洋福特主義模式成長危機之後,而大西洋福特主義乃結合了繁榮前景與對於普涵型政黨和擴張福利國家的強力支持。
有幾種重要說法都指出,「威權」統治形式是成熟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且不只出現於原始積累時期和晚期發展階段,或是依賴型與邊陲資本主義。此處的例子有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指出的強官僚國家趨勢──不論其形式是威權或極權──這是在經濟危機脈絡下,伴隨國家資本主義的萌生而發展。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這些理論家主張,這種國家形式與組織化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或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聯,其意識形態權力愈來愈仰賴大眾媒體,而且若非將勞工運動整合入政治支持,就是作為鞏固極權統治的手法而粉碎它。
在戰後理論家之間,人們或許會提起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晚期資本主義公共領域衰頹主張。其他例子還有赫希(Joachim Hirsch)指出的戰後福特主義脈絡下,安全國家(Sicherheitsstaat)(security state)的崛起;各種有關「強國家」(starker Staat)(strong state)、「軍武國家」(garrison state)、「友善法西斯主義」(friendly fascism)等傾向的主張。這類論證通常關切的是先進歐洲與北美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就目前國家主義與發展型國家同化的狀態而言,邊陲資本主義彰顯的國家主義議題甚至更為嚴峻(例如凱末爾的土耳其、李光耀的新加坡)。除了這些較「常態」的發展型國家主義形式,我們還發現例外的「發展型」國家(例如,南韓和臺灣發展型國家的早期階段,它們有獨裁體制主導的強大國家安全體制──在資本分支間的分歧與人民壓力升高導致的民主化發生之前)。
進入戰後時期不久,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即形容美國這個國家是由「常規國家階序」(regular state hierarchy)組成的拼裝體,它既依法治行動,也有監測並控管常規國家的更隱蔽「安全階序」(security hierarchy),限制著民主的影響力,並藉由培養對國內外敵人的懼怕而激發保護需求。更晚近,圖納德(Ola Tunander)發展並調整了蕭爾(Martin Shaw)的西方集團國家(western conglomerate state)概念,主張美國帝國(the US Reich)已然將西方國家(他也稱為西方勢力範圍〔western Großraum〕)一分為二:一系列在法治下運作的常規民主或公眾國民國家;以及,隱蔽的跨國安全國家,它可否決自身決策,並藉著將特定活動建構為國家或國際安全的根本威脅而「安全化」常規政治,在某些案例子中更訴諸恐怖主義來合理化軍事政變或政變企圖。
更晚近,安全階序或安全國家的想法,也反映在對「深層國家」(deep state)的更多關注。「深層國家」一詞是土耳其的發明(土耳其的對應字眼是derin devlet),指由情報服務、軍事、安全、司法和組織性犯罪內部的高層人士構成的系統。類似的網絡已經出現在埃及和烏克蘭、西班牙和哥倫比亞、義大利和以色列,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對於以這些角度撰寫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內幕爆料書的洛夫格倫(Mike Lofgren)而言,深層國家是個「政府元素與部分金融與產業高層結盟的混合體,無須參照被治理者經正式政治過程表達的同意,仍能有效治理美國」。
同樣道理,林西(Jason Lindsey)區分了淺層國家(shallow state)與暗黑國家(dark state)。淺層國家是國家的公眾面貌──它構成政治場景的前臺:演講、選舉、政黨政治及類似產物;相對的,深層國家愈來愈脫離了公眾的凝視(或謂「公然隱身」),其網絡包括了官員、私人公司、媒體管道、智庫、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以及其他關注資本需求而非日常生活需求的力量。事實上,它愈來愈隱身於新自由主義的庇護下,也通過新自由主義實踐來隱身: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主權消蝕的迷思──這遮掩了許多藉由公共-私人劃界而交扣資本和國家利益的方式。基進記者恩格哈特(Tom Engelhardt)稱其為美國政府除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門」;於他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更加不受箝制且無可課責,在祕密面紗背後運作的華盛頓中心。
普蘭札斯除了分析平行權力網絡和例外體制中作為硬核的「掩體」的角色,也主張此前曾是例外且暫時的政治秩序特徵,正愈來愈在他稱為威權國家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型態裡常態化。因為隨著世界市場更加整合,其矛盾也變得普遍化,而其危機傾向也益發明顯。這使得移置或延遲危機愈來愈困難,它們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恆常特徵。於是,隨著它們編納進入與官方國家系統平行運作的恆久結構裡,明顯的「例外」特徵便與資本主義型國家的「常態」特徵共存,並修正了後者。這個過程蘊含著常態與例外結構持續的共生和功能交錯,置於國家機器與主導政黨的制高點控制下。
於是,普蘭札斯主張,資本主義型國家如今「永久(permanent)且結構性的特徵,就是政治危機與國家危機之共通元素的獨特尖銳化(sharpening)」。這反映出1970年代已然顯現的,當代資本主義的長期結構性經濟危機,及這項危機如何凝縮於正在裂解干預型國家之社會基礎的各種政治與意識形態危機,譬如資產階級與新舊小資產階級的傳統聯盟的解組;工會和其他從屬群體的普通成員愈來愈好戰;伴隨著過往的「次要」戰線上的新社會運動成長而出現的意識形態危機;以及權力集團內部的矛盾,隨著國際化對各資本分支之間關係的衝擊而加劇(。這些徵候反映了大西洋福特主義危機,但類似徵候也可見於1990年代與本世紀頭二十年的出口導向知識經濟體,以及新自由主義金融主導經濟體。再者,由於當前的世界市場比1970年代中期整合程度更高,相較於普蘭札斯的預想,危機傾向已變得更具有多重形態、多重尺度,以及更多中心,而且由更多的分歧、物質與理念利益,以及認同所驅動。
雖然普蘭札斯分析中的細節反映的是他寫作當時的局勢,但他對新浮現的資本主義型國家之「常態」形式的描述,頗有先見之明。他將「威權國家主義」的基本發展傾向,形容為「對所有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加強國家控制,結合政治民主制度的劇烈衰退,以及對所謂『形式』自由施以嚴苛且形式多重的限制」。更具體地說,威權國家主義的元素,以及它們對代議制民主的意涵是:
•權力從立法移轉到行政與管理系統,而且實質權力集中於後者,從而封鎖來自被視為人民代表之政黨與議會的明確影響。實際上,政治愈來愈集中在總統或首相的職員辦公室。占據行政頂點的這個辦公室,儼然是純粹人格化的總統-首相系統。不存在將專制權力集中於他(或她)手上的真正波拿巴主義獨裁者;反之,此處尋求的是奇魅型的門面人物,他能對政治的複雜性提出有意義的策略方向──不論是面對支配階級,或是以更偏公民決定的風格,面對人民大眾。人格主義(personalism)實際上是許多矛盾壓力的濃縮,其致力於重新平衡仍以矛盾形式顯現於行政體系中的衝突力量與民眾利益。
•立法、行政與司法的加速融合,並伴隨法治的衰退。議會和政黨如今是權力極為有限的單純選舉「登記室」──其代理者很可能轉由競選資助者、遊說者,以及當代政治旋轉門中的潛在未來雇主「擁有」。因此,成為國家政策發展主要位址的,是由政治執行者引導的國家行政體系。這些變化使掌權的政黨(或是「政府的自然政黨」,對比於註定扮演永久反對角色的政黨)轉變成為單一(或雙頭壟斷〔duopolistic〕)型的威權大眾政黨(authoritarian mass party),比起直接闡述及代表人民的利益與對國家的要求,其任務更關乎以公民表決(plebiscitary)的方式去動員民眾支持國家政策。這使得行政大幅政治化,在官僚階序與統一的正式門面底下,冒著行政片斷化的風險。此一趨勢的存在得到卡茨與梅爾(Katz and Mair)的佐證,他們分析政黨菁英策略的轉換,以及政黨競爭的變化動態,如何導致「擔任公職政黨」的優勢,卻以草根成員和全國政黨執行委員為代價(也參見第三章)。
•作為與行政體系進行政治對話的優先管道,以及組織霸權的主要力量,政黨的這種功能衰退了。掌權的政黨也發生了改變,「它們嘗試參與,也確實參與了政府,遵照既有整體國家制度有機地固定且預期的常規輪替模式(而且不只是遵照憲政)」。壟斷資本發現愈來愈難透過議會政黨去組織自身的霸權,因而將遊說行動集中於行政,政黨與權力集團之間的代表性紐帶遂變得更為鬆散(。於是,政黨不再能完成它們在政策制定(環繞著共同政黨綱領而妥協和結盟)或政治正當化(通過選舉競爭來贏取國民-人民的授權)上的傳統功能。如今,它們只不過是官方決策的輸送帶,也僅在它們選擇宣揚的官方政策面向上有些差別。政治正當化也在行政單位的主導下,經由基於公投和操縱性技巧的管道來調整方向,並透過大眾媒體擴大宣揚。
•平行的權力網絡成長,它們與正式國家組織交錯,並且在其各種活動裡占有決策分量。更精確地說,威權國家主義意味著行政部門、占支配地位的「國家政黨」(擔任從國家到人民,而非人民到國家的輸送帶),以及一種新的反民主意識形態的角色提升。這進一步侵蝕了大眾在政治決策裡已然受限的參與,嚴重弱化了政黨系統的有機運作(即使仍有許多政黨完好無缺地繼續存在),也消磨了民主政治論述的活力。於是,威權-國家主義形式持續穿透所有社會生活領域時,遇到的阻礙漸少──我們或可補充,當這種穿透是以(國家)安全和反恐戰爭之名來合理化時,尤為顯著。甚且,普蘭札斯實際上就宣稱,若說得誇張一些,那麼,「所有的當代權力都為威權國家主義所用」。
事實上,普蘭札斯指出國家行政活動會持續遭逢自身政治結構與運作的內在限制時,有稍微撤回這項主張。行政體系的小團體、派別和派系的內部分歧,以及階級衝突和矛盾在國家系統內的再生產,是這些限制尤為鮮明之處。於是,我們必須探問,行政體系如何克服這些張力,方能有效為了壟斷資本的利益而行動。例外國家透過與行政體系明顯有別的政治機器(例如法西斯政黨、軍隊或政治警察)而達致此一目的。在代議制民主的常態形式裡,同樣目的則是透過位居中央行政機器之外,多元政黨系統的有機運作而達成。
隨之浮現的問題是,這種有機運作如何可能在威權國家主義底下實現。普蘭札斯指出,這是藉由將占支配地位的大眾政黨轉型成為支配性國家政黨。如今,這個政黨的功能是以行政核心之政治委員身分而行動的平行網絡,它與位居要津的公務員一同發展出物質與意識形態的利益共同體,將國家呈現給大眾,而非反過來。它也將國家意識形態傳遞給人民群眾,並強化威權國家主義的公民決議正當性(plebiscitary legitimation)。如此高度統一且結構化的大眾政黨,最有可能長期發展而期間沒有執政輪替發生。同樣的功能也可能由單一的跨黨「中心」實行,而這個中心主導了執政黨的輪替。
「國家行政以勢不可擋之姿崛起」之現象,被普蘭札斯關聯至國家日益上升的經濟角色,但他的論點必須受到政治情境的修正。原因是,他的說法仍然是以1970年代的局勢為特色,只是,我們可以重塑他的理論,以吻合當前的新自由主義體制轉變、務實(pragmatic)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調整,以及外部強加的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