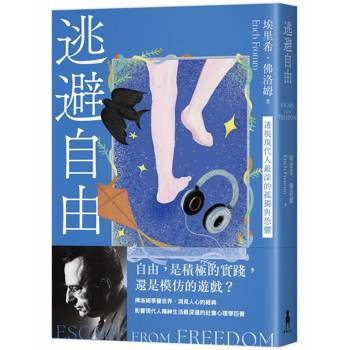第一章
自由是心理學的問題?
當代歐美史的重點圍繞在人們努力爭取政治、經濟與心靈自由,並試圖擺脫往昔加諸於身的束
縛。備受壓抑的人們掀起一場場爭奪自由之戰,渴望從原本的特權階級手中得到全新的自由。當這群人試圖擺脫宰制並爭取自由的當下,他們相信自己是為爭取人類的自由而戰,因此有資格訴諸一份理想、訴諸一份根植於所有受壓迫者對於自由的渴望。然而長久以來,在漫長且持續的自由戰役中,奮力對抗壓抑和宰制的那群人,往往在某階段便轉為投入捍衛自由的敵對陣營,也就是說,一旦原本的抗爭獲得勝利,就會出現新的特權階級來維護自身的權力。
即便史上存在不少開倒車的情況,但是最終自由仍贏得許多勝利。許多人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犧
牲生命,他們堅信為反抗壓迫而死去,遠勝於在無自由的狀態中活著,這類例子可視為人類展現個體性的極致表現。歷史似乎證實了人的確有可能管理自己、替自己做決定,以及以自認適當的方式思考與感覺。充分發揮人的潛能似乎就是社會發展正快速接近的目標。經濟自由、政治民主、宗教自主,以及個人主義式的個體生活,在在傳達出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人類似乎越來越能真正地實踐自由。各種外在束縛逐一被斬斷,人類戰勝了大自然,甚至成為自然界的主宰,同時推翻了天主教會與專制政體加諸於個人身上的限制。要實現珍貴的個人自由,「廢除外在的主宰」不僅是必要條件,也是充分條件。
許多人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最終戰鬥,其最終結果就是自由的絕對
勝利。戰後,既存的民主政體益發強大,舊的君主政體也被新的民主政權取代。但僅僅數年間,新的社會體系便否定了人類自以為歷經數世紀奮鬥才得到的成果。這些新的社會體系有效掌控了所有人的社會與生活,更使得絕大多數的人屈服於他們所無法掌控的權威之下。
起初,許多人在這樣的想法中找到安慰:威權體制的勝利只是因為少數幾個人的瘋狂,而他們的
瘋狂終將使他們自行走向毀滅。有些人則不無得意地相信,義大利人與德國人長期缺乏民主訓練,所以我們可以泰然地等待他們終將達到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成熟度。另一種常見的誤解,或許也是最危險的一種,那就是認定像希特勒這樣的人之所以能獲得掌控整個國家的巨大權力,完全只憑藉著他的狡黠與欺騙手段,他的組織是以武力獲取統治權,而所有受統治的人,只能視為遭受背叛與恐怖酷行的無意志個體。數年後,這些論點的謬誤已變得十分明朗。
我們不得不承認,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迫不及待地想交出自由,簡直就像他們祖先當年爭取自由時那樣的熱切;也就是說,這些人不想要自由,反而想辦法逃避自由。另外更有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對此問題漠不關心,他們不認為自由是值得努力奮鬥、甚至付出生命來捍衛的東西。我們也認識到這類民主危機,不僅是德國人與義大利人才會面對的問題,而是所有現代國家都會遭遇到的困境。人類自由的敵對陣營究竟打著什麼旗幟其實並不重要:反法西斯主義對自由所造成的危害,並不亞於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約翰.杜威曾大力陳述這項事實:「對我們的民主政體造成最嚴重威脅的,並非其他極權國家的存在,而是存於我們自身的態度,內建於我們的組織和制度,使外在權威、紀律、規範和對外國領袖的依賴占了上風。真正的戰場其實就在我們身上,內在於我們內心與我們的體系之中。」
###
當我們探討自由的人性面、對順從的渴望及權力欲時,會明顯產生下列問題:人類體驗到的自由
究竟是什麼?對自由的渴望是否內建於人性中?是無論什麼文化的人都具備相同的自由渴望,還是會因不同社會中自由主義的發展程度而有所差異?所謂自由只是沒有外在壓力嗎?或者還需其他要素來支持?如果有,那會是什麼?在一個社會裡,什麼樣的經濟或社會問題會導致人們想要爭取自由?自由會不會成為某種沉重到令人難以承受的負擔,甚至讓人想要逃避?為什麼自由對某些人來說是珍貴的願望,對某些人而言卻是一項威脅?
除了對自由擁有天生的渴望,人們是否也在本能上產生對「順從」的欲求?否則我們如何解釋當
今竟有這麼多人自願服從領導者?再者,人們服從的對象是否總是具體化為外在的當權者,還是包括某種已經內化的權威,如義務或良心、內在驅力,甚至如公眾意見等無名的權威?對於這些服從,人們是否從中得到某種隱微的滿足感?那麼,服從的本質究竟為何?
是什麼因素使人們對權力懷抱著永不饜足的貪欲?這是否正是人類得以生機盎然的原因,或這是當人自發性地熱愛生命時所必然產生的脆弱與無能?哪些心理因素會使人產生動機去爭奪權力,而又
是哪些社會條件造就了這些心理因素?
藉由分析自由與權威主義的人性面,使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普遍性問題,也就是心理因素在社會
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這個提問最終指向探討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心理、經濟,與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果我們試圖理解法西斯主義如何能吸引眾多力量強大的國家,那麼便必須先理解心理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這種政治體制在本質上並不訴諸追求個人利益的理性力量,卻是在驅動並動員人心中那股我們以為不存在,或至少在許久前已消失殆盡的邪惡力量。近幾個世紀以來,我們所熟悉的「人類」形象是一種理性生物,其行為取決於自我利益及追求利益的能力。即便像霍布斯(Hobbes)這類學者認為:「對權力的渴求與對他人的敵意,乃人類行為最基本的驅動力」,但他同時也指出,這些力量實際上仍來自個人的自我利益,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追求幸福,當社會不存在足夠的財富讓每個人都得到滿足時,人便開始爭權奪利,以確保擁有權的永續長存。然而,霍布斯對人的理解已然過時。中產階級越成功地打破舊時代政治或宗教統治者的權威,人類就越能掌控大自然,也更具備經濟獨立的能力。綜上所述,人開始相信一個「理性的世界」,認定自己是「理性的生物」。人們逐漸將人性中的黑暗力量歸屬於僅存於中世紀或更早期的歷史產物,並認定這些力量來自缺乏知識,或肇始於偽善的王權或教宗所領導的狡黠體制。
我們檢視這些過往的時期,就好像觀察一座長久以來已不再構成威脅的火山一樣。人們自信地認
為當代民主的成就已經徹底掃除了所有的邪惡勢力,這個世界既光明又安全,如同現代城市中寬敞明亮的街道。戰爭被視為舊時代的遺物,我們只需要最後一場戰爭就能終止所有的征戰;經濟危機被視為偶發事件,即使類似的意外持續在發生。
###
為了完整理解即將進行的討論,我們應先釐清「適應」(adaptation)這個概念,這同時也能闡釋
我們所指稱的心理機制與法則。
我們應區分「靜態適應」與「動態適應」這兩個概念。我所謂「靜態適應」,是個人在整體性格
結構未變動的情況下去適應某些模式,也就是採用某種新習慣。例如,從中式飲食習慣轉變為使用刀叉的西式飲食習慣。一個中國人在美國生活,會適應這個新模式,但這種適應對本身人格並無影響,不會在他心裡引發新的驅力,或形成新的性格特質。
而我所謂的動態適應,舉例來說,當一個小男孩屈從於父親嚴厲威嚇的命令時,因為太過害怕而
不敢忤逆,遂成為一個「乖兒子」。當這個男孩順應環境需要的同時,內心也發生了某種轉變。他可能對父親產生強烈的敵意,但他卻將這份敵意壓抑下來,因為意識到這份敵意,或將之表現出來,將對自身造成危險。然而,這份被壓抑的敵意雖然不明顯,卻成為他性格結構中的一項動態因素。他可能產生新的焦慮,導致更加服從,也可能形成一種模糊的違抗意識——不見得特別針對誰,而是針對整個生命歷程。如同第一種情況,個人順從了某些外在環境,但這樣的適應行為卻在他身上創造出新的東西,引發新的驅力和新的焦慮。每一則神經官能症的案例都可視為這類動態適應的例證,它必然是為了適應某種不合理的外在情境(尤其是幼年時期的遭遇),而且普遍來說,這些情境都會對幼童成長與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同樣地,這些類似神經官能現象的社會心理現象(我在後文會解釋為什麼不將這些現象直接稱為神經官能現象),諸如存在於社群裡的毀滅性或施虐衝動,正是動態適應非理性且有害人類在社會上發展的例子。
除了探討個人心理的適應機制,我們也應檢視:什麼力量會驅使人調整自身來適應幾乎任何一種
可以想像的生命處境?而人類的適應能力,又有什麼極限?
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我們必須討論的現象是:人類天性中有某些部分比較富有彈性、適應力強,有些部分則不然。最具有彈性與可塑性的部分,是人與人之間不同的欲望與性格特質,如愛、毀
滅性、施虐、服從傾向、權力欲、疏離、自我擴張的渴望、節儉癖、感官享受,以及對縱欲的恐懼
等。上述或其他關於人的欲求與恐懼,都是為了回應特定生命情境而發展出來的特質,它們並非特別有彈性,因為它們一旦變成某人個性的一環,就不容易消失或轉變為其他驅力。然而,它們在某種情況下很有彈性,由於個人(特別在幼童時期)是根據生活方式而發展出各種需求,因此這些需求並非固定和僵化到有如與生俱來的人性本質那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非得到滿足不可。
另外有些需求與上述相反,而成為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迫切需要得到滿足,那就是根
植於個人生理結構中的需求,如飢餓、口渴、睡眠等。這類需求都具備特定的基本值,每個人都無法承受滿足的程度低於這個門檻,而當超過該基本值時,滿足欲求的意向就帶有威力極強的欲求特質。
所有的生理需求都可被化約為自我保護的概念,這種自保的需求便是在所有情況下都必須獲得滿足的人類本性,也形成了個人行為的首要動機。
簡單來說,我們必須吃喝、睡覺、保護自身以免受到敵人侵害等,為了達成這些目的,而必須工
作與生產。此處所謂的「工作」並非一種籠統或抽象的指稱,而是指具體的工作——在經濟體系中可從事的具體工作。一個人在封建體系中可能擔任奴隸工作,在印第安族的村莊中可能是個農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可能是個獨立的商人,在現代百貨公司中可能是個銷售員,也可能是某企業生產帶上的一個小工人。不同的工作需要相異的人格特質,也使個人與他人產生不同的關係。一個人出生後,他的生命舞臺就已經展現在面前——他必須為了生存而工作。這代表他必須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以他所處的社會為他所決定的方式工作。個人的生存需求及其身處的社會體系,這兩個要素原則上都是個體本身無法改變的,因此也成為發展其他較具可塑性的特質發展的因素。
由此可見,個人的生活方式已經被特定的經濟體系所決定了,也變成決定整個性格結構的基本因
素,因為自保的重要需求迫使他接受自己所處的生活條件。這並不代表個人不能結合他人的力量,試圖創造某種經濟與政治的變革,但基本上,他的人格特質主要還是受到特定生活方式的形塑,因為當他還年幼時,就已透過家庭的媒介接觸到這些生活方式,家庭環境幾乎能重現特定社會或階級所獨具的各項特質。
伴隨生理機能而產生的各種需求,並非人類性格中唯一絕對必須被滿足的部分。人性中還存在著
另一種同樣具有強制力的需求,這並非根植於身體演進的機能,而奠基於人類生活方式與生命實踐的特有本質:與外界建立連結的需求,亦即「避免孤獨」的需求。感覺完全的孤立與孤單會使人精神崩潰,就如同身體飢餓會導致死亡。這種與他人的關係並不等同肉體接觸,個人在身體上也許能獨處許多年,但仍然可與許多理念、價值觀或至少是社會模式產生連結,使得他感受到一種交流與歸屬的感覺。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身處眾人之間,卻依然被徹底的孤獨感襲擊,這種情況若超越了某個臨界點,就會使人呈現精神分裂的瘋癲狀態。
對於個人這種缺乏與價值觀、象徵、模式連結的狀態,我們不妨稱之為「心理/道德上的孤獨」,心理孤獨與生理孤獨一樣令人無法忍受,甚至可以說,生理孤獨只有在伴隨著心理孤獨時,才會變得難以忍受。與外界的精神連結可以有多種形式:住在修道院單人斗室中信仰上帝的僧侶,以及被孤獨囚禁卻仍感到與同袍同在的政治犯,他們在心理上並不孤獨。某位身處遙遠異國卻身穿著燕尾服的英國紳士,或某個深受同儕孤立、卻感覺自己與民族或民族象徵同在的小資產階級,這些人都不算處於心理孤獨的狀態。與外界連結的形式可以是高尚也可以是低俗的,但即便是與最基本的模式產生連結,都遠勝處於完全的孤獨中。宗教、民族主義或任何荒謬或低俗的風俗與信念,只要能夠與他人產生連結,都為個人提供了遠離人類最恐懼的——孤獨——的避難所。
關於個人意欲逃避心理孤獨的強烈渴望,巴爾札克(Balzac)在《創造者的苦痛》(The Inventor’s
Suffering)中強而有力地描述道:
然而,請學會這件事,並將之烙印在你那可塑性仍強的大腦裡:人非常害怕孤獨。在各種孤獨
中,心理孤獨是最可怖的。心靈與上帝同在的隱士所居住的世界,其實是最擁擠的世界,因為那是
眾多心靈同屬的世界。不論是痲瘋病患或是監獄囚犯,不論是罪人或傷殘者,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
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有個同伴。為了滿足這種本身是生機的驅力,個人會用盡一切力量與能力去爭
取,若非無法忍受這種渴望,撒旦又怎麼會去尋找同伴?甚至為此寫出一整部史詩,剛好可作為
《失樂園》(Paradise Lost)的開場白,因為該書正是描寫對反叛的辯護罷了。
若想解答人們為何如此強烈害怕孤獨,將會偏離本書的主要論述。然而,為了讓讀者不至以為個
體與他者連結的需求具有某種神祕特質,我在此試著解釋我對此問題的基本認知。
一項重要的事實是,個人無法脫離與他人的合作而獨自生存。在任何可以想像的文化情境中,個
體若想生存,便必須與他人合作,或許是為了讓自己遠離敵人與自然界的危險,或許是為了讓自己能從事工作與生產。即便是魯賓遜也有他的「星期五先生」為伴;若沒有星期五先生,魯賓遜不僅會瘋掉,也可能面臨死亡。每個人都會深刻體認到需要他人的協助,就如同幼兒一般。由於幼童在各種重大機能方面都無法照顧自己,因此與他人的溝通可謂攸關生死,若不幸遭到拋棄,將面臨最嚴重的生存威脅。
不過,還有另一個原因使得「歸屬感」成為一項迫切的需求:那就是「自我意識」的存在。藉由
這種自覺思考的能力,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單獨存在的,而且有別於大自然與他人。下一章將指出,每個人的這種自覺會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這種自覺使人們面臨到只有人類才會面臨的問題:藉由意識到自身不同於大自然及他人,藉由(即便只是模糊地)意識到死亡、生病與衰老,相較於整個世界以及那些跟我不同的人,而必然性地感覺到自身極其渺小且微不足道。除非他屬於某個地方,除非他的人生具有某種意義或方向,否則他將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最終被這種自我價值的否定感所擊潰。他將無法連結於能賦予其生命意義與方向的任何體系,他的內心將充滿疑惑,而這份疑惑終將癱瘓他的行為能力——也就是活下去的能力。
在進行後續討論之前,我應總結一下前文對社會心理問題的約略論點。所謂的人類本性,並非是
生物學上固定和與生俱來驅力的總和,也不是既定文化模式下毫無生氣的追隨者,只能依據外在文化來調整自身以求適應;人的本性應是人類演進的產物,具有獨特的運作機制與法則。在人性中有某些東西是既定存在而且無法改變的,包括滿足生理需求的必要性,以及避免孤立感與心理孤獨。誠如前文所言,個人必須接受某種既定的生活方式,這根植於個人所處之社會特有的生產與分配制度。個人在對文化的動態適應過程中,會激發出許多促成個人行動與情感的強烈驅力。當然,個人或許會(或許不會)感受到這些欲望,但這些驅力一旦生成就強而有力,而且亟需獲得滿足,並反過來對形塑社會過程產生影響。關於社會經濟、個人心理與意識形態之間如何交互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從這類交互作用得出什麼結論,將在後文論及宗教改革與法西斯主義時一併探討。本書所有的討論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個人,若從原本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初始境況中得到更多自由,若在更大的程度上成為一個「個體」,將毫無選擇地必須透過自發性的愛與生產性的工作,與外在世界產生連結,否則就只能藉由犧牲自由與自我完整的方式與外在世界產生聯繫,以尋求安全感。
自由是心理學的問題?
當代歐美史的重點圍繞在人們努力爭取政治、經濟與心靈自由,並試圖擺脫往昔加諸於身的束
縛。備受壓抑的人們掀起一場場爭奪自由之戰,渴望從原本的特權階級手中得到全新的自由。當這群人試圖擺脫宰制並爭取自由的當下,他們相信自己是為爭取人類的自由而戰,因此有資格訴諸一份理想、訴諸一份根植於所有受壓迫者對於自由的渴望。然而長久以來,在漫長且持續的自由戰役中,奮力對抗壓抑和宰制的那群人,往往在某階段便轉為投入捍衛自由的敵對陣營,也就是說,一旦原本的抗爭獲得勝利,就會出現新的特權階級來維護自身的權力。
即便史上存在不少開倒車的情況,但是最終自由仍贏得許多勝利。許多人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犧
牲生命,他們堅信為反抗壓迫而死去,遠勝於在無自由的狀態中活著,這類例子可視為人類展現個體性的極致表現。歷史似乎證實了人的確有可能管理自己、替自己做決定,以及以自認適當的方式思考與感覺。充分發揮人的潛能似乎就是社會發展正快速接近的目標。經濟自由、政治民主、宗教自主,以及個人主義式的個體生活,在在傳達出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人類似乎越來越能真正地實踐自由。各種外在束縛逐一被斬斷,人類戰勝了大自然,甚至成為自然界的主宰,同時推翻了天主教會與專制政體加諸於個人身上的限制。要實現珍貴的個人自由,「廢除外在的主宰」不僅是必要條件,也是充分條件。
許多人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最終戰鬥,其最終結果就是自由的絕對
勝利。戰後,既存的民主政體益發強大,舊的君主政體也被新的民主政權取代。但僅僅數年間,新的社會體系便否定了人類自以為歷經數世紀奮鬥才得到的成果。這些新的社會體系有效掌控了所有人的社會與生活,更使得絕大多數的人屈服於他們所無法掌控的權威之下。
起初,許多人在這樣的想法中找到安慰:威權體制的勝利只是因為少數幾個人的瘋狂,而他們的
瘋狂終將使他們自行走向毀滅。有些人則不無得意地相信,義大利人與德國人長期缺乏民主訓練,所以我們可以泰然地等待他們終將達到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成熟度。另一種常見的誤解,或許也是最危險的一種,那就是認定像希特勒這樣的人之所以能獲得掌控整個國家的巨大權力,完全只憑藉著他的狡黠與欺騙手段,他的組織是以武力獲取統治權,而所有受統治的人,只能視為遭受背叛與恐怖酷行的無意志個體。數年後,這些論點的謬誤已變得十分明朗。
我們不得不承認,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迫不及待地想交出自由,簡直就像他們祖先當年爭取自由時那樣的熱切;也就是說,這些人不想要自由,反而想辦法逃避自由。另外更有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對此問題漠不關心,他們不認為自由是值得努力奮鬥、甚至付出生命來捍衛的東西。我們也認識到這類民主危機,不僅是德國人與義大利人才會面對的問題,而是所有現代國家都會遭遇到的困境。人類自由的敵對陣營究竟打著什麼旗幟其實並不重要:反法西斯主義對自由所造成的危害,並不亞於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約翰.杜威曾大力陳述這項事實:「對我們的民主政體造成最嚴重威脅的,並非其他極權國家的存在,而是存於我們自身的態度,內建於我們的組織和制度,使外在權威、紀律、規範和對外國領袖的依賴占了上風。真正的戰場其實就在我們身上,內在於我們內心與我們的體系之中。」
###
當我們探討自由的人性面、對順從的渴望及權力欲時,會明顯產生下列問題:人類體驗到的自由
究竟是什麼?對自由的渴望是否內建於人性中?是無論什麼文化的人都具備相同的自由渴望,還是會因不同社會中自由主義的發展程度而有所差異?所謂自由只是沒有外在壓力嗎?或者還需其他要素來支持?如果有,那會是什麼?在一個社會裡,什麼樣的經濟或社會問題會導致人們想要爭取自由?自由會不會成為某種沉重到令人難以承受的負擔,甚至讓人想要逃避?為什麼自由對某些人來說是珍貴的願望,對某些人而言卻是一項威脅?
除了對自由擁有天生的渴望,人們是否也在本能上產生對「順從」的欲求?否則我們如何解釋當
今竟有這麼多人自願服從領導者?再者,人們服從的對象是否總是具體化為外在的當權者,還是包括某種已經內化的權威,如義務或良心、內在驅力,甚至如公眾意見等無名的權威?對於這些服從,人們是否從中得到某種隱微的滿足感?那麼,服從的本質究竟為何?
是什麼因素使人們對權力懷抱著永不饜足的貪欲?這是否正是人類得以生機盎然的原因,或這是當人自發性地熱愛生命時所必然產生的脆弱與無能?哪些心理因素會使人產生動機去爭奪權力,而又
是哪些社會條件造就了這些心理因素?
藉由分析自由與權威主義的人性面,使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普遍性問題,也就是心理因素在社會
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這個提問最終指向探討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心理、經濟,與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果我們試圖理解法西斯主義如何能吸引眾多力量強大的國家,那麼便必須先理解心理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這種政治體制在本質上並不訴諸追求個人利益的理性力量,卻是在驅動並動員人心中那股我們以為不存在,或至少在許久前已消失殆盡的邪惡力量。近幾個世紀以來,我們所熟悉的「人類」形象是一種理性生物,其行為取決於自我利益及追求利益的能力。即便像霍布斯(Hobbes)這類學者認為:「對權力的渴求與對他人的敵意,乃人類行為最基本的驅動力」,但他同時也指出,這些力量實際上仍來自個人的自我利益,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追求幸福,當社會不存在足夠的財富讓每個人都得到滿足時,人便開始爭權奪利,以確保擁有權的永續長存。然而,霍布斯對人的理解已然過時。中產階級越成功地打破舊時代政治或宗教統治者的權威,人類就越能掌控大自然,也更具備經濟獨立的能力。綜上所述,人開始相信一個「理性的世界」,認定自己是「理性的生物」。人們逐漸將人性中的黑暗力量歸屬於僅存於中世紀或更早期的歷史產物,並認定這些力量來自缺乏知識,或肇始於偽善的王權或教宗所領導的狡黠體制。
我們檢視這些過往的時期,就好像觀察一座長久以來已不再構成威脅的火山一樣。人們自信地認
為當代民主的成就已經徹底掃除了所有的邪惡勢力,這個世界既光明又安全,如同現代城市中寬敞明亮的街道。戰爭被視為舊時代的遺物,我們只需要最後一場戰爭就能終止所有的征戰;經濟危機被視為偶發事件,即使類似的意外持續在發生。
###
為了完整理解即將進行的討論,我們應先釐清「適應」(adaptation)這個概念,這同時也能闡釋
我們所指稱的心理機制與法則。
我們應區分「靜態適應」與「動態適應」這兩個概念。我所謂「靜態適應」,是個人在整體性格
結構未變動的情況下去適應某些模式,也就是採用某種新習慣。例如,從中式飲食習慣轉變為使用刀叉的西式飲食習慣。一個中國人在美國生活,會適應這個新模式,但這種適應對本身人格並無影響,不會在他心裡引發新的驅力,或形成新的性格特質。
而我所謂的動態適應,舉例來說,當一個小男孩屈從於父親嚴厲威嚇的命令時,因為太過害怕而
不敢忤逆,遂成為一個「乖兒子」。當這個男孩順應環境需要的同時,內心也發生了某種轉變。他可能對父親產生強烈的敵意,但他卻將這份敵意壓抑下來,因為意識到這份敵意,或將之表現出來,將對自身造成危險。然而,這份被壓抑的敵意雖然不明顯,卻成為他性格結構中的一項動態因素。他可能產生新的焦慮,導致更加服從,也可能形成一種模糊的違抗意識——不見得特別針對誰,而是針對整個生命歷程。如同第一種情況,個人順從了某些外在環境,但這樣的適應行為卻在他身上創造出新的東西,引發新的驅力和新的焦慮。每一則神經官能症的案例都可視為這類動態適應的例證,它必然是為了適應某種不合理的外在情境(尤其是幼年時期的遭遇),而且普遍來說,這些情境都會對幼童成長與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同樣地,這些類似神經官能現象的社會心理現象(我在後文會解釋為什麼不將這些現象直接稱為神經官能現象),諸如存在於社群裡的毀滅性或施虐衝動,正是動態適應非理性且有害人類在社會上發展的例子。
除了探討個人心理的適應機制,我們也應檢視:什麼力量會驅使人調整自身來適應幾乎任何一種
可以想像的生命處境?而人類的適應能力,又有什麼極限?
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我們必須討論的現象是:人類天性中有某些部分比較富有彈性、適應力強,有些部分則不然。最具有彈性與可塑性的部分,是人與人之間不同的欲望與性格特質,如愛、毀
滅性、施虐、服從傾向、權力欲、疏離、自我擴張的渴望、節儉癖、感官享受,以及對縱欲的恐懼
等。上述或其他關於人的欲求與恐懼,都是為了回應特定生命情境而發展出來的特質,它們並非特別有彈性,因為它們一旦變成某人個性的一環,就不容易消失或轉變為其他驅力。然而,它們在某種情況下很有彈性,由於個人(特別在幼童時期)是根據生活方式而發展出各種需求,因此這些需求並非固定和僵化到有如與生俱來的人性本質那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非得到滿足不可。
另外有些需求與上述相反,而成為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迫切需要得到滿足,那就是根
植於個人生理結構中的需求,如飢餓、口渴、睡眠等。這類需求都具備特定的基本值,每個人都無法承受滿足的程度低於這個門檻,而當超過該基本值時,滿足欲求的意向就帶有威力極強的欲求特質。
所有的生理需求都可被化約為自我保護的概念,這種自保的需求便是在所有情況下都必須獲得滿足的人類本性,也形成了個人行為的首要動機。
簡單來說,我們必須吃喝、睡覺、保護自身以免受到敵人侵害等,為了達成這些目的,而必須工
作與生產。此處所謂的「工作」並非一種籠統或抽象的指稱,而是指具體的工作——在經濟體系中可從事的具體工作。一個人在封建體系中可能擔任奴隸工作,在印第安族的村莊中可能是個農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可能是個獨立的商人,在現代百貨公司中可能是個銷售員,也可能是某企業生產帶上的一個小工人。不同的工作需要相異的人格特質,也使個人與他人產生不同的關係。一個人出生後,他的生命舞臺就已經展現在面前——他必須為了生存而工作。這代表他必須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以他所處的社會為他所決定的方式工作。個人的生存需求及其身處的社會體系,這兩個要素原則上都是個體本身無法改變的,因此也成為發展其他較具可塑性的特質發展的因素。
由此可見,個人的生活方式已經被特定的經濟體系所決定了,也變成決定整個性格結構的基本因
素,因為自保的重要需求迫使他接受自己所處的生活條件。這並不代表個人不能結合他人的力量,試圖創造某種經濟與政治的變革,但基本上,他的人格特質主要還是受到特定生活方式的形塑,因為當他還年幼時,就已透過家庭的媒介接觸到這些生活方式,家庭環境幾乎能重現特定社會或階級所獨具的各項特質。
伴隨生理機能而產生的各種需求,並非人類性格中唯一絕對必須被滿足的部分。人性中還存在著
另一種同樣具有強制力的需求,這並非根植於身體演進的機能,而奠基於人類生活方式與生命實踐的特有本質:與外界建立連結的需求,亦即「避免孤獨」的需求。感覺完全的孤立與孤單會使人精神崩潰,就如同身體飢餓會導致死亡。這種與他人的關係並不等同肉體接觸,個人在身體上也許能獨處許多年,但仍然可與許多理念、價值觀或至少是社會模式產生連結,使得他感受到一種交流與歸屬的感覺。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身處眾人之間,卻依然被徹底的孤獨感襲擊,這種情況若超越了某個臨界點,就會使人呈現精神分裂的瘋癲狀態。
對於個人這種缺乏與價值觀、象徵、模式連結的狀態,我們不妨稱之為「心理/道德上的孤獨」,心理孤獨與生理孤獨一樣令人無法忍受,甚至可以說,生理孤獨只有在伴隨著心理孤獨時,才會變得難以忍受。與外界的精神連結可以有多種形式:住在修道院單人斗室中信仰上帝的僧侶,以及被孤獨囚禁卻仍感到與同袍同在的政治犯,他們在心理上並不孤獨。某位身處遙遠異國卻身穿著燕尾服的英國紳士,或某個深受同儕孤立、卻感覺自己與民族或民族象徵同在的小資產階級,這些人都不算處於心理孤獨的狀態。與外界連結的形式可以是高尚也可以是低俗的,但即便是與最基本的模式產生連結,都遠勝處於完全的孤獨中。宗教、民族主義或任何荒謬或低俗的風俗與信念,只要能夠與他人產生連結,都為個人提供了遠離人類最恐懼的——孤獨——的避難所。
關於個人意欲逃避心理孤獨的強烈渴望,巴爾札克(Balzac)在《創造者的苦痛》(The Inventor’s
Suffering)中強而有力地描述道:
然而,請學會這件事,並將之烙印在你那可塑性仍強的大腦裡:人非常害怕孤獨。在各種孤獨
中,心理孤獨是最可怖的。心靈與上帝同在的隱士所居住的世界,其實是最擁擠的世界,因為那是
眾多心靈同屬的世界。不論是痲瘋病患或是監獄囚犯,不論是罪人或傷殘者,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
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有個同伴。為了滿足這種本身是生機的驅力,個人會用盡一切力量與能力去爭
取,若非無法忍受這種渴望,撒旦又怎麼會去尋找同伴?甚至為此寫出一整部史詩,剛好可作為
《失樂園》(Paradise Lost)的開場白,因為該書正是描寫對反叛的辯護罷了。
若想解答人們為何如此強烈害怕孤獨,將會偏離本書的主要論述。然而,為了讓讀者不至以為個
體與他者連結的需求具有某種神祕特質,我在此試著解釋我對此問題的基本認知。
一項重要的事實是,個人無法脫離與他人的合作而獨自生存。在任何可以想像的文化情境中,個
體若想生存,便必須與他人合作,或許是為了讓自己遠離敵人與自然界的危險,或許是為了讓自己能從事工作與生產。即便是魯賓遜也有他的「星期五先生」為伴;若沒有星期五先生,魯賓遜不僅會瘋掉,也可能面臨死亡。每個人都會深刻體認到需要他人的協助,就如同幼兒一般。由於幼童在各種重大機能方面都無法照顧自己,因此與他人的溝通可謂攸關生死,若不幸遭到拋棄,將面臨最嚴重的生存威脅。
不過,還有另一個原因使得「歸屬感」成為一項迫切的需求:那就是「自我意識」的存在。藉由
這種自覺思考的能力,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單獨存在的,而且有別於大自然與他人。下一章將指出,每個人的這種自覺會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這種自覺使人們面臨到只有人類才會面臨的問題:藉由意識到自身不同於大自然及他人,藉由(即便只是模糊地)意識到死亡、生病與衰老,相較於整個世界以及那些跟我不同的人,而必然性地感覺到自身極其渺小且微不足道。除非他屬於某個地方,除非他的人生具有某種意義或方向,否則他將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最終被這種自我價值的否定感所擊潰。他將無法連結於能賦予其生命意義與方向的任何體系,他的內心將充滿疑惑,而這份疑惑終將癱瘓他的行為能力——也就是活下去的能力。
在進行後續討論之前,我應總結一下前文對社會心理問題的約略論點。所謂的人類本性,並非是
生物學上固定和與生俱來驅力的總和,也不是既定文化模式下毫無生氣的追隨者,只能依據外在文化來調整自身以求適應;人的本性應是人類演進的產物,具有獨特的運作機制與法則。在人性中有某些東西是既定存在而且無法改變的,包括滿足生理需求的必要性,以及避免孤立感與心理孤獨。誠如前文所言,個人必須接受某種既定的生活方式,這根植於個人所處之社會特有的生產與分配制度。個人在對文化的動態適應過程中,會激發出許多促成個人行動與情感的強烈驅力。當然,個人或許會(或許不會)感受到這些欲望,但這些驅力一旦生成就強而有力,而且亟需獲得滿足,並反過來對形塑社會過程產生影響。關於社會經濟、個人心理與意識形態之間如何交互影響,以及我們可以從這類交互作用得出什麼結論,將在後文論及宗教改革與法西斯主義時一併探討。本書所有的討論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個人,若從原本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初始境況中得到更多自由,若在更大的程度上成為一個「個體」,將毫無選擇地必須透過自發性的愛與生產性的工作,與外在世界產生連結,否則就只能藉由犧牲自由與自我完整的方式與外在世界產生聯繫,以尋求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