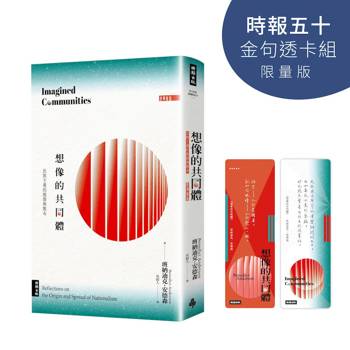第一章 導論
也許這個現象尚未廣受注意,然而,我們正面臨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運動史上一次根本的轉型。最近在越南、柬埔寨和中國之間的戰爭,就是這個轉型最明顯的徵候。這幾場戰爭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僅因為它們是在幾個無可置疑的獨立革命政權之間最早發生的戰爭,同時也因為交戰各國中沒有任何一方嘗試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辯護這些屠戮。雖然我們還是可能從「社會帝國主義」或「捍衛社會主義」之類的角度——這要視個人品味而定——來詮釋一九六九年的中蘇邊界衝突,以及蘇聯對德國(一九五三)、匈牙利(一九五六)、捷克(一九六八),和阿富汗(一九八○)等國的軍事干預,但是,我猜想,沒有人會真的相信這些術語和中南半島上發生的事情可以扯上什麼關係。
如果越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以及一九七九年一月對柬埔寨的入侵與占領,代表第一次由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權向另一個革命馬克思政權所發動的大規模傳統戰爭,那麼中國在七九年二月攻擊越南則迅速確認了這個先例。只有那些最深信不疑的人才敢打賭說,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幾年裡面,如果有任何大規模的國際衝突爆發,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不必說較小的社會主義國家了——會站在同一陣線。誰敢保證南斯拉夫哪一天不會和阿爾巴尼亞打起來?那些企圖使紅軍從東歐駐地撤出的各種團體應該先想一想,一九四五年以來,無所不在的紅軍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了這個地區的馬克思主義政權之間爆發武裝衝突。
上述的思考,有助於彰顯一個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等等,都是用民族來自我界定的;經由這樣的做法,這些革命扎實地植根於一個從革命前的過去繼承而來的領土與社會空間之中。相反的,蘇聯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卻有一個少見的共同特性,就是拒絕用民族來為國家命名。這個事實顯示,這兩國不但是十九世紀前民族期王朝國家的繼承人,也是二十一世紀國際主義秩序的先驅。
艾瑞克.霍布斯邦說過:「馬克思主義運動和尊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不管在形式或實質上都有變成民族運動和民族政權——也就是轉化成民族主義——的傾向。沒有任何事實顯示這個趨勢不會持續下去。」在這點上,他是完全正確的。然而,這個傾向並非只發生在社會主義世界之內而已。聯合國幾乎年年都接受新的會員。許多過去被認為已經完全穩固的「老民族」如今卻面臨境內一些「次」民族主義(sub-nationalisms)的挑戰。這些民族主義運動自然夢想著有這麼快樂的一天,它們將要褪去這個「次級」的外衣。事實擺在眼前:長久以來被預言將要到來的「民族主義時代的終結」,根本還遙遙無期。事實上,民族屬性(nation-ness)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價值。
但是,如果事實是清清楚楚的,那麼該如何解釋這些事實則是一段長期聚訟紛紜的公案。nation(民族),nationality(民族歸屬),4nationalism(民族主義)——這幾個名詞涵義之難以界定,早已是惡名昭彰,遑論對之加以分析了。民族主義已經對現代世界發生過巨大的影響了;然而,與此事實適成對比的是,具有說服力的民族主義理論卻明顯的屈指可數。休.賽頓-華生(Hugh Seton-Watson),這位關於民族主義的英文論著中最好、涵蓋面最廣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義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繼承人,悲傷地觀察道:「我被迫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也就是說,我們根本無法為民族下一個『科學的』定義;然而,從以前到現在,這個現象卻一直持續存在著。」湯姆.奈倫(Tom Nairn),《不列顛的崩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這部開創性作品的作者,同時也是規模未遑多讓(於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與社會科學傳統的傳人,做了如此坦白的評論:「民族主義的理論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歷史性的大失敗。」然而甚至這樣的表白也還是有些誤導,因為我們會誤以為這段話的含意是,馬克思主義確實曾經長期而自覺地追尋一個清晰的民族主義理論,只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努力失敗罷了。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言,民族主義已經證明是一個令人不快的異常現象;並且,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常常略過民族主義不提,不願正視。不然,我們該如何解釋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難忘的對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闡述當中,竟然沒有說明其中那個關鍵性的形容詞的意義:「當然,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必須先處理和它自己的(its own)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我們又怎樣解釋「民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這個概念被用了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卻沒有人認真地從理論上合理化(民族)這個形容詞的相關性?如果以生產關係來界定,資產階級明明是一個世界性的階級,那麼,為什麼這個特定部分的資產階級在理論上是重要的?
本書的目的在於嘗試對民族主義這個「異常現象」,提出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詮釋。我覺得,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都因為陷入一種「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這個現象」的努力,所以都變得蒼白無力;我們亟需將理解這個問題的角度,調整到一種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我的研究起點是,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者,有人會傾向使用能夠表現其多重意義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適當地理解這些現象,我們必須審慎思考在歷史上它們是怎樣出現的,它們的意義怎樣在漫長的時間中產生變化,以及為何今天能夠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當性。我將會嘗試論證,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末被創造出來,其實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它們就變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態下,它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可以吸納同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我也會試圖說明,為什麼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會引發人們如此深沉的依戀之情。
概念與定義
在處理上面提出的問題之前,我們似乎應該先簡短地考慮一下「民族」這個概念,並且給它下一個可行的定義。下列這三個詭論經常讓民族的理論家感到惱怒而困惑:(一)民族在歷史學家眼中的客觀的現代性相對於民族在民族主義者眼中主觀的古老性。(二)民族歸屬作為社會文化概念的形式普遍性——在現代世界每個人,就像他或她擁有一個性別一樣,都能夠、應該,並且將會擁有一個民族成員的身分─相對於民族歸屬在具體表徵上無可救贖的特殊性,例如,「希臘」民族成員的身分,依照定義本來就是獨特的(sui generis)。(三)各種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力量相對於它們在哲學上的貧困與不統一。換言之,和大多數其他主義不同的是,民族主義從未產生它自己的偉大思想家:沒有它的霍布斯(Hobbes)、托克維爾、馬克思,或韋伯。這種「空洞性」很容易讓具有世界主義精神和能夠使用多種語言的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產生某種輕鄙的態度。就像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面對奧克蘭(Oakland)的時候一樣,人們會很快下結論說民族主義是一個「空無一物的地方」(there is ‘no there there.’)。即使像奈倫這麼同情民族主義的學者也還是會如此寫道:「『民族主義』是現代歷史發展上的病態。如同『神經衰弱』之於個人一樣的不可避免;它既帶有與神經衰弱極類似的本質上的曖味性,也同樣有著退化成痴呆症的內在潛能─這個退化潛能乃是根源於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所共同面臨的無助的兩難困境之中(這種痴呆症等於是社會的幼稚病),並且,在多數情況下是無藥可醫的。」
有一部分的困難來自於,人們雖然不會把「年齡」這個概念當作一個專有名詞,卻常常不自覺地把民族主義當作專有名詞,將它視為一個具有特定專屬內容的存在實體,然後把「它」區別為一種意識形態。(請注意,假如每個人都有年齡,那麼「年齡」只不過是一種分析性的表達語彙而已。)我想,如果我們把民族主義當作像「血緣關係」(kinship)或「宗教」(religion)這類的概念來處理,而不要把它理解為像「自由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事情應該會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依循著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做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當赫南寫道:「然而民族的本質在於每個人都會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同時每個人也都遺忘了許多事情。」他其實就以一種文雅而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到了這個想像。當蓋爾納判定「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族」,他是帶著幾分粗暴地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論點。但是,蓋爾納這個表述的缺點是,他太熱切地想指出民族主義其實是偽裝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發明(invention)等同於「捏造」(fabrication)和「虛假」(falsity),而不是「想像」(imaginging)與「創造」(creation)。在此情形下,他暗示了有「真實」的共同體存在,而相較於民族,這些真實的共同體享有更優越的地位。事實上,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括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它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它們被想像的方式。爪哇的村落居民總是知道他們和從未謀面的人們有所關聯,然而這種關聯性,就如同可以無限延伸的親族或侍從(clientship)
也許這個現象尚未廣受注意,然而,我們正面臨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運動史上一次根本的轉型。最近在越南、柬埔寨和中國之間的戰爭,就是這個轉型最明顯的徵候。這幾場戰爭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僅因為它們是在幾個無可置疑的獨立革命政權之間最早發生的戰爭,同時也因為交戰各國中沒有任何一方嘗試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辯護這些屠戮。雖然我們還是可能從「社會帝國主義」或「捍衛社會主義」之類的角度——這要視個人品味而定——來詮釋一九六九年的中蘇邊界衝突,以及蘇聯對德國(一九五三)、匈牙利(一九五六)、捷克(一九六八),和阿富汗(一九八○)等國的軍事干預,但是,我猜想,沒有人會真的相信這些術語和中南半島上發生的事情可以扯上什麼關係。
如果越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以及一九七九年一月對柬埔寨的入侵與占領,代表第一次由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權向另一個革命馬克思政權所發動的大規模傳統戰爭,那麼中國在七九年二月攻擊越南則迅速確認了這個先例。只有那些最深信不疑的人才敢打賭說,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幾年裡面,如果有任何大規模的國際衝突爆發,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不必說較小的社會主義國家了——會站在同一陣線。誰敢保證南斯拉夫哪一天不會和阿爾巴尼亞打起來?那些企圖使紅軍從東歐駐地撤出的各種團體應該先想一想,一九四五年以來,無所不在的紅軍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了這個地區的馬克思主義政權之間爆發武裝衝突。
上述的思考,有助於彰顯一個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等等,都是用民族來自我界定的;經由這樣的做法,這些革命扎實地植根於一個從革命前的過去繼承而來的領土與社會空間之中。相反的,蘇聯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卻有一個少見的共同特性,就是拒絕用民族來為國家命名。這個事實顯示,這兩國不但是十九世紀前民族期王朝國家的繼承人,也是二十一世紀國際主義秩序的先驅。
艾瑞克.霍布斯邦說過:「馬克思主義運動和尊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不管在形式或實質上都有變成民族運動和民族政權——也就是轉化成民族主義——的傾向。沒有任何事實顯示這個趨勢不會持續下去。」在這點上,他是完全正確的。然而,這個傾向並非只發生在社會主義世界之內而已。聯合國幾乎年年都接受新的會員。許多過去被認為已經完全穩固的「老民族」如今卻面臨境內一些「次」民族主義(sub-nationalisms)的挑戰。這些民族主義運動自然夢想著有這麼快樂的一天,它們將要褪去這個「次級」的外衣。事實擺在眼前:長久以來被預言將要到來的「民族主義時代的終結」,根本還遙遙無期。事實上,民族屬性(nation-ness)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價值。
但是,如果事實是清清楚楚的,那麼該如何解釋這些事實則是一段長期聚訟紛紜的公案。nation(民族),nationality(民族歸屬),4nationalism(民族主義)——這幾個名詞涵義之難以界定,早已是惡名昭彰,遑論對之加以分析了。民族主義已經對現代世界發生過巨大的影響了;然而,與此事實適成對比的是,具有說服力的民族主義理論卻明顯的屈指可數。休.賽頓-華生(Hugh Seton-Watson),這位關於民族主義的英文論著中最好、涵蓋面最廣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義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繼承人,悲傷地觀察道:「我被迫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也就是說,我們根本無法為民族下一個『科學的』定義;然而,從以前到現在,這個現象卻一直持續存在著。」湯姆.奈倫(Tom Nairn),《不列顛的崩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這部開創性作品的作者,同時也是規模未遑多讓(於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與社會科學傳統的傳人,做了如此坦白的評論:「民族主義的理論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歷史性的大失敗。」然而甚至這樣的表白也還是有些誤導,因為我們會誤以為這段話的含意是,馬克思主義確實曾經長期而自覺地追尋一個清晰的民族主義理論,只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努力失敗罷了。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言,民族主義已經證明是一個令人不快的異常現象;並且,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常常略過民族主義不提,不願正視。不然,我們該如何解釋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難忘的對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闡述當中,竟然沒有說明其中那個關鍵性的形容詞的意義:「當然,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必須先處理和它自己的(its own)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我們又怎樣解釋「民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這個概念被用了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卻沒有人認真地從理論上合理化(民族)這個形容詞的相關性?如果以生產關係來界定,資產階級明明是一個世界性的階級,那麼,為什麼這個特定部分的資產階級在理論上是重要的?
本書的目的在於嘗試對民族主義這個「異常現象」,提出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詮釋。我覺得,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都因為陷入一種「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這個現象」的努力,所以都變得蒼白無力;我們亟需將理解這個問題的角度,調整到一種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我的研究起點是,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者,有人會傾向使用能夠表現其多重意義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適當地理解這些現象,我們必須審慎思考在歷史上它們是怎樣出現的,它們的意義怎樣在漫長的時間中產生變化,以及為何今天能夠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當性。我將會嘗試論證,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末被創造出來,其實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它們就變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態下,它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可以吸納同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我也會試圖說明,為什麼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會引發人們如此深沉的依戀之情。
概念與定義
在處理上面提出的問題之前,我們似乎應該先簡短地考慮一下「民族」這個概念,並且給它下一個可行的定義。下列這三個詭論經常讓民族的理論家感到惱怒而困惑:(一)民族在歷史學家眼中的客觀的現代性相對於民族在民族主義者眼中主觀的古老性。(二)民族歸屬作為社會文化概念的形式普遍性——在現代世界每個人,就像他或她擁有一個性別一樣,都能夠、應該,並且將會擁有一個民族成員的身分─相對於民族歸屬在具體表徵上無可救贖的特殊性,例如,「希臘」民族成員的身分,依照定義本來就是獨特的(sui generis)。(三)各種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力量相對於它們在哲學上的貧困與不統一。換言之,和大多數其他主義不同的是,民族主義從未產生它自己的偉大思想家:沒有它的霍布斯(Hobbes)、托克維爾、馬克思,或韋伯。這種「空洞性」很容易讓具有世界主義精神和能夠使用多種語言的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產生某種輕鄙的態度。就像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面對奧克蘭(Oakland)的時候一樣,人們會很快下結論說民族主義是一個「空無一物的地方」(there is ‘no there there.’)。即使像奈倫這麼同情民族主義的學者也還是會如此寫道:「『民族主義』是現代歷史發展上的病態。如同『神經衰弱』之於個人一樣的不可避免;它既帶有與神經衰弱極類似的本質上的曖味性,也同樣有著退化成痴呆症的內在潛能─這個退化潛能乃是根源於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所共同面臨的無助的兩難困境之中(這種痴呆症等於是社會的幼稚病),並且,在多數情況下是無藥可醫的。」
有一部分的困難來自於,人們雖然不會把「年齡」這個概念當作一個專有名詞,卻常常不自覺地把民族主義當作專有名詞,將它視為一個具有特定專屬內容的存在實體,然後把「它」區別為一種意識形態。(請注意,假如每個人都有年齡,那麼「年齡」只不過是一種分析性的表達語彙而已。)我想,如果我們把民族主義當作像「血緣關係」(kinship)或「宗教」(religion)這類的概念來處理,而不要把它理解為像「自由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事情應該會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依循著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做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當赫南寫道:「然而民族的本質在於每個人都會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同時每個人也都遺忘了許多事情。」他其實就以一種文雅而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到了這個想像。當蓋爾納判定「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族」,他是帶著幾分粗暴地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論點。但是,蓋爾納這個表述的缺點是,他太熱切地想指出民族主義其實是偽裝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發明(invention)等同於「捏造」(fabrication)和「虛假」(falsity),而不是「想像」(imaginging)與「創造」(creation)。在此情形下,他暗示了有「真實」的共同體存在,而相較於民族,這些真實的共同體享有更優越的地位。事實上,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括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它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它們被想像的方式。爪哇的村落居民總是知道他們和從未謀面的人們有所關聯,然而這種關聯性,就如同可以無限延伸的親族或侍從(client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