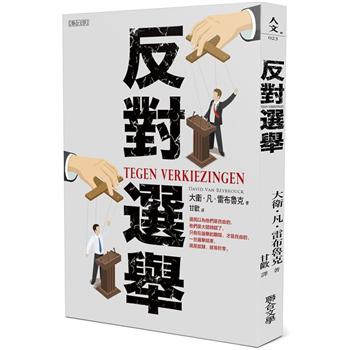效率的危機:活力下降
民主制度的合法性陷入了危機,其效率也面臨問題。幾近明瞭的各種各樣的缺陷都表明,要進行有效的政府管理越來越困難。議會有時需要十五年才能通過一條法律;要組建政府更是困難重重,就算組織起了政府,它也時常不太穩固,任期滿後,選民對其的抨擊經常會越來越猛烈。雖說投票率一再跑低,但選舉時常限制了政府的效率。我再來說一說那三條症狀。
第一,組建政府所需的協商時間越來越長,尤其在多黨制國家。在二○一○年六月的選舉之後,比利時長達一年半沒有政府,這打破了歷史紀錄。比利時絕非孤例,義大利和希臘也出現過類似情形,在近幾次投票後,兩國都歷盡艱辛才組建了政府團隊。甚至在荷蘭,形勢同樣錯綜複雜。二戰後,在組建荷蘭政府的談判中,有九場持續時間超過八十天,而其中有五場發生在一九九四年以後。*19原因自然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之一是,組建政府機構涉及的協約越來越長,且力圖事無巨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尤其考慮到所需時長變得前所未有地難以預測,而且對於急迫的需求必須靈活地予以回應。然而,執政聯盟的夥伴變得互不信任,選民可能施加的「懲罰」讓政府深感懼怕與不安,所以,政府成立後所需的方方面面的政策顯然應該提前就制定好。每個政黨都希望達成最好的協約,希望提前夯實盡可能牢固的基礎,關鍵在於達成目標,盡可能完全地落實政黨的計畫。如此一來,談判當然就沒完沒了了。
第二,政黨不得不承受越來越嚴重的攻擊。雖說代議制政府的比較還只是一個十分年輕的研究領域,但已取得相當震撼的研究成果,而針對歐洲選舉的「回報」的研究更是如此。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政黨將面臨何種命運呢?在二十世紀五、六○年代,曾經當選的黨派會失去一%─一‧五%的支持率;在一九七○年代,失去的是二%;在一九八○年代,失去的是六%;而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這一比例高達八%或者更高。在芬蘭、荷蘭和愛爾蘭的最近一次選舉中,當權的政黨喪失的支持率分別為十一%、一五%和二七%。既然行使權力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誰還想要積極地管理國家呢?從目前形勢看,無所作為才是理性的,尤其是當這樣做不會影響政黨的資金來源時(如在國家會提供資金的政治制度中)。
第三,政府的效率越來越低下。浩大的基礎建設工程,如阿姆斯特丹的南北地鐵路線、斯圖加特的新火車站、安特衛普的環城大道、南特的國際機場項目,都開展得舉步維艱,或者直接就陷入癱瘓。由於歐洲有了數十個地方企業和跨國企業,所以政府部門大受限制,威信和權力大不如從前。在以前,這些項目是國家在技術型事業上的壯舉,因而樹立了國家的威信;可現在,它們就是政府的一場噩夢。政府曾經修建須德海(Zuiderzee)攔海大壩,治理萊茵河和馬斯河三角洲,還建成了高速火車系統和英法海底隧道,不過那樣的光榮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政府如果連鑿條隧道或建座大橋都不行,那還能做什麼呢?它能夠做到的事情實在是少之又少,因為不管做什麼,由於受到國債、歐洲立法、美國評價機構、跨國企業以及國際條例的鉗制,政府時常會感到束手束腳、無法行動。在21世紀初,曾經作為民族國家根基的主權成了一個相對性概念。所以,政府沒有能力迎接我們這個時代的氣候變化、銀行危機、歐元危機、經濟危機、避稅天堂、移民、人口過剩等重大挑戰。
我們現在的關鍵字是「無能為力」:公民面對政府部門感到無能為力,政府部門面對歐洲感到無能為力,歐洲面對世界感到無能為力。人們從每個等級往下面看時,看到的都是一團糟,心裡充滿蔑視,然後懷著絕望和憤怒,而非希望和信任,不再把目光往高處看。今天的權力等級就是一道梯子,上面擠滿了互相謾駡之人。
政治以前一直都是可能的藝術,但現在它是微觀藝術。它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導致媒體瘋狂助長對邊角之事的過度曝光;媒體按照市場邏輯,把誇大無謂的衝突而不是為現實問題提供卓識當作首要任務,尤其是在新聞媒體行業的低迷期。換言之,媒體一時的關注焦點空前地控制著局面。荷蘭的議會近來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議會的自我反省委員會撰寫的報告顯示了一定的洞見:
「為了贏得接下來的選舉,政客一直想要獲得分數。日益商業化的媒體隨時願意為他們提供陣地,這讓三個部門(政府、媒體和企業)在實力較量中互相鉗制,這個百慕大三角以一些神秘的方式把每件事都拉進來,而誰都摸不著頭腦,弄不清其中緣由……政治與媒體的相互作用似乎確實是創造越來越多政治偶發性(incidentalism)的一個重要因素。新聞就是媒體的食糧。在與記者的談話中我們注意到,比起同時進行的高水準辯論,一些小插曲更容易吸引媒體的眼球。」
偶發性這個新詞非常有用,資料則讓我們毫無疑慮。近些年來,在荷蘭的議會中,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提問,無論是提交的議案還是緊急的辯論,都在大幅增長;與此同時,荷蘭電視臺的政治脫口秀節目的數量也大大增加,因為一旦攝像機被打開,任何一個名副其實的議員都需要得分。在這個報告中,一位受訪人指出:「議員們『很驚訝』,『很震驚』,『非常不滿』。在十九世紀時,年邁的法學家在下議院或許比比皆是,在當下則是寥若晨星。」
如果官員們不想治理國家而只想提升公共形象,如果對選舉的熱情成了一種慢性疾病,如果妥協總是被當作背叛,如果黨派政治經常引起蔑視,如果行使權力必然會導致嚴重的選舉懲罰,那麼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怎麼還會想要進入政壇呢?議會面臨著貧血的危險,它越來越難吸引到鬥志昂揚的新人(效率危機的第二條症狀)。政客這一職業正經受著和教員相同的命運:教員以前可以說是德高望重,如今卻一文不值。一本為政府招賢納士的小冊子使用了一個極具揭示性意義的題目:找到並留住人才。
然而,留住政治人才並非易事,因為相比以往,政治才幹的耗費變得更加迅速。歐洲理事會主席赫爾曼‧范宏畢(Herman Van Rompuy)近來就這一話題發表了言論:「我們實行的民主制度以驚人的速度『磨損』著我們。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民主本身並不會衰竭。」
以上就是民主制的效率面臨的主要危機。民主的銳氣漸漸消弭,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它同時又越來越熱鬧。政客們不會躲到牆角嘟嘟囔囔,為自己的無能為力備感恥辱,為自己的行動範圍有限而心有慚愧;相反,他們會──甚至是應該──向公眾宣傳自己的德行(選舉和媒體沒有給予他們選擇的餘地),同時還要緊握拳頭、雙腿站直、張大嘴巴,因為擺出這樣的姿勢能傳達出力量感,對他們大有裨益,至少他們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們沒有羞愧地承認權力的平衡狀態已被打破,或去尋找有效的政府組織新形式,而是不顧他們自己和公民的利益,繼續玩著媒體-選舉的遊戲。公民受夠了這種演出:這種誇張、做作的歇斯底里並不能從根本上重建公民對民主制的信任。民主制的效率也出現了危機,對合法性的危機而言這無異於雪上加霜。
分析完以上種種,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症狀既繁多又含混,但如果我們羅列出棄票論、選舉的不穩定性、政黨的人員流失、管理上的無能、政治癱瘓、害怕選舉失敗、人才招攬的欠缺、強迫性的自我推銷、持久的選舉熱忱、讓人筋疲力盡的媒體壓力、質疑、淡漠以及其他根深蒂固的惡習,症候的輪廓就能明晰可辨,這就是“民主疲勞綜合症”。針對這一疾病的系統性研究尚未展開,但無可否認的是,不少西方民主制國家已罹患此病。我們現在就來審視已確定的診斷吧!
民主制度的合法性陷入了危機,其效率也面臨問題。幾近明瞭的各種各樣的缺陷都表明,要進行有效的政府管理越來越困難。議會有時需要十五年才能通過一條法律;要組建政府更是困難重重,就算組織起了政府,它也時常不太穩固,任期滿後,選民對其的抨擊經常會越來越猛烈。雖說投票率一再跑低,但選舉時常限制了政府的效率。我再來說一說那三條症狀。
第一,組建政府所需的協商時間越來越長,尤其在多黨制國家。在二○一○年六月的選舉之後,比利時長達一年半沒有政府,這打破了歷史紀錄。比利時絕非孤例,義大利和希臘也出現過類似情形,在近幾次投票後,兩國都歷盡艱辛才組建了政府團隊。甚至在荷蘭,形勢同樣錯綜複雜。二戰後,在組建荷蘭政府的談判中,有九場持續時間超過八十天,而其中有五場發生在一九九四年以後。*19原因自然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之一是,組建政府機構涉及的協約越來越長,且力圖事無巨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尤其考慮到所需時長變得前所未有地難以預測,而且對於急迫的需求必須靈活地予以回應。然而,執政聯盟的夥伴變得互不信任,選民可能施加的「懲罰」讓政府深感懼怕與不安,所以,政府成立後所需的方方面面的政策顯然應該提前就制定好。每個政黨都希望達成最好的協約,希望提前夯實盡可能牢固的基礎,關鍵在於達成目標,盡可能完全地落實政黨的計畫。如此一來,談判當然就沒完沒了了。
第二,政黨不得不承受越來越嚴重的攻擊。雖說代議制政府的比較還只是一個十分年輕的研究領域,但已取得相當震撼的研究成果,而針對歐洲選舉的「回報」的研究更是如此。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政黨將面臨何種命運呢?在二十世紀五、六○年代,曾經當選的黨派會失去一%─一‧五%的支持率;在一九七○年代,失去的是二%;在一九八○年代,失去的是六%;而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這一比例高達八%或者更高。在芬蘭、荷蘭和愛爾蘭的最近一次選舉中,當權的政黨喪失的支持率分別為十一%、一五%和二七%。既然行使權力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誰還想要積極地管理國家呢?從目前形勢看,無所作為才是理性的,尤其是當這樣做不會影響政黨的資金來源時(如在國家會提供資金的政治制度中)。
第三,政府的效率越來越低下。浩大的基礎建設工程,如阿姆斯特丹的南北地鐵路線、斯圖加特的新火車站、安特衛普的環城大道、南特的國際機場項目,都開展得舉步維艱,或者直接就陷入癱瘓。由於歐洲有了數十個地方企業和跨國企業,所以政府部門大受限制,威信和權力大不如從前。在以前,這些項目是國家在技術型事業上的壯舉,因而樹立了國家的威信;可現在,它們就是政府的一場噩夢。政府曾經修建須德海(Zuiderzee)攔海大壩,治理萊茵河和馬斯河三角洲,還建成了高速火車系統和英法海底隧道,不過那樣的光榮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政府如果連鑿條隧道或建座大橋都不行,那還能做什麼呢?它能夠做到的事情實在是少之又少,因為不管做什麼,由於受到國債、歐洲立法、美國評價機構、跨國企業以及國際條例的鉗制,政府時常會感到束手束腳、無法行動。在21世紀初,曾經作為民族國家根基的主權成了一個相對性概念。所以,政府沒有能力迎接我們這個時代的氣候變化、銀行危機、歐元危機、經濟危機、避稅天堂、移民、人口過剩等重大挑戰。
我們現在的關鍵字是「無能為力」:公民面對政府部門感到無能為力,政府部門面對歐洲感到無能為力,歐洲面對世界感到無能為力。人們從每個等級往下面看時,看到的都是一團糟,心裡充滿蔑視,然後懷著絕望和憤怒,而非希望和信任,不再把目光往高處看。今天的權力等級就是一道梯子,上面擠滿了互相謾駡之人。
政治以前一直都是可能的藝術,但現在它是微觀藝術。它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導致媒體瘋狂助長對邊角之事的過度曝光;媒體按照市場邏輯,把誇大無謂的衝突而不是為現實問題提供卓識當作首要任務,尤其是在新聞媒體行業的低迷期。換言之,媒體一時的關注焦點空前地控制著局面。荷蘭的議會近來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議會的自我反省委員會撰寫的報告顯示了一定的洞見:
「為了贏得接下來的選舉,政客一直想要獲得分數。日益商業化的媒體隨時願意為他們提供陣地,這讓三個部門(政府、媒體和企業)在實力較量中互相鉗制,這個百慕大三角以一些神秘的方式把每件事都拉進來,而誰都摸不著頭腦,弄不清其中緣由……政治與媒體的相互作用似乎確實是創造越來越多政治偶發性(incidentalism)的一個重要因素。新聞就是媒體的食糧。在與記者的談話中我們注意到,比起同時進行的高水準辯論,一些小插曲更容易吸引媒體的眼球。」
偶發性這個新詞非常有用,資料則讓我們毫無疑慮。近些年來,在荷蘭的議會中,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提問,無論是提交的議案還是緊急的辯論,都在大幅增長;與此同時,荷蘭電視臺的政治脫口秀節目的數量也大大增加,因為一旦攝像機被打開,任何一個名副其實的議員都需要得分。在這個報告中,一位受訪人指出:「議員們『很驚訝』,『很震驚』,『非常不滿』。在十九世紀時,年邁的法學家在下議院或許比比皆是,在當下則是寥若晨星。」
如果官員們不想治理國家而只想提升公共形象,如果對選舉的熱情成了一種慢性疾病,如果妥協總是被當作背叛,如果黨派政治經常引起蔑視,如果行使權力必然會導致嚴重的選舉懲罰,那麼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怎麼還會想要進入政壇呢?議會面臨著貧血的危險,它越來越難吸引到鬥志昂揚的新人(效率危機的第二條症狀)。政客這一職業正經受著和教員相同的命運:教員以前可以說是德高望重,如今卻一文不值。一本為政府招賢納士的小冊子使用了一個極具揭示性意義的題目:找到並留住人才。
然而,留住政治人才並非易事,因為相比以往,政治才幹的耗費變得更加迅速。歐洲理事會主席赫爾曼‧范宏畢(Herman Van Rompuy)近來就這一話題發表了言論:「我們實行的民主制度以驚人的速度『磨損』著我們。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民主本身並不會衰竭。」
以上就是民主制的效率面臨的主要危機。民主的銳氣漸漸消弭,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它同時又越來越熱鬧。政客們不會躲到牆角嘟嘟囔囔,為自己的無能為力備感恥辱,為自己的行動範圍有限而心有慚愧;相反,他們會──甚至是應該──向公眾宣傳自己的德行(選舉和媒體沒有給予他們選擇的餘地),同時還要緊握拳頭、雙腿站直、張大嘴巴,因為擺出這樣的姿勢能傳達出力量感,對他們大有裨益,至少他們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們沒有羞愧地承認權力的平衡狀態已被打破,或去尋找有效的政府組織新形式,而是不顧他們自己和公民的利益,繼續玩著媒體-選舉的遊戲。公民受夠了這種演出:這種誇張、做作的歇斯底里並不能從根本上重建公民對民主制的信任。民主制的效率也出現了危機,對合法性的危機而言這無異於雪上加霜。
分析完以上種種,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症狀既繁多又含混,但如果我們羅列出棄票論、選舉的不穩定性、政黨的人員流失、管理上的無能、政治癱瘓、害怕選舉失敗、人才招攬的欠缺、強迫性的自我推銷、持久的選舉熱忱、讓人筋疲力盡的媒體壓力、質疑、淡漠以及其他根深蒂固的惡習,症候的輪廓就能明晰可辨,這就是“民主疲勞綜合症”。針對這一疾病的系統性研究尚未展開,但無可否認的是,不少西方民主制國家已罹患此病。我們現在就來審視已確定的診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