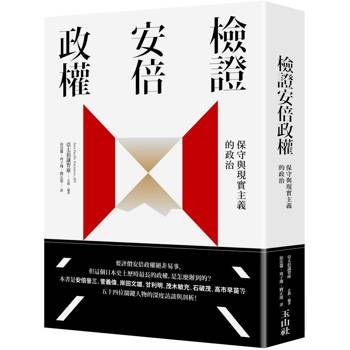序論 為什麼能夠變成長期穩定的政權 中北浩爾
檢證對象──第二次安倍政權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安倍晉三首相突然表態辭去內閣總理大臣的職務,理由是宿疾的惡化。當天的記者會上,安倍被問到有關安倍政權的政績(政治遺產)時,回答舉出,安倍政權不僅僅是致力於東日本大地震災後的復興工作,更以擺脫通貨緊縮為目標的安倍經濟學來創造工作機會,將成長的果實轉化為擴充托育政策、兒童教育與托育的無償化、高等教育的無償化等等,著手於勞動方式改革和一億總活躍社會;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上,制定有限度行使集體自衛權為前提的和平安全法制(譯按:新安保法,又稱:安全保障關連法),在鞏固日美同盟的同時,致力於創造TPP等自由公平的區域經濟體。安倍也提及尚待解決的有,修改憲法、締結日俄和平條約、北韓綁架日本人等三個問題。
最後,安倍政權於九月十六日內閣總辭。安倍首相的任職天數,若從第一次內閣起算,長達三千一百八十八天;若從第二次內閣成立時算起,連續任職天數則達到二千八百二十二天。不論哪一種計算方式,都是日本憲政史上執政最長的首相。也可以說,作為特例的長期政權就此落幕。
安倍內閣不只是長期政權,也是特例的穩定政權,而其象徵性的語彙就是「一強」吧。「一強」在使用上具有雙重意涵,一方面,所謂自民黨「一強」,是指積弱不振的在野黨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明顯不高;另一方面,所謂安倍「一強」,是指政權內部的權力集中於首相、總裁。
本書從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開始,至二○二○年九月十六日第四次安倍內閣的總辭為止,對第二次安倍政權進行了檢證。這裡採用所謂的「第二次安倍政權」,將七年八個月看作一個整體,是為了與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內閣總辭的「第一次安倍政權」作出區別。以下,全部的職稱皆以當時為主,並省略所有敬稱。敬請見諒。
第二次安倍政權早已成為眾說紛紜的標的,因此,在檢證上會徹底重視實證的手法。並不是按照事先準備的理論和分析架構來論斷,而是再三對當事人進行訪談,然後與之互相比對文獻和相關資料,想要引導出歸納性的結論。我們的目標並不是要讚揚或批判第二次安倍政權,而是要透過檢證,探索實現更好的日本政治的線索。
應該要檢證的疑問
貫穿本書整體的疑問是,為什麼第二次安倍政權會在日本政界變成特例的長期穩定政權呢?
從現在來看,雖然或許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但絕非如此。在就職當天的記者會上,被問及第一次安倍政權之後,首相頻繁輪替的問題時,安倍回答:「身為執政一年不得不結束政權的負責人,我感到責任相當重大。同時,想活用執政過的經驗和經歷過挫折的經驗。」另外還補充道:「我認為現在,為了『畫上政治混亂和停滯的休止符』,推動穩定的政府運作,才是我們要追求的使命。」
二○○六年第一次安倍內閣成立,執政一年便內閣總辭,之後福田康夫內閣和麻生太郎內閣不到一年就結束執政。二○○九年從自民黨到民主黨,完成真正的政黨輪替,雖然成立了鳩山由紀夫內閣,但卻不滿一年,繼任的菅直人內閣和野田佳彥內閣也都只維持一年多的時間,就不得不結束執政。包含第一次安倍政權,歷經六任短命的政權之後登場的第二次安倍政權,依舊被認為無法長期執政。
另外,在野時期的自民黨開始右傾化。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黨大會通過新的黨綱,為了對抗奪走政權的民主黨,新黨綱內容傾向「很具日本特色的日本保守主義」,把「新憲法制定」放到具體方針的最前端(譯按:在該綱領的第二大項,指出本黨政策的基本構想如下所述,第一點顯示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樣態,以制定可以貢獻世界的新憲法為目標。)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布的「日本國憲法修正草案」提到,天皇元首化、保有國防軍、家人相互尊重和扶持之義務等條項,比起二○○五年的「新憲法草案」,明顯增添右傾的內容。於是,在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安倍以右派團體的「創生日本」作為基礎,出馬競選並成功當選。
在這個原委下成立的第二次安倍政權,被認為推動了包含修憲在內的右傾政策,不是嗎?再者,如同第一次安倍政權所公布的「擺脫戰後體制」,不會又因為相同的原因而變成短命政權吧?
然而,若回顧以往,也可以說現在與上述的猜想有著很大的差異。
就政府運作來看,包含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的二○一二年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在安倍總裁的帶領下,連續六次贏得國會大選,內閣支持率也跟著水漲船高。與被批評的第一次安倍政權的「首相官邸失能」不同,第二次安倍政權實現了強而有力且穩定的官邸主導,巧妙地掌握執政的自民與公明兩黨,以及各省廳的官僚。當然,對各省廳強而有力的領導手腕,也產生了所謂官僚的「消極態度」和「揣摩上意」等歪風,因而招來批判,特別是森友學園問題發生了所謂竄改公文書等嚴重事件,一定會被記錄下來。
關於政策方面,安倍首相在第一次政權以來,對於參拜靖國神社的夙願,只進行過一次,就將代表安倍經濟學的經濟政策端上檯面。雖然推動將日美同盟作為主軸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但承認行使集體自衛權並非全面開綠燈、暢行無阻,而是內容仍有所限制,為了合乎日本國憲法的規定,制定利用內閣會議決定動用武力的「新三要件」。即使戰後七十年的首相談話等歷史問題有所收斂,也沒有走到持續以修憲為目標的這一步,甚至致力於接收在野黨主張的女性、兒童政策,以及勞動政策等內容。
本書就為何能夠維持長期穩定政權的提問,從安倍經濟學、選舉‧輿論對策、官邸主導、外交‧安全保障、TPP‧通商、歷史問題、執政黨的統治體系、女性政策、憲法修正等九個面向進行檢證。
歷史背景─政治改革和民主黨政權的失敗
第二次安倍政權之所以成為日本政治史上少有的長期穩定政權,歷史背景就是一九九四年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被稱為五五年體制的自民黨近三十八年長期執政期間,派系和族議員利用分權的自民黨組織,產生出政、官、財三方的緊密關係,也發生欠缺領導中心和結構性貪汙等問題;應該要解決上述問題,以英國型的政治體制,也就是將可能政黨輪替的兩大政黨制,和以此為前提的首相權力集中作為目標,就可以持續不斷地進行改革。
在一九九四年的政治改革中,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被導入眾議院選舉,取代以往的中選舉區制,另一方面強化對企業、利益團體政治獻金的規範,並導入政黨補助金制度。此外,透過橋本政權的行政改革,強化省廳重組和內閣功能的計畫,並於二○○一年實施。其中,在小選舉區制的背景之下,一九九八年成立的民主黨雖幾經波折,仍持續成長,並在二○○九年的眾議院大選上大勝自民黨,真正達成了政黨輪替,這可以看作是一連串政治改革的成果。
與政治改革並列的另一歷史背景,是民主黨政權的失敗;詳見亞太倡議智庫的前身──重建日本倡議基金會所著《檢證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一書。民主黨政權無法履行政見,於二○一○年參議院選舉失敗而陷入「分立國會」的窘境,短時間之內就顯現出窒礙難行之處。民主黨因增加消費稅而產生分歧,其中一派作為「第三勢力」成立日本維新會,並活躍於日本政界,導致二○一二年的眾議院選舉以失敗收場。如此一來,兩大政黨中能與自民黨抗衡的一端遂逐漸衰弱。
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的當時,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明顯低落,權力也逐漸集中於首相。其中,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低落指的就是自民黨「一強」,首相集中權力則是安倍「一強」。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為長期穩定政權特例的原因,可以從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和其部分性的挫折,還有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中尋求。
然而,第二次安倍政權也有過瀕臨政黨輪替的危機。二○一七年,安倍首相爆出森友‧加計學園醜聞期間,在東京都議員選舉中贏得多數席次的「都民優先會」,憑藉著勝利的餘熱,試圖推派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參與國政。雖然安倍首相因考慮到「只能趁小池百合子還未準備好時出奇不意地突襲他們」而決定解散眾議院,但安倍回憶起解散國會的記者會和希望之黨組黨為同一天舉行時,不禁「打了個冷顫」。結果,首相的解散預測成功,繼承民主黨路線的民進黨分裂成希望之黨(國民民主黨的前身)和立憲民主黨;獲得眾議院大選勝利的自民黨,就此穩固「一強」的地位。
安倍「一強」也曾因醜聞產生動搖。透過政治改革而制度化的首相權力強化,本就沒有自動保障首相的領導力,反而隨著權力擴大,開始要求首相具備經營政權以及政策相關的高度能力。實際上,二○○一年實施橋本行政改革以後,成為長期穩定政權的,就只有小泉純一郎政權和第二次安倍政權。繼任第二次安倍政權的菅義偉政權,一年多就結束執政。儘管我們的檢證已十分留意制度性的前提,但還是會重視政權的治國才能(statecraft),就是基於這一層認識。
上半部─累積政治資本和安倍色彩的諸多政策
本書的檢證,是以主題類別逐一進行,首先在序論整理出有關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時間序列變化。歷經七年八個月的第二次安倍政權,可透過安倍任期內的兩屆眾議院選舉和三屆參議院選舉,大致上區分成六個時期。
第一期,從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開始,至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參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的特徵是,執政黨在未擁有參議院過半席次的「分立國會」之下,以經濟政策為核心,採取「堅持安全駕駛」的方式突破困境。將由金融寬鬆、擴大國家財政支出、刺激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所組成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推上檯面,並表態加入TPP談判。儘管有意修改憲法第九十六條的修憲程序規定,但是在受到輿論撻伐後,實際上撤回修憲案,並在下一屆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特徵是,推出具有安倍色彩的政策,同時兩度延後增加消費稅,並贏得國會大選。安倍在二○一五年九月八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上以無投票自動連任,顯示安倍政權在該時期的穩定性。於是,在長期政權的預測逐漸明朗化,以及在去年眾議院選舉中的勝利,確立了自民黨、安倍的雙重「一強」。
其中的第二期,到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眾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具有安倍色彩的政策是,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通過特定祕密保護法、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內閣會議通過有限度地行使集體自衛權等等。另外,替換黨內頭號政敵石破茂,自民黨幹事長改由自由主義派的谷垣禎一擔任,決定延後一年半實施消費稅八%增加至一○%後,表態解散眾議院,並贏得壓倒性的勝利。
第三期是,從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三次安倍內閣成立至二○一六年七月十日參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具有安倍色彩的代表政策是,通過新安保法,還有戰後七十年首相談話、TPP談判的初步協議、日韓「慰安婦」協議等一連串的政策。然後安倍表態再度延期提高消費稅,並贏得二○一六年參議院選舉的勝利。自民、公明、維新等「修憲勢力」,確保了在參眾兩院提出修憲案所必須的三分之二席次。
可以將上述的前三期稱作上半部,此時期安倍政權藉由以安倍經濟學為主軸的經濟政策,和增加消費稅的多次延期,來獲得更高的內閣支持率,並贏得國會大選。政權累積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後,再轉移實行具安倍色彩的政策。透過這種循環方式,達成很多政策。特別是曾引起大規模反對運動的二○一五年新安保法的制定,對第二次安倍政權而言,是最大的政治遺產。
在我們的訪談中,安倍被問及第二次政權最大的成果時,這麼說道:「果然如同我所想的就是新安保法。面對中國持續不斷的挑戰,日美同盟變得更加穩固。」
檢證對象──第二次安倍政權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安倍晉三首相突然表態辭去內閣總理大臣的職務,理由是宿疾的惡化。當天的記者會上,安倍被問到有關安倍政權的政績(政治遺產)時,回答舉出,安倍政權不僅僅是致力於東日本大地震災後的復興工作,更以擺脫通貨緊縮為目標的安倍經濟學來創造工作機會,將成長的果實轉化為擴充托育政策、兒童教育與托育的無償化、高等教育的無償化等等,著手於勞動方式改革和一億總活躍社會;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上,制定有限度行使集體自衛權為前提的和平安全法制(譯按:新安保法,又稱:安全保障關連法),在鞏固日美同盟的同時,致力於創造TPP等自由公平的區域經濟體。安倍也提及尚待解決的有,修改憲法、締結日俄和平條約、北韓綁架日本人等三個問題。
最後,安倍政權於九月十六日內閣總辭。安倍首相的任職天數,若從第一次內閣起算,長達三千一百八十八天;若從第二次內閣成立時算起,連續任職天數則達到二千八百二十二天。不論哪一種計算方式,都是日本憲政史上執政最長的首相。也可以說,作為特例的長期政權就此落幕。
安倍內閣不只是長期政權,也是特例的穩定政權,而其象徵性的語彙就是「一強」吧。「一強」在使用上具有雙重意涵,一方面,所謂自民黨「一強」,是指積弱不振的在野黨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明顯不高;另一方面,所謂安倍「一強」,是指政權內部的權力集中於首相、總裁。
本書從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開始,至二○二○年九月十六日第四次安倍內閣的總辭為止,對第二次安倍政權進行了檢證。這裡採用所謂的「第二次安倍政權」,將七年八個月看作一個整體,是為了與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內閣總辭的「第一次安倍政權」作出區別。以下,全部的職稱皆以當時為主,並省略所有敬稱。敬請見諒。
第二次安倍政權早已成為眾說紛紜的標的,因此,在檢證上會徹底重視實證的手法。並不是按照事先準備的理論和分析架構來論斷,而是再三對當事人進行訪談,然後與之互相比對文獻和相關資料,想要引導出歸納性的結論。我們的目標並不是要讚揚或批判第二次安倍政權,而是要透過檢證,探索實現更好的日本政治的線索。
應該要檢證的疑問
貫穿本書整體的疑問是,為什麼第二次安倍政權會在日本政界變成特例的長期穩定政權呢?
從現在來看,雖然或許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但絕非如此。在就職當天的記者會上,被問及第一次安倍政權之後,首相頻繁輪替的問題時,安倍回答:「身為執政一年不得不結束政權的負責人,我感到責任相當重大。同時,想活用執政過的經驗和經歷過挫折的經驗。」另外還補充道:「我認為現在,為了『畫上政治混亂和停滯的休止符』,推動穩定的政府運作,才是我們要追求的使命。」
二○○六年第一次安倍內閣成立,執政一年便內閣總辭,之後福田康夫內閣和麻生太郎內閣不到一年就結束執政。二○○九年從自民黨到民主黨,完成真正的政黨輪替,雖然成立了鳩山由紀夫內閣,但卻不滿一年,繼任的菅直人內閣和野田佳彥內閣也都只維持一年多的時間,就不得不結束執政。包含第一次安倍政權,歷經六任短命的政權之後登場的第二次安倍政權,依舊被認為無法長期執政。
另外,在野時期的自民黨開始右傾化。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黨大會通過新的黨綱,為了對抗奪走政權的民主黨,新黨綱內容傾向「很具日本特色的日本保守主義」,把「新憲法制定」放到具體方針的最前端(譯按:在該綱領的第二大項,指出本黨政策的基本構想如下所述,第一點顯示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樣態,以制定可以貢獻世界的新憲法為目標。)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布的「日本國憲法修正草案」提到,天皇元首化、保有國防軍、家人相互尊重和扶持之義務等條項,比起二○○五年的「新憲法草案」,明顯增添右傾的內容。於是,在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安倍以右派團體的「創生日本」作為基礎,出馬競選並成功當選。
在這個原委下成立的第二次安倍政權,被認為推動了包含修憲在內的右傾政策,不是嗎?再者,如同第一次安倍政權所公布的「擺脫戰後體制」,不會又因為相同的原因而變成短命政權吧?
然而,若回顧以往,也可以說現在與上述的猜想有著很大的差異。
就政府運作來看,包含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的二○一二年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在安倍總裁的帶領下,連續六次贏得國會大選,內閣支持率也跟著水漲船高。與被批評的第一次安倍政權的「首相官邸失能」不同,第二次安倍政權實現了強而有力且穩定的官邸主導,巧妙地掌握執政的自民與公明兩黨,以及各省廳的官僚。當然,對各省廳強而有力的領導手腕,也產生了所謂官僚的「消極態度」和「揣摩上意」等歪風,因而招來批判,特別是森友學園問題發生了所謂竄改公文書等嚴重事件,一定會被記錄下來。
關於政策方面,安倍首相在第一次政權以來,對於參拜靖國神社的夙願,只進行過一次,就將代表安倍經濟學的經濟政策端上檯面。雖然推動將日美同盟作為主軸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但承認行使集體自衛權並非全面開綠燈、暢行無阻,而是內容仍有所限制,為了合乎日本國憲法的規定,制定利用內閣會議決定動用武力的「新三要件」。即使戰後七十年的首相談話等歷史問題有所收斂,也沒有走到持續以修憲為目標的這一步,甚至致力於接收在野黨主張的女性、兒童政策,以及勞動政策等內容。
本書就為何能夠維持長期穩定政權的提問,從安倍經濟學、選舉‧輿論對策、官邸主導、外交‧安全保障、TPP‧通商、歷史問題、執政黨的統治體系、女性政策、憲法修正等九個面向進行檢證。
歷史背景─政治改革和民主黨政權的失敗
第二次安倍政權之所以成為日本政治史上少有的長期穩定政權,歷史背景就是一九九四年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被稱為五五年體制的自民黨近三十八年長期執政期間,派系和族議員利用分權的自民黨組織,產生出政、官、財三方的緊密關係,也發生欠缺領導中心和結構性貪汙等問題;應該要解決上述問題,以英國型的政治體制,也就是將可能政黨輪替的兩大政黨制,和以此為前提的首相權力集中作為目標,就可以持續不斷地進行改革。
在一九九四年的政治改革中,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被導入眾議院選舉,取代以往的中選舉區制,另一方面強化對企業、利益團體政治獻金的規範,並導入政黨補助金制度。此外,透過橋本政權的行政改革,強化省廳重組和內閣功能的計畫,並於二○○一年實施。其中,在小選舉區制的背景之下,一九九八年成立的民主黨雖幾經波折,仍持續成長,並在二○○九年的眾議院大選上大勝自民黨,真正達成了政黨輪替,這可以看作是一連串政治改革的成果。
與政治改革並列的另一歷史背景,是民主黨政權的失敗;詳見亞太倡議智庫的前身──重建日本倡議基金會所著《檢證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一書。民主黨政權無法履行政見,於二○一○年參議院選舉失敗而陷入「分立國會」的窘境,短時間之內就顯現出窒礙難行之處。民主黨因增加消費稅而產生分歧,其中一派作為「第三勢力」成立日本維新會,並活躍於日本政界,導致二○一二年的眾議院選舉以失敗收場。如此一來,兩大政黨中能與自民黨抗衡的一端遂逐漸衰弱。
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的當時,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明顯低落,權力也逐漸集中於首相。其中,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低落指的就是自民黨「一強」,首相集中權力則是安倍「一強」。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為長期穩定政權特例的原因,可以從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和其部分性的挫折,還有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中尋求。
然而,第二次安倍政權也有過瀕臨政黨輪替的危機。二○一七年,安倍首相爆出森友‧加計學園醜聞期間,在東京都議員選舉中贏得多數席次的「都民優先會」,憑藉著勝利的餘熱,試圖推派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參與國政。雖然安倍首相因考慮到「只能趁小池百合子還未準備好時出奇不意地突襲他們」而決定解散眾議院,但安倍回憶起解散國會的記者會和希望之黨組黨為同一天舉行時,不禁「打了個冷顫」。結果,首相的解散預測成功,繼承民主黨路線的民進黨分裂成希望之黨(國民民主黨的前身)和立憲民主黨;獲得眾議院大選勝利的自民黨,就此穩固「一強」的地位。
安倍「一強」也曾因醜聞產生動搖。透過政治改革而制度化的首相權力強化,本就沒有自動保障首相的領導力,反而隨著權力擴大,開始要求首相具備經營政權以及政策相關的高度能力。實際上,二○○一年實施橋本行政改革以後,成為長期穩定政權的,就只有小泉純一郎政權和第二次安倍政權。繼任第二次安倍政權的菅義偉政權,一年多就結束執政。儘管我們的檢證已十分留意制度性的前提,但還是會重視政權的治國才能(statecraft),就是基於這一層認識。
上半部─累積政治資本和安倍色彩的諸多政策
本書的檢證,是以主題類別逐一進行,首先在序論整理出有關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時間序列變化。歷經七年八個月的第二次安倍政權,可透過安倍任期內的兩屆眾議院選舉和三屆參議院選舉,大致上區分成六個時期。
第一期,從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開始,至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參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的特徵是,執政黨在未擁有參議院過半席次的「分立國會」之下,以經濟政策為核心,採取「堅持安全駕駛」的方式突破困境。將由金融寬鬆、擴大國家財政支出、刺激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所組成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推上檯面,並表態加入TPP談判。儘管有意修改憲法第九十六條的修憲程序規定,但是在受到輿論撻伐後,實際上撤回修憲案,並在下一屆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特徵是,推出具有安倍色彩的政策,同時兩度延後增加消費稅,並贏得國會大選。安倍在二○一五年九月八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上以無投票自動連任,顯示安倍政權在該時期的穩定性。於是,在長期政權的預測逐漸明朗化,以及在去年眾議院選舉中的勝利,確立了自民黨、安倍的雙重「一強」。
其中的第二期,到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眾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具有安倍色彩的政策是,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通過特定祕密保護法、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內閣會議通過有限度地行使集體自衛權等等。另外,替換黨內頭號政敵石破茂,自民黨幹事長改由自由主義派的谷垣禎一擔任,決定延後一年半實施消費稅八%增加至一○%後,表態解散眾議院,並贏得壓倒性的勝利。
第三期是,從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三次安倍內閣成立至二○一六年七月十日參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具有安倍色彩的代表政策是,通過新安保法,還有戰後七十年首相談話、TPP談判的初步協議、日韓「慰安婦」協議等一連串的政策。然後安倍表態再度延期提高消費稅,並贏得二○一六年參議院選舉的勝利。自民、公明、維新等「修憲勢力」,確保了在參眾兩院提出修憲案所必須的三分之二席次。
可以將上述的前三期稱作上半部,此時期安倍政權藉由以安倍經濟學為主軸的經濟政策,和增加消費稅的多次延期,來獲得更高的內閣支持率,並贏得國會大選。政權累積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後,再轉移實行具安倍色彩的政策。透過這種循環方式,達成很多政策。特別是曾引起大規模反對運動的二○一五年新安保法的制定,對第二次安倍政權而言,是最大的政治遺產。
在我們的訪談中,安倍被問及第二次政權最大的成果時,這麼說道:「果然如同我所想的就是新安保法。面對中國持續不斷的挑戰,日美同盟變得更加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