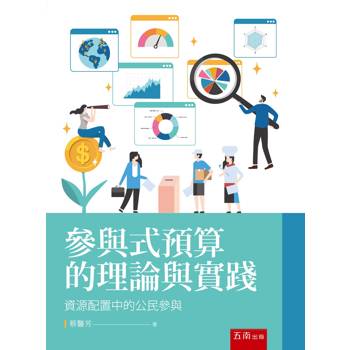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參與式預算的意義、內涵及特徵
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是一種讓市民直接參與政府預算過程的民主創新機制,透過公民審議決定公共預算的配置和使用,促進財政透明度、公共課責及公民參與,有助於改善公共服務的效能及提升公平正義。學者Shah(2007)定義參與式預算為一個「賦予市民直接參與決策權的過程,這些決策會影響地方政府的預算分配」;Wampler(2010a)認為參與式預算是一種「讓普通市民參與政府預算編製和優先事項決定的機制,這樣的參與能夠促進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及公民責任」。學者Fung(2006)將參與式預算描述為是「一種特定的公共參與模式,公眾能夠在這一過程中影響公共資金的分配決策,從而促進更公平及有效的公共服務」。Sintomer等人(2008)則將參與式預算定義為「是一種在地方政府層面導入的創新性公共政策工具,旨在透過市民的直接參與來決定財政預算的優先事項和分配」,並提出符合參與式預算的五項判準條件:
一、必須討論有關公共事務的財務或預算面向。
二、執行單位為自治層級,即經由民主方式產生首長的地區。
三、必須是一項具有重覆性的過程,而非一次性的會議或論壇。
四、過程必須具備某種公共審議的形式。
五、要求對於決議的結果進行某種程度的課責。
參與式預算是「公共參與」和「政府預算」的結合,此兩項核心要素的結合,讓參與式預算比傳統的公民參與管道(如:專家諮詢、請願連署、公聽會、世界咖啡館、公民會議、民意調查等)更有力量、更受歡迎。因為它不只強調公共參與,讓受到政府決策影響的民眾,能對公共事務更關注及理解,可以對有興趣的公共議題直接表達意見及建議,以提升公共政策品質;同時更能以政府預算作為公共參與的後盾,將民眾的提案納入政府預算中付諸執行,真正成為推動社區改變的平台,發揮對於政策的實質影響力,這就是參與式預算的特色及魅力(蘇彩足,2022:34-35)。
政府預算可分為籌編、審議、執行及審計等階段,在不同的預算階段中,皆有導入公民參與的潛力(Moynihan & Pandey, 2007)。首先,在預算籌編階段,政府機關依據施政方針及預算政策,編製年度單位預算,在此階段導入公民參與較有機會影響公共資源之配置,目前全球各城市推動之參與式預算模式,多數是在籌編階段導入公民參與。巴西在1996年時,估計有超過10萬名公民(約占全國人口的8%)曾參與預算的編製過程。公民參與資源分配,也有發揮解除財政危機的例子,1999年美國華盛頓特區州長在策略規劃及預算過程中,組織召集一系列「公民高峰會(citizen summits),蒐集有助於各種預算表單設計及資源配置之公民意見,協助政府度過地方財政黑暗期(蘇彩足等人,2015)。
其次,一般民主國家政府預算的最後決策是在審議階段完成,由於政府預算涉及巨大資源及利益的分配,各方勢力及利益的衝突在預算審議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此階段可說是政治決策的中心,也是預算合法化的重要階段。「看緊人民荷包」是民意機關在預算審議階段的主要任務,此階段導入公民參與,可強化預算的公開透明及公民教育。南非的非營利組織「南非民主機構」(Institute for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IDASA),致力於預算分析,提供有關政府資源配置之分析資料,聘請研究婦幼議題之專家進行預算訓練,強化其倡議及監督政府預算的效果,也經常透過媒體及網際網路,公布其理念及分析結果,擴大公眾對預算資訊取得的深度及廣度,是公民在審議階段發揮協助監督政府預算的例子(蘇彩足等人,2015; Moynihan & Pandey, 2007)。
第一節 參與式預算的意義、內涵及特徵
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是一種讓市民直接參與政府預算過程的民主創新機制,透過公民審議決定公共預算的配置和使用,促進財政透明度、公共課責及公民參與,有助於改善公共服務的效能及提升公平正義。學者Shah(2007)定義參與式預算為一個「賦予市民直接參與決策權的過程,這些決策會影響地方政府的預算分配」;Wampler(2010a)認為參與式預算是一種「讓普通市民參與政府預算編製和優先事項決定的機制,這樣的參與能夠促進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及公民責任」。學者Fung(2006)將參與式預算描述為是「一種特定的公共參與模式,公眾能夠在這一過程中影響公共資金的分配決策,從而促進更公平及有效的公共服務」。Sintomer等人(2008)則將參與式預算定義為「是一種在地方政府層面導入的創新性公共政策工具,旨在透過市民的直接參與來決定財政預算的優先事項和分配」,並提出符合參與式預算的五項判準條件:
一、必須討論有關公共事務的財務或預算面向。
二、執行單位為自治層級,即經由民主方式產生首長的地區。
三、必須是一項具有重覆性的過程,而非一次性的會議或論壇。
四、過程必須具備某種公共審議的形式。
五、要求對於決議的結果進行某種程度的課責。
參與式預算是「公共參與」和「政府預算」的結合,此兩項核心要素的結合,讓參與式預算比傳統的公民參與管道(如:專家諮詢、請願連署、公聽會、世界咖啡館、公民會議、民意調查等)更有力量、更受歡迎。因為它不只強調公共參與,讓受到政府決策影響的民眾,能對公共事務更關注及理解,可以對有興趣的公共議題直接表達意見及建議,以提升公共政策品質;同時更能以政府預算作為公共參與的後盾,將民眾的提案納入政府預算中付諸執行,真正成為推動社區改變的平台,發揮對於政策的實質影響力,這就是參與式預算的特色及魅力(蘇彩足,2022:34-35)。
政府預算可分為籌編、審議、執行及審計等階段,在不同的預算階段中,皆有導入公民參與的潛力(Moynihan & Pandey, 2007)。首先,在預算籌編階段,政府機關依據施政方針及預算政策,編製年度單位預算,在此階段導入公民參與較有機會影響公共資源之配置,目前全球各城市推動之參與式預算模式,多數是在籌編階段導入公民參與。巴西在1996年時,估計有超過10萬名公民(約占全國人口的8%)曾參與預算的編製過程。公民參與資源分配,也有發揮解除財政危機的例子,1999年美國華盛頓特區州長在策略規劃及預算過程中,組織召集一系列「公民高峰會(citizen summits),蒐集有助於各種預算表單設計及資源配置之公民意見,協助政府度過地方財政黑暗期(蘇彩足等人,2015)。
其次,一般民主國家政府預算的最後決策是在審議階段完成,由於政府預算涉及巨大資源及利益的分配,各方勢力及利益的衝突在預算審議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此階段可說是政治決策的中心,也是預算合法化的重要階段。「看緊人民荷包」是民意機關在預算審議階段的主要任務,此階段導入公民參與,可強化預算的公開透明及公民教育。南非的非營利組織「南非民主機構」(Institute for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IDASA),致力於預算分析,提供有關政府資源配置之分析資料,聘請研究婦幼議題之專家進行預算訓練,強化其倡議及監督政府預算的效果,也經常透過媒體及網際網路,公布其理念及分析結果,擴大公眾對預算資訊取得的深度及廣度,是公民在審議階段發揮協助監督政府預算的例子(蘇彩足等人,2015; Moynihan & Pandey,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