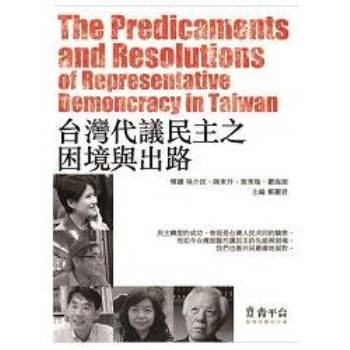1-1 看見台灣的「市民憲政主義」:2014 年太陽花學運的啟示
◎葉俊榮 國立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前言
2014 年台灣與香港兩個華人社會分別於年初和年末爆發群眾運動,監督國會與爭取真普選,皆為全球憲政發展的焦點。本文分別觀察太陽花學運與 1980 年代民主轉型後的台灣憲政發展,主張太陽花學運充分展現濃厚「市民憲政主義」(civic constitutionalism),尤更甚者,台灣自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後,不僅沒有發展出國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傳統,不以民主代議制度的充分落實為終點,反而奠基市民憲政主義的傳統。因此,市民社會不因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接選舉而退居後線,反而隨時監督政府與制衡國會,與逐漸獲得信念的法院以及成形的民主代議制度,共同形塑憲法秩序,共同促進憲法的變遷。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 憲法變遷採取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七次修憲看似雜亂隨機,卻皆以「代表性強化」(representation-reinforcing)為依歸,解決「大中國」的憲法套用在台灣所造成的代表性扭曲問題,邁向正常的代議民主政治。然而,這個憲改的過程並不以單純的代議民主為終極目標,台灣市民社會展現不以國會至上為主的精神,民主憲改活絡了市民社會間以及市民社會與政治權力者間的對話,促進對於政府的監督批判。換言之,在台灣,民主改革及修憲,與市民社會的量能強化之間,自始即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代議民主制度的建立並非終點,市民社會並不因此歸於沈寂。而太陽花學運,放在這個脈絡下,不僅消除了民主困境的疑慮,更可被視為積極深化台灣民主憲政的一大契機。
本文以下依序點出市民憲政主義的核心內涵,再描繪太陽花學運的市民憲政主義圖像,進而從市民憲政主義觀察台灣1980 年代民主轉型後的憲政發展,最後則提出台灣市民憲政主義的啟示。何謂「市民憲政主義」?
一、探尋市民在民主轉型下的憲政角色
民主轉型的國家(如東歐、南非或台灣韓國等東亞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均朝向民主憲政的制度設計,使政府各權在制度上得以回應憲法要求。在立法方面,建立定期改選制度、推及全民普選等機制,形塑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憲政體制。在司法方面,法院(特別是憲法法院),承擔保障人權與維護憲政秩序的憲法責任。新興民主國家政府藉由憲政改革,邁向自由主義憲政秩序。但不論是轉型過程或轉型之後,民主代議體制逐漸建立,市民的角色反而顯得尷尬。市民應退居二線,由具有代表性的政府代勞?抑或是應該積極參與憲政秩序形塑?這是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課題。
面對這個選擇,部分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呈現出市民沈寂的現象。在蘇聯解體後,東歐政權面臨民主轉型。當時,許多來自歐美的學者紛紛關心中東歐的新憲運動。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部分來自美國的學者(Cass R. Sunstein)提出警告,認為民主轉型啟動制定新憲法的過程中,對憲法上人民權利的保障要很小心,不應過度擴張權利(尤其是社會權)進入憲法。他認為,一旦憲法對人民權利保障無微不至,將會使獨佔憲法解釋權的法院(尤其是憲法法院)掌握實踐人民權利的唯一機會,人民透過法院的判決獲取權利,好像「權利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變成過度在意法院是否承認權利以及保障權利,終將導致人民喪失透過運動與動員爭取權利的動能。經過了二十幾年來的實踐,學者 Paul Blokker 指出中東歐正面臨新興民主國家的危機。他認為東歐新興民主國家過分強調憲法文本以及形式法治與法院解釋,忽視市民動能與憲政參與,致使市民沒有形塑憲政的動力,甚至對司法產生敵意(legal resentment)。Blokker 以憲法法院為例,認為憲法專家獨佔憲法解釋權,不鼓勵廣大市民社會討論憲法議題,形成強調形式專業的一面倒「司法霸權」(juristocracy)。因此,氏建議這些國家制度上應設計管道,增加公民憲政參與機會,促進社會、政治與司法部門三方的溝通互動。相反的,美國學者 Elizabeth Beaumont 最近提出,憲法秩序的形塑並不單純根據開國制憲先賢、知名政治人物、知識分子、法院等的意向發展,廣大的市民社會更是形塑憲法秩序的重要推手。一般憲政制度歷史的討論,大多聚焦於前述人士的論述,但氏認為,此舉埋沒一般市民對於憲法秩序的想像,忽略人民在憲政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氏分析美國憲政歷史的重大事件─起草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廢除奴隸制度、爭取婦女選舉權、制定 1960 年代民權法律─並爬梳其中一般民眾的憲法觀,發現參與的民眾皆思索相關權利的內涵,透過報章雜誌等管道發表意見,激發有關人士政治參與的意願與動力。雖然一般民眾的用字遣詞並不如專業憲法學者,但是其討論者即是憲法。一般人民的觀點真正影響,進而形塑當今美國的憲政秩序。
二、市民的憲政參與
市民憲政參與─亦即,市民在制定、解釋憲法與憲法對話互動中的積極角色─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容有不同的理解與用語。例如,Bruce Ackerman 所提出的「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點出公民對憲政秩序與政府體制的高度動員,尤其是透過總統或國會選舉表達集體的意志,支持改革意見,這對於形塑憲政典範具有規範上的重要性。在另外一方面,普羅憲政主義(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的論點,則針對(憲法)法院的憲政霸權提出反思,提倡人民在法院形成憲法解釋的過程中,仍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院在行使最後且絕對的憲法解釋權時,能謙虛地瞭解人民的主張與想法。另外,如上所述,Beaumont 提出的市民參與憲政秩序型塑,則更為深入且全面,讓市民在憲政的建立與轉型的重要關鍵時期,都能進行憲政議題的思辨與對話,進而形塑憲政秩序。
中東歐國家及新興民主國家的危機論,點出市民在憲政秩序形塑中缺席的可能原因:司法與國會至上的觀點。司法至上強調以法院為中心的憲法論述,認為法官獨佔憲法最終解釋權,市民的觀點在其中無足輕重。國會至上認為,代議民主制度下,市民憲政參與內涵被化約為國會選舉,其後則交由國會議員遵循、建立憲政體制。不同於總統制底下,直接民選總統與國會共同承擔憲法義務,以西敏寺傳統(Westminster tradition)為典型的體制,更可以反映出國會至上觀念中,國會議員與市民的緊張關係。
◎葉俊榮 國立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前言
2014 年台灣與香港兩個華人社會分別於年初和年末爆發群眾運動,監督國會與爭取真普選,皆為全球憲政發展的焦點。本文分別觀察太陽花學運與 1980 年代民主轉型後的台灣憲政發展,主張太陽花學運充分展現濃厚「市民憲政主義」(civic constitutionalism),尤更甚者,台灣自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後,不僅沒有發展出國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傳統,不以民主代議制度的充分落實為終點,反而奠基市民憲政主義的傳統。因此,市民社會不因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接選舉而退居後線,反而隨時監督政府與制衡國會,與逐漸獲得信念的法院以及成形的民主代議制度,共同形塑憲法秩序,共同促進憲法的變遷。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 憲法變遷採取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七次修憲看似雜亂隨機,卻皆以「代表性強化」(representation-reinforcing)為依歸,解決「大中國」的憲法套用在台灣所造成的代表性扭曲問題,邁向正常的代議民主政治。然而,這個憲改的過程並不以單純的代議民主為終極目標,台灣市民社會展現不以國會至上為主的精神,民主憲改活絡了市民社會間以及市民社會與政治權力者間的對話,促進對於政府的監督批判。換言之,在台灣,民主改革及修憲,與市民社會的量能強化之間,自始即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代議民主制度的建立並非終點,市民社會並不因此歸於沈寂。而太陽花學運,放在這個脈絡下,不僅消除了民主困境的疑慮,更可被視為積極深化台灣民主憲政的一大契機。
本文以下依序點出市民憲政主義的核心內涵,再描繪太陽花學運的市民憲政主義圖像,進而從市民憲政主義觀察台灣1980 年代民主轉型後的憲政發展,最後則提出台灣市民憲政主義的啟示。何謂「市民憲政主義」?
一、探尋市民在民主轉型下的憲政角色
民主轉型的國家(如東歐、南非或台灣韓國等東亞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均朝向民主憲政的制度設計,使政府各權在制度上得以回應憲法要求。在立法方面,建立定期改選制度、推及全民普選等機制,形塑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憲政體制。在司法方面,法院(特別是憲法法院),承擔保障人權與維護憲政秩序的憲法責任。新興民主國家政府藉由憲政改革,邁向自由主義憲政秩序。但不論是轉型過程或轉型之後,民主代議體制逐漸建立,市民的角色反而顯得尷尬。市民應退居二線,由具有代表性的政府代勞?抑或是應該積極參與憲政秩序形塑?這是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課題。
面對這個選擇,部分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呈現出市民沈寂的現象。在蘇聯解體後,東歐政權面臨民主轉型。當時,許多來自歐美的學者紛紛關心中東歐的新憲運動。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部分來自美國的學者(Cass R. Sunstein)提出警告,認為民主轉型啟動制定新憲法的過程中,對憲法上人民權利的保障要很小心,不應過度擴張權利(尤其是社會權)進入憲法。他認為,一旦憲法對人民權利保障無微不至,將會使獨佔憲法解釋權的法院(尤其是憲法法院)掌握實踐人民權利的唯一機會,人民透過法院的判決獲取權利,好像「權利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變成過度在意法院是否承認權利以及保障權利,終將導致人民喪失透過運動與動員爭取權利的動能。經過了二十幾年來的實踐,學者 Paul Blokker 指出中東歐正面臨新興民主國家的危機。他認為東歐新興民主國家過分強調憲法文本以及形式法治與法院解釋,忽視市民動能與憲政參與,致使市民沒有形塑憲政的動力,甚至對司法產生敵意(legal resentment)。Blokker 以憲法法院為例,認為憲法專家獨佔憲法解釋權,不鼓勵廣大市民社會討論憲法議題,形成強調形式專業的一面倒「司法霸權」(juristocracy)。因此,氏建議這些國家制度上應設計管道,增加公民憲政參與機會,促進社會、政治與司法部門三方的溝通互動。相反的,美國學者 Elizabeth Beaumont 最近提出,憲法秩序的形塑並不單純根據開國制憲先賢、知名政治人物、知識分子、法院等的意向發展,廣大的市民社會更是形塑憲法秩序的重要推手。一般憲政制度歷史的討論,大多聚焦於前述人士的論述,但氏認為,此舉埋沒一般市民對於憲法秩序的想像,忽略人民在憲政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氏分析美國憲政歷史的重大事件─起草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廢除奴隸制度、爭取婦女選舉權、制定 1960 年代民權法律─並爬梳其中一般民眾的憲法觀,發現參與的民眾皆思索相關權利的內涵,透過報章雜誌等管道發表意見,激發有關人士政治參與的意願與動力。雖然一般民眾的用字遣詞並不如專業憲法學者,但是其討論者即是憲法。一般人民的觀點真正影響,進而形塑當今美國的憲政秩序。
二、市民的憲政參與
市民憲政參與─亦即,市民在制定、解釋憲法與憲法對話互動中的積極角色─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容有不同的理解與用語。例如,Bruce Ackerman 所提出的「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點出公民對憲政秩序與政府體制的高度動員,尤其是透過總統或國會選舉表達集體的意志,支持改革意見,這對於形塑憲政典範具有規範上的重要性。在另外一方面,普羅憲政主義(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的論點,則針對(憲法)法院的憲政霸權提出反思,提倡人民在法院形成憲法解釋的過程中,仍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院在行使最後且絕對的憲法解釋權時,能謙虛地瞭解人民的主張與想法。另外,如上所述,Beaumont 提出的市民參與憲政秩序型塑,則更為深入且全面,讓市民在憲政的建立與轉型的重要關鍵時期,都能進行憲政議題的思辨與對話,進而形塑憲政秩序。
中東歐國家及新興民主國家的危機論,點出市民在憲政秩序形塑中缺席的可能原因:司法與國會至上的觀點。司法至上強調以法院為中心的憲法論述,認為法官獨佔憲法最終解釋權,市民的觀點在其中無足輕重。國會至上認為,代議民主制度下,市民憲政參與內涵被化約為國會選舉,其後則交由國會議員遵循、建立憲政體制。不同於總統制底下,直接民選總統與國會共同承擔憲法義務,以西敏寺傳統(Westminster tradition)為典型的體制,更可以反映出國會至上觀念中,國會議員與市民的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