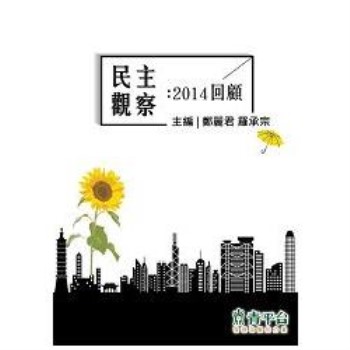行政民主 ◎李彥賦
前言
政府施政究竟該怎麼與民意連結?根據趨勢民調以及台灣智庫的相關調查,馬政府 2014 年的施政滿意度只從前一年度 9 月政爭後的最低點提升了 1.9 個百分點,約為 17.4%左右,不滿意度則高達 72%;在其上任 6 周年前夕所做的調查,不論是清廉度、誠實度、民意度、信任度、經濟力、改革力、說服力、維護國家力等指標,無一及格。我們不禁要問,行政與民意之間的關聯性,難道僅繫於一次總統大選的投票行為?不論人民如何反彈,難道只要選上就能壟斷國家重大政策的決策權而不需再受民意監督?
在民主國家中,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藉由持續不間斷的民主正當性鎖鏈連結到國民全體之上,這也是憲法第 2 條「國民主權」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說,在民主原則的要求下,所有國家的行為都必須回溯到人民的自主決定。這樣的回溯觀點,在權力分立架構下,司法權是透過依法獨立審判與民主正當性連結;立法權則是由國民以直接選舉的方式產生代議士,透過代議士制定法律、做出政治決策,並且能在事後對於背離民意的立法委員行使罷免權。
不過在行政權的領域,民主正當性的鎖鏈則須透過較多層次的連結,畢竟大部分的行政行為與決定都會影響甚至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例如闖紅燈罰單、課稅處分、大巨蛋停工等這些直接涉及處分相對人權益的侵益處分,即便是在公費獎學金這種授予利益的經濟補助措施當中,也會有競爭者權益受侵害問題。換句話說, 「行政」與「民主」之間表面上存在著緊張關係,而這種「自己決定授權行政機關侵害自己」的外觀上矛盾,便必須透過「組織人事」與「事物內容」的民主正當性鎖鏈進一步調和。
在組織與人事的民主正當性要求下,行使國家公權力之公務員,其身分地位的取得必須能夠回溯到國民的意志之上,據以證明執行國家任務及權限之人乃經人民授權而產生。而我國在歷次修憲之後,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行政院長,其身分取得即是透過由人民直選的總統任命,藉以回溯到國民意志本身。而在「事物內容」的層次中,行政機關所為的任何決策及行為,都必須受到國會所通過的法律所制約,也就是透過「依法行政」以作為民主正當性的連結樞紐;此外,當行政逸脫民主的控制時,即得以藉由司法究責、國會的文件調閱權及我國特有監察院的調查權等事後監督機制以追究責任。不過,當執政者主導法律詮釋的話語權,同時掌握議會多數,阻斷可能的事後監督機制,形式上所牽起的鎖鏈可能只剩下民主的外觀,實質正當性的內涵則可能極為脆弱,不堪面對人民經常性的檢驗。本章將以 2014 年所發生的時事及其後續發展為基礎,探究與民意脫節的政府施政所可能引發的民主危機。
「Z>B」的兩岸政策?
2014 年最熱門的邏輯算式非「Z>B」莫屬,就連知名英語連鎖補教業都在媒體購入廣告「『Z>B』的英文怎麼說」來吸引消費者點閱,此一公式肇因於馬政府欲與中國簽訂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來,對於可能危及台灣產業的協議內容以及協商過程,馬政府的操作方式是完全秘而不宣的黑箱作業,不斷重複「政府所採的基本原則,就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兩岸所簽署的協議,對台灣來講,全部都是『利大於弊』」等跳針式回應,迴避向人民說明利弊具體內容,網友取「利大於弊」其諧音為「Z>B」,這也是後來引發「318 學運」的關鍵因素。
其實早在學運發生前,國民黨立委對於服貿協議的公聽會操作過程便已惹起民怨。早在 2013 年 7 月立院加開臨時會時,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賴中強律師便於國民黨立委江啟臣所召開的第 1 場公聽會中指出,在8 分鐘的公聽會發言時間內根本無法把服貿協議內所開放的產業清單念完,怎麼可能在 20 場公聽會中匯集所有利害關係團體的意見?更有甚者,在國民黨立委張慶忠擔任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委期間,更在 3 天內密集排定 8 場公聽會,一天便有 3 場之多,而每場 4 小時、每人不到 10 分鐘的意見表述根本無法廣泛、審慎探求民意趨向,更遑論行政機關有做成影響評估的能力及可能性。
更令民眾擔心的是,政府對於對方「讓利」所採取的判斷基準究竟何在?「讓利」的後果是什麼?這些問題在民眾認知到馬英九總統欠缺一般生活經驗及基本常識-例如將「鹿茸」認定為「鹿耳朵裡面的毛」-以及九月政爭時對於法治的基本認知─認為檢察總長可以恣意非法監聽並在案件未偵結前向總統及行政院長洩密, 並且能以政黨黨主席的身分,就一件未經確定判決即自行認定為「司法關說」弊案要求立法院院長下台─之後愈發重要,特別是在馬政府不斷混淆兩岸協議的位階, 將其指鹿為馬片面解釋為「行政命令」藉以規避國會審查時,便更加深民眾的疑慮。
前言
政府施政究竟該怎麼與民意連結?根據趨勢民調以及台灣智庫的相關調查,馬政府 2014 年的施政滿意度只從前一年度 9 月政爭後的最低點提升了 1.9 個百分點,約為 17.4%左右,不滿意度則高達 72%;在其上任 6 周年前夕所做的調查,不論是清廉度、誠實度、民意度、信任度、經濟力、改革力、說服力、維護國家力等指標,無一及格。我們不禁要問,行政與民意之間的關聯性,難道僅繫於一次總統大選的投票行為?不論人民如何反彈,難道只要選上就能壟斷國家重大政策的決策權而不需再受民意監督?
在民主國家中,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藉由持續不間斷的民主正當性鎖鏈連結到國民全體之上,這也是憲法第 2 條「國民主權」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說,在民主原則的要求下,所有國家的行為都必須回溯到人民的自主決定。這樣的回溯觀點,在權力分立架構下,司法權是透過依法獨立審判與民主正當性連結;立法權則是由國民以直接選舉的方式產生代議士,透過代議士制定法律、做出政治決策,並且能在事後對於背離民意的立法委員行使罷免權。
不過在行政權的領域,民主正當性的鎖鏈則須透過較多層次的連結,畢竟大部分的行政行為與決定都會影響甚至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例如闖紅燈罰單、課稅處分、大巨蛋停工等這些直接涉及處分相對人權益的侵益處分,即便是在公費獎學金這種授予利益的經濟補助措施當中,也會有競爭者權益受侵害問題。換句話說, 「行政」與「民主」之間表面上存在著緊張關係,而這種「自己決定授權行政機關侵害自己」的外觀上矛盾,便必須透過「組織人事」與「事物內容」的民主正當性鎖鏈進一步調和。
在組織與人事的民主正當性要求下,行使國家公權力之公務員,其身分地位的取得必須能夠回溯到國民的意志之上,據以證明執行國家任務及權限之人乃經人民授權而產生。而我國在歷次修憲之後,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行政院長,其身分取得即是透過由人民直選的總統任命,藉以回溯到國民意志本身。而在「事物內容」的層次中,行政機關所為的任何決策及行為,都必須受到國會所通過的法律所制約,也就是透過「依法行政」以作為民主正當性的連結樞紐;此外,當行政逸脫民主的控制時,即得以藉由司法究責、國會的文件調閱權及我國特有監察院的調查權等事後監督機制以追究責任。不過,當執政者主導法律詮釋的話語權,同時掌握議會多數,阻斷可能的事後監督機制,形式上所牽起的鎖鏈可能只剩下民主的外觀,實質正當性的內涵則可能極為脆弱,不堪面對人民經常性的檢驗。本章將以 2014 年所發生的時事及其後續發展為基礎,探究與民意脫節的政府施政所可能引發的民主危機。
「Z>B」的兩岸政策?
2014 年最熱門的邏輯算式非「Z>B」莫屬,就連知名英語連鎖補教業都在媒體購入廣告「『Z>B』的英文怎麼說」來吸引消費者點閱,此一公式肇因於馬政府欲與中國簽訂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來,對於可能危及台灣產業的協議內容以及協商過程,馬政府的操作方式是完全秘而不宣的黑箱作業,不斷重複「政府所採的基本原則,就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兩岸所簽署的協議,對台灣來講,全部都是『利大於弊』」等跳針式回應,迴避向人民說明利弊具體內容,網友取「利大於弊」其諧音為「Z>B」,這也是後來引發「318 學運」的關鍵因素。
其實早在學運發生前,國民黨立委對於服貿協議的公聽會操作過程便已惹起民怨。早在 2013 年 7 月立院加開臨時會時,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召集人賴中強律師便於國民黨立委江啟臣所召開的第 1 場公聽會中指出,在8 分鐘的公聽會發言時間內根本無法把服貿協議內所開放的產業清單念完,怎麼可能在 20 場公聽會中匯集所有利害關係團體的意見?更有甚者,在國民黨立委張慶忠擔任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委期間,更在 3 天內密集排定 8 場公聽會,一天便有 3 場之多,而每場 4 小時、每人不到 10 分鐘的意見表述根本無法廣泛、審慎探求民意趨向,更遑論行政機關有做成影響評估的能力及可能性。
更令民眾擔心的是,政府對於對方「讓利」所採取的判斷基準究竟何在?「讓利」的後果是什麼?這些問題在民眾認知到馬英九總統欠缺一般生活經驗及基本常識-例如將「鹿茸」認定為「鹿耳朵裡面的毛」-以及九月政爭時對於法治的基本認知─認為檢察總長可以恣意非法監聽並在案件未偵結前向總統及行政院長洩密, 並且能以政黨黨主席的身分,就一件未經確定判決即自行認定為「司法關說」弊案要求立法院院長下台─之後愈發重要,特別是在馬政府不斷混淆兩岸協議的位階, 將其指鹿為馬片面解釋為「行政命令」藉以規避國會審查時,便更加深民眾的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