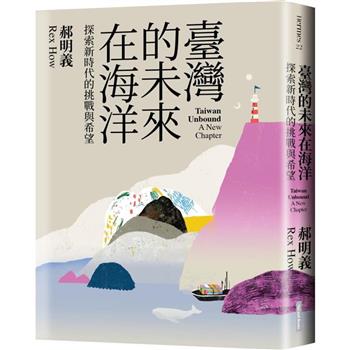第一部 迷霧
一、民進黨的情況
當人均GDP超韓趕日本時
今年二月臺北國際書展期間,有一天和韓國朋友聚餐。他感嘆韓國的經濟表現不佳,恭喜臺灣的人均GDP超越了韓國。
我說是啊,甚至我們還超越了日本呢。
這一下不只韓國人,連同桌的其他臺灣人也大呼驚奇。這麼大的新聞,他們都沒注意到。
最先見諸新聞報導的,是去年十月蔡英文總統表示,根據IMF的數據,臺灣的人均GDP將首次超越日本及韓國,成為東亞第一。到十二月中,日本經濟新聞,也報導臺灣將超越日本。
儘管其後實際的統計顯示,臺灣的人均GDP是三二、五八六美元,比日本的三三、七三一美元差了大約一千美元,但已經是有史以來最小的差距。並且,從二〇〇三年臺灣被韓國超越之後,的確二十年後來首次逆轉,多過韓國的三二、四一〇美元。
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成績。
以日本在經濟、生活上諸多層面對臺灣都有標竿性意義,臺灣對韓國又有諸多緊盯的競爭指標來說,發生了這麼大事,即使不舉國歡騰,大家也該很興奮。
然而為什麼許多人都沒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也覺得很不真實,很無感?
今年六月,《報導者》有一篇報導特別分析為什麼臺灣的GDP數字亮眼,卻和不少臺灣人的「體感」存在落差。
如果有感的話,以民進黨執政有如此突出的成績,不致於在野各方一度主張有六〇%的民意想要再次政黨輪替,使得二〇二四總統大位顯得如此多嬌,引來多方人馬競折腰,而賴清德只能寄望於三腳督或四腳督來取勝。
無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暴增的百億富豪
我先去訪問了財金文化董事長謝金河。
二〇一五年訪問他的時候,馬英九政府雖然一直在喊「拚經濟」、「拚出口」,但經濟成長率連保一都出了問題,出口連續衰退、股市崩盤,唯一仰仗半導體和電子業兩個明星產業支撐。
當時謝金河最擔心的是,「等紅色供應鏈的威脅再增強,我們就可能動搖國本。」而那年稍晚的時候,中國紫光集團的趙偉國來臺灣,高調號稱要合併聯發科,還要買下台積電的二十五%股份。
而當時不只聯發科心動,連台積電的張忠謀的表態也很含糊。他說唯一的準則是「只要價格合適,而且對股東有利」。
所以從謝金河的角度,不只看到八年來蔡英文政府比當年馬英九政府超越之處,也可以充分理解臺灣去年亮眼的經濟成績的原因。
謝金河說台積電真正「轉大人」是從二〇一八年起。當時英特爾的市值還是台積電的三倍,而現在台積電的市值是英特爾的四倍,有了護國神山之稱。
謝金河認為這其中是蔡英文全力支持台積電的決策發揮了關鍵作用。相形之下,紫光集團則在二〇二一年宣告破產重整。
謝金河也肯定蔡英文政府大力扶植起一些產業,每個產業都出現了亮眼的代表性企業,譬如軍工產業及其中的中信造船、龍德造船、生產飛彈晶片的全訊;綠能產業及其中的世紀鋼、世紀風電。
這些產業和企業的表現是如此之突出,造就了許多人的財富。謝金河說,八年前臺灣的百億級富豪為數很少,但現在暴增。並且二〇二二年富比世報導,臺灣總計 五十一人身價突破十億美元,人數排名全球第十。
至於當年馬英九政府當年把臺灣的經濟成長寄望於鎖進中國,簽訂《服貿協議》最終引發太陽花運動而破局之後,二〇一六年眼看韓國卻和中國簽訂了FTA(《自由貿易協定》),許多藍營政治人物及媒體感嘆臺灣把機會拱手讓給了韓國,接下來和韓國的差距會越拉越遠。
謝金河則認為事實證明:韓國經濟表現之所以在去年被臺灣超車,除了匯率變化的因素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從韓國和中國簽署FTA之後,反而造成中國在化工、面板、汽車、手機等韓國原先領先的領域節節敗退,不只失去產業領先優勢,也終於在二〇二二年結束長期對中國的貿易出超,而出現逆差。
「馬英九一直說兩岸關係不好,臺灣經濟不會好。但是事實證明,兩岸關係不好,臺灣經濟反而可以更好。」謝金河說,「韓國還證明,你和他關係越好,經濟還可能越不好。」
我問謝金河那怎麼解釋臺灣去年人均GDP超韓趕日,經濟表現這麼好,許多一般人卻無感?
《報導者》的分析裡,提到的可能原因有一個是:「從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二一年間,臺灣人的年薪中位數只成長了十四.四八%,明顯落後於GDP的成長率」;以及顯示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近年來都在逐漸拉大。尤其疫情期間臺灣企業(和地主及股東)實在太賺錢了,而勞工分配到的GDP比例不但沒有提升,還明顯縮水。
所以我問謝金河,會不會是這人均GDP增加的現象,主要由於少數富有者和大多數其他人的貧富差距拉得更大而導致?
謝金河承認有這個可能。「所以臺灣接下來的課題是要讓這些富有者的財富如何補貼到貧窮的人身上。」
從這一點看,他說像七月宣布私立大學學費的補助,就是可以讓人有感的。
訪問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秘書長彭揚凱,和長期研究臺灣經濟發展與年輕人薪資關係的中研院林宗弘研究員,這種貧富差距的落差原因就更清楚。
千分之一的人和其他人
臺灣急劇拉大的貧富差距,除了反映在謝金河說的人數暴增的百億富豪上,也顯示在有錢人擁有的房子數量上。
臺灣居住正義所涉及的課題,不只是房價高昂,很多人只能望屋興嘆,聽彭揚凱分析的一點尤其令人驚奇。
臺灣為了打擊房價的飆升喊著要開徵囤房稅很久了,但事實上並沒有一個特定的囤房稅,只是縣市政府視各自情況,就若干戶以上的非自用住宅課以比較高的稅率。平均起來,每個人大約從自己擁有的第四戶房屋才略為調高稅率。但因為幅度不大,不痛不癢。
而擁有多間房產的人數,在過去幾年時間裡也急劇增加。
二〇一四年,臺灣個人擁有三間房以上的人,有三十萬人;到二〇二〇年,個人擁有三間房以上的人,多達五十萬人。六年間增加了二十萬人,將近七成。
在大家普遍感嘆房價太高買不起房子的時候,這固然是實證貧富差距巨大的一個例子,還不是最驚人的。
林宗弘看到的無感原因,在於薪資的比例沒有增加太多,消費也沒有增加太多。
雖然蔡政府八年來改變馬英九政府時代的情況,持續在拉高最低工資水準,但是林宗弘說目前也不過就拉回崩世代應有的基準上而已。
並且平均薪資雖然在上升,但是通膨也上升,實質所得反而萎縮。
所以林宗弘指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第一個,固然有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還不能用一般講的貧富兩端這種觀念來看。
林宗弘從財政部的「家庭收支調查」來分析,近年來,臺灣只有頂端一%到〇.一%的人口的收入才有明顯成長,連頂端五%到一〇%的人的收入成長率都不明顯。而他們擁有的財富還不在不動產上,而是金融資產上。
所以臺灣貧富差距拉大不能只用籠統的貧富兩端來看,要用一%到〇.一%極富有的尖端,和其他所有的人的對比來看。
第二,GDP從收入面來看有三大面向,包括薪資、產業主所得(也就是利潤),加上資本支出和地租。
而林宗弘看到,相對於名目工資所得稍有上漲,產業主的所得是停滯的。在GDP增長的結構裡,增加最多的是因資本支出而產生的資本折損。
因此,GDP雖然有成長,但是實際上其中真正在成長的不是受薪者的薪資,也不是產業主的所得(利潤),而是資本支出的受益者。所以真正獲益的圈子不只限縮在高階工程師、經理人,或是投資者,而是在資本支出的獲益者,也就是電子業購買那些昂貴、資本密集設備的相對方。像荷蘭提供晶片製造設備的艾司摩爾(ASML)。
也因此,林宗弘跟我說,雖然台積電得到「護國神山」之名,但相對於臺灣的投資者有八〇%是來自國外,臺灣本身要為台積電的用電用水付出偌大代價,連GDP的成長也有很大一塊是被台積電所代表的電子業的供應鏈給吃掉,大家應該思考一件事情:「臺灣電子業的利益是否等同於臺灣人民的利益?台積電的利益是否等同於臺灣人民的利益?」
總之,臺灣有些人可以歡慶人均GDP的超韓趕日,卻有更多的人無感於這種成長,不是沒有原因。
然而,光是這種無感,應該不至於形成那麼多人想要民進黨下台。
站在民進黨對面的人到底是什麼面貌?
(未完)
二、國民黨的情況
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
很長一段時間,我想不通二〇一三年馬英九總統是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想要通過《服貿協議》,非要把臺灣的經濟鎖進中國不可。
《服貿協議》內容的制定、和對岸簽約的安排,一切都保密到家。不只是在國民黨完全執政時期的國會把在野的民進黨立法委員蒙在鼓裡,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也沒人知道;不但國民黨的立委不知道,連同黨的立院龍頭王金平都蒙在鼓裡。在上海的簽約時間和簽約內容,都是在簽後才對外公布。而到底誰要為《服貿協議》的內容和談判負責,一時也沒有人承認。
等到後來輿論大嘩,是馬英九總統親自上陣,帶著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四處滅火。
堂堂中華民國總統,為什麼會這麼急切地非要臺灣與對岸簽下一張風險與爭議如此之大的協議?
後來,我想到答案應該從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找起。
那天是個常見的春日。雖然是星期三,但因為是五一勞動節假日,臺北街頭的人去看《沉默的羔羊》,留在家裡的人看三台的電視節目。
但那也是劃分歷史里程的一天。
當天,李登輝總統經國民大會諮請公告,廢止了施行四十三年之久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國共內戰的產物。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一方面據以把臺灣和大陸界定為自由地區和匪區,成為剿匪、對付中共匪諜的法律依據,一方面也成為在臺灣實施威權統治的有力工具,瀰漫白色恐怖,同時也鎮壓臺灣本土意識的工具。
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裡,從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之後,到再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必須的一步;有了這一步,次年再修正刑法第一百條,再配合警備總部這樣單位的改制,才全面奠定保護臺灣言論自由、基本人權的基石。
然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也要搭配著另兩件事情看。
一個是在前一年出現的國統會,及當年二月出現的《國家統一綱領》。
《國統綱領》提出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把兩岸看作兩個政治實體,避談主權歸屬,而希望將來追求終極統一。
另一個,是在五月同時宣布撤裁的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
簡單說,國民黨李登輝黨主席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有別於過去兩蔣時代國民黨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宣布了要和對岸進入國家統一的途徑和期程,另一方面也不再把對岸視之為動員戡亂時期的「匪區」,也不需要再「光復大陸」了。
隨著這個臨時條款的廢止,之前的「匪區」改名為「大陸地區」,不只不再需要「剿匪」,連「資匪」、「通匪」這些帽子也都跟著消失,對於大量過去長期習慣於反攻大陸、匪我不兩立的人來說,世界徹底改觀。
對國民黨,或所謂藍營的許多人來說,不再需要剿匪,對岸不再是「匪」而是可以經由談判而統一的對象之後,加上早已開放的探親、投資,大陸所承載的「中國」記憶和印象,血濃於水的說法,就產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然而另一方面,隨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而啟動各種相關法律、機關的改變、言論和思想禁忌的解除,不論是基於歷史因素,還是基於社會價值觀和中國的差異,臺灣本土意識不可避免地日益抬頭,意識到需要和中國即使不是保持對立也要保持距離,並且想和中國人有清楚區分的臺灣人身分認同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多。所以,從這個臨時條款的廢止開始,注定繼續以「統一」為目標的國民黨在臺灣會日益背離主流民意,越漂越遠。
看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調查」,三十年的消長一目瞭然。
一九九二年,也就是民國八十一年,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是十六.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是二十五.五%;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是四十六.四%。合起來看,接受自己中國人身分的,佔了七十一.九%。接受自己臺灣人身分的,是六十三.一%。
但接下來,三種認同比率的消長對比,越來越明顯。到今年二〇二三年六月,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達到六十二.八%;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降到二.五%;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則是三十.五%。合起來,接受自己是臺灣人身分的,佔了九十三.三%,接受自己是中國人身分的,是三十三%。
但是許多國民黨人及其支持者,卻站上了另一端。
在馬英九的努力之下
在一九九〇年國統會成立的時候,馬英九是國統會研究委員,想必對其後提出的《國統綱領》的擬定參與很多。
眼看國統會和《國統綱領》都在民進黨陳水扁任上廢止,臺灣主流的國家認同意識又和他當年參與設計的方向越來越遠,以他為代表的許多國民黨人感受到的衝擊和焦慮可以想見。
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國民黨交出政權,當時擔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在卸任前提出「九二共識」的說法。蘇起之所以要在距一九九二年八年之後才提出「九二共識」的說法,很可能就是在參與《國統綱領》設計的國民黨人眼見政權輪替,又預見在民進黨主政下《國統綱領》可能被廢止的風險,而提出不同名稱的論述。這樣,等將來即使有《國統綱領》被廢止的一天(六年後也的確發生),他們仍然有一個對兩岸關係的論述,和對岸來往的依據。這可以說是國民黨另類版的「《國統綱領》」。
而馬英九在二〇〇八年當選總統後,想要從施政上實踐這個論述,力挽狂瀾。
馬英九當選總統後,不顧如果再多一些談判可以為臺灣爭取到更好的條件,就立即大開兩岸三通;二〇〇九年就提出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並在次年與對岸簽約;二〇一三年在拚經濟屢不見效之下,企圖把臺灣經濟和中國緊密結合,簽下《服貿協議》;同年啟動自經區並企圖開放中資進入;二〇一五年甚至準備開放中國紫光集團來臺灣「買下台積電、合併聯發科」。
馬英九這些越來越毫不顧忌把臺灣鎖進中國的政策,都是因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對岸不再是「匪區」而成為「大陸地區」之後,他心中就少了對對岸應有的戒心和警醒,一心努力要把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緊密結合了。
如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還在,學法律的馬英九就不會說他都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行事,他會想到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資匪、通匪了。
然而,國民黨人忘了一件事:他們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他們不再稱呼對岸為「匪區」,他們認為從此可以和對岸來往,可以透過坐下來談判將來追求統一,但是一九四九年把他們大江南北一路追殺到臺灣的共產黨人又怎麼想呢?
如果他們也有一個類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東西,在當時也同時廢止了,那還可以多少說表露了同樣的意圖。還比較可以說是有共識。
但可惜他們沒有。
而中國共產黨沒有,並不是說他們沒把國民黨當敵手,沒有把臺灣當「匪區」,而是他們認為中華民國早已滅亡了,不存在了。都已經滅亡、不存在的對手,不需要有個法律來對付。
他們不會忘記的,應該還是毛澤東那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未完)
一、民進黨的情況
當人均GDP超韓趕日本時
今年二月臺北國際書展期間,有一天和韓國朋友聚餐。他感嘆韓國的經濟表現不佳,恭喜臺灣的人均GDP超越了韓國。
我說是啊,甚至我們還超越了日本呢。
這一下不只韓國人,連同桌的其他臺灣人也大呼驚奇。這麼大的新聞,他們都沒注意到。
最先見諸新聞報導的,是去年十月蔡英文總統表示,根據IMF的數據,臺灣的人均GDP將首次超越日本及韓國,成為東亞第一。到十二月中,日本經濟新聞,也報導臺灣將超越日本。
儘管其後實際的統計顯示,臺灣的人均GDP是三二、五八六美元,比日本的三三、七三一美元差了大約一千美元,但已經是有史以來最小的差距。並且,從二〇〇三年臺灣被韓國超越之後,的確二十年後來首次逆轉,多過韓國的三二、四一〇美元。
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成績。
以日本在經濟、生活上諸多層面對臺灣都有標竿性意義,臺灣對韓國又有諸多緊盯的競爭指標來說,發生了這麼大事,即使不舉國歡騰,大家也該很興奮。
然而為什麼許多人都沒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也覺得很不真實,很無感?
今年六月,《報導者》有一篇報導特別分析為什麼臺灣的GDP數字亮眼,卻和不少臺灣人的「體感」存在落差。
如果有感的話,以民進黨執政有如此突出的成績,不致於在野各方一度主張有六〇%的民意想要再次政黨輪替,使得二〇二四總統大位顯得如此多嬌,引來多方人馬競折腰,而賴清德只能寄望於三腳督或四腳督來取勝。
無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暴增的百億富豪
我先去訪問了財金文化董事長謝金河。
二〇一五年訪問他的時候,馬英九政府雖然一直在喊「拚經濟」、「拚出口」,但經濟成長率連保一都出了問題,出口連續衰退、股市崩盤,唯一仰仗半導體和電子業兩個明星產業支撐。
當時謝金河最擔心的是,「等紅色供應鏈的威脅再增強,我們就可能動搖國本。」而那年稍晚的時候,中國紫光集團的趙偉國來臺灣,高調號稱要合併聯發科,還要買下台積電的二十五%股份。
而當時不只聯發科心動,連台積電的張忠謀的表態也很含糊。他說唯一的準則是「只要價格合適,而且對股東有利」。
所以從謝金河的角度,不只看到八年來蔡英文政府比當年馬英九政府超越之處,也可以充分理解臺灣去年亮眼的經濟成績的原因。
謝金河說台積電真正「轉大人」是從二〇一八年起。當時英特爾的市值還是台積電的三倍,而現在台積電的市值是英特爾的四倍,有了護國神山之稱。
謝金河認為這其中是蔡英文全力支持台積電的決策發揮了關鍵作用。相形之下,紫光集團則在二〇二一年宣告破產重整。
謝金河也肯定蔡英文政府大力扶植起一些產業,每個產業都出現了亮眼的代表性企業,譬如軍工產業及其中的中信造船、龍德造船、生產飛彈晶片的全訊;綠能產業及其中的世紀鋼、世紀風電。
這些產業和企業的表現是如此之突出,造就了許多人的財富。謝金河說,八年前臺灣的百億級富豪為數很少,但現在暴增。並且二〇二二年富比世報導,臺灣總計 五十一人身價突破十億美元,人數排名全球第十。
至於當年馬英九政府當年把臺灣的經濟成長寄望於鎖進中國,簽訂《服貿協議》最終引發太陽花運動而破局之後,二〇一六年眼看韓國卻和中國簽訂了FTA(《自由貿易協定》),許多藍營政治人物及媒體感嘆臺灣把機會拱手讓給了韓國,接下來和韓國的差距會越拉越遠。
謝金河則認為事實證明:韓國經濟表現之所以在去年被臺灣超車,除了匯率變化的因素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從韓國和中國簽署FTA之後,反而造成中國在化工、面板、汽車、手機等韓國原先領先的領域節節敗退,不只失去產業領先優勢,也終於在二〇二二年結束長期對中國的貿易出超,而出現逆差。
「馬英九一直說兩岸關係不好,臺灣經濟不會好。但是事實證明,兩岸關係不好,臺灣經濟反而可以更好。」謝金河說,「韓國還證明,你和他關係越好,經濟還可能越不好。」
我問謝金河那怎麼解釋臺灣去年人均GDP超韓趕日,經濟表現這麼好,許多一般人卻無感?
《報導者》的分析裡,提到的可能原因有一個是:「從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二一年間,臺灣人的年薪中位數只成長了十四.四八%,明顯落後於GDP的成長率」;以及顯示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近年來都在逐漸拉大。尤其疫情期間臺灣企業(和地主及股東)實在太賺錢了,而勞工分配到的GDP比例不但沒有提升,還明顯縮水。
所以我問謝金河,會不會是這人均GDP增加的現象,主要由於少數富有者和大多數其他人的貧富差距拉得更大而導致?
謝金河承認有這個可能。「所以臺灣接下來的課題是要讓這些富有者的財富如何補貼到貧窮的人身上。」
從這一點看,他說像七月宣布私立大學學費的補助,就是可以讓人有感的。
訪問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秘書長彭揚凱,和長期研究臺灣經濟發展與年輕人薪資關係的中研院林宗弘研究員,這種貧富差距的落差原因就更清楚。
千分之一的人和其他人
臺灣急劇拉大的貧富差距,除了反映在謝金河說的人數暴增的百億富豪上,也顯示在有錢人擁有的房子數量上。
臺灣居住正義所涉及的課題,不只是房價高昂,很多人只能望屋興嘆,聽彭揚凱分析的一點尤其令人驚奇。
臺灣為了打擊房價的飆升喊著要開徵囤房稅很久了,但事實上並沒有一個特定的囤房稅,只是縣市政府視各自情況,就若干戶以上的非自用住宅課以比較高的稅率。平均起來,每個人大約從自己擁有的第四戶房屋才略為調高稅率。但因為幅度不大,不痛不癢。
而擁有多間房產的人數,在過去幾年時間裡也急劇增加。
二〇一四年,臺灣個人擁有三間房以上的人,有三十萬人;到二〇二〇年,個人擁有三間房以上的人,多達五十萬人。六年間增加了二十萬人,將近七成。
在大家普遍感嘆房價太高買不起房子的時候,這固然是實證貧富差距巨大的一個例子,還不是最驚人的。
林宗弘看到的無感原因,在於薪資的比例沒有增加太多,消費也沒有增加太多。
雖然蔡政府八年來改變馬英九政府時代的情況,持續在拉高最低工資水準,但是林宗弘說目前也不過就拉回崩世代應有的基準上而已。
並且平均薪資雖然在上升,但是通膨也上升,實質所得反而萎縮。
所以林宗弘指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第一個,固然有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還不能用一般講的貧富兩端這種觀念來看。
林宗弘從財政部的「家庭收支調查」來分析,近年來,臺灣只有頂端一%到〇.一%的人口的收入才有明顯成長,連頂端五%到一〇%的人的收入成長率都不明顯。而他們擁有的財富還不在不動產上,而是金融資產上。
所以臺灣貧富差距拉大不能只用籠統的貧富兩端來看,要用一%到〇.一%極富有的尖端,和其他所有的人的對比來看。
第二,GDP從收入面來看有三大面向,包括薪資、產業主所得(也就是利潤),加上資本支出和地租。
而林宗弘看到,相對於名目工資所得稍有上漲,產業主的所得是停滯的。在GDP增長的結構裡,增加最多的是因資本支出而產生的資本折損。
因此,GDP雖然有成長,但是實際上其中真正在成長的不是受薪者的薪資,也不是產業主的所得(利潤),而是資本支出的受益者。所以真正獲益的圈子不只限縮在高階工程師、經理人,或是投資者,而是在資本支出的獲益者,也就是電子業購買那些昂貴、資本密集設備的相對方。像荷蘭提供晶片製造設備的艾司摩爾(ASML)。
也因此,林宗弘跟我說,雖然台積電得到「護國神山」之名,但相對於臺灣的投資者有八〇%是來自國外,臺灣本身要為台積電的用電用水付出偌大代價,連GDP的成長也有很大一塊是被台積電所代表的電子業的供應鏈給吃掉,大家應該思考一件事情:「臺灣電子業的利益是否等同於臺灣人民的利益?台積電的利益是否等同於臺灣人民的利益?」
總之,臺灣有些人可以歡慶人均GDP的超韓趕日,卻有更多的人無感於這種成長,不是沒有原因。
然而,光是這種無感,應該不至於形成那麼多人想要民進黨下台。
站在民進黨對面的人到底是什麼面貌?
(未完)
二、國民黨的情況
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
很長一段時間,我想不通二〇一三年馬英九總統是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想要通過《服貿協議》,非要把臺灣的經濟鎖進中國不可。
《服貿協議》內容的制定、和對岸簽約的安排,一切都保密到家。不只是在國民黨完全執政時期的國會把在野的民進黨立法委員蒙在鼓裡,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也沒人知道;不但國民黨的立委不知道,連同黨的立院龍頭王金平都蒙在鼓裡。在上海的簽約時間和簽約內容,都是在簽後才對外公布。而到底誰要為《服貿協議》的內容和談判負責,一時也沒有人承認。
等到後來輿論大嘩,是馬英九總統親自上陣,帶著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四處滅火。
堂堂中華民國總統,為什麼會這麼急切地非要臺灣與對岸簽下一張風險與爭議如此之大的協議?
後來,我想到答案應該從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找起。
那天是個常見的春日。雖然是星期三,但因為是五一勞動節假日,臺北街頭的人去看《沉默的羔羊》,留在家裡的人看三台的電視節目。
但那也是劃分歷史里程的一天。
當天,李登輝總統經國民大會諮請公告,廢止了施行四十三年之久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國共內戰的產物。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一方面據以把臺灣和大陸界定為自由地區和匪區,成為剿匪、對付中共匪諜的法律依據,一方面也成為在臺灣實施威權統治的有力工具,瀰漫白色恐怖,同時也鎮壓臺灣本土意識的工具。
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裡,從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之後,到再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必須的一步;有了這一步,次年再修正刑法第一百條,再配合警備總部這樣單位的改制,才全面奠定保護臺灣言論自由、基本人權的基石。
然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也要搭配著另兩件事情看。
一個是在前一年出現的國統會,及當年二月出現的《國家統一綱領》。
《國統綱領》提出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把兩岸看作兩個政治實體,避談主權歸屬,而希望將來追求終極統一。
另一個,是在五月同時宣布撤裁的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
簡單說,國民黨李登輝黨主席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有別於過去兩蔣時代國民黨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宣布了要和對岸進入國家統一的途徑和期程,另一方面也不再把對岸視之為動員戡亂時期的「匪區」,也不需要再「光復大陸」了。
隨著這個臨時條款的廢止,之前的「匪區」改名為「大陸地區」,不只不再需要「剿匪」,連「資匪」、「通匪」這些帽子也都跟著消失,對於大量過去長期習慣於反攻大陸、匪我不兩立的人來說,世界徹底改觀。
對國民黨,或所謂藍營的許多人來說,不再需要剿匪,對岸不再是「匪」而是可以經由談判而統一的對象之後,加上早已開放的探親、投資,大陸所承載的「中國」記憶和印象,血濃於水的說法,就產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然而另一方面,隨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而啟動各種相關法律、機關的改變、言論和思想禁忌的解除,不論是基於歷史因素,還是基於社會價值觀和中國的差異,臺灣本土意識不可避免地日益抬頭,意識到需要和中國即使不是保持對立也要保持距離,並且想和中國人有清楚區分的臺灣人身分認同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多。所以,從這個臨時條款的廢止開始,注定繼續以「統一」為目標的國民黨在臺灣會日益背離主流民意,越漂越遠。
看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調查」,三十年的消長一目瞭然。
一九九二年,也就是民國八十一年,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是十六.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是二十五.五%;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是四十六.四%。合起來看,接受自己中國人身分的,佔了七十一.九%。接受自己臺灣人身分的,是六十三.一%。
但接下來,三種認同比率的消長對比,越來越明顯。到今年二〇二三年六月,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達到六十二.八%;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降到二.五%;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則是三十.五%。合起來,接受自己是臺灣人身分的,佔了九十三.三%,接受自己是中國人身分的,是三十三%。
但是許多國民黨人及其支持者,卻站上了另一端。
在馬英九的努力之下
在一九九〇年國統會成立的時候,馬英九是國統會研究委員,想必對其後提出的《國統綱領》的擬定參與很多。
眼看國統會和《國統綱領》都在民進黨陳水扁任上廢止,臺灣主流的國家認同意識又和他當年參與設計的方向越來越遠,以他為代表的許多國民黨人感受到的衝擊和焦慮可以想見。
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國民黨交出政權,當時擔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在卸任前提出「九二共識」的說法。蘇起之所以要在距一九九二年八年之後才提出「九二共識」的說法,很可能就是在參與《國統綱領》設計的國民黨人眼見政權輪替,又預見在民進黨主政下《國統綱領》可能被廢止的風險,而提出不同名稱的論述。這樣,等將來即使有《國統綱領》被廢止的一天(六年後也的確發生),他們仍然有一個對兩岸關係的論述,和對岸來往的依據。這可以說是國民黨另類版的「《國統綱領》」。
而馬英九在二〇〇八年當選總統後,想要從施政上實踐這個論述,力挽狂瀾。
馬英九當選總統後,不顧如果再多一些談判可以為臺灣爭取到更好的條件,就立即大開兩岸三通;二〇〇九年就提出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並在次年與對岸簽約;二〇一三年在拚經濟屢不見效之下,企圖把臺灣經濟和中國緊密結合,簽下《服貿協議》;同年啟動自經區並企圖開放中資進入;二〇一五年甚至準備開放中國紫光集團來臺灣「買下台積電、合併聯發科」。
馬英九這些越來越毫不顧忌把臺灣鎖進中國的政策,都是因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對岸不再是「匪區」而成為「大陸地區」之後,他心中就少了對對岸應有的戒心和警醒,一心努力要把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緊密結合了。
如果《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還在,學法律的馬英九就不會說他都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行事,他會想到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資匪、通匪了。
然而,國民黨人忘了一件事:他們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他們不再稱呼對岸為「匪區」,他們認為從此可以和對岸來往,可以透過坐下來談判將來追求統一,但是一九四九年把他們大江南北一路追殺到臺灣的共產黨人又怎麼想呢?
如果他們也有一個類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東西,在當時也同時廢止了,那還可以多少說表露了同樣的意圖。還比較可以說是有共識。
但可惜他們沒有。
而中國共產黨沒有,並不是說他們沒把國民黨當敵手,沒有把臺灣當「匪區」,而是他們認為中華民國早已滅亡了,不存在了。都已經滅亡、不存在的對手,不需要有個法律來對付。
他們不會忘記的,應該還是毛澤東那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