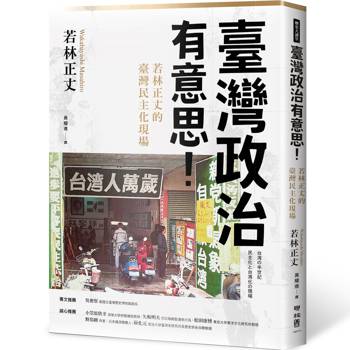內文選摘
迎向臺灣政治的激盪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蔣經國容許在野黨民主進步黨成立,自此臺灣的政治便進入動盪期。彼時取得東大助教授職位的我,在每個動盪的階段都被要求撰寫時事評論性的文章,與此同時也為自己的學術性臺灣政治研究打穩基礎。
此處先整理臺灣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史。自一九七九年底的美麗島事件起至一九八六年民進黨組成為止,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體制的動搖期。之後歷經一九八七年解除長期戒嚴令,依據憲改後的《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政治制度,基於此實施國會的全面改選等過程,到一九九六年初實施首次總統直選的民主政治體制最終成立為止的十年期
……
面臨迫近的重大政治時程
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此時期李登輝被迫做出極為重大的政治決斷。我在前述二〇〇八年的著作中推測,「最遲到一九八九年底選舉之後,李登輝才較具體地決定與反對力量再度交涉,以推動民主化」,其根據之一即是前文引用的附註。
接續在任內過世的蔣經國,李登輝的總統任期至一九九〇年五月為止。在此前的三月,國民代表大會將舉行正副總統選舉,其中除了多數延續舊制未經改選的「萬年國代」,還包括透過「增額選舉」產生的少數代表。此外,在此之前,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也將先行決定國民黨內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
在此重大政治時程之前,國民黨政權內的各派系中握有影響力之外省人也開始行動,進入後蔣經國時期不久,國民黨要員之間相互牽制的均衡行將崩毀。同時,在野黨民進黨面對從蔣經國末年至逝後不久制度化之「附加限制的自由化」(新成立政黨不得主張「臺灣獨立」)以及緩步的政治改革(以發放退休金促其自發性退職的形式來解除「萬年國會」)感到不滿,此外,對於把憲法的重要條款束諸高閣,長期以來作為治安法治依據的嚴苛《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依舊未被廢止的狀況,更是大感不悅。這種狀況從戒嚴令解除後臺北街頭陸續、不斷出現各種高舉政治、社會改革要求的遊行、集會即可清楚看出。
決心成為「實權總統」
一九九一年夏季左右,許水德以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身分赴任,筆者聽到他以日語發表評論,稱李登輝是「赤手空拳進入總統府」。在外省人看來,李登輝不過是蔣經國基於政治戰略提拔的本省人從屬菁英。一如前述我的推測,反對勢力不滿蔣經國掛保證的溫吞改革,李登輝若打算與他們進入二度交涉,就不能僅成為外省人菁英為他設定的「暫時總統」、「傀儡總統」,而必須是自身擁有獨自交涉能力的「實權總統」。為此對決的時刻迅速迫近。若強加忖度李登輝的內心,那應該是「從清水寺的高臺上一躍而下」(清水の舞台から飛び降りる,下定決心豁出去做)的決心。不過,如果沒有此時的決心,也就不會出現日後被讚為「民主先生(Mr. Democracy )」的李登輝。
即便如此,以上是我自己認為較為可靠的推測。即便曾有機會,但關於此時的間接詢問卻在我疏於向李登輝本人或鍾振宏求證之下,二位都已過世。對於自己未搞清楚此事只感到羞愧。如此一般,雖說只是間接的、單方面的問答,不過這就是李登輝與我的最初連接點。不久之後便迎來能與他直接對話的機會。
「總統蒞臨!」
時至今日,有些當時寫的筆記也難以判讀,其中有一條寫著「一七:四〇」。日方成員於七月十九日下午抵達臺北後,在隔天開始的會議之前便被帶往總統府。當然對我而言,這是首次進入總統府(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總督府)這棟建築。進入會客室依照禮賓人員指示順序就座後,立正站在入口附近的禮賓人員旋即高聲道:「總統蒞臨!」用日語來說就是「総統のおなり!」瞬間感覺到蔣家父子二代的宮廷政治味道。
總統在隨從的陪伴下帶著笑容進入,中嶋老師在一旁開始介紹日方的參加成員。輪到我時,在中嶋老師介紹後,總統突然大聲對我說:「我正在讀你的論文呢」,讓我吃了一驚。閱讀我的論文並不令我感到意外,但在這種場合大聲說出則讓我訝異。日後一想,這或許是他對來賓發揮的一種服務精神吧。
之後有總統的歡迎致詞,內容強調此研討會的意義,照稿宣讀中文原稿,由當時行政院新聞局人員、出身筑波大學的邱榮金先生照稿口譯。之後可以由日方進行發問,接下來便不再口譯,全部以日語進行對話。總統以日語說話時感覺更為放鬆。一旁陪同理當不懂日語的總統府參軍長蔣仲苓將軍對此毫不介意。
「我是走鋼索的人啊」
暫且由年長成員與總統談話之後,輪到中嶋老師向我提問,我思索著開頭所述的原委,大略提出如下的問題。「民主化開始後,無論大眾傳媒或臺北街頭,都對臺灣政治的未來提出各種各樣的主張並發生爭論。總統也是國民黨主席,套用棒球用語,看起來就像是球員兼裁判,對此您本身的想法如何?」
對此李登輝一開口便說,「我是走鋼索的人啊。」我僅清楚記得他就是如此以日語回答。他想要表達的,參照先前提過我那份不太可靠的筆記,推演開來大致是:現狀為既得利益、傳統思考方式與新的主張相爭,民主政治雖在原則上以民意為基礎,卻無法達到百分之百。與其從改革伊始便決定必須這麼做,不如邊摸索並從中找出合適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樣的發言旨趣。因為我筆記上也寫著「真的是在走鋼索」字樣,可以看出一直煞費苦心地在看似流動中的政治平衡中確立領導權。
這是首次與李登輝交談的經驗。從本人口中聽到「我是走鋼索的人啊」一語,對已開始的「憲政改革」觀察而言算是重大收穫。
迎向臺灣政治的激盪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蔣經國容許在野黨民主進步黨成立,自此臺灣的政治便進入動盪期。彼時取得東大助教授職位的我,在每個動盪的階段都被要求撰寫時事評論性的文章,與此同時也為自己的學術性臺灣政治研究打穩基礎。
此處先整理臺灣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史。自一九七九年底的美麗島事件起至一九八六年民進黨組成為止,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體制的動搖期。之後歷經一九八七年解除長期戒嚴令,依據憲改後的《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政治制度,基於此實施國會的全面改選等過程,到一九九六年初實施首次總統直選的民主政治體制最終成立為止的十年期
……
面臨迫近的重大政治時程
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此時期李登輝被迫做出極為重大的政治決斷。我在前述二〇〇八年的著作中推測,「最遲到一九八九年底選舉之後,李登輝才較具體地決定與反對力量再度交涉,以推動民主化」,其根據之一即是前文引用的附註。
接續在任內過世的蔣經國,李登輝的總統任期至一九九〇年五月為止。在此前的三月,國民代表大會將舉行正副總統選舉,其中除了多數延續舊制未經改選的「萬年國代」,還包括透過「增額選舉」產生的少數代表。此外,在此之前,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也將先行決定國民黨內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
在此重大政治時程之前,國民黨政權內的各派系中握有影響力之外省人也開始行動,進入後蔣經國時期不久,國民黨要員之間相互牽制的均衡行將崩毀。同時,在野黨民進黨面對從蔣經國末年至逝後不久制度化之「附加限制的自由化」(新成立政黨不得主張「臺灣獨立」)以及緩步的政治改革(以發放退休金促其自發性退職的形式來解除「萬年國會」)感到不滿,此外,對於把憲法的重要條款束諸高閣,長期以來作為治安法治依據的嚴苛《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依舊未被廢止的狀況,更是大感不悅。這種狀況從戒嚴令解除後臺北街頭陸續、不斷出現各種高舉政治、社會改革要求的遊行、集會即可清楚看出。
決心成為「實權總統」
一九九一年夏季左右,許水德以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身分赴任,筆者聽到他以日語發表評論,稱李登輝是「赤手空拳進入總統府」。在外省人看來,李登輝不過是蔣經國基於政治戰略提拔的本省人從屬菁英。一如前述我的推測,反對勢力不滿蔣經國掛保證的溫吞改革,李登輝若打算與他們進入二度交涉,就不能僅成為外省人菁英為他設定的「暫時總統」、「傀儡總統」,而必須是自身擁有獨自交涉能力的「實權總統」。為此對決的時刻迅速迫近。若強加忖度李登輝的內心,那應該是「從清水寺的高臺上一躍而下」(清水の舞台から飛び降りる,下定決心豁出去做)的決心。不過,如果沒有此時的決心,也就不會出現日後被讚為「民主先生(Mr. Democracy )」的李登輝。
即便如此,以上是我自己認為較為可靠的推測。即便曾有機會,但關於此時的間接詢問卻在我疏於向李登輝本人或鍾振宏求證之下,二位都已過世。對於自己未搞清楚此事只感到羞愧。如此一般,雖說只是間接的、單方面的問答,不過這就是李登輝與我的最初連接點。不久之後便迎來能與他直接對話的機會。
「總統蒞臨!」
時至今日,有些當時寫的筆記也難以判讀,其中有一條寫著「一七:四〇」。日方成員於七月十九日下午抵達臺北後,在隔天開始的會議之前便被帶往總統府。當然對我而言,這是首次進入總統府(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總督府)這棟建築。進入會客室依照禮賓人員指示順序就座後,立正站在入口附近的禮賓人員旋即高聲道:「總統蒞臨!」用日語來說就是「総統のおなり!」瞬間感覺到蔣家父子二代的宮廷政治味道。
總統在隨從的陪伴下帶著笑容進入,中嶋老師在一旁開始介紹日方的參加成員。輪到我時,在中嶋老師介紹後,總統突然大聲對我說:「我正在讀你的論文呢」,讓我吃了一驚。閱讀我的論文並不令我感到意外,但在這種場合大聲說出則讓我訝異。日後一想,這或許是他對來賓發揮的一種服務精神吧。
之後有總統的歡迎致詞,內容強調此研討會的意義,照稿宣讀中文原稿,由當時行政院新聞局人員、出身筑波大學的邱榮金先生照稿口譯。之後可以由日方進行發問,接下來便不再口譯,全部以日語進行對話。總統以日語說話時感覺更為放鬆。一旁陪同理當不懂日語的總統府參軍長蔣仲苓將軍對此毫不介意。
「我是走鋼索的人啊」
暫且由年長成員與總統談話之後,輪到中嶋老師向我提問,我思索著開頭所述的原委,大略提出如下的問題。「民主化開始後,無論大眾傳媒或臺北街頭,都對臺灣政治的未來提出各種各樣的主張並發生爭論。總統也是國民黨主席,套用棒球用語,看起來就像是球員兼裁判,對此您本身的想法如何?」
對此李登輝一開口便說,「我是走鋼索的人啊。」我僅清楚記得他就是如此以日語回答。他想要表達的,參照先前提過我那份不太可靠的筆記,推演開來大致是:現狀為既得利益、傳統思考方式與新的主張相爭,民主政治雖在原則上以民意為基礎,卻無法達到百分之百。與其從改革伊始便決定必須這麼做,不如邊摸索並從中找出合適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樣的發言旨趣。因為我筆記上也寫著「真的是在走鋼索」字樣,可以看出一直煞費苦心地在看似流動中的政治平衡中確立領導權。
這是首次與李登輝交談的經驗。從本人口中聽到「我是走鋼索的人啊」一語,對已開始的「憲政改革」觀察而言算是重大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