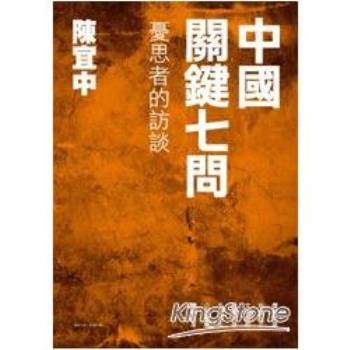崛起中國的十字路口:許紀霖訪談錄
許紀霖先生,浙江紹興人,1957年出生於上海。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1977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1982年留校任教。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受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影響,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反思,以及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和知識分子的研究。從「啟蒙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國思想界的分化,並積極介入當代論爭,為大陸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寫有《無窮的困惑》、《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化史》(主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著作。
一、1980年代的啟蒙及其分裂
王超華(以下簡稱「王」):許先生,可否請您先談談您的成長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屆的?
許紀霖(以下簡稱「許」):我1957年出生,在上海長大。文革時我是小學生,紅小兵。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在上海市郊的東海農場。1978年作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考進了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我本科4年畢業後,剛好缺青年教師,所以我就留校了,在任教的期間在職讀碩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時,歲數算是比較小的。
許:我們班上,幾乎全都是「老三屆」,所以我是小字輩。班長與班裡年齡最小的相差15歲,他開玩笑地對他說:「我都可以把你生出來了。」我自己觀察,老三屆的話題總是繞不過文革。關於文革,有三個不同的年齡層,區別在於康有為所說的「所經之事」、「所見之事」和「所聞之事」。對老三屆,文革是「所經之事」。對我這個紅小兵而言是「所見之事」,因為我沒有直接經歷,就算經歷也是很間接的。而對文革後的一代,文革則是「所聞之事」了。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學的時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鄉雖然經歷過,但畢竟經歷有限,沒有很直接的心理衝撞。我覺得跟老三屆相比,自己與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有親和性。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您最初做的是民主黨派研究,大學時代就對這題目感興趣?
許:純屬偶然。念大學時,自己亂看書。畢業留校之後,系裡要我跟著一個老師研究中國民主黨派。我對民主黨派本身沒什麼興趣,但發現那些民主黨派人士不得了,個個都是大知識分子;他們在20世紀前半葉的命運,與當代知識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內心之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我的第一篇稿,寫的是黃遠生。他是民國初年的名記者,袁世凱稱帝時要他幫忙造勢。他非常掙扎,寫完了又很後悔,因此後來寫了《懺悔錄》,懺悔自己的一生。我看了很有感受,就寫了一篇〈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王焱是《讀書》的編輯部主任,竟然把我這個無名之輩的處女作發了出來,給我很大的鼓勵。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我寫了二、三十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個案研究的文章。
那些個案我稱之為「心態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態史研究」提升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從個案出發,提煉出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就像以賽亞‧柏林和別爾嘉耶夫對俄國知識分子的研究。
王:您為何認為大學的經歷是最重要的?
許:1980年代大學的氛圍,與現在完全不一樣。當時私人空間很少,連談戀愛都很拘束,與女同學稍為接觸多一點,支部書記就會來干預。但1980年代校園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躍:競選人大代表、模擬審判、討論國家大事、上街遊行等等,熱鬧極了。1980年代有一種後文革的氛圍,文革中的紅衛兵精神轉化為一種「後理想主義」,從「奉旨造反」轉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開放。1980年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大視野、大思路、大氣魄,這種精神對我影響很深。
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父與子兩代人。父親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比如赫爾岑、屠格涅夫,既有懷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內涵而沒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動猶豫。兒子一代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識分子,他們的信念很簡單,為一個簡單的主義奮鬥,非常有行動力;但他們有力量而沒有內涵,堅信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當代中國兩代知識分子似乎剛好倒過來。像我們這些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輕信而行動力強;我們都是行動主義者,總是要有一個信念,都喜歡大問題,具有實踐性,而這恐怕都與文革的紅衛兵精神有關。而1990年代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比如我的學生一代,書讀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國父親那代,常常有一種無力感;他們在虛無主義的環境中生長,經常懷疑行動的功效與意義,成為遊移不定的「多餘的人」。
陳:您怎麼看1980年代跟文革的關係?
許:像我們這些1980年代人,總是從大處著眼,總是在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大問題,胸懷責任感,而且有所行動。如果我們把毛澤東時代看作一種紅色宗教,類似革命烏托邦的宗教時代,具有一種神聖性,那麼1980年代不過是這神聖性的世俗版。1980年代去掉了毛的神聖性,但重新賦予啟蒙、現代化以某種神魅性。中國真正的世俗化要到1990年代之後才完全展開。在中國,1960-70年代生的人還多少受到1980年代的精神洗禮;但「80後」一代則完全在1990年代之後的世俗化環境下成長起來,在文化性格上是全新的一代人,與1980年代開始格格不入。這個新,一個是世俗化,另一個就是虛無主義。
陳:您如何看待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以及1990年代以後的變化?
許:傅柯講過,啟蒙是一種態度。1980年代的啟蒙,按照汪暉對五四運動的說法,擁有「態度的同一性」。在1980年代,大家對現代性的想像是同一的,這可以用帕森斯關於現代性的三條鐵律來形容:個人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這就是新的現代性烏托邦,1980年代的啟蒙陣營是建立在這種共同的現代性想像基礎上的。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思想界,可以分為1980年代、1990年代與2000年以來三個階段。1980年代是「啟蒙時代」;1990年代是「啟蒙後時代」,即所謂later enlightenment;2000年以來則是「後啟蒙時代」,這個「後」是post的意思。1980年代之所以是啟蒙時代,乃是有兩場運動: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與中後期的「文化熱」,現在被理解為繼五四以後的「新啟蒙運動」。新啟蒙運動與五四一樣,謳歌人的理性,高揚人的解放,激烈地批判傳統,擁抱西方的現代性。它具備啟蒙時代一切的特徵,充滿著激情、理想與理性,當然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緊張性。
到1990年代,進入了「啟蒙後時代」,或者叫「啟蒙後期」。1980年代啟蒙陣營所形成的「態度的同一性」,在市場社會出現之後,逐漸發生了分化,分裂為各種各樣的「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新左派等等。啟蒙是一個文化現象,最初是非政治的;啟蒙運動的內部混沌一片,包含各種主義的元素。歐洲的啟蒙運動發生在18世紀,也是到19世紀經濟高速增長、階級分化的時候,出現了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化。不過,1990年代的許多基本命題依然是啟蒙的延續,依然是一個「啟蒙後時代」。
2000年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之所以稱之為「後啟蒙時代」,這個post的意思是說:在很多人看來啟蒙已經過時了,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
陳:關於啟蒙,在六四之前,就已經有了不同的意見,像是李澤厚等人認為不需要再談啟蒙了,但王元化仍主張要談。
許:1989年王元化先生談啟蒙的變與不變,所針對的是林毓生先生。那時林先生已經看到了啟蒙的負面,但國內學者還是認為啟蒙是好的。當時他們不贊成林毓生對全盤反傳統的分析。一直到1990年代初以後,大家才開始反思,才注意到啟蒙的負面性。這反思是跟六四有關係的。
陳:林毓生先生所講的創造性轉化,今天有不少人覺得太西化了。但在1980年代,他的觀點卻被認為是太反啟蒙、太反五四、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太友善。您如何理解這個反差?
許: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那些高調反傳統的,對傳統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通過批傳統來批現實中的政治專制主義,就像文革時「批林批孔」也是借批孔而打林一樣。但1980年代老一輩的中國文化書院派,像湯一介、龐樸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有同情性了解的。他們是一批釋古派,通過重新解釋傳統,將傳統與現代化結合起來。他們成為1990年代初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先聲。
儘管1990年代出現了文化保守主義,但他們仍在啟蒙陣營的裡面。他們追求現代性這點是不變的,只是要為普遍現代性在中國找到它的特殊表現,即以儒家為代表的、具有中國特殊性的現代性道路。19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承認普世現代性的;這與近10年出現的以狂批普遍主義為前提的「中國模式」論、「中國道路」論、「中國特殊」論是很不一樣的。
1990年代的保守主義是溫和的,基本是文化保守主義。余英時認為儒教分兩部分:政治儒教已經不適應民主政治,過時了;但心性儒家還有其存在的意義。1990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想把心性儒家與民主政治接軌,即從「老內聖」開出「新外王」。
然而,新儒家中的蔣慶是個極端的個案。他從一開始感興趣的就是政治儒學,不是心性修養的宋明理學,而是漢代董仲舒那套政治意識型態。而且還像康有為那樣,企圖以儒教
許紀霖先生,浙江紹興人,1957年出生於上海。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1977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1982年留校任教。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受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影響,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反思,以及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和知識分子的研究。從「啟蒙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國思想界的分化,並積極介入當代論爭,為大陸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寫有《無窮的困惑》、《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化史》(主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著作。
一、1980年代的啟蒙及其分裂
王超華(以下簡稱「王」):許先生,可否請您先談談您的成長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屆的?
許紀霖(以下簡稱「許」):我1957年出生,在上海長大。文革時我是小學生,紅小兵。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在上海市郊的東海農場。1978年作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考進了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我本科4年畢業後,剛好缺青年教師,所以我就留校了,在任教的期間在職讀碩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時,歲數算是比較小的。
許:我們班上,幾乎全都是「老三屆」,所以我是小字輩。班長與班裡年齡最小的相差15歲,他開玩笑地對他說:「我都可以把你生出來了。」我自己觀察,老三屆的話題總是繞不過文革。關於文革,有三個不同的年齡層,區別在於康有為所說的「所經之事」、「所見之事」和「所聞之事」。對老三屆,文革是「所經之事」。對我這個紅小兵而言是「所見之事」,因為我沒有直接經歷,就算經歷也是很間接的。而對文革後的一代,文革則是「所聞之事」了。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學的時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鄉雖然經歷過,但畢竟經歷有限,沒有很直接的心理衝撞。我覺得跟老三屆相比,自己與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有親和性。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您最初做的是民主黨派研究,大學時代就對這題目感興趣?
許:純屬偶然。念大學時,自己亂看書。畢業留校之後,系裡要我跟著一個老師研究中國民主黨派。我對民主黨派本身沒什麼興趣,但發現那些民主黨派人士不得了,個個都是大知識分子;他們在20世紀前半葉的命運,與當代知識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內心之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我的第一篇稿,寫的是黃遠生。他是民國初年的名記者,袁世凱稱帝時要他幫忙造勢。他非常掙扎,寫完了又很後悔,因此後來寫了《懺悔錄》,懺悔自己的一生。我看了很有感受,就寫了一篇〈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王焱是《讀書》的編輯部主任,竟然把我這個無名之輩的處女作發了出來,給我很大的鼓勵。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我寫了二、三十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個案研究的文章。
那些個案我稱之為「心態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態史研究」提升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從個案出發,提煉出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就像以賽亞‧柏林和別爾嘉耶夫對俄國知識分子的研究。
王:您為何認為大學的經歷是最重要的?
許:1980年代大學的氛圍,與現在完全不一樣。當時私人空間很少,連談戀愛都很拘束,與女同學稍為接觸多一點,支部書記就會來干預。但1980年代校園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躍:競選人大代表、模擬審判、討論國家大事、上街遊行等等,熱鬧極了。1980年代有一種後文革的氛圍,文革中的紅衛兵精神轉化為一種「後理想主義」,從「奉旨造反」轉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開放。1980年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大視野、大思路、大氣魄,這種精神對我影響很深。
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父與子兩代人。父親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比如赫爾岑、屠格涅夫,既有懷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內涵而沒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動猶豫。兒子一代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識分子,他們的信念很簡單,為一個簡單的主義奮鬥,非常有行動力;但他們有力量而沒有內涵,堅信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當代中國兩代知識分子似乎剛好倒過來。像我們這些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輕信而行動力強;我們都是行動主義者,總是要有一個信念,都喜歡大問題,具有實踐性,而這恐怕都與文革的紅衛兵精神有關。而1990年代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比如我的學生一代,書讀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國父親那代,常常有一種無力感;他們在虛無主義的環境中生長,經常懷疑行動的功效與意義,成為遊移不定的「多餘的人」。
陳:您怎麼看1980年代跟文革的關係?
許:像我們這些1980年代人,總是從大處著眼,總是在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大問題,胸懷責任感,而且有所行動。如果我們把毛澤東時代看作一種紅色宗教,類似革命烏托邦的宗教時代,具有一種神聖性,那麼1980年代不過是這神聖性的世俗版。1980年代去掉了毛的神聖性,但重新賦予啟蒙、現代化以某種神魅性。中國真正的世俗化要到1990年代之後才完全展開。在中國,1960-70年代生的人還多少受到1980年代的精神洗禮;但「80後」一代則完全在1990年代之後的世俗化環境下成長起來,在文化性格上是全新的一代人,與1980年代開始格格不入。這個新,一個是世俗化,另一個就是虛無主義。
陳:您如何看待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以及1990年代以後的變化?
許:傅柯講過,啟蒙是一種態度。1980年代的啟蒙,按照汪暉對五四運動的說法,擁有「態度的同一性」。在1980年代,大家對現代性的想像是同一的,這可以用帕森斯關於現代性的三條鐵律來形容:個人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這就是新的現代性烏托邦,1980年代的啟蒙陣營是建立在這種共同的現代性想像基礎上的。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思想界,可以分為1980年代、1990年代與2000年以來三個階段。1980年代是「啟蒙時代」;1990年代是「啟蒙後時代」,即所謂later enlightenment;2000年以來則是「後啟蒙時代」,這個「後」是post的意思。1980年代之所以是啟蒙時代,乃是有兩場運動: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與中後期的「文化熱」,現在被理解為繼五四以後的「新啟蒙運動」。新啟蒙運動與五四一樣,謳歌人的理性,高揚人的解放,激烈地批判傳統,擁抱西方的現代性。它具備啟蒙時代一切的特徵,充滿著激情、理想與理性,當然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緊張性。
到1990年代,進入了「啟蒙後時代」,或者叫「啟蒙後期」。1980年代啟蒙陣營所形成的「態度的同一性」,在市場社會出現之後,逐漸發生了分化,分裂為各種各樣的「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新左派等等。啟蒙是一個文化現象,最初是非政治的;啟蒙運動的內部混沌一片,包含各種主義的元素。歐洲的啟蒙運動發生在18世紀,也是到19世紀經濟高速增長、階級分化的時候,出現了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化。不過,1990年代的許多基本命題依然是啟蒙的延續,依然是一個「啟蒙後時代」。
2000年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之所以稱之為「後啟蒙時代」,這個post的意思是說:在很多人看來啟蒙已經過時了,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
陳:關於啟蒙,在六四之前,就已經有了不同的意見,像是李澤厚等人認為不需要再談啟蒙了,但王元化仍主張要談。
許:1989年王元化先生談啟蒙的變與不變,所針對的是林毓生先生。那時林先生已經看到了啟蒙的負面,但國內學者還是認為啟蒙是好的。當時他們不贊成林毓生對全盤反傳統的分析。一直到1990年代初以後,大家才開始反思,才注意到啟蒙的負面性。這反思是跟六四有關係的。
陳:林毓生先生所講的創造性轉化,今天有不少人覺得太西化了。但在1980年代,他的觀點卻被認為是太反啟蒙、太反五四、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太友善。您如何理解這個反差?
許: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那些高調反傳統的,對傳統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通過批傳統來批現實中的政治專制主義,就像文革時「批林批孔」也是借批孔而打林一樣。但1980年代老一輩的中國文化書院派,像湯一介、龐樸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有同情性了解的。他們是一批釋古派,通過重新解釋傳統,將傳統與現代化結合起來。他們成為1990年代初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先聲。
儘管1990年代出現了文化保守主義,但他們仍在啟蒙陣營的裡面。他們追求現代性這點是不變的,只是要為普遍現代性在中國找到它的特殊表現,即以儒家為代表的、具有中國特殊性的現代性道路。19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承認普世現代性的;這與近10年出現的以狂批普遍主義為前提的「中國模式」論、「中國道路」論、「中國特殊」論是很不一樣的。
1990年代的保守主義是溫和的,基本是文化保守主義。余英時認為儒教分兩部分:政治儒教已經不適應民主政治,過時了;但心性儒家還有其存在的意義。1990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想把心性儒家與民主政治接軌,即從「老內聖」開出「新外王」。
然而,新儒家中的蔣慶是個極端的個案。他從一開始感興趣的就是政治儒學,不是心性修養的宋明理學,而是漢代董仲舒那套政治意識型態。而且還像康有為那樣,企圖以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