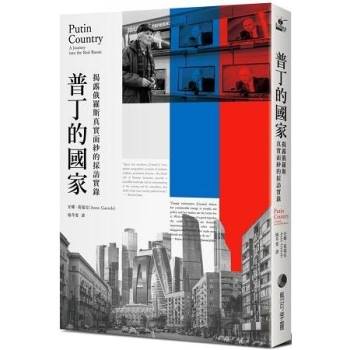第三章 認同
我對於被逐出車里雅賓斯克感到絕望,伴隨隱約指控我是一名間諜,那代表我數十年來的俄羅斯旅行已到盡頭。可是我驚訝地發現,我仍舊拿到簽證。驚奇還沒完,我的仇敵移民局局長謝爾蓋.里阿札諾夫稍後遭到逮捕,理由是「大規模」收賄。結果我得以跟在車里雅賓斯克認識的人保持聯繫,包括一位三十多歲的雜誌編輯伊黎娜.寇蘇諾娃(Irina Korsunova)。我回到車里雅賓斯克時,我們在她的辦公室碰面,吃著壽司和披薩。她穿著剪裁優雅的棕色洋裝和造型時髦的長靴,在一本同等體面的雜誌擔任編輯。拿地方政府的補助,這本雜誌把車里雅賓斯克介紹給潛在投資人,對城市投以炫目燈光。當你翻閱雜誌頁面時,你會得到置身於柏林的印象,而非一座困頓、腐敗的俄國工業城市。不過城市裡僅有一小撮人負擔得起雜誌介紹的生活方式,伊黎娜只想看見此地最好的那面。她相信俄國曾經是,也能再度成為世人的典範,西方的批評僅僅反映了他們想見到俄國重新屈膝遵從。儘管目前面臨諸多問題,她預期俄國憑藉國內的天然資源、遼闊土地和人才,將會再次成為完全自立的國家。
跟她談話會遭遇到猛烈防備和諸多自相矛盾,而那正是重點。俄國人正試圖釐清他們是誰,以及他們要從何處與世界接合。他們擁抱大部分的西方文化,並選擇性否認什麼不切合正式的「俄羅斯」模式,這鮮少說得通。
從一個層面看來,伊黎娜西方得不得了。她母親迅速利用對西方的開放,躍升為成功的女商人,且把伊黎娜送往一所上流階層的瑞士精修學校(finishing school)。伊黎娜的旅行足跡廣闊。她身穿最精緻的歐洲服飾,嫁給一位事業有成的工程師。她是堅定的中產階級,她的兒子如今得以獲取眾多西方消費商品和科技,這些在她的蘇聯童年從未擁有過,對此她感到快樂。
即使如此,伊黎娜對西方心懷憎惡、幾近忿恨。她是一個驕傲的俄國人,堅定相信俄國把最好的帶給世人,卻鮮少得到回報。她也相信蘇聯-俄國的研究替日本的商業和科技打下基礎。她說中國體育如今躋身世界強權,原因是基於蘇聯的運動技巧。她懊悔蘇聯解體,並責怪西方引進的貪汙摧毀了她國家最好的部分。她代表了我在車里雅賓斯克認識的許多人,他們厭倦了一再受到打擊。他們厭倦了國家被視為僅僅是黑幫滿街的竊盜統治(kleptocracy)──即使他們身為埋怨貪腐的先聲。他們厭倦了西方一再因為蘇聯的罪過打擊俄國人,尤其是現在他們知悉了更多西方的罪過。
在欠缺國家意志下,俄國人習於責怪外人,而非解決手頭上的議題。在過去,俄國人面臨入侵敵人時,展現過他們最強悍的一面:十八世紀的瑞典、十九世紀的拿破崙,或是一九四一年的德國人。今日的政府、教堂和國營媒體合力對付一個更難捉摸的敵人,即「外國支配」。這些強大勢力有效植入懷疑論點,認為美國-西方陰謀削弱較為衰敗的俄羅斯。
俄國人對他們在世界上正當位置的信念,根植於他們動亂的歷史──車里雅賓斯克熟知的一段苦難、驕傲和矛盾歷史。這座城市在十八世紀建立,做為軍事要塞,當時沙皇軍隊開拔至未知的大陸東部,朝西伯利亞和太平洋前行。沙皇軍隊從世居當地的巴什基爾人(Bashkirs)和韃靼人(Tatars)手裡徵收土地所有權,他們本是遊牧的穆斯林牧人。費心記錄這些事件的本地歷史學者弗拉基米爾.波士(Vladimir Bozhe),拿它們來比擬美國西部的血腥征服占領。我遇見的大部分俄國人從未聽聞土地徵用,或者否認這種事發生過,即使受過教育的人也是如此。
在十九世紀,車里雅賓斯克成為貿易中心,連通正在擴張的俄羅斯帝國與中國。舊時商人擁有的兩層樓木造房屋遺跡,依然星散於市中心。這些精細刻上薑餅糕點的木屋,其中有些已重建,但是大多腐朽不堪、屋頂陷落,等待遭受無可避免的土地侵占。俄羅斯的東正教會旋即跟著軍隊前哨站而來,洋蔥狀圓頂聳立的修道院建物蔓生開來,逐漸支配這座成長中的小鎮。此情此景只有留下照片紀錄,因為廣闊的修道院隨後被史達林的黨羽拆除,改成一片空涼的閱兵廣場,仍然樹立著一座大型列寧塑像增添光采。
那是一段繁榮與蕭條跌宕起伏的故事。在十九世紀晚期,鐵路開通直往西伯利亞,人口從七千五百人迅速成長至七萬五千人。儘管嚴格說來,猶太商人禁止住在某些指定的俄國區域之外,擴展的生意機會吸引他們搬到此地。他們填補了需求,得到極大寬容。一座猶太教堂於一九○五年建成。然而不久後,一場革命席捲而來。
一九一七年革命與後續的內戰使發展踩下煞車。新的蘇維埃當局一再充公地區收成,而大規模饑荒襲來。歷史學者弗拉基米爾.波士估計,車里雅賓斯克地區有成千上萬人死去,大幅削減本地人口。當地對宗教的打壓比其他許多地方更為嚴厲,儘管蘇聯法律規定每種教派在一個社區可以有一座禮拜場所,車里雅賓斯克地區僅餘一座東正教會,而清真寺、猶太教堂和其他基督教派的教堂統統要停止運作。本地蘇維埃領導人驕傲地宣稱,車里雅賓斯克會是一座「不信神」的城市。
莫斯科接著決定這個地區要成為工業中心,原因是本地的礦產和蘊藏量,但是勞工人力不足。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必須尋找大批工人和專家以實現莫斯科的計畫,包括擴展與建立冶煉和化學廠,以及龐大的拖拉機和坦克車新工廠,這是史達林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核心。送往本地的許多人是受到看管的政治犯,其他人是kulaks──俗稱的富農地主──他們被剝奪了微薄的財產,遭囚禁或放逐。
到了一九四一年與德國開戰,更多囚犯被送到這裡工作,這次是已住在蘇聯好幾代的德裔公民,卻遭懷疑為潛在的間諜。歷史學者伊蓮娜.圖洛娃(Elena Turova)採用終於在一九九○年代公開的檔案,記錄被送往車里雅賓斯克的三萬八千名德裔蘇聯人:「他們(譯按:指蘇聯當局)在嚴冬時節把他們帶來,並扔在空地裡,他們開始朝地下挖掘一個棲身之地,與此同時他們必須建造冶煉廠。」她記得看到一張年輕男孩的資料卡片,他因為沒完成當日「勞動定額」遭到槍殺。由於懲處、寒冷、飢餓和生病,死亡率居高不下。「當他們死去,他們(譯按:指蘇聯當局)只是送更多放逐者過來,這些人一開始先送去了西伯利亞和哈薩克。起初是男人,接著是青少年,接著是女人,孩子留給誰照顧只有天知道。」
莫斯科和本地政府並未資助圖洛娃周到而費力的資料彙編。資金來自德國,當時是較為開放的一九九○年代與二十一世紀最初幾年。當圖洛娃從發黃而詳盡的史達林時代檔案夾裡,把資料轉錄至電腦資料庫時,她常感到身體不適。她產生矛盾的情緒:對她的政府的殘忍感到驚恐,卻仍然對她國人建立軍武工業且擊退希特勒的能力感到驕傲。而檢視新近公開的檔案時,她發現自己的祖父在一九三一年遭到槍斃。根據這些文件,有人聽見她祖父吟唱被視為反蘇聯的某種歌謠。他遭人帶走,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圖洛娃的母親未曾提過他,惟恐家人因他遭控「叛國」而背上汙名。
城市中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這些過去的隱情可供述說。但是在一九九○年代常外顯的憤怒已趨於淡薄。俄國人現在被灌輸要無視於殺戮,專注於史達林時代的國家發展和艱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這傳達的訊息很明顯,認為結果可以替手段辯護。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志工蒐集打壓下受害者的資料,希望替他們求得補償,如今同一群志工說「我們活在陰影之下」。許多人是「紀念」(Memorial)的成員,那是一個歷史和人權組織,致力於防止極權主義回歸。在普丁政權下組織受到攻擊,一位領導成員說,「紀念」受到普丁政權攻擊,原因是「組織在普丁主義下站在錯的一邊,確切來說,在於普丁主義認為史達林和蘇聯政權成功打造一個偉大的國家」。『紀念』已關閉車里雅賓斯克的辦公室。
不過回到歷史層面。在戰爭物資方面,車里雅賓斯克位於中心位置,戰時人口呈現爆炸增長。靠近前線的工人和軍備廠搬到本地,遠離希特勒空軍的轟炸範圍。有一陣子,車里雅賓斯克自傲地以Tankograd(坦克城)為人所知,而身處最簡陋條件下的工人製造出一萬八千輛坦克車,將近五萬部坦克車柴油引擎,以及超過一千七百萬發子彈。到了冷戰期間,史達林則選擇此地來發展他的祕密核武計畫。
***
做為核能軍工業據點,車里雅賓斯克禁止所有外國人進入,聲望與孤立雙雙隨之而來。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的死亡,帶來穩定表象的開端:恐怖時期的終結,且對於夜間失蹤和飢餓的畏懼終於消減。生活條件──許多工人的住房僅僅比地下防空洞或者擁擠磚造公社略好一些──改善了。蘇聯發展核子武器以抗衡美國,他們把第一個人送上太空。長久以來國家終於得到和平,儘管是冷戰時期的和平。克里姆林宮承諾要「趕上且勝過」西方。然而不景氣逐漸到來,由於企業效率低落耗費的成本、欠缺經濟誘因,加上蘇聯的帝國雄心及其在如阿富汗等地扶植勢力,使財庫竭盡。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這個國家瀕臨破產的態勢明朗。挨餓再一次成為真確的恐懼。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力抗上述挑戰,不過他提倡的更加「開放」、公眾示威抗議、擁有更多新聞自由的媒體和更公平的選舉並不足以團結蘇聯。他最大的挑戰者是剛當選的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而俄羅斯屬於蘇聯的其中一個共和國。在一九九○年,葉爾欽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總統密謀,要以鬆散且無實權的聯盟取代蘇聯。
當時與其後的發展,在許多方面構成了今日西方面臨危機的核心。當西方眾人慶賀蘇聯的末日,十五個共和國裡的大多數成員,包括俄羅斯,還並未準備好利用成為新獨立國家後意外獲得的自由和經濟挑戰。葉爾欽和俄羅斯政府裡掌權的「自由派」,無法抗拒藉由貪汙手段來快速致富。當西方支持的眾多非政府組織提倡有益專案和公民社會的參與,到頭來外國人卻被責怪保護且鼓勵貪汙官員。俄國人逐漸相信外國人是在企圖破壞國家根基。
這類想法依然普遍──如同拜訪伊黎娜一趟對我的提醒。在如此一個大國裡,她說,民主並不總是好的;過度的自由將會導致無政府狀態。她希望俄羅斯東正教會發揮其父權、團結與愛國的影響力。本地的眾多穆斯林人口會如何看待這件事,她毫不在意,然而她抱持著有點浪漫的想法,認為在昔日蘇聯,國內多種民族快樂共處。
總統普丁迎合像她這樣的人們。他在二○一四年接管克里米亞,及隨後捍衛烏克蘭的俄語區,使他委靡的支持率提升至超過百分之八十的高檔。他宣示的俄國優越精神,勝過了西方的個人主義、衰退和表裡不一。當這一切發揮作用,他支持東正教會是俄國唯一真正信仰的主張,且為俄國通往偉大之路的源頭。他要求中學統一歷史課本,「消除內部矛盾與分歧」──拿任何國家的歷史來說均屬挑戰,尤其是俄國的歷史。在我書寫的當下,召集委員會未能提出經核可的課本。
車里雅賓斯克國立大學的歷史學年輕教授亞歷山大.福金(Alexandr Fokin)說,學術界被要求去辨識出獨特的俄國特性,只偏重在好的那一面。他說這同時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以及對歷史的曲解。儘管如此,國族主義者和所謂的愛國人士施加影響力,箝制他所能研究的與在課堂上所能傳授的內容。車里雅賓斯克還沒像鄰近城市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的情況那麼壞,普丁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青年側翼,在那裡公開點名他們指認為叛國者的教授。對於車里雅賓斯克大學裡膽敢挑戰政府的那些人,僅在網路上遭受到匿名攻擊。
聯邦安全局正企圖重新定義叛國罪的概念,意在囊括「對外國或國際組織提供財務、科技、顧問或其他協助,導致傷害俄國安全」。在一場國際會議前,福金接到他的大學告知,他必須簽署一份文件以確認他拒絕向外國同行透露祕密,即使如今什麼算是祕密全憑個人猜測。大學的表格上包括一條命令,要求與會者不透露有可能「導致俄國損傷」的任何事。他在臉書上發文諷刺,開頭是「我的祖國又一次管束我的歡愉」。全國學術界同事的回應反映出類似擔憂──而許多人說著「歡迎重返蘇聯」。
取得政府檔案文件變得愈來愈困難,而官員說最好別提出令人不快的問題。在「開放」盛世一九九○年代見光的檔案,又遭受封藏命運。缺少特別核可,就無法獲取當下視為敏感的檔案,而核可發下時裡頭可能同時包括國外旅遊限令,這是多數人希望避免的限制。當然了,外國研究者面對的問題甚至更大,現在需要取得國家安全機構的放行批准。何其幸運,我在這波完全管制前見過幾位本地歷史學者和檔案管理人。要是我現在試圖跟他們見面,他們會帶著莫大遺憾說,他們沒有選擇,只能拒絕。
雖然俄國人對西方的懷疑常不切實,且受到政府的自私操弄,但他們並非毫無根據。早在一九九二年,喬治.H.W.布希總統於國情咨文演說時宣稱,「蒙上帝恩典,美國贏得了冷戰」。但是蘇聯解體時期的美國大使傑克.麥洛克(Jack Matlock)主張,冷戰結束並不是勝利;它是細緻的協商議定,理應惠及每一方且保證未來的合作。根據麥洛克所言,美國太常把新的俄羅斯視為輸家,形塑受辱與復仇的情感。儘管麥洛克並非普丁的擁護者,但他敢於主張對俄國和俄國人缺乏理解,可能會不必要地導致酷寒冷戰,以及核武競賽的重啟。
從來不曾有任何具體承諾說西方不會擴張北約,然而的確存在著誓言,不在俄國的弱點上占便宜。在那之後,俄國人尤其相信美國已經這麼做了。俄國人絮絮叨叨的擔憂之中,包括冷戰結束後北約擴張進入東歐。然後發生了北約在未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准許下轟炸塞爾維亞,這個與俄國同為斯拉夫民族與東正教會的國家;允許科索沃自塞爾維亞獨立,儘管美國在其他的情況下均支持領土主權;以及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並威脅要在前華沙公約國家部署防衛飛彈。俄國人也提到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未批准下入侵伊拉克;美國涉入在他們眼裡站不住腳的烏克蘭、喬治亞和吉爾吉斯民主革命,以及北約擴展進入喬治亞和烏克蘭的言論,兩地均與俄羅斯接壤。
西方許多人以及俄國的某些人爭論這一切,認為真正的問題是莫斯科變得益發極權主義,且回復它的帝國舊夢。由於俄國的經濟挑戰與未能現代化,他們主張,普丁向國外找敵人以掩飾自家的問題。
二○一四年,普丁找到他尋尋覓覓的敵人。美國支持的烏克蘭反對黨推翻與俄國友好的總統後,緊張態勢高漲。烏克蘭國會起草一項法案,撤銷俄語的官方語言地位,而當法案遭到否決時,普丁已經準備好要動搖新任政府。
首先他併吞克里米亞,一座伸入黑海的半島,在歷史上隸屬於俄羅斯,於一九五四年併入烏克蘭。當俄國和烏克蘭同屬於一個國家,這個舉動主要是象徵性的;然而一旦兩國分道揚鑣,克里米亞的地位形同創傷。在戰略上具關鍵地位的克里米亞,擁有壓倒性的俄國人口。莫斯科被迫要為黑海艦隊租借設施,且持續面臨租約會被撤銷的威脅。這成為微微發亮的閃火點,且當俄國認定基輔(Kiev) 在美國支持下,變得較不站在俄國的利益這一邊時,即迅速行動。接管克里米亞後,普丁把武器和軍隊送往烏克蘭東部工業區,做為尋求更大程度自治或分離的俄語人口的後盾。
我立即收到車里雅賓斯克聯絡人的激昂電子郵件,他們大多數人譴責西方的制裁並支持普丁。許多人有親戚在烏克蘭東部,在完全仰賴俄國市場的工廠和礦場裡工作。他們惟恐烏克蘭往歐洲靠攏,會使他們的親人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陷入困境。
擁護普丁的、尤其是支持接管克里米亞的那群人,組成分子範圍廣得驚人,包括一度自稱為「反對者」的人們。接下來稱為V的一位本地精英階層成員,比起像伊黎娜.寇蘇諾娃那樣的激烈俄羅斯國族主義者,他務實得多,他對克里米亞表示贊同。然而他認為普丁干預烏克蘭東部是場災難,他責怪普丁和歐巴馬總統都對放這把火有責任。在他看來,美國插手烏克蘭的舉止愚蠢,完全沒注意到情勢有多麼一觸即發。在他眼中,美國支持了對抗一位民選總統的政變。
論及的這位總統或許貪腐且令人憎惡,但如此行徑僅僅強化美國說一套、做一套的觀點。他說美國需要了解,烏克蘭對俄國具有「存在上的重要性」。對他來說,少了俄國的烏克蘭經濟顯然無法健全,那是他認為美國未能理解的另一件事。「西方真的準備要資助一個貪腐、破敗的國家嗎?」他問道。對於雙方未能尋求外交途徑解決危機,他感到沮喪。如同大多數俄國人,他主張僵局至少有部分成因來自美國在歐洲延續的安全體系,植基於許久以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不必要地孤立俄國,且不再適合今日的世界。熟知美國時事,他的小孩在那裡讀書,且讚賞他在美國目睹的許多事,V仍然驚異於美國的無知與傲慢,對於華府輕易譴責俄國犯下他相信美國同樣觸犯的罪責,感到氣憤不已。
V在一間高級餐廳裡,以及伊黎娜.寇蘇諾娃在雜誌辦公室發表的看法,在鎔鑄的高熱中強化。尤拉.柯瓦克(Yura Kovach)是車里雅賓斯克一間鋼鐵工廠的員工,也是我結識超過二十年的朋友,儘管他對普丁愈來愈強烈的支持,有時會使我們的關係緊張。我們透過他的妻子伊黎娜認識,她是一位受挫的蘇聯經濟學家,原本在一九九○年代有過榮景。她建立了一檔早期的股票型基金,也有保護退休金領取人的作用;她組織起一群鋼鐵工人,使他們隨即獲得賺錢的合約,替新建築物打造裝飾的圍欄和樓梯欄杆。在她的丈夫,一位擁有專業技術的工程師失去收入時,她賺到錢。但這導致婚姻問題。在那之後她結束生意,搖身一變為一位心理學家,因過度疲勞,隨後留在家裡好幾年照顧病危的母親。一路走來,她成為一位印度教導師的虔誠學生,獻身於冥想。她改吃素,創立且失去豆腐生意──原因並非缺乏需求,而是政府的地產操弄。她接著投入外匯市場,試圖補救債務。他們四十年的婚姻遭受嚴重考驗;他們的生活方式分歧,但是他們留在彼此身邊且贊同一件事──普丁是俄國最好的領導人。尤拉看著他的行業落居於新興的銀行家、貿易商和公關專員之後。當普丁在二○一○至二○一二年間稱呼莫斯科的抗議者「只是辦公室的浮游生物」,他鼓掌叫好。他介紹我認識一位受歡迎的勞工詩人,名叫伊果.拉斯特耶夫(Igor Rasteryaev),他喊北約是「垃圾」,還讚揚「不吃壽司或不上日光浴美容院」的那些人。柯瓦克一家人不上館子吃飯,也不去國外度假。
在網路上瀏覽新聞的尤拉,相信美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暗地裡支持莫斯科的反普丁示威,以及烏克蘭的反對黨抗議者。他不相信美國會容忍俄國對其國內事務或者利益範圍,做出類似的干預。如同眾多俄國人,現在他說當美國在捍衛國際利益時,自己適用一套規則,而對俄國是另一套。
當 我詢問,是否普丁和他的貪汙富商小圈子適用一套規則,而全國其他人適用另一套時,他自有藉口。他說到處都有貪汙,忽視俄國在國際評比上名列貪汙最烈的其中 一個國家。他擁戴普丁的聰明和能力,把他看作將會重建國家的工業和國際地位的人。他擋下我拋向他所有對普丁的批評,包括用一句俄國人的諺語回應:「起火的 時候,不要問誰是救火員。」
我對於被逐出車里雅賓斯克感到絕望,伴隨隱約指控我是一名間諜,那代表我數十年來的俄羅斯旅行已到盡頭。可是我驚訝地發現,我仍舊拿到簽證。驚奇還沒完,我的仇敵移民局局長謝爾蓋.里阿札諾夫稍後遭到逮捕,理由是「大規模」收賄。結果我得以跟在車里雅賓斯克認識的人保持聯繫,包括一位三十多歲的雜誌編輯伊黎娜.寇蘇諾娃(Irina Korsunova)。我回到車里雅賓斯克時,我們在她的辦公室碰面,吃著壽司和披薩。她穿著剪裁優雅的棕色洋裝和造型時髦的長靴,在一本同等體面的雜誌擔任編輯。拿地方政府的補助,這本雜誌把車里雅賓斯克介紹給潛在投資人,對城市投以炫目燈光。當你翻閱雜誌頁面時,你會得到置身於柏林的印象,而非一座困頓、腐敗的俄國工業城市。不過城市裡僅有一小撮人負擔得起雜誌介紹的生活方式,伊黎娜只想看見此地最好的那面。她相信俄國曾經是,也能再度成為世人的典範,西方的批評僅僅反映了他們想見到俄國重新屈膝遵從。儘管目前面臨諸多問題,她預期俄國憑藉國內的天然資源、遼闊土地和人才,將會再次成為完全自立的國家。
跟她談話會遭遇到猛烈防備和諸多自相矛盾,而那正是重點。俄國人正試圖釐清他們是誰,以及他們要從何處與世界接合。他們擁抱大部分的西方文化,並選擇性否認什麼不切合正式的「俄羅斯」模式,這鮮少說得通。
從一個層面看來,伊黎娜西方得不得了。她母親迅速利用對西方的開放,躍升為成功的女商人,且把伊黎娜送往一所上流階層的瑞士精修學校(finishing school)。伊黎娜的旅行足跡廣闊。她身穿最精緻的歐洲服飾,嫁給一位事業有成的工程師。她是堅定的中產階級,她的兒子如今得以獲取眾多西方消費商品和科技,這些在她的蘇聯童年從未擁有過,對此她感到快樂。
即使如此,伊黎娜對西方心懷憎惡、幾近忿恨。她是一個驕傲的俄國人,堅定相信俄國把最好的帶給世人,卻鮮少得到回報。她也相信蘇聯-俄國的研究替日本的商業和科技打下基礎。她說中國體育如今躋身世界強權,原因是基於蘇聯的運動技巧。她懊悔蘇聯解體,並責怪西方引進的貪汙摧毀了她國家最好的部分。她代表了我在車里雅賓斯克認識的許多人,他們厭倦了一再受到打擊。他們厭倦了國家被視為僅僅是黑幫滿街的竊盜統治(kleptocracy)──即使他們身為埋怨貪腐的先聲。他們厭倦了西方一再因為蘇聯的罪過打擊俄國人,尤其是現在他們知悉了更多西方的罪過。
在欠缺國家意志下,俄國人習於責怪外人,而非解決手頭上的議題。在過去,俄國人面臨入侵敵人時,展現過他們最強悍的一面:十八世紀的瑞典、十九世紀的拿破崙,或是一九四一年的德國人。今日的政府、教堂和國營媒體合力對付一個更難捉摸的敵人,即「外國支配」。這些強大勢力有效植入懷疑論點,認為美國-西方陰謀削弱較為衰敗的俄羅斯。
俄國人對他們在世界上正當位置的信念,根植於他們動亂的歷史──車里雅賓斯克熟知的一段苦難、驕傲和矛盾歷史。這座城市在十八世紀建立,做為軍事要塞,當時沙皇軍隊開拔至未知的大陸東部,朝西伯利亞和太平洋前行。沙皇軍隊從世居當地的巴什基爾人(Bashkirs)和韃靼人(Tatars)手裡徵收土地所有權,他們本是遊牧的穆斯林牧人。費心記錄這些事件的本地歷史學者弗拉基米爾.波士(Vladimir Bozhe),拿它們來比擬美國西部的血腥征服占領。我遇見的大部分俄國人從未聽聞土地徵用,或者否認這種事發生過,即使受過教育的人也是如此。
在十九世紀,車里雅賓斯克成為貿易中心,連通正在擴張的俄羅斯帝國與中國。舊時商人擁有的兩層樓木造房屋遺跡,依然星散於市中心。這些精細刻上薑餅糕點的木屋,其中有些已重建,但是大多腐朽不堪、屋頂陷落,等待遭受無可避免的土地侵占。俄羅斯的東正教會旋即跟著軍隊前哨站而來,洋蔥狀圓頂聳立的修道院建物蔓生開來,逐漸支配這座成長中的小鎮。此情此景只有留下照片紀錄,因為廣闊的修道院隨後被史達林的黨羽拆除,改成一片空涼的閱兵廣場,仍然樹立著一座大型列寧塑像增添光采。
那是一段繁榮與蕭條跌宕起伏的故事。在十九世紀晚期,鐵路開通直往西伯利亞,人口從七千五百人迅速成長至七萬五千人。儘管嚴格說來,猶太商人禁止住在某些指定的俄國區域之外,擴展的生意機會吸引他們搬到此地。他們填補了需求,得到極大寬容。一座猶太教堂於一九○五年建成。然而不久後,一場革命席捲而來。
一九一七年革命與後續的內戰使發展踩下煞車。新的蘇維埃當局一再充公地區收成,而大規模饑荒襲來。歷史學者弗拉基米爾.波士估計,車里雅賓斯克地區有成千上萬人死去,大幅削減本地人口。當地對宗教的打壓比其他許多地方更為嚴厲,儘管蘇聯法律規定每種教派在一個社區可以有一座禮拜場所,車里雅賓斯克地區僅餘一座東正教會,而清真寺、猶太教堂和其他基督教派的教堂統統要停止運作。本地蘇維埃領導人驕傲地宣稱,車里雅賓斯克會是一座「不信神」的城市。
莫斯科接著決定這個地區要成為工業中心,原因是本地的礦產和蘊藏量,但是勞工人力不足。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必須尋找大批工人和專家以實現莫斯科的計畫,包括擴展與建立冶煉和化學廠,以及龐大的拖拉機和坦克車新工廠,這是史達林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核心。送往本地的許多人是受到看管的政治犯,其他人是kulaks──俗稱的富農地主──他們被剝奪了微薄的財產,遭囚禁或放逐。
到了一九四一年與德國開戰,更多囚犯被送到這裡工作,這次是已住在蘇聯好幾代的德裔公民,卻遭懷疑為潛在的間諜。歷史學者伊蓮娜.圖洛娃(Elena Turova)採用終於在一九九○年代公開的檔案,記錄被送往車里雅賓斯克的三萬八千名德裔蘇聯人:「他們(譯按:指蘇聯當局)在嚴冬時節把他們帶來,並扔在空地裡,他們開始朝地下挖掘一個棲身之地,與此同時他們必須建造冶煉廠。」她記得看到一張年輕男孩的資料卡片,他因為沒完成當日「勞動定額」遭到槍殺。由於懲處、寒冷、飢餓和生病,死亡率居高不下。「當他們死去,他們(譯按:指蘇聯當局)只是送更多放逐者過來,這些人一開始先送去了西伯利亞和哈薩克。起初是男人,接著是青少年,接著是女人,孩子留給誰照顧只有天知道。」
莫斯科和本地政府並未資助圖洛娃周到而費力的資料彙編。資金來自德國,當時是較為開放的一九九○年代與二十一世紀最初幾年。當圖洛娃從發黃而詳盡的史達林時代檔案夾裡,把資料轉錄至電腦資料庫時,她常感到身體不適。她產生矛盾的情緒:對她的政府的殘忍感到驚恐,卻仍然對她國人建立軍武工業且擊退希特勒的能力感到驕傲。而檢視新近公開的檔案時,她發現自己的祖父在一九三一年遭到槍斃。根據這些文件,有人聽見她祖父吟唱被視為反蘇聯的某種歌謠。他遭人帶走,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圖洛娃的母親未曾提過他,惟恐家人因他遭控「叛國」而背上汙名。
城市中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這些過去的隱情可供述說。但是在一九九○年代常外顯的憤怒已趨於淡薄。俄國人現在被灌輸要無視於殺戮,專注於史達林時代的國家發展和艱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這傳達的訊息很明顯,認為結果可以替手段辯護。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志工蒐集打壓下受害者的資料,希望替他們求得補償,如今同一群志工說「我們活在陰影之下」。許多人是「紀念」(Memorial)的成員,那是一個歷史和人權組織,致力於防止極權主義回歸。在普丁政權下組織受到攻擊,一位領導成員說,「紀念」受到普丁政權攻擊,原因是「組織在普丁主義下站在錯的一邊,確切來說,在於普丁主義認為史達林和蘇聯政權成功打造一個偉大的國家」。『紀念』已關閉車里雅賓斯克的辦公室。
不過回到歷史層面。在戰爭物資方面,車里雅賓斯克位於中心位置,戰時人口呈現爆炸增長。靠近前線的工人和軍備廠搬到本地,遠離希特勒空軍的轟炸範圍。有一陣子,車里雅賓斯克自傲地以Tankograd(坦克城)為人所知,而身處最簡陋條件下的工人製造出一萬八千輛坦克車,將近五萬部坦克車柴油引擎,以及超過一千七百萬發子彈。到了冷戰期間,史達林則選擇此地來發展他的祕密核武計畫。
***
做為核能軍工業據點,車里雅賓斯克禁止所有外國人進入,聲望與孤立雙雙隨之而來。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的死亡,帶來穩定表象的開端:恐怖時期的終結,且對於夜間失蹤和飢餓的畏懼終於消減。生活條件──許多工人的住房僅僅比地下防空洞或者擁擠磚造公社略好一些──改善了。蘇聯發展核子武器以抗衡美國,他們把第一個人送上太空。長久以來國家終於得到和平,儘管是冷戰時期的和平。克里姆林宮承諾要「趕上且勝過」西方。然而不景氣逐漸到來,由於企業效率低落耗費的成本、欠缺經濟誘因,加上蘇聯的帝國雄心及其在如阿富汗等地扶植勢力,使財庫竭盡。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這個國家瀕臨破產的態勢明朗。挨餓再一次成為真確的恐懼。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力抗上述挑戰,不過他提倡的更加「開放」、公眾示威抗議、擁有更多新聞自由的媒體和更公平的選舉並不足以團結蘇聯。他最大的挑戰者是剛當選的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而俄羅斯屬於蘇聯的其中一個共和國。在一九九○年,葉爾欽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總統密謀,要以鬆散且無實權的聯盟取代蘇聯。
當時與其後的發展,在許多方面構成了今日西方面臨危機的核心。當西方眾人慶賀蘇聯的末日,十五個共和國裡的大多數成員,包括俄羅斯,還並未準備好利用成為新獨立國家後意外獲得的自由和經濟挑戰。葉爾欽和俄羅斯政府裡掌權的「自由派」,無法抗拒藉由貪汙手段來快速致富。當西方支持的眾多非政府組織提倡有益專案和公民社會的參與,到頭來外國人卻被責怪保護且鼓勵貪汙官員。俄國人逐漸相信外國人是在企圖破壞國家根基。
這類想法依然普遍──如同拜訪伊黎娜一趟對我的提醒。在如此一個大國裡,她說,民主並不總是好的;過度的自由將會導致無政府狀態。她希望俄羅斯東正教會發揮其父權、團結與愛國的影響力。本地的眾多穆斯林人口會如何看待這件事,她毫不在意,然而她抱持著有點浪漫的想法,認為在昔日蘇聯,國內多種民族快樂共處。
總統普丁迎合像她這樣的人們。他在二○一四年接管克里米亞,及隨後捍衛烏克蘭的俄語區,使他委靡的支持率提升至超過百分之八十的高檔。他宣示的俄國優越精神,勝過了西方的個人主義、衰退和表裡不一。當這一切發揮作用,他支持東正教會是俄國唯一真正信仰的主張,且為俄國通往偉大之路的源頭。他要求中學統一歷史課本,「消除內部矛盾與分歧」──拿任何國家的歷史來說均屬挑戰,尤其是俄國的歷史。在我書寫的當下,召集委員會未能提出經核可的課本。
車里雅賓斯克國立大學的歷史學年輕教授亞歷山大.福金(Alexandr Fokin)說,學術界被要求去辨識出獨特的俄國特性,只偏重在好的那一面。他說這同時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以及對歷史的曲解。儘管如此,國族主義者和所謂的愛國人士施加影響力,箝制他所能研究的與在課堂上所能傳授的內容。車里雅賓斯克還沒像鄰近城市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的情況那麼壞,普丁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青年側翼,在那裡公開點名他們指認為叛國者的教授。對於車里雅賓斯克大學裡膽敢挑戰政府的那些人,僅在網路上遭受到匿名攻擊。
聯邦安全局正企圖重新定義叛國罪的概念,意在囊括「對外國或國際組織提供財務、科技、顧問或其他協助,導致傷害俄國安全」。在一場國際會議前,福金接到他的大學告知,他必須簽署一份文件以確認他拒絕向外國同行透露祕密,即使如今什麼算是祕密全憑個人猜測。大學的表格上包括一條命令,要求與會者不透露有可能「導致俄國損傷」的任何事。他在臉書上發文諷刺,開頭是「我的祖國又一次管束我的歡愉」。全國學術界同事的回應反映出類似擔憂──而許多人說著「歡迎重返蘇聯」。
取得政府檔案文件變得愈來愈困難,而官員說最好別提出令人不快的問題。在「開放」盛世一九九○年代見光的檔案,又遭受封藏命運。缺少特別核可,就無法獲取當下視為敏感的檔案,而核可發下時裡頭可能同時包括國外旅遊限令,這是多數人希望避免的限制。當然了,外國研究者面對的問題甚至更大,現在需要取得國家安全機構的放行批准。何其幸運,我在這波完全管制前見過幾位本地歷史學者和檔案管理人。要是我現在試圖跟他們見面,他們會帶著莫大遺憾說,他們沒有選擇,只能拒絕。
雖然俄國人對西方的懷疑常不切實,且受到政府的自私操弄,但他們並非毫無根據。早在一九九二年,喬治.H.W.布希總統於國情咨文演說時宣稱,「蒙上帝恩典,美國贏得了冷戰」。但是蘇聯解體時期的美國大使傑克.麥洛克(Jack Matlock)主張,冷戰結束並不是勝利;它是細緻的協商議定,理應惠及每一方且保證未來的合作。根據麥洛克所言,美國太常把新的俄羅斯視為輸家,形塑受辱與復仇的情感。儘管麥洛克並非普丁的擁護者,但他敢於主張對俄國和俄國人缺乏理解,可能會不必要地導致酷寒冷戰,以及核武競賽的重啟。
從來不曾有任何具體承諾說西方不會擴張北約,然而的確存在著誓言,不在俄國的弱點上占便宜。在那之後,俄國人尤其相信美國已經這麼做了。俄國人絮絮叨叨的擔憂之中,包括冷戰結束後北約擴張進入東歐。然後發生了北約在未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准許下轟炸塞爾維亞,這個與俄國同為斯拉夫民族與東正教會的國家;允許科索沃自塞爾維亞獨立,儘管美國在其他的情況下均支持領土主權;以及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並威脅要在前華沙公約國家部署防衛飛彈。俄國人也提到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未批准下入侵伊拉克;美國涉入在他們眼裡站不住腳的烏克蘭、喬治亞和吉爾吉斯民主革命,以及北約擴展進入喬治亞和烏克蘭的言論,兩地均與俄羅斯接壤。
西方許多人以及俄國的某些人爭論這一切,認為真正的問題是莫斯科變得益發極權主義,且回復它的帝國舊夢。由於俄國的經濟挑戰與未能現代化,他們主張,普丁向國外找敵人以掩飾自家的問題。
二○一四年,普丁找到他尋尋覓覓的敵人。美國支持的烏克蘭反對黨推翻與俄國友好的總統後,緊張態勢高漲。烏克蘭國會起草一項法案,撤銷俄語的官方語言地位,而當法案遭到否決時,普丁已經準備好要動搖新任政府。
首先他併吞克里米亞,一座伸入黑海的半島,在歷史上隸屬於俄羅斯,於一九五四年併入烏克蘭。當俄國和烏克蘭同屬於一個國家,這個舉動主要是象徵性的;然而一旦兩國分道揚鑣,克里米亞的地位形同創傷。在戰略上具關鍵地位的克里米亞,擁有壓倒性的俄國人口。莫斯科被迫要為黑海艦隊租借設施,且持續面臨租約會被撤銷的威脅。這成為微微發亮的閃火點,且當俄國認定基輔(Kiev) 在美國支持下,變得較不站在俄國的利益這一邊時,即迅速行動。接管克里米亞後,普丁把武器和軍隊送往烏克蘭東部工業區,做為尋求更大程度自治或分離的俄語人口的後盾。
我立即收到車里雅賓斯克聯絡人的激昂電子郵件,他們大多數人譴責西方的制裁並支持普丁。許多人有親戚在烏克蘭東部,在完全仰賴俄國市場的工廠和礦場裡工作。他們惟恐烏克蘭往歐洲靠攏,會使他們的親人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陷入困境。
擁護普丁的、尤其是支持接管克里米亞的那群人,組成分子範圍廣得驚人,包括一度自稱為「反對者」的人們。接下來稱為V的一位本地精英階層成員,比起像伊黎娜.寇蘇諾娃那樣的激烈俄羅斯國族主義者,他務實得多,他對克里米亞表示贊同。然而他認為普丁干預烏克蘭東部是場災難,他責怪普丁和歐巴馬總統都對放這把火有責任。在他看來,美國插手烏克蘭的舉止愚蠢,完全沒注意到情勢有多麼一觸即發。在他眼中,美國支持了對抗一位民選總統的政變。
論及的這位總統或許貪腐且令人憎惡,但如此行徑僅僅強化美國說一套、做一套的觀點。他說美國需要了解,烏克蘭對俄國具有「存在上的重要性」。對他來說,少了俄國的烏克蘭經濟顯然無法健全,那是他認為美國未能理解的另一件事。「西方真的準備要資助一個貪腐、破敗的國家嗎?」他問道。對於雙方未能尋求外交途徑解決危機,他感到沮喪。如同大多數俄國人,他主張僵局至少有部分成因來自美國在歐洲延續的安全體系,植基於許久以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不必要地孤立俄國,且不再適合今日的世界。熟知美國時事,他的小孩在那裡讀書,且讚賞他在美國目睹的許多事,V仍然驚異於美國的無知與傲慢,對於華府輕易譴責俄國犯下他相信美國同樣觸犯的罪責,感到氣憤不已。
V在一間高級餐廳裡,以及伊黎娜.寇蘇諾娃在雜誌辦公室發表的看法,在鎔鑄的高熱中強化。尤拉.柯瓦克(Yura Kovach)是車里雅賓斯克一間鋼鐵工廠的員工,也是我結識超過二十年的朋友,儘管他對普丁愈來愈強烈的支持,有時會使我們的關係緊張。我們透過他的妻子伊黎娜認識,她是一位受挫的蘇聯經濟學家,原本在一九九○年代有過榮景。她建立了一檔早期的股票型基金,也有保護退休金領取人的作用;她組織起一群鋼鐵工人,使他們隨即獲得賺錢的合約,替新建築物打造裝飾的圍欄和樓梯欄杆。在她的丈夫,一位擁有專業技術的工程師失去收入時,她賺到錢。但這導致婚姻問題。在那之後她結束生意,搖身一變為一位心理學家,因過度疲勞,隨後留在家裡好幾年照顧病危的母親。一路走來,她成為一位印度教導師的虔誠學生,獻身於冥想。她改吃素,創立且失去豆腐生意──原因並非缺乏需求,而是政府的地產操弄。她接著投入外匯市場,試圖補救債務。他們四十年的婚姻遭受嚴重考驗;他們的生活方式分歧,但是他們留在彼此身邊且贊同一件事──普丁是俄國最好的領導人。尤拉看著他的行業落居於新興的銀行家、貿易商和公關專員之後。當普丁在二○一○至二○一二年間稱呼莫斯科的抗議者「只是辦公室的浮游生物」,他鼓掌叫好。他介紹我認識一位受歡迎的勞工詩人,名叫伊果.拉斯特耶夫(Igor Rasteryaev),他喊北約是「垃圾」,還讚揚「不吃壽司或不上日光浴美容院」的那些人。柯瓦克一家人不上館子吃飯,也不去國外度假。
在網路上瀏覽新聞的尤拉,相信美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暗地裡支持莫斯科的反普丁示威,以及烏克蘭的反對黨抗議者。他不相信美國會容忍俄國對其國內事務或者利益範圍,做出類似的干預。如同眾多俄國人,現在他說當美國在捍衛國際利益時,自己適用一套規則,而對俄國是另一套。
當 我詢問,是否普丁和他的貪汙富商小圈子適用一套規則,而全國其他人適用另一套時,他自有藉口。他說到處都有貪汙,忽視俄國在國際評比上名列貪汙最烈的其中 一個國家。他擁戴普丁的聰明和能力,把他看作將會重建國家的工業和國際地位的人。他擋下我拋向他所有對普丁的批評,包括用一句俄國人的諺語回應:「起火的 時候,不要問誰是救火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