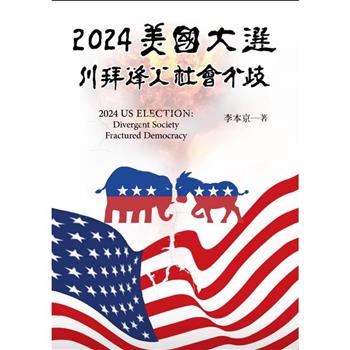拜登主義之要點
拜登也有主義,就好像是川普主義(Trumpism Doctrine)、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歐巴馬主義(Obama Doctrine)。每一個總統都有主義,有些高聲望的流傳,有些則慢慢消失了。
例如尼克森主義之意義非常清楚,那就是「亞洲人的戰爭要亞洲人自己打」,非常簡潔。拜登主義主要有三項要點,其一為國防,在拜登大力提高軍備下,今年軍費已達天價8860億美元。其二為氣候問題,美國過去未曾注意過,今日則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其三為提振經濟,拉高中產階級者之收入。
總體而言,「拜登主義」旨在延續美國統領世界,坐擁世界霸主(Hegemony)之寶座,以維持其「美式世界秩序」之雄心(American Way of World Order),並繼續捍衛「美國至尊」(American Primacy)之光輝,有可能創造「世紀霸權」之地位(1940-2040)。「經濟學人」對此有異議,認為當前美國對外政策時有矛盾現象,進而引致國際間之猜忌與不安。(見2023年5月20日之該周刊)
事實是,美國刻正全力拉幫結派對抗中國,而將之視為第一號敵人,興起「零和對抗」( Zero-Sum Approach)。如此,則國際間只有爭戰,也就是說拜登並未排除世界大戰之可能性,也可以說他所領導的就是一個備戰政府,然而他卻又顯示其對與習近平對話之熱誠。這些行為顯示出拜登政府之對外政策是波浪式的動盪,不夠穩定。
再嚴肅解釋他的「拜登主義」,則輕易地就發現,他的三項指標其實只有一項,那就是「國安」,也就是「備戰」。美國也自然地成為一個軍國主義者,他的強硬外交政策主要係針對中國,這也就是「拜登主義」之中心思想。
現實之川普主義
反觀川普,則輕易地就看出他是一個超級現實主義者,他看到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之失敗與羞辱,就很現實的聲稱反對出兵海外。他並且開支票,說一天就可結束俄烏戰爭。
簡單的說「川普主義」就是鬥而不戰,要鬥爭而不要戰爭。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在阿富汗戰爭上的對策,就在他於2017年登基之後,即正式宣稱要終止對阿戰爭,他真的說到做到,經過4年努力,終於在他的任期將屆滿前,與阿富汗之塔利班簽約終止戰爭,這才有了2021年8月阿戰之結束。
對川普而言,他重視美國之民族主義( Nationalism),將美國利益盡量擴大。他對華之重要政策即是強勢國貿政策,他在實施強勢政策的主要獻計者就是納瓦羅(Peter Navarro),他是一個最最反中、恨中、仇中與衰中者,可稱得上是世上最反中之人。在他的獻策下,川普對華政策自然就呈現極不尋常之反華特點,這也就是為何川普與中關係走衰之最大原因。(見拙著「仇中納瓦羅:劍指北京貿易戰之真相」,海峽評論20 18年10月)。
川普極力維護「單邊集權外交政策」而成立「川氏世界秩序」(Trumpian World Order)。此中心制定WASP(White-Anglo-Saxon Protestants)為主,也就是英國血統之白人基督教者為主之國際社會中心。由此可看出他也是一個種族歧視者。
他喜愛在國際間建立小圈圈(Micro Alliance),以單邊主義者主持世界大局(Unilateralism)。對華採取「全面對抗」(Comprehensive Confrontation) 與華對抗,然而僅限於此,並非對戰。川自認為「民主國族主義者」(Democratic Nationalist),而自封為「美式霸主」(American Hegemony)。他也認為國際間無永恆朋友,這一句來自故英首相派麥斯東(Lord Palmerston)之言,就成為川普之座右銘。
川普深信國際間就是「現勢外交」與「強權政治」(Realist Diplomacy and Realpolitics)之結合。他認為世界雖大,一個超強就夠了,如此就可實施「單向確保毀滅」(Unilateral Assured Destruction),而保證世界只能有一個超強,那就是美國。
總統大選政治版圖
2024決戰轉瞬即至,對民主、共和兩黨而言,究竟何者較有利?攤開大選政治版圖,就可以看出幾個趨勢: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多半投民主黨,鄉村區、城市外圍郊區以及農業區多半投共和黨。用人口條件來區分:非裔美國人(黑人)以及女人多半投民主黨,白人多半投共和黨,尤其是教育程度比較不高的白人。於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社會的分歧,主要是沿著二個軸線來發展。
第一大軸線是全球化與產業變遷。所謂中西部「鐵鏽帶」,指的就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造成的產業外移,原本最繁榮的工業區變成最生鏽的地方,大批的「經濟輸家」覺得自己已經被這整套體制給遺忘了,畢竟沒有人可以真正解決整個結構轉變帶來的失業問題。
傳統上,民主黨和工會的關係密切,從1980年代以來也一直是站在比較反對全球化的一方,主要理由就是擔心產業外移以及加深貧富差距,這也是為什麼在1990年代討論對中國貿易關稅優惠待遇,以及2000年要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民主黨國會議員反對者都遠多於共和黨。然而,經過時間演變,民主黨早已大力地擁抱全球化和整個資本市場,推出許多吸引各種資本密集產業與高技術人才的政策,但是卻忘記了傳統製造業以及勞力密集產業的人們。
事實上,二大黨在經濟政策的差別其實很小,雖然共和黨比民主黨更常主張自由市場機制以及去管制化,民主黨也有許多針對最低工資或勞動權益保障方面的政策主張,但實際執行方面,大體上都是傾向市場機制,各種針對財團的減稅招商措施,也從來沒少過。同時,美國超低水準的社會福利支出,則讓二大黨之立場非常相像。
對經濟輸家來說,在長期不受到二大黨政策關懷的狀況下,當川普強調製造業優先、要把工作機會帶回來的時候,這群選民很快就會被吸引。川普從十幾年前尚未從政時,就開始強調「全球化以致許多貿易大國搶走美國工作」這樣的論點,經由與他批判「傳統政治菁英把持利益」這樣的論點相結合,再加上最平實簡單的語言,成為廣大勞力密集產業藍領勞工階級的代言人。
相對來看,在全球化下受益族群,例如高科技產業、資本密集產業、以及工作比較不容易被取代的高知識分子們,則是愈來愈支持民主黨。有些學者把勞動市場極化現象稱做勞動市場二元化(dualization),而在這當中,失業風險較低且受到體制內社會安全網保障的「局內人」(insider),和那些邊陲的、不受到體制保障的局外人(outsider)勞工們,在政治態度方面的鴻溝愈來愈大。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方面也發展出了一股政治勢力,主張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來重新找回這些經濟輸家選民的信任,主要就是參議員桑德斯這一派,他們走的是許多歐洲左派政黨的提升稅收及高度社會福利路線,和川普的小政府、去管制化、產業重組的方法形成強烈對比。桑德斯和川普的特色都是訴諸於對傳統政治菁英的不信任,而且也同樣獲得許多支持,很顯然人們對於這套政黨政治運作成果的不滿由來已久。
川普上次在鐵鏽帶搖擺州當中(威斯康辛、密西根、賓州等)大多以極小的差距險勝,僅在明尼蘇達州輸了一點;而在2020大選當中,拜登在此區多半只能說是慘勝,川普的得票數也是有大量的成長。看起來,這些地區的選民們,仍然很不確定,到底哪種方式,才能夠真正地把工作機會帶回來。
美國國內分歧的第二大軸線是階級政治,主要是價值觀念與文化的社會分歧,這部分主要觸動了美國長期種族間各種社經不平等的敏感神經。美國社會長久以來都存在深層的族群不平等。例如,非裔人士至今仍然面對各方面政治制度系統性的歧視對待,像是在司法的執法、起訴及審判過程,各方面都對非裔有顯著的偏誤,以及在幾乎所有社會和經濟指標上面,非裔族群跟其他族群相比都是處於不利的位置。
另一方面,白人之間瀰漫著一種即將失去人口多數組成分子的擔憂,這就會和比較傳統的、基督教核心的那些保守觀念結合(保守並非貶意,而只是意識型態的標籤稱呼)。許多人看著各種歡迎新移民、主張多元價值、以及女權、人權、環保這些「新」的「自由派」價值不斷興起,更多人開始擔憂自己信奉一輩子的價值觀被破壞。對這些信奉保守價值觀的人們來說,那些自由派以及都市裡的人們,每次談到這些價值,就像是在教訓人一樣,況且,自己一生都奉公守法、愛這片土地以及以國家為榮,為什麼會忽然被指責說自己的價值觀是錯的?
經歷第一位非裔總統歐巴馬之後,非裔及少數族裔選民感到失望,因為結構並未改善,而白人的危機感則繼續增長。在川普之前,這樣的分歧就已經存在,而他從2015年參與初選以來,發言主軸常常就是去強調「我群」和「他者」的不同。他為美國人民塑造出不同的對立對象,例如把移民說成是來搶奪工作機會、造成社會負擔的威脅,把穆斯林說成是恐怖分子,把任何社會議題上增加社會福利的主張都說成是極端社會主義。這些話語常常會有歧視之嫌,但他確實喚起了各族群的危機意識。
在貧富差距屢創新高的時代,這些操作群體對立的招數特別管用,而且許多群眾也大力稱讚他率直、敢講真話。經過四年任期,很多人們認為川普個人言行雖有爭議,但不影響到政策層面,而他總是身體力行、真正地去實現政見。
以上二條軸線的發展,常常是互相交織而成,而美國特殊的選舉制度「選舉人團制」,正好就是放大了以上光譜二端的價值衝突,讓人數較少的經濟輸家以及白人為主的保守派選民,透過決定「搖擺州」的選舉結果,使其具有超過其人數比例的影響力。但美國聯邦制度也正是因為如此地平衡「州權」與「聯邦權」,而能夠維繫下去。放大較少數選民的影響力,也代表著執政者必須要花費很多心思來照顧他們的需求,不會因為他們人數比較少而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