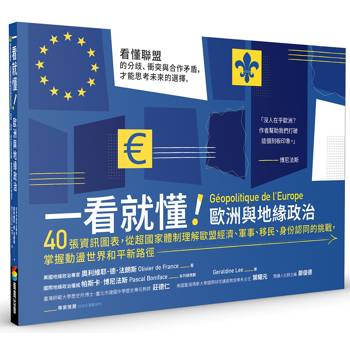前言
「歐洲地緣政治」從根本上來說,是否是個不恰當的詞彙?畢竟這片古老的大陸,如今正因擺脫了過去的地緣政治災難而感到自豪,同時致力於塑造一個後歷史時代的世界。當前歐洲政治的特殊性,正在於這個既不劃分勢力範圍、也不玩零和遊戲、更不服膺於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下,以自身利益為中心的全新模式。即便當前世界的步伐紛亂不堪,歐洲的榮耀依然向世人揮舞著一支充滿理想的和平旗幟。總而言之,歐洲難道不是最典型的「非地緣政治行動者」嗎?
事實上,20世紀的種種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重新分配了權力,並迫使歐洲接受自己不再是世界政治重心的事實。尼古拉.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在此過程中扮演了要角,迫使這個古老大陸承認其他文明早已知曉的事實——人類既不位於宇宙的中心,也不站在歷史的終點,更不是自身行為的絕對主宰。
昔日當哥白尼證明人類不位於宇宙中心時,不但消除了佛洛伊德所稱的第一次自戀幻覺,也同時提出了日心說,為人類提供了一個替代舊日學說的模式。今天的歐洲並沒有提出新的模式,因此只能為過去的地位哀悼,但自身卻尚未塑造出未來的角色。事實上,能夠使歐洲政府與其人民和解的政治系統仍有待構建,而更糟的是,英國脫歐確定了一件事:歐洲政治一體化是一項「可逆的過程」。
這是歐洲的第二次自戀傷害:無論有意識與否,歐盟如今不能再將自己視為西方歷史進程的巔峰之作。相反地,歐盟連其最初建立的原則都難以維護。技術性地維持現狀已無法阻止歐洲核心價值的瓦解,例如因新冠病毒和難民危機而蒙受威脅的申根區,或是歐盟內部對法治的侵犯。
第三次自戀傷害則最隱蔽。它來自一種普遍的社會印象,即人民已經失去了對集體命運的控制,甚至對世界的理解能力。這種對未來集體影響力的喪失感,來自於科技發展的猛烈變化、金融資本主義的快速成長、和氣候變遷的不可名狀之力。
歐洲大陸目前正處於創造新歷史的起始點。過往那種心照不宣的例外主義已不復存在,以帝國工業化模式進行經濟成長的必要性也不再是共識,而今日的歐洲必須在這種情況下,嘗試書寫歷史。歐洲必須首先能夠提出夢想中的未來:一個降低暴力、減少霸權獨佔、更具包容性、更提倡共享、對其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更有益的未來,並努力將其實現。
這是否意味著,歐洲能夠重新構建一種更「女性化」的政治形式,與過去那些充滿征服和破壞性的帝國主義分道揚鑣,同時又能夠捍衛自身利益?也許可以,儘管歐洲過去的歷史經驗並無法使得這項任務變得容易:如古老傳說中的歐羅巴公主(Europa),在提香(Titian)的畫中溫順地被公牛帶走;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的華麗中世紀地圖上,歐羅巴女王手持地球儀,身上穿戴著成套的男權飾物,準備將基督教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些傳說故事和人物形象需要徹底翻新,就像這本書封面上的「歐洲化」的瑪麗安娜[5](Marianne)所代表的精神)。在歐羅巴公主的被動與歐羅巴女王的侵略性之間,存在著一個充滿可能性的領域。
然而,僅僅更新自己的答案並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新時代的答案早已以一種無法拒絕的態勢,充斥於網絡和日常生活中。關鍵在於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問題。若我們將歐洲的未來限制為民族主義和聯邦主義之間的選擇,就等同於提前斬斷了創造尚不存在的未來模式的可能性。若將20世紀的宏大的集體極權主義,和21世紀充滿自由、但卻專制且忿忿不平的渺小個人相提並論,固然可以讓我們與逐漸走向衰敗的「過去」和「現在」劃清界限,但卻難以幫助我們構建「未來」。
英國小說家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法國饒舌歌手布巴(Booba)或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是嘗試重新思考歐洲的幾個例子;歐洲是一本不斷被重複書寫的手稿,是一幅文字和思想的拼圖,也是一個實驗室,世世代代的混合體在其中不斷重新創造出個體與社群、國家與大陸、身份認同與共和體制、村莊聚落與遠端的地平線。本書接下來的內容是對創造新時代的微小貢獻,而古老的歐洲大陸尚未完全理解這項事業的規模。本書最終呼籲,建立一個真正關係密切的歐洲,既植根於其共同的歷史和集體演變,也植根於其生態、地理和戰略環境。新的歐洲不應該再將固定的、內向的和反應性的身份認同拼湊在一起,而應該在永恆的變化與塑造的過程中,尋找出共同的基礎
「歐洲地緣政治」從根本上來說,是否是個不恰當的詞彙?畢竟這片古老的大陸,如今正因擺脫了過去的地緣政治災難而感到自豪,同時致力於塑造一個後歷史時代的世界。當前歐洲政治的特殊性,正在於這個既不劃分勢力範圍、也不玩零和遊戲、更不服膺於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下,以自身利益為中心的全新模式。即便當前世界的步伐紛亂不堪,歐洲的榮耀依然向世人揮舞著一支充滿理想的和平旗幟。總而言之,歐洲難道不是最典型的「非地緣政治行動者」嗎?
事實上,20世紀的種種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重新分配了權力,並迫使歐洲接受自己不再是世界政治重心的事實。尼古拉.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在此過程中扮演了要角,迫使這個古老大陸承認其他文明早已知曉的事實——人類既不位於宇宙的中心,也不站在歷史的終點,更不是自身行為的絕對主宰。
昔日當哥白尼證明人類不位於宇宙中心時,不但消除了佛洛伊德所稱的第一次自戀幻覺,也同時提出了日心說,為人類提供了一個替代舊日學說的模式。今天的歐洲並沒有提出新的模式,因此只能為過去的地位哀悼,但自身卻尚未塑造出未來的角色。事實上,能夠使歐洲政府與其人民和解的政治系統仍有待構建,而更糟的是,英國脫歐確定了一件事:歐洲政治一體化是一項「可逆的過程」。
這是歐洲的第二次自戀傷害:無論有意識與否,歐盟如今不能再將自己視為西方歷史進程的巔峰之作。相反地,歐盟連其最初建立的原則都難以維護。技術性地維持現狀已無法阻止歐洲核心價值的瓦解,例如因新冠病毒和難民危機而蒙受威脅的申根區,或是歐盟內部對法治的侵犯。
第三次自戀傷害則最隱蔽。它來自一種普遍的社會印象,即人民已經失去了對集體命運的控制,甚至對世界的理解能力。這種對未來集體影響力的喪失感,來自於科技發展的猛烈變化、金融資本主義的快速成長、和氣候變遷的不可名狀之力。
歐洲大陸目前正處於創造新歷史的起始點。過往那種心照不宣的例外主義已不復存在,以帝國工業化模式進行經濟成長的必要性也不再是共識,而今日的歐洲必須在這種情況下,嘗試書寫歷史。歐洲必須首先能夠提出夢想中的未來:一個降低暴力、減少霸權獨佔、更具包容性、更提倡共享、對其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更有益的未來,並努力將其實現。
這是否意味著,歐洲能夠重新構建一種更「女性化」的政治形式,與過去那些充滿征服和破壞性的帝國主義分道揚鑣,同時又能夠捍衛自身利益?也許可以,儘管歐洲過去的歷史經驗並無法使得這項任務變得容易:如古老傳說中的歐羅巴公主(Europa),在提香(Titian)的畫中溫順地被公牛帶走;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的華麗中世紀地圖上,歐羅巴女王手持地球儀,身上穿戴著成套的男權飾物,準備將基督教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些傳說故事和人物形象需要徹底翻新,就像這本書封面上的「歐洲化」的瑪麗安娜[5](Marianne)所代表的精神)。在歐羅巴公主的被動與歐羅巴女王的侵略性之間,存在著一個充滿可能性的領域。
然而,僅僅更新自己的答案並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新時代的答案早已以一種無法拒絕的態勢,充斥於網絡和日常生活中。關鍵在於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問題。若我們將歐洲的未來限制為民族主義和聯邦主義之間的選擇,就等同於提前斬斷了創造尚不存在的未來模式的可能性。若將20世紀的宏大的集體極權主義,和21世紀充滿自由、但卻專制且忿忿不平的渺小個人相提並論,固然可以讓我們與逐漸走向衰敗的「過去」和「現在」劃清界限,但卻難以幫助我們構建「未來」。
英國小說家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法國饒舌歌手布巴(Booba)或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是嘗試重新思考歐洲的幾個例子;歐洲是一本不斷被重複書寫的手稿,是一幅文字和思想的拼圖,也是一個實驗室,世世代代的混合體在其中不斷重新創造出個體與社群、國家與大陸、身份認同與共和體制、村莊聚落與遠端的地平線。本書接下來的內容是對創造新時代的微小貢獻,而古老的歐洲大陸尚未完全理解這項事業的規模。本書最終呼籲,建立一個真正關係密切的歐洲,既植根於其共同的歷史和集體演變,也植根於其生態、地理和戰略環境。新的歐洲不應該再將固定的、內向的和反應性的身份認同拼湊在一起,而應該在永恆的變化與塑造的過程中,尋找出共同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