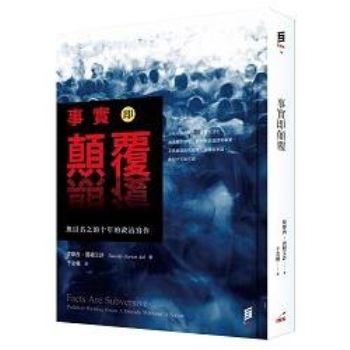第一章 天鵝絨革命,綿延不絕
米洛塞維奇的奇怪倒台
二○○○年十月五日,星期四,塞爾維亞人衝進位於貝爾格勒的議會大樓,從燃燒著的窗戶中揮舞著旗幟,並占領了國家電視台的總部(有一位反對派領導人曾經將它們稱為「電視巴士底獄」),這看起來像是一場真正的舊式歐洲革命。攻打冬宮!攻陷巴士底獄!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共產主義終結後繼續掌權的最後東歐統治者、「巴爾幹屠夫」會步上所有暴君的後塵。有激動人心的報導稱,三架飛機正在將斯洛博丹.米洛塞維奇及其家人送出國。也有報導稱他像希特勒一樣躲在地下掩體中。他會被私刑處死嗎?會像西奧塞古一樣被處死?還是會像他的父母一樣自殺?「拯救塞爾維亞,」人群喊道,「自殺吧,斯洛博丹。」革命的形象以及「巴爾幹半島人」讓人聯想到的所有血腥場面,引來了數百名記者,前來報導這一可怕卻適合上鏡的結局。
出人意料的是,十月六日,星期五晚上夜深的時候,米洛塞維奇出現在另一個國家電視台上,發表了和善的敗選演講。人們覺得美國總統或者英國首相才會發表這樣的演講。他說,他剛剛收到消息,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Vojislav Koštunica)贏得了總統大選。(這話竟然出自他之口,過去十一天,他一直在努力通過選舉舞弊、恐嚇以及操縱法庭來否認這一點。)他感謝了那些選他的人,同時也感謝了那些沒有選他的人。現在,他打算「多陪陪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孫子馬爾科」。隨後,他希望重建其社會黨,使它成為反對黨。「我祝賀科什圖尼察先生獲得勝利,」他總結道,「我祝願南斯拉夫的所有公民在今後幾年取得成功。」
他像往常一樣穿著整潔的西服、白襯衫,打著領帶,但卻僵硬地站在南斯拉夫國旗的旁邊,雙手交叉著,在身前放得很低,像一個作弊被抓的男學生一樣,或者說像在牧師前懺悔的人(他的父親曾經希望當牧師)。對不起,神父,我在選舉中作弊了,毀掉了我的國家,帶給了鄰國無盡的殺戮和痛苦,但是從現在起我將做一個好人。假裝這只是一次普通又民主的領導人換屆,既不協調又離奇可笑。然而,這也正是新總統希望假裝的。科什圖尼察總統後來告訴我,米洛塞維奇曾打電話問他是否可以發表演講,他很高興,因為他希望讓塞爾維亞的所有人知道,權力的民主和平交接是可能的。同一天晚上早些時候,科什圖尼察曾出現在「解放」的國家電視台上,一如既往地穿著得體且嚴肅,回答公眾的電話提問,鎮定自如地談論投票制度,似乎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
沒錯,當晚,我發現有年輕人在議會大樓前吹哨跳舞慶祝。但是與我交談過的大多數朋友—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推翻米洛塞維奇的人—既沒有表現出欣喜若狂,也沒有表現出憤怒不已,而是在情不自禁的喜悅中略感疑惑。他真的完蛋了嗎?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很明白。見鬼,這不應該是一場革命嗎?但這場革命似乎始於星期四晚上,而星期五早上就結束了。不再有壯觀的場面。沒有流血事件。塞爾維亞人沒有引發流血事件。他們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廣播公司(A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失望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更會配合。他們正在互相拚殺。因此,第二天,一半攝影組奔向了以色列。那些留下來的人還在繼續琢磨這樣一個問題:這算怎麼一回事?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混合體。同日早上,科什圖尼察搬進了有回聲的聯邦宮(Federation Palace),就在接待俄羅斯外長前幾分鐘,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叛亂中的傳奇老兵「德拉甘上校」(Captain Dragan)在他的手臂下面別著一把天蠍式自動武器,帶著一隊武裝人員向聯邦海關大樓走來。他去那是為了將米哈利.科特斯(Mihalj Kertes)驅逐出境,米哈利.科特斯是米洛塞維奇的親信,通過海關控制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交易。德拉甘上校告訴我,科特斯在顫抖,苦苦哀求饒他不死。
星期六,科什圖尼察不得不在二十世紀七○年代風格的薩瓦中心的簡陋接待室裡站了幾個小時,等待反對黨和米洛塞維奇的社會黨新當選的議員解決他們的分歧,讓他按照憲法正式宣誓就職。與此同時,一隊「紅色貝雷帽」國家安全特種突擊隊,包括參加過武科瓦爾(Vukovar)和科索沃(Kosovo)行動的塞爾維亞老兵,正在占領內政部。但是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表明反對米洛塞維奇,或者說至少部分原因是如此。
在政黨會面共同討論新聯邦政府之際,工廠和辦公室內自封的「危機委員會」以人民的名義解雇了他們先前的老闆。前一分鐘,我還在看準軍事部隊領導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在塞爾維亞議會的會議上譴責這場革命。接下來,我就在仔細觀察德拉甘上校從可恨的科特斯那裡拿過來的手槍了。那把手槍相當輕便,紫檀木的槍托上刻有花紋,相當漂亮,裡面有五發軟頭子彈和一發普通子彈。
然而,米洛塞維奇一直靜靜地坐在德丁傑(Dedinje)郊區鬱鬱蔥蔥的山間別墅中,與他的舊黨在一起商討。在貝爾格勒的最後一天,我開車經過尤茲克卡(Uæicka)大街上的這些房子,它們躲在高牆和防護籬笆後面。不知道怎麼回事,我連門鈴都無法找到。這場塞爾維亞革命是什麼?顯然,有關塞爾維亞事件的許多事情尚不明朗,但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會被跟波蘭一九八○—一九八一年間「自我約束」的革命和一九八九年歐洲的天鵝絨革命(velvet evolution)進行比較。我最初的解讀是,在塞爾維亞發生的一切是一個獨一無二又錯綜複雜的組合體,由四個要素組成:有點兒民主的選舉、自我約束的新天鵝絨革命、較古老的短暫革命政變和些許舊式的巴爾幹陰謀。
首先是選舉。許多外界人士不知道的是,與西奧塞古統治下的羅馬尼亞不同,米洛塞維奇統治下的塞爾維亞從來不是一個極權國家。這是他倒台與眾不同的一個主要原因。沒錯,他是一個戰爭犯,給前南斯拉夫中塞爾維亞的鄰國帶來了巨大的苦難。但在國內,他不是一個極權的專制統治者。相反,他的政權是民主和獨裁的奇怪混合體:民主專制國家。
在米洛塞維奇的統治下,黨派鬥爭不斷,多個黨派互相鬥爭。連執政黨也有兩個:他自己和他妻子各自所屬的政黨。他自己的後共產主義時代塞爾維亞社會黨與妻子的南斯拉夫左翼聯盟(Yugoslav United Left)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他的權力根基動搖。但是如今即將掌權的反對黨和反對派政客,包括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也已經參政十年了。沒錯,是有警察及祕密警察的鎮壓活動,甚至還包括政治暗殺,但是也有選舉,米洛塞維奇在選舉中獲勝了。
它們不是自由公平的選舉。他的政權最重要的單一支柱是國家電視台,被用來維持民族主義的受困心理,在居住於沒有什麼其他信息來源的鄉下和小鎮上的人們中間尤其是如此。因此,他最早的政治對手之一,武克.德拉斯科維奇(Vuk DraškoviÊ)稱之為電視巴士底獄。但是也有設防的獨立廣播電台和私營報紙。人們可以旅行,幾乎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還可以上街遊行。反對黨可以組織活動和競選,在議會和市議會中也有他們的代表。米洛塞維奇掌權的另一種方法是在他們中間巧妙周旋,分而治之。比如,上面提到的德拉斯科維奇受命接管了貝爾格勒市政府,人們都說他同時也接收了隨之而來的致富源泉。
在這個貧窮、目前深陷腐敗的國家,錢財在政壇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所指的錢財是指塞在黑色皮夾克口袋裡或裝在手提箱裡帶出國的大量德國馬克。政界、商界和有組織犯罪機構之間的邊界完全消失了。米洛塞維奇的可惡兒子馬可是一名商人,同時也是個強盜。他有眾多家產,其中一家位於貝爾格勒市中心的香水店叫斯康達(Skandal),這個名字真是再合適不過了(諧音 scandal,意為「醜聞」)。十月六日,星期五晚,我和一群人站在一起注視著這家被洗劫一空、燒焦的店。他帶著米洛塞維奇的孫子馬爾科逃到莫斯科。從黑手黨的角度來理解,執政的家庭是更大家庭的核心。然而,這位「教父」還在表面上保留了憲法的形式,定期在選舉中尋求連任。他獲勝得益於電視巴士底獄和有些悄無聲息的投票舞弊,還因為他可以利用四分五裂的反對派,依靠真正相當高的支持率。
只有知道這些背景,才能理解為何七月初米洛塞維奇決定修改憲法,尋求直接連任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總統。現在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了。但當初,這樣認為的人寥寥無幾。
他自己呼籲在九月二十四日進行選舉,為什麼他會在選舉中敗北?最首要也最溫暖人心的部分答案無疑是:動員其他塞爾維亞人擊敗他。在「塞爾維亞人」都被妖魔化的情況下,再加上「他們」在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所作所為,人們常常無法堅定地說總是還有其他塞爾維亞人。一開始就有塞爾維亞人發表演說、寫文章和組織活動來反對米洛塞維奇。他們的鬥爭與在蘇聯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異見分子的鬥爭不同,但難度或者危險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他們。蘇聯的異見分子冒著被KGB逮捕入獄的危險。塞爾維亞的異見分子冒著在漆黑的小巷中被陌生的暗殺者槍殺的危險。他們人數不多,但總是有這麼一些人。
韋蘭.馬蒂奇(Veran MatiÊ)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身材粗壯,留著大黑鬍子,性格沉著冷靜。你總可以在他的辦公室裡看到他在一台輕巧的手提電腦上打字。馬蒂奇有一個敬業的記者團,又有西方的大量金融資助,於是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廣播電台—B92電台,科索沃戰爭剛爆發的時候,當局控制了這個電台,但它仍然在網上提供新聞。他還開辦了一個叫ANEM的網站,為不受米洛塞維奇控制的省級廣播電台和電視台提供獨立的新聞和時事節目。目前,「電視巴士底獄」譴責科什圖尼察和反對派是北約的走狗、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特工,但該網站卻泰然自若地告知貝爾格勒外面的人這場競選活動的真相。此外,還有一些不太知名的記者因為報導他們自認為是真相的東西鋃鐺入獄。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名為「奧特波爾」(Otpor)——意為「抵抗」——的學生運動。它成立於一九九八年,與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的抗議一脈相承,但更加激進。一名活動人士告訴我,在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舉辦的研討會上,奧特波爾的成員學習了其他地方的權力運動和非暴力反抗是如何組織的,從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到去年在克羅埃西亞的活動。這些都是「比較革命」專業的學生。但是他們自己添加了很多種創新的變化。比如,他們會穿著上面有「塞爾維亞的一切都不錯」字樣的T恤,出現在購買糖和石油的長隊中。他們舉著畫著緊握拳頭圖案的獨特橫幅,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抗警察。在革命爆發前的一年裡,有一千五百多名奧特波爾的活動分子被捕。在一九九八年的斯洛伐克選舉中,民間團體的活動分子推翻了弗拉基米爾.梅恰爾(Vladimir MeËiar),與此一樣,他們組織了運動來「搖動投票」。流行的搖滾音樂會與出去投票的信息相結合。他們設計了一個口號,「Vreme je!」即「時機已到!」或「現在是時候了!」而這恰恰是一九八九年人們在布拉格所喊的口號。隨後他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口號,「Gotov je!」即「他完蛋了!」作為這場革命的名言,塗在米洛塞維奇的海報上,寫在帽子和橫幅上,塗在這座城市的牆壁上,還被十萬人喊著。
在這個獨立活動的世界中,還有許多人——在斯洛伐克,他們被稱為「第三部門」——致力於該事業。獨立的民意調查者(其中一些人由美國資助)會定期作調查,調查表明科什圖尼察正在取得勝利。競選志願者和獨立的選舉監督人員數不勝數。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歐洲,西方在「民間團體」項目上浪費了數百萬美元。但是這次,在這裡,確實是物有所值了。
其次是意見迥異的反對黨最終團結起來的事實。可以肯定的是,並不是所有反對黨。最大的反對黨,即武克.德拉斯科維奇的塞爾維亞復興運動黨(Serbian Renewal Movement),拒絕加入。此外,蒙特內哥羅總統米洛.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Ê)呼籲抵制選舉,因而讓米洛塞維奇實際上拿到了所有留下來的蒙特內哥羅人的選票。但是還是有十八個黨一起加入了塞爾維亞民主反對黨(Democratic Opposition of Serbia)。其中最大的黨是民主黨,該黨黨首是反對派領導人佐蘭.金吉奇(Zoran DjindjiÊ),他任職很久了,但容易妥協,不得人心。
米洛塞維奇敗北的第三個原因是,金吉奇和其他人徹底平息了他們內部的爭執,一致提名讓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當候選人。科什圖尼察是小塞爾維亞民主黨的領袖,該黨在二十世紀九○年代初從民主黨分離出來。科什圖尼察不太願意去競選—他自嘲道,自己是第一位猶豫不決的選民,但這是一個完美的選擇,因為他集反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不腐敗和遲鈍四種品質於一身,獨一無二。
科什圖尼察從來都不屬共產黨。他是一名憲法律師和政治學家,一九七○年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反對黨在多黨制中的作用。他後來翻譯了《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還專門研究了托克維爾(Tocqueville)和洛克(Locke)。由於反對狄托(Tito)一九七四年頒布的憲法,稱該憲法對塞爾維亞人不公平,他被貝爾格勒大學開除。與大多數其他反對黨領導人不同,他竟然從未見過米洛塞維奇,直到十月六日,星期五,軍隊總司令內博伊沙.帕夫科維奇(Nebojsa PavkoviÊ)才給即將離任和上任的總統安排了一次簡短的會面。科什圖尼察自豪地告訴我:「因此我是在他垮台的時候第一次見到他的。」
他是個溫和的民族主義者,曾支持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強烈批評北約在科索沃發動的戰爭。與德拉斯科維奇和金吉奇不同,人們從未看到他與馬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過從甚密。轟炸期間,他一直留在貝爾格勒,而金吉奇逃到了蒙特內哥羅,或許正是擔心自己的小命不保。他不腐敗。我基本上還未見過比他的黨務辦公室還簡陋的辦公室。他和妻子還有兩隻貓一起住在一個小公寓裡,開的是一輛破舊不堪的南斯拉夫牌汽車。這又與其他反對派領導人(尤其是金吉奇和德拉斯科維奇)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穿著光鮮亮麗的西服,開著快車,人們普遍認為他們貪汙腐敗。在後鄂圖曼帝國時代的世界裡,大多數政客都是這樣做的,由來已久。
他的一大劣勢是他的遲鈍。不過在這件事上,連遲鈍也是一項優勢。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他們喜歡他慢條斯理、行動遲鈍的風格。他們說,遲鈍非常受歡迎,與米洛塞維奇悲壯的裝模作樣和他的許多對手,比如說武克.德拉斯科維奇的誇誇其談形成對比。一位首席獨立記者告訴我:「你懂的,我想要一位乏味的總統,還想生活在一個乏味的國家裡。」
話說回來,畢竟科什圖尼察也沒有那麼遲鈍。他發現自己成為祖國解放運動的領袖,備受鼓舞(誰會不受鼓舞呢),於是帶來了一些英勇無畏又令人難忘的時刻。他在議會和電視台被占領的那天晚上所說的「晚上好,解放的塞爾維亞」將載入史冊。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至少有二百四十萬塞爾維亞人在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的名字旁邊畫了一個圓圈。當然,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讓他們這樣做的所有動機,但是有人給我提供了兩個引人注目的部分解釋。
一個解釋與北約的轟炸有關。我問政客和分析人士,他們認為革命是何時開始的。有幾個人表示,常常噘著嘴說:嗯,老實說,科索沃戰爭結束的時候。在戰爭期間和戰爭一結束後,都在國旗下舉行過愛國集會,米洛塞維奇也從中受益。但是這也太荒唐,太「歐威爾」(Orwellian)了,國家電視台竟然聲稱這個歷史性的明顯戰敗是一次勝利:塞爾維亞的耶路撒冷—科索沃—輸得其所。在經濟方面,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在轟炸的影響下,每一項勒緊褲腰帶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科盧巴拉煤礦的礦工—他們的罷工對這場革命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告訴我,戰後他們的工資從平均每月一百五十德國馬克降到了七十德國馬克的低位。對此給出的解釋是為戰後重建交稅。但這讓他們怒不可遏。
正如韋蘭.馬蒂奇所說,當時米洛塞維奇「競選不是為了對抗我們,而是為了對抗北約」。然而,這沒有起作用,因為人們內心更深處認為:「不過,他對抗北約輸了,不是嗎?」如果馬蒂奇說得對,那麼科什圖尼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他所譴責的轟炸的受益人。當然,這種解釋疑點重重,永遠無法證實。但戰爭推波助瀾引發革命在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
米洛塞維奇的奇怪倒台
二○○○年十月五日,星期四,塞爾維亞人衝進位於貝爾格勒的議會大樓,從燃燒著的窗戶中揮舞著旗幟,並占領了國家電視台的總部(有一位反對派領導人曾經將它們稱為「電視巴士底獄」),這看起來像是一場真正的舊式歐洲革命。攻打冬宮!攻陷巴士底獄!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共產主義終結後繼續掌權的最後東歐統治者、「巴爾幹屠夫」會步上所有暴君的後塵。有激動人心的報導稱,三架飛機正在將斯洛博丹.米洛塞維奇及其家人送出國。也有報導稱他像希特勒一樣躲在地下掩體中。他會被私刑處死嗎?會像西奧塞古一樣被處死?還是會像他的父母一樣自殺?「拯救塞爾維亞,」人群喊道,「自殺吧,斯洛博丹。」革命的形象以及「巴爾幹半島人」讓人聯想到的所有血腥場面,引來了數百名記者,前來報導這一可怕卻適合上鏡的結局。
出人意料的是,十月六日,星期五晚上夜深的時候,米洛塞維奇出現在另一個國家電視台上,發表了和善的敗選演講。人們覺得美國總統或者英國首相才會發表這樣的演講。他說,他剛剛收到消息,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Vojislav Koštunica)贏得了總統大選。(這話竟然出自他之口,過去十一天,他一直在努力通過選舉舞弊、恐嚇以及操縱法庭來否認這一點。)他感謝了那些選他的人,同時也感謝了那些沒有選他的人。現在,他打算「多陪陪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孫子馬爾科」。隨後,他希望重建其社會黨,使它成為反對黨。「我祝賀科什圖尼察先生獲得勝利,」他總結道,「我祝願南斯拉夫的所有公民在今後幾年取得成功。」
他像往常一樣穿著整潔的西服、白襯衫,打著領帶,但卻僵硬地站在南斯拉夫國旗的旁邊,雙手交叉著,在身前放得很低,像一個作弊被抓的男學生一樣,或者說像在牧師前懺悔的人(他的父親曾經希望當牧師)。對不起,神父,我在選舉中作弊了,毀掉了我的國家,帶給了鄰國無盡的殺戮和痛苦,但是從現在起我將做一個好人。假裝這只是一次普通又民主的領導人換屆,既不協調又離奇可笑。然而,這也正是新總統希望假裝的。科什圖尼察總統後來告訴我,米洛塞維奇曾打電話問他是否可以發表演講,他很高興,因為他希望讓塞爾維亞的所有人知道,權力的民主和平交接是可能的。同一天晚上早些時候,科什圖尼察曾出現在「解放」的國家電視台上,一如既往地穿著得體且嚴肅,回答公眾的電話提問,鎮定自如地談論投票制度,似乎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
沒錯,當晚,我發現有年輕人在議會大樓前吹哨跳舞慶祝。但是與我交談過的大多數朋友—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推翻米洛塞維奇的人—既沒有表現出欣喜若狂,也沒有表現出憤怒不已,而是在情不自禁的喜悅中略感疑惑。他真的完蛋了嗎?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很明白。見鬼,這不應該是一場革命嗎?但這場革命似乎始於星期四晚上,而星期五早上就結束了。不再有壯觀的場面。沒有流血事件。塞爾維亞人沒有引發流血事件。他們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廣播公司(A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失望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更會配合。他們正在互相拚殺。因此,第二天,一半攝影組奔向了以色列。那些留下來的人還在繼續琢磨這樣一個問題:這算怎麼一回事?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混合體。同日早上,科什圖尼察搬進了有回聲的聯邦宮(Federation Palace),就在接待俄羅斯外長前幾分鐘,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叛亂中的傳奇老兵「德拉甘上校」(Captain Dragan)在他的手臂下面別著一把天蠍式自動武器,帶著一隊武裝人員向聯邦海關大樓走來。他去那是為了將米哈利.科特斯(Mihalj Kertes)驅逐出境,米哈利.科特斯是米洛塞維奇的親信,通過海關控制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交易。德拉甘上校告訴我,科特斯在顫抖,苦苦哀求饒他不死。
星期六,科什圖尼察不得不在二十世紀七○年代風格的薩瓦中心的簡陋接待室裡站了幾個小時,等待反對黨和米洛塞維奇的社會黨新當選的議員解決他們的分歧,讓他按照憲法正式宣誓就職。與此同時,一隊「紅色貝雷帽」國家安全特種突擊隊,包括參加過武科瓦爾(Vukovar)和科索沃(Kosovo)行動的塞爾維亞老兵,正在占領內政部。但是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表明反對米洛塞維奇,或者說至少部分原因是如此。
在政黨會面共同討論新聯邦政府之際,工廠和辦公室內自封的「危機委員會」以人民的名義解雇了他們先前的老闆。前一分鐘,我還在看準軍事部隊領導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在塞爾維亞議會的會議上譴責這場革命。接下來,我就在仔細觀察德拉甘上校從可恨的科特斯那裡拿過來的手槍了。那把手槍相當輕便,紫檀木的槍托上刻有花紋,相當漂亮,裡面有五發軟頭子彈和一發普通子彈。
然而,米洛塞維奇一直靜靜地坐在德丁傑(Dedinje)郊區鬱鬱蔥蔥的山間別墅中,與他的舊黨在一起商討。在貝爾格勒的最後一天,我開車經過尤茲克卡(Uæicka)大街上的這些房子,它們躲在高牆和防護籬笆後面。不知道怎麼回事,我連門鈴都無法找到。這場塞爾維亞革命是什麼?顯然,有關塞爾維亞事件的許多事情尚不明朗,但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會被跟波蘭一九八○—一九八一年間「自我約束」的革命和一九八九年歐洲的天鵝絨革命(velvet evolution)進行比較。我最初的解讀是,在塞爾維亞發生的一切是一個獨一無二又錯綜複雜的組合體,由四個要素組成:有點兒民主的選舉、自我約束的新天鵝絨革命、較古老的短暫革命政變和些許舊式的巴爾幹陰謀。
首先是選舉。許多外界人士不知道的是,與西奧塞古統治下的羅馬尼亞不同,米洛塞維奇統治下的塞爾維亞從來不是一個極權國家。這是他倒台與眾不同的一個主要原因。沒錯,他是一個戰爭犯,給前南斯拉夫中塞爾維亞的鄰國帶來了巨大的苦難。但在國內,他不是一個極權的專制統治者。相反,他的政權是民主和獨裁的奇怪混合體:民主專制國家。
在米洛塞維奇的統治下,黨派鬥爭不斷,多個黨派互相鬥爭。連執政黨也有兩個:他自己和他妻子各自所屬的政黨。他自己的後共產主義時代塞爾維亞社會黨與妻子的南斯拉夫左翼聯盟(Yugoslav United Left)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他的權力根基動搖。但是如今即將掌權的反對黨和反對派政客,包括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也已經參政十年了。沒錯,是有警察及祕密警察的鎮壓活動,甚至還包括政治暗殺,但是也有選舉,米洛塞維奇在選舉中獲勝了。
它們不是自由公平的選舉。他的政權最重要的單一支柱是國家電視台,被用來維持民族主義的受困心理,在居住於沒有什麼其他信息來源的鄉下和小鎮上的人們中間尤其是如此。因此,他最早的政治對手之一,武克.德拉斯科維奇(Vuk DraškoviÊ)稱之為電視巴士底獄。但是也有設防的獨立廣播電台和私營報紙。人們可以旅行,幾乎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還可以上街遊行。反對黨可以組織活動和競選,在議會和市議會中也有他們的代表。米洛塞維奇掌權的另一種方法是在他們中間巧妙周旋,分而治之。比如,上面提到的德拉斯科維奇受命接管了貝爾格勒市政府,人們都說他同時也接收了隨之而來的致富源泉。
在這個貧窮、目前深陷腐敗的國家,錢財在政壇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所指的錢財是指塞在黑色皮夾克口袋裡或裝在手提箱裡帶出國的大量德國馬克。政界、商界和有組織犯罪機構之間的邊界完全消失了。米洛塞維奇的可惡兒子馬可是一名商人,同時也是個強盜。他有眾多家產,其中一家位於貝爾格勒市中心的香水店叫斯康達(Skandal),這個名字真是再合適不過了(諧音 scandal,意為「醜聞」)。十月六日,星期五晚,我和一群人站在一起注視著這家被洗劫一空、燒焦的店。他帶著米洛塞維奇的孫子馬爾科逃到莫斯科。從黑手黨的角度來理解,執政的家庭是更大家庭的核心。然而,這位「教父」還在表面上保留了憲法的形式,定期在選舉中尋求連任。他獲勝得益於電視巴士底獄和有些悄無聲息的投票舞弊,還因為他可以利用四分五裂的反對派,依靠真正相當高的支持率。
只有知道這些背景,才能理解為何七月初米洛塞維奇決定修改憲法,尋求直接連任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總統。現在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了。但當初,這樣認為的人寥寥無幾。
他自己呼籲在九月二十四日進行選舉,為什麼他會在選舉中敗北?最首要也最溫暖人心的部分答案無疑是:動員其他塞爾維亞人擊敗他。在「塞爾維亞人」都被妖魔化的情況下,再加上「他們」在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所作所為,人們常常無法堅定地說總是還有其他塞爾維亞人。一開始就有塞爾維亞人發表演說、寫文章和組織活動來反對米洛塞維奇。他們的鬥爭與在蘇聯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異見分子的鬥爭不同,但難度或者危險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他們。蘇聯的異見分子冒著被KGB逮捕入獄的危險。塞爾維亞的異見分子冒著在漆黑的小巷中被陌生的暗殺者槍殺的危險。他們人數不多,但總是有這麼一些人。
韋蘭.馬蒂奇(Veran MatiÊ)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身材粗壯,留著大黑鬍子,性格沉著冷靜。你總可以在他的辦公室裡看到他在一台輕巧的手提電腦上打字。馬蒂奇有一個敬業的記者團,又有西方的大量金融資助,於是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廣播電台—B92電台,科索沃戰爭剛爆發的時候,當局控制了這個電台,但它仍然在網上提供新聞。他還開辦了一個叫ANEM的網站,為不受米洛塞維奇控制的省級廣播電台和電視台提供獨立的新聞和時事節目。目前,「電視巴士底獄」譴責科什圖尼察和反對派是北約的走狗、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特工,但該網站卻泰然自若地告知貝爾格勒外面的人這場競選活動的真相。此外,還有一些不太知名的記者因為報導他們自認為是真相的東西鋃鐺入獄。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名為「奧特波爾」(Otpor)——意為「抵抗」——的學生運動。它成立於一九九八年,與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的抗議一脈相承,但更加激進。一名活動人士告訴我,在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舉辦的研討會上,奧特波爾的成員學習了其他地方的權力運動和非暴力反抗是如何組織的,從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到去年在克羅埃西亞的活動。這些都是「比較革命」專業的學生。但是他們自己添加了很多種創新的變化。比如,他們會穿著上面有「塞爾維亞的一切都不錯」字樣的T恤,出現在購買糖和石油的長隊中。他們舉著畫著緊握拳頭圖案的獨特橫幅,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抗警察。在革命爆發前的一年裡,有一千五百多名奧特波爾的活動分子被捕。在一九九八年的斯洛伐克選舉中,民間團體的活動分子推翻了弗拉基米爾.梅恰爾(Vladimir MeËiar),與此一樣,他們組織了運動來「搖動投票」。流行的搖滾音樂會與出去投票的信息相結合。他們設計了一個口號,「Vreme je!」即「時機已到!」或「現在是時候了!」而這恰恰是一九八九年人們在布拉格所喊的口號。隨後他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口號,「Gotov je!」即「他完蛋了!」作為這場革命的名言,塗在米洛塞維奇的海報上,寫在帽子和橫幅上,塗在這座城市的牆壁上,還被十萬人喊著。
在這個獨立活動的世界中,還有許多人——在斯洛伐克,他們被稱為「第三部門」——致力於該事業。獨立的民意調查者(其中一些人由美國資助)會定期作調查,調查表明科什圖尼察正在取得勝利。競選志願者和獨立的選舉監督人員數不勝數。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歐洲,西方在「民間團體」項目上浪費了數百萬美元。但是這次,在這裡,確實是物有所值了。
其次是意見迥異的反對黨最終團結起來的事實。可以肯定的是,並不是所有反對黨。最大的反對黨,即武克.德拉斯科維奇的塞爾維亞復興運動黨(Serbian Renewal Movement),拒絕加入。此外,蒙特內哥羅總統米洛.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Ê)呼籲抵制選舉,因而讓米洛塞維奇實際上拿到了所有留下來的蒙特內哥羅人的選票。但是還是有十八個黨一起加入了塞爾維亞民主反對黨(Democratic Opposition of Serbia)。其中最大的黨是民主黨,該黨黨首是反對派領導人佐蘭.金吉奇(Zoran DjindjiÊ),他任職很久了,但容易妥協,不得人心。
米洛塞維奇敗北的第三個原因是,金吉奇和其他人徹底平息了他們內部的爭執,一致提名讓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當候選人。科什圖尼察是小塞爾維亞民主黨的領袖,該黨在二十世紀九○年代初從民主黨分離出來。科什圖尼察不太願意去競選—他自嘲道,自己是第一位猶豫不決的選民,但這是一個完美的選擇,因為他集反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不腐敗和遲鈍四種品質於一身,獨一無二。
科什圖尼察從來都不屬共產黨。他是一名憲法律師和政治學家,一九七○年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反對黨在多黨制中的作用。他後來翻譯了《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還專門研究了托克維爾(Tocqueville)和洛克(Locke)。由於反對狄托(Tito)一九七四年頒布的憲法,稱該憲法對塞爾維亞人不公平,他被貝爾格勒大學開除。與大多數其他反對黨領導人不同,他竟然從未見過米洛塞維奇,直到十月六日,星期五,軍隊總司令內博伊沙.帕夫科維奇(Nebojsa PavkoviÊ)才給即將離任和上任的總統安排了一次簡短的會面。科什圖尼察自豪地告訴我:「因此我是在他垮台的時候第一次見到他的。」
他是個溫和的民族主義者,曾支持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強烈批評北約在科索沃發動的戰爭。與德拉斯科維奇和金吉奇不同,人們從未看到他與馬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過從甚密。轟炸期間,他一直留在貝爾格勒,而金吉奇逃到了蒙特內哥羅,或許正是擔心自己的小命不保。他不腐敗。我基本上還未見過比他的黨務辦公室還簡陋的辦公室。他和妻子還有兩隻貓一起住在一個小公寓裡,開的是一輛破舊不堪的南斯拉夫牌汽車。這又與其他反對派領導人(尤其是金吉奇和德拉斯科維奇)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穿著光鮮亮麗的西服,開著快車,人們普遍認為他們貪汙腐敗。在後鄂圖曼帝國時代的世界裡,大多數政客都是這樣做的,由來已久。
他的一大劣勢是他的遲鈍。不過在這件事上,連遲鈍也是一項優勢。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他們喜歡他慢條斯理、行動遲鈍的風格。他們說,遲鈍非常受歡迎,與米洛塞維奇悲壯的裝模作樣和他的許多對手,比如說武克.德拉斯科維奇的誇誇其談形成對比。一位首席獨立記者告訴我:「你懂的,我想要一位乏味的總統,還想生活在一個乏味的國家裡。」
話說回來,畢竟科什圖尼察也沒有那麼遲鈍。他發現自己成為祖國解放運動的領袖,備受鼓舞(誰會不受鼓舞呢),於是帶來了一些英勇無畏又令人難忘的時刻。他在議會和電視台被占領的那天晚上所說的「晚上好,解放的塞爾維亞」將載入史冊。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至少有二百四十萬塞爾維亞人在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的名字旁邊畫了一個圓圈。當然,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讓他們這樣做的所有動機,但是有人給我提供了兩個引人注目的部分解釋。
一個解釋與北約的轟炸有關。我問政客和分析人士,他們認為革命是何時開始的。有幾個人表示,常常噘著嘴說:嗯,老實說,科索沃戰爭結束的時候。在戰爭期間和戰爭一結束後,都在國旗下舉行過愛國集會,米洛塞維奇也從中受益。但是這也太荒唐,太「歐威爾」(Orwellian)了,國家電視台竟然聲稱這個歷史性的明顯戰敗是一次勝利:塞爾維亞的耶路撒冷—科索沃—輸得其所。在經濟方面,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在轟炸的影響下,每一項勒緊褲腰帶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科盧巴拉煤礦的礦工—他們的罷工對這場革命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告訴我,戰後他們的工資從平均每月一百五十德國馬克降到了七十德國馬克的低位。對此給出的解釋是為戰後重建交稅。但這讓他們怒不可遏。
正如韋蘭.馬蒂奇所說,當時米洛塞維奇「競選不是為了對抗我們,而是為了對抗北約」。然而,這沒有起作用,因為人們內心更深處認為:「不過,他對抗北約輸了,不是嗎?」如果馬蒂奇說得對,那麼科什圖尼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他所譴責的轟炸的受益人。當然,這種解釋疑點重重,永遠無法證實。但戰爭推波助瀾引發革命在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