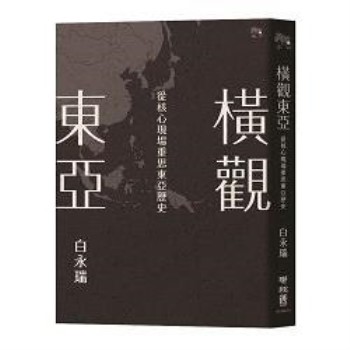第一章 從「核心現場」探索東亞共生之路 王艷麗、謝秀梅譯
一、沖繩歸屬問題爭議再起的意義
沖繩是中國領土嗎?二○一三年五月八日中國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有關沖繩歸屬問題的論文(題要),由此在中國和日本掀起了一場關於沖繩歷史定位的大討論。曾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中國近代史專家張海鵬與邊疆問題(特別是南海問題)專家李國強共同撰寫的這篇文章,重點是要從中找尋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的歷史根據。但該文章結尾處「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的言論引發了軒然大波。文章中指出,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和沖繩都曾位於中國朝貢體制的版圖之內,甲午戰爭時期清軍戰敗後日本強占了上述地區,二戰後只是沒有重新歸還中國而已。作者張海鵬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解釋說,論文的目的並不是主張沖繩的主權屬於中國。之所以說沖繩歸屬問題懸而未決,是因為日本政府認為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屬於沖繩管轄,因此這種說法只不過是為了證明中國所主張的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不是日本領土而舉出的旁證。他對自己的學術觀點被別人誤解為主張沖繩是中國領土的事實感到吃驚,因此特意出面進行澄清。但他作為學術界的元老在中共黨報上發表這篇文章,不可避免地會讓外人猜測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政府的聲音。因此,外界有人分析這是中方為了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問題上占有先機而進行的心理戰,或者說是一種談判協商的戰術。所以就不難理解日本政府對此進行抗議和反駁的舉動了。
在東亞的領土糾紛和歷史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所發生的沖繩問題,再次證明了這絕不是圍繞著幾個島嶼發生的領土問題,而是由各自的歷史問題交織而成的。特別是在沖繩,原本存在的有關東亞近代史的結構性矛盾被進一步激化了。我所說的沖繩即是核心現場(之一)這一觀點變得更加清晰。
二、什麼是核心現場?
此前,我曾提出「雙重的周邊視角」理論,以便更好地分析東亞的歷史與現實。如果重新介紹一下的話,可以說它是在以西歐為中心的世界史發展過程中,東亞被迫走非主體化道路的周邊視角與被禁錮於東亞內部等級序列中的周邊視角同時需要的一種問題意識。我所說的中央與周邊的關係不是單純的地理位置關係,而是無限連鎖關係和無限壓迫轉讓關係。「雙重的周邊視角」是對這種關係的認識,也是為克服這種情況而進行的實踐。在提出這個視角的同時,還強調要從歷史的脈絡角度,特別是在世界秩序的等級序列內對中心與周邊的關係進行具體分析。但東亞地區並不是一個平面而均質的國家組合體,而是由多層中心和周邊劃分成的立體和非均質的地區。因此,為提高「雙重的周邊視角」的說服力,應相應地增加對複合的多層時空的認識;要同時結合全球性及歷經了長期若干個時間段的討論、中小規模地區以及中長期課題進行思考,並與一貫的實踐進行對接。核心現場就是要求對複合的多層時空進行認知的地方,也是這個理論最適用的對象。這點和孫歌所說的歷史「關節點」也是相通的。時空矛盾凝聚的地方也就是核心現場了。除沖繩以外,分斷狀態下的朝鮮半島、台灣等都屬於(我最近所關注的)核心現場。按中華帝國─日本帝國─美帝國順序發生的軸心變動,使得等級森嚴的東亞秩序所產生的歷史矛盾日積月累,同時在殖民與冷戰的雙重影響下,傳統空間遭到嚴重破壞也導致糾紛不斷增加。如此所產生的時空矛盾與糾紛相互關聯,不斷進行惡性循環,使得隨著解決問題的深入,為締造東亞和平而作為良性循環媒介的波及力變得越來越大。正如加文.麥考馬克(Gavan McCormack)所準確描述的那樣,核心現場「如同用來判斷能否克服日本的帝國主義與美國的冷戰霸權主義時代的試金石」。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各自對待生活的態度肯定也會發生變化。我們期待著由核心現場來實現這一夢想。
三、核心現場與主權的再構成
東亞近代史的矛盾與糾紛聚集而成的核心現場,特徵是指主權從多層性開始變得更加集中。我們再回到本文的線索──沖繩問題上去。針對《人民日報》的文章,沖繩的媒體所做出的反應是「複雜且非一邊倒地批判中國」。為什麼會這樣呢?一是因為雖然大多數沖繩縣居民對現在的中國持批判態度,但對過去的中國卻有歷史性的親近感。另一個是因為日本是以暴力手段將沖繩編入日本版圖,至今仍將沖繩置於民主主義的框架之外。然儘管如此,沖繩的媒體也不認同根據與中國具有儀禮上朝貢關係的歷史事實而將琉球視為中國的屬國,且充滿沖繩屬於中國語氣的文章。另一方面沖繩的媒體也認為《人民日報》的文章「從國際觀點來分析琉球問題有其意義」。
單從這個反應上來看,沖繩的主權歸屬問題可以說並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對主權問題做更深層次思考的話,會發現他們那些複雜的反應都是有歷史淵源的。眾所周知,從十五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的明清王朝與琉球王國一直保持著朝貢關係。而且即使在一六○九年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王國,並建立幕藩體制進行干涉之後,琉球一邊臣服於日本幕府統治的同時,一邊還繼續向中國朝貢,維持著雙重被支配體系(即一支兩屬)。但這種關係的形成,從琉球王國的角度來看,它是為了維繫政權的存在而自發並又積極地選擇了這種從屬於雙方的彈性外交政策的結果;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種選擇既可以確保自身海上貿易據點的穩定,從戰略防禦角度考慮還具有實用性,同時還可以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提供佐證。處於非對稱關係的兩個當事人,從自身戰略角度出發確立了這種關係,這絕不是中國單方面強壓導致的結果(如同近代的國境與領土),因此無法確認這是一種明晰的歸屬關係。同時,依照「琉球處分」,琉球被編入沖繩縣成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之後,從主權角度來看,沖繩的地位並不是那麼簡單。這裡是日本帝國向作為國民國家進行轉變和殖民擴張的交織地帶,在一段時期內一直作為國內殖民地存在。這種主權上的複雜性,用二戰後對美軍占領下的地位說明用語「潛在主權」來詮釋的話,也許更為貼切。針對美軍占領狀態下的沖繩地位,美日兩國協商後給出的定義為「潛在主權」。即由美國來行使管轄權(administrative rights)進行統治,而日本則行使對沖繩的潛在主權。
這種國家主權歸屬的複雜性,在一九七二年沖繩歸還日本之後也沒有徹底消除。歸還沖繩之際,受日本國內強烈的(民族主義)潮流影響,出現了眾多分支來針對沖繩應有身分進行研究。從一直被日本政府和國民所忽視的現實出發,根據「沖繩應具有的面孔」所強調的重點是有差別的(例如:《再問日本》、《反歸還思想》、《沖繩意識化的溯根》等),但卻強烈地反映出沖繩人的真實想法。但,即便是沖繩納入了日本版圖,沖繩人對實現主權意志的期待依舊與殘酷的現實發生了碰撞。出現這種挫折的必然性,是因為沖繩並沒有歸還給了戰後和平憲法框架下的日本,而是歸還給現實中存在的《美日安保條約》下的日本。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只占日本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一個縣的居民,不可能對由來自日本全國各地代表構成的代議制民主主義的表決體制產生任何影響。特別是仍舊(或者說比之前擴大了)存在的美國基地作為「構造性的沖繩差別」的根源,讓沖繩人民現在也對回歸日本本土的意義,或者說主權的意義充滿疑問。
但如果多留意沖繩以外的其他核心現場相關聯的情況的話,沖繩所經歷的這種主權多層性問題就很容易理解。對此,讓我們來看一下台灣。
上面所說的《人民日報》報導,在台灣當地也掀起了小波瀾。支持台獨(和民進黨)傾向的《自由時報》,對該報導鮮明地指出這是中國在強辭奪理,是霸權主義的表現。和它不同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並沒有闡明自身的立場,只有《中國時報》的評論比較引人注目,它認為領土的歷史根據是由現實國家間角力的結果所左右的,最終將由中日美三國國力變化來決定該問題走向。如果支持中國立場的話,則會被看成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如果支持日本立場的話,就會被人解讀為有台獨傾向,因此可以看出它的左右為難。但通過這一事件,「台灣地位未定論」有可能重新抬頭。事實上,如果連沖繩也是地位未定的話,那麼台灣十有八九也會被認為其地位未定。在台灣,主權的複雜性是個歷史問題,也是個現實問題。
曾經作為中國朝貢國的韓國,對《人民日報》所載文章所引起的爭議也進行了報導,但只是將爭議的緣由和經過進行了報導,並沒有對此發表任何立場。但由於東亞的歷史問題都是與領土相關連的,因此對於沖繩主權歸屬引起的爭議,韓國隨時局的變化完全可以對此巧以利用。
其實韓國在主權問題上也面臨過困擾。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韓國不僅是大清國朝貢體制下的一員,同時又與眾多國家締結了條約關係。在這種(兩截體制的)國際秩序下,韓國很早就對主權的複雜性有了清醒的認識。後來在殖民地時期,又喪失了主權,醒悟到恢復主權的重要性。在冷戰時期,朝鮮半島被置於分斷狀態之中,大韓民國在以美國為中心的非正式帝國框架中又經歷了「夾縫中的主權」(perforated sovereignty)。而在加強南北韓間的相關交流與合作過程中曾提出過有關朝鮮半島統一的富有創意的思考及實踐,這期間提出的「複合國家」論(即朝鮮半島人民在相互承認對方國家主權的情況下,採取漸近的和分階段方式實現國家的再次合併,建設一個非單一形式的新型國家)就是對主權問題的一個偶然的思考範例。
在東亞的核心現場,我們對主權的複雜性可以說是感同身受的。但是從東亞整個格局來看,隨著領土與歷史相互交織的糾紛不斷深化,主權的正當性主張深入人心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了解決這些爭執,單純地去否定固有領土論或主權(的崇高性)也是一種不現實的舉動。與此相對照,如果將固有領土論設定在一個新的領域,並將不斷弱化固有領土論的漸近式修正主義路線作為解決領土糾紛的短期而有效的方案,也許會更具有說服力。再進一步的話,借助主權意識出現龜裂而產生的彈力,與重組主權意識這個中長期課題緊緊聯繫在一起也顯得尤為重要。在此期待著對主權分割/分享的討論能給我們一個有價值的啟發。
四、在核心現場擴大自治權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之後,專門研究核能與主權關係的日本哲學家中島隆博以賈克.德希達的「主權分享」為理論基礎,對主權的至高無上性乃至不可分割性進行挑戰,並將同一領域複數主權的重疊機制展望成能夠實現「即將到達的民主主義」的可能性。為此,他還引入了與國家主權和國民主權所不同的「人民主權」概念。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人民作為主權人,由於以統治主體的人民主權為基礎形成的統治主體可以分為若干個,他們可以自行以州或聯邦為單位分割國家主權或進一步去規畫小規模的地區主權,甚至那種超越國家的連帶形式也是可能的。
經歷了日本本土的震災並進行思想摸索後,在讀著他有關主權的再構成論的同時,我回想起了在沖繩提出的「生活圈」概念。兩者的問題意識是有相通之處的。
作為早期的朝鮮史研究學者,瑽村秀樹曾提出過將「作為定居外國人的在日朝鮮人」的生活世界定義為「跨越國境的生活圈」。由於他們那與祖國相連的紐帶是在觀念或意識的存在形式遷移中所積累出的生活狀態,而且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形成的。因此對他們來說,強迫他們回國(韓國或朝鮮)或是歸化(入籍日本)都與暴力措施無異。而且對他們來說,祖國並不是分裂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作為「本應存在的統一民族國家」在民眾的卓越智慧下,在自主地去經歷創造和變革過程中所必需的課題。
沖繩的知識界人士為超越國境與領土的概念,而創造性地引用了瑽村的生活圈理論。他們摒棄了抽象的、觀念性的固有領土論,提出了那些在生活上與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等爭議地區息息相關的漁民們的「生活圈」(在歷史上、文化上和經濟上有交流及合作關係的區域)概念。當我們關注這個可以保障生活實際利益的生活圈時,那麼同樣在生活上與該區域有著密切聯繫的台灣漁民就不能排除在外,要考慮到如何共處這一問題。這個構想可以說是在從期待超越《威斯特法倫和約》締結以來的固有領土論和主權概念的角度出發,與「主權分割/分享」的設想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但是,這個創造性的理論在日本政界卻被汙衊成是在為「中國的沖繩屬國論工程」服務。沖繩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可以說是日本國內對中國最具好感的地區,可是非但不能期待這個特點使沖繩成為「冷靜處理中日關係的先鋒」,反而成為它飽受攻擊的禍根。中國提出沖繩地位未定論如同是為迎合這個「右翼」思想激增的時代提供了的口實依據。我們可以說是由於中國的「失策」,導致日本出現「愚策」嗎?不管怎麼說,在面對禁錮於國家主權至上思想中的右翼勢力的想像力會去阻礙生活圈構想實施的情況下,沖繩民眾們如何發揮自身聰明智慧開闢一條對應之路呢?
這條路最初的開拓者雖說應是沖繩人自己,但我準備從彼此相關聯的核心現場角度、用連帶的思想來闡述一下個人觀點。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抨擊,不要迴避表明繼承中華帝國遺產的中國存在感(或者說是存在樣式)的責任,從開展回歸運動那一刻開始,我們將所堅持的自治.反戰.人權思想不斷進行昇華的做法也許就是我們所找的那條路。特別是要以人民主權概念為基礎,立足於生活中實際感受來進一步擴大自治權。沖繩民眾在長期的鬥爭中鍛鍊出了敏銳的國際政治洞察力,他們即便有追求沖繩獨立的想法,也不會草率地利用其社會規模提出這種要求。新崎盛暉提出的觀點是有必要引起我們重視的,即通過加強沖繩的自治權,敦促加快日本的國家改革,並期待著進一步衝擊到其背後的美日同盟關係。
沖繩知識界的這種立場與另一核心現象──韓國提出的「公民參與下的統一」思想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脈相通的。在二○○○年六.一五共同宣言中,南北韓首腦(排除包括武力統一或和平統一等單方面的吸收統一手段)提出了協商統一,即分階段、漸進式的朝鮮半島式的統一進程,這就加大了韓國公民參與其中的機會。白樂晴(Nak-chung Paik)一直在用(相對於南北韓政府的)第三方(也可以說成是六方會談中六方以外的第七方)的作用來烘托公民作用的重要性。朝鮮半島作為維持目前分斷體制下的世界秩序、以及對美國強硬派和軍工企業的武器裝備生產起決定性作用的核心現場,我們期待著公民參與下的統一能夠打破美國霸權主義的局面,通過不斷地對世界秩序進行變革謀求建設一個新形態下全球共同體的機會。
如上所述,在沖繩和朝鮮半島等(當然台灣等之外的事例也可以包括進去)核心現場開展的公民積極參與現象,可以說就是作為「雙重周邊」在反抗所受壓迫過程中的集體實踐。這是冷戰結束後為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同時也符合備受關注的加強多樣性主體自治權的趨勢。
五、東亞共生的條件
在東亞,擴大自治權的主體應該是對「共生感覺」感同身受的個人。這裡所說的共生感覺是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有機整體的感覺,不管好壞,我們都是近代文明化作用之下產生的,並都在不停地消耗著這種感覺,現在到了我們要修復這種感覺的時候了。
因此,為了在生活圈的具體基礎之上實現共生,有必要在歷史和現實中找出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經驗並加以提煉。而在核心現場所積累的經驗肯定是需要去優先探索的資源。這是在經歷了反差別倫理等生活世界的各階段後出現的,難道不該將其整合到一起統稱為「共生哲學」嗎?
共生,不同於只將自己所在共同體的存屬當作目標並追求閉塞的同質性的共同性原理,同時也區別於那種對孤獨個人實際存在的回歸。共生,承認與別人的不同,同時還去嘗試與這種不同建立聯繫。因此,它既存在於共同性之中,也超越了共同性去追求那種共生生活的方式。即不單純地否定共同性的矛盾,而是在意識到它的同時還依然照常生活的態度。也就是說,由於這種特性使得共生(即共同經營的生活)需在共苦(即共同承受痛苦)的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建立排除或同化差別的封閉共同體並不是目的,而是對被排除在外的個體負起責任,以多層次、橫跨的方式去實現結社和紐帶的方式。
最近,在東亞諸國中流傳著「共生」這個新創詞彙。比如說,與自然的共生、多元文化共生,同亞洲的共生等詞彙正在不斷地廣為流傳。但這裡是否也包含著需要共生擁抱安撫的共苦方面、現實中與矛盾發生衝突的方面、以及思想苦悶方面呢?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搞清楚的問題。這就是共生所要求的條件。
我們是否滿足共生所要求的條件呢?我想,對包括生活在核心現場中居民們的痛苦在內的整體生活,我們能夠有多少同感,這應該就是判斷這個問題的尺度之一吧。在這裡,我想講一個發生在沖繩地區的相關故事。在普天間美軍基地附近的佐喜真美術館常年展示著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大型圖畫〈沖繩戰之圖〉,裡面有很多被殘酷殺害的犧牲者,他們中間還有朝鮮人。停戰之後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與日本女性結婚後一起生活在久米島的朝鮮男性和其家人被屠殺,這就是所謂的「朝鮮人一家被殺事件」,這幅畫就是以此事件為題材創作的。這是一幅能夠喚醒我們麻木情感的畫,無論你是第一次看,還是第幾次看,去回應其中所發聲音的能力將會成為將分散的我們引向共生的力量。這將作為既是倫理的、又是政治實踐的原動力而發生作用。這種能力只有在各自面對痛苦時,發生生活方式改變的情況下,才能夠被正確地培養出來。因為這種能力才是(中心軸從中華帝國到日本帝國再到美帝國的演變中而排出等級的)東亞秩序的矛盾和紛爭在濃縮的日常生活苦痛中被激發出來的產物。
我們要開啟「共生的地平線」。對於開闢了天地的假想地平線,我們總是越接近就越感到它遙不可及。同樣的道理,所謂「共生」也是無法到達的新經驗世界。但是我相信,因為這個地平線是我能看到的世界,是我生活的空間,因此在其中有可能發生使我改變、同時也以此去改變別人的事情。換言之,開放的主體以開放的紐帶為中心,將私人的生活改變為共生的生活,這種事情終將會在未來得以實現。
一、沖繩歸屬問題爭議再起的意義
沖繩是中國領土嗎?二○一三年五月八日中國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有關沖繩歸屬問題的論文(題要),由此在中國和日本掀起了一場關於沖繩歷史定位的大討論。曾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中國近代史專家張海鵬與邊疆問題(特別是南海問題)專家李國強共同撰寫的這篇文章,重點是要從中找尋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的歷史根據。但該文章結尾處「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的言論引發了軒然大波。文章中指出,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和沖繩都曾位於中國朝貢體制的版圖之內,甲午戰爭時期清軍戰敗後日本強占了上述地區,二戰後只是沒有重新歸還中國而已。作者張海鵬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解釋說,論文的目的並不是主張沖繩的主權屬於中國。之所以說沖繩歸屬問題懸而未決,是因為日本政府認為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屬於沖繩管轄,因此這種說法只不過是為了證明中國所主張的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不是日本領土而舉出的旁證。他對自己的學術觀點被別人誤解為主張沖繩是中國領土的事實感到吃驚,因此特意出面進行澄清。但他作為學術界的元老在中共黨報上發表這篇文章,不可避免地會讓外人猜測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政府的聲音。因此,外界有人分析這是中方為了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問題上占有先機而進行的心理戰,或者說是一種談判協商的戰術。所以就不難理解日本政府對此進行抗議和反駁的舉動了。
在東亞的領土糾紛和歷史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所發生的沖繩問題,再次證明了這絕不是圍繞著幾個島嶼發生的領土問題,而是由各自的歷史問題交織而成的。特別是在沖繩,原本存在的有關東亞近代史的結構性矛盾被進一步激化了。我所說的沖繩即是核心現場(之一)這一觀點變得更加清晰。
二、什麼是核心現場?
此前,我曾提出「雙重的周邊視角」理論,以便更好地分析東亞的歷史與現實。如果重新介紹一下的話,可以說它是在以西歐為中心的世界史發展過程中,東亞被迫走非主體化道路的周邊視角與被禁錮於東亞內部等級序列中的周邊視角同時需要的一種問題意識。我所說的中央與周邊的關係不是單純的地理位置關係,而是無限連鎖關係和無限壓迫轉讓關係。「雙重的周邊視角」是對這種關係的認識,也是為克服這種情況而進行的實踐。在提出這個視角的同時,還強調要從歷史的脈絡角度,特別是在世界秩序的等級序列內對中心與周邊的關係進行具體分析。但東亞地區並不是一個平面而均質的國家組合體,而是由多層中心和周邊劃分成的立體和非均質的地區。因此,為提高「雙重的周邊視角」的說服力,應相應地增加對複合的多層時空的認識;要同時結合全球性及歷經了長期若干個時間段的討論、中小規模地區以及中長期課題進行思考,並與一貫的實踐進行對接。核心現場就是要求對複合的多層時空進行認知的地方,也是這個理論最適用的對象。這點和孫歌所說的歷史「關節點」也是相通的。時空矛盾凝聚的地方也就是核心現場了。除沖繩以外,分斷狀態下的朝鮮半島、台灣等都屬於(我最近所關注的)核心現場。按中華帝國─日本帝國─美帝國順序發生的軸心變動,使得等級森嚴的東亞秩序所產生的歷史矛盾日積月累,同時在殖民與冷戰的雙重影響下,傳統空間遭到嚴重破壞也導致糾紛不斷增加。如此所產生的時空矛盾與糾紛相互關聯,不斷進行惡性循環,使得隨著解決問題的深入,為締造東亞和平而作為良性循環媒介的波及力變得越來越大。正如加文.麥考馬克(Gavan McCormack)所準確描述的那樣,核心現場「如同用來判斷能否克服日本的帝國主義與美國的冷戰霸權主義時代的試金石」。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各自對待生活的態度肯定也會發生變化。我們期待著由核心現場來實現這一夢想。
三、核心現場與主權的再構成
東亞近代史的矛盾與糾紛聚集而成的核心現場,特徵是指主權從多層性開始變得更加集中。我們再回到本文的線索──沖繩問題上去。針對《人民日報》的文章,沖繩的媒體所做出的反應是「複雜且非一邊倒地批判中國」。為什麼會這樣呢?一是因為雖然大多數沖繩縣居民對現在的中國持批判態度,但對過去的中國卻有歷史性的親近感。另一個是因為日本是以暴力手段將沖繩編入日本版圖,至今仍將沖繩置於民主主義的框架之外。然儘管如此,沖繩的媒體也不認同根據與中國具有儀禮上朝貢關係的歷史事實而將琉球視為中國的屬國,且充滿沖繩屬於中國語氣的文章。另一方面沖繩的媒體也認為《人民日報》的文章「從國際觀點來分析琉球問題有其意義」。
單從這個反應上來看,沖繩的主權歸屬問題可以說並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對主權問題做更深層次思考的話,會發現他們那些複雜的反應都是有歷史淵源的。眾所周知,從十五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的明清王朝與琉球王國一直保持著朝貢關係。而且即使在一六○九年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王國,並建立幕藩體制進行干涉之後,琉球一邊臣服於日本幕府統治的同時,一邊還繼續向中國朝貢,維持著雙重被支配體系(即一支兩屬)。但這種關係的形成,從琉球王國的角度來看,它是為了維繫政權的存在而自發並又積極地選擇了這種從屬於雙方的彈性外交政策的結果;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種選擇既可以確保自身海上貿易據點的穩定,從戰略防禦角度考慮還具有實用性,同時還可以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提供佐證。處於非對稱關係的兩個當事人,從自身戰略角度出發確立了這種關係,這絕不是中國單方面強壓導致的結果(如同近代的國境與領土),因此無法確認這是一種明晰的歸屬關係。同時,依照「琉球處分」,琉球被編入沖繩縣成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之後,從主權角度來看,沖繩的地位並不是那麼簡單。這裡是日本帝國向作為國民國家進行轉變和殖民擴張的交織地帶,在一段時期內一直作為國內殖民地存在。這種主權上的複雜性,用二戰後對美軍占領下的地位說明用語「潛在主權」來詮釋的話,也許更為貼切。針對美軍占領狀態下的沖繩地位,美日兩國協商後給出的定義為「潛在主權」。即由美國來行使管轄權(administrative rights)進行統治,而日本則行使對沖繩的潛在主權。
這種國家主權歸屬的複雜性,在一九七二年沖繩歸還日本之後也沒有徹底消除。歸還沖繩之際,受日本國內強烈的(民族主義)潮流影響,出現了眾多分支來針對沖繩應有身分進行研究。從一直被日本政府和國民所忽視的現實出發,根據「沖繩應具有的面孔」所強調的重點是有差別的(例如:《再問日本》、《反歸還思想》、《沖繩意識化的溯根》等),但卻強烈地反映出沖繩人的真實想法。但,即便是沖繩納入了日本版圖,沖繩人對實現主權意志的期待依舊與殘酷的現實發生了碰撞。出現這種挫折的必然性,是因為沖繩並沒有歸還給了戰後和平憲法框架下的日本,而是歸還給現實中存在的《美日安保條約》下的日本。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只占日本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一個縣的居民,不可能對由來自日本全國各地代表構成的代議制民主主義的表決體制產生任何影響。特別是仍舊(或者說比之前擴大了)存在的美國基地作為「構造性的沖繩差別」的根源,讓沖繩人民現在也對回歸日本本土的意義,或者說主權的意義充滿疑問。
但如果多留意沖繩以外的其他核心現場相關聯的情況的話,沖繩所經歷的這種主權多層性問題就很容易理解。對此,讓我們來看一下台灣。
上面所說的《人民日報》報導,在台灣當地也掀起了小波瀾。支持台獨(和民進黨)傾向的《自由時報》,對該報導鮮明地指出這是中國在強辭奪理,是霸權主義的表現。和它不同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並沒有闡明自身的立場,只有《中國時報》的評論比較引人注目,它認為領土的歷史根據是由現實國家間角力的結果所左右的,最終將由中日美三國國力變化來決定該問題走向。如果支持中國立場的話,則會被看成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如果支持日本立場的話,就會被人解讀為有台獨傾向,因此可以看出它的左右為難。但通過這一事件,「台灣地位未定論」有可能重新抬頭。事實上,如果連沖繩也是地位未定的話,那麼台灣十有八九也會被認為其地位未定。在台灣,主權的複雜性是個歷史問題,也是個現實問題。
曾經作為中國朝貢國的韓國,對《人民日報》所載文章所引起的爭議也進行了報導,但只是將爭議的緣由和經過進行了報導,並沒有對此發表任何立場。但由於東亞的歷史問題都是與領土相關連的,因此對於沖繩主權歸屬引起的爭議,韓國隨時局的變化完全可以對此巧以利用。
其實韓國在主權問題上也面臨過困擾。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韓國不僅是大清國朝貢體制下的一員,同時又與眾多國家締結了條約關係。在這種(兩截體制的)國際秩序下,韓國很早就對主權的複雜性有了清醒的認識。後來在殖民地時期,又喪失了主權,醒悟到恢復主權的重要性。在冷戰時期,朝鮮半島被置於分斷狀態之中,大韓民國在以美國為中心的非正式帝國框架中又經歷了「夾縫中的主權」(perforated sovereignty)。而在加強南北韓間的相關交流與合作過程中曾提出過有關朝鮮半島統一的富有創意的思考及實踐,這期間提出的「複合國家」論(即朝鮮半島人民在相互承認對方國家主權的情況下,採取漸近的和分階段方式實現國家的再次合併,建設一個非單一形式的新型國家)就是對主權問題的一個偶然的思考範例。
在東亞的核心現場,我們對主權的複雜性可以說是感同身受的。但是從東亞整個格局來看,隨著領土與歷史相互交織的糾紛不斷深化,主權的正當性主張深入人心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了解決這些爭執,單純地去否定固有領土論或主權(的崇高性)也是一種不現實的舉動。與此相對照,如果將固有領土論設定在一個新的領域,並將不斷弱化固有領土論的漸近式修正主義路線作為解決領土糾紛的短期而有效的方案,也許會更具有說服力。再進一步的話,借助主權意識出現龜裂而產生的彈力,與重組主權意識這個中長期課題緊緊聯繫在一起也顯得尤為重要。在此期待著對主權分割/分享的討論能給我們一個有價值的啟發。
四、在核心現場擴大自治權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之後,專門研究核能與主權關係的日本哲學家中島隆博以賈克.德希達的「主權分享」為理論基礎,對主權的至高無上性乃至不可分割性進行挑戰,並將同一領域複數主權的重疊機制展望成能夠實現「即將到達的民主主義」的可能性。為此,他還引入了與國家主權和國民主權所不同的「人民主權」概念。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人民作為主權人,由於以統治主體的人民主權為基礎形成的統治主體可以分為若干個,他們可以自行以州或聯邦為單位分割國家主權或進一步去規畫小規模的地區主權,甚至那種超越國家的連帶形式也是可能的。
經歷了日本本土的震災並進行思想摸索後,在讀著他有關主權的再構成論的同時,我回想起了在沖繩提出的「生活圈」概念。兩者的問題意識是有相通之處的。
作為早期的朝鮮史研究學者,瑽村秀樹曾提出過將「作為定居外國人的在日朝鮮人」的生活世界定義為「跨越國境的生活圈」。由於他們那與祖國相連的紐帶是在觀念或意識的存在形式遷移中所積累出的生活狀態,而且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形成的。因此對他們來說,強迫他們回國(韓國或朝鮮)或是歸化(入籍日本)都與暴力措施無異。而且對他們來說,祖國並不是分裂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作為「本應存在的統一民族國家」在民眾的卓越智慧下,在自主地去經歷創造和變革過程中所必需的課題。
沖繩的知識界人士為超越國境與領土的概念,而創造性地引用了瑽村的生活圈理論。他們摒棄了抽象的、觀念性的固有領土論,提出了那些在生活上與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等爭議地區息息相關的漁民們的「生活圈」(在歷史上、文化上和經濟上有交流及合作關係的區域)概念。當我們關注這個可以保障生活實際利益的生活圈時,那麼同樣在生活上與該區域有著密切聯繫的台灣漁民就不能排除在外,要考慮到如何共處這一問題。這個構想可以說是在從期待超越《威斯特法倫和約》締結以來的固有領土論和主權概念的角度出發,與「主權分割/分享」的設想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但是,這個創造性的理論在日本政界卻被汙衊成是在為「中國的沖繩屬國論工程」服務。沖繩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可以說是日本國內對中國最具好感的地區,可是非但不能期待這個特點使沖繩成為「冷靜處理中日關係的先鋒」,反而成為它飽受攻擊的禍根。中國提出沖繩地位未定論如同是為迎合這個「右翼」思想激增的時代提供了的口實依據。我們可以說是由於中國的「失策」,導致日本出現「愚策」嗎?不管怎麼說,在面對禁錮於國家主權至上思想中的右翼勢力的想像力會去阻礙生活圈構想實施的情況下,沖繩民眾們如何發揮自身聰明智慧開闢一條對應之路呢?
這條路最初的開拓者雖說應是沖繩人自己,但我準備從彼此相關聯的核心現場角度、用連帶的思想來闡述一下個人觀點。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抨擊,不要迴避表明繼承中華帝國遺產的中國存在感(或者說是存在樣式)的責任,從開展回歸運動那一刻開始,我們將所堅持的自治.反戰.人權思想不斷進行昇華的做法也許就是我們所找的那條路。特別是要以人民主權概念為基礎,立足於生活中實際感受來進一步擴大自治權。沖繩民眾在長期的鬥爭中鍛鍊出了敏銳的國際政治洞察力,他們即便有追求沖繩獨立的想法,也不會草率地利用其社會規模提出這種要求。新崎盛暉提出的觀點是有必要引起我們重視的,即通過加強沖繩的自治權,敦促加快日本的國家改革,並期待著進一步衝擊到其背後的美日同盟關係。
沖繩知識界的這種立場與另一核心現象──韓國提出的「公民參與下的統一」思想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脈相通的。在二○○○年六.一五共同宣言中,南北韓首腦(排除包括武力統一或和平統一等單方面的吸收統一手段)提出了協商統一,即分階段、漸進式的朝鮮半島式的統一進程,這就加大了韓國公民參與其中的機會。白樂晴(Nak-chung Paik)一直在用(相對於南北韓政府的)第三方(也可以說成是六方會談中六方以外的第七方)的作用來烘托公民作用的重要性。朝鮮半島作為維持目前分斷體制下的世界秩序、以及對美國強硬派和軍工企業的武器裝備生產起決定性作用的核心現場,我們期待著公民參與下的統一能夠打破美國霸權主義的局面,通過不斷地對世界秩序進行變革謀求建設一個新形態下全球共同體的機會。
如上所述,在沖繩和朝鮮半島等(當然台灣等之外的事例也可以包括進去)核心現場開展的公民積極參與現象,可以說就是作為「雙重周邊」在反抗所受壓迫過程中的集體實踐。這是冷戰結束後為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同時也符合備受關注的加強多樣性主體自治權的趨勢。
五、東亞共生的條件
在東亞,擴大自治權的主體應該是對「共生感覺」感同身受的個人。這裡所說的共生感覺是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有機整體的感覺,不管好壞,我們都是近代文明化作用之下產生的,並都在不停地消耗著這種感覺,現在到了我們要修復這種感覺的時候了。
因此,為了在生活圈的具體基礎之上實現共生,有必要在歷史和現實中找出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經驗並加以提煉。而在核心現場所積累的經驗肯定是需要去優先探索的資源。這是在經歷了反差別倫理等生活世界的各階段後出現的,難道不該將其整合到一起統稱為「共生哲學」嗎?
共生,不同於只將自己所在共同體的存屬當作目標並追求閉塞的同質性的共同性原理,同時也區別於那種對孤獨個人實際存在的回歸。共生,承認與別人的不同,同時還去嘗試與這種不同建立聯繫。因此,它既存在於共同性之中,也超越了共同性去追求那種共生生活的方式。即不單純地否定共同性的矛盾,而是在意識到它的同時還依然照常生活的態度。也就是說,由於這種特性使得共生(即共同經營的生活)需在共苦(即共同承受痛苦)的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建立排除或同化差別的封閉共同體並不是目的,而是對被排除在外的個體負起責任,以多層次、橫跨的方式去實現結社和紐帶的方式。
最近,在東亞諸國中流傳著「共生」這個新創詞彙。比如說,與自然的共生、多元文化共生,同亞洲的共生等詞彙正在不斷地廣為流傳。但這裡是否也包含著需要共生擁抱安撫的共苦方面、現實中與矛盾發生衝突的方面、以及思想苦悶方面呢?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搞清楚的問題。這就是共生所要求的條件。
我們是否滿足共生所要求的條件呢?我想,對包括生活在核心現場中居民們的痛苦在內的整體生活,我們能夠有多少同感,這應該就是判斷這個問題的尺度之一吧。在這裡,我想講一個發生在沖繩地區的相關故事。在普天間美軍基地附近的佐喜真美術館常年展示著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大型圖畫〈沖繩戰之圖〉,裡面有很多被殘酷殺害的犧牲者,他們中間還有朝鮮人。停戰之後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與日本女性結婚後一起生活在久米島的朝鮮男性和其家人被屠殺,這就是所謂的「朝鮮人一家被殺事件」,這幅畫就是以此事件為題材創作的。這是一幅能夠喚醒我們麻木情感的畫,無論你是第一次看,還是第幾次看,去回應其中所發聲音的能力將會成為將分散的我們引向共生的力量。這將作為既是倫理的、又是政治實踐的原動力而發生作用。這種能力只有在各自面對痛苦時,發生生活方式改變的情況下,才能夠被正確地培養出來。因為這種能力才是(中心軸從中華帝國到日本帝國再到美帝國的演變中而排出等級的)東亞秩序的矛盾和紛爭在濃縮的日常生活苦痛中被激發出來的產物。
我們要開啟「共生的地平線」。對於開闢了天地的假想地平線,我們總是越接近就越感到它遙不可及。同樣的道理,所謂「共生」也是無法到達的新經驗世界。但是我相信,因為這個地平線是我能看到的世界,是我生活的空間,因此在其中有可能發生使我改變、同時也以此去改變別人的事情。換言之,開放的主體以開放的紐帶為中心,將私人的生活改變為共生的生活,這種事情終將會在未來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