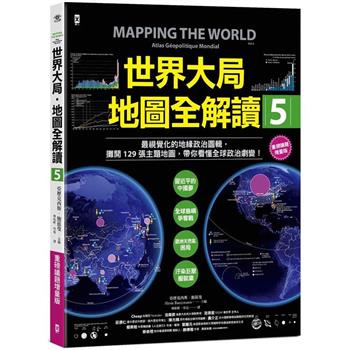【Ch 4 烏克蘭:世界戰火的中心】(節錄)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原已淪為次要的國際時事,卻從2022年2月24日起發生了出乎意料的劇烈變化。雖說烏克蘭與美國已預想到俄羅斯可能入侵頓巴斯、甚至整個烏克蘭,但從俄羅斯總統普丁於2月21日發表的談話,完全無法預料戰事會升級到如此程度。如今,這場戰爭不僅震撼歐洲,甚至對全世界的地緣政治皆造成重大影響。
◎攸關歐洲集體安全的戰略要地
烏克蘭處於黑海之北,橫跨歐亞大草原和歐洲中部的波利西亞(Polesia)地區,四周幾乎沒有天然邊界,地理位置特殊,可說是一個各方強權投射勢力的空間。烏克蘭是歐洲最大的國家,包括克里米亞在內,面積為60萬3,550平方公里,然而土地卻輪番遭到外來勢力占領。十六世紀,烏克蘭被併入君主制的波蘭-立陶宛聯邦,至1667年又遭到俄羅斯沙皇國控制。其後,烏克蘭便主要固著於俄羅斯世界,西部的加利西亞地區(Galicie)則先後受到奧匈帝國和波蘭統治,直到1939年才併入蘇聯,而烏克蘭獨特的國族身分也於焉誕生(參見圖2、3)。
一次又一次受到外來者占領,讓烏克蘭在地緣戰略上更顯得至關重要。日耳曼人(Germanic)認為烏克蘭是中歐與東歐和平的關鍵。對於當時正在尋找資源和機會的日耳曼人而言,德國一旦控制了烏克蘭,不僅能大大增強實力,進而創造一個自主經濟空間,脫離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主導的世界經濟;同時也能在俄羅斯帝國將觸角日漸深入德意志帝國的斯拉夫(Slav)少數民族之際,打造出一面防禦俄羅斯勢力的屏障。此外,控制烏克蘭也意味著打開殖民加利西亞和黑海地區的大門,為德國開闢一條通往中東的陸上通道。到了納粹德國時期,因應其「生存空間」(Lebensraum)理論的概念,控制烏克蘭的主張再度浮上檯面。不過,賦予烏克蘭重大地緣政治意義的,是英國地理暨政治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 ∼ 1947年)。1904年他發表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指稱烏克蘭為一個「開放空間」,亞洲強權透過這個「開放空間」來「打擊」歐洲半島。為了歐洲全體的安全,控制烏克蘭是生死攸關之事。
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美國與歐洲競爭影響力的戰場上,烏克蘭的戰略地位顯得更為關鍵。烏克蘭於2014年爆發廣場革命以前,公民社會便已呈現「親西方vs.親俄羅斯」的兩極分化,同時也反映在烏克蘭的政治場域。基輔當局搖擺不定,不確定自己是否盼望與自由解放的歐洲(重新)建立連結,就此與俄羅斯分道揚鑣。烏克蘭早已獨立,至今卻仍未能從俄羅斯世界抽身,而俄烏戰爭更反映出這樣的地理現實所孕育的權力關係。
◎俄羅斯虛構的烏克蘭歷史?
2021年7月,普丁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烏克蘭和俄羅斯人民組成同一個、且是唯一一個政治實體,因此烏克蘭這個國家的存在缺乏正當依據。蘇聯內部的崩解、1990年代的政治混亂深深烙印在普丁心裡,他於1999年甫上台,便著手重建俄羅斯強權,而在他的計畫裡,烏克蘭至關重要。自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以來,普丁不僅著眼於戰略與經濟上的利害關係,更企圖披上「蘇聯解體後散落各地的『俄羅斯民族』的聚集者」、「『歷史俄羅斯』的捍衛者」的外衣;這個所謂「歷史俄羅斯」的領土範圍號稱與已解體的蘇聯邊界一致,烏克蘭則被視為一個應該糾正的歷史錯誤,被迫接受源自帝俄、蘇聯時代的老舊歷史與地理虛構的神話。
而俄羅斯所謂關於烏克蘭的「歷史真理」,建基於中世紀的基輔羅斯(參見圖1)。基輔羅斯(Kievan Rus’,約880 ∼ 1240年)在中世紀時期由來自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的瓦良格人(Varangian)所建立,曾是歐洲數一數二龐大且繁榮的國家,於988年更成為斯拉夫東正教的搖籃。而1721年才成立的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1721 ∼ 1917年),其前身「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oscow,1283 ∼ 1547年)與基輔羅斯相差四個世紀,卻毫不猶豫地自詡為羅斯人的「長女」。這個在史學界飽受爭議的「血緣關係」餵養了現今的俄羅斯論述,當代文本更為這種論述增添羽翼,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 ∼ 2008年)於1990年發表的《重建俄羅斯》(Rebuilding Russia),文中不僅創造了一個由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構成的「混合」俄羅斯民族,更合理化俄羅斯在烏克蘭東南部「收復領土」的行徑。
普丁的論點將俄羅斯民族精粹(essentialize)為語言及東正教文化,也呼應了他「編造共同記憶」政策的主要基底—蘇聯歷史。在2022年2月21日的演說中,普丁表示,烏克蘭是由列寧(Vladimir Lenin,1870 ∼ 1924年)在1917 ∼ 1923年的內戰之後建立的。儘管這種說法忽視烏克蘭曾於1918年獨立的事實,卻也讓1929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1878 ∼ 1953年)無預警終止的「列寧對蘇聯各加盟國政策」重新浮上檯面。此一政策對烏克蘭的主要方針是讓此前禁用的烏克蘭語(參見圖4)重新啟用和發展,目的是使當時新誕生的蘇聯成為一個可信賴的立國計畫,將一群國家、一群民族團結起來,走向共同的命運—共產主義。總而言之,「烏克蘭民族」此一概念既被過去某些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民族主義運動妖魔化,又在蘇聯反法西斯的戰爭論述中遭到忽視(好讓俄羅斯民族躍升為反法西斯的主要戰士),而普丁的目的就是合理化所謂「統一」的正當性。
◎普丁重拾「帝國塵埃」的野心
俄羅斯意圖在烏克蘭發動多方攻擊。烏克蘭首都基輔當然是俄軍最初的主要目標之一──占領基輔將是足以與1945年5月1日蘇聯紅軍占領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媲美的象徵,同時能夠合理化普丁「為烏克蘭『去納粹化』」的主張。但實際上,俄羅斯卻花了最多力氣在烏克蘭東部,這一點於2022年3月29日獲得證實。
併吞克里米亞能為俄羅斯聯邦帶來巨大的利益。克里米亞昔日曾是克里米亞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54年在「去史達林化」的實施者赫魯雪夫(Nikita Khrouchtchev,1894 ∼ 1971年)的主導下,劃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克里米亞半島的地理位置極為關鍵,因為其領海橫跨黑海和亞速海(Sea of Azov),對於俄羅斯來說是個重要的資源開採基地。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烏克蘭便企圖降低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而俄羅斯也設法應對。黑海底部至少蘊藏3,000億立方公尺的化石燃料資源,在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之前,烏克蘭政府一直積極開採黑海礦藏,相繼與產業巨頭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2012年)、殼牌(Shell;2013年)和布里斯瑪控股公司(BurismaHoldings;2014年)簽訂多項合約。一旦併吞克里米亞,俄羅斯便擁有專屬管道可以取得重要的談判資源,與歐盟對抗。此外,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這三個北約成員國共享黑海水域,俄羅斯若要與北約在黑海對抗,克里米亞是重要的軍事據點。自從收回1997年以來與烏克蘭共享的塞凡堡(Sevastopol)港口後,俄羅斯在黑海的軍事存在感大增(參見圖6)。克里米亞半島至今仍是一座「四面楚歌的圍城」,在國際制裁下,該半島與大陸之間為數不多的陸路通道受阻,不僅依賴俄羅斯投資,還得聽憑烏克蘭擺布,因為烏克蘭能藉由聶伯河(Dnipro River)上的水壩控制其85%的水源供應(參見圖5)。因此,俄羅斯從克里米亞發動攻勢,相當於用武力助克里米亞掙脫重圍。
頓巴斯地區昔日是蘇聯工業蓬勃發展的堡壘,在莫斯科政府的戰略中屬於符合「人道主義」的目標。普丁操弄「烏克蘭的『納粹政權』準備使頓巴斯地區的俄語族群種族滅絕」的說法,讓頓巴斯的分離主義死灰復燃,同時也正面回應西方支持科索沃(Kosovo)獨立(2008年生效)的作為。經年累月的戰火讓頓巴斯的工業和生態環境飽受摧殘,榮景不再(參見圖7)。亞速海旁的馬立波(Mariupol)是俄羅斯野心的焦點,這個擁有46萬2,000人(戰前統計)的大都會,工業生產占全烏克蘭的10%,共有50家大型企業聚集於此,且大部分是冶金業。其中首屈一指的要數亞速鋼鐵廠(Azovstal)和煉焦廠(Markhokhim),自2014年廣場革命以來,這家聯合企業就一刻不得閒。此外還有烏克蘭東南部,從頓內茨克一路延伸到敖德薩(Odessa),這塊區域可謂是地中海等溫暖海域的「陽台」,也是「新俄羅斯」(Novorossiya)這個歷史名詞的誕生地。「新俄羅斯」源自俄羅斯帝國女皇凱瑟琳二世(Catherine II,1762 ∼ 1796年在位)提出的「希臘計畫」,此一計畫於1780年代驅使俄羅斯帝國征服克里米亞,是一個帶有末世論東正教彌賽亞(Messiah)色彩的地緣政治虛構神話。
◎驅動俄羅斯與普丁的恐懼
俄羅斯渴望能藉由編造歷史記憶定義自己的身分,且永遠無法饜足。這種執念反映出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大陸國家害怕遭受圍困,因而產生不適感,同時也導向俄羅斯的國家主義(statism)以及與邊陲地區的關係。自從遭受來自東方(十五世紀的蒙古人)與西方(十七世紀的波蘭人)的入侵後,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策略在俄羅斯大行其道,深化發揚。這類所謂的「堡壘國家」不能承受領土縮減,因為或許會導致國家消失,而普丁極其重視這個問題。1989年以前,俄羅斯自認中、東歐能夠不受西方國家影響,因為中、東歐的「利害區」(area of interest,烏克蘭即是其中一部分)與蘇聯及其一黨專政緊密連結,而鐵幕和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的成員國也能為俄羅斯與西方和北約之間提供緩衝區。過去,這些邊陲地區皆有邊界且等級劃分清楚,如今則變得老舊僵化。歐盟與北約在2000年代相繼擴張,讓普丁再次產生歷史重演的想法。且由於美國的「體制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中國開始在一場場新的影響力戰爭中現身,帶動強化區域結構的趨勢,更加深了俄羅斯的恐懼。
2014年烏克蘭的廣場革命與2020年8月的白俄羅斯革命,都讓俄羅斯措手不及;而2020年11月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衝突過後,儼然是新一代鄂圖曼帝國的北約成員土耳其,也重新返回南高加索地區;緊接著,哈薩克又在2022年1月爆發政治衝突。對俄羅斯而言,這些鄰近國家皆是打破昔日均勢的風險因子(參見圖8),其帶來的壓力在在威脅到冷戰後艱難維持的平衡。因此,莫斯科當局把烏克蘭當作籌碼,挾持烏克蘭與西方重新討價還價,提議回到1993年以前大部分中、東歐國家都未加入北約的狀態。
莫斯科當局透過宣傳合理化這個「新《雅爾達密約》」(new Yalta),扭曲了真正的力量對比。首先,衝突爆發前,北約在烏克蘭部署的部隊人數從未超過4萬人,而在烏克蘭邊境
集結的俄羅斯士兵卻有15萬人;再者,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也澄清,美國從未口頭承諾北約不會向東擴張。
◎俄烏衝突加速全球地緣政治重組?
俄烏戰爭的衝擊才剛開始發酵,然而與普丁期望的相反,這場衝突喚醒了北約。芬蘭和瑞典加強邊境兵力,計畫申請加入北約。美國確認重返歐洲,主導制裁措施,同時向俄羅斯
的鄰國派兵,提供武器給烏克蘭,並將俄羅斯的銀行排除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之外。對美國而言,從長遠來看,支持烏克蘭至關重要,因為有助於展現力量對
比,以嚇阻覬覦台灣的中國。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就任)也完全沒有把經濟擴張的前途押在中國與俄羅斯的「永恆聯盟」上。短短幾星期內,歐洲的和平就變成了刀光劍影,也讓各國認清最新的優先事項—加強能源主權及擘畫歐洲防務。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德國的抉擇(投入1,000億歐元強化軍隊、分散天然氣供給)、各國軍援烏克蘭並與90%為婦女及兒童的526萬烏克蘭難民(聯合國2022年4月25日的數據)站在一起,凡此種種皆證實歐洲將防範俄羅斯的威脅納入近程展望中。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問題已搬上檯面,雖然莫斯科當局大概會將此舉視作戰爭的藉口,而且通過的機會也不大,但烏克蘭仍於2022年2月28日正式提交申請,成為歐盟候選國。歐洲的重心正逐漸改變,區域強權國家將愈來愈舉足輕重,其中波蘭在地理上鄰近俄羅斯和烏克蘭,在歷史上與兩國也曾為對手,勢必會在此次歐洲重組中扮演要角。
【Ch 19 東南亞 :在中國陰影下捍衛自身利益】
▌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中,東南亞向來占有關鍵地位。近年來,由於中美貿易及外交關係緊張,東南亞在戰略和經濟上的重要性更有增無減,而幾乎所有東南亞國家最重要的合作夥伴都是中國。然而Covid-19危機爆發以後,就算東南亞國家未能因此反思對中關係,這場危機也已體現出持續對中國加深依賴將帶來何等挑戰。
東南亞是全球化的十字路口,接納中國僑民(全球共約3,500萬人)的歷史最為悠久,規模也最大。東南亞包含11個獨立國家──緬甸、泰國、越南、寮國、柬埔寨、印尼、東帝汶、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汶萊,這些國家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位居戰略要津,在中國政治領域裡也同樣地位特殊。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北京政府曾多次涉入東南亞事務。1997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宣示「睦鄰友好」原則;2012年起領導中國共產黨的習近平在2013年升任國家主席,上台以來重申中國對東南亞的興趣,試圖將東南亞納入被中國形容為「命運共同體」的天朝秩序之下。
中國企圖打造一套囊括一切的政治修辭,該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卻因地理、文化、歷史和經濟現實而各有不同。中國在緬甸和寮國北部的存在感相當強烈,當地以中國遊客和移民為中心,形成了如假包換的飛地。中國在泰國經濟中的身影同樣難以忽視。相反地,越南與北京當局的關係則搖擺不定,經濟上合作、地緣政治上對抗,在南海問題上尤其針鋒相對。
◎東協能否成為抗衡中國的利器?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自1967年創立以來即對東南亞國家發展發揮關鍵作用,並成為各會員國表達關切的外交工具,特別是針對中國,因為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地緣戰略局勢。此外,東協並非軍事組織,成員國卻與美國、澳洲和日本保持緊密聯繫,甚至組成戰略聯盟,這有助於避免東協國家受到孤立。1996年以來,在越南和菲律賓當局的推動下,東協開始與中國談判「南海行為準則」,正說明了這種夥伴關係能夠在戰略架構下發揮助益。
中國已經看到了與東協合作的價值,特別是在經濟方面。東協與中國的貿易額從1991年的83億美元成長到2020年的6,866億美元,這使得中國成為東南亞最大的貿易夥伴,超越歐盟(6,514億美元)和美國(5,870億美元)。中國也是東南亞國家的一大投資者,件數最多的是透過基礎建設契約進行的投資。儘管美國仍然是東協的最大投資者(2020年為347億美元),但來自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了65%,從2011 ∼2015年的年均69億美元增加到2016 ∼ 2020年的年均115億美元。中國的主要投資目的地是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但
對某些國家(尤其是柬埔寨和寮國)而言,中國已是最主要的投資來源。大多數中國投資契約涉及運輸、電力和電信領域,許多契約被認為與一帶一路計畫有關。
◎面對中國覬覦,捍衛南海利益將成挑戰
上述國際關係的核心皆在於能源問題。國際能源總署(IEA)研究顯示,2017 ∼ 2040年間,東南亞的能源需求預計將增加65%,這樣的趨勢源於經濟和人口成長。缺電對部分東協國家而言仍是持續存在、媒體不斷報導的挑──2016年,東南亞無電可用的總人數為4,700萬人,主要分布在緬甸(2,200萬人)、菲律賓(900萬人)、柬埔寨(800萬人)和印尼(600萬人)。湄公河流域同樣多處情勢緊繃,北京政府出資建設的水壩讓中國得利,流域內其他國家的水資源則遭到剝奪。
中國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背後隱含著龐大的地緣政治企圖,目的是為了滿足北京當局的野心。經濟聯盟與投資計畫旨在確保中國在東南亞的利益,然而這一戰略也引起東協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對於東協來說,在中美競爭中捍衛自身利益已成為重大挑戰。
眼見美國的影響力遍及東南亞各處,中國渴望將第一道海上防線擴展到日本和菲律賓以外。台灣便是達成這份野心的關鍵,南海也是如此。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緊繃情勢的中心,中國宣稱擁有這兩個群島的主權,企圖控制其鄰國的經濟海域及財富(參見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