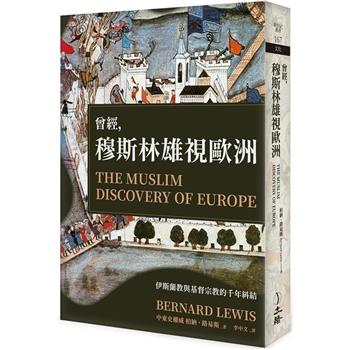1接觸與衝擊
Contact and Impact
回教史家看歷史性戰役
西元七世紀前半葉,先知穆罕默德於阿拉伯開始宣教時,整個地中海區都還是基督教的領域。就連歐洲、非洲乃至亞洲沿岸,居民幾乎都分屬基督教的各宗派。在希臘羅馬世界的其他宗教中,只有兩種宗教還延續著,即猶太教和摩尼教,它們被這塊土地上的少數人信奉著。位於地中海東部的東羅馬帝國,即所謂拜占庭帝國,仍極強盛,以君士坦丁堡為國都,統治著敘利亞、巴勒斯坦,和部分北非、小亞細亞和東南歐。地中海西部的羅馬政權已衰落,各蠻族及其王國從羅馬的廢墟崛起,皈依了基督教,並以若干成果,維持羅馬國家和基督教會的門面。但基督教版圖並不僅限於地中海地區,在拜占庭帝國東境的美索不達米亞,包含波斯帝國的大城及西部主要省份,在七世紀初葉仍奉基督教,這是羅馬世界以外的基督教領域。除羅馬和波斯邊境外,就連阿拉伯信奉不同教的居民中,也有少數基督徒和猶太人(譯註:一般而言,猶太人就等同於猶太教徒)。
穆罕默德歸真(意即過世,六三二年)後,短短幾十年間,繼位者就跨出阿拉伯半島,侵入拜占庭和波斯,使這兩大帝國讓出之間的中東地帶,奪得廣大的疆土。波斯帝國受到全面的征伐與滲透。這些阿拉伯人從羅馬世界拿下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部分北非,從而成為進佔西班牙和地中海島嶼(尤其是西西里)的跳板。只要再打敗拜占庭及蠻族部隊,即可將各國合併成伊斯蘭帝國,使基督教國家腹背受敵。就東疆而言,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阿拉伯軍進逼安那托利亞,接著到了希臘、基督教國家(Christendom,一譯基督宗教國,或基督王國)和拜占庭帝國心臟地帶,而西疆的阿拉伯軍和(北非)柏柏爾(Berber)軍,則從已佔領的西班牙越過庇里牛斯山脈,覬覦西歐。沒多久,穆斯林軍就佔領西西里島和義大利南部,而對著整個羅馬帝國虎視眈眈。
就西方傳統的史觀來看,遏阻回教徒的進逼並保全西歐基督教的關鍵戰役,是圖爾戰役與普瓦捷戰役(Battle of Tours and Poitiers)。七三二年,鐵鎚查理(Charles Martel)所率領的法蘭克軍重挫了伊斯蘭軍,這可說是歐洲史上救亡圖存的第一個轉捩點。(英國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有段膾炙人口的話,顯示西洋人對該戰役的觀感,及其扭轉命運的意義:
「常勝軍的路線由直布羅陀海峽到(法國中部)羅亞爾河,綿延一千英里(一千六百公里);阿拉伯人擴張到波蘭和蘇格蘭高地;萊因河和尼羅河或幼發拉底河同樣遭受到威脅,阿拉伯艦隊或許不需要經過戰鬥,就可長驅直入泰晤士河。如今牛津的小學可能要教起《古蘭經》,佈道壇則用於對行過割禮的人(譯註:即改宗的信眾或回教徒)宣講穆罕默德受真主降示的神蹟與真理。」
吉朋接著表示:「幸虧此人(譯註:即鐵鎚查理)的才能和運勢,基督教才得以脫離此般不幸。」
對於鐵鎚查理的成就,和圖爾及普瓦捷兩戰役的結果,回教傳統則反映不同的觀點。阿拉伯人擁有豐富的歷史文獻,對吉哈德(jihād,即為了信仰對不同教者展開的聖戰)若干成果大書特書,並忠實記載對手的挫敗(甚或勝利)。
不消說,阿拉伯人也很清楚,他們的西向擴張到了法國就遭遇瓶頸,一些作者提到了納博那(Narbonne),即阿拉伯人堅守到西元七五九年的城池,「回教徒攻克法蘭克版圖的最後據點」(譯註:當時穆斯林通稱西歐人、甚至稱歐洲人為法蘭克人)。日後某作者以慨嘆的口吻,引述納博那紀念碑上的碑文:「掉過頭去吧,易司瑪儀(Ishmael,譯註:即以實馬利,回教天房的建造者)之子孫,這是你的極限。若你們質疑,我將答覆,但倘若你們不肯回頭,就將會相互廝殺,直到末日審判。」但中世紀阿拉伯史家不曾提及圖爾或普瓦捷二詞,對鐵鎚查理也一無所知。戰役叫做Balāţal-Shuhadā,即取名為殉道者的光輝大道,記載成小規模的遭遇戰。該詞彙無人加以求證,直至十七世紀,才出現在西班牙阿拉伯史家的著作。在阿拉伯人的東方史學中,對此事件頂多是一筆帶過。撰著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和西班牙史事的權威史家伊本.阿布達.哈坎(Ibn `Abd al-Hakam,八○三至八七一年),只有以下寥寥幾句:
「烏貝達(`Ubayda,北非統治者)將西班牙統治權交給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l-Rahmān ibn `Abdallah al-`Akkī)。此人因出征法蘭克人而名重一時,他們是離西班牙最遠的敵手。他打敗法蘭克人,擄獲許多戰利品……隨後,他繼續遠征,並和所有戰友為伊斯蘭而慷慨犧牲。他……歸真於回曆一一五年(西元七三三到七三四年)。」
其他史家的態度也相仿。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東方阿拉伯史家塔百里(Tabarī,九二三年歿),及回教西班牙史最傑出的史家伊本.奎提亞(Ibn al-Qūţiyya,九七七年歿),對這兩場戰役均隻字未提。
相對於穆斯林史學傳統的略之不論或不予重視,其對於當時阿拉伯人一心想攻佔君士坦丁堡,倒是大書特書。這些未有斬獲的包圍和攻擊,在正史和野史中受到肯定,其中有些事件的細節還透露末世論的氛圍,預言救世主時代的來臨。
然而,就這種厚此薄彼的歷史評價而言,若說穆斯林史家的觀點比後世西方史家翔實,其實並不必太懷疑。法蘭克人在普瓦捷戰役中所遭遇到的,是離家鄉數千里來遠征的掠奪者。他們所擊倒的,乃是瀕臨瓶頸、精疲力竭的部隊。相反地,君士坦丁堡希臘的守城將士,所面臨的是哈里發(caliph,譯註:為伊斯蘭王朝統治者的稱呼)部隊的精銳,是直接由本國基地出發、對敵國首都發動的主要攻勢。換言之,希臘人在此抗擊的伊斯蘭軍,是未經損耗且強而有力的。就如吉朋所說,其路線從直布羅陀海峽到羅亞爾河河岸,長達一千英里;而直布羅陀海峽離阿拉伯有數千英里之遙。阿拉伯人認為,經中歐到萊因河的路線較短──比取道烏滸水(Oxus,譯註:現今的阿姆河,流經北阿富汗匯入鹹海)和中國邊境省力許多。因此,使東、西方基督教得以延續的,是阿拉伯軍攻佔君士坦丁堡的挫敗,而不是他們在圖爾和普瓦捷戰役中攻略作業的失利。
回教政權重心的轉移與分散
阿拉伯人十分清楚東、西方基督徒的差別。他們通常用Rūm(魯姆)這個阿拉伯語詞稱呼拜占庭人,之後,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也沿用這個語詞來代表羅馬。拜占庭人稱羅馬帝國,自稱為羅馬人。當時的伊斯蘭語,以Rūm來涵蓋希臘人,而拜占庭帝國之前的疆域,則以Rūm國而為人所知,希臘語則稱之為Rūmī。事有湊巧,連希臘人自己也常以Romaike(本指基督教)一詞指稱拜占庭的事物。對於在義大利也有個叫羅馬的城市這件事,阿拉伯地理學者也略有所聞。不過,相較於博斯普魯斯海峽附近的羅馬城,義大利的羅馬城似乎就較不重要而少有人知了。
儘管穆斯林軍在君士坦丁堡遭挫,卻仍繼續從東、西邊境包夾該帝國,但此時的擴張行動已是後勁不足。在西疆方面,征服西西里島是唯一的輝煌戰果(八二七至九○二年)。在東疆,回教徒於印度和中國邊境陷入膠著。在正中央,拜占庭邊疆相安無事,攻克君士坦丁堡的計畫就此順延下去。
回教徒這第一階段的聖戰,已確實告一段落。早期的征伐狂熱已大受損耗,其飢渴(不管對戰利品或對殉教)已得到滿足。新的哈里發時代──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s),在八世紀中期接替伍麥葉王朝(the Umayyads),首都由敘利亞東遷至伊拉克。如此一來,這片廣大領土就轉型為重亞洲、輕地中海的帝國。此時對於聖戰的興致就變得可有可無,對西部邊疆的關切也降至最低。
以地中海各國為主的新回教國家,曾與歐洲基督徒進行過長時期的鬥爭。但不久後,對於反異教徒(譯註:異教徒在此指不同宗教的信徒,即基督徒,不是指沒有宗教的異議份子,下同;另外,《古蘭經》中稱不同宗教的信徒為「不信道的人」,或「以物配主者」,即指偶像崇拜者)聖戰的熱衷,就轉移到處理內部問題上。在伊斯蘭世界中,很早就出現教義分歧,遜尼派奉巴格達的阿拔斯哈里發為正統,後來成為主流,其他不同教派大都鬆散地統轄在什葉派名下,挑戰遜尼派的見解及其哈里發的正統。十世紀時,一不同教派的哈里發(法蒂瑪地方王朝,the Fatimids)先是在突尼西亞(Tunisia),後來在埃及崛起,向阿拔斯王朝爭奪全回教世界的領導權。在法蒂瑪王朝之前,回教各國中也出現過其他自主、獨立的統治者,不過,他們大都樂於在口頭上承認遜尼派的阿拔斯哈里發的宗主權。法蒂瑪王朝則加以否認,主張本身就是伊斯蘭唯一正統的哈里發,有權罷黜阿拔斯的僭位。於是乎,回教世界的哈里發由一位變成兩位,之後又成了三位,因為西班牙科爾多瓦(Cordova)的伍麥葉王公,感到法蒂瑪擴張與顛覆的威脅,就在領土上自封哈里發。所以,宗派分歧與政權傾軋,就成為回教世界的主要關切,原先的邊境衝突就被拋諸腦後。遜尼派與什葉派和衷共濟的大時代已然過去,伊斯蘭和基督教的分立彷彿就此底定,而伊斯蘭一些相互承認的形式,以及與非回教國家間的關係,也就應運而生。
若說回教聖戰已暫告一段落,那麼基督徒的聖戰才正要開始。基督徒始終記得,回教帝國中的大部分國家,曾是皈依基督教的,其中還包括基督教起源的聖地本身。基督徒反攻伊斯蘭,是受到回教世界中明顯的積弱與內訌的刺激。不消說,有人趁動亂從中漁利。但發動攻擊、進犯回教版圖的人,既不是基督徒,也非回教徒,而是外教者──東方的土耳其人及西方的維京人,只不過這些活動為期甚短。其中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權力的恢復和收服基督教失土的決心。
回教徒看基督教反攻
基督徒的收復失土運動肇始於西、東邊陲。西班牙的各小公國原本就想將版圖推進到伊比利半島以北,當時便開始集中力量,從事擴張,期間得到法蘭克人的支援,後來諾曼人襲擊回教國家,也成為一股助力。在東疆,來自高加索的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基督教部族,也開始反叛其穆斯林君主。到了十世紀後半,拜占庭人也開始對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希臘諸島等的回教徒發動反攻,收復許多失土。
十一世紀期間,基督教部隊常打敗伊斯蘭軍。在東方,基督教的喬治亞王國,成功抗阻回教徒的入侵,並開始對外擴張,掌控黑海與裡海之間的高加索隘路。在地中海方面,基督教部隊收復薩丁尼亞和西西里,使其脫離回教統治者的掌控。在伊比利半島方面,捲土重來的部隊持續南進,將(西班牙)托萊多(Toledo)和(葡萄牙)孔布拉(Coimbra)收回基督教的版圖。
其後,來自西歐的基督教部隊於一○九八年發兵,在一連串征討下,很快攻克了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海岸平原,此即所謂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
這場東征對回教徒而言,並非那麼家喻戶曉。在當時穆斯林的著作中,「十字軍」和「十字軍東征」二詞甚為罕見,該語詞相當晚近才收入阿拉伯人有關基督教的著作中,之前在阿拉伯文或其他伊斯蘭的語文中,其實是找不到對應詞的。就當時的穆斯林觀察家而言,這批十字軍不過是法蘭克人或烏合之眾──即擅自入侵伊斯蘭世界的眾多異教徒和蠻族之一,其特徵就在驍勇善戰,才僥倖成功的。就這點而言,歐洲基督徒和回教徒差別不大,他們也是許久都不願承認伊斯蘭是足以平起平坐的宗教,視回教徒為異教徒、不信教者,或最多是以阿拉伯人或摩爾人、土耳其人或韃靼人的種族名來稱呼。
十字軍的成就,大半要歸諸於回教徒的積弱。早在十一世紀中期,伊斯蘭文明就顯露某些病徵。在內政問題和政權分立下,各部領土主要是巧取豪奪的結果,這種裡裡外外(在回教徒眼中)都是蠻族的情況,持續將近三個世紀。在非洲方面,新的宗教運動使摩洛哥南部和塞內加爾│尼日(Senegal-Niger)等地的各柏柏爾部族團結起來。該運動持續擴大,形成包括西北非大部及穆斯林西班牙的新柏柏爾王朝。東方的伊斯蘭國,遭到中亞及以東的草原部族(先是突厥人,後是蒙古人)的侵略,他們的遷徙和征服,改變了整個中東社會的種族、社會和文化型態。甚至帝國內部行政組織的腐敗,也利於貝都因人(the Bedouin)和其他游牧族,出沒於曾受到灌溉栽培的土地上。
不過,當中卻沒有任何一股勢力,能給回教世界造成巨大、難以彌補的損害。因為柏柏爾人和貝都因人畢竟都是回教徒,而突厥人則很快就成為伊斯蘭有史以來最強壯的戰士。第一個對伊斯蘭形成致命威脅的,是來自於北方(即歐洲)的蠻族。
當時大馬士革的官方史家伊本.開拉尼希(Ibn al-Qalānisī),記錄了回曆(譯註:即以穆罕默德遷徙之年為回曆元年)四九○年時(西元一○九六到九七年間)十字軍的到來如下:
「今年,彙報不斷傳來,在君士坦丁堡方位出現了法蘭克部隊,兵員多到不計其數。消息接連不斷,在四處傳播後,民心開始不安 ……」
在百餘年後,遙遠的(伊拉克)摩蘇爾(Mosul)大史家伊本.阿西爾(Ibn al-Athīr),以更開闊的眼光看待這事件:
「法蘭克人的帝國之首度出現,其權力的擴大,侵犯伊斯蘭版圖和佔領若干領土,是發生在(回曆)四七八年(西元一○八五到八六年間),他們拿下托萊多及安達魯西亞的一些城池,這是之前就開始的。之後在四八四年(一○九一到九二年間),他們襲擊並佔領西西里島,這也是筆者之前提過的。後來他們甚至登上非洲海岸,奪取若干領土,但也可說是收復。再來他們就征服了其他現今眾所周知的地方。到了四九○年(一○九六到九七年間),他們進攻敘利亞……」
十字軍以無堅不摧的凌厲攻勢,將敘利亞到巴勒斯坦海岸、托羅斯山脈(Taurus)丘陵地帶往西奈(Sinai)山隘路等等的法蘭克人、基督徒、封建諸侯連成一氣。回教版圖上的這些基督教城市遺址,還要兩個多世紀才被回教聖戰所清除。
起初,伊斯蘭王朝態度冷淡地接見這些遠道而來的洋人,而前不久,拉丁民族(譯按:似指十字軍)才在敘利亞│巴勒斯坦詭譎多變的政局中贏得地位。原先的吉哈德早已落幕,聖戰精神似乎也早已被忘卻。當時正值暴力與動亂的時期,伊斯蘭國遭受各方的夾擊,亦即中亞、柏柏爾人的非洲和基督教國的夾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陷落,一開始即使在大馬士革、開羅和(敘利亞)阿勒坡(Aleppo)也只稍稍引人注意罷了,在其他地方簡直可說是不為人知。十三世紀初,伊本.阿西爾記錄了十字軍佔領期間,第一批巴勒斯坦難民逃到巴格達的經過,談到他們流離失所並請求支援,卻不見任何後續措施。這樣的消息可見諸於當時的伊拉克詩人,他哀悼耶路撒冷陷落與回教徒失敗,並諷喻其防禦措施,其中還提到Rūm,即拜占庭征服者。不管是東方或西方的回教統治者,都樂於和新友邦往來,甚至在必要時和他們聯盟起來鬥爭穆斯林同胞。在兩百多年間,處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回教徒與法蘭克人你來我往,有時交戰,有時也進行通商、外交,甚而結盟。十字軍東征結束後,西洋的貿易商和朝聖者,在埃及和黎凡特(the Levant,譯註:地中海東部諸國及島嶼,含敘利亞、黎巴嫩在內的、自希臘至埃及的地區)暢行無阻,回教統治者也接連與往來的西方各國簽署貿易合約。
在遠東方面,基督教收復失土運動最後獲得了全盤勝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穆斯林君主甚至人民遭到驅逐,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更乘勝追擊.進入非洲追逐他們先前的統治者。在東疆方面,由於不斷有歐洲調兵增援,十字軍一時得以立於不敗之地,不過在回教徒連續反攻下,逐漸耗弱,後來到一二九一年,拉丁勢力的最後堡壘──巴勒斯坦的阿卡(Acre)港,最終落入馬木路克(the Mamluk)蘇丹(sultan,一譯素檀)之手。
(全文未完)
Contact and Impact
回教史家看歷史性戰役
西元七世紀前半葉,先知穆罕默德於阿拉伯開始宣教時,整個地中海區都還是基督教的領域。就連歐洲、非洲乃至亞洲沿岸,居民幾乎都分屬基督教的各宗派。在希臘羅馬世界的其他宗教中,只有兩種宗教還延續著,即猶太教和摩尼教,它們被這塊土地上的少數人信奉著。位於地中海東部的東羅馬帝國,即所謂拜占庭帝國,仍極強盛,以君士坦丁堡為國都,統治著敘利亞、巴勒斯坦,和部分北非、小亞細亞和東南歐。地中海西部的羅馬政權已衰落,各蠻族及其王國從羅馬的廢墟崛起,皈依了基督教,並以若干成果,維持羅馬國家和基督教會的門面。但基督教版圖並不僅限於地中海地區,在拜占庭帝國東境的美索不達米亞,包含波斯帝國的大城及西部主要省份,在七世紀初葉仍奉基督教,這是羅馬世界以外的基督教領域。除羅馬和波斯邊境外,就連阿拉伯信奉不同教的居民中,也有少數基督徒和猶太人(譯註:一般而言,猶太人就等同於猶太教徒)。
穆罕默德歸真(意即過世,六三二年)後,短短幾十年間,繼位者就跨出阿拉伯半島,侵入拜占庭和波斯,使這兩大帝國讓出之間的中東地帶,奪得廣大的疆土。波斯帝國受到全面的征伐與滲透。這些阿拉伯人從羅馬世界拿下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部分北非,從而成為進佔西班牙和地中海島嶼(尤其是西西里)的跳板。只要再打敗拜占庭及蠻族部隊,即可將各國合併成伊斯蘭帝國,使基督教國家腹背受敵。就東疆而言,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阿拉伯軍進逼安那托利亞,接著到了希臘、基督教國家(Christendom,一譯基督宗教國,或基督王國)和拜占庭帝國心臟地帶,而西疆的阿拉伯軍和(北非)柏柏爾(Berber)軍,則從已佔領的西班牙越過庇里牛斯山脈,覬覦西歐。沒多久,穆斯林軍就佔領西西里島和義大利南部,而對著整個羅馬帝國虎視眈眈。
就西方傳統的史觀來看,遏阻回教徒的進逼並保全西歐基督教的關鍵戰役,是圖爾戰役與普瓦捷戰役(Battle of Tours and Poitiers)。七三二年,鐵鎚查理(Charles Martel)所率領的法蘭克軍重挫了伊斯蘭軍,這可說是歐洲史上救亡圖存的第一個轉捩點。(英國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有段膾炙人口的話,顯示西洋人對該戰役的觀感,及其扭轉命運的意義:
「常勝軍的路線由直布羅陀海峽到(法國中部)羅亞爾河,綿延一千英里(一千六百公里);阿拉伯人擴張到波蘭和蘇格蘭高地;萊因河和尼羅河或幼發拉底河同樣遭受到威脅,阿拉伯艦隊或許不需要經過戰鬥,就可長驅直入泰晤士河。如今牛津的小學可能要教起《古蘭經》,佈道壇則用於對行過割禮的人(譯註:即改宗的信眾或回教徒)宣講穆罕默德受真主降示的神蹟與真理。」
吉朋接著表示:「幸虧此人(譯註:即鐵鎚查理)的才能和運勢,基督教才得以脫離此般不幸。」
對於鐵鎚查理的成就,和圖爾及普瓦捷兩戰役的結果,回教傳統則反映不同的觀點。阿拉伯人擁有豐富的歷史文獻,對吉哈德(jihād,即為了信仰對不同教者展開的聖戰)若干成果大書特書,並忠實記載對手的挫敗(甚或勝利)。
不消說,阿拉伯人也很清楚,他們的西向擴張到了法國就遭遇瓶頸,一些作者提到了納博那(Narbonne),即阿拉伯人堅守到西元七五九年的城池,「回教徒攻克法蘭克版圖的最後據點」(譯註:當時穆斯林通稱西歐人、甚至稱歐洲人為法蘭克人)。日後某作者以慨嘆的口吻,引述納博那紀念碑上的碑文:「掉過頭去吧,易司瑪儀(Ishmael,譯註:即以實馬利,回教天房的建造者)之子孫,這是你的極限。若你們質疑,我將答覆,但倘若你們不肯回頭,就將會相互廝殺,直到末日審判。」但中世紀阿拉伯史家不曾提及圖爾或普瓦捷二詞,對鐵鎚查理也一無所知。戰役叫做Balāţal-Shuhadā,即取名為殉道者的光輝大道,記載成小規模的遭遇戰。該詞彙無人加以求證,直至十七世紀,才出現在西班牙阿拉伯史家的著作。在阿拉伯人的東方史學中,對此事件頂多是一筆帶過。撰著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和西班牙史事的權威史家伊本.阿布達.哈坎(Ibn `Abd al-Hakam,八○三至八七一年),只有以下寥寥幾句:
「烏貝達(`Ubayda,北非統治者)將西班牙統治權交給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l-Rahmān ibn `Abdallah al-`Akkī)。此人因出征法蘭克人而名重一時,他們是離西班牙最遠的敵手。他打敗法蘭克人,擄獲許多戰利品……隨後,他繼續遠征,並和所有戰友為伊斯蘭而慷慨犧牲。他……歸真於回曆一一五年(西元七三三到七三四年)。」
其他史家的態度也相仿。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東方阿拉伯史家塔百里(Tabarī,九二三年歿),及回教西班牙史最傑出的史家伊本.奎提亞(Ibn al-Qūţiyya,九七七年歿),對這兩場戰役均隻字未提。
相對於穆斯林史學傳統的略之不論或不予重視,其對於當時阿拉伯人一心想攻佔君士坦丁堡,倒是大書特書。這些未有斬獲的包圍和攻擊,在正史和野史中受到肯定,其中有些事件的細節還透露末世論的氛圍,預言救世主時代的來臨。
然而,就這種厚此薄彼的歷史評價而言,若說穆斯林史家的觀點比後世西方史家翔實,其實並不必太懷疑。法蘭克人在普瓦捷戰役中所遭遇到的,是離家鄉數千里來遠征的掠奪者。他們所擊倒的,乃是瀕臨瓶頸、精疲力竭的部隊。相反地,君士坦丁堡希臘的守城將士,所面臨的是哈里發(caliph,譯註:為伊斯蘭王朝統治者的稱呼)部隊的精銳,是直接由本國基地出發、對敵國首都發動的主要攻勢。換言之,希臘人在此抗擊的伊斯蘭軍,是未經損耗且強而有力的。就如吉朋所說,其路線從直布羅陀海峽到羅亞爾河河岸,長達一千英里;而直布羅陀海峽離阿拉伯有數千英里之遙。阿拉伯人認為,經中歐到萊因河的路線較短──比取道烏滸水(Oxus,譯註:現今的阿姆河,流經北阿富汗匯入鹹海)和中國邊境省力許多。因此,使東、西方基督教得以延續的,是阿拉伯軍攻佔君士坦丁堡的挫敗,而不是他們在圖爾和普瓦捷戰役中攻略作業的失利。
回教政權重心的轉移與分散
阿拉伯人十分清楚東、西方基督徒的差別。他們通常用Rūm(魯姆)這個阿拉伯語詞稱呼拜占庭人,之後,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也沿用這個語詞來代表羅馬。拜占庭人稱羅馬帝國,自稱為羅馬人。當時的伊斯蘭語,以Rūm來涵蓋希臘人,而拜占庭帝國之前的疆域,則以Rūm國而為人所知,希臘語則稱之為Rūmī。事有湊巧,連希臘人自己也常以Romaike(本指基督教)一詞指稱拜占庭的事物。對於在義大利也有個叫羅馬的城市這件事,阿拉伯地理學者也略有所聞。不過,相較於博斯普魯斯海峽附近的羅馬城,義大利的羅馬城似乎就較不重要而少有人知了。
儘管穆斯林軍在君士坦丁堡遭挫,卻仍繼續從東、西邊境包夾該帝國,但此時的擴張行動已是後勁不足。在西疆方面,征服西西里島是唯一的輝煌戰果(八二七至九○二年)。在東疆,回教徒於印度和中國邊境陷入膠著。在正中央,拜占庭邊疆相安無事,攻克君士坦丁堡的計畫就此順延下去。
回教徒這第一階段的聖戰,已確實告一段落。早期的征伐狂熱已大受損耗,其飢渴(不管對戰利品或對殉教)已得到滿足。新的哈里發時代──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s),在八世紀中期接替伍麥葉王朝(the Umayyads),首都由敘利亞東遷至伊拉克。如此一來,這片廣大領土就轉型為重亞洲、輕地中海的帝國。此時對於聖戰的興致就變得可有可無,對西部邊疆的關切也降至最低。
以地中海各國為主的新回教國家,曾與歐洲基督徒進行過長時期的鬥爭。但不久後,對於反異教徒(譯註:異教徒在此指不同宗教的信徒,即基督徒,不是指沒有宗教的異議份子,下同;另外,《古蘭經》中稱不同宗教的信徒為「不信道的人」,或「以物配主者」,即指偶像崇拜者)聖戰的熱衷,就轉移到處理內部問題上。在伊斯蘭世界中,很早就出現教義分歧,遜尼派奉巴格達的阿拔斯哈里發為正統,後來成為主流,其他不同教派大都鬆散地統轄在什葉派名下,挑戰遜尼派的見解及其哈里發的正統。十世紀時,一不同教派的哈里發(法蒂瑪地方王朝,the Fatimids)先是在突尼西亞(Tunisia),後來在埃及崛起,向阿拔斯王朝爭奪全回教世界的領導權。在法蒂瑪王朝之前,回教各國中也出現過其他自主、獨立的統治者,不過,他們大都樂於在口頭上承認遜尼派的阿拔斯哈里發的宗主權。法蒂瑪王朝則加以否認,主張本身就是伊斯蘭唯一正統的哈里發,有權罷黜阿拔斯的僭位。於是乎,回教世界的哈里發由一位變成兩位,之後又成了三位,因為西班牙科爾多瓦(Cordova)的伍麥葉王公,感到法蒂瑪擴張與顛覆的威脅,就在領土上自封哈里發。所以,宗派分歧與政權傾軋,就成為回教世界的主要關切,原先的邊境衝突就被拋諸腦後。遜尼派與什葉派和衷共濟的大時代已然過去,伊斯蘭和基督教的分立彷彿就此底定,而伊斯蘭一些相互承認的形式,以及與非回教國家間的關係,也就應運而生。
若說回教聖戰已暫告一段落,那麼基督徒的聖戰才正要開始。基督徒始終記得,回教帝國中的大部分國家,曾是皈依基督教的,其中還包括基督教起源的聖地本身。基督徒反攻伊斯蘭,是受到回教世界中明顯的積弱與內訌的刺激。不消說,有人趁動亂從中漁利。但發動攻擊、進犯回教版圖的人,既不是基督徒,也非回教徒,而是外教者──東方的土耳其人及西方的維京人,只不過這些活動為期甚短。其中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權力的恢復和收服基督教失土的決心。
回教徒看基督教反攻
基督徒的收復失土運動肇始於西、東邊陲。西班牙的各小公國原本就想將版圖推進到伊比利半島以北,當時便開始集中力量,從事擴張,期間得到法蘭克人的支援,後來諾曼人襲擊回教國家,也成為一股助力。在東疆,來自高加索的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基督教部族,也開始反叛其穆斯林君主。到了十世紀後半,拜占庭人也開始對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希臘諸島等的回教徒發動反攻,收復許多失土。
十一世紀期間,基督教部隊常打敗伊斯蘭軍。在東方,基督教的喬治亞王國,成功抗阻回教徒的入侵,並開始對外擴張,掌控黑海與裡海之間的高加索隘路。在地中海方面,基督教部隊收復薩丁尼亞和西西里,使其脫離回教統治者的掌控。在伊比利半島方面,捲土重來的部隊持續南進,將(西班牙)托萊多(Toledo)和(葡萄牙)孔布拉(Coimbra)收回基督教的版圖。
其後,來自西歐的基督教部隊於一○九八年發兵,在一連串征討下,很快攻克了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海岸平原,此即所謂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
這場東征對回教徒而言,並非那麼家喻戶曉。在當時穆斯林的著作中,「十字軍」和「十字軍東征」二詞甚為罕見,該語詞相當晚近才收入阿拉伯人有關基督教的著作中,之前在阿拉伯文或其他伊斯蘭的語文中,其實是找不到對應詞的。就當時的穆斯林觀察家而言,這批十字軍不過是法蘭克人或烏合之眾──即擅自入侵伊斯蘭世界的眾多異教徒和蠻族之一,其特徵就在驍勇善戰,才僥倖成功的。就這點而言,歐洲基督徒和回教徒差別不大,他們也是許久都不願承認伊斯蘭是足以平起平坐的宗教,視回教徒為異教徒、不信教者,或最多是以阿拉伯人或摩爾人、土耳其人或韃靼人的種族名來稱呼。
十字軍的成就,大半要歸諸於回教徒的積弱。早在十一世紀中期,伊斯蘭文明就顯露某些病徵。在內政問題和政權分立下,各部領土主要是巧取豪奪的結果,這種裡裡外外(在回教徒眼中)都是蠻族的情況,持續將近三個世紀。在非洲方面,新的宗教運動使摩洛哥南部和塞內加爾│尼日(Senegal-Niger)等地的各柏柏爾部族團結起來。該運動持續擴大,形成包括西北非大部及穆斯林西班牙的新柏柏爾王朝。東方的伊斯蘭國,遭到中亞及以東的草原部族(先是突厥人,後是蒙古人)的侵略,他們的遷徙和征服,改變了整個中東社會的種族、社會和文化型態。甚至帝國內部行政組織的腐敗,也利於貝都因人(the Bedouin)和其他游牧族,出沒於曾受到灌溉栽培的土地上。
不過,當中卻沒有任何一股勢力,能給回教世界造成巨大、難以彌補的損害。因為柏柏爾人和貝都因人畢竟都是回教徒,而突厥人則很快就成為伊斯蘭有史以來最強壯的戰士。第一個對伊斯蘭形成致命威脅的,是來自於北方(即歐洲)的蠻族。
當時大馬士革的官方史家伊本.開拉尼希(Ibn al-Qalānisī),記錄了回曆(譯註:即以穆罕默德遷徙之年為回曆元年)四九○年時(西元一○九六到九七年間)十字軍的到來如下:
「今年,彙報不斷傳來,在君士坦丁堡方位出現了法蘭克部隊,兵員多到不計其數。消息接連不斷,在四處傳播後,民心開始不安 ……」
在百餘年後,遙遠的(伊拉克)摩蘇爾(Mosul)大史家伊本.阿西爾(Ibn al-Athīr),以更開闊的眼光看待這事件:
「法蘭克人的帝國之首度出現,其權力的擴大,侵犯伊斯蘭版圖和佔領若干領土,是發生在(回曆)四七八年(西元一○八五到八六年間),他們拿下托萊多及安達魯西亞的一些城池,這是之前就開始的。之後在四八四年(一○九一到九二年間),他們襲擊並佔領西西里島,這也是筆者之前提過的。後來他們甚至登上非洲海岸,奪取若干領土,但也可說是收復。再來他們就征服了其他現今眾所周知的地方。到了四九○年(一○九六到九七年間),他們進攻敘利亞……」
十字軍以無堅不摧的凌厲攻勢,將敘利亞到巴勒斯坦海岸、托羅斯山脈(Taurus)丘陵地帶往西奈(Sinai)山隘路等等的法蘭克人、基督徒、封建諸侯連成一氣。回教版圖上的這些基督教城市遺址,還要兩個多世紀才被回教聖戰所清除。
起初,伊斯蘭王朝態度冷淡地接見這些遠道而來的洋人,而前不久,拉丁民族(譯按:似指十字軍)才在敘利亞│巴勒斯坦詭譎多變的政局中贏得地位。原先的吉哈德早已落幕,聖戰精神似乎也早已被忘卻。當時正值暴力與動亂的時期,伊斯蘭國遭受各方的夾擊,亦即中亞、柏柏爾人的非洲和基督教國的夾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陷落,一開始即使在大馬士革、開羅和(敘利亞)阿勒坡(Aleppo)也只稍稍引人注意罷了,在其他地方簡直可說是不為人知。十三世紀初,伊本.阿西爾記錄了十字軍佔領期間,第一批巴勒斯坦難民逃到巴格達的經過,談到他們流離失所並請求支援,卻不見任何後續措施。這樣的消息可見諸於當時的伊拉克詩人,他哀悼耶路撒冷陷落與回教徒失敗,並諷喻其防禦措施,其中還提到Rūm,即拜占庭征服者。不管是東方或西方的回教統治者,都樂於和新友邦往來,甚至在必要時和他們聯盟起來鬥爭穆斯林同胞。在兩百多年間,處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回教徒與法蘭克人你來我往,有時交戰,有時也進行通商、外交,甚而結盟。十字軍東征結束後,西洋的貿易商和朝聖者,在埃及和黎凡特(the Levant,譯註:地中海東部諸國及島嶼,含敘利亞、黎巴嫩在內的、自希臘至埃及的地區)暢行無阻,回教統治者也接連與往來的西方各國簽署貿易合約。
在遠東方面,基督教收復失土運動最後獲得了全盤勝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穆斯林君主甚至人民遭到驅逐,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更乘勝追擊.進入非洲追逐他們先前的統治者。在東疆方面,由於不斷有歐洲調兵增援,十字軍一時得以立於不敗之地,不過在回教徒連續反攻下,逐漸耗弱,後來到一二九一年,拉丁勢力的最後堡壘──巴勒斯坦的阿卡(Acre)港,最終落入馬木路克(the Mamluk)蘇丹(sultan,一譯素檀)之手。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