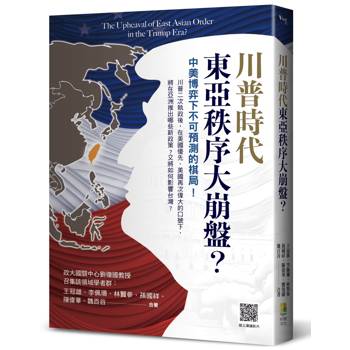第一章 川普如何面對臺灣海峽新現狀
陳偉華|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壹、川普回歸:全然改變的臺海現狀
「我得進行談判,所以永遠不會承諾會怎麼做。」
美國第47任總統川普就職前專訪 2024年12月7日
—《NBC News》Meet the Press
2025年2月10日,在美國海軍驅逐艦強森號護航下,美軍海洋測量船包迪奇號自北向南通過臺灣海峽,距離川普就職尚未滿月。美軍船艦於川普第二任期上任初始首度通過臺海,象徵意涵自然重大。如果說,川普第一任期與第二任期所要面對截然不同的「印度–太平洋地區」安全結構,當屬臺灣海峽的「現狀」已然改變。
當世人仍然以2022年俄烏戰爭的場景,想像臺灣海峽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型態時,實際上,中國已悄然地改變了過去75年來臺灣海峽的現狀。但是,這種現狀是什麼呢?如果我們認知到,臺灣海峽已進入一種「新現狀」或「新常態」,它又呈現怎樣的新面貌?川普2.0政府又如何回應此種臺灣海峽的安全現狀?
在國際體系層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正在迅速崩解。隨著川普2.0外交政策驟變,過往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架構為中心),轉向以「交易」為基礎的國家交往模式,大國之間訴求實力競爭。此一系列的轉變軌跡,體現在川普啟動俄烏戰爭和平談判,在聯合國大會對俄羅斯三週年譴責案中投反對票(中國棄權),以及施壓基輔簽署雙邊礦業協議等作為。美國主流媒體稱,川普政府意圖運用俄烏戰爭的調停角色,敦促烏克蘭簽訂停戰協議,拉攏俄羅斯與中國脫鉤,推動「反向尼克森」外交政策,採取「聯俄制中」強化對於中國的圍堵戰略,但此將以犧牲歐洲與烏克蘭安全為代價。
川普2.0政府亦展現出明確的「擴張主義」傾向,就職前川普已提出多項具有戰略意涵的政策主張,包括接管巴拿馬運河的管轄權、建議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更名墨西哥灣為「美國灣」、購買格陵蘭島、促成以色列與哈馬斯的停火與接管迦薩走廊等國際事務的安排,顯示出川普政府不僅試圖重新定義美國的全球地位,更可能藉由強勢外交手段,重新塑造國際地緣政治版圖。
在國際關係領域,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強權尋求結盟或增強自身實力,防止崛起大國主導國際體系,若一國軍事力量過強,周邊國家亦會形成反制聯盟。川普政府顯然正在操作一場「大棋局」,可能通過與俄羅斯合作,削弱中俄聯盟,進而影響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此舉將對臺灣海峽的安全產生哪些影響?臺灣仍然是美國亞洲戰略的核心嗎?
一直以來,對於「中國可能入侵臺灣」的命題,華盛頓政策圈對於防衛臺灣的承諾,究應採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立場,始終存在辯論。隨著解放軍加速改變臺海安全結構,再度引發「棄臺論」效應,如今,美國應避免直接軍事介入臺海衝突,已在華府逐漸形成戰略共識。在競選期間與白宮就職後,川普及其國安幕僚要求臺灣提升國防預算占GDP(2025年臺灣GDP預估值約26兆4493億元新臺幣)比例,方能有效嚇阻中國大陸入侵,避免戰爭。可以預期,川普將取消拜登時期明確防衛臺灣的政策宣示,通過軍售和軍事技術支持強化臺灣的不對稱防禦能力,也不會明確承諾出兵協防臺海,以降低美國捲入戰爭的風險。
儘管川普2.0戰略將再次轉向印太布局,此時此刻,華盛頓政策界仍為2027年「戴維森窗口」(The Davidson window)(美國印太司令部前司令菲利普·戴維森於2021年在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表示,中國可能在2027年至2035年間嘗試以武力奪取臺灣,這段期間被稱為「戴維森窗口」)是否存在進行辯論。美國內部似乎陷入與中國在臺灣海峽競爭的戰略分歧,看似兩黨「反中」立場趨向一致,然而,分歧仍展現在「短期應對 vs. 長期競爭」的步驟之爭。前者主張2027年是解放軍達成「現代化建軍」的指標年,美國應加大投入軍事資源,為臺海可能爆發的短期衝突做好準備。後者則強調美中長期競爭的必然,認為美國不應過度聚焦短期軍事威脅,而忽略在經貿與科技領域的持久性戰爭。顯然,如何平衡短期威懾與長期競爭的資源分配,將是川普第二任期的重要任務。可以確認的是,如果在2025年雙方走向更加對抗,川普國安隊伍將愈願意運用臺灣作為戰略槓桿,加劇臺灣海峽的軍備競賽,並視其為華府加大對北京挑釁行為的回應。
貳、上任之前:川普對臺灣安全的政策取向
根據美國總統權的研究,每一任美國總統在入主白宮之前,對於執政的政策目標和對幕僚人事的政治任命,已有初步的構想,這是上任之後執政團隊得以即刻啟動總統決策機制的基礎。因此,在分析川普第二任的「總統任期」似乎應可將時間範疇擴展至他勝選之後和就職前。進一步看,觀察美國總統上任前對外部威脅認知的形成,有助於避免我們混淆總統上任後面臨政治壓力下的決策行為。誠如季辛吉1979年所言,在總統執政期間,面對諸多危機決策時刻,領導人對於威脅來源的判斷可能受到多重的干擾因素和體制壓力,致使最終決策本身可能未能真正反映出總統的想法。
回顧川普第一任期,他對於中國對美國和臺灣威脅的認知,深受其政策顧問、地緣政治,以及其「美國優先」的政治信念影響。觀察川普第一任期的政務領導風格,他的認知根植於強烈的經濟競爭、軍事威脅以及價值觀對立的三重特性,這些特性形塑出所謂的「川普主義」。
首先,川普本人及執政團隊對中國的經濟威脅,來自共和黨民族保守主義陣營對於中美長期競爭結構的認知。川普勝選功臣和白宮首席策略長班農(Steve Bannon)與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力主「貿易戰與經濟脫鉤」,彼等深受經濟民族主義論者的推斷,認定中國「百年馬拉松」的最終目標是超越美國,篡奪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因此,川普推動全面的貿易戰,強調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如對電動車的高額補貼)、竊取智慧財產權,以及對美國製造業的掠奪。2018年起,川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川普本人則多次公開批評中國透過經濟手段削弱美國的地位。
在政策執行上,川普任命國務卿龐培歐、國家安全顧問波頓等鷹派現實主義者,致力於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擴張。2017年,川普政府公布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揭櫫「大國競爭」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挑戰,將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強調中國「經濟掠奪行為」為美國主要威脅。在2020年12月川普任內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升級為「主要挑戰者」,指出中國對美國經濟、技術、軍事與價值觀的全面威脅,北京不僅試圖改變國際秩序,更意圖取代美國和美元體系的霸權地位。
在軍事威脅上,川普對北京在臺海與南海爭議上的侵略意圖有清晰的認識,任內將臺海安全與南海動態連結,賦予兩者連動性的政策操作空間。在執政首年,川普擴增對臺軍售的範疇,在任內通過11次對臺軍售,總金額超過180億美元,項目涵蓋:加強空域優勢(F-16V、MQ-9B無人機系統)、海軍與防空能力(魚叉飛彈、標準防空飛彈、區域防空系統升級)、增強本島陸地防衛與不對稱作戰能力(M1A2戰車、HIMARS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同時,「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明確將臺灣視為該戰略的一部分,強調臺灣作為民主夥伴的重要性。美臺軍售範疇的擴大,顯示川普第一任期在戰略上積極協助臺灣提升整體軍事能力,並形成在臺灣海峽的嚇阻力量。
在價值觀競爭上,共和黨人視共產主義為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威脅。2019年,川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直接向中國表達對其壓制香港自治的反對,川普政府亦批評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並對相關官員實施制裁。2020年7月23日,國務卿龐培歐於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發表對中政策演說,呼籲世界各國與中國人民「改變中國共產黨的行為」,龐氏的發言等同宣示美國將致力顛覆共產政權,被外界視為開啟新一場冷戰的「新鐵幕演說」。
關於來自兩岸衝突的威脅,誠如前國安顧問波頓書中的爆料,他直言川普對臺灣並不友善,川普屢次用「桌上的筆尖」比喻臺灣,以「筆尖、桌面」比喻兩岸在川普心中的懸殊地位。對於習近平,川普更願意推崇習主席為中國歷史「最偉大的領袖」,有意拉近兩國元首情誼。如果波頓所言如實,臺灣在川普心中可謂微不足道,那麼臺灣是否還有被美國保護的價值?或只是川普牌局中的籌碼?在川普第二任期中,美國究竟是否延續民主盟友的承諾,或選擇透過對習近平的直接談判,以交易型外交來對應臺灣問題?或許檢視川普團隊對應臺灣海峽新現狀的政策立場,可以提供一個參照的指標。
特別是,過往川普國安團隊中的關鍵友臺官員已離開川普政府,他們並未受邀列入川普2.0政務任命的名單,這些跡象顯示,臺灣在川普第二任期下地位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
參、川普第二任期對臺海安全的意涵
1950年冷戰初期,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的演講中,闡明美國在東亞的防禦立場,意在穩定美國的盟友信心,重申美國的防禦承諾,並在此背景下,艾奇遜劃定了所謂的「艾奇遜防線」。這條防線涵蓋日本本土、沖繩和菲律賓,但未將韓國和臺灣納入防禦範圍,冷戰史學者認為,艾奇遜防線事實上鼓勵北韓檢驗美國的防衛決心,直接導致了韓戰的爆發,深刻地影響冷戰期間的東亞地緣政治。艾奇遜防線的歷史教訓,是否足以提醒川普政府,在定義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時,不應該排除臺灣,避免重蹈艾奇遜當年的覆轍?
一、對應臺灣海峽新現狀
首先,當世人還在以2022年俄烏戰爭的場景,想像臺灣海峽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型態時,實際上,中國已悄然地改變過去75年來臺灣海峽事實上的現狀。但是,這種現狀是什麼呢?如果我們認知到,臺灣海峽已進入一種「新現狀」或「新常態」,它又呈現怎樣的新面貌?
長期以來,儘管兩岸在法理上處於「主權競合」的狀態,兩岸政府之間仍維繫著1954年以來「臺灣海峽中線」(簡稱「臺海中線」)的某種默契,形成「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法理關係。彷如賽局理論中維持「納許平衡」(「納許平衡」是賽局理論核心概念之一,指在非合作賽局中,各參與方根據其他參與方的策略選擇最優策略,而當所有人皆選擇自身最優策略時,沒有任何一方能夠透過單方面改變策略來獲得更好的結果)的兩個政治實體,在不同階段,總會有一方強勢立場,而另一方必須選擇讓步。北京雖從未承認此種法律關係,惟在兩岸實務上已透過海峽雙邊協定與司法文書往返,接受此種「治權相互承認」的互動關係。
然而,自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民主黨籍加州)訪問臺灣,中國對臺海周邊發動大規模「圍臺軍演」,操演範圍幾乎涵蓋整個臺灣海峽,亦有意對臺灣形成「封鎖」之勢。演習期間,中國外交、國防與國臺辦發言系統稱「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此後,解放軍的軍機、艦等武裝勢力常態性的穿越海峽中線。
在2024年2月間「金門近海快艇翻覆事故」(本章簡稱「金門事件」)後,國臺辦發言系統稱,「海峽兩岸都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對臺灣海峽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中國國內法,臺灣海峽水域分別為中國內水、領海、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水域』」。顯然,中國此舉等同否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關係條例」)第29條授權國防部劃設限制或禁止水域。
為回應2024年賴清德總統在就職典禮和國慶演說重申兩岸「互不隸屬」,解放軍東部戰區先後展開代號「聯合利劍—2024A」和「聯合利劍—2024B」的系列演習,軍演範圍涵蓋臺灣周邊海域與空域,延伸至東海與南海部分地區,展示對第一島鏈的控制力與投射能力。2024年12月初,解放軍舉行近3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集結各類艦艇約90艘,活動範圍從日本南部延伸至南海,涵蓋東海與南海部分區域。至此,中國此舉等同將全世界宣告,臺灣海峽已在中國管轄權控制之下。
顯然,由中國以單邊行動推動臺灣海峽的「新現狀」的意圖已是昭然若揭。此前,中國在法律定性上徹底否認「海峽中線」、「禁、限制水域」的地位,北京主張臺灣不具備管轄權的實體身分。在此法律戰論述下,解放軍海、空軍、海警船、民用商船可常態性的進入海峽中線以東、外離島「禁、限制水域」內,行使海域執法權。進一步地,中國海上艦船或由軍方調度的海上民兵,得以常態性部署在臺灣本島鄰接區外界線(離領海基線約24浬),確保其得以實施有限或全面的封控措施,或運用海上執法部門在海峽攔截船隻的實力。
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所屬「中國實力計畫」,在2022年8月與2023年11月期間,針對美臺雙方官員與專家學者進行訪談(包括52位美國專家和35位臺灣專家,涵蓋學術界、智庫和政府部門專業人士),調查結果顯示超過90%的美國專家和約六成的臺灣專家贊同,中國在臺灣海峽具備執行「主導隔離」的能力。關於解放軍的封鎖方式,超過八成的美臺專家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高度動態的聯合封鎖「非常可能」或「可能」。
此前,美國「蘭德公司」於2022年5月公布《中國對臺灣施行強制隔離的影響意涵》,該報告從「封鎖」與「隔離」的指涉內涵出發,探究中國對臺灣採取強制隔離的政經效應,提醒世人臺灣供應鏈的脆弱性。蘭德研究團隊判斷,中國基於否認臺灣的主權地位,因此亦不認為兩岸之間存在戰爭狀態,故將不會使用「封鎖」一詞,而傾向採取「隔離」措施。相對於「封鎖」易被解讀為走向戰爭,「隔離」被視為一種非戰爭行為,並非要完全切斷臺灣的糧食和物資供應,而是意圖通過管控臺灣周邊的空域和水域來展現中國的「實際主權」,試圖在不直接爆發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達成對臺施壓的目標。
從國際法視角,「封鎖」被視為一種敵對行為,通常會被認定為戰爭行為,受《海牙公約》及《聯合國憲章》第51條的自衛條款規範,而封鎖行動須滿足公開宣布、實施有效且不能有選擇性等條件,以防止違反中立國的權利。相較而言,「隔離」迄今仍然缺乏明確的國際法條文規範,其法律性質仍屬爭議。對此,蘭德公司援引「1962年古巴危機」(1962年10月22日至11月20日),將臺海與美國當年對古巴實施隔離措施的情境相比,「隔離」比「封鎖」具有較低的戰爭風險,當時提供美方與蘇聯一個避免戰爭的選項,此模式或將是中國對臺灣施行隔離的參考。
如果「隔離臺灣」的想像落實,臺灣對進口資源(如能源、食品)的依賴性及其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角色,將使臺灣在面臨中國的經濟施壓時處於更為脆弱的位置。一旦中國實施隔離措施,臺灣的能源和食品等必需品可能會供應短缺,或價格大幅上漲,從而嚴重影響臺灣的經濟活動
然而,中國採取隔離措施,尚須考慮所需承擔的風險,由於臺灣的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一旦實施隔離措施,臺灣將面臨嚴重的物資短缺,隔離措施可能迅速產生重大影響,並迫使美國採取更強硬的回應。同時,中國的隔離措施,將會嚴重衝擊全球產業供應鏈,引發各國的強烈反彈,國際社會將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或採取其他懲罰性措施,要求其解除隔離,此對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地位均造成負面衝擊。
陳偉華|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壹、川普回歸:全然改變的臺海現狀
「我得進行談判,所以永遠不會承諾會怎麼做。」
美國第47任總統川普就職前專訪 2024年12月7日
—《NBC News》Meet the Press
2025年2月10日,在美國海軍驅逐艦強森號護航下,美軍海洋測量船包迪奇號自北向南通過臺灣海峽,距離川普就職尚未滿月。美軍船艦於川普第二任期上任初始首度通過臺海,象徵意涵自然重大。如果說,川普第一任期與第二任期所要面對截然不同的「印度–太平洋地區」安全結構,當屬臺灣海峽的「現狀」已然改變。
當世人仍然以2022年俄烏戰爭的場景,想像臺灣海峽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型態時,實際上,中國已悄然地改變了過去75年來臺灣海峽的現狀。但是,這種現狀是什麼呢?如果我們認知到,臺灣海峽已進入一種「新現狀」或「新常態」,它又呈現怎樣的新面貌?川普2.0政府又如何回應此種臺灣海峽的安全現狀?
在國際體系層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正在迅速崩解。隨著川普2.0外交政策驟變,過往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架構為中心),轉向以「交易」為基礎的國家交往模式,大國之間訴求實力競爭。此一系列的轉變軌跡,體現在川普啟動俄烏戰爭和平談判,在聯合國大會對俄羅斯三週年譴責案中投反對票(中國棄權),以及施壓基輔簽署雙邊礦業協議等作為。美國主流媒體稱,川普政府意圖運用俄烏戰爭的調停角色,敦促烏克蘭簽訂停戰協議,拉攏俄羅斯與中國脫鉤,推動「反向尼克森」外交政策,採取「聯俄制中」強化對於中國的圍堵戰略,但此將以犧牲歐洲與烏克蘭安全為代價。
川普2.0政府亦展現出明確的「擴張主義」傾向,就職前川普已提出多項具有戰略意涵的政策主張,包括接管巴拿馬運河的管轄權、建議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更名墨西哥灣為「美國灣」、購買格陵蘭島、促成以色列與哈馬斯的停火與接管迦薩走廊等國際事務的安排,顯示出川普政府不僅試圖重新定義美國的全球地位,更可能藉由強勢外交手段,重新塑造國際地緣政治版圖。
在國際關係領域,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強權尋求結盟或增強自身實力,防止崛起大國主導國際體系,若一國軍事力量過強,周邊國家亦會形成反制聯盟。川普政府顯然正在操作一場「大棋局」,可能通過與俄羅斯合作,削弱中俄聯盟,進而影響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此舉將對臺灣海峽的安全產生哪些影響?臺灣仍然是美國亞洲戰略的核心嗎?
一直以來,對於「中國可能入侵臺灣」的命題,華盛頓政策圈對於防衛臺灣的承諾,究應採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立場,始終存在辯論。隨著解放軍加速改變臺海安全結構,再度引發「棄臺論」效應,如今,美國應避免直接軍事介入臺海衝突,已在華府逐漸形成戰略共識。在競選期間與白宮就職後,川普及其國安幕僚要求臺灣提升國防預算占GDP(2025年臺灣GDP預估值約26兆4493億元新臺幣)比例,方能有效嚇阻中國大陸入侵,避免戰爭。可以預期,川普將取消拜登時期明確防衛臺灣的政策宣示,通過軍售和軍事技術支持強化臺灣的不對稱防禦能力,也不會明確承諾出兵協防臺海,以降低美國捲入戰爭的風險。
儘管川普2.0戰略將再次轉向印太布局,此時此刻,華盛頓政策界仍為2027年「戴維森窗口」(The Davidson window)(美國印太司令部前司令菲利普·戴維森於2021年在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表示,中國可能在2027年至2035年間嘗試以武力奪取臺灣,這段期間被稱為「戴維森窗口」)是否存在進行辯論。美國內部似乎陷入與中國在臺灣海峽競爭的戰略分歧,看似兩黨「反中」立場趨向一致,然而,分歧仍展現在「短期應對 vs. 長期競爭」的步驟之爭。前者主張2027年是解放軍達成「現代化建軍」的指標年,美國應加大投入軍事資源,為臺海可能爆發的短期衝突做好準備。後者則強調美中長期競爭的必然,認為美國不應過度聚焦短期軍事威脅,而忽略在經貿與科技領域的持久性戰爭。顯然,如何平衡短期威懾與長期競爭的資源分配,將是川普第二任期的重要任務。可以確認的是,如果在2025年雙方走向更加對抗,川普國安隊伍將愈願意運用臺灣作為戰略槓桿,加劇臺灣海峽的軍備競賽,並視其為華府加大對北京挑釁行為的回應。
貳、上任之前:川普對臺灣安全的政策取向
根據美國總統權的研究,每一任美國總統在入主白宮之前,對於執政的政策目標和對幕僚人事的政治任命,已有初步的構想,這是上任之後執政團隊得以即刻啟動總統決策機制的基礎。因此,在分析川普第二任的「總統任期」似乎應可將時間範疇擴展至他勝選之後和就職前。進一步看,觀察美國總統上任前對外部威脅認知的形成,有助於避免我們混淆總統上任後面臨政治壓力下的決策行為。誠如季辛吉1979年所言,在總統執政期間,面對諸多危機決策時刻,領導人對於威脅來源的判斷可能受到多重的干擾因素和體制壓力,致使最終決策本身可能未能真正反映出總統的想法。
回顧川普第一任期,他對於中國對美國和臺灣威脅的認知,深受其政策顧問、地緣政治,以及其「美國優先」的政治信念影響。觀察川普第一任期的政務領導風格,他的認知根植於強烈的經濟競爭、軍事威脅以及價值觀對立的三重特性,這些特性形塑出所謂的「川普主義」。
首先,川普本人及執政團隊對中國的經濟威脅,來自共和黨民族保守主義陣營對於中美長期競爭結構的認知。川普勝選功臣和白宮首席策略長班農(Steve Bannon)與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力主「貿易戰與經濟脫鉤」,彼等深受經濟民族主義論者的推斷,認定中國「百年馬拉松」的最終目標是超越美國,篡奪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因此,川普推動全面的貿易戰,強調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如對電動車的高額補貼)、竊取智慧財產權,以及對美國製造業的掠奪。2018年起,川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川普本人則多次公開批評中國透過經濟手段削弱美國的地位。
在政策執行上,川普任命國務卿龐培歐、國家安全顧問波頓等鷹派現實主義者,致力於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擴張。2017年,川普政府公布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揭櫫「大國競爭」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挑戰,將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強調中國「經濟掠奪行為」為美國主要威脅。在2020年12月川普任內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升級為「主要挑戰者」,指出中國對美國經濟、技術、軍事與價值觀的全面威脅,北京不僅試圖改變國際秩序,更意圖取代美國和美元體系的霸權地位。
在軍事威脅上,川普對北京在臺海與南海爭議上的侵略意圖有清晰的認識,任內將臺海安全與南海動態連結,賦予兩者連動性的政策操作空間。在執政首年,川普擴增對臺軍售的範疇,在任內通過11次對臺軍售,總金額超過180億美元,項目涵蓋:加強空域優勢(F-16V、MQ-9B無人機系統)、海軍與防空能力(魚叉飛彈、標準防空飛彈、區域防空系統升級)、增強本島陸地防衛與不對稱作戰能力(M1A2戰車、HIMARS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同時,「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明確將臺灣視為該戰略的一部分,強調臺灣作為民主夥伴的重要性。美臺軍售範疇的擴大,顯示川普第一任期在戰略上積極協助臺灣提升整體軍事能力,並形成在臺灣海峽的嚇阻力量。
在價值觀競爭上,共和黨人視共產主義為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威脅。2019年,川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直接向中國表達對其壓制香港自治的反對,川普政府亦批評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並對相關官員實施制裁。2020年7月23日,國務卿龐培歐於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發表對中政策演說,呼籲世界各國與中國人民「改變中國共產黨的行為」,龐氏的發言等同宣示美國將致力顛覆共產政權,被外界視為開啟新一場冷戰的「新鐵幕演說」。
關於來自兩岸衝突的威脅,誠如前國安顧問波頓書中的爆料,他直言川普對臺灣並不友善,川普屢次用「桌上的筆尖」比喻臺灣,以「筆尖、桌面」比喻兩岸在川普心中的懸殊地位。對於習近平,川普更願意推崇習主席為中國歷史「最偉大的領袖」,有意拉近兩國元首情誼。如果波頓所言如實,臺灣在川普心中可謂微不足道,那麼臺灣是否還有被美國保護的價值?或只是川普牌局中的籌碼?在川普第二任期中,美國究竟是否延續民主盟友的承諾,或選擇透過對習近平的直接談判,以交易型外交來對應臺灣問題?或許檢視川普團隊對應臺灣海峽新現狀的政策立場,可以提供一個參照的指標。
特別是,過往川普國安團隊中的關鍵友臺官員已離開川普政府,他們並未受邀列入川普2.0政務任命的名單,這些跡象顯示,臺灣在川普第二任期下地位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
參、川普第二任期對臺海安全的意涵
1950年冷戰初期,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的演講中,闡明美國在東亞的防禦立場,意在穩定美國的盟友信心,重申美國的防禦承諾,並在此背景下,艾奇遜劃定了所謂的「艾奇遜防線」。這條防線涵蓋日本本土、沖繩和菲律賓,但未將韓國和臺灣納入防禦範圍,冷戰史學者認為,艾奇遜防線事實上鼓勵北韓檢驗美國的防衛決心,直接導致了韓戰的爆發,深刻地影響冷戰期間的東亞地緣政治。艾奇遜防線的歷史教訓,是否足以提醒川普政府,在定義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時,不應該排除臺灣,避免重蹈艾奇遜當年的覆轍?
一、對應臺灣海峽新現狀
首先,當世人還在以2022年俄烏戰爭的場景,想像臺灣海峽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型態時,實際上,中國已悄然地改變過去75年來臺灣海峽事實上的現狀。但是,這種現狀是什麼呢?如果我們認知到,臺灣海峽已進入一種「新現狀」或「新常態」,它又呈現怎樣的新面貌?
長期以來,儘管兩岸在法理上處於「主權競合」的狀態,兩岸政府之間仍維繫著1954年以來「臺灣海峽中線」(簡稱「臺海中線」)的某種默契,形成「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法理關係。彷如賽局理論中維持「納許平衡」(「納許平衡」是賽局理論核心概念之一,指在非合作賽局中,各參與方根據其他參與方的策略選擇最優策略,而當所有人皆選擇自身最優策略時,沒有任何一方能夠透過單方面改變策略來獲得更好的結果)的兩個政治實體,在不同階段,總會有一方強勢立場,而另一方必須選擇讓步。北京雖從未承認此種法律關係,惟在兩岸實務上已透過海峽雙邊協定與司法文書往返,接受此種「治權相互承認」的互動關係。
然而,自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民主黨籍加州)訪問臺灣,中國對臺海周邊發動大規模「圍臺軍演」,操演範圍幾乎涵蓋整個臺灣海峽,亦有意對臺灣形成「封鎖」之勢。演習期間,中國外交、國防與國臺辦發言系統稱「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線』」。此後,解放軍的軍機、艦等武裝勢力常態性的穿越海峽中線。
在2024年2月間「金門近海快艇翻覆事故」(本章簡稱「金門事件」)後,國臺辦發言系統稱,「海峽兩岸都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對臺灣海峽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中國國內法,臺灣海峽水域分別為中國內水、領海、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水域』」。顯然,中國此舉等同否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關係條例」)第29條授權國防部劃設限制或禁止水域。
為回應2024年賴清德總統在就職典禮和國慶演說重申兩岸「互不隸屬」,解放軍東部戰區先後展開代號「聯合利劍—2024A」和「聯合利劍—2024B」的系列演習,軍演範圍涵蓋臺灣周邊海域與空域,延伸至東海與南海部分地區,展示對第一島鏈的控制力與投射能力。2024年12月初,解放軍舉行近3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集結各類艦艇約90艘,活動範圍從日本南部延伸至南海,涵蓋東海與南海部分區域。至此,中國此舉等同將全世界宣告,臺灣海峽已在中國管轄權控制之下。
顯然,由中國以單邊行動推動臺灣海峽的「新現狀」的意圖已是昭然若揭。此前,中國在法律定性上徹底否認「海峽中線」、「禁、限制水域」的地位,北京主張臺灣不具備管轄權的實體身分。在此法律戰論述下,解放軍海、空軍、海警船、民用商船可常態性的進入海峽中線以東、外離島「禁、限制水域」內,行使海域執法權。進一步地,中國海上艦船或由軍方調度的海上民兵,得以常態性部署在臺灣本島鄰接區外界線(離領海基線約24浬),確保其得以實施有限或全面的封控措施,或運用海上執法部門在海峽攔截船隻的實力。
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所屬「中國實力計畫」,在2022年8月與2023年11月期間,針對美臺雙方官員與專家學者進行訪談(包括52位美國專家和35位臺灣專家,涵蓋學術界、智庫和政府部門專業人士),調查結果顯示超過90%的美國專家和約六成的臺灣專家贊同,中國在臺灣海峽具備執行「主導隔離」的能力。關於解放軍的封鎖方式,超過八成的美臺專家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高度動態的聯合封鎖「非常可能」或「可能」。
此前,美國「蘭德公司」於2022年5月公布《中國對臺灣施行強制隔離的影響意涵》,該報告從「封鎖」與「隔離」的指涉內涵出發,探究中國對臺灣採取強制隔離的政經效應,提醒世人臺灣供應鏈的脆弱性。蘭德研究團隊判斷,中國基於否認臺灣的主權地位,因此亦不認為兩岸之間存在戰爭狀態,故將不會使用「封鎖」一詞,而傾向採取「隔離」措施。相對於「封鎖」易被解讀為走向戰爭,「隔離」被視為一種非戰爭行為,並非要完全切斷臺灣的糧食和物資供應,而是意圖通過管控臺灣周邊的空域和水域來展現中國的「實際主權」,試圖在不直接爆發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達成對臺施壓的目標。
從國際法視角,「封鎖」被視為一種敵對行為,通常會被認定為戰爭行為,受《海牙公約》及《聯合國憲章》第51條的自衛條款規範,而封鎖行動須滿足公開宣布、實施有效且不能有選擇性等條件,以防止違反中立國的權利。相較而言,「隔離」迄今仍然缺乏明確的國際法條文規範,其法律性質仍屬爭議。對此,蘭德公司援引「1962年古巴危機」(1962年10月22日至11月20日),將臺海與美國當年對古巴實施隔離措施的情境相比,「隔離」比「封鎖」具有較低的戰爭風險,當時提供美方與蘇聯一個避免戰爭的選項,此模式或將是中國對臺灣施行隔離的參考。
如果「隔離臺灣」的想像落實,臺灣對進口資源(如能源、食品)的依賴性及其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角色,將使臺灣在面臨中國的經濟施壓時處於更為脆弱的位置。一旦中國實施隔離措施,臺灣的能源和食品等必需品可能會供應短缺,或價格大幅上漲,從而嚴重影響臺灣的經濟活動
然而,中國採取隔離措施,尚須考慮所需承擔的風險,由於臺灣的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一旦實施隔離措施,臺灣將面臨嚴重的物資短缺,隔離措施可能迅速產生重大影響,並迫使美國採取更強硬的回應。同時,中國的隔離措施,將會嚴重衝擊全球產業供應鏈,引發各國的強烈反彈,國際社會將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或採取其他懲罰性措施,要求其解除隔離,此對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地位均造成負面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