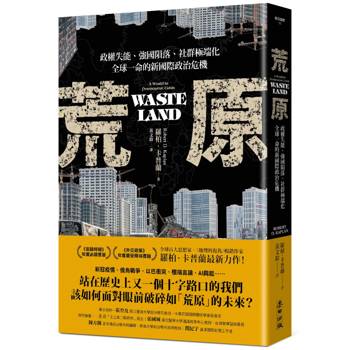厄運是提到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第一個會聯想到的詞。威瑪是一則包裹著糖衣的恐怖故事:這座現代性的搖籃卻孕育了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威瑪時期是藝術領域與知識界的繁榮時期──包含托馬斯.曼(Thomas Mann)與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的小說、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表現主義詩歌、阿諾.荀貝格(Arnold Schönberg)所創作的無調性音樂,以及包浩斯學派的設計與建築實驗──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實驗蓬勃發展,但國內卻充斥著激烈的種族與宗教衝突,更甭提通貨膨脹與經濟蕭條了,這一連串的問題直接導致了……希特勒的崛起。是的,我們都明瞭最終的下場。但身處其中的當事人無法預見未來。
我們會比他們更有智慧嗎?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如今威瑪時代的陰影再度浮現。
只是形式與我們所預期的大相逕庭。
我們不應僅從美國民主衰退的角度來思考威瑪共和國,而應從全球的角度來反思這段時期。
此刻,我們正一頭栽進光鮮亮麗卻空洞的未來,日常生活在絕望中反覆上演,卻又充滿了無限可能,而這一切,全由我們無法擺脫的科技裝置所主宰。我們既是科技的操控者,也是它的俘虜,深陷泥淖的程度遠遠大過從前。人們自以為能違抗地心引力,但透過行動裝置不斷湧入的焦慮,卻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這個世界十分封閉、緊密,卻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能與住在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聯繫,與隔壁鄰居卻有如住在不同星球。這樣的疏離感從社區延伸到國家政治。現代政治的競爭局勢遠比過往激烈,影響更擴及全球,再加上電子通訊讓人際溝通變得愈加虛擬抽象,政治語言隨之變得更尖銳極端──這些因素導致我們即使比鄰而居,彼此間卻隔著巨大的政治鴻溝。
但科技也讓我們的世界變小了,壓縮了海洋與不同陸地間的距離。我們深刻感受到科技新興城市與光鮮亮麗的金融中心有如雨後春筍不斷增長,但這些建築不論經緯所在,外觀都極為相似。未來已經來臨,但看看我們腳下,我們仍堵在車陣中。
我們正著手打造一個串連全世界的文明,但這正是挑戰所在。確切來說,挑戰在於這個全球文明仍持續演變,卻尚未演化完成,仍得等上一段時間,世界各地皆存在著親密與疏離並存的現象。除非科技與全球治理出現顯著進步,否則真正的全球文明永遠只是個假象。我們對彼此影響甚鉅並相互依賴,才能共同生活在一個極不穩定的全球系統中。就像沙特(Sartre)的劇本《無路可出》(No Exit),劇中三個角色被鎖在一個小房間裡,彼此互相折磨。牆上沒有鏡子,他們唯有透過他人凝視才能看見自己。隨著媒體影響政府決策的力道愈強,我們的確因連結性(connectedness)而不受束縛,卻也因此受制。美俄、中美與中俄之間,更甭提中型與小型強國,彼此緊張對峙,加上科技不斷發展,使得世界愈趨緊密相連,當前政治局勢有如當年的威瑪共和國再現:德國曾在一戰後的戰火餘燼中,實行這個虛弱、搖搖欲墜的政治體制,苟延殘喘了十五年,直到最終希特勒掌權。現在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大型威瑪共和國,儘管各地緊密相連,某些地區只要發生動盪,就足以對他國產生致命的影響;但這般緊密程度,卻又不足以產生一個有共識的全球政治型態。如同威瑪共和國四分五裂的政治勢力,我們正處於一個極為脆弱的過渡轉型期,科技不斷演進,政治秩序卻未隨之趨於穩定。
在我們當中,我並沒有看見像希特勒的人物,或一個極權統治的世界政府。但別以為未來人類歷史的發展能對當前困境有任何的解方。這就是我以威瑪共和國為例,作為警示的意義。
我們會比他們更有智慧嗎?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如今威瑪時代的陰影再度浮現。
只是形式與我們所預期的大相逕庭。
我們不應僅從美國民主衰退的角度來思考威瑪共和國,而應從全球的角度來反思這段時期。
此刻,我們正一頭栽進光鮮亮麗卻空洞的未來,日常生活在絕望中反覆上演,卻又充滿了無限可能,而這一切,全由我們無法擺脫的科技裝置所主宰。我們既是科技的操控者,也是它的俘虜,深陷泥淖的程度遠遠大過從前。人們自以為能違抗地心引力,但透過行動裝置不斷湧入的焦慮,卻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這個世界十分封閉、緊密,卻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能與住在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聯繫,與隔壁鄰居卻有如住在不同星球。這樣的疏離感從社區延伸到國家政治。現代政治的競爭局勢遠比過往激烈,影響更擴及全球,再加上電子通訊讓人際溝通變得愈加虛擬抽象,政治語言隨之變得更尖銳極端──這些因素導致我們即使比鄰而居,彼此間卻隔著巨大的政治鴻溝。
但科技也讓我們的世界變小了,壓縮了海洋與不同陸地間的距離。我們深刻感受到科技新興城市與光鮮亮麗的金融中心有如雨後春筍不斷增長,但這些建築不論經緯所在,外觀都極為相似。未來已經來臨,但看看我們腳下,我們仍堵在車陣中。
我們正著手打造一個串連全世界的文明,但這正是挑戰所在。確切來說,挑戰在於這個全球文明仍持續演變,卻尚未演化完成,仍得等上一段時間,世界各地皆存在著親密與疏離並存的現象。除非科技與全球治理出現顯著進步,否則真正的全球文明永遠只是個假象。我們對彼此影響甚鉅並相互依賴,才能共同生活在一個極不穩定的全球系統中。就像沙特(Sartre)的劇本《無路可出》(No Exit),劇中三個角色被鎖在一個小房間裡,彼此互相折磨。牆上沒有鏡子,他們唯有透過他人凝視才能看見自己。隨著媒體影響政府決策的力道愈強,我們的確因連結性(connectedness)而不受束縛,卻也因此受制。美俄、中美與中俄之間,更甭提中型與小型強國,彼此緊張對峙,加上科技不斷發展,使得世界愈趨緊密相連,當前政治局勢有如當年的威瑪共和國再現:德國曾在一戰後的戰火餘燼中,實行這個虛弱、搖搖欲墜的政治體制,苟延殘喘了十五年,直到最終希特勒掌權。現在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大型威瑪共和國,儘管各地緊密相連,某些地區只要發生動盪,就足以對他國產生致命的影響;但這般緊密程度,卻又不足以產生一個有共識的全球政治型態。如同威瑪共和國四分五裂的政治勢力,我們正處於一個極為脆弱的過渡轉型期,科技不斷演進,政治秩序卻未隨之趨於穩定。
在我們當中,我並沒有看見像希特勒的人物,或一個極權統治的世界政府。但別以為未來人類歷史的發展能對當前困境有任何的解方。這就是我以威瑪共和國為例,作為警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