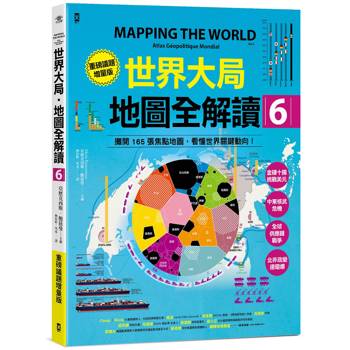【內容試閱】
【Ch 10 加薩戰火:哈瑪斯為何而戰?巴勒斯坦分裂的大起義】
▋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Hamas)在巴勒斯坦地區十餘個組織的支持下,從加薩走廊(Gaza Strip)向以色列發射5,000枚火箭彈,同時派出麾下戰士入侵以色列,共殺害將近1,200人,並擄走252名人質,隨後以色列也不計後果地發動軍事反擊。短短數月間,狹小的加薩走廊遭到徹底摧殘,釀成二十一世紀上半葉數一數二的人道悲劇。
簡稱「哈瑪斯」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伊斯蘭抵抗運動」(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瞞過以色列國防軍(Tzahal )及情報機構的耳目發動突襲,從加薩走廊向邊界另一側發射了5,000枚火箭彈,隨後又派出戰士闖入以色列境內,攻擊多處指揮中心、派出所、市鎮與村莊,造成逾千人死傷。哈瑪斯更擄走252名人質,計畫用來交換身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政府隨即展開反擊,誓言要徹底剷除哈瑪斯。占地360平方公里的加薩走廊自2007年哈瑪斯接管後便遭到以色列封鎖,如今還須承受密集的炮火轟炸(參見圖2)。哈瑪斯此次的暴力行動其實是巴勒斯坦起義(Intifada)的一部分,根源可追溯至2015年,在約旦河西岸(West Bank)醞釀的第三次起義。
2005~2015年,約旦河西岸的情勢相對穩定(參見圖7)。當時第二次起義(2000~2005年)剛剛隨著權力交替而平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巴解)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逝世,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 PNA)主席之位由阿巴斯(Mahmoud ¬Abbas)於2005年1月繼任。此後十年間,巴勒斯坦不僅與以色列當局的安全合作運作順暢,主要武裝團體也一一遭到瓦解。直到2015年9月,情勢突變,以色列當局開始鎮壓所謂的「哨兵」,也就是監看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廣場、防止猶太殖民者闖入的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就此陷入動盪,約旦河西岸也隨之動亂。同年10月,一場名為「刺刀起義」(Knife Intifada)的行動爆發,巴勒斯坦年輕人紛紛以利器攻擊以色列士兵與平民。
◎跨越派系,凝聚巴勒斯坦年輕人的大起義
2017年7月,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幾處伊斯蘭聖地入口設置安檢門。此舉隨即在巴勒斯坦引發示威活動,而後在同年12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首屆任期2017~2021年,2025年再度上任)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抗議的聲浪隨之達到頂峰。2018年4月,加薩地區針對難民「回歸權」的示威雖然遭到以色列國防軍鎮壓,卻從未平息,有時也不惜訴諸暴力。從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到加薩走廊各地的年輕世代,甚至是出自擁有以色列國籍的「1948年巴勒斯坦人」(參見圖1),在沒有任何中心黨派領導之下,仍然串連起來,一場起義逐漸醞釀成形。由此可見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的影響,一部分巴勒斯坦年輕人已然揚棄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而協議中以「兩國方案」為基礎的和平進程也早已破局。
2021年春天,越線時刻到來。5月10日,哈瑪斯武裝支部「艾茲丁.卡薩姆旅」(Ezzedine al-Qassam Brigades)宣稱,若以色列部隊與猶太殖民者不撤出耶路撒冷清真寺廣場與東耶路撒冷的「謝赫賈拉」(Cheikh Jarrah)社區,他們就要對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為這場從加薩走廊擴散出去的全面起義揭開序幕。5月17日,法塔赫(Fatah,全稱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武裝支部「阿克薩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s)的成員16年來首次在自治政府所在地拉馬拉(Ramallah)示威遊行,而來自黎巴嫩與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也紛紛向以色列邊界前進。
事實上,約旦河西岸早已被以色列的殖民活動割據得支離破碎,據2021年統計,當地共有71萬9,452名猶太殖民者,其中32萬6,523人定居在耶路撒冷,分散於151個「屯墾區」。敵視新一波起義分子的以色列占領軍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安全部門便在這些地區密集巡邏。阿巴斯一度指望美國拜登政府(2021~2025年)重啟談判,同時封殺來自哈瑪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等反對派的勢力,然而局勢已經失控。「哲寧旅」(The Jenin Brigade)和「獅穴」(The Lions' Den )等武裝團體對猶太殖民者及以色列部隊發動的攻擊日益頻繁,自然又引發以色列新一輪的反擊。此次起義行動主要是由紮根在地的年輕地下成員組織而成,透過彼此的人際網絡相互連結,還獲得民眾與家庭的保護,起事後便在約旦河西岸引發骨牌效應。
這些團體另有三大共同特徵:同世代、同階級、跨派系。其麾下戰士主要出生於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他們成長於以色列殖民與法塔赫-哈瑪斯分裂的時代,在巴勒斯坦民族滿目瘡痍的歷史中走向政治、武裝抗爭與地下活動的道路。此外,這些團體大多由不同派系組成,比如哲寧旅與獅穴的成員即來自哈瑪斯、法塔赫、伊斯蘭聖戰組織與人民解放陣線。由於他們無法「由上而下」推動民族團結,只好採取「由下而上」的做法。階級相同則是基於這些團體泰半活躍於人口稠密的都市地帶,所以能動員的以貧困家庭的年輕人居多。
◎以色列擔憂哈瑪斯恐與真主黨串連
隨著以色列社會愈趨分裂,巴勒斯坦人看準時機,在約旦河西岸的行動也日益白熱化。2023年1月以來,針對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2022年12月重返以色列總理之位,以及最高法院改革計畫的反對聲浪達到空前規模。與此同時,以色列安全內閣對於約旦河西岸民情沸騰以及加薩走廊脫離掌控感到憂心忡忡,而且與前兩次巴勒斯坦起義不同的是,如今以色列內部正處於山雨欲來的政治危機之中(參見圖4)。
巴勒斯坦方面已經改變戰略,特別是哈瑪斯,他們的目標不再只是控制加薩走廊,而是要重新鎖定耶路撒冷,並在約旦河西岸擴張勢力,建立更多武裝據點。2023年6~7月,「阿亞什營」(Al-Ayyash Battalion)宣稱他們就是從約旦河西岸的哲寧市向以色列屯墾區發射土製火箭炮的幕後主使。哈瑪斯旗下的武裝人員更加頻繁地在約旦河西岸攻擊以色列殖民者與士兵,同時也挑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國家安全部隊(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NSF),而後者亦監禁了部分哈瑪斯成員。直到2023年10月7日,雙方的衝突達到巔峰——哈瑪斯襲擊了以色列領土。
自2022年底至2023年初的這個冬天以來,什葉派(Shia)組織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與以色列之間同樣關係緊張,從區域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巴勒斯坦也不可能置身事外。2023年,以色列指控真主黨策畫了3月15日針對以色列北部米吉多(Megiddo)地區的武裝攻擊行動;同年4月,又有火箭炮自南黎巴嫩射向以色列,而時任哈瑪斯政治局主席的哈尼雅(Ismail Haniyeh)正好在黎巴嫩首都會見真主黨總書記納斯拉勒(Hassan Nasrallah)。以色列也曾對哈瑪斯的二號人物艾魯里(Saleh al-Arouri)多次發出警告,懷疑他在約旦河西岸策畫起義。以色列國防軍擔憂整片區域的戰線會串連起來,從加薩走廊穿越到約旦河西岸,再延伸至1967年遭以色列占領的敘利亞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最後連接到南黎巴嫩。如今真主黨支持哈瑪斯於2023年10月7日的攻擊行動,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應驗了以色列當時的預測。
◎引發全球矚目的加薩人道災難
2024年5月底,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根據加薩走廊衛生部的資料指出,當地死亡人數已超過3萬5,800人,另有8萬200人受傷;共有75%的加薩人口流離失所,110萬人受飢餓所苦,醫療設施也完全被摧毀。據統計,2023年10月7日到2024年5月15日之間,約旦河西岸與東耶路撒冷共有480名巴勒斯坦人(包括116名未成年人)遭以色列軍隊或殖民者殺害(參見圖6)。
這場人道危機一躍成為全球焦點,促使國際社會紛紛呼籲停火(參見圖5)。2023年12月29日,南非根據《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於海牙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對以色列提起訴訟。2024年5月20日,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檢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起訴三位哈瑪斯領導人(哈尼雅、戴夫[Mohamed Deif]與辛瓦[Yahya Sinwar]),同時也起訴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與國防部長葛朗特(Yoav Gallant)犯下「戰爭罪」與「反人類罪」。以色列如今陷入僵局,哈瑪斯未被殲滅,其武裝支部「艾茲丁.卡薩姆旅」仍然頑強。2024年5月6日,以色列攻擊加薩南部的拉法市(Rafah),而哈瑪斯仍有餘力在賈巴利亞(Jabaliya)難民營與加薩北部的以軍控制地貝特漢諾(Beit Hanoun)發動一連串攻勢。哈瑪斯與一干結盟的巴勒斯坦組織很有耐心地透過不對稱的城市游擊戰,憑藉地利之便騷擾以軍,舉凡摧毀戰車、狙擊、在建築物中裝設炸藥陷阱、發射迫擊砲攻擊等無所不為。
當然,哈瑪斯一方亦蒙受損失。2024年1月2日,以色列暗殺了哈瑪斯的二號人物艾魯里,兩個月後又宣布擊斃其軍事副指揮伊薩(Marwan Issa);同年7月,領導人哈尼雅遭到刺殺身亡,「艾茲丁.卡薩姆旅」指揮官戴夫與政治局主席辛瓦也相繼死於以色列發動的空襲與圍剿行動。然而,這些戰果與以色列起初宣稱的目標相比差距甚大,截至2024年5月,還有124名以色列人質在巴勒斯坦各路組織手上未能獲釋,遑論哈瑪斯的地下隧道網絡仍未遭破獲。哈瑪斯不只在軍事上十分頑強,政治上也扎根加薩多年(自2007年接管至今),既是武裝民兵亦是執政黨,擁有數以千計的公務員、社工與警員支持。自2023年10月27日以色列發動地面反攻以來,這些人一直是哈瑪斯的中流砥柱。
◎潛藏在以哈戰火下的分裂危機
然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卻無人敢提及「第三次起義」。為何巴勒斯坦部分地區已脫離以色列軍隊掌控,自治政府中的要角卻遲遲不順勢而起?首要阻礙是巴勒斯坦內部的分裂。1987~1993年的第一次起義獲得巴解全體派系一致支持,並透過全國統一指揮部協調行動;2000年的第二次起義則有精神領袖阿拉法特支持,然而今非昔比。2022年10月的《阿爾及爾協議》(Algiers Declaration)本應為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議改選與巴解改革鋪平道路,卻從未真正落實。預計於2023年7月底於開羅召開的巴勒斯坦各派系書記長會議,也遭到伊斯蘭聖戰組織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總指揮部抵制。阿爾及利亞、埃及、卡達都曾經試圖從中調解,就連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2014年就任)也曾在2023年7月26日於首都安卡拉(Ankara)會晤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與哈瑪斯政治局主席哈尼雅,並於2024年2月與4月兩度斡旋,但所有敦促哈瑪斯與法塔赫和解的努力皆宣告失敗。
至於阿拉伯國家是否會支持巴勒斯坦起義,則尚未可知。隨著2023年10月以哈衝突爆發,《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2020年簽訂,又稱《以阿和平協議》)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蘇丹、摩洛哥承認以色列建國的事宜似乎再無進展;沙烏地阿拉伯不再考慮與以色列建立和平關係,而主導以色列與阿拉伯諸國談判的人士也不得不重新關注原本有意忽略的巴勒斯坦議題。
另一項阻礙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各個武裝團體之間的關係。雖然「哲寧旅」與「獅穴」為避免爆發內戰,不打算與國家安全部隊開戰,但自治政府與以色列國防軍長期以來的安全合作確實顯得礙手礙腳,尤其是許多激進分子遭到巴勒斯坦預防安全部隊(Palestinian Preventive Security)逮捕拘禁,而一般民眾對於阿巴斯領導的自治政府也滿是怒火。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加薩走廊,擔心這塊土地在以色列的轟炸下會灰飛煙滅。然而在約旦河西岸,起義暗潮洶湧,許多自治區烽火不休。
【Ch 57 新鴉片戰爭:吩坦尼彎折大都會,殭屍片街頭上演?】
▋舊金山的田德隆區(Tenderloin)、費城的肯辛頓區(Kensington)以及渥太華的下城區(Lower Town)等北美大都會中,隨處可見一具具因為強效藥物吩坦尼(fentanyl)而「彎折」的身體。據統計,美國每年約 10 萬人因用藥過量致死,其中2/3案例的禍首就是吩坦尼。然而,這不過是「冰山一角」,長此以往,很可能引發社會亂象。
這場悲劇的源頭可以追溯到 1959年,化學家保羅.楊森(Paul Janssen,1926~2003年 )在比利時合成出藥物吩坦尼,主要作為醫療用的麻醉劑。到了 1990年代,吩坦尼皮膚貼片與噴霧劑問世,可用於緩解手術後疼痛與癌症疼痛。2021年合法製造的醫用吩坦尼約2 公噸,而美國是主要生產國。吩坦尼屬於合成類鴉片藥物,功效是海洛因的 50 倍、嗎啡的 100 倍,而且衍生物眾多,其中成分會影響腦幹的受體,用藥過量很可能導致呼吸驟停。
◎中國在吩坦尼製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類鴉片藥物在大都會區氾濫,在社會與經濟層面皆造成莫大損害(參見圖2)。舉例來說,2022年,舊金山總人口數為 80萬8,400 人,其中 8,000 人為遊民,每天約有2人死於藥物過量。類鴉片藥物在當地引發「貧窮世襲」危機,市政府甚至宣布田德隆區進入緊急狀態。辦公室和商家紛紛關閉,貧窮、情節輕微的犯罪與吸毒問題更加猖獗,導致社會大眾對此街區的負面印象更深。而且,不只是底層人民,所有社會階層都受到這場亂象的影響。
吩坦尼是如何來到美國大都會街頭?說起來可真是一段漫長的旅程。不同於海洛因和古柯鹼受到產地的限制,合成類鴉片藥物可以在任何地方生產(參見圖1),然而製造吩坦尼需要先驅化學品,而中國正是原料藥的主要出口國。1980年代初在中國最早成立的製藥公司之一,就是吩坦尼發明者所創立的楊森藥廠(Janssen)。
儘管美國已成功阻擋中國直接出口吩坦尼,但是其先驅化學品在中國依然合法。由於茲事體大,美國前總統拜登(任期2021~2025年)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2013年上任)還曾於2023年11月15日在舊金山會晤,討論如何加強美中共同打擊非法走私的問題。
◎墨西哥毒販靠藍色藥丸賺取暴利,下一站鎖定歐洲?
中國的先驅化學品會透過郵件、貨櫃甚至專用貨機出口,送往墨西哥的吩坦尼化工廠,所以美國很難控管(參見圖3)。曼札尼約(Manzanillo)是墨西哥最大的貨櫃港口,在南美洲排名第三,是防範這種藥物入境的第一線。2021年,墨西哥海軍在曼札尼約查獲 42公噸的先驅化學品,但是每年在此過境的貨運量約 350 萬TEU,相比之下根本是九牛一毛。此外,走私吩坦尼的販毒集團以恐嚇和賄賂等手段控制了整個區域。進口的原料藥透過太平洋高速公路北上,途經被當地黑幫占據的哈里斯科州(Jalisco)與西納羅亞州(Sinaloa),最後抵達古拉坎市(Culiacán),此處設有許多製毒工廠,且為了降低風險,通常工廠規模較小,窩藏於民宅或商家後面,甚至是在山上。吩坦尼的原料在這裡經過「加工」製成糊狀物,之後再壓製成藥丸。據悉,一間工廠在24 小時內可以生產 4 萬顆吩坦尼。一公斤的先驅化學品售價 800 美元,壓成吩坦尼藥丸後,價值約 1.7萬美元,在美國轉售則可以高達 60 萬美元,如此高的利潤促使這種藥物在美國快速氾濫。據統計,墨西哥政府於2022年查緝到的吩坦尼約2 公噸,而2019年的查緝量還不到 500 公斤。
販毒集團經由汽車或卡車將吩坦尼運過美國邊境,先存放在洛杉磯、艾爾帕索(El Paso)或鳳凰城附近的藏貨地點,再分送到美國各地。這些藍色藥丸的售價是 15 美元一顆,在費城街頭甚至能以同樣價格換取三顆。儘管前總統拜登推動耗資 460 億美元的計畫來打擊毒品走私,美國每天依然有將近一台客機乘客數的人口死於吩坦尼。
而今,類鴉片藥物氾濫的問題已經蔓延到鄰國加拿大,雖然歐洲僥倖還未受到影響,但是能維持多久?畢竟有些歐洲國家是吩坦尼的主要生產國與進口國之一,比如比利時的產量占全球的 15%,德國則是主要進口國,占全球進口量將近 40%。目前吩坦尼在歐洲大陸還不是主流毒品,根據調查,2021年法國境內沒有任何與藍色藥丸相關的藥物過量紀錄,即使有查緝到零星案件,也是透過「暗網」從中國購入。
美國的吩坦尼亂象若要追本溯源,就不能不提到類鴉片藥物的濫用。從 1996年起,市場上大力推銷強效止痛藥「疼始康定」(OxyContin,又稱「奧施康定」)便引發了嚴重的藥物依賴問題。2010年美國政府開始限制這種藥物後,成癮者先是以海洛因替代,接著又轉向更便宜的吩坦尼。由此可知為什麼在芬蘭或愛沙尼亞等海洛因氾濫的國家,更容易發生類鴉片藥物濫用的現象。歐洲,無疑是墨西哥販毒集團下一個覬覦的新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