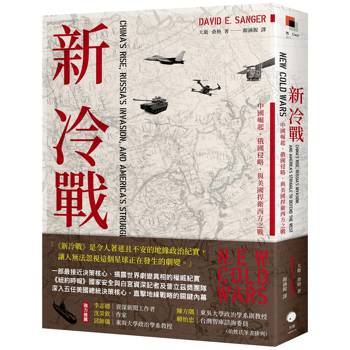第十六章 小院高牆
在離台北西南方約一個多小時車程的地方,這片曾是農地的土地,數百年來先後曾為台灣原住民、西班牙傳教士、荷蘭探險家與日本占領者所居,如今則藏著台灣最大的商業寶藏。這個地方現在名為新竹工業園區,而坐落其間的,正是亞洲最有價值的公司: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台積電。
台積電只生產一樣東西:電腦晶片。當然,它所生產的高品質半導體產品非常多樣,從記憶體、繪圖晶片到先進製程、蘋果iPhone手機專用、依客戶設計量身打造的微處理器,樣樣皆有。台積電之所以打響名號,正是因為其在科學園區內建置的半導體製造廠,對於精密與低價生產的極致追求,而這些製造廠後來更拓展到全台灣各地。不過,台積電本身並不設計晶片,而是負責代工生產其他公司設計的晶片,這些晶片被全世界倚重,舉凡F- 35戰鬥機、海馬斯飛彈發射系統,到安卓手機和智慧型電視,無一不需仰賴。今天政治人物稱晶片為「新石油」,這個比喻雖不全然準確,卻的確點出了晶片在全球經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
晶片製造其實來是於美國釋放的技術。當年矽谷的先驅如快捷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英特爾(Intel)與摩托羅拉(Motorola)才是真正開創晶片技術、改變世界的力量。但在之後數十年間,這些公司因各自追求利潤的因素,逐步將製造業務移往海外,未顧及這會使美國過度依賴一座離中國不遠的小島供應晶片,進而危及國家安全。他們當時的想法是,就如石油通過波斯灣的霍爾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後能源源不絕地輸往全球,晶片應該也能如此。
沒想到美國對晶片這條複雜且容易斷裂的供應鏈的依賴,遠遠超過對波斯灣石油的依賴。一些用於基本電器產品如洗碗機、燃油車儀表板與工業器材的成熟製程晶片,要不是中國生產,就是在中國完成後段組裝作業,例如將晶片插入電路板後整合完成。這賦予中國龐大的籌碼與優勢。但更大的問題,是美國對台灣所生產的最先進晶片過度依賴。拜登政府上任初期所掌握的數據顯示,台灣生產了全球近九成最先進晶片,僅因各界對「先進晶片」定義略有差異而有細部落差。
撇開定義不論,有件事卻極為明確:那就是台積電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晶片廠若是停擺,那蘋果iPhone手機一旦損壞需要零件更換,用戶恐怕就得愁眉不展。蘋果iPhone15所用小小的蘋果A-17「仿生」(bionic)晶片中,一共塞進了一百九十億顆電晶體,而這些晶片,蘋果幾乎都仰賴台積電進行生產。蘋果首席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花了極大的心力想要讓蘋果供應來源多樣化,將部分製造移往印度和其他地區。即便如此,短期內蘋果仍離不開台灣,輝達(Nvidia)亦是如此。這家晶片設計公司如今已是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如ChatGPT的核心推手。
台積電在全球晶片競賽中的主導地位,為全台灣帶來的財富與國際重要性,絕非當年蔣介石為躲避國共內戰而撤退來台時所能預料。但也正因台積電的成功,改變了中國一旦入侵台灣、或包圍孤立台灣、或企圖武力統一時的戰略部署。而這些台灣可能面對的風險,全世界直到最近才真正意識到其嚴重性。
台積電草創之初,最擔心的風險其實是地震,因此晶片廠未集中在單一地點,而是分布全島。但隨著習近平喊出武統台灣的聲量日增,經濟學家與戰略規劃專家開始沙盤推演,思考若台積電晶片廠遭破壞或全毀、或中國侵略行動導致供應鏈中斷,將對全球經濟造成何種衝擊。他們的模擬結果顯示,全球經濟將會損失高達數十億到數百億美金,而且這還只是針對頭幾天的估計。
一名在中國與台灣均有重大投資的公司總裁,在參與模擬台海衝突對全球經濟影響後對我說:「這種事誰都不想去設想,所以也沒人真的去評估。」他說當向其他企業高層提起這問題時,「大家都不太願意多談。」這背後部分原因,是因為不願正視現實。但企業高層本應有最壞打算。中國對台積電的依賴不亞於歐美,中國許多產品同樣需要台積電的晶片。北京若想在太空與人工智慧領域領先全球,亦仰賴台積電的高端晶片。也正因這種中台間的互賴關係,有些人主張這為台灣建立起所謂「矽盾」:台積電對中國過於關鍵,使得習近平不得不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畢竟,哪個理性領導人會刻意炸毀自己的供應鏈?
這樣的理論表面說得通,但是否真能成立,卻無人能保證。習近平若優先考慮中國的經濟利益,或許會推遲武統幾年。但我問過台積電高層、台灣總統府官員及五角大廈人士,卻無一人認為光靠「矽盾」就能永遠阻止中國武統。
長遠來看,「矽盾」終將失效,因為中國最終仍會掌握台灣的技術。即使短期內假設習近平與其決策圈皆為重視經濟、謹慎理性的領導人,但一旦面對重大經濟或政治危機,這些假設也可能不成立。持此觀點的鷹派指出:只要看看習近平一旦覺得香港這個中國最會賺錢的金雞母可能成為異議發酵溫床,就毫不留情地踩下重手;又或者觀察他如何整肅阿里巴巴創辦人、中國科技巨頭馬雲──若連馬雲那樣為中國帶來數百億經濟與關鍵技術的企業都能被犧牲,他是否也會為維護自身權力,賭上台積電的命運?
是否會走到這一步,台積電內部當然不願多談,至少不會公開談。我問了當時擔任台積電執行長的劉德音──這位在柏克萊大學受教育、精明老練的經理人──怎麼看這項風險。他平靜地說:「我完全不去想侵略這件事,因為無從想像起。」事實上,這並非無從想像:這正是台北當局與華府戰略規劃人員每天設想的末日場景。
台灣之所以能成為今日全球供應鏈的關鍵核心,乃是多項重大歷史事件的匯聚成果。一方面,是台灣在民主轉型初期適逢其時,配合富有遠見的國家戰略;另一方面,則有畢業於哈佛與麻省理工學院、因不滿德州儀器忽視而離職的傑出美籍華人工程師張忠謀的遠見卓識;再加上美國一連串錯誤的商業判斷,共同造就今日局面。
其中最關鍵的角色,就是張忠謀本人。這位出生於中國、在美國受教育的工程師與企業家,在接受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亦曾任經濟與財政部長的李國鼎之邀來台訪問前,其實只來過台灣幾次。李國鼎的構想,是借重張忠謀的專業與歷練,讓台灣半導體產業扎根發展。在當時的台灣政府高層中,李國鼎最能看清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地位:長期處於毛利最低的下游,只負責封裝或組裝低價電器用的晶片。若台灣要像日本一樣邁向富裕,就得設法進入供應鏈的核心環節。
而張忠謀正是這項構想中不可或缺的要角。他多年來一直懷有一個想法:創立一間專責製造、能為全球各家設計需求量身打造晶片的半導體工廠,專注於高端製造技術。在當時,這種模式並不符合業界主流。像英特爾與德州儀器這類大公司,都是設計、生產一手包辦。然而張忠謀認為,若台積電要成功,應讓其他企業負責設計,由台積電專精於為客戶代工製造。
李國鼎對他的構想深感認同。他問張:「你需要多少錢?」聽到數字後,眼睛連眨都沒眨一下。
張忠謀的遠見,果然在對的時機做了對的決定。當時半導體技術日益複雜,製造成本也節節攀升。新的晶圓廠需導入最先進的雷射光技術,雕刻更細密的電路,以便將更多電晶體壓進晶片中,這類工廠造價動輒數十億美元。數年後,一座十億美元的晶圓廠竟變得像撿便宜似的划算。正如張忠謀預測,許多大公司陸續將晶圓製造外包代工。一些仍維持自產晶圓的企業,也開始遭遇美國技術人才短缺問題。
華府素來會檢視中國在美國科技公司的投資,只要查覺到投資威脅到國家安全,隨時都會喊停。但對於製造業外移,卻視為單純的商業自由,並未設立防線。長年下來,美國科技公司紛紛選擇專注晶片設計,而將製造外包給如台積電這類專業廠商。這套策略後來與「全球化」的思維相輔相成──當時普遍相信,在全球化的時代,資訊時代的晶片在哪裡生產並無差別。偶有供應干擾也無妨,畢竟以賺錢為最高原則的資本世界中,維持供應鏈不斷,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尤其中國更是如此。
數十年來,這就是主流的想法。但沒想到新冠疫情一來,所有人頓時驚覺,一旦供應鏈中斷,各種問題將接踵而來。多數晶圓廠被迫關閉,貨機航班也取消,新出廠的汽車與卡車只能堆在工廠裡,等待那遲遲未到、卻是組成導航系統或防滑剎車所必需的那一小片晶片。寶馬(BMW)開始頭痛,因為它的新世代純電豪華旗艦車i7,一台車就裝了上千片晶片。
經濟問題極為複雜,難以理解,也更難解決。政策制定者大多不了解晶片製造程序的複雜性,只好趕緊補課,試圖搞清楚為何美國無法乾脆將晶片生產全部遷回國內。事實上,美國國內仍有數十家晶圓廠,從佛蒙特州的柏林頓(Burlington)、明尼蘇達州的布魯明頓(Bloomington)、到奧勒岡州的希爾斯伯洛(Hillsboro)都有分布。問題在於,晶片並非通用格式:福特F-150汽車儀表板的晶片,無法用於惠而浦(Whirlpool)洗衣機上。建造新晶圓廠所需的時間、成本與難度極高。而且即使疫情期間台積電晶圓廠仍可正常運行,大家也心知肚明:萬一哪天這些晶圓廠停工,對全球經濟會造成多麼嚴重的衝擊。
疫情現實終於驚醒了政策制定者,但這其實是國安幕僚與五角大廈一小群核心官員多年前就不斷提醒的事。等到拜登上任時,經常被引用的一項統計是:美國自製半導體在全球的占比,從一九九○年的三成七下降到二○二○年的一成二。由此可見,台積電面臨的最大戰略風險已昭然若揭。中國對裴洛西訪台的反應,即使是最樂觀或無知的高階管理層與投資者,也不得不嚴肅看待中國若入侵台灣、或僅僅封鎖台灣、逼迫其回歸統一所帶來的潛在影響。一旦中國採取這些手段,台積電那些生產最精密晶片的工廠都將停擺。如果連台灣周邊的海底電纜也遭切斷,台積電將瞬間失去與西方世界晶片設計者的聯繫。而若中國發動海軍封鎖,台積電將迅速面臨化學原料與矽原料短缺,工程師們甚至可能攜家帶眷逃往聖荷西(San Jose)、東京或歐洲。(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