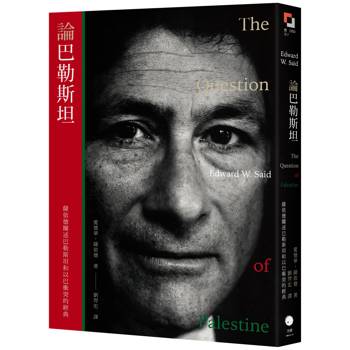前言
本書的大部分內容完稿於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初,成書於近東現代史中極為重要的年間,但參考座標絕不僅限於上述時期。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是提供西方讀者一個能廣泛代表巴勒斯坦的立場。許多人在此刻談論著巴勒斯坦與巴勒斯坦問題,但「巴勒斯坦立場」仍不太為人所知,也從未被充分理解。本書在闡述這個立場時,主要依據的是那些我認為足以被稱為巴勒斯坦的經驗。就任何層面而言,自一八八○年代早期,當第一批猶太復國主義者抵達巴勒斯坦海岸時,「巴勒斯坦經驗」即成了一個具備自我意識的經驗;從此,巴勒斯坦的歷史展開了不同於阿拉伯世界的特殊走向。在整個二十世紀當中,儘管巴勒斯坦人與阿拉伯人的行動確實有許多關聯,但巴勒斯坦歷史的決定性因素,也就是猶太復國主義所致的創傷性民族遭遇,是近東地區獨一無二的。
我寫作本書時,我的目標與預期成果(先不論兩者可能的瑕疵),皆是以巴勒斯坦獨有的特性為指南。身為一名巴勒斯坦人,我始終努力意識到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弱點與缺失。依某些標準來看,巴勒斯坦民族也許並不特殊;我們的民族史證實了,我們面對那些基本上來自歐洲且野心勃勃的意識形態(及其實踐)時,對抗屢遭挫敗,我們也無力讓西方對巴勒斯坦謀求的正義事業產生太多興趣。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也已經開始建構屬於自己的政治身分認同與企圖,展現出非凡的韌性以及驚人的民族復甦力,我們也獲得了第三世界所有人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儘管巴勒斯坦人如碎片般分散各地、儘管我們沒有自己的領土,我們多半因為巴勒斯坦理念(idea)而團結成一個民族;出於自己被剝奪、被排除的經驗,我們表達了巴勒斯坦理念,這個理念一以貫之,而我們以積極的熱情回應。本書嘗試要做的,正是要盡最大的可能詳述巴勒斯坦的失敗,與隨後復歸的生動細節。
我想,對許多讀者來說,「巴勒斯坦問題」隨即會讓他們想起「恐怖主義」的概念,而這樣的不公平聯想,是本書沒有多談恐怖主義的部分原因。若我將此議題納入討論,那我就得以防禦的姿態提出辯護──要不主張我們的「恐怖主義」具有正當性,要不堅稱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巴勒斯坦恐怖主義」。但事實遠比這複雜,有一些值得我在此先行陳述。單就數值而言,尤以人命與財產損失的殘酷數字來看,猶太復國主義者施加於巴勒斯坦人身上的行為,遠大於巴勒斯坦人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報復性行動。過去二十年間,以色列幾乎不間斷地攻擊位在黎巴嫩與約旦的巴勒斯坦平民難民營,而這只是雙方完全不對稱的攻擊紀錄中的一個指標。與此同時,我認為更嚴重的是,西方(尤其是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者)新聞媒體與知識論述的偽善:他們幾乎從未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恐怖行動別置一喙。當他們報導「阿拉伯」針對「以色列平民」、「城鎮村落」或「學童」的恐怖襲擊時,言詞是憤慨的,但在報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陣地」的攻擊時,卻換上了中立的語調,沒有人會知道「巴勒斯坦陣地」指的是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有什麼比上述修辭還要不公允?(我此處引用的是最近發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的事件報導。)自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佔領西岸與加薩以來,其非法佔領每日都引發民怨沸騰,但西方媒體(與以色列的傳媒)無動於衷──直到耶路撒冷的一個市集發生了爆炸案。事件後,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古爾(Mordechai Gur)接受訪問,但我必須帶著幾近徹底的厭惡指出,沒有一家美國新聞報紙提到這個訪問:
問:〔以色列一九七八年三月入侵黎巴嫩期間〕你們針對聚集群眾進行無差別轟炸一事,是真的嗎?
答:我不是那種會選擇性記憶的人。你以為我會假裝不知道這些年來我們做了什麼嗎?蘇伊士運河軍事衝突時,我們做了什麼?炸了一百五十萬的難民!這是真的,你住哪?⋯⋯我們炸了埃及的伊斯梅利亞(Ismailia)、蘇伊士、塞得港、福阿得港,一百五十萬的難民⋯⋯。黎巴嫩南部的人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神聖了?那些人完全知道恐怖分子在做什麼。阿維維姆(Avivim)發生屠殺後,我未經授權就先炸了黎巴嫩南部的四個村。
問:那些轟炸沒有區分平民和非平民?
答:區分什麼?你知道伊爾比德(Irbid)的居民做了些事才會被我們炸吧。〔伊爾比德是一座位在約旦北部的大城,主要居民是巴勒斯坦人。〕
問:但軍方的聲明都說是還擊,也說是針對恐怖分子目標的反擊。
答:請你認真點。你不知道約旦整個谷地的居民都因為消耗戰被清空了嗎?
問:所以你主張那些居民應該被懲罰?
答:當然,而且我對這件事完全沒有疑慮。我批准亞努什〔Avigdor “Yanouch” Ben-Gal,於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行動中擔任北部指揮官〕在入侵時動用飛機、大砲與坦克時,我完全知道我在做什麼。我們的獨立戰爭結束後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年,但我們還在跟那些住在城鎮村落裡的〔阿拉伯〕平民打仗,每次我們都會被問同樣的問題:我們該或不該攻擊平民?(《哈米什馬爾報》〔Al-Hamishmar〕,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
由此可見,關於「恐怖主義」的一個問題,在於人們對它的認知失調,以及其犯罪的失衡。舉例來說,當巴勒斯坦人試圖用以色列人質來換取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的巴勒斯坦人時,每一次,以色列軍隊總是率先開砲,蓄意導致一場血腥殺戮。但事實上,這些數據與解釋也不夠充分,畢竟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巴勒斯坦人與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巴勒斯坦人與其他人類(或看來如此)之間、猶太人與西方人之間歷來的敵對紀錄,都令人心寒沮喪。身為巴勒斯坦人,我對於這一切恐怖事態的震動迴響及其道德難題的細部被剝去,以一種簡單且天經地義的方式,被壓縮在「巴勒斯坦恐怖行動」的標題下,深感怨恨且悲痛。然而,我也必須說,身為一個從各方面接觸到此議題的人,我(僅此一名的巴勒斯坦人)也對劫機、自殺任務、暗殺行動、轟炸學校與飯店感到恐懼。令我驚恐的不只是受害者所承受的恐怖行動,更是內在於那些被迫行動的巴勒斯坦男女們的恐懼。我不會佯稱自己是超然的觀察家,因此,我認為,與其正面討論恐怖行動,不如試著向我的讀者傳達一個更大的巴勒斯坦故事,上述的所有一切正是從這個故事而來。假若這個故事終究沒有──而它本就不能──緩解消耗與不幸的災難,至少這個故事能向讀者呈現長久以來遺漏的事實,也就是內含於巴勒斯坦問題裡,每一個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集體民族創傷。
非歐洲小型民族的特徵之一是,它的文件紀錄並不豐富,其歷史、自傳、紀事等,也不充沛。巴勒斯坦民族即是這樣的狀況,而這導致了巴勒斯坦歷史欠缺一個主要且權威的文本。但我現在的書寫,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並不是為了補足這個缺失。我試圖指出的是,巴勒斯坦經驗即是重要且具體的歷史,這些歷史往往被兩個群體所忽略:猶太復國主義人士希望巴勒斯坦經驗從不存在,歐洲人與美國人則因為不知如何處理「巴勒斯坦」而忽視之。我試圖指出的是,當基督教歐洲一心要終結對猶太人的迫害時,那些於一九四八年遭到驅逐、在巴勒斯坦住了幾百年的穆斯林與基督徒,正是那一個運動的不幸受害者。然而,正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如此成功,順利將猶太人帶到巴勒斯坦,並為他們打造了一個國家,世界也就未曾關注到,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大業對原本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來說,意味著失落、流離與災禍。為了同時看到眾所周知的成功與鮮為人知的災難,我們需要一個帶有反諷意味的雙重視角,正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描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透過殖民而征服一塊領土,此前毫無解法的猶太問題確實是解決了,但這個解方沒有解決少數族群與無國籍者的問題。恰恰相反:就像我們這個世紀的幾乎一切事件,針對猶太問題的解方只是製造了一個新的難民類別,也就是阿拉伯人,從而,無國籍者又增加了七十萬至八十萬人。
就如我在本書指出的,當人們不斷頌揚以色列及其歷史時,他們直到最近才承認,存在著巴勒斯坦人的現實,包括其日常生活、經歷過的小歷史,以及渴望達成目標的感受。而突然間,巴勒斯坦問題需要解答:世界輿論要求合理看待長年遭到忽略的近東僵局關鍵。但遺憾的是,就目前來看,我們難以開啟適當的辯論,更別提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解決方式。首先,可供辯論的話語是貧瘠的,一如前述,巴勒斯坦人總是被視為難民、極端分子或恐怖分子,而一大票的中東「專家」,又會用那些似是而非的社會科學術語與意識形態濫調,習於壟斷討論。我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們面對巴勒斯坦人時,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態度,那樣的態度衍生自西方長年以來對伊斯蘭、阿拉伯人與東方的偏見,而猶太復國主義又從中汲取對巴勒斯坦人的看法。由於這樣的文化態度,巴勒斯坦人被非人化,我們的民族被貶低成一個讓人難以容忍的麻煩。
這樣的陳述或許是過於籠統了:「關於中東與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學研究多半延續上述傳統」,但我認為,確實有這個傾向。這些研究大多衍生自──且在多個重要層面毫不遲疑接受了──正當化猶太復國主義而不利於巴勒斯坦權利的框架,因此無助於理解中東的真實情況。自二戰以來,幾乎所有在美國國內產出的關於當代中東的嚴肅研究,都沒辦法讓人們應對該地區的狀況;最近在伊朗發生的事,以及黎巴嫩內戰、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阿拉伯國家於一九七三年戰爭的表現,都清楚反映這點。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爭辯、反對(特別是冷戰以降)社會科學研究佯裝「科學客觀」的意識形態傾向,然而,我確實有意識地避免其「價值中立」的陷阱。這個陷阱導致政治現實的論述,往往聚焦在強權競爭;聲稱西方及其在第三世界的現代化使命,都是可取的;忽視民眾運動,卻讚揚推崇那些無建樹且壓迫性的附庸政權;將那些無法輕易套進特定目的論或(以「理性」、「實證」、「實用」為目標的)特定方法論的事情,都稱作「非歷史」並屏除在外。對於這些研究明顯的缺陷,人們往往歸咎於「我們」在伊朗的失敗,以及「我們」無法預測「伊斯蘭再起」,卻沒有檢討這些研究的前提,反而一再強化之。於是,在決策過程中扮演要角的政治學家,反覆提出目光短淺的建議,而外行人如我也看得出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又再一次被賭在明顯會失敗的動機與倒退的歷史視野上。我寫下這些字的同時,大衛營的嚴重缺陷似乎也證實了我的論點。
然而,我認為在一九七六年以前,巴勒斯坦人也默許了外界對他們的貶抑,因而接受猶太復國主義者與專家們認為巴勒斯坦無關緊要的看法。但巴勒斯坦人找到自己了,我們發現了世界,世界也發現了我們。本書試圖描述我們的漫漫長夜與徐徐甦醒,與此同時,本書也不會忽略構成我們生活的土地、宗教、全球政治等背景,而在我們的經驗裡,猶太復國主義正是一個要素。這個說法既不是理論層次的問題,也無意指名謾罵。猶太復國主義對猶太人來說有多重要,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也就同等重要──儘管其意義截然不同。巴勒斯坦人必須告訴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對我們意味著某些具體事情,而我們得共同承擔那些仍然鮮活的痕跡。
我稱本書是一篇「政治論說文」。我試著把我們的處境擺在西方讀者面前,將之呈現為需要思考、實踐、參與的問題,而不是嚴謹且完善的陳述;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需要在政治層次上處理的議題。長久以來,巴勒斯坦置身於歷史之外,當然也不在人們的討論範圍內,而本書則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試圖讓巴勒斯坦問題成為討論與政治理解的主題。我希望讀者很快就會發現,本書所提出的並非「專家」看法,也不是個人證詞,而是一系列切身經歷的現實──它們根植於對人權的理解,以及社會經驗中的種種矛盾,以盡可能貼近日常現實的語言表達出來。
本書的主張有幾個基本前提。首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都在,而我們必須藉由理解他們的經歷,來理解猶太復國主義與阿拉伯世界間的僵局。其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不斷透過語言及行動試圖抹除巴勒斯坦,原因是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國家,在許多層面(但並非全部),就是奠基在對巴勒斯坦與巴勒斯坦人的否定之上。直到今天,一項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僅僅在以色列──或對著一個深信猶太復國主義之人──提起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就等於說出了不可言說之事;我們赤裸裸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譴責以色列對我們所做之事。最後,我認為在道德意義上,人類作為個體與特定群體本就應該享有基本權利,其中包括民族自決權。這意味著:沒有人應該被迫「移轉」(transfer)出他們的家園或土地,沒有人理當因為不信X教或Y教就受到歧視;無論何種理由,沒有人活該被剝奪他們的土地、民族身分與文化。
本書所要問的問題是:「以色列是什麼?美國是什麼?阿拉伯人要如何應對巴勒斯坦人?」從巴勒斯坦經驗的現實來說,我完全不認同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al-Sadat)及其支持者所說的「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方法,百分之九十九都在美國手上」,我也不認為解決之道多半在以色列或阿拉伯國家的手上。我的重點是──而這也是本書之所以能寫成的原因──巴勒斯坦人有「自己的手」,他們也扮演著主動的角色,促成了巴勒斯坦的志向、政治鬥爭與成就,乃至挫折和失敗。但我也不否認,猶太人與美國人的想法與行為,確實在巴勒斯坦問題中佔有一席之地,而這正是我的書要處理的。
巴勒斯坦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的經驗有其存在基礎,為了強調這點,我得說些也許是顯而易見的事。我們曾經生活在名為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難道為了要救助從納粹主義中存活下來的歐洲猶太人,我們的被剝奪與被抹除(近一百萬人被迫離開巴勒斯坦、我們的社會不復存在),就是合理的嗎?人們基於什麼樣的道德或政治標準,期待巴勒斯坦人放棄民族生存、土地與人權?當一個民族被告知它在法理上不存在,甚至被出兵討伐;當這個民族的名字被組織性地攻擊,歷史被改寫以「證明」此民族不存在──而世界沒有論爭,這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即使所有圍繞著巴勒斯坦人的爭議都是難解的,涉及強權政治、地區爭端、階級衝突、意識形態張力等,但巴勒斯坦運動的生命力,即是對上述簡單卻關鍵問題的察覺與體認。
本書的大部分內容完稿於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初,成書於近東現代史中極為重要的年間,但參考座標絕不僅限於上述時期。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是提供西方讀者一個能廣泛代表巴勒斯坦的立場。許多人在此刻談論著巴勒斯坦與巴勒斯坦問題,但「巴勒斯坦立場」仍不太為人所知,也從未被充分理解。本書在闡述這個立場時,主要依據的是那些我認為足以被稱為巴勒斯坦的經驗。就任何層面而言,自一八八○年代早期,當第一批猶太復國主義者抵達巴勒斯坦海岸時,「巴勒斯坦經驗」即成了一個具備自我意識的經驗;從此,巴勒斯坦的歷史展開了不同於阿拉伯世界的特殊走向。在整個二十世紀當中,儘管巴勒斯坦人與阿拉伯人的行動確實有許多關聯,但巴勒斯坦歷史的決定性因素,也就是猶太復國主義所致的創傷性民族遭遇,是近東地區獨一無二的。
我寫作本書時,我的目標與預期成果(先不論兩者可能的瑕疵),皆是以巴勒斯坦獨有的特性為指南。身為一名巴勒斯坦人,我始終努力意識到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弱點與缺失。依某些標準來看,巴勒斯坦民族也許並不特殊;我們的民族史證實了,我們面對那些基本上來自歐洲且野心勃勃的意識形態(及其實踐)時,對抗屢遭挫敗,我們也無力讓西方對巴勒斯坦謀求的正義事業產生太多興趣。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也已經開始建構屬於自己的政治身分認同與企圖,展現出非凡的韌性以及驚人的民族復甦力,我們也獲得了第三世界所有人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儘管巴勒斯坦人如碎片般分散各地、儘管我們沒有自己的領土,我們多半因為巴勒斯坦理念(idea)而團結成一個民族;出於自己被剝奪、被排除的經驗,我們表達了巴勒斯坦理念,這個理念一以貫之,而我們以積極的熱情回應。本書嘗試要做的,正是要盡最大的可能詳述巴勒斯坦的失敗,與隨後復歸的生動細節。
我想,對許多讀者來說,「巴勒斯坦問題」隨即會讓他們想起「恐怖主義」的概念,而這樣的不公平聯想,是本書沒有多談恐怖主義的部分原因。若我將此議題納入討論,那我就得以防禦的姿態提出辯護──要不主張我們的「恐怖主義」具有正當性,要不堅稱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巴勒斯坦恐怖主義」。但事實遠比這複雜,有一些值得我在此先行陳述。單就數值而言,尤以人命與財產損失的殘酷數字來看,猶太復國主義者施加於巴勒斯坦人身上的行為,遠大於巴勒斯坦人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報復性行動。過去二十年間,以色列幾乎不間斷地攻擊位在黎巴嫩與約旦的巴勒斯坦平民難民營,而這只是雙方完全不對稱的攻擊紀錄中的一個指標。與此同時,我認為更嚴重的是,西方(尤其是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者)新聞媒體與知識論述的偽善:他們幾乎從未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恐怖行動別置一喙。當他們報導「阿拉伯」針對「以色列平民」、「城鎮村落」或「學童」的恐怖襲擊時,言詞是憤慨的,但在報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陣地」的攻擊時,卻換上了中立的語調,沒有人會知道「巴勒斯坦陣地」指的是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有什麼比上述修辭還要不公允?(我此處引用的是最近發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的事件報導。)自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佔領西岸與加薩以來,其非法佔領每日都引發民怨沸騰,但西方媒體(與以色列的傳媒)無動於衷──直到耶路撒冷的一個市集發生了爆炸案。事件後,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古爾(Mordechai Gur)接受訪問,但我必須帶著幾近徹底的厭惡指出,沒有一家美國新聞報紙提到這個訪問:
問:〔以色列一九七八年三月入侵黎巴嫩期間〕你們針對聚集群眾進行無差別轟炸一事,是真的嗎?
答:我不是那種會選擇性記憶的人。你以為我會假裝不知道這些年來我們做了什麼嗎?蘇伊士運河軍事衝突時,我們做了什麼?炸了一百五十萬的難民!這是真的,你住哪?⋯⋯我們炸了埃及的伊斯梅利亞(Ismailia)、蘇伊士、塞得港、福阿得港,一百五十萬的難民⋯⋯。黎巴嫩南部的人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神聖了?那些人完全知道恐怖分子在做什麼。阿維維姆(Avivim)發生屠殺後,我未經授權就先炸了黎巴嫩南部的四個村。
問:那些轟炸沒有區分平民和非平民?
答:區分什麼?你知道伊爾比德(Irbid)的居民做了些事才會被我們炸吧。〔伊爾比德是一座位在約旦北部的大城,主要居民是巴勒斯坦人。〕
問:但軍方的聲明都說是還擊,也說是針對恐怖分子目標的反擊。
答:請你認真點。你不知道約旦整個谷地的居民都因為消耗戰被清空了嗎?
問:所以你主張那些居民應該被懲罰?
答:當然,而且我對這件事完全沒有疑慮。我批准亞努什〔Avigdor “Yanouch” Ben-Gal,於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行動中擔任北部指揮官〕在入侵時動用飛機、大砲與坦克時,我完全知道我在做什麼。我們的獨立戰爭結束後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年,但我們還在跟那些住在城鎮村落裡的〔阿拉伯〕平民打仗,每次我們都會被問同樣的問題:我們該或不該攻擊平民?(《哈米什馬爾報》〔Al-Hamishmar〕,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
由此可見,關於「恐怖主義」的一個問題,在於人們對它的認知失調,以及其犯罪的失衡。舉例來說,當巴勒斯坦人試圖用以色列人質來換取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的巴勒斯坦人時,每一次,以色列軍隊總是率先開砲,蓄意導致一場血腥殺戮。但事實上,這些數據與解釋也不夠充分,畢竟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巴勒斯坦人與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巴勒斯坦人與其他人類(或看來如此)之間、猶太人與西方人之間歷來的敵對紀錄,都令人心寒沮喪。身為巴勒斯坦人,我對於這一切恐怖事態的震動迴響及其道德難題的細部被剝去,以一種簡單且天經地義的方式,被壓縮在「巴勒斯坦恐怖行動」的標題下,深感怨恨且悲痛。然而,我也必須說,身為一個從各方面接觸到此議題的人,我(僅此一名的巴勒斯坦人)也對劫機、自殺任務、暗殺行動、轟炸學校與飯店感到恐懼。令我驚恐的不只是受害者所承受的恐怖行動,更是內在於那些被迫行動的巴勒斯坦男女們的恐懼。我不會佯稱自己是超然的觀察家,因此,我認為,與其正面討論恐怖行動,不如試著向我的讀者傳達一個更大的巴勒斯坦故事,上述的所有一切正是從這個故事而來。假若這個故事終究沒有──而它本就不能──緩解消耗與不幸的災難,至少這個故事能向讀者呈現長久以來遺漏的事實,也就是內含於巴勒斯坦問題裡,每一個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集體民族創傷。
非歐洲小型民族的特徵之一是,它的文件紀錄並不豐富,其歷史、自傳、紀事等,也不充沛。巴勒斯坦民族即是這樣的狀況,而這導致了巴勒斯坦歷史欠缺一個主要且權威的文本。但我現在的書寫,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並不是為了補足這個缺失。我試圖指出的是,巴勒斯坦經驗即是重要且具體的歷史,這些歷史往往被兩個群體所忽略:猶太復國主義人士希望巴勒斯坦經驗從不存在,歐洲人與美國人則因為不知如何處理「巴勒斯坦」而忽視之。我試圖指出的是,當基督教歐洲一心要終結對猶太人的迫害時,那些於一九四八年遭到驅逐、在巴勒斯坦住了幾百年的穆斯林與基督徒,正是那一個運動的不幸受害者。然而,正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如此成功,順利將猶太人帶到巴勒斯坦,並為他們打造了一個國家,世界也就未曾關注到,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大業對原本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來說,意味著失落、流離與災禍。為了同時看到眾所周知的成功與鮮為人知的災難,我們需要一個帶有反諷意味的雙重視角,正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描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透過殖民而征服一塊領土,此前毫無解法的猶太問題確實是解決了,但這個解方沒有解決少數族群與無國籍者的問題。恰恰相反:就像我們這個世紀的幾乎一切事件,針對猶太問題的解方只是製造了一個新的難民類別,也就是阿拉伯人,從而,無國籍者又增加了七十萬至八十萬人。
就如我在本書指出的,當人們不斷頌揚以色列及其歷史時,他們直到最近才承認,存在著巴勒斯坦人的現實,包括其日常生活、經歷過的小歷史,以及渴望達成目標的感受。而突然間,巴勒斯坦問題需要解答:世界輿論要求合理看待長年遭到忽略的近東僵局關鍵。但遺憾的是,就目前來看,我們難以開啟適當的辯論,更別提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解決方式。首先,可供辯論的話語是貧瘠的,一如前述,巴勒斯坦人總是被視為難民、極端分子或恐怖分子,而一大票的中東「專家」,又會用那些似是而非的社會科學術語與意識形態濫調,習於壟斷討論。我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們面對巴勒斯坦人時,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態度,那樣的態度衍生自西方長年以來對伊斯蘭、阿拉伯人與東方的偏見,而猶太復國主義又從中汲取對巴勒斯坦人的看法。由於這樣的文化態度,巴勒斯坦人被非人化,我們的民族被貶低成一個讓人難以容忍的麻煩。
這樣的陳述或許是過於籠統了:「關於中東與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學研究多半延續上述傳統」,但我認為,確實有這個傾向。這些研究大多衍生自──且在多個重要層面毫不遲疑接受了──正當化猶太復國主義而不利於巴勒斯坦權利的框架,因此無助於理解中東的真實情況。自二戰以來,幾乎所有在美國國內產出的關於當代中東的嚴肅研究,都沒辦法讓人們應對該地區的狀況;最近在伊朗發生的事,以及黎巴嫩內戰、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阿拉伯國家於一九七三年戰爭的表現,都清楚反映這點。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爭辯、反對(特別是冷戰以降)社會科學研究佯裝「科學客觀」的意識形態傾向,然而,我確實有意識地避免其「價值中立」的陷阱。這個陷阱導致政治現實的論述,往往聚焦在強權競爭;聲稱西方及其在第三世界的現代化使命,都是可取的;忽視民眾運動,卻讚揚推崇那些無建樹且壓迫性的附庸政權;將那些無法輕易套進特定目的論或(以「理性」、「實證」、「實用」為目標的)特定方法論的事情,都稱作「非歷史」並屏除在外。對於這些研究明顯的缺陷,人們往往歸咎於「我們」在伊朗的失敗,以及「我們」無法預測「伊斯蘭再起」,卻沒有檢討這些研究的前提,反而一再強化之。於是,在決策過程中扮演要角的政治學家,反覆提出目光短淺的建議,而外行人如我也看得出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又再一次被賭在明顯會失敗的動機與倒退的歷史視野上。我寫下這些字的同時,大衛營的嚴重缺陷似乎也證實了我的論點。
然而,我認為在一九七六年以前,巴勒斯坦人也默許了外界對他們的貶抑,因而接受猶太復國主義者與專家們認為巴勒斯坦無關緊要的看法。但巴勒斯坦人找到自己了,我們發現了世界,世界也發現了我們。本書試圖描述我們的漫漫長夜與徐徐甦醒,與此同時,本書也不會忽略構成我們生活的土地、宗教、全球政治等背景,而在我們的經驗裡,猶太復國主義正是一個要素。這個說法既不是理論層次的問題,也無意指名謾罵。猶太復國主義對猶太人來說有多重要,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也就同等重要──儘管其意義截然不同。巴勒斯坦人必須告訴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對我們意味著某些具體事情,而我們得共同承擔那些仍然鮮活的痕跡。
我稱本書是一篇「政治論說文」。我試著把我們的處境擺在西方讀者面前,將之呈現為需要思考、實踐、參與的問題,而不是嚴謹且完善的陳述;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需要在政治層次上處理的議題。長久以來,巴勒斯坦置身於歷史之外,當然也不在人們的討論範圍內,而本書則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試圖讓巴勒斯坦問題成為討論與政治理解的主題。我希望讀者很快就會發現,本書所提出的並非「專家」看法,也不是個人證詞,而是一系列切身經歷的現實──它們根植於對人權的理解,以及社會經驗中的種種矛盾,以盡可能貼近日常現實的語言表達出來。
本書的主張有幾個基本前提。首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都在,而我們必須藉由理解他們的經歷,來理解猶太復國主義與阿拉伯世界間的僵局。其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不斷透過語言及行動試圖抹除巴勒斯坦,原因是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國家,在許多層面(但並非全部),就是奠基在對巴勒斯坦與巴勒斯坦人的否定之上。直到今天,一項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僅僅在以色列──或對著一個深信猶太復國主義之人──提起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就等於說出了不可言說之事;我們赤裸裸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譴責以色列對我們所做之事。最後,我認為在道德意義上,人類作為個體與特定群體本就應該享有基本權利,其中包括民族自決權。這意味著:沒有人應該被迫「移轉」(transfer)出他們的家園或土地,沒有人理當因為不信X教或Y教就受到歧視;無論何種理由,沒有人活該被剝奪他們的土地、民族身分與文化。
本書所要問的問題是:「以色列是什麼?美國是什麼?阿拉伯人要如何應對巴勒斯坦人?」從巴勒斯坦經驗的現實來說,我完全不認同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al-Sadat)及其支持者所說的「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方法,百分之九十九都在美國手上」,我也不認為解決之道多半在以色列或阿拉伯國家的手上。我的重點是──而這也是本書之所以能寫成的原因──巴勒斯坦人有「自己的手」,他們也扮演著主動的角色,促成了巴勒斯坦的志向、政治鬥爭與成就,乃至挫折和失敗。但我也不否認,猶太人與美國人的想法與行為,確實在巴勒斯坦問題中佔有一席之地,而這正是我的書要處理的。
巴勒斯坦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的經驗有其存在基礎,為了強調這點,我得說些也許是顯而易見的事。我們曾經生活在名為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難道為了要救助從納粹主義中存活下來的歐洲猶太人,我們的被剝奪與被抹除(近一百萬人被迫離開巴勒斯坦、我們的社會不復存在),就是合理的嗎?人們基於什麼樣的道德或政治標準,期待巴勒斯坦人放棄民族生存、土地與人權?當一個民族被告知它在法理上不存在,甚至被出兵討伐;當這個民族的名字被組織性地攻擊,歷史被改寫以「證明」此民族不存在──而世界沒有論爭,這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即使所有圍繞著巴勒斯坦人的爭議都是難解的,涉及強權政治、地區爭端、階級衝突、意識形態張力等,但巴勒斯坦運動的生命力,即是對上述簡單卻關鍵問題的察覺與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