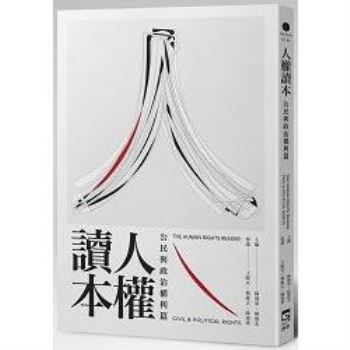轉型正義與人權保障:導讀/陳瑤華
六○年代一群德國高中生興高彩烈到法國鄉間騎腳踏車旅行,途中在一間農舍前的空地休息。大家七嘴八舌地暢談一路上的見聞。突然農舍的女主人開門走出來,請求她們離開。她的家人全都在奧史維玆集中營的毒氣室中喪生,既使過了十多年,仍然無法忍受德語交談的聲音。
這一群年輕人並沒有參與納粹的恐怖統治,為甚麼必須承受過去極權統治所帶來的後果呢?被稱為「納粹」是德國人的原罪嗎?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認為罪責有很多種,既使沒有直接參與,仍然有消極、間接使之可能的責任。再者,就算過去曾經參與反抗希特勒的陣營,也必須面對受害者家破人亡、無法止息的傷痛;以及這個無可挽回的傷害所帶來的仇恨。一九七〇年,當德國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在波蘭華沙的尤太禁區下跪時,很多人都為之動容。他曾經是對抗希特勒的英雄,但他沒有逃避他作為當時西德波昂(Bonn)政府領導人對受害者的責任,必須還給受害家屬一個公開、正式的道歉,作為不會重蹈覆轍的承諾。
台灣經歷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長達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又經歷三十八年多的戒嚴及動員戡亂的法制,至少有超過五分之四世紀的時間,大多數的台灣住民生活在軍人、警察的濫權、不同意見者動輒得咎的世界中。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既使距離解嚴已經超過二十五年後的現在,既使有所謂「補償」的各種措施和條例,受難者仍然必須忍受過去加諸自身的暴行,自己找尋正義和真相。對比於德國政府戰戰兢兢地唯恐極權的迫害行動有可能再起,任何美化極權暴行的言論和行動都必須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釐清真相以正視聽;台灣的政府和民間仍然遮遮掩掩,不願面對被神格化的統治者,其實是掩護劊子手及情報頭子的作為,給殘害人權各種重新來過的機會。
誰該給後威權社會的台灣住民一個不會重蹈覆轍的承諾?
誠如雅斯培所言,罪責的反思不僅僅只是停留在對加害者的追訴而已,還包括公佈真相、還原歷史、教育下一代,建立責任政治及法治,以避免重蹈覆轍。
恐怖統治可以橫行無阻,一定有許多使之可能的共犯結構,後威權的社會必須好好反省及面對。無論行政、立法與司法,都是這個共犯結構的一環,需要徹底的檢討。當希特勒開始區隔尤太與非尤太人的生活領域時,部分尤太社群甚至非常認同,使這樣的區隔更有組織地進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尤太人如果不是一個那麼有秩序、有組織的群體,說不定集體的屠殺不會那麼容易進行。
大部分處於後威權社會的人們會羞於承認自己過去沒有反抗,當然更不願承認自己的沈默是使恐怖統治可以暢行無阻的原因。社會對過去、自己對自己、自己對家人、自己對他人保持沈默是最「安全」的方式,因為無須替自己或他人加害或受害提出合理的解釋和辯護。理論上,清算加害陣營黨派首腦的罪責僅需要成立獨立的調查機構,展開證據的蒐集和舉證,不算太難(既使這樣,台灣社會還是看不到歷任國家的領導人肯這樣做)。不過對社會整體而言,反思自己面對他人無辜被拘捕、拷打、失蹤、槍斃卻噤聲、保持沈默,才是杜絕威權體制復辟的不二法門。這些對過去迫害及殘暴經驗的反思,不應只是個人、隱藏式的私下進行,而是應該透過公開、集體討論的方式來面對。因為恐怖統治的真正恐怖之處,不是因為統治手段的殘忍而已,而是人們的順從。明明知道很多的制度、法律是錯的,竟然還繼續屈從!在這樣的屈從之中,正義沒有聲音,沒有一個人會獲得真正的安全。
由以上可知,認識過去統治的不正義不僅僅只在乎真相大白、還給受害者及社會一個正義而已。更積極而言,在檢討不正義如何發生的當下,也讓我們看到人是可以作出不同及多元選擇的,不一定只有英雄式的殉道和委曲求全而已。在這兩個極端之中,人們還是有可能作出各式各樣的選擇,而且仍然可以集體地不順從和行動。在討論為甚麼人需要有過去不正義經驗的記憶時,最哲學性的回答莫過於自我的「解放」與「自由」。
因為只有瞭解到自己其實可以有其他不同的選擇,並且為此感到懊悔時,人才有可能從自己造成的牢籠中解放出來,獲得真正的自由,建立責任政治。
對目前台灣的年輕人而言,日治時期、戒嚴和白色恐怖好像是上一代距離自己十分遙遠的事。就像之前提到的德國高中生,可以無憂無慮地騎著腳踏車悠遊在法國美麗如畫的鄉間。為甚麼仍然需要面對過去恐怖統治的記憶呢?選擇遺忘(所謂「忘記背後、努力向前」)不是更能感受生活的舒適和愜意嗎?
開頭這個故事的主角之一,後來成為萬湖會議紀念館的館長,這一趟法國鄉間的旅行徹底改變了他的生命。歷史是不能逆轉的,但未來可以。記憶、記錄過去的不正義是為了理解現在、扭轉未來。而且每一個人都有無法抵賴,必須承擔未來可能的不正義之責任。說自己無可選擇是推諉責任,因為讓曾經發生的事一再重演,沒有作出不同的選擇就是諉過、不負責任。
受到黨派政治化轉型正義的誤導,一般人會認為轉型正義只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殊不知,轉型正義最重要的關鍵是反思過去不正義的集體記憶,認識到自己的自由,並且願意保障這個得來不易的自由,承擔維護人權的責任。記憶不是為了延續隔離與仇恨,記憶是為了理解不同的可能性,以及自己在這些可能性當中可以作出的選擇。歷史記憶的找尋、維護和重建,為的是從錯誤中學到教訓,讓過去受到強權壓迫者可以慢慢獲得解放,社會也能逐漸脫離被監看的恐懼而擁有真正的自由。
這個單元中有兩篇文章:第一篇是林山田〈五十年來的台灣法制〉;第二篇劉熙明〈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
第一篇雖然是法制史的專門著作,但藉由追溯台灣戒嚴、動員及戡亂體制的由來,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台灣五○到九○年代,涉及國家體制及刑罰的「法令」和「法律」,其實都只有臨時條款或行政命令的特性,卻凌駕憲法及一般法律之上,成為鞏固政權、侵害人權的工具。
既使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這些「法令」僅在名稱上去除「動員」、「戡亂」等字眼,依然無視於憲法保障人權的基本規範,繼續成為侵害人權的工具。
大多數探究白色恐怖的文獻會陷在「惡法是否亦法?」的問題,受制於「惡法」的抽象概念,無法看清:既然是「惡法」,也就是不應該存在的規定,為甚麼還會有是否是「法」的問題呢?最該思考的問題不是惡法亦法,而是如何解消「惡法」這個混淆的概念。林山田直接指出這些特殊的法令:(一)產生的脈絡,也就是在中國大陸對日本及共軍作戰的狀態,直接引用到經過五十年日本統治、後來並沒有交戰狀態的台灣社會;(二)透過不法手段讓國民大會及立法院為這些「特別」的法令背書;以及(三)違背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說明這些法令並非法律,本身即違法而不應該存在。
閱讀〈五十年來的台灣法制〉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理解到檢視現有制度和法律的重要性,尤其是當這些制度和法律有侵害人權之虞,需要從最根本的觀念開始,廢除或宣布為非法,以達到維護人權之目的。同時,可以暴露威權體制暴力統治、罔顧正當程序的真實面貌,人們在這樣的制度中無辜受難。
劉熙明的〈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以當時公布的〈大溪檔案〉為依據,說明白色恐怖時期,情治單位的組織和架構直接聽命於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成為行政、立法、司法及監察機關的「上級」單位,可以在完全不受監督、管控的條件下,獨攬人民的生殺大權。雖然有人以「台灣處於動員戡亂的非常時期」作為理由,為這樣的措施辯護;但這篇文章清楚地指出:很多案件根本和所謂「防範未然、弭禍無形」、「保衛台灣」完全無關,大部分是因故得罪或冒犯兩蔣的威權而無故被連誅入罪,成為「不當審判」的最大受害者。兩蔣不但任由情治單位製造類似的假案及錯案,而且從始至終都主導這些案件的發生和結案。
劉熙明提出很多文獻證據,顯示蔣經國試圖以「革命大業」、「非常時期」來合理化情治單位的非常手段,甚至以各種動員、戡亂的法律,來賦予情治機關超越一般警察維護治安及法院拘留、審訊的「合法」權力。但從文章具體陳述的案例中,我們看不到這些案件與所謂「革命大業」、「非常時期」有任何可能的關連,反而看到為了鞏固專政而有的公報私仇、玩弄法律以遂行其統治意志的恐怖現象。
林山田及劉熙明以「非法」及「不當審判」討論過去的人民權利侵害,主要以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為核心,並未以「違反普世人權價值」,反駁特定「法令」、「組織」及「制度」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人民的基本權利」概念上仍侷限於本國國民及公民,而非以普遍的「人」之概念為立基點,擴大到過去、現在及未來居住在這塊土地的所有人。
任何法律的制訂都不能侵害人的基本自由及尊嚴,一旦違反人權,就僅僅只是統治者維護其威權的工具而已。這樣的法律不僅僅應該被廢除而已,更應該正式宣布其為「非法」,而過去因為這樣法律而被入罪者不僅僅只是「不當審判」;而更是「不法審判」,政府應該釐清事情發生的真相,賠償這些受到不當審判的受害者。
換句話說,概念上「酷刑」、「奴隸」及「奴役」都因為與人作為人的基本自由和尊嚴相矛盾而不應該存在;既使相關的約定是自願的,或是基於大多數的共識,符合所謂的「法律程序」,也不具備成為法律的要件。法令的落實若是妨礙個人享有完整的人權,國際法就會要求國內的法律必須逐漸修改以維護人權。這樣的主張背後並不需要預設有高於實證法律之上的「自然法」、「道德權利」或「自然權利」,而是基於任何法律都不能以取消及侵害人權為代價,而誤使法律成為維護特定族群掌握其統治權力的工具。
六○年代一群德國高中生興高彩烈到法國鄉間騎腳踏車旅行,途中在一間農舍前的空地休息。大家七嘴八舌地暢談一路上的見聞。突然農舍的女主人開門走出來,請求她們離開。她的家人全都在奧史維玆集中營的毒氣室中喪生,既使過了十多年,仍然無法忍受德語交談的聲音。
這一群年輕人並沒有參與納粹的恐怖統治,為甚麼必須承受過去極權統治所帶來的後果呢?被稱為「納粹」是德國人的原罪嗎?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認為罪責有很多種,既使沒有直接參與,仍然有消極、間接使之可能的責任。再者,就算過去曾經參與反抗希特勒的陣營,也必須面對受害者家破人亡、無法止息的傷痛;以及這個無可挽回的傷害所帶來的仇恨。一九七〇年,當德國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在波蘭華沙的尤太禁區下跪時,很多人都為之動容。他曾經是對抗希特勒的英雄,但他沒有逃避他作為當時西德波昂(Bonn)政府領導人對受害者的責任,必須還給受害家屬一個公開、正式的道歉,作為不會重蹈覆轍的承諾。
台灣經歷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長達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又經歷三十八年多的戒嚴及動員戡亂的法制,至少有超過五分之四世紀的時間,大多數的台灣住民生活在軍人、警察的濫權、不同意見者動輒得咎的世界中。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既使距離解嚴已經超過二十五年後的現在,既使有所謂「補償」的各種措施和條例,受難者仍然必須忍受過去加諸自身的暴行,自己找尋正義和真相。對比於德國政府戰戰兢兢地唯恐極權的迫害行動有可能再起,任何美化極權暴行的言論和行動都必須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釐清真相以正視聽;台灣的政府和民間仍然遮遮掩掩,不願面對被神格化的統治者,其實是掩護劊子手及情報頭子的作為,給殘害人權各種重新來過的機會。
誰該給後威權社會的台灣住民一個不會重蹈覆轍的承諾?
誠如雅斯培所言,罪責的反思不僅僅只是停留在對加害者的追訴而已,還包括公佈真相、還原歷史、教育下一代,建立責任政治及法治,以避免重蹈覆轍。
恐怖統治可以橫行無阻,一定有許多使之可能的共犯結構,後威權的社會必須好好反省及面對。無論行政、立法與司法,都是這個共犯結構的一環,需要徹底的檢討。當希特勒開始區隔尤太與非尤太人的生活領域時,部分尤太社群甚至非常認同,使這樣的區隔更有組織地進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尤太人如果不是一個那麼有秩序、有組織的群體,說不定集體的屠殺不會那麼容易進行。
大部分處於後威權社會的人們會羞於承認自己過去沒有反抗,當然更不願承認自己的沈默是使恐怖統治可以暢行無阻的原因。社會對過去、自己對自己、自己對家人、自己對他人保持沈默是最「安全」的方式,因為無須替自己或他人加害或受害提出合理的解釋和辯護。理論上,清算加害陣營黨派首腦的罪責僅需要成立獨立的調查機構,展開證據的蒐集和舉證,不算太難(既使這樣,台灣社會還是看不到歷任國家的領導人肯這樣做)。不過對社會整體而言,反思自己面對他人無辜被拘捕、拷打、失蹤、槍斃卻噤聲、保持沈默,才是杜絕威權體制復辟的不二法門。這些對過去迫害及殘暴經驗的反思,不應只是個人、隱藏式的私下進行,而是應該透過公開、集體討論的方式來面對。因為恐怖統治的真正恐怖之處,不是因為統治手段的殘忍而已,而是人們的順從。明明知道很多的制度、法律是錯的,竟然還繼續屈從!在這樣的屈從之中,正義沒有聲音,沒有一個人會獲得真正的安全。
由以上可知,認識過去統治的不正義不僅僅只在乎真相大白、還給受害者及社會一個正義而已。更積極而言,在檢討不正義如何發生的當下,也讓我們看到人是可以作出不同及多元選擇的,不一定只有英雄式的殉道和委曲求全而已。在這兩個極端之中,人們還是有可能作出各式各樣的選擇,而且仍然可以集體地不順從和行動。在討論為甚麼人需要有過去不正義經驗的記憶時,最哲學性的回答莫過於自我的「解放」與「自由」。
因為只有瞭解到自己其實可以有其他不同的選擇,並且為此感到懊悔時,人才有可能從自己造成的牢籠中解放出來,獲得真正的自由,建立責任政治。
對目前台灣的年輕人而言,日治時期、戒嚴和白色恐怖好像是上一代距離自己十分遙遠的事。就像之前提到的德國高中生,可以無憂無慮地騎著腳踏車悠遊在法國美麗如畫的鄉間。為甚麼仍然需要面對過去恐怖統治的記憶呢?選擇遺忘(所謂「忘記背後、努力向前」)不是更能感受生活的舒適和愜意嗎?
開頭這個故事的主角之一,後來成為萬湖會議紀念館的館長,這一趟法國鄉間的旅行徹底改變了他的生命。歷史是不能逆轉的,但未來可以。記憶、記錄過去的不正義是為了理解現在、扭轉未來。而且每一個人都有無法抵賴,必須承擔未來可能的不正義之責任。說自己無可選擇是推諉責任,因為讓曾經發生的事一再重演,沒有作出不同的選擇就是諉過、不負責任。
受到黨派政治化轉型正義的誤導,一般人會認為轉型正義只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殊不知,轉型正義最重要的關鍵是反思過去不正義的集體記憶,認識到自己的自由,並且願意保障這個得來不易的自由,承擔維護人權的責任。記憶不是為了延續隔離與仇恨,記憶是為了理解不同的可能性,以及自己在這些可能性當中可以作出的選擇。歷史記憶的找尋、維護和重建,為的是從錯誤中學到教訓,讓過去受到強權壓迫者可以慢慢獲得解放,社會也能逐漸脫離被監看的恐懼而擁有真正的自由。
這個單元中有兩篇文章:第一篇是林山田〈五十年來的台灣法制〉;第二篇劉熙明〈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
第一篇雖然是法制史的專門著作,但藉由追溯台灣戒嚴、動員及戡亂體制的由來,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台灣五○到九○年代,涉及國家體制及刑罰的「法令」和「法律」,其實都只有臨時條款或行政命令的特性,卻凌駕憲法及一般法律之上,成為鞏固政權、侵害人權的工具。
既使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這些「法令」僅在名稱上去除「動員」、「戡亂」等字眼,依然無視於憲法保障人權的基本規範,繼續成為侵害人權的工具。
大多數探究白色恐怖的文獻會陷在「惡法是否亦法?」的問題,受制於「惡法」的抽象概念,無法看清:既然是「惡法」,也就是不應該存在的規定,為甚麼還會有是否是「法」的問題呢?最該思考的問題不是惡法亦法,而是如何解消「惡法」這個混淆的概念。林山田直接指出這些特殊的法令:(一)產生的脈絡,也就是在中國大陸對日本及共軍作戰的狀態,直接引用到經過五十年日本統治、後來並沒有交戰狀態的台灣社會;(二)透過不法手段讓國民大會及立法院為這些「特別」的法令背書;以及(三)違背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說明這些法令並非法律,本身即違法而不應該存在。
閱讀〈五十年來的台灣法制〉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理解到檢視現有制度和法律的重要性,尤其是當這些制度和法律有侵害人權之虞,需要從最根本的觀念開始,廢除或宣布為非法,以達到維護人權之目的。同時,可以暴露威權體制暴力統治、罔顧正當程序的真實面貌,人們在這樣的制度中無辜受難。
劉熙明的〈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以當時公布的〈大溪檔案〉為依據,說明白色恐怖時期,情治單位的組織和架構直接聽命於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成為行政、立法、司法及監察機關的「上級」單位,可以在完全不受監督、管控的條件下,獨攬人民的生殺大權。雖然有人以「台灣處於動員戡亂的非常時期」作為理由,為這樣的措施辯護;但這篇文章清楚地指出:很多案件根本和所謂「防範未然、弭禍無形」、「保衛台灣」完全無關,大部分是因故得罪或冒犯兩蔣的威權而無故被連誅入罪,成為「不當審判」的最大受害者。兩蔣不但任由情治單位製造類似的假案及錯案,而且從始至終都主導這些案件的發生和結案。
劉熙明提出很多文獻證據,顯示蔣經國試圖以「革命大業」、「非常時期」來合理化情治單位的非常手段,甚至以各種動員、戡亂的法律,來賦予情治機關超越一般警察維護治安及法院拘留、審訊的「合法」權力。但從文章具體陳述的案例中,我們看不到這些案件與所謂「革命大業」、「非常時期」有任何可能的關連,反而看到為了鞏固專政而有的公報私仇、玩弄法律以遂行其統治意志的恐怖現象。
林山田及劉熙明以「非法」及「不當審判」討論過去的人民權利侵害,主要以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為核心,並未以「違反普世人權價值」,反駁特定「法令」、「組織」及「制度」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人民的基本權利」概念上仍侷限於本國國民及公民,而非以普遍的「人」之概念為立基點,擴大到過去、現在及未來居住在這塊土地的所有人。
任何法律的制訂都不能侵害人的基本自由及尊嚴,一旦違反人權,就僅僅只是統治者維護其威權的工具而已。這樣的法律不僅僅應該被廢除而已,更應該正式宣布其為「非法」,而過去因為這樣法律而被入罪者不僅僅只是「不當審判」;而更是「不法審判」,政府應該釐清事情發生的真相,賠償這些受到不當審判的受害者。
換句話說,概念上「酷刑」、「奴隸」及「奴役」都因為與人作為人的基本自由和尊嚴相矛盾而不應該存在;既使相關的約定是自願的,或是基於大多數的共識,符合所謂的「法律程序」,也不具備成為法律的要件。法令的落實若是妨礙個人享有完整的人權,國際法就會要求國內的法律必須逐漸修改以維護人權。這樣的主張背後並不需要預設有高於實證法律之上的「自然法」、「道德權利」或「自然權利」,而是基於任何法律都不能以取消及侵害人權為代價,而誤使法律成為維護特定族群掌握其統治權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