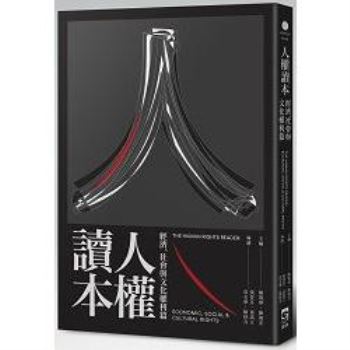分冊序:台灣人權實踐的軌跡與圖像: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篇/陳瑤華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工作及勞動、家庭、最起碼的生活水準、健康、教育、參與文化生活等是基本人權。這些權利的侵害會造成人們無法過有意義的生活,甚至無法繼續生存。聯合國的人權體系會作出這樣的人權規範,與人類在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方面遭遇到的不正義有關。這些不正義的制度有些來自於國家或執政者的好惡,如納粹對尤太人的仇視和屠殺,有些則是國家的不作為,如沒有依法消除歧視或處罰歧視。前者涉及政府直接違反人權,後者則是間接的侵害人權。
在歐美文化傳統中,「人權」通常以公民與政治的權利為主導性的概念,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比較不受重視。加上處於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人權治理的世界體制受到這個文化傳統及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作為「人權」,比較晚才獲得世界各國的確認。
雖然以上這樣的說法對於共產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宣稱捍衛無產階級和工農利益的國家,可能不一定適用。不過,一方面由於聯合國監測各國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人權體系,要到一九八五年才趨於完備,所以在此之前,共產或社會主義國家是否真正確認這些權利為人權,還需要更多具體的證據來證明。因為有越來越多的經驗證據顯示,人權涉及人最起碼生存及生活的自由和平等,缺少平等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以及公平參與政治決定的可能性,等於空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說辭,反而讓統治者或少數有金權、勢力者擁有壟斷言論及政治決定而可以宰制大多數的人。
從現有人權理論的文獻討論可以發現,由於古典人權概念涉及約束政府的權限,讓人民的公民及政治的自由得以確保及落實。而落實人民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保障,不但涉及各國發展程度及資源條件的差異性,而且賦予政府過多重新分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之權限,似乎不符合既有人權的基礎概念。
雖然古典政治、經濟理論有這樣的顧慮,實際上的經驗證據卻顯示:這兩種類型的權利之落實同樣都涉及約束及賦予政府權力,都需要受到嚴格檢視及監督。因此,如何透過落實資訊蒐集與監測,使政府真正承擔尊重、保護及實現保障人權的職責,使之更俱備可咎責性(accountability),才是最困難之處。
以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台灣的戒嚴時期為例,勞動者無法擁有集會、結社的權利,勞動三權,也就是能增進勞動權益的團結、爭議及協商的自由,根本就沒辦法真正落實。另一方面,RCA的毒物污染及職業病的案例也顯示:跨國企業可以利用戒嚴時期職災資訊及權利意識不足,使在地勞動者的身心受到嚴重的傷害,卻仍無法獲得應有的賠償。儘管勞動的人權被歸類為一種經濟的權利,其真正的落實不可能缺少公民及政治權利的相互支持。
根據〈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人權是維持人民最起碼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及住房,並不斷改進生活條件」,廣設人民負擔得起的國民住宅,以及維持便宜、價格穩定、可及的生活必需品就是政府的義務和責任。如果有人因為勞動的薪資過低,無法負擔最起碼的生活所需,政府應作相應的補貼,以承擔「維持人民最起碼的生活水準」這項人權的責任。相反地,當政府因應都市發展計劃而強拆民宅,使住民無家可歸,無論這些住民是否擁有原來居住地的產權,如果沒有嚴格的聽證程序及住民負擔得起的居住安置,都涉及政府直接違反人權。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機關任由財團炒地皮及強制收購房子及土地,造成人民生命及財產的損失,則是間接違反人權。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違反人權,都應有咎責的管道和方式,由政府相關人員接受懲罰及負擔賠償的責任。一般容易將維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想像成為國家的「恩惠」、「個殊照顧」或「社會福利」,這其實是與它作為國際人權規範的概念相違背。
在台灣,人權最不受保障的成員莫過於原住民、外籍家庭照護工、新移民,如果加上她們大部份是女性、勞動者的身分,就不難看出她們易成為多重交織歧視(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及貧窮受害者的結構性因素。因此,個別及單方面權利保障的提升並無法完全解決她們權利不受保障的現實處境,而需要有更全面的取徑(holistic approachs)。換句話說,對於這些群體而言,歧視及人權保障不足的處境涉及種族、性別及階級的多重因素,包括建立在種族、性別及階級的刻板印象及錯誤評價,不但造成制度性的歧視,如迫使原住民族漢化、外籍家庭照護工不受勞基法保障、新移民身分的認定及家庭、工作權利的缺乏保障等,而且使她們更容易受到私部門的剝削和侵害。政府法令及政策直接違反人權的問題,和間接的放任和不作為,都是造成這些群體處境更加惡化的原因。
基於以上分析,要解決這些群體在人權方面不受侵害的問題,應該具體分析她們各項基本權利在制度方面的排除和限制,尤其是她們文化、社會及經濟權利的弱勢,有可能和公民及政治權利的弱勢密不可分。如果單單專注於解決她們經濟上的貧窮問題,以為經濟及生活水準方面的改善,就可以提升她們的社會地位,其實是不夠細緻的做法,甚至會造成更多政策性的偏差和間接的歧視。目前制度及政策方面最為人所詬病的部分莫過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反映政府各部會在解決這些問題時缺乏橫向溝通,無法辨識出這些議題所涉及的種族、性別及階級蘊含的交織及多重歧視問題,以致於期待按照兩公約施行法及CEDAW施行法的規定,來修改國內法以及訂定行動方針,以解決這些群體的人權保障問題,一直有見樹不見林的困境。
本書四位導讀的作者:張晉芬、黃嵩立、范芯華及陳妙芬持續關注台灣勞動人權及貧窮的議題,期待外籍移工、新移民及原住民在人權方面的困境可以受到政府、社會更多的關懷,提升人權的意識與解決問題的細緻程度。
雖然各自的領域不同,有社會學、公衛學、哲學及法律學研究領域的差異,但也因為在各自專精的領域不同,反而讓弱勢族群的困境及各領域邊緣所涉及的制度問題,可以更廣泛地獲得彰顯。《人權讀本》籌備過程中,因專業領域的不同及取徑的差異,的確使導讀的作者群在選擇文獻時,除了在確立來源以本土的文獻為主外,仍有很多形式、內容及主題方向的認知差距。最後大家同意以下列八個概念來選取文獻:「傷害」、「恐懼」、「人道」(涵蓋「不人道」)、「善的生活」(尤其無法達到最起碼的程度)、「壓制」、「沈默以對」、「不正義」和「奴役」。在這八個概念底下,之所以「人權」通常會被提出來討論,是因為個人在特定處境及作為特定群體的成員,就算形式上有受到特定制度及法律的保障,她們的處境依然與以上八個概念密不可分。會訴諸人權來說明這樣的處境,很可能與制度設計不良、有對特定群體的區隔、排除及限制或沒有真正落實有關。原則的建立,讓後來的工作比較順暢。
另一個選擇的困難是文獻的學術研究嚴謹程度,如何能夠與社會運動倡議的實用程度相互平衡。尤其是如何兼顧這兩者。本書不希望因為定位為高等學院的教科書,而失去提升社會人權意識的廣大目標。所以在選取文獻時,有一部分是報導文學,如勞動人權部分選自苦勞網柳琬玲〈哭泣的RCA母親們—記那一代電子業女工的飲泣〉,原住民族基本權利的部分選自《山海文化》古韃鳴〈划向自治的孤舟—蘭嶼(Pongso-No-Tau)聚落重建的困境與展望〉以及陳板〈凱達格蘭.霄裡•核四〉;有一部分則為台灣勞動的重要歷史文件,如張曉春等〈勞動人權宣言〉;此外,夏傳位〈卡債族的成因、實況與出路〉一文擷選自《塑膠鴉片:雙卡風暴刷出台灣負債危機》一書;其他大部分是探討不同議題的研究論文。
在勞動、貧窮、新移民及原住民族人權各篇中,除了四位作者精闢的導讀外,還有討論問題、延伸閱讀及行動的建議。
目的在鼓勵讀者多方面思考這些議題的複雜內容、搜集更多的資訊、繼續相關的研究,並且能藉由行動的參與,提高人權的意識和敏感度。除了可以作為教科書或讀書會的媒材,也希望透過本書所建立的部落格,讓讀者上傳及下載相關的資訊,使得本書的內容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延伸、發酵而更為深入。人權的議題不可能單純透過抽象的理論來解決,而是需要在實際的問題中藉由規範性的人權標準發現可行的改變之道。
最後,本書非常期待未來有更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無論來自學院,還是研究機構、智庫、非政府組織、草根團體,都能從事人權的跨領域研究。台灣自一九七一年後不再直接參與聯合國的運作,政府部門對於之後國際人權治理的進展十分陌生。相較之下,民間組織雖有較多的機會參與聯合國人權的外圍組織,但在政府缺少國際人權體制的壓力、不受國際人權組織監督的狀況下,如果人民及公民社會的人權意識沒有提升,台灣在落實人權保障方面會遠遠落後。
走過戒嚴、解嚴並逐步民主化的台灣,需要更多以增進人權保障、維護個人尊嚴為目標的知識生產,作為制度的法律及政策修正的參照。尤其是在這過程中因專注於司法、政治改革而比較容易被忽略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這些權利會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腳步而更為顯著,成為鞏固民主的重要支柱。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工作及勞動、家庭、最起碼的生活水準、健康、教育、參與文化生活等是基本人權。這些權利的侵害會造成人們無法過有意義的生活,甚至無法繼續生存。聯合國的人權體系會作出這樣的人權規範,與人類在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方面遭遇到的不正義有關。這些不正義的制度有些來自於國家或執政者的好惡,如納粹對尤太人的仇視和屠殺,有些則是國家的不作為,如沒有依法消除歧視或處罰歧視。前者涉及政府直接違反人權,後者則是間接的侵害人權。
在歐美文化傳統中,「人權」通常以公民與政治的權利為主導性的概念,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比較不受重視。加上處於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人權治理的世界體制受到這個文化傳統及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作為「人權」,比較晚才獲得世界各國的確認。
雖然以上這樣的說法對於共產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宣稱捍衛無產階級和工農利益的國家,可能不一定適用。不過,一方面由於聯合國監測各國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人權體系,要到一九八五年才趨於完備,所以在此之前,共產或社會主義國家是否真正確認這些權利為人權,還需要更多具體的證據來證明。因為有越來越多的經驗證據顯示,人權涉及人最起碼生存及生活的自由和平等,缺少平等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以及公平參與政治決定的可能性,等於空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說辭,反而讓統治者或少數有金權、勢力者擁有壟斷言論及政治決定而可以宰制大多數的人。
從現有人權理論的文獻討論可以發現,由於古典人權概念涉及約束政府的權限,讓人民的公民及政治的自由得以確保及落實。而落實人民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保障,不但涉及各國發展程度及資源條件的差異性,而且賦予政府過多重新分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之權限,似乎不符合既有人權的基礎概念。
雖然古典政治、經濟理論有這樣的顧慮,實際上的經驗證據卻顯示:這兩種類型的權利之落實同樣都涉及約束及賦予政府權力,都需要受到嚴格檢視及監督。因此,如何透過落實資訊蒐集與監測,使政府真正承擔尊重、保護及實現保障人權的職責,使之更俱備可咎責性(accountability),才是最困難之處。
以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台灣的戒嚴時期為例,勞動者無法擁有集會、結社的權利,勞動三權,也就是能增進勞動權益的團結、爭議及協商的自由,根本就沒辦法真正落實。另一方面,RCA的毒物污染及職業病的案例也顯示:跨國企業可以利用戒嚴時期職災資訊及權利意識不足,使在地勞動者的身心受到嚴重的傷害,卻仍無法獲得應有的賠償。儘管勞動的人權被歸類為一種經濟的權利,其真正的落實不可能缺少公民及政治權利的相互支持。
根據〈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人權是維持人民最起碼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及住房,並不斷改進生活條件」,廣設人民負擔得起的國民住宅,以及維持便宜、價格穩定、可及的生活必需品就是政府的義務和責任。如果有人因為勞動的薪資過低,無法負擔最起碼的生活所需,政府應作相應的補貼,以承擔「維持人民最起碼的生活水準」這項人權的責任。相反地,當政府因應都市發展計劃而強拆民宅,使住民無家可歸,無論這些住民是否擁有原來居住地的產權,如果沒有嚴格的聽證程序及住民負擔得起的居住安置,都涉及政府直接違反人權。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機關任由財團炒地皮及強制收購房子及土地,造成人民生命及財產的損失,則是間接違反人權。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違反人權,都應有咎責的管道和方式,由政府相關人員接受懲罰及負擔賠償的責任。一般容易將維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想像成為國家的「恩惠」、「個殊照顧」或「社會福利」,這其實是與它作為國際人權規範的概念相違背。
在台灣,人權最不受保障的成員莫過於原住民、外籍家庭照護工、新移民,如果加上她們大部份是女性、勞動者的身分,就不難看出她們易成為多重交織歧視(intersectional discrimination)及貧窮受害者的結構性因素。因此,個別及單方面權利保障的提升並無法完全解決她們權利不受保障的現實處境,而需要有更全面的取徑(holistic approachs)。換句話說,對於這些群體而言,歧視及人權保障不足的處境涉及種族、性別及階級的多重因素,包括建立在種族、性別及階級的刻板印象及錯誤評價,不但造成制度性的歧視,如迫使原住民族漢化、外籍家庭照護工不受勞基法保障、新移民身分的認定及家庭、工作權利的缺乏保障等,而且使她們更容易受到私部門的剝削和侵害。政府法令及政策直接違反人權的問題,和間接的放任和不作為,都是造成這些群體處境更加惡化的原因。
基於以上分析,要解決這些群體在人權方面不受侵害的問題,應該具體分析她們各項基本權利在制度方面的排除和限制,尤其是她們文化、社會及經濟權利的弱勢,有可能和公民及政治權利的弱勢密不可分。如果單單專注於解決她們經濟上的貧窮問題,以為經濟及生活水準方面的改善,就可以提升她們的社會地位,其實是不夠細緻的做法,甚至會造成更多政策性的偏差和間接的歧視。目前制度及政策方面最為人所詬病的部分莫過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反映政府各部會在解決這些問題時缺乏橫向溝通,無法辨識出這些議題所涉及的種族、性別及階級蘊含的交織及多重歧視問題,以致於期待按照兩公約施行法及CEDAW施行法的規定,來修改國內法以及訂定行動方針,以解決這些群體的人權保障問題,一直有見樹不見林的困境。
本書四位導讀的作者:張晉芬、黃嵩立、范芯華及陳妙芬持續關注台灣勞動人權及貧窮的議題,期待外籍移工、新移民及原住民在人權方面的困境可以受到政府、社會更多的關懷,提升人權的意識與解決問題的細緻程度。
雖然各自的領域不同,有社會學、公衛學、哲學及法律學研究領域的差異,但也因為在各自專精的領域不同,反而讓弱勢族群的困境及各領域邊緣所涉及的制度問題,可以更廣泛地獲得彰顯。《人權讀本》籌備過程中,因專業領域的不同及取徑的差異,的確使導讀的作者群在選擇文獻時,除了在確立來源以本土的文獻為主外,仍有很多形式、內容及主題方向的認知差距。最後大家同意以下列八個概念來選取文獻:「傷害」、「恐懼」、「人道」(涵蓋「不人道」)、「善的生活」(尤其無法達到最起碼的程度)、「壓制」、「沈默以對」、「不正義」和「奴役」。在這八個概念底下,之所以「人權」通常會被提出來討論,是因為個人在特定處境及作為特定群體的成員,就算形式上有受到特定制度及法律的保障,她們的處境依然與以上八個概念密不可分。會訴諸人權來說明這樣的處境,很可能與制度設計不良、有對特定群體的區隔、排除及限制或沒有真正落實有關。原則的建立,讓後來的工作比較順暢。
另一個選擇的困難是文獻的學術研究嚴謹程度,如何能夠與社會運動倡議的實用程度相互平衡。尤其是如何兼顧這兩者。本書不希望因為定位為高等學院的教科書,而失去提升社會人權意識的廣大目標。所以在選取文獻時,有一部分是報導文學,如勞動人權部分選自苦勞網柳琬玲〈哭泣的RCA母親們—記那一代電子業女工的飲泣〉,原住民族基本權利的部分選自《山海文化》古韃鳴〈划向自治的孤舟—蘭嶼(Pongso-No-Tau)聚落重建的困境與展望〉以及陳板〈凱達格蘭.霄裡•核四〉;有一部分則為台灣勞動的重要歷史文件,如張曉春等〈勞動人權宣言〉;此外,夏傳位〈卡債族的成因、實況與出路〉一文擷選自《塑膠鴉片:雙卡風暴刷出台灣負債危機》一書;其他大部分是探討不同議題的研究論文。
在勞動、貧窮、新移民及原住民族人權各篇中,除了四位作者精闢的導讀外,還有討論問題、延伸閱讀及行動的建議。
目的在鼓勵讀者多方面思考這些議題的複雜內容、搜集更多的資訊、繼續相關的研究,並且能藉由行動的參與,提高人權的意識和敏感度。除了可以作為教科書或讀書會的媒材,也希望透過本書所建立的部落格,讓讀者上傳及下載相關的資訊,使得本書的內容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延伸、發酵而更為深入。人權的議題不可能單純透過抽象的理論來解決,而是需要在實際的問題中藉由規範性的人權標準發現可行的改變之道。
最後,本書非常期待未來有更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無論來自學院,還是研究機構、智庫、非政府組織、草根團體,都能從事人權的跨領域研究。台灣自一九七一年後不再直接參與聯合國的運作,政府部門對於之後國際人權治理的進展十分陌生。相較之下,民間組織雖有較多的機會參與聯合國人權的外圍組織,但在政府缺少國際人權體制的壓力、不受國際人權組織監督的狀況下,如果人民及公民社會的人權意識沒有提升,台灣在落實人權保障方面會遠遠落後。
走過戒嚴、解嚴並逐步民主化的台灣,需要更多以增進人權保障、維護個人尊嚴為目標的知識生產,作為制度的法律及政策修正的參照。尤其是在這過程中因專注於司法、政治改革而比較容易被忽略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這些權利會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腳步而更為顯著,成為鞏固民主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