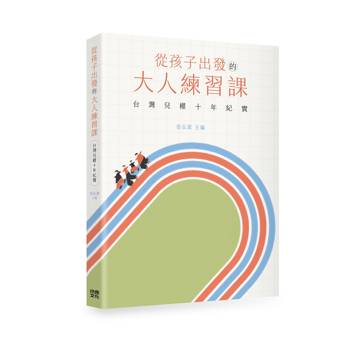一間不算寬敞的會議室裡,坐著幾位西裝筆挺的官員,也坐著幾位看起來有些緊張的學生。桌上的文件封面寫著「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等字樣。如果「那年」沒有發生那樣的事,那些「兒少代表」,恐怕也很難踏進政策制定的現場。
如同前面幾篇文章提到, 2012 年以來,台灣通過修法,要求政府邀請兒少代表列席正式會議。這項制度性的改變,讓原本在體制外無聲的孩子,終於有了一個可以說出心聲的平台。
就在歷史瞬間,本文的主角們忽然發現,原來學生不只是坐在教室裡等考試的人,也可以站出來,說出自己的需求、為同齡的朋友發聲。
這篇故事的主角有三——小新、短短和昀臻。他們都分別於桃園、高雄、臺南擔任過地方少代。當別的同齡人在補習、考試,他們在市政會議上學著用一字一句,爭取更多屬於孩子的權利。
幾年後,三人踏入大學,小新和短短緊接前往中央層級擔任兒少代表(下文簡稱少代),在國家級會議上繼續參與政策討論;相對地,昀臻選擇了另一條路,進入「青諮」(青年諮詢委員會)體系,從不同的角度開展「參與」的意義。
如今,24 歲的他們,仍沒有停下兒少自治的腳步,而是各自回到地方,重新開始。他們分別成立了以兒少代表為主體的協會,嘗試從最熟悉的土地出發,陪伴更多年輕世代,一起學習、一起發聲。
這不是一段只關於他們三人的故事,而是關於每一位想讓「小孩不是只能聽話,而是可以說話」的人的心路歷程。接下來,讓我們一起走進三位主角的生命軌跡,聽他們怎麼開始、怎麼堅持,又是怎麼把一段代表的經歷,變成前半生的志業。
他們是如何踏上少代之路的?
短短是第一批搭上少代列車的兒少。他在 12 歲便選上高雄市少代,直到擔任中央兒少代表後已年滿 19;因為長時間沈浸在少代體系中,總被戲稱為少代圈的活化石。
短短之所以萌生對少代的興趣,必須歸功於她國中開放的校園風氣。當時學校使用的聯絡簿有一欄「心情小語」,學生必須寫下每天的心得,舉凡反思讀書方法、檢討考試成績、紀錄班上趣聞、分享追星心情等都可以大方寫進去。
起初,短短與大部分同學一樣,寫著很一般的內容,直到某天她發現校內行人與自行車的路線規劃有問題,在通勤的高峰期間容易使學生發生危險,因此她針對這個現象,在該日的心情小語中抱怨一番。
原以為這篇小記,只是生命中再普通不過的小插曲,出乎意料的是,她的的班導卻非常認真回覆這篇小記;不但針對她細膩的觀察做出讚許,同時也引導她更深入思考:這件事情有多久了?有多少人受這樣的政策影響?目前學校這樣規劃有沒有什麼理由?其他學生有同樣感到不方便嗎?如果換成她來制定規範,會如何改善呢?
在導師循循善誘下,短短開始思考政策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對於身邊、甚至整體社會發生的事情萌生興趣。她寫在聯絡簿的心情小語字數逐漸增加,對於議題的刻畫也越發深刻;為了寫出讓自己滿意的文章,她下課後還會主動到圖書館查資料、上網找新聞、翻閱報紙雜誌,甚至還會訪問相關人員。
學校老師開始發現短短對社會議題有濃厚興趣。正巧,當時高雄正在招募第一屆兒少代表,學校老師便大力推薦短短加入,令其結識同樣興趣的夥伴──一起研究社會、改變社會,一走就走到了今天。
其中一位同伴便是昀臻。雖然昀臻是臺南人,但她之所以加入少代行列,和短短有著莫大關係。
一切可回推至昀臻的國中時期,當時學校仍對學生設有許多不合理的規範。雖然昀臻心裡覺得奇怪,卻遲遲沒有行動的契機;直到升上臺南二中,受到學校自由開放的風氣影響,她開始對「成人單方面制定規則及兒少須無條件服從」的要求產生反思,促使他進一步參與「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舉辦的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營。
該營隊標榜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與批判性思考,吸引各校的優秀人才參與。短短幸運地與昀臻分到同一梯次,受到短短談吐及思考應對的吸引,昀臻近一步追問,得知「少代」這個組織幫助短短培育了這些能力,因此也暗自決定自己也要加入臺南少代。
在擔任少代及兒少顧問(註一)三年時間,她與同屆的戰友們不斷集思廣益,希望可以讓更多人認識兒童權利公約、瞭解兒少權益並尊重兒少聲音。不但嘗試入校宣導、與局處溝通,倡導兒少代表能參與更多不同會議,也參與公共建設的興建過程,以兒少視角提供建議並確認落實。
她期許可以藉此為兒少爭取權益,也希望能讓社會知道,年紀從來不會是判斷兒少是否能為自己發聲的標準。相較短短與昀臻,從學校獲得公共參與的能量,小新的求學過程就沒這麼幸運了。
中學時期的小新,極度討厭在學校裡學習。雖然師長都認為他在校表現十分優異,但面對校園處處皆是的權力壓迫,無論是制服規範、升旗或是無止境的加強班,都令小新感到非常不舒服。他知道自己總是為了換取最大的自由,不斷滿足他人期待。
因為如此,小新開始不斷尋找體制外學習的機會。高一那年暑假,小新拉著他的父親,從中壢至台北國圖聽一位歷史學家的演講,他還記得那場演講座無虛席,晚到的他只能和爸爸坐在旁邊的視聽教室看轉播。然而就算無法和講師面對面接觸,小新仍受到這場演講啟發,他更加堅定相信:學習不該只發生在校園裡而已。
為了開展校園外的學習之旅,小新繼而投入桃園少代。擔任少代的四年間,除了學校的生活以外,其餘時間大多沈浸於少代的培力活動,包含每月一次的例會及培力課程,還有各式有趣的會議都是他保持學習的動力之一。他說:「參與少代是拾回學習意義、探索真實自我的有感過程。」
少代還讓小新發現,做人做事的學習是課本中學不來的。在我們主流教育中,除非幸運抽到將教育作為志業,願意用生命影響生命的 SSR 級教師(SSR 是電玩遊戲的比喻,象徵很高級的意思),否則卡在當前資源與機制,再有熱忱的教師,都容易被體制消磨殆盡。
幸運地,在小新成為少代的第一年裡,遇見了當時的培力者「徐社工師」。她讓小新第一次感受到成人把兒少當作權利主體,讓能被平等對待、同理、傾聽與真實接納的滋味。徐社工師是位溫暖且理性的培力者,為桃園少代創造各種舞台,鼓勵他們上台發言,卻從不會對兒少頤指氣使,反而願意耐心陪伴他們成長。
那一年,小新不只當上了少代,也遇見了一種不一樣的大人。她讓他知道,原來「被相信」和「被尊重」這件事,真的可以發生在現實生活裡。只是,少代任期終有結束的一天,當那道舞台燈光漸漸熄滅,下一步,「三名主角」又該往哪裡去?
離開兒少代表之後,然後呢?
在離開地方與中央兒少代表後,短短緊接進入兒福聯盟成為培力者。當時兒盟承接中央兒少代表的方案,短短也擔任了兩年多的社工;對於在少代圈闖蕩八年有餘的她,越發體會對兒少成長來說,培力者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個稱職的培力者,不只能為兒少賦權與增能;更重要的是,可以陪伴兒少面對公共參與,獲得平等的話語權,使每位兒少都能爭取合適的成長發展,進而建立對於自身的自信,與可茲信賴的夥伴。
但理想歸理想,現實卻從不輕鬆。尤其少代成立不過十年,絕大部分的培力者對於少代運作都尚未嫻熟;更何況,各縣市資源落差極大,經費不足與人力緊縮的重重限制下,都很難要求培力者擁有的相關知識。為了突破這些困境,短短一直覺得——如果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場域,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一起共創協會,那該有多好!
而命運的齒輪似乎也剛剛好轉動起來——那頭,小新與一群少代出身的夥伴們,已悄悄成立了「臺灣桃湛公民培力協會」,希望延續「好好對話」的理念,打造一個不靠抽中 SSR 級老師也能安心成長的地方——一個屬於在地、平等、溫暖的對話場域。
他們鼓起勇氣問了短短一句:「妳,願不願意一起來?」答案沒有多想,一拍即合。他們就這樣,撐起了協會運作的每一天,從實體場地、到活動設計、到陪伴下一批兒少——一步一腳印,走出屬於他們的培力路。
在此同時,昀臻也沒有閒著,她一樣為了少代而努力耕耘。
昀臻是第四屆少代的副主席。任期中,與同屆的兒少代表們合作無間,充分感受彼此是一個團隊;雖然對不同議題有不同想像,但目標卻是一致的。團隊一起努力、互相扶持,在與政府溝通不良、被幼體化、不被尊重時,不斷共同找尋突破的方式。
雖然阻礙未曾消失,但她們也看到了不同得進展,瞭解自身的參與並非沒有意義。
卸任之後,她並沒有離開這個場域,反而更加積極地擔任顧問、串連新一屆的兒少代表。在歷經培力單位更換的情況下,她與夥伴們觀察到一個長年存在的問題——許多議題總是被大人「定義」為是否與兒少「有關」,但這種定義往往狹隘又失焦。夥伴羅承彥一句話說得鏗鏘有力:「不是與兒少有關的議題才是兒少議題,而是兒少關心的議題皆是兒少議題!」
為了推翻這個現況,她與其他夥伴決心成立「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代表協會」,秉持「以兒少為主體、與兒少共創」的精神,自行承接地方少代的培力任務。他們不只是延續記憶,更想在臺南的土地上,打造一個真正讓兒少安心發聲、安心成長的基地。
到此,我們可以看見:桃園的協會悄悄成形,短短與小新攜手為下一代兒少鋪出一條更穩的參與之路;另一頭的臺南,也悄悄吹起一股熟悉的風。不是回憶,不是懷舊,而是另一位少代——昀臻,準備從過去的經驗出發,踏上同樣關於傳承、關於共創的路。
三位主角腳步的節奏不同,但方向一致。
離開發言席,改在背後撐傘
從少代轉變為培力工作者的角色並非易事,其中難免充滿許多困難與糾結。
首先,他們必須面對的是學業與培力工作的平衡。像是昀臻便在承接培力工作後,為了穩定協會而選擇暫時休學,短短也為同時兼顧課業與培力而延畢。
其次,培力經費與資源的多寡,與政府考核有著絕對的關聯。中央制定了許多考核指標來檢視培力單位;然而這些指標,並未全部貼合兒少的需求,協會常為了符合指標而被迫做出相關調整。
而這些指標是讓「願景被現實消磨』的原因之一。
為了符合指標的要求,兒少必須推動一定數量的議題,同時也必須進行兒童權利公約的校園與社區宣導。原本學校的課業與升學壓力就很大了,長期下來前述要求更會讓兒少代表蠟燭兩頭燒,引發負荷過載的問題。
雖然政府是因背負社會大眾的期待,才轉嫁許多不合理的成本到兒少及培力單位身上,但由於兒少及培力單位都缺乏試錯的空間,實際運作起來往往令人心力交瘁,甚至感到憤怒。而兒少或者培力工作者為了突破桎梏,相關爭取反而在政府眼中是「不聽話」與「麻煩」的體現。
其三,經營非營利組織有其難度。先不提創立過程中複雜的法規與行政流程,光是在龐雜行政庶務中,需不斷兼顧活動成效與組織永續就足夠令人煩惱。他們必須時常問自己:身為工作者能不能成為兒少支柱?組職是否能長久陪伴兒少?作為組織領導人能不能帶領協會走向共同目標?成為承包培力方案的廠商後,如果因為維權而與政府關係緊張,是不是就無法得到相關資源?
其四,身份的轉變也讓成就感有了不同的來源。以往擔任兒少代表時,他們總是自己關注相關議題,從尋找專家諮詢、搜集同儕意見、查詢相關數據、發想可行方案直到將落筆為提案單,通常在會議當下便知道提案的結果與展望,通常具有「即時回饋」的特性,成就感也隨之容易體會。
然而,成為培力工作者後,他們必須從「自己捕魚變為教人釣魚」,工作過程中不只需學會如何按耐住指導別人的慾望,留給少代自行探索與討論的空間,同時也必須對團體動力的運行更加敏銳,觀察何時是少代的卡關期,學習如何在適當時機對少代進行適當「引導」而非「指導」,逐漸將重點由自我能力的展現,轉變為適當且恰好的陪伴,時時提醒自己將舞台留給少代。
舉例來說,在政府會議已經身經百戰的他們,在陪同少代參與會議時(註二),面對政府的質疑,很自然會產生佐證與反駁的種種想法,也能夠輕易辨識出成人複雜言論下的深層含義,警覺對方是真心回應議題還是在敷衍兒少;但在現行體制下,他們並不能直接回應政府端──一方面,因他們的角色只是陪同少代列席,在會議規範上本就沒有主動發言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走過相同流程,深知學習表達意見、迅速分析與組織詞彙的應對需要時間練習。
但撐傘的人也會濕啊,會累啊。因此,他們內心時常出現掙扎:明明知道在這個時間點多說一點就能夠促成政策轉變,卻希望能使少代有多一點的發揮空間而選擇放棄。在那個會議關卡,他們究竟應以社會政策的轉變為主,把握機會來改善兒少處境,還是應以兒少的學習空間為主,給予足夠時間使兒少慢慢成長,都會是永遠需要反思與討論的靈魂拷問。
最後,在選擇以少代途徑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心中,有時難免覺得「這個頭銜好酷!」或是「感覺與眾不同」這都是很自然的心態。
這也讓部分少代覺得「效能感爆棚」,小小年紀竟能在與父母,甚至爺爺奶奶年齡相仿的高官面前一同討論公共政策,不免使有些兒少會自認:「贏過 99% 同齡人」,進而產生不合理的優越感,以自己能「嗆」政府官員感到自豪。
而培力者若因未設定明確的培力目標,或本身即是激進的倡議團體,而放任兒少代表大放厥詞,也就隨之容易有「泛政治化」的舉措,把提案討論變做政論節目;在缺乏完整的結構認知下,輕易地攻擊政府或是業務單位。但我們都知道這並非是「兒少表意權」的展現,而是在弱化公民社會,傷害了利益關係人之間的信任關係。
因此,主角們都知道,要成為培力者前必須先釐清自身的價值信念,釐清真正想要的著力點。當然,引導的能力需要練習,他們創立協會,也有一部分是希望藉由共學共創的過程,彼此增長培力的知能。
少代之路充滿挑戰,從政策限制到資源不足,三位培力工作者在成長過程中不僅面臨身分轉變的掙扎,還要在現實框架下找到突破的出口。為了打破這些困境,三人創立協會,希望打造一個以兒少為主體的支持平台,他們不僅重視平等對話,還積極探索新的培力模式,試圖讓兒少在自主與被賦權間取得平衡,找到適合成長的空間。
這不是完美的結局,而是打拼的中場。也因此,我們得繼續說下去——下一集,我們將帶大家走進三位主角攜手創造的新篇章。從會議室到街頭巷尾,從提案的紙上,到落實的現場,他們如何培力?讓「兒少參與」不會只停留在單純口號?
如同前面幾篇文章提到, 2012 年以來,台灣通過修法,要求政府邀請兒少代表列席正式會議。這項制度性的改變,讓原本在體制外無聲的孩子,終於有了一個可以說出心聲的平台。
就在歷史瞬間,本文的主角們忽然發現,原來學生不只是坐在教室裡等考試的人,也可以站出來,說出自己的需求、為同齡的朋友發聲。
這篇故事的主角有三——小新、短短和昀臻。他們都分別於桃園、高雄、臺南擔任過地方少代。當別的同齡人在補習、考試,他們在市政會議上學著用一字一句,爭取更多屬於孩子的權利。
幾年後,三人踏入大學,小新和短短緊接前往中央層級擔任兒少代表(下文簡稱少代),在國家級會議上繼續參與政策討論;相對地,昀臻選擇了另一條路,進入「青諮」(青年諮詢委員會)體系,從不同的角度開展「參與」的意義。
如今,24 歲的他們,仍沒有停下兒少自治的腳步,而是各自回到地方,重新開始。他們分別成立了以兒少代表為主體的協會,嘗試從最熟悉的土地出發,陪伴更多年輕世代,一起學習、一起發聲。
這不是一段只關於他們三人的故事,而是關於每一位想讓「小孩不是只能聽話,而是可以說話」的人的心路歷程。接下來,讓我們一起走進三位主角的生命軌跡,聽他們怎麼開始、怎麼堅持,又是怎麼把一段代表的經歷,變成前半生的志業。
他們是如何踏上少代之路的?
短短是第一批搭上少代列車的兒少。他在 12 歲便選上高雄市少代,直到擔任中央兒少代表後已年滿 19;因為長時間沈浸在少代體系中,總被戲稱為少代圈的活化石。
短短之所以萌生對少代的興趣,必須歸功於她國中開放的校園風氣。當時學校使用的聯絡簿有一欄「心情小語」,學生必須寫下每天的心得,舉凡反思讀書方法、檢討考試成績、紀錄班上趣聞、分享追星心情等都可以大方寫進去。
起初,短短與大部分同學一樣,寫著很一般的內容,直到某天她發現校內行人與自行車的路線規劃有問題,在通勤的高峰期間容易使學生發生危險,因此她針對這個現象,在該日的心情小語中抱怨一番。
原以為這篇小記,只是生命中再普通不過的小插曲,出乎意料的是,她的的班導卻非常認真回覆這篇小記;不但針對她細膩的觀察做出讚許,同時也引導她更深入思考:這件事情有多久了?有多少人受這樣的政策影響?目前學校這樣規劃有沒有什麼理由?其他學生有同樣感到不方便嗎?如果換成她來制定規範,會如何改善呢?
在導師循循善誘下,短短開始思考政策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對於身邊、甚至整體社會發生的事情萌生興趣。她寫在聯絡簿的心情小語字數逐漸增加,對於議題的刻畫也越發深刻;為了寫出讓自己滿意的文章,她下課後還會主動到圖書館查資料、上網找新聞、翻閱報紙雜誌,甚至還會訪問相關人員。
學校老師開始發現短短對社會議題有濃厚興趣。正巧,當時高雄正在招募第一屆兒少代表,學校老師便大力推薦短短加入,令其結識同樣興趣的夥伴──一起研究社會、改變社會,一走就走到了今天。
其中一位同伴便是昀臻。雖然昀臻是臺南人,但她之所以加入少代行列,和短短有著莫大關係。
一切可回推至昀臻的國中時期,當時學校仍對學生設有許多不合理的規範。雖然昀臻心裡覺得奇怪,卻遲遲沒有行動的契機;直到升上臺南二中,受到學校自由開放的風氣影響,她開始對「成人單方面制定規則及兒少須無條件服從」的要求產生反思,促使他進一步參與「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舉辦的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育營。
該營隊標榜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與批判性思考,吸引各校的優秀人才參與。短短幸運地與昀臻分到同一梯次,受到短短談吐及思考應對的吸引,昀臻近一步追問,得知「少代」這個組織幫助短短培育了這些能力,因此也暗自決定自己也要加入臺南少代。
在擔任少代及兒少顧問(註一)三年時間,她與同屆的戰友們不斷集思廣益,希望可以讓更多人認識兒童權利公約、瞭解兒少權益並尊重兒少聲音。不但嘗試入校宣導、與局處溝通,倡導兒少代表能參與更多不同會議,也參與公共建設的興建過程,以兒少視角提供建議並確認落實。
她期許可以藉此為兒少爭取權益,也希望能讓社會知道,年紀從來不會是判斷兒少是否能為自己發聲的標準。相較短短與昀臻,從學校獲得公共參與的能量,小新的求學過程就沒這麼幸運了。
中學時期的小新,極度討厭在學校裡學習。雖然師長都認為他在校表現十分優異,但面對校園處處皆是的權力壓迫,無論是制服規範、升旗或是無止境的加強班,都令小新感到非常不舒服。他知道自己總是為了換取最大的自由,不斷滿足他人期待。
因為如此,小新開始不斷尋找體制外學習的機會。高一那年暑假,小新拉著他的父親,從中壢至台北國圖聽一位歷史學家的演講,他還記得那場演講座無虛席,晚到的他只能和爸爸坐在旁邊的視聽教室看轉播。然而就算無法和講師面對面接觸,小新仍受到這場演講啟發,他更加堅定相信:學習不該只發生在校園裡而已。
為了開展校園外的學習之旅,小新繼而投入桃園少代。擔任少代的四年間,除了學校的生活以外,其餘時間大多沈浸於少代的培力活動,包含每月一次的例會及培力課程,還有各式有趣的會議都是他保持學習的動力之一。他說:「參與少代是拾回學習意義、探索真實自我的有感過程。」
少代還讓小新發現,做人做事的學習是課本中學不來的。在我們主流教育中,除非幸運抽到將教育作為志業,願意用生命影響生命的 SSR 級教師(SSR 是電玩遊戲的比喻,象徵很高級的意思),否則卡在當前資源與機制,再有熱忱的教師,都容易被體制消磨殆盡。
幸運地,在小新成為少代的第一年裡,遇見了當時的培力者「徐社工師」。她讓小新第一次感受到成人把兒少當作權利主體,讓能被平等對待、同理、傾聽與真實接納的滋味。徐社工師是位溫暖且理性的培力者,為桃園少代創造各種舞台,鼓勵他們上台發言,卻從不會對兒少頤指氣使,反而願意耐心陪伴他們成長。
那一年,小新不只當上了少代,也遇見了一種不一樣的大人。她讓他知道,原來「被相信」和「被尊重」這件事,真的可以發生在現實生活裡。只是,少代任期終有結束的一天,當那道舞台燈光漸漸熄滅,下一步,「三名主角」又該往哪裡去?
離開兒少代表之後,然後呢?
在離開地方與中央兒少代表後,短短緊接進入兒福聯盟成為培力者。當時兒盟承接中央兒少代表的方案,短短也擔任了兩年多的社工;對於在少代圈闖蕩八年有餘的她,越發體會對兒少成長來說,培力者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個稱職的培力者,不只能為兒少賦權與增能;更重要的是,可以陪伴兒少面對公共參與,獲得平等的話語權,使每位兒少都能爭取合適的成長發展,進而建立對於自身的自信,與可茲信賴的夥伴。
但理想歸理想,現實卻從不輕鬆。尤其少代成立不過十年,絕大部分的培力者對於少代運作都尚未嫻熟;更何況,各縣市資源落差極大,經費不足與人力緊縮的重重限制下,都很難要求培力者擁有的相關知識。為了突破這些困境,短短一直覺得——如果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場域,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一起共創協會,那該有多好!
而命運的齒輪似乎也剛剛好轉動起來——那頭,小新與一群少代出身的夥伴們,已悄悄成立了「臺灣桃湛公民培力協會」,希望延續「好好對話」的理念,打造一個不靠抽中 SSR 級老師也能安心成長的地方——一個屬於在地、平等、溫暖的對話場域。
他們鼓起勇氣問了短短一句:「妳,願不願意一起來?」答案沒有多想,一拍即合。他們就這樣,撐起了協會運作的每一天,從實體場地、到活動設計、到陪伴下一批兒少——一步一腳印,走出屬於他們的培力路。
在此同時,昀臻也沒有閒著,她一樣為了少代而努力耕耘。
昀臻是第四屆少代的副主席。任期中,與同屆的兒少代表們合作無間,充分感受彼此是一個團隊;雖然對不同議題有不同想像,但目標卻是一致的。團隊一起努力、互相扶持,在與政府溝通不良、被幼體化、不被尊重時,不斷共同找尋突破的方式。
雖然阻礙未曾消失,但她們也看到了不同得進展,瞭解自身的參與並非沒有意義。
卸任之後,她並沒有離開這個場域,反而更加積極地擔任顧問、串連新一屆的兒少代表。在歷經培力單位更換的情況下,她與夥伴們觀察到一個長年存在的問題——許多議題總是被大人「定義」為是否與兒少「有關」,但這種定義往往狹隘又失焦。夥伴羅承彥一句話說得鏗鏘有力:「不是與兒少有關的議題才是兒少議題,而是兒少關心的議題皆是兒少議題!」
為了推翻這個現況,她與其他夥伴決心成立「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代表協會」,秉持「以兒少為主體、與兒少共創」的精神,自行承接地方少代的培力任務。他們不只是延續記憶,更想在臺南的土地上,打造一個真正讓兒少安心發聲、安心成長的基地。
到此,我們可以看見:桃園的協會悄悄成形,短短與小新攜手為下一代兒少鋪出一條更穩的參與之路;另一頭的臺南,也悄悄吹起一股熟悉的風。不是回憶,不是懷舊,而是另一位少代——昀臻,準備從過去的經驗出發,踏上同樣關於傳承、關於共創的路。
三位主角腳步的節奏不同,但方向一致。
離開發言席,改在背後撐傘
從少代轉變為培力工作者的角色並非易事,其中難免充滿許多困難與糾結。
首先,他們必須面對的是學業與培力工作的平衡。像是昀臻便在承接培力工作後,為了穩定協會而選擇暫時休學,短短也為同時兼顧課業與培力而延畢。
其次,培力經費與資源的多寡,與政府考核有著絕對的關聯。中央制定了許多考核指標來檢視培力單位;然而這些指標,並未全部貼合兒少的需求,協會常為了符合指標而被迫做出相關調整。
而這些指標是讓「願景被現實消磨』的原因之一。
為了符合指標的要求,兒少必須推動一定數量的議題,同時也必須進行兒童權利公約的校園與社區宣導。原本學校的課業與升學壓力就很大了,長期下來前述要求更會讓兒少代表蠟燭兩頭燒,引發負荷過載的問題。
雖然政府是因背負社會大眾的期待,才轉嫁許多不合理的成本到兒少及培力單位身上,但由於兒少及培力單位都缺乏試錯的空間,實際運作起來往往令人心力交瘁,甚至感到憤怒。而兒少或者培力工作者為了突破桎梏,相關爭取反而在政府眼中是「不聽話」與「麻煩」的體現。
其三,經營非營利組織有其難度。先不提創立過程中複雜的法規與行政流程,光是在龐雜行政庶務中,需不斷兼顧活動成效與組織永續就足夠令人煩惱。他們必須時常問自己:身為工作者能不能成為兒少支柱?組職是否能長久陪伴兒少?作為組織領導人能不能帶領協會走向共同目標?成為承包培力方案的廠商後,如果因為維權而與政府關係緊張,是不是就無法得到相關資源?
其四,身份的轉變也讓成就感有了不同的來源。以往擔任兒少代表時,他們總是自己關注相關議題,從尋找專家諮詢、搜集同儕意見、查詢相關數據、發想可行方案直到將落筆為提案單,通常在會議當下便知道提案的結果與展望,通常具有「即時回饋」的特性,成就感也隨之容易體會。
然而,成為培力工作者後,他們必須從「自己捕魚變為教人釣魚」,工作過程中不只需學會如何按耐住指導別人的慾望,留給少代自行探索與討論的空間,同時也必須對團體動力的運行更加敏銳,觀察何時是少代的卡關期,學習如何在適當時機對少代進行適當「引導」而非「指導」,逐漸將重點由自我能力的展現,轉變為適當且恰好的陪伴,時時提醒自己將舞台留給少代。
舉例來說,在政府會議已經身經百戰的他們,在陪同少代參與會議時(註二),面對政府的質疑,很自然會產生佐證與反駁的種種想法,也能夠輕易辨識出成人複雜言論下的深層含義,警覺對方是真心回應議題還是在敷衍兒少;但在現行體制下,他們並不能直接回應政府端──一方面,因他們的角色只是陪同少代列席,在會議規範上本就沒有主動發言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走過相同流程,深知學習表達意見、迅速分析與組織詞彙的應對需要時間練習。
但撐傘的人也會濕啊,會累啊。因此,他們內心時常出現掙扎:明明知道在這個時間點多說一點就能夠促成政策轉變,卻希望能使少代有多一點的發揮空間而選擇放棄。在那個會議關卡,他們究竟應以社會政策的轉變為主,把握機會來改善兒少處境,還是應以兒少的學習空間為主,給予足夠時間使兒少慢慢成長,都會是永遠需要反思與討論的靈魂拷問。
最後,在選擇以少代途徑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心中,有時難免覺得「這個頭銜好酷!」或是「感覺與眾不同」這都是很自然的心態。
這也讓部分少代覺得「效能感爆棚」,小小年紀竟能在與父母,甚至爺爺奶奶年齡相仿的高官面前一同討論公共政策,不免使有些兒少會自認:「贏過 99% 同齡人」,進而產生不合理的優越感,以自己能「嗆」政府官員感到自豪。
而培力者若因未設定明確的培力目標,或本身即是激進的倡議團體,而放任兒少代表大放厥詞,也就隨之容易有「泛政治化」的舉措,把提案討論變做政論節目;在缺乏完整的結構認知下,輕易地攻擊政府或是業務單位。但我們都知道這並非是「兒少表意權」的展現,而是在弱化公民社會,傷害了利益關係人之間的信任關係。
因此,主角們都知道,要成為培力者前必須先釐清自身的價值信念,釐清真正想要的著力點。當然,引導的能力需要練習,他們創立協會,也有一部分是希望藉由共學共創的過程,彼此增長培力的知能。
少代之路充滿挑戰,從政策限制到資源不足,三位培力工作者在成長過程中不僅面臨身分轉變的掙扎,還要在現實框架下找到突破的出口。為了打破這些困境,三人創立協會,希望打造一個以兒少為主體的支持平台,他們不僅重視平等對話,還積極探索新的培力模式,試圖讓兒少在自主與被賦權間取得平衡,找到適合成長的空間。
這不是完美的結局,而是打拼的中場。也因此,我們得繼續說下去——下一集,我們將帶大家走進三位主角攜手創造的新篇章。從會議室到街頭巷尾,從提案的紙上,到落實的現場,他們如何培力?讓「兒少參與」不會只停留在單純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