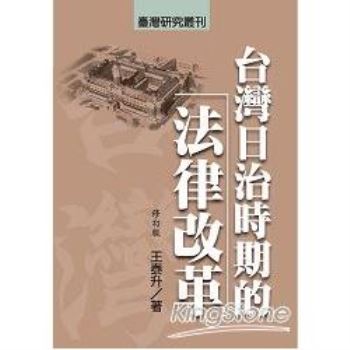內文選摘(節錄)
導論
第一節 「台灣研究」的一個新興議題
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法律發展,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戰後美國學界對於台灣的研究,原大多出於研究中國之需要,即一般所謂將台灣視為「中國研究」的代用品。以往西方歷史學者經常視台灣史為「中國地方史」,故總將關心焦點置於清朝中國統治下的台灣(1683-1895),而忽略台灣曾是戰前日本帝國的一部分(1895-1945)。美國許多對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或社會變遷感興趣的社會科學家,似乎也認為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的自日本手中轉由中國統治,已足以將其歷史發展截然二分為彼此不相干涉的兩個時期,以致於未能深刻地反省其社會本身戰前狀況與戰後發展所可能具有的延續關係。當時許多美國人類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更將這種把台灣等同於「中國」、輕忽台灣歷史發展上獨特性的學術傾向給強化了。按美國學者在1950及60年代,一方面因難以進入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進行實地研究,另一方面有關台灣傳統漢人(華人,亦有逕稱「中國人」者)社會的參考文獻又十分豐富,故將台灣視為從事「中國研究」理想的田野調查對象。
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的美國人類學者,固然對台灣社會曾被一個高效率的「非中國」政權統治五十年有所認知,但多半不太關注日本統治的這段時期,因為他們得先肯定「在台灣可以找到傳統中國(漢人)社會」這個必要的前提,以便將自己在台灣的田野調查活動合理化。這些學者認為他們在台灣所調查之特定地區的生活水準,儘管在物質方面已經隨著日本的統治而有所提升,但鄉村中傳統漢人社會的生活方式並未隨之改變。在上述強勢學說的籠罩下,某些研究台灣漢人社會法律發展的美國學者,也不免認為日本的殖民地法律對台灣人民的影響相當有限。
然而當研究的對象不再是「傳統中國(漢人)社會」,而是整個「台灣社會」時,前揭的研究取徑就不得不有所調整。正如部分原為「英國人」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那樣,部分原為「中國人」的漢人在台灣所建立起來的移民社會,多少已異於在中國原鄉的傳統漢人社會。事實上,至少大約要到1860年代,台灣的漢人才逐漸發展出所謂的「傳統中國社會」(其特性將於本書第一章加以說明)。
換句話說,清治晚期的台灣社會尚足以代表傳統中國社會,故有不少學者以此為前提,廣泛使用該時期台灣法律運作實況的資料,來探索傳統中國的法律。但接踵而來的問題卻是: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對台灣社會的影響,除了物質建設(例如鐵路、電力等)以外,果真那麼有限?
前述人類學者之認為日本統治影響有限,多半是針對傳統的親屬繼承事項而發,其研究主題不外是婚姻、收養、宗教、祭祀等,且研究區域多屬台灣鄉村。雖然以往的學說認為:傳統的農村結構因為有利於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經營,所以日本當局不願全盤改造台灣的鄉村社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設於台灣殖民地的法院,很可能已藉由司法判決之作成而改變台灣人某些有關親屬繼承的習慣。
即使認為台灣傳統中國式的親屬繼承事項未受日本法院判例太大的影響,也不宜遽然斷言當時台灣其他的民事生活事項亦原封不動地保存了漢人原有的(傳統中國的)習慣。誠如本書第五章所述,許多原有的「民事財產法」習慣,於日治時期已被轉化成西方式法律。況且台灣自1930、40年代即逐漸有都市化現象,使得當時城市與鄉村之間已存在著若干差異。因此,若欲觀察的對象是整個台灣社會,則所蒐集的資料,即不應單單著眼於親屬繼承事項,或僅僅針對鄉村地區。
最近美國學界對台灣的研究,已有逐漸自「中國研究」分離出來的趨勢,但台灣的法律發展,仍未被當成一個專門的議題來討論。事實上,早自1960年代晚期或1970年代初期,某些美國學者已注意到台灣社會發展的獨特性,亦即除了承認台灣與傳統中國在社會與文化上的傳承關係之外,也重新檢討台灣本身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產生之相對的「獨特」現象。今日台灣社會之形成,是否皆可一概追本溯源至傳統中國?抑或其已被傳統中國以外的勢力所改造?目前仍頗受爭議。探討這些問題的一個恰當的取徑,即是從日治時期切入。因為「對於那些強調(中國)文化連續性的人,日治時期是一座通往過去的橋樑;對於那些認為日治時期已重大地改變台灣的人,亦有必要顯示台灣在這些歲月裡已產生了什麼樣重要的轉變。」美國學術界迄今已有不少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的專論,但大多是針對政治、社會、經濟及教育等所作的研究,法律方面僅僅是在該研究所需的必要範圍內附帶提及。
當研究法律發展的眼界擴展至整個世界,而不再侷限於較狹隘的中國時,則戰前日本帝國在台灣所實施的西方式法律,就顯現出極高的學術價值。在極端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日本統治底下台灣的法律,只不過是「日本的」法律,且幾乎等於是「壞的」法律。但事實上,日本人引進台灣的,是一套已經日本化且殖民地化的西方式法律。回顧歷史,自19世紀後期,西方強權早已直接地強制其亞非殖民地人民接受西方的法律制度及觀念,或間接地誘使某些亞洲的獨立國家「繼受」西方法。1895年,日本獲得第一塊殖民地──台灣,且逐步在這個島嶼上,施行其甫自西方繼受而來的法律,台灣(及朝鮮)的經驗因此在眾多繼受近代西方法的案例中,顯現出某種獨特性,也就是說,西方式法律,竟然是由一個非西方的亞洲殖民主義強權所推行,藉以取代根深蒂固於殖民地台灣的傳統中國式法律。遺憾的是,目前有關繼受西方法之研究,似乎無視於台灣(及朝鮮)案例中的這項獨特性。
此外,令人疑惑的是,外國人可能因為文化與生活經驗的隔閡而無動於衷,但為什麼連台灣人本身也不關心「日治時期繼受西方法」這個與自身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恐怕在於國民黨政府過去長期地將台灣史研究視若蛇蠍,除非它依從官方觀點──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且須以『中國地方史』而非『台灣人本身的歷史』,來詮釋曾發生在這個島嶼上的所有社會現象」。結果,依官方的詮釋,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這段歷史,歸納起來只有二句話:「遭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剝削」,以及「在台灣的中國人,始終強烈反抗日本政府」。那麼當時的法律,也只是壓迫者邪惡的工具而已,有什麼值得深入探討的?進入1980年代,情勢才稍見改變。由於國民黨威權政府對台灣社會的控制力已相對減弱,以台灣為主體(不再依附於中國),且從台灣人民的立場作為歷史詮釋之基點的台灣史研究,逐漸在台灣島內取得生存發展的空間。今天已有許多學者認為,研究台灣史應摒棄過去「漢人本位」或「中國本位」的態度,宜把眼光延伸至台灣原住民族,以及台灣在整個世界大環境裡的定位,而非僅是注意其在「中國」內的處境。倘若能夠走出「中國史觀」的窠臼,則台灣由日本統治的五十年,絕對是值得仔細深究的關鍵年代。誠如近年來某些論著所指出的,日本人的統治已為台灣社會帶來激烈的變革,且持續影響著戰後台灣的發展。
類似的研究趨勢,也可在台灣的法學研究上窺見。長期以來,台灣法學界在討論「法制史」時,幾乎都排除了日治時期法律的存在。只有極少數的法學研究,曾於三十餘年前討論過殖民統治時代的法律,且總是將重點置於批判那些具有壓迫人民性質的殖民地法制。降至1980年代,開始有異於往昔的聲音。1986年,即台灣解除戒嚴的前一年,有兩位台灣法學者在公開的演講中表示:日本的殖民統治,對台灣的繼受西方式法典具有若干貢獻。雖然這並非該演講的主題,但願意公開肯定日治時期在法律史上應有的地位,實已蘊含相當的意義。特別是戰後台灣的法學界,向來一提及「繼受西方法」,馬上就聯想到中國政權──即清朝及嗣後的中華民國政府──自20世紀初開始推動的法制西方化。然而,問題的焦點若是「台灣的繼受西方法」,則台灣事實上在1895年至1945年間,並未被這兩個中國政權所統治。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個斷層呢?中國大陸法制的西方化,對於1945年以前的台灣社會而言,是另一個社會的經驗。我們固然無法否認:中國大陸在1945年以前的法制改革經驗,極可能影響到1945年(尤其是1949年)以後始自中國大陸移居台灣,並構成今日台灣社會一部分的「外省」族群。但更不應忘記:今日台灣的社會環境及多數人口,都是1945年以前日本統治下之台灣社會的延續。而台灣社會首次接觸近代西方式法律,正是19世紀末開始接受日本統治之時。
日本人做為「當事者」的另一造,就其於台灣殖民地所施行的法律,或許會有不同於台灣人的看法。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學界對台灣似乎欠缺研究的興趣。不過,戰前殖民主義發展史畢竟是日本近代史的重心之一,台灣殖民地的經營又是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諸如台灣人民對殖民地政府的反抗、日本對殖民地的經濟剝削等等,乃成為若干日本學者的研究主題,其中更不乏曾親身在台經歷殖民統治的學者。對於台灣殖民地的法律,戰後的日本也僅有少數學者,站在研究日本近代法史的立場,稍加討論。但近來已有某日本學術機構,擬利用台灣總督府檔案,研究日本殖民統治政策與台灣殖民地法制間的關係。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日本人,對其過去的殖民地法制進行研究。
導論
第一節 「台灣研究」的一個新興議題
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法律發展,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戰後美國學界對於台灣的研究,原大多出於研究中國之需要,即一般所謂將台灣視為「中國研究」的代用品。以往西方歷史學者經常視台灣史為「中國地方史」,故總將關心焦點置於清朝中國統治下的台灣(1683-1895),而忽略台灣曾是戰前日本帝國的一部分(1895-1945)。美國許多對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或社會變遷感興趣的社會科學家,似乎也認為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的自日本手中轉由中國統治,已足以將其歷史發展截然二分為彼此不相干涉的兩個時期,以致於未能深刻地反省其社會本身戰前狀況與戰後發展所可能具有的延續關係。當時許多美國人類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更將這種把台灣等同於「中國」、輕忽台灣歷史發展上獨特性的學術傾向給強化了。按美國學者在1950及60年代,一方面因難以進入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進行實地研究,另一方面有關台灣傳統漢人(華人,亦有逕稱「中國人」者)社會的參考文獻又十分豐富,故將台灣視為從事「中國研究」理想的田野調查對象。
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的美國人類學者,固然對台灣社會曾被一個高效率的「非中國」政權統治五十年有所認知,但多半不太關注日本統治的這段時期,因為他們得先肯定「在台灣可以找到傳統中國(漢人)社會」這個必要的前提,以便將自己在台灣的田野調查活動合理化。這些學者認為他們在台灣所調查之特定地區的生活水準,儘管在物質方面已經隨著日本的統治而有所提升,但鄉村中傳統漢人社會的生活方式並未隨之改變。在上述強勢學說的籠罩下,某些研究台灣漢人社會法律發展的美國學者,也不免認為日本的殖民地法律對台灣人民的影響相當有限。
然而當研究的對象不再是「傳統中國(漢人)社會」,而是整個「台灣社會」時,前揭的研究取徑就不得不有所調整。正如部分原為「英國人」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那樣,部分原為「中國人」的漢人在台灣所建立起來的移民社會,多少已異於在中國原鄉的傳統漢人社會。事實上,至少大約要到1860年代,台灣的漢人才逐漸發展出所謂的「傳統中國社會」(其特性將於本書第一章加以說明)。
換句話說,清治晚期的台灣社會尚足以代表傳統中國社會,故有不少學者以此為前提,廣泛使用該時期台灣法律運作實況的資料,來探索傳統中國的法律。但接踵而來的問題卻是: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對台灣社會的影響,除了物質建設(例如鐵路、電力等)以外,果真那麼有限?
前述人類學者之認為日本統治影響有限,多半是針對傳統的親屬繼承事項而發,其研究主題不外是婚姻、收養、宗教、祭祀等,且研究區域多屬台灣鄉村。雖然以往的學說認為:傳統的農村結構因為有利於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經營,所以日本當局不願全盤改造台灣的鄉村社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設於台灣殖民地的法院,很可能已藉由司法判決之作成而改變台灣人某些有關親屬繼承的習慣。
即使認為台灣傳統中國式的親屬繼承事項未受日本法院判例太大的影響,也不宜遽然斷言當時台灣其他的民事生活事項亦原封不動地保存了漢人原有的(傳統中國的)習慣。誠如本書第五章所述,許多原有的「民事財產法」習慣,於日治時期已被轉化成西方式法律。況且台灣自1930、40年代即逐漸有都市化現象,使得當時城市與鄉村之間已存在著若干差異。因此,若欲觀察的對象是整個台灣社會,則所蒐集的資料,即不應單單著眼於親屬繼承事項,或僅僅針對鄉村地區。
最近美國學界對台灣的研究,已有逐漸自「中國研究」分離出來的趨勢,但台灣的法律發展,仍未被當成一個專門的議題來討論。事實上,早自1960年代晚期或1970年代初期,某些美國學者已注意到台灣社會發展的獨特性,亦即除了承認台灣與傳統中國在社會與文化上的傳承關係之外,也重新檢討台灣本身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產生之相對的「獨特」現象。今日台灣社會之形成,是否皆可一概追本溯源至傳統中國?抑或其已被傳統中國以外的勢力所改造?目前仍頗受爭議。探討這些問題的一個恰當的取徑,即是從日治時期切入。因為「對於那些強調(中國)文化連續性的人,日治時期是一座通往過去的橋樑;對於那些認為日治時期已重大地改變台灣的人,亦有必要顯示台灣在這些歲月裡已產生了什麼樣重要的轉變。」美國學術界迄今已有不少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的專論,但大多是針對政治、社會、經濟及教育等所作的研究,法律方面僅僅是在該研究所需的必要範圍內附帶提及。
當研究法律發展的眼界擴展至整個世界,而不再侷限於較狹隘的中國時,則戰前日本帝國在台灣所實施的西方式法律,就顯現出極高的學術價值。在極端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日本統治底下台灣的法律,只不過是「日本的」法律,且幾乎等於是「壞的」法律。但事實上,日本人引進台灣的,是一套已經日本化且殖民地化的西方式法律。回顧歷史,自19世紀後期,西方強權早已直接地強制其亞非殖民地人民接受西方的法律制度及觀念,或間接地誘使某些亞洲的獨立國家「繼受」西方法。1895年,日本獲得第一塊殖民地──台灣,且逐步在這個島嶼上,施行其甫自西方繼受而來的法律,台灣(及朝鮮)的經驗因此在眾多繼受近代西方法的案例中,顯現出某種獨特性,也就是說,西方式法律,竟然是由一個非西方的亞洲殖民主義強權所推行,藉以取代根深蒂固於殖民地台灣的傳統中國式法律。遺憾的是,目前有關繼受西方法之研究,似乎無視於台灣(及朝鮮)案例中的這項獨特性。
此外,令人疑惑的是,外國人可能因為文化與生活經驗的隔閡而無動於衷,但為什麼連台灣人本身也不關心「日治時期繼受西方法」這個與自身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恐怕在於國民黨政府過去長期地將台灣史研究視若蛇蠍,除非它依從官方觀點──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且須以『中國地方史』而非『台灣人本身的歷史』,來詮釋曾發生在這個島嶼上的所有社會現象」。結果,依官方的詮釋,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這段歷史,歸納起來只有二句話:「遭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剝削」,以及「在台灣的中國人,始終強烈反抗日本政府」。那麼當時的法律,也只是壓迫者邪惡的工具而已,有什麼值得深入探討的?進入1980年代,情勢才稍見改變。由於國民黨威權政府對台灣社會的控制力已相對減弱,以台灣為主體(不再依附於中國),且從台灣人民的立場作為歷史詮釋之基點的台灣史研究,逐漸在台灣島內取得生存發展的空間。今天已有許多學者認為,研究台灣史應摒棄過去「漢人本位」或「中國本位」的態度,宜把眼光延伸至台灣原住民族,以及台灣在整個世界大環境裡的定位,而非僅是注意其在「中國」內的處境。倘若能夠走出「中國史觀」的窠臼,則台灣由日本統治的五十年,絕對是值得仔細深究的關鍵年代。誠如近年來某些論著所指出的,日本人的統治已為台灣社會帶來激烈的變革,且持續影響著戰後台灣的發展。
類似的研究趨勢,也可在台灣的法學研究上窺見。長期以來,台灣法學界在討論「法制史」時,幾乎都排除了日治時期法律的存在。只有極少數的法學研究,曾於三十餘年前討論過殖民統治時代的法律,且總是將重點置於批判那些具有壓迫人民性質的殖民地法制。降至1980年代,開始有異於往昔的聲音。1986年,即台灣解除戒嚴的前一年,有兩位台灣法學者在公開的演講中表示:日本的殖民統治,對台灣的繼受西方式法典具有若干貢獻。雖然這並非該演講的主題,但願意公開肯定日治時期在法律史上應有的地位,實已蘊含相當的意義。特別是戰後台灣的法學界,向來一提及「繼受西方法」,馬上就聯想到中國政權──即清朝及嗣後的中華民國政府──自20世紀初開始推動的法制西方化。然而,問題的焦點若是「台灣的繼受西方法」,則台灣事實上在1895年至1945年間,並未被這兩個中國政權所統治。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個斷層呢?中國大陸法制的西方化,對於1945年以前的台灣社會而言,是另一個社會的經驗。我們固然無法否認:中國大陸在1945年以前的法制改革經驗,極可能影響到1945年(尤其是1949年)以後始自中國大陸移居台灣,並構成今日台灣社會一部分的「外省」族群。但更不應忘記:今日台灣的社會環境及多數人口,都是1945年以前日本統治下之台灣社會的延續。而台灣社會首次接觸近代西方式法律,正是19世紀末開始接受日本統治之時。
日本人做為「當事者」的另一造,就其於台灣殖民地所施行的法律,或許會有不同於台灣人的看法。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學界對台灣似乎欠缺研究的興趣。不過,戰前殖民主義發展史畢竟是日本近代史的重心之一,台灣殖民地的經營又是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諸如台灣人民對殖民地政府的反抗、日本對殖民地的經濟剝削等等,乃成為若干日本學者的研究主題,其中更不乏曾親身在台經歷殖民統治的學者。對於台灣殖民地的法律,戰後的日本也僅有少數學者,站在研究日本近代法史的立場,稍加討論。但近來已有某日本學術機構,擬利用台灣總督府檔案,研究日本殖民統治政策與台灣殖民地法制間的關係。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日本人,對其過去的殖民地法制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