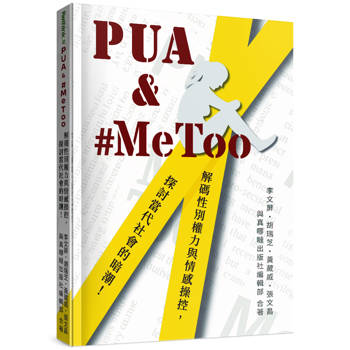第七章
加害者的重生與受害者的選擇
在這一章,我們試圖探討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當一位曾犯下性侵罪行的加害者(尤其是名人)在服刑與接受治療後,想要重新回到社會時,這條路應該怎麼走?而作為曾經受傷的人,受害者是否也有重新選擇的空間?
我們在此明確聲明:絕無縱容或同情加害者之意;對任何違法行為我們都不抱輕易寬恕的心態,但也不得忽視法律與心理復健所帶來的真正意義。
而對於曾經歷類似創傷的您,我想對您說:無論傷痛多麼深重,您並非孤單一人。願您在這裡找到理解與支持的力量,同時也請放心,若這一章的內容讓您感到不適,您完全可以選擇跳過,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片安寧。
一、為何談完受害者後,我們還要談加害者?
前幾章中,我們將重點放在受害者身上:創傷的影響、司法與社會支持的缺口,以及我們如何避免二度傷害。但僅有受害者觀點仍不足以帶來完整修復。因為一個社會的修復,不只是止痛,更包含預防傷害的再度發生。若無法處理加害者的轉化與監督,就無法真正降低再犯風險,也會讓受害者的安全感始終岌岌可危。本章並非為任何人脫罪,而是站在公共安全與社會復原的角度出發,談責任的落實,也談未竟的改變。
當一位具有高度知名度的加害者選擇重回舞台時,他的每個舉動都不只是個人的選擇,更牽動著整體社會對司法正義與悔改真意的信任感。
一方面,社會需要看見「真正的悔改與承擔」——他必須公開面對當初的傷害、誠實回應媒體與公眾的質疑,並接受司法與心理治療後的成效檢驗,才能重建公信力;否則,他的「回歸」就淪為一場自我包裝的秀,對制度與他人都毫無幫助。
另一方面,若我們對這樣的回歸態度輕忽、草率放行,便等同於向所有曾在深淵邊緣掙扎、勇敢站起來的受害者宣告:你的痛苦不重要,你的聲音不值得被傾聽,你們守護正義的努力不被尊重。如此一來,受害者的療癒道路不但無法往前,更可能在社會輿論與制度失信中再次蒙受二度傷害。
當一位知名人物因性侵被判刑,他所面對的不僅是法律責任,更是一場關於人性與信任的長期修復歷程。法律的審判與刑責或許畫下了制度上的句點,卻無法抹去受害者身心的餘震,也無法立刻重建社會對他的信任。想重新開始,不只是服完刑期這麼簡單,而是必須在法律認定、內在轉化與公眾觀感三個方向同時深耕、同步前行。
或許在危機處理與信任重建的領域常用的「四R原則」──也就是認錯(recognition)、負責(responsibility)、懺悔(remorse)與補償(restitution)──可以提供一個衡量誠意的基本框架。真正的道歉不是表演出來的語句,而是一連串具體行動的累積。
刑罰之外,責任還沒結束
法律定罪只是起點。加害者除了刑期與罰金,還需接受心理治療、電子監控、定期報到等社區監督措施。《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 2023 年進行修法,更強化了刑中與刑後的治療流程。此外,透過民事訴訟與修復式司法機制,受害者也有機會獲得應有的賠償與道歉。對於名人而言,這些過程是否誠實面對、是否配合落實,將直接影響大眾對其悔意的判斷。
心理轉化:從認錯到修復
治療不是走個過場、流於形式而已,加害者必須自行拆解錯誤認知與建立自我約束的過程。以認知行為治療(CBT)及再犯預防訓練為核心的方法,能幫助加害者真正認識行為背後的動機,並從根本調整其心態。對名人來說,公開的治療歷程不只是個人療癒的過程,也是一種對社會負責的表態。
公共修復的難題
真正的悔改不是一則聲明,而是一連串可驗證的行動。從道歉、承擔、悔意到補償,每一項都必須有跡可循。某些受害者需要的不是抽象的「我改了」,而是具體可見的「我在改」。公開說明賠償進度、公益投入與個人限制,是建立信任的起點。尤其對名人而言,復出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社會願不願意再次給機會的結果。
結束與開始
整合多項實務與研究成果的「參考性建議」,從真誠悔改到有條件復出,可能至少需歷經三個階段:
沉澱期(至少前六個月):正式道歉、暫停商業活動、開始治療與法律責任的履行。
修復期(至少一年半):持續公開治療與賠償進度,接受媒體專訪聚焦受害者觀點。
試水期(至少第三年):嘗試低曝光度的復出方式,如幕後工作或非營利演出。
每一步都必須穩健,任何倉促都可能重創已建立的修復努力。
離開鎂光燈,也是重建的方式
有些名人難以放下掌聲,彷彿失去曝光就等於失去價值。然而,在舞台下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悔改的一部分。無論是轉向幕後、投入公益或跨界轉職,真正的改變在於不再依賴光環,而是學會在無人喝采的地方,繼續活出責任與誠意。
學會面對「不被原諒」
不是所有人都會選擇原諒加害人,甚至有些人永遠無法原諒。這不是加害者能掌控的事。重建社會信任,是他們該努力的方向,但是否原諒,永遠屬於受害者的自由與權利。悔改的路上,必須學會尊重拒絕,並持續履行責任。
重啟人生的三條主線
重生不是口號,而是三個層面的交叉點:
完整執行法律責任,
真實完成心理重建,
長期展現具體補償與社會行動。
唯有這樣的「三線並行」,加害者才可能真正踏上重生的道路——那或許不再是眾人矚目的舞台,而是更誠實、謙卑、負責任的生命場域。
二、當重生的光照進傷痛之地──受害者如何面對加害者的回歸
當加害者選擇「悔改」這條路,他所放出的每一道希望的光芒,對某些受害者來說,卻可能反射成刺眼的回光──提醒著那道無法遺忘的傷痕,提醒著社會往往關心「他變了沒」,卻很少問「你還好嗎」。雖然從台灣目前名人涉案的例子可以看出,社會輿論似乎無法原諒加害者,但我們不妨假設有一天,當社會開始讚賞一個加害者「已經悔改」的改變時,受害者該如何自處?
決定權永遠屬於受害者
當加害者高調宣稱「我已經重生、我願意承擔責任」,那道看似光明的訊號,往往會成為受害者心中最刺眼的逆光。它似乎在提醒著受害者,那段深深刺入骨髓的傷痛從未被抹去。
因此無論媒體如何渲染、輿論如何呼喊,甚至連最親近的家人或朋友都可能傾向「要不要原諒」、「要不要重啟對話」這類聲音時,真正關鍵的選擇——是否原諒、是否再見面、是否參與修復式司法——都只能由受害者自己來做決定。這並非純粹的道德問題,而是關乎受害者安全與情緒復原的真實課題。
時間感的錯位,是受害者難以跨越的痛
加害者往往宣稱「我已經沉澱多年」,他口中的「多年」或許只有短短數月;然而,受害者可能在最初的震驚與恐懼中度過無數個漫長而痛苦的夜晚。兩者時間感的錯位,使得外界的「他好了嗎?」對話對受害者來說,無比刺耳,因為這個問題永遠對不上「我好了沒?」的節拍。
更有甚者,當加害者在鏡頭前理性地談責任、談補償時,受害者的身體仍會立即發出警報:心悸、出汗、胃痛。(創傷經歷並不僅存於語意或敘事記憶declarative memory,更深植於隱性或程序性記憶系統中──這類記憶不需要經過有意「回想」,而是由外在線索如加害者的面孔、聲音、語調自動喚起。)這些生理反應不需要任何語言解釋,它們只是身體最誠實的記憶——記得危險、記得恐懼、記得那些隱秘的夜晚。
加害者的重生與受害者的選擇
在這一章,我們試圖探討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當一位曾犯下性侵罪行的加害者(尤其是名人)在服刑與接受治療後,想要重新回到社會時,這條路應該怎麼走?而作為曾經受傷的人,受害者是否也有重新選擇的空間?
我們在此明確聲明:絕無縱容或同情加害者之意;對任何違法行為我們都不抱輕易寬恕的心態,但也不得忽視法律與心理復健所帶來的真正意義。
而對於曾經歷類似創傷的您,我想對您說:無論傷痛多麼深重,您並非孤單一人。願您在這裡找到理解與支持的力量,同時也請放心,若這一章的內容讓您感到不適,您完全可以選擇跳過,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片安寧。
一、為何談完受害者後,我們還要談加害者?
前幾章中,我們將重點放在受害者身上:創傷的影響、司法與社會支持的缺口,以及我們如何避免二度傷害。但僅有受害者觀點仍不足以帶來完整修復。因為一個社會的修復,不只是止痛,更包含預防傷害的再度發生。若無法處理加害者的轉化與監督,就無法真正降低再犯風險,也會讓受害者的安全感始終岌岌可危。本章並非為任何人脫罪,而是站在公共安全與社會復原的角度出發,談責任的落實,也談未竟的改變。
當一位具有高度知名度的加害者選擇重回舞台時,他的每個舉動都不只是個人的選擇,更牽動著整體社會對司法正義與悔改真意的信任感。
一方面,社會需要看見「真正的悔改與承擔」——他必須公開面對當初的傷害、誠實回應媒體與公眾的質疑,並接受司法與心理治療後的成效檢驗,才能重建公信力;否則,他的「回歸」就淪為一場自我包裝的秀,對制度與他人都毫無幫助。
另一方面,若我們對這樣的回歸態度輕忽、草率放行,便等同於向所有曾在深淵邊緣掙扎、勇敢站起來的受害者宣告:你的痛苦不重要,你的聲音不值得被傾聽,你們守護正義的努力不被尊重。如此一來,受害者的療癒道路不但無法往前,更可能在社會輿論與制度失信中再次蒙受二度傷害。
當一位知名人物因性侵被判刑,他所面對的不僅是法律責任,更是一場關於人性與信任的長期修復歷程。法律的審判與刑責或許畫下了制度上的句點,卻無法抹去受害者身心的餘震,也無法立刻重建社會對他的信任。想重新開始,不只是服完刑期這麼簡單,而是必須在法律認定、內在轉化與公眾觀感三個方向同時深耕、同步前行。
或許在危機處理與信任重建的領域常用的「四R原則」──也就是認錯(recognition)、負責(responsibility)、懺悔(remorse)與補償(restitution)──可以提供一個衡量誠意的基本框架。真正的道歉不是表演出來的語句,而是一連串具體行動的累積。
刑罰之外,責任還沒結束
法律定罪只是起點。加害者除了刑期與罰金,還需接受心理治療、電子監控、定期報到等社區監督措施。《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 2023 年進行修法,更強化了刑中與刑後的治療流程。此外,透過民事訴訟與修復式司法機制,受害者也有機會獲得應有的賠償與道歉。對於名人而言,這些過程是否誠實面對、是否配合落實,將直接影響大眾對其悔意的判斷。
心理轉化:從認錯到修復
治療不是走個過場、流於形式而已,加害者必須自行拆解錯誤認知與建立自我約束的過程。以認知行為治療(CBT)及再犯預防訓練為核心的方法,能幫助加害者真正認識行為背後的動機,並從根本調整其心態。對名人來說,公開的治療歷程不只是個人療癒的過程,也是一種對社會負責的表態。
公共修復的難題
真正的悔改不是一則聲明,而是一連串可驗證的行動。從道歉、承擔、悔意到補償,每一項都必須有跡可循。某些受害者需要的不是抽象的「我改了」,而是具體可見的「我在改」。公開說明賠償進度、公益投入與個人限制,是建立信任的起點。尤其對名人而言,復出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社會願不願意再次給機會的結果。
結束與開始
整合多項實務與研究成果的「參考性建議」,從真誠悔改到有條件復出,可能至少需歷經三個階段:
沉澱期(至少前六個月):正式道歉、暫停商業活動、開始治療與法律責任的履行。
修復期(至少一年半):持續公開治療與賠償進度,接受媒體專訪聚焦受害者觀點。
試水期(至少第三年):嘗試低曝光度的復出方式,如幕後工作或非營利演出。
每一步都必須穩健,任何倉促都可能重創已建立的修復努力。
離開鎂光燈,也是重建的方式
有些名人難以放下掌聲,彷彿失去曝光就等於失去價值。然而,在舞台下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悔改的一部分。無論是轉向幕後、投入公益或跨界轉職,真正的改變在於不再依賴光環,而是學會在無人喝采的地方,繼續活出責任與誠意。
學會面對「不被原諒」
不是所有人都會選擇原諒加害人,甚至有些人永遠無法原諒。這不是加害者能掌控的事。重建社會信任,是他們該努力的方向,但是否原諒,永遠屬於受害者的自由與權利。悔改的路上,必須學會尊重拒絕,並持續履行責任。
重啟人生的三條主線
重生不是口號,而是三個層面的交叉點:
完整執行法律責任,
真實完成心理重建,
長期展現具體補償與社會行動。
唯有這樣的「三線並行」,加害者才可能真正踏上重生的道路——那或許不再是眾人矚目的舞台,而是更誠實、謙卑、負責任的生命場域。
二、當重生的光照進傷痛之地──受害者如何面對加害者的回歸
當加害者選擇「悔改」這條路,他所放出的每一道希望的光芒,對某些受害者來說,卻可能反射成刺眼的回光──提醒著那道無法遺忘的傷痕,提醒著社會往往關心「他變了沒」,卻很少問「你還好嗎」。雖然從台灣目前名人涉案的例子可以看出,社會輿論似乎無法原諒加害者,但我們不妨假設有一天,當社會開始讚賞一個加害者「已經悔改」的改變時,受害者該如何自處?
決定權永遠屬於受害者
當加害者高調宣稱「我已經重生、我願意承擔責任」,那道看似光明的訊號,往往會成為受害者心中最刺眼的逆光。它似乎在提醒著受害者,那段深深刺入骨髓的傷痛從未被抹去。
因此無論媒體如何渲染、輿論如何呼喊,甚至連最親近的家人或朋友都可能傾向「要不要原諒」、「要不要重啟對話」這類聲音時,真正關鍵的選擇——是否原諒、是否再見面、是否參與修復式司法——都只能由受害者自己來做決定。這並非純粹的道德問題,而是關乎受害者安全與情緒復原的真實課題。
時間感的錯位,是受害者難以跨越的痛
加害者往往宣稱「我已經沉澱多年」,他口中的「多年」或許只有短短數月;然而,受害者可能在最初的震驚與恐懼中度過無數個漫長而痛苦的夜晚。兩者時間感的錯位,使得外界的「他好了嗎?」對話對受害者來說,無比刺耳,因為這個問題永遠對不上「我好了沒?」的節拍。
更有甚者,當加害者在鏡頭前理性地談責任、談補償時,受害者的身體仍會立即發出警報:心悸、出汗、胃痛。(創傷經歷並不僅存於語意或敘事記憶declarative memory,更深植於隱性或程序性記憶系統中──這類記憶不需要經過有意「回想」,而是由外在線索如加害者的面孔、聲音、語調自動喚起。)這些生理反應不需要任何語言解釋,它們只是身體最誠實的記憶——記得危險、記得恐懼、記得那些隱秘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