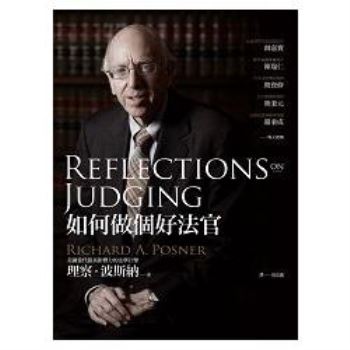第一章 通往第爾本南街219號之路
本章標題並不像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或艾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的《前往芬蘭車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那麼戲劇化;芝加哥第爾本南街(South Dearborn Street)219號,是美國上訴法院第七巡迴庭的地址,恰好意外地成為我職業生涯的終點。而我走過的「路」能夠提供一些洞見,藉以瞭解聯邦司法體系複雜化的過程。
教育與早年的職業
我在一九五九年十六歲時進入耶魯學院(Yale College),跳過了中學的最後一年。我進耶魯沒有什麼更好的理由,只因為我父親從《紐約時報》上看到,哈佛與耶魯招收中學三年畢業的小孩(芝加哥大學長期以來就收只念過兩年中學的學生,但在當時因為我成長的地方,對我來說哈德遜河以西的地方根本不存在)。我向哈佛與耶魯提出申請,哈佛拒絕了我,耶魯錄取我,所以我進到耶魯。那時候我比較想去哈佛(那是個錯誤,我稍後會提到),而且如果我繼續留在中學念第四年,然後再申請,我可能會被錄取;但我想要繼續前進。我很訝異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完全不急著確立自己的生涯規畫,或者根本就不自己做生涯的決定。
我在耶魯主修英文,文學長期以來都是我最喜愛的科目,部分原因在於我母親是中學英文老師,我才三歲(也有可能更早)時,她就唸荷馬與莎士比亞給我聽。新評論主義(The New Criticism)在我就讀學院時正值全盛期,而耶魯正是其重鎮;新評論主義不重視以自傳與歷史方法研究文學,而將文學作品視為一種獨立存在的美學客體,可加以理解並賞析,讀者毋須知道太多作者個人資訊或其時代背景。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一位著名的新評論主義者,當時是我的資深論文指導人(我的論文以一本書的篇幅研究葉慈〔W. B. Yeats〕晚期的詩作)。當時我對於新評論主義的方法有極大的熱誠,現在仍然如此。我提到這件事是因為那影響了我的司法方法,若不是它,我無法成為細膩的讀者,而能詮釋複雜的文件。還有一點,新評論主義方法讓我脫離過度依賴歷史作為理解文件的指引的限制。
我不認為新評論主義在哈佛會有多大影響力,加上耶魯事實上較著重大學部的教育,這讓我很感謝哈佛當初拒絕我的申請。
耶魯畢業後我直接進入哈佛法學院。我對法律並無熾熱的興趣,但我父親是個律師(也是個生意人),而法律當時是許多人設定的職業選擇,今天依然如此。雖然我喜愛文學,卻無意靠著寫作謀生,也沒興趣執教。我也申請了耶魯法學院並獲得錄取,但最後認定哈佛比較有挑戰性;它不會像耶魯法學院過去與現在那樣把學生當孩子寵。我想我做了正確的選擇。
我喜愛在哈佛法學院的第一年,我喜歡它的殘酷。哈佛把最好的老師都排在第一年,而他們確實非常厲害,儘管冷酷、苛求,有時候還有些討厭。那一年結束時,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覺得自己顯然變得比前一年的我更聰明了。我也發展出一種尊敬法律與法律人(至少是哈佛法學院教職員所投射出來的法律人性格)的情感,而且特別看重普通法,那是第一年的主要科目。第二年與第三年的課程就沒那麼有趣了。(有些課教得很爛,也就是那時我才發現法學院把它最好的老師都排在大一課程。)我退掉了大二的許多課程(所以我的成績掉下來,而我在大三變成較認真的學生),並且將最後兩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哈佛法學論叢》(Harvard Law Review)的工作上;附帶一提,那是一個真正菁英領導的組織,社員資格完全是基於分數決定的(現在已非如此),而且雖然法學論叢的會長是由會員選舉的,但沒有任何政治活動(現在也已非如此)。有些微的傾向選舉最好的學生,只要他在擔任論叢工作時確實認真盡責。
我原本以為我會在紐約執業(我出生在紐約,成長的過程住過紐約與斯卡斯代爾〔Scarsdale〕),儘管我在大一與大二暑假時都未到法律事務所打工;在那個年代,暑期的法律事務所打工尚屬少見,而我也沒有應徵。我對法律教學沒有興趣,也沒想過會成為法官,雖然我依稀有點印象自己曾經想過若能成為一名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應該會很有趣。我也不曉得該怎麼做才能成為一個法官。
保羅.福隆德(Paul Freund)是哈佛法學院很有名的教授,大法官布瑞南(William Brennan,哈佛法學院的校友)委託他每年幫忙挑選兩名法官助理,而他問我願不願意擔任,我同意了。我必須冒著有些不敬的風險說,我發現聯邦最高法院實在不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機構。我很驚訝地發現,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意見書並不完全是由他們自己寫的(道格拉斯大法官〔William Douglas〕確實自己寫, 但他的意見書是最弱的,不是因為他笨,而是因為他的行文乏味);哈佛法學院教授雖然對自由派大法官嚴厲批判,但還沒有讓法律助理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在準備擔任布瑞南的助理時,我讀了許多他的意見書,而且印象深刻;直到後來我才知道,當中最好的意見書都是由他的前任助理所寫,也是一位優秀的哈佛法學院畢業生,名字是丹尼斯.里昂斯(Dennis Lyons)。
布瑞南曾經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律師,後來也成為新澤西州最高法院非常傑出的法官。我很確定他寫過很好的司法意見書,也確實有人告訴我,在他服務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期間,有幾年他的助理所寫的意見書初稿他覺得不滿意,便自己寫,而且那些意見書寫得非常好。我想大部分的聯邦上訴法院法官都至少能寫出還可以的意見書。但也的確,法官助理是由法官選任的,不像法官那樣由政治人物所選,所以比起法官,法官助理時常更是稱職的法律分析者與寫作者。大部分的法官不太喜歡寫,比較喜歡審閱並編輯助理的意見初稿。這種編輯有時候是很輕微的。
在我服務的那時候(一九六二年那一審期),最高法院的工作步調很慢;我那一年勞力的程度比先前幾年都更低。我利用晚上與週末讀了很多文學,特別是英國與美國的經典小說,從狄更斯到福克納,因為我在耶魯念書時著重詩與戲劇,那是新評論主義偏好的主題。我當時真的對法律(尚)不太感興趣,甚至曾突發奇想(雖然很快放棄這麼想)脫離法律,去拿個英國文學研究所的學位。但很偶然的,就在助理生涯快結束時,我進到紐約一家大型法律事務所(寶維斯〔Paul Weiss〕)當受僱律師,我的工作是擔任一位非常卓越而能幹的聯邦貿易委員(Federal Trade Commissioner)菲力普.艾爾曼(Philip Elman)(曾任大法官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 〕的助理,而且長期擔任聯邦檢察總長的幕僚)。我為他工作了兩年,學到很多;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律師。
擔任布瑞南大法官助理期間,我在一件重要的銀行合併案上對反托拉斯法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這個興趣在為聯邦貿易委員會工作時再度加深,該機構管轄反托拉斯案件與消費者保護案件;我覺得消費者保護也很有趣。在艾爾曼的指導與其他幕僚的協助下,我撰寫委員會的聲明,發布一項強制在香菸包裝與廣告上增加健康警語的規則,並撰寫此等規則的辯護理由。雖然這項規則很快被國會推翻,但也成為最終成功抑制吸菸的管制努力之開端。
任職於委員會時,我與首席經濟學家威拉德.穆勒(Willard Mueller)變成好友,而且開始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奇怪的是,這種興趣的種子或許在我參加《哈佛法學論叢》的第一個月就種下了,當時我偶然地被指派校對德瑞克.包克(Derek Bok)一份反托拉斯長篇著作的引註(當時他是哈佛法學教授,後來成為法學院院長,而後成為哈佛校長),在那篇著作中他討論寡占的經濟理論。我從未聽過寡占理論,但我發現那相當吸引人,而且我也將之運用在我為大法官布瑞南撰寫的銀行併購案件意見書裡。
離開艾爾曼的辦公室之後,我進了檢察總長的辦公室,在那裡待了兩年多,寫作許多書狀,並在聯邦最高法院進行六件案子的辯論。我的工作重點在於反托拉斯與管制,而我對這些領域變得非常感興趣。但我不認為政府的書狀或口頭辯論影響了判決,無論造成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的因素為何,都不是律師的辯論。所以我在檢察總長辦公室任職兩年後劃下了句點,而我開始得到教職的面試機會,我決定試著教書。(執業對我沒有吸引力。我也不記得為什麼,但我猜那是因為我不想繼續為別人工作,也不想為不是我自己而是老闆或客戶的立場辯護。)就在我接受史丹佛大學的邀請並開始教職前,我在政府單位再工作了一年(同樣是收到邀請,而非自己應徵),擔任電信政策總統專案小組幕僚的工作。那是一份很棒的工作,增強了我在反托拉斯與管制上的興趣,也加強我對於經濟分析運用的興趣,雖然在這方面我當時還是個初學者,不太瞭解此等領域的法律應用。那個專案小組的研究主管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蘭德公司(RAND)經濟學者,名為勒蘭.強森(Leland Johnson),大幅激發我對經濟學的興趣。
由於我在第十章將討論司法與學術之間的關係,在此值得特別說明某次說服我嘗試法律教學的對話。當時史丹佛法學院院長貝利斯.曼寧(Bayless Manning)是一個很有才華也很有魅力的企業律師。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在檢察總長辦公室工作的第二年,曼寧(當時我未曾遇過他,也未曾聽過他)打電話或寫信給我,表示他到了華盛頓特區,希望我能跟他吃個午飯。我說當然好,之後我們共進午餐。時值阿拉伯與以色列六日戰爭(Six-Day War)剛結束,我們的討論話題都圍繞著戰爭。我著迷於他的興趣與知識的廣博,並且開始想或許法學教授是比律師更有趣的人。(我並不知道曼寧對外交事務有特別深的興趣;他後來成為外交關係協會主席)。但是當他試圖引發我對法律教學的興趣時,我表示我沒辦法想像自己寫作學術文章。他說不要緊,法學教授可以用其他方式貢獻於法律。任何人如果今天對法學教師的招募者這麼說,可能會立刻被排除考慮。在一九六○年代,法學界比較認同法律實務界,而非大學的學術文化;今日則變得非常「學術化」,導致法律教授與法律實務工作者(包括法官)的分化,這也讓非常需要協助以因應日益升高複雜性的挑戰的司法機構得不到幫助。
在史丹佛待了一年之後,當時我有幸認識了亞隆.德瑞特(Aaron Director)與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們兩位是傑出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德瑞特退休後回到灣區,並在史丹佛法學院有個辦公室;而斯蒂格勒在我於史丹佛任教的時間,恰好在那裡擔任訪問學者),於是我接受了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一項邀請,因為那裡有一群有興趣跟法學教授往來,也對法律有興趣的經濟學者。從那之後,我開始講授新興的法律經濟分析,並出版學術著作。我也從事許多諮詢工作,特別是反托拉斯法,也涉及公共事業與運輸業管制,例如航空與鐵路產業。我也提供環境管制上的建言,以及為福特政府命運不濟的價格管制提供建議。
一九八一年聯邦司法任命程序
我從沒想過會成為一位法官。但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某一天,我在雷斯康顧問公司(Lexecon Inc.)的辦公室內,這家公司是我跟威廉.藍德斯(William Landes)與安德魯.羅森菲爾德(Andrew Rosenfield)在一九七七年設立的,那天我的一個朋友同時也是之前史丹佛的同事,也就是當時獲得雷根總統任命擔任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主管的威廉.巴斯特(William Baxter),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有興趣接受任命到第七巡迴庭。我說沒興趣,而他說他也想過我會這麼回答。但是當他要掛電話時,我說,好吧,給我二十四小時想一想,而他同意了。我思考這件事,並且告訴我妻子(她願意接受收入顯著減少,我在學術機構有豐富的薪酬,顧問公司那裡也賺很多),也跟我父親與艾爾曼談過,他們兩位都鼓勵我接受法官職位;二十四小時期限到了之前,我跟巴斯特說,我想要再仔細想想前途。大約一星期後,我說我接受。我認為薪水減少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擔任法官還是可以兼職教書,所以能有一份教書的收入,貼補法官的薪資,儘管比擔任全職教職少。而我那時也對諮詢服務感到厭煩,部分原因在於我的時間不是花在分析工作,而是跟客戶推銷我們的服務,因為我是公司的資深人員。
我也覺得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應該是有趣且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聯邦案件具多樣性與重要性,我將有機會在真實世界的情境下運用經濟分析,以及學術寫作上用不到的修辭方法,況且拿自己跟過去一些偉大的法官比較應該別有趣味。而這一切最後也實現了。但我要提到最後一個攸關我是否接受任命較瑣細的考量。在我第一次拜訪司法部討論接受任命的可能性的前一天,我恰好出席某個州際商務委員會,要在一位行政法官(已過世)面前作證。柯文頓.柏靈律師事務所(Covington & Burling)一位年輕的律師威廉.李文斯頓(William Livingston)對我進行了一次非常有力的反詰問,而我的客戶,一家西部鐵路公司的法務長,對於我輕易就讓李文斯頓牽著鼻子走非常不滿。我當時的反應是,誰需要這樣?我想要坐到審判席的另一邊。我想要做折磨別人的人,而不是被折磨的。
我想要繼續從事學術工作,而我猜(最後證明猜對了)不做顧問,兼職教書,不用承擔全職法學教授需要承擔的行政責任,我在審判工作之外將有足夠的時間從事學術寫作。有種對公眾的責任感驅使我接受司法任命。我在一九七○年代時屬保守派(而直到一九六○年代末以前我都是自由派),部分原因是受一九六○年代脫序的情況所影響,部分原因則是受到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影響。我熱情地支持雷根,而且我覺得如果他的政府想要我效力,我不應該拒絕。如果那個工作對我來說會造成財務負擔,或者是很無趣的,我想我還是會拒絕,但是我不太願意拒絕服務社會大眾的召喚這件事多少左右了我的決定。
在我整個法官生涯中,仍然持續學術寫作,主要是將經濟分析(有時候是社會科學的相關領域)運用於法律上。我將這樣的分析運用在多種法律的實體與程序領域,也運用在司法行為本身。我也將經濟分析運用在我許多司法意見書中。經濟學基本上是關於人們如何回應誘因與限制,以及那樣的回應如何形塑(或侵害)規則、實務與機制,包括法律體系的規則、實務與機制。因此,相較於法律形式主義,法律現實主義更能與經濟學相容。我對於經濟學的興趣反應且增強了我對於法律形式主義的保留態度,而使我轉向現實主義。
我必須說明一下一九八一年時的司法任命程序,因為與今天的情況非常不同,雖然當時的作法有些粗糙且幾乎有些可笑,卻比後來的作法更好。程序的變化更顯示了我所說的內部複雜性的升高。
在我告訴巴斯特我對那份工作有興趣之後,我經歷了一般的人事審查程序,包括填寫表格,而就我記憶所及,表格要求我列出從出生後的所有地址;聯邦調查局(FBI)會搜查關於我的一切檔案,並詢問鄰居與同事有關我的事情;由白宮幕僚進行某種審查;還有參議院司法委員會(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幕僚根據聯邦調查局調查結果的摘要再進行進一步審查;還要接受司法部副部長與美國律師公會下的一個委員會訪談。美國律師公會的委員會覺得我的學術成就沒什麼,對我欠缺審判經驗則持負面印象(當時美國律師公會是由執業律師組成的行會,他們認為除了少數例外,聯邦法官原則上應該只由訴訟律師擔任,就我所知或許美國律師公會今天仍這麼想),他們對我的評價是「符合資格」,而不是「非常符合資格」。這整個程序持續了大約四個月。但我除了到場接受訪談,其他就是填表格,這只是小小的麻煩。最後總統提名了我,而針對我的提名安排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進行聽證。
聽證程序中有兩項阻礙。其一事後證明無關緊要,是關於我母親較為特殊的背景。我的雙親,特別是我的母親,是非常左派的,而且事實上頗讚賞史達林(Joseph Stalin),他過世的那一天,他們還在我家裡為他哀悼。一九五○年代晚期與一九六○年代初期,我母親是某個名為「女人為和平示威」(Women Strike for Peace)的組織要員,該組織倡議解除核武。該組織的許多領導人曾是共產黨員。一九六二年,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決議調查這個中上階級郊區中年女性之邪惡陰謀集團,而我母親也在被傳喚作證之列。她被質問是否曾為美國共產黨黨員,而她援引憲法第五增修案的權利拒絕回答。
這是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最後一次的調查。媒體嘲弄他們對這些無害的女性進行這樣的調查,該委員會之後也很快被廢除。後來當我得到檢察總長辦公室的職務機會時,也要經過聯邦調查局的人事審查,我提到我母親曾經是個共產黨員(非常有可能,雖然她從未承認,我相信聯邦調查局也沒有真正的黨員名單,只能仰賴始終不是很可靠的線民)。但一九六五年那時根本沒人在乎這件事。而一九八一年這一次,當我同意接受法官提名時,我跟司法部提到我母親,他們顯然也不在乎。
本章標題並不像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或艾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的《前往芬蘭車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那麼戲劇化;芝加哥第爾本南街(South Dearborn Street)219號,是美國上訴法院第七巡迴庭的地址,恰好意外地成為我職業生涯的終點。而我走過的「路」能夠提供一些洞見,藉以瞭解聯邦司法體系複雜化的過程。
教育與早年的職業
我在一九五九年十六歲時進入耶魯學院(Yale College),跳過了中學的最後一年。我進耶魯沒有什麼更好的理由,只因為我父親從《紐約時報》上看到,哈佛與耶魯招收中學三年畢業的小孩(芝加哥大學長期以來就收只念過兩年中學的學生,但在當時因為我成長的地方,對我來說哈德遜河以西的地方根本不存在)。我向哈佛與耶魯提出申請,哈佛拒絕了我,耶魯錄取我,所以我進到耶魯。那時候我比較想去哈佛(那是個錯誤,我稍後會提到),而且如果我繼續留在中學念第四年,然後再申請,我可能會被錄取;但我想要繼續前進。我很訝異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完全不急著確立自己的生涯規畫,或者根本就不自己做生涯的決定。
我在耶魯主修英文,文學長期以來都是我最喜愛的科目,部分原因在於我母親是中學英文老師,我才三歲(也有可能更早)時,她就唸荷馬與莎士比亞給我聽。新評論主義(The New Criticism)在我就讀學院時正值全盛期,而耶魯正是其重鎮;新評論主義不重視以自傳與歷史方法研究文學,而將文學作品視為一種獨立存在的美學客體,可加以理解並賞析,讀者毋須知道太多作者個人資訊或其時代背景。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一位著名的新評論主義者,當時是我的資深論文指導人(我的論文以一本書的篇幅研究葉慈〔W. B. Yeats〕晚期的詩作)。當時我對於新評論主義的方法有極大的熱誠,現在仍然如此。我提到這件事是因為那影響了我的司法方法,若不是它,我無法成為細膩的讀者,而能詮釋複雜的文件。還有一點,新評論主義方法讓我脫離過度依賴歷史作為理解文件的指引的限制。
我不認為新評論主義在哈佛會有多大影響力,加上耶魯事實上較著重大學部的教育,這讓我很感謝哈佛當初拒絕我的申請。
耶魯畢業後我直接進入哈佛法學院。我對法律並無熾熱的興趣,但我父親是個律師(也是個生意人),而法律當時是許多人設定的職業選擇,今天依然如此。雖然我喜愛文學,卻無意靠著寫作謀生,也沒興趣執教。我也申請了耶魯法學院並獲得錄取,但最後認定哈佛比較有挑戰性;它不會像耶魯法學院過去與現在那樣把學生當孩子寵。我想我做了正確的選擇。
我喜愛在哈佛法學院的第一年,我喜歡它的殘酷。哈佛把最好的老師都排在第一年,而他們確實非常厲害,儘管冷酷、苛求,有時候還有些討厭。那一年結束時,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覺得自己顯然變得比前一年的我更聰明了。我也發展出一種尊敬法律與法律人(至少是哈佛法學院教職員所投射出來的法律人性格)的情感,而且特別看重普通法,那是第一年的主要科目。第二年與第三年的課程就沒那麼有趣了。(有些課教得很爛,也就是那時我才發現法學院把它最好的老師都排在大一課程。)我退掉了大二的許多課程(所以我的成績掉下來,而我在大三變成較認真的學生),並且將最後兩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哈佛法學論叢》(Harvard Law Review)的工作上;附帶一提,那是一個真正菁英領導的組織,社員資格完全是基於分數決定的(現在已非如此),而且雖然法學論叢的會長是由會員選舉的,但沒有任何政治活動(現在也已非如此)。有些微的傾向選舉最好的學生,只要他在擔任論叢工作時確實認真盡責。
我原本以為我會在紐約執業(我出生在紐約,成長的過程住過紐約與斯卡斯代爾〔Scarsdale〕),儘管我在大一與大二暑假時都未到法律事務所打工;在那個年代,暑期的法律事務所打工尚屬少見,而我也沒有應徵。我對法律教學沒有興趣,也沒想過會成為法官,雖然我依稀有點印象自己曾經想過若能成為一名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應該會很有趣。我也不曉得該怎麼做才能成為一個法官。
保羅.福隆德(Paul Freund)是哈佛法學院很有名的教授,大法官布瑞南(William Brennan,哈佛法學院的校友)委託他每年幫忙挑選兩名法官助理,而他問我願不願意擔任,我同意了。我必須冒著有些不敬的風險說,我發現聯邦最高法院實在不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機構。我很驚訝地發現,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意見書並不完全是由他們自己寫的(道格拉斯大法官〔William Douglas〕確實自己寫, 但他的意見書是最弱的,不是因為他笨,而是因為他的行文乏味);哈佛法學院教授雖然對自由派大法官嚴厲批判,但還沒有讓法律助理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在準備擔任布瑞南的助理時,我讀了許多他的意見書,而且印象深刻;直到後來我才知道,當中最好的意見書都是由他的前任助理所寫,也是一位優秀的哈佛法學院畢業生,名字是丹尼斯.里昂斯(Dennis Lyons)。
布瑞南曾經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律師,後來也成為新澤西州最高法院非常傑出的法官。我很確定他寫過很好的司法意見書,也確實有人告訴我,在他服務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期間,有幾年他的助理所寫的意見書初稿他覺得不滿意,便自己寫,而且那些意見書寫得非常好。我想大部分的聯邦上訴法院法官都至少能寫出還可以的意見書。但也的確,法官助理是由法官選任的,不像法官那樣由政治人物所選,所以比起法官,法官助理時常更是稱職的法律分析者與寫作者。大部分的法官不太喜歡寫,比較喜歡審閱並編輯助理的意見初稿。這種編輯有時候是很輕微的。
在我服務的那時候(一九六二年那一審期),最高法院的工作步調很慢;我那一年勞力的程度比先前幾年都更低。我利用晚上與週末讀了很多文學,特別是英國與美國的經典小說,從狄更斯到福克納,因為我在耶魯念書時著重詩與戲劇,那是新評論主義偏好的主題。我當時真的對法律(尚)不太感興趣,甚至曾突發奇想(雖然很快放棄這麼想)脫離法律,去拿個英國文學研究所的學位。但很偶然的,就在助理生涯快結束時,我進到紐約一家大型法律事務所(寶維斯〔Paul Weiss〕)當受僱律師,我的工作是擔任一位非常卓越而能幹的聯邦貿易委員(Federal Trade Commissioner)菲力普.艾爾曼(Philip Elman)(曾任大法官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 〕的助理,而且長期擔任聯邦檢察總長的幕僚)。我為他工作了兩年,學到很多;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律師。
擔任布瑞南大法官助理期間,我在一件重要的銀行合併案上對反托拉斯法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這個興趣在為聯邦貿易委員會工作時再度加深,該機構管轄反托拉斯案件與消費者保護案件;我覺得消費者保護也很有趣。在艾爾曼的指導與其他幕僚的協助下,我撰寫委員會的聲明,發布一項強制在香菸包裝與廣告上增加健康警語的規則,並撰寫此等規則的辯護理由。雖然這項規則很快被國會推翻,但也成為最終成功抑制吸菸的管制努力之開端。
任職於委員會時,我與首席經濟學家威拉德.穆勒(Willard Mueller)變成好友,而且開始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奇怪的是,這種興趣的種子或許在我參加《哈佛法學論叢》的第一個月就種下了,當時我偶然地被指派校對德瑞克.包克(Derek Bok)一份反托拉斯長篇著作的引註(當時他是哈佛法學教授,後來成為法學院院長,而後成為哈佛校長),在那篇著作中他討論寡占的經濟理論。我從未聽過寡占理論,但我發現那相當吸引人,而且我也將之運用在我為大法官布瑞南撰寫的銀行併購案件意見書裡。
離開艾爾曼的辦公室之後,我進了檢察總長的辦公室,在那裡待了兩年多,寫作許多書狀,並在聯邦最高法院進行六件案子的辯論。我的工作重點在於反托拉斯與管制,而我對這些領域變得非常感興趣。但我不認為政府的書狀或口頭辯論影響了判決,無論造成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的因素為何,都不是律師的辯論。所以我在檢察總長辦公室任職兩年後劃下了句點,而我開始得到教職的面試機會,我決定試著教書。(執業對我沒有吸引力。我也不記得為什麼,但我猜那是因為我不想繼續為別人工作,也不想為不是我自己而是老闆或客戶的立場辯護。)就在我接受史丹佛大學的邀請並開始教職前,我在政府單位再工作了一年(同樣是收到邀請,而非自己應徵),擔任電信政策總統專案小組幕僚的工作。那是一份很棒的工作,增強了我在反托拉斯與管制上的興趣,也加強我對於經濟分析運用的興趣,雖然在這方面我當時還是個初學者,不太瞭解此等領域的法律應用。那個專案小組的研究主管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蘭德公司(RAND)經濟學者,名為勒蘭.強森(Leland Johnson),大幅激發我對經濟學的興趣。
由於我在第十章將討論司法與學術之間的關係,在此值得特別說明某次說服我嘗試法律教學的對話。當時史丹佛法學院院長貝利斯.曼寧(Bayless Manning)是一個很有才華也很有魅力的企業律師。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在檢察總長辦公室工作的第二年,曼寧(當時我未曾遇過他,也未曾聽過他)打電話或寫信給我,表示他到了華盛頓特區,希望我能跟他吃個午飯。我說當然好,之後我們共進午餐。時值阿拉伯與以色列六日戰爭(Six-Day War)剛結束,我們的討論話題都圍繞著戰爭。我著迷於他的興趣與知識的廣博,並且開始想或許法學教授是比律師更有趣的人。(我並不知道曼寧對外交事務有特別深的興趣;他後來成為外交關係協會主席)。但是當他試圖引發我對法律教學的興趣時,我表示我沒辦法想像自己寫作學術文章。他說不要緊,法學教授可以用其他方式貢獻於法律。任何人如果今天對法學教師的招募者這麼說,可能會立刻被排除考慮。在一九六○年代,法學界比較認同法律實務界,而非大學的學術文化;今日則變得非常「學術化」,導致法律教授與法律實務工作者(包括法官)的分化,這也讓非常需要協助以因應日益升高複雜性的挑戰的司法機構得不到幫助。
在史丹佛待了一年之後,當時我有幸認識了亞隆.德瑞特(Aaron Director)與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們兩位是傑出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德瑞特退休後回到灣區,並在史丹佛法學院有個辦公室;而斯蒂格勒在我於史丹佛任教的時間,恰好在那裡擔任訪問學者),於是我接受了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一項邀請,因為那裡有一群有興趣跟法學教授往來,也對法律有興趣的經濟學者。從那之後,我開始講授新興的法律經濟分析,並出版學術著作。我也從事許多諮詢工作,特別是反托拉斯法,也涉及公共事業與運輸業管制,例如航空與鐵路產業。我也提供環境管制上的建言,以及為福特政府命運不濟的價格管制提供建議。
一九八一年聯邦司法任命程序
我從沒想過會成為一位法官。但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某一天,我在雷斯康顧問公司(Lexecon Inc.)的辦公室內,這家公司是我跟威廉.藍德斯(William Landes)與安德魯.羅森菲爾德(Andrew Rosenfield)在一九七七年設立的,那天我的一個朋友同時也是之前史丹佛的同事,也就是當時獲得雷根總統任命擔任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主管的威廉.巴斯特(William Baxter),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有興趣接受任命到第七巡迴庭。我說沒興趣,而他說他也想過我會這麼回答。但是當他要掛電話時,我說,好吧,給我二十四小時想一想,而他同意了。我思考這件事,並且告訴我妻子(她願意接受收入顯著減少,我在學術機構有豐富的薪酬,顧問公司那裡也賺很多),也跟我父親與艾爾曼談過,他們兩位都鼓勵我接受法官職位;二十四小時期限到了之前,我跟巴斯特說,我想要再仔細想想前途。大約一星期後,我說我接受。我認為薪水減少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擔任法官還是可以兼職教書,所以能有一份教書的收入,貼補法官的薪資,儘管比擔任全職教職少。而我那時也對諮詢服務感到厭煩,部分原因在於我的時間不是花在分析工作,而是跟客戶推銷我們的服務,因為我是公司的資深人員。
我也覺得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應該是有趣且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聯邦案件具多樣性與重要性,我將有機會在真實世界的情境下運用經濟分析,以及學術寫作上用不到的修辭方法,況且拿自己跟過去一些偉大的法官比較應該別有趣味。而這一切最後也實現了。但我要提到最後一個攸關我是否接受任命較瑣細的考量。在我第一次拜訪司法部討論接受任命的可能性的前一天,我恰好出席某個州際商務委員會,要在一位行政法官(已過世)面前作證。柯文頓.柏靈律師事務所(Covington & Burling)一位年輕的律師威廉.李文斯頓(William Livingston)對我進行了一次非常有力的反詰問,而我的客戶,一家西部鐵路公司的法務長,對於我輕易就讓李文斯頓牽著鼻子走非常不滿。我當時的反應是,誰需要這樣?我想要坐到審判席的另一邊。我想要做折磨別人的人,而不是被折磨的。
我想要繼續從事學術工作,而我猜(最後證明猜對了)不做顧問,兼職教書,不用承擔全職法學教授需要承擔的行政責任,我在審判工作之外將有足夠的時間從事學術寫作。有種對公眾的責任感驅使我接受司法任命。我在一九七○年代時屬保守派(而直到一九六○年代末以前我都是自由派),部分原因是受一九六○年代脫序的情況所影響,部分原因則是受到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影響。我熱情地支持雷根,而且我覺得如果他的政府想要我效力,我不應該拒絕。如果那個工作對我來說會造成財務負擔,或者是很無趣的,我想我還是會拒絕,但是我不太願意拒絕服務社會大眾的召喚這件事多少左右了我的決定。
在我整個法官生涯中,仍然持續學術寫作,主要是將經濟分析(有時候是社會科學的相關領域)運用於法律上。我將這樣的分析運用在多種法律的實體與程序領域,也運用在司法行為本身。我也將經濟分析運用在我許多司法意見書中。經濟學基本上是關於人們如何回應誘因與限制,以及那樣的回應如何形塑(或侵害)規則、實務與機制,包括法律體系的規則、實務與機制。因此,相較於法律形式主義,法律現實主義更能與經濟學相容。我對於經濟學的興趣反應且增強了我對於法律形式主義的保留態度,而使我轉向現實主義。
我必須說明一下一九八一年時的司法任命程序,因為與今天的情況非常不同,雖然當時的作法有些粗糙且幾乎有些可笑,卻比後來的作法更好。程序的變化更顯示了我所說的內部複雜性的升高。
在我告訴巴斯特我對那份工作有興趣之後,我經歷了一般的人事審查程序,包括填寫表格,而就我記憶所及,表格要求我列出從出生後的所有地址;聯邦調查局(FBI)會搜查關於我的一切檔案,並詢問鄰居與同事有關我的事情;由白宮幕僚進行某種審查;還有參議院司法委員會(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幕僚根據聯邦調查局調查結果的摘要再進行進一步審查;還要接受司法部副部長與美國律師公會下的一個委員會訪談。美國律師公會的委員會覺得我的學術成就沒什麼,對我欠缺審判經驗則持負面印象(當時美國律師公會是由執業律師組成的行會,他們認為除了少數例外,聯邦法官原則上應該只由訴訟律師擔任,就我所知或許美國律師公會今天仍這麼想),他們對我的評價是「符合資格」,而不是「非常符合資格」。這整個程序持續了大約四個月。但我除了到場接受訪談,其他就是填表格,這只是小小的麻煩。最後總統提名了我,而針對我的提名安排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進行聽證。
聽證程序中有兩項阻礙。其一事後證明無關緊要,是關於我母親較為特殊的背景。我的雙親,特別是我的母親,是非常左派的,而且事實上頗讚賞史達林(Joseph Stalin),他過世的那一天,他們還在我家裡為他哀悼。一九五○年代晚期與一九六○年代初期,我母親是某個名為「女人為和平示威」(Women Strike for Peace)的組織要員,該組織倡議解除核武。該組織的許多領導人曾是共產黨員。一九六二年,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決議調查這個中上階級郊區中年女性之邪惡陰謀集團,而我母親也在被傳喚作證之列。她被質問是否曾為美國共產黨黨員,而她援引憲法第五增修案的權利拒絕回答。
這是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最後一次的調查。媒體嘲弄他們對這些無害的女性進行這樣的調查,該委員會之後也很快被廢除。後來當我得到檢察總長辦公室的職務機會時,也要經過聯邦調查局的人事審查,我提到我母親曾經是個共產黨員(非常有可能,雖然她從未承認,我相信聯邦調查局也沒有真正的黨員名單,只能仰賴始終不是很可靠的線民)。但一九六五年那時根本沒人在乎這件事。而一九八一年這一次,當我同意接受法官提名時,我跟司法部提到我母親,他們顯然也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