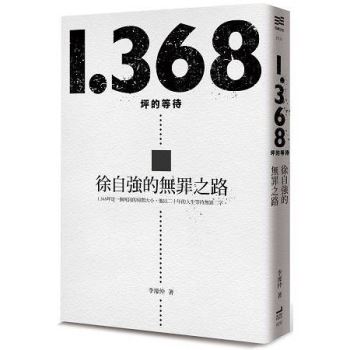第一天
第一幕 火速破案
炎熱潮溼的泰國芭苔雅,臨海而立,風光旖旎,即使進入十二月最涼爽的月分,每日最高溫仍有達攝氏三十度以上的可能。此處市集車水馬龍,沿途海濱度假酒店林立,長年門庭若市,因而素有「東方夏威夷」之稱。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芭苔雅正值觀光熱季,遊客熙來攘往,徐徐海風讓人心曠神怡,卻有人無視這座城市綺麗多姿的景貌,心起殺機。一位名叫「張保羅」的男子,當月十六日即遭人縊死在下榻飯店的浴室內。
他的死狀奇慘,透露潛伏在案情裡的深仇大恨。飯店人員發現張保羅時,他的雙手、雙腳均受到綑綁,凶手同時再以床單撕成的繩子纏繞住他的頸部,最後張保羅整個人且被懸吊於浴室的氣窗前,仿若一場警告意味濃厚的私刑。一個人若欲尋短自盡,其實根本不必這麼大費周章。透過泰國警方蒐證資料顯示,現場不僅有兩人以上搏鬥跡象,張保羅的臀部還有清楚受人在地上拖行的紅腫傷痕。
就在飯店業者因為這起血腥凶案惴惴不安之時,泰國警方卻在張保羅的房間內發現一本中華民國護照。護照的照片和死者面容相符;但英文的署名和他登記住房的「張保羅」名字大有出入。泰國警方隨即將採集的指紋傳真到臺灣的刑事警察局請求協查其身分。經過刑事局指紋室比對,赫然發現張保羅竟是同年九月,犯下內湖房屋仲介商黃春樹綁架撕票案的主嫌之一—黃銘泉。
這項消息經臺灣媒體披露,原先似已真相大白的綁票案,進而再掀波瀾。主要因為這起案件,當時除已被逮獲、正關在看守所裡的兩名同夥,以及在泰國橫死的黃銘泉外,尚有一名綽號「阿強」的嫌犯在逃。警方因此懷疑,黃銘泉是和阿強一起潛逃泰國,之後因為彼此利益擺不平而起衝突,結果引來不測。如今非得將本名徐自強的阿強緝拿歸案,否則綁票案的來龍去脈何以水落石出。更何況,警方數月前宣告偵破這起綁架案時,甚至是以「主謀」身分對徐自強發出通緝。
兩嫌被逮,黃銘泉已逝(幕後原因迄今未明),新聞媒體大篇幅報導的汐止山區富商遭撕票案,自九月間發生數月後,徐自強仍不見蹤跡。他的下落不明,讓警方火速偵破的擄人勒贖事件徒留一條大尾巴。
擄人勒贖唯一死刑
內湖房屋仲介商黃春樹遭綁架撕票的年代,尚是臺灣擄人勒贖必處唯一死刑的年代。不過,極刑的威嚇性,好像也無法確保利慾薰心或被逼上絕路的普通人不會變成惡棍,年年還是有綁架案發生。一九八七年底,新竹市東區東門國小四年級學生陸正,自補習班下課後失蹤,從此音訊全無,此一早期幼童綁架案大舉震驚了臺灣社會;一九八八年,另有曾成山因積欠債務無力償還,綁架撕票表哥的三歲稚子;一九八九年,則有張木火、卓三貴共同犯下多起綁架案,並殺害肉票;一九九○年底,新光集團少東吳東亮被胡關寶犯罪集團綁票,歹徒一開口就是索討一億元贖金,名人效應加上天價贖金,使得此案益發喧騰;一九九一年,「反共義士」卓長仁綁架了當時的國泰醫院副院長王欲明之子王俊傑,勒贖五千萬,是為英雄人物最大的嘲諷;一九九二年,無業的郭金村、蕭素貞,被控共謀擄掠年僅三歲的韓小弟弟,而後向其家人勒贖且撕票;一九九三年,吳欽明、吳火土兄弟因經濟拮据,共同駕計程車綁架撕票乘客;一九九四年,王禎耀將三名債務人擄走,並活活燒死於車內……綁匪之中,有尚在獄中等待槍決者,有已遭槍決者,從舉國矚目的陸正案開始,前列歹徒的下場和遭遇,似乎沒有帶來必然的警醒作用。一九九五年九月,內湖房屋仲介商黃春樹也就因此難逃一劫。
第二天
清晨,電話鈴響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清晨四點鐘左右,富甲一方的黃健雲,於睡夢中被一通電話吵醒,對方連名帶姓指名要找他,卻不待黃健雲回神,就把電話給掛了。由於兒子黃春樹前一天上午離家後即不見人影,黃健雲直覺這通電話可能和兒子的行蹤有關,最不希望的事情難道發生了?隔了五、六分鐘,家裡同一支電話再度鈴聲大作,四下靜謐無聲的大清早,聒噪的電話聲格外讓人感到不安。
對方說話了。但一開口,吐出的就是一把利劍:「你兒子現在在我手上,趕快準備七千萬做贖金,不可以報警。」不待黃健雲問個究竟,對方立刻又掛斷電話。歹徒反覆來電,倉促結束通話,也許是害怕被警方監聽,或者擔心被家屬識破犯局的機靈反應,但也可能純粹是心虛,因為心神緊張的下意識表現。
九月初,盛夏未盡尾聲,兩通電話,卻足以讓黃健雲背脊發涼。二十年前,黃健雲放棄彰化家族世代承襲的農務,北上改經營汽車材料行。乘著當年房地產熱潮,黃健雲順勢將手頭積蓄投入臺北縣(今新北市)汐止一帶的土地,土地交易獲利遠勝過汽車材料買賣,愈加激勵他改為投身房地產生意。很快的,他從一介鄉下農夫,而後一名小小汽車材料商人,轉眼財富三級跳,最終成為一間知名建設公司的大老闆,在地方上已非泛泛之輩。只是,沒想到世間常理,果真禍福相倚,他的兒子黃春樹也是因此招致歹徒的覬覦。
通話結束,黃健雲拿起話筒,立刻轉撥電話給黃春樹的妻子黃玉燕,告知她的先生被人綁架了。黃玉燕原以為先生只是和平常一樣,偶爾在外應酬沒有回家,未感覺出反常跡象,這下才知道事態嚴重。
清晨五點半,歹徒再度來電。黃健雲早睡意全失,他必須振作精神,以應付接下來一連串和歹徒之間的糾纏。電話那頭,傳來的內容和前一通如出一轍,再也沒有任何僥倖的可能,黃健雲陷入的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擄人勒贖案。
自接到歹徒第一通電話後,黃健雲當天上午七點不到,立刻前往自家附近的警察局報案,他明快地要把營救兒子的行動交給警方。事後證明,黃健雲起初並未考慮私了,自行和歹徒周旋應對,確實是正確的選擇,如此警方才得以立即成立專案小組,短短二十八天就將嫌犯之一逮捕,再循線掌握同謀,一舉破案。不過,一個月內即可讓歹徒現形,某種程度,或者也要歸因歹徒作案手法未必縝密無失,甚至還處處留下讓警方得以布局收網的線索。
歹徒為了逃避追蹤,多次仿效電影情節,每每來電和家屬對話,都盡可能精簡通話過程,及至察覺所使用手機已被掌握,便改以公用電話聯繫,不過,此時警方早已全程守在黃家,逐一監聽每一通來電。
也就是在事發兩個多禮拜後,黃健雲在一次和歹徒的對話中,為判斷兒子的生死,要求歹徒說出黃春樹女兒的生日,結果對方支吾其詞,沒有給出答案,那麼,已遭撕票的機率為之大增。逝者已矣,縱然再抱一線生機,此時則以逮人為首要之務,至少錢不要再落入歹徒口袋。在敵暗我明下,黃家人持續和歹徒針對贖金討價還價,價碼一度從原本的七千萬降至一千五百萬,後因為歹徒認為黃家和警方合作,導致他們取贖難度增高,一氣之下,再把贖金提高至一億元。來來回回,最後是黃春樹的妻子黃玉燕苦苦哀求,雙方才以一千六百萬說定。
第三天
第四幕 大逃亡
埋伏在公用電話停附近的警察很快地就將黃春棋逮獲,過程似乎比警方原先的沙盤推演還要順利。不過當晚,就在電話亭附近,他們隱約察覺似乎另外有個人趁亂逃跑。根據警方掌握的監聽紀錄,他們懷疑同一時間跑掉的那個人,就是亦曾打電話向被害者家屬勒索贖金的陳憶隆。
事發隔天中午,阿強接到一通陳憶隆的來電。阿強直覺,因為賭博電玩生意屢屢被警方查扣的陳憶隆,這回八成又是要開口跟他借錢。阿強的太太卓嘉慧平常除了和阿強一起照顧檳榔攤的生意,之前還曾在陳憶隆的電玩店打工,阿強去店裡接太太下班時,偶爾會到店裡順便玩上兩把,因為多了層主雇關係,阿強進而結識太太的老闆—陳憶隆。阿強有時會邀請他到家裡玩牌,那段時間,他們的牌搭子就是黃銘泉和黃春棋。因為手頭經常短缺,經濟狀況相對穩定的阿強,便多次成為陳憶隆調頭寸的對象。
民國八○年代,賭博性電玩以其迷幻人心的誘惑力,吸光了多少人的青春和財富。遊藝場裡只要擺著幾臺賽馬機、水果盤、十三章麻將和吃角子老虎,天天都有人捧著大把鈔票上門。賭博性電玩的樂趣從來不只為了追求贏錢的快感,那是一種「癮頭」,讓人純粹沉溺在機率做主的靡想之中。即使一天下來浪擲千金,僅開了一次「役滿貫」(為日本麻將最高級的牌型,達成條件相當困難),還是有可能鼓舞你明天重返現場再接再厲。
當時賭博性電玩皆是非法營業,就像色情業者一樣,必須躲著陽光牟利。於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業者遭警方查扣的消息出現。一九九四年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曾雷厲風行掃蕩城裡的電玩業,一併阻斷了賭博性電玩的後路。此舉評價有好有壞,但營業場所總是龍蛇雜處,客人出入背景少有單純,因而在生活平實規矩的市民眼中,至少算得上是某種程度的德政。
陳憶隆即在賭博性電玩時興、尚有鑽營空間的年代,於桃園縣內屢仆屢起。一九九四年被以賭博罪判刑五個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隨即再犯,之後又被以賭博罪另外再判了五個月。直到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在參與綁架黃春樹之前,他再因賭博罪名,遭處有期徒刑七個月,是個不折不扣的累犯。每每被查扣賭博電玩機臺,陳憶隆就得再找門路籌措資金,好讓自己東山再起,因而前前後後向阿強借了數十萬元。阿強原本以為可以從中收取一些利息,誰知為了這點蠅頭小利,日後竟讓他付出無比慘痛的代價。
阿強直覺不對勁。陳憶隆那回除了再向他情商現金周轉外,還沒頭沒腦告訴他,警察早上曾經找上門,剛好他不在家,警察於是留話給他太太,說是要找他自己和阿強。難不成又是電玩店被查扣,要被判刑罰錢?陳憶隆已是前科累累,刑期說不定會更重。不過,警察找陳憶隆本來就不是什麼新鮮事,指名要找阿強,又是為了什麼?阿強追問緣由,陳憶隆卻始終支吾其詞,說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便把電話掛了。滿心狐疑的阿強之後回撥了一通電話給陳憶隆的太太,想問清楚到底警察找他做什麼,陳憶隆的太太又說警察根本沒提到他的名字,只拿走了家裡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電話簿。只是,那本電話簿裡阿強的名字剛好也在其中。
第四天
更加詭異的是,就在陳憶隆來電沒多久,而阿強拒絕再次拿錢出來幫忙應急後,輪到黃春棋打電話給他。電話那頭,黃春棋問阿強人在哪裡,阿強說自己正在檳榔攤。「喔,這樣啊,那我等一下去找你。」黃春棋話一說完就匆匆把電話掛斷。接連兩通讓人摸不著頭緒的來電,阿強其實心裡有數,這兩人一定惹出了什麼麻煩。當時已遭逮捕的黃春棋,顯然是受警方指示,被要求打電話給阿強,探一探阿強的動向,且謹慎小心不要打草驚蛇,讓這位黃春棋口中的「綁架撕票案主謀」不小心給跑了。
結束通話,阿強轉身離開檳榔攤,回到鄰近向岳母承租的公寓,愈想愈不對勁。約莫下午兩點鐘左右,租屋處的電話響起,這次是岳母打來的。岳母跟他說,「有一群人現在在檳榔攤外面,說是要找你。」阿強當時心想,黃春棋還沒來,檳榔攤外倒是圍著一群彪形大漢,會不會是他前不久曾出面替黃春棋租車,才讓自己惹上麻煩?如果找他的是警察,是不是因為黃春棋尚有別的案子通緝在案?如果找他的是黑道分子(那群彪形大漢其實是便衣警察),又是否是為了黃春棋欠下的賭債而來?從阿強的租屋處探頭往外看,數十公尺外,剛好可以撇見平常他們夫妻看顧的檳榔攤。看著好幾個來意不善的陌生男子,在檳榔攤前左顧右盼,阿強一陣背脊發涼,自覺在這節骨眼上,恐怕還是不要貿然露臉,否則真不知道會有什麼意外發生。接著,阿強小心翼翼不被那群人發現,躡手躡腳地離開租屋處,打算在搞清楚狀況前,先到臺北閃避風頭。之後阿強的媽媽曾和阿強通過電話,並問他,為什麼警察要到家裡找人。阿強說,「我就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啊。」
從避鋒頭變成逃亡
此時此刻要離開山腳村前去臺北,已不若二十多年前阿強媽媽那般躊躇不前。年代不同了,山腳村和臺北之間的差異,因為時空變化而拉近了不少距離。不久前,阿強才帶著太太去九份玩,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星期,這回索性在抵達臺北後,阿強立刻又轉乘客運,避走九份。
住在九份那一天,阿強和媽媽持續保持聯絡,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警察要找阿強?以及為什麼又會有一群「凶神惡煞」也在問阿強的下落?阿強的媽媽勸告阿強,不如就在外頭再待個幾天吧,總之先避一避。他們只是住在鄉下地方的平凡人,不可能和誰結下深仇大恨,阿強和太太每天都忙著檳榔攤生意,阿強的媽媽已改行從事家庭理髮,這樣的生活背景,實在沒道理替自己惹禍上身。
隔天,眼看什麼事也沒發生,一頭霧水的阿強傍晚又回到了桃園,返底家門,卻覺氣氛仍讓人不安,阿強的媽媽又一次勸告阿強去外頭待個幾天等情況明朗一點再回來。阿強這回乾脆帶著太太一起匆匆離開,夫妻兩人二十八日便決定搭乘夜車南下高雄。那時的心情也許還不至於帶有「逃亡」的感受,只覺得是不是因為黃春棋的關係,自己被莫名所以的事件拖下水。果真如此,也許外出避個一兩天,鋒頭一過,一切就可重回軌道。
黃春棋有案在身,麻煩不斷,還積欠人家賭債,難不成是債主找黃春棋討債不成,轉而要他這個表哥代償?阿強愈想愈心煩意亂,卻又理不出半點頭緒。到了高雄,已是九月二十九日清晨,才下車,他和太太疲累不堪,以致玩興全無,加上這趟旅程,總是夾雜著一股不安的情緒,哪有心思規劃玩樂的路徑。(南下高雄前,他們其實先去了一趟九份,隨即再又搭車南下。)剛從桃園到九份,再從九份搭夜車抵達高雄,兩人在不知作何是好下,立刻又買了火車票,準備前往花蓮。也或許確實有那麼一絲絲心神不寧,他們才會有如此反常的舉措出現。
第五天
那年阿強才二十六歲,太太卓嘉慧年紀更小,一對兩小無猜的年輕男女,先是未婚生子,及至登記結婚,阿強退伍回來,也幸好阿強的媽媽適時挺身而出,願意替他們照顧幼子,兩人才得以一起出外賺錢養家。因為孩子那時留在阿媽家中,生活瑣務有阿媽打點,阿強和太太這趟避鋒頭之旅,才能了無牽掛。
但這只是驚心動魄的逃亡前奏。他們益發感到事有蹊蹺,但又不知道自己應該為了什麼事情覺得不安。就在高雄火車站大廳,準備搜尋前往花蓮的車班時,阿強看到一旁書報攤販賣的報紙,隨手一翻,赫然驚見自己的照片被登在其上,而且還被指為是一起綁架撕票案的主謀,阿強立刻翻搜自己的口袋和行李,把身上任何可以證明自己身分的證件全部撕毀丟棄。他們被報上的新聞事件嚇傻了,卻不是因為其內容多麼驚悚恐怖、駭人聽聞,也許自己從小不喜歡唸書,沒有過什麼值得稱道的偉大事蹟,但也從來沒做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那麼,自己又有什麼樣天大的本事,可以和人共謀擄人、勒贖,最後還將之撕票?
整起綁架事件雖非縝密嚴謹而至萬無一失,阿強又有什麼自信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他不就是山腳村一間檳榔攤的老闆,之前頂多做過卡車司機,他沒混過幫派,不是與人打打殺殺的料,有什麼理由會讓自己如此手段凶殘,犯下殺人毀屍滅跡?缺錢嗎?他還有能力借錢給朋友、親戚。雖說狗急也會跳牆,阿強又沒什麼事情被逼急。若是利慾薰心,當初又怎麼會因為不願開每一趟都超載的砂石車,而把砂石車賣掉,轉做檳榔攤生意?被自己的表弟一口咬定涉案,實在是晴天霹靂。原來真正的逃亡才即將展開。至於若真的沒做那件事,阿強又為什麼要逃?
擔心警方「曉以大義」
「因為怕被警察打到招認做了這件事。」這是阿強之後所說決定「逃跑」的理由。當初,阿強的媽媽也是以此建議阿強暫時先不要出面。阿強的媽媽因為在自家從事家庭理髮,客人進進出出,因而聽聞不少街談巷議。有個店裡常客的工作是到警察局送飯菜,只要來洗頭髮,她都會對阿強的媽媽如實轉述個人在警察局裡看到的情景。包括老是有人被打,或者哪個嫌犯因遭到警察拳打腳踢,哭著躲到桌子底下求饒。新聞報導出來,阿強媽媽的朋友紛紛前來關心,他們多數不相信平日木訥寡言的阿強,會是個如此心狠手辣的傢伙。於是他們七嘴八舌勸說阿強的媽媽,要她轉告阿強,如果沒做就先不要出來,免得被抓進去後,讓警察打到承認自己有做。阿強的媽媽心想,如果阿強沒有參與這起綁架撕票案,那麼躲起來應該也不算是犯罪的行為才對。想起小時候,阿強因為幫忙家裡洗碗,隔天睡過頭,上學遲到被老師體罰,阿強的媽媽為自己那個總是遭人誤解又不善辯駁的兒子,感到一陣心酸不捨。
「因為怕被警察打到招認做了這件事」而決定逃跑,理由很牽強嗎?多年以後,尤伯祥律師成了阿強這起官司的辯護律師之後,便經常有人向他問及,如果當初阿強沒有犯罪,又為什麼要逃亡?言下之意,似乎「逃亡」就必然是屬於犯罪者的專利。尤伯祥律師坦言,雖然他自始至終相信阿強並沒有涉案,但「逃亡」這件事,確實為阿強帶來十分不利的觀感。不過經過多年律師工作磨練,他終於理解,在當時那樣的警界文化中,「刑求逼供」不僅時有所聞,甚至還相當普遍,因此以他個人出身中產階級的背景,理所當然會認為「逃跑」就是心虛,是畏罪潛逃;可是,對臺灣屬於中下階層的族群來說,警察的面目有時是很可怕的。在他們的世界裡,警察會打人也會索賄,然後抓到就是打,打到你承認為止。阿強之所以會選擇逃跑並非沒有道理。只是我們的社會新聞,從來不會如實寫下某人是受到刑求招供才願意說出真相,讓一切水落石出。多半情況下,他們只會採用制式的表述方式,以「在警方『曉以大義』下,嫌犯終於坦誠不諱」一語簡單帶過。
第六天
話說回來,黃春棋被捕的隔天,不就在警察局遭到刑求了。九月二十七日,改由檢察官負責偵訊時,黃春棋便改口否認自己涉案。檢察官問他,既然如此,為什麼之前會在警局坦誠犯行,黃春棋則回答,因為他受不了警察刑求他。根據檢察官偵訊筆錄上的記載,黃春棋曾說,「警方借提時,把我眼睛矇住,吊起來灌水,還捏我奶頭,用不知道何物夾我手指。」雖然黃春棋一度翻供,並未對案情帶來轉圜,但我們不難推論,阿強如果沒有逃跑,下場可能也難逃被毒打一頓。那個年代,警局裡經常上演那樣的劇情。
警方尚且握有黃春棋涉案的監聽錄音帶,使得就算有刑求事實存在,黃春棋也難自圓其說,即使如此還得受皮肉之苦。那麼,換作是阿強呢?在警方未能掌握他參與犯罪的任何證據前,他更有可能被打到認罪,且坐實了刑求之下,何謂百口莫辯。只是這一切終究沒有發生。阿強沒有因此遭到刑求招供,但也因為偕妻逃亡之舉,徒然讓自己在社會大眾的眼光中成了一名畏罪潛逃、罪無可恕的大壞蛋。
阿強和太太從高雄又回到九份,這次住了十天,手邊盤纏幾乎用罄。於是改而移至臺北市,尋找租金便宜的套房。背著在逃共犯的身分,被害者家屬還公開懸賞一百萬,夫妻兩人這才體會到什麼是亡命天涯,一度有共赴黃泉的念頭出現。阿強成天不敢出門,只能靠太太每天搭公車,到數公里外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回家報平安,阿強的太太還臨時接了些手工,以為逃亡籌措生活費。
主謀黃銘泉現形
逃亡的同時,阿強努力回想,黃春棋等人指控他參與犯案的九月一日,他究竟做了些什麼。就在阿強和太太藏匿於臺北市,約莫一個月後,因為陳憶隆的落網,這起事件再度成為熱門新聞話題。報上寫著:黃春樹撕票案,共犯陳憶隆落網,逃亡近一個月,栽在雲林,陳嫌供稱,主謀係黃春棋胞兄黃銘泉,目前二嫌(黃銘泉和阿強)在逃。
陳憶隆的供述迥異於黃春棋,雖然將主謀人選轉向黃春棋的哥哥黃銘泉,卻也沒有半點替阿強脫罪。根據警方提供給媒體的消息,警方曾在二十五日逮捕黃春棋後,立刻趕赴桃園圍捕阿強和陳憶隆,結果兩人先一步聞風逃逸。陳憶隆逃跑內情不得而知,倒是阿強這一方的理解,和警方認知略有出入。阿強認為當時自己並沒有逃跑的計畫,警方也沒有真正對其展開圍捕行動,純粹因為警方在檳榔攤「撲空」,才讓一切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經過警方初步偵訊,陳憶隆供出,黃銘泉才是策劃這次綁架案的主謀,並實際參與綁架且出手殺害人質。他自己則是因為經營電玩店不善倒閉,積欠債務,才接受黃春棋的提議參與作案。在著手綁架前,黃銘泉及黃春棋即計劃將黃春樹綁走後,隨即予以撕票,再向黃春樹家人勒贖。因此他們在綁架黃春樹的前兩、三天,就在黃春棋兩兄弟帶領下,前往臺北縣汐止山區棄屍地點,先一步挖好埋屍坑洞,待九月一日將黃春樹綁走,便直接將他帶到棄屍地點,逼問家裡電話後,就著手予以殺害。
陳憶隆所言,其實和黃春棋先前對案情的描述相去不遠。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原本黃春棋落網時,媒體曾根據他的說詞,把綁架案主謀的矛頭指向阿強,突然全部又轉而變成是黃銘泉所為。也就是說,陳憶隆若沒有說謊,那麼黃春棋就是把自己哥哥黃銘泉的犯行全部嫁禍到阿強身上,以此掩飾黃銘泉在這起案件中的角色。
第七天
事實上,黃春棋也把部分犯罪事實推到陳憶隆一方,這讓陳憶隆落網後,迭有怨言。陳憶隆其實也希望透過詳細交代案情,減輕自己的罪責。根據陳憶隆的說法,他是在八月中旬,於阿強家中,和黃銘泉、黃春棋兄弟,以及阿強一起謀劃綁架案,黃銘泉因為常到海外投資生意,同時也想幫自己弟弟還債,所以兩人就邀他入夥,他們兄弟都計劃好了,在人手不足下,且還缺一部車,才找上他幫忙,而他自己因為有資金周轉的需求,於是就爽快加入。阿強則因為是黃銘泉的表弟,也有車,聽到這件事也就參上一腳。
和黃春棋供詞出入之處,除了黃銘泉和阿強的角色之外,陳憶隆還說,阿強事先買了三瓶硫酸,準備滅屍;但黃春棋的說法是他們是以汽油燒毀屍體。但既然有硫酸的一段,則又更加證實這起犯罪是預謀殺人。阿強的角色儘管有黃銘泉頂替,卻也難逃擄人、殺人共犯之嫌。檢方於是再回頭訊問黃春棋,為什麼沒有老實供出黃銘泉,顯然是手足之情讓黃春棋扯了瞞天大謊。「之前我是為了保護我哥哥,怕我父母受不了,現在我想紙包不住火了。」在關於黃春棋的偵訊筆錄上,留有這樣一段文字。不過他還是緊咬著阿強不放,在同一份筆錄中,黃春棋說,「他(黃銘泉)告訴我他很後悔,就離開了(逃往泰國),他叫我不要打勒贖電話,但阿強(徐自強)說拿不到錢他不甘心。」這分明還是要把罪過加諸在阿強身上(根據陳憶隆的說法,黃銘泉殺害黃春樹之後,人都傻掉了,也許是因為害怕,才逃出國外)。
不過,黃春棋另外還補充說明,亦即因為阿強怕被害者家屬認出他來,所以從頭到尾都沒有出面打勒贖電話。此一說法,也吻合為什麼在警方掌握的監聽資料中,只有黃春棋、陳憶隆兩人和家屬之間的對話,從頭到尾都沒有阿強的聲音。看似言之成理,但在阿強投案之後,黃春棋這套說詞其實也不能說沒有破綻。
很快的,緊接陳憶隆落網,檢方一個月後,就對黃春棋、陳憶隆、黃銘泉和阿強四人求處死刑。檢察官認為,這起案件四名被告涉嫌預謀擄人勒贖鉅款,擄走被害人黃春樹當天即先滅口,再向家屬勒贖七千萬,贖金一度還增加到一億元,其手法相當殘酷,完全泯滅天良。四人正值青壯,觸犯重典,固令人惋惜,但因好逸惡勞,不思奮進,為謀不法之財,致人於死,本件犯行披露後,致人心惶惶,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罪無可逭,有與社會永久隔離的必要(指死刑)。
原本以為只要避避風頭,風波過了,夫妻兩人又可回到山腳村那處檳榔攤做生意,偶爾開車到城裡走走,又或者騎著摩托車買些小吃打打牙祭。沒想到,事情似是沒完沒了。他從一個砂石車司機,變成檳榔攤老闆,最後成了綁架撕票案的犯嫌,因而成了通緝犯,在被通緝的過程,因為他人的供述,一下又從主謀成為共犯,不過,卻又涉及了預謀殺人。
如果早知道等在臍帶纏繞、肺炎、車禍斷腿這些劫難後的人生是這樣,阿強自己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阿強的媽媽幾度將他從鬼門關救回,還曾為了阿強被罰半蹲,到學校跟老師理論,前一段人生的點滴,就只為了要把成年後的阿強送上刑臺?再逃下去,能躲到幾時?檢察官已經求處極刑,舉國民眾都確信阿強就是個十惡不赦、心狠手辣的歹徒。為逃避懲罰而四處藏匿,其心境不難理解。但是,自認根本沒有參與犯行,卻遭到警方鋪天蓋地的通緝,這一類的躲藏或許就少有人能夠體會了。
「心情沉澱下來後,你似乎也不認為那會是假的。」在阿強逃亡初期,和阿強夫妻、阿強父母同受煎熬的,還有阿強的姊姊。事過境遷,阿強的姊姊徐沛晴才終於敢在人前承認,自己當時確實一度以為自己的弟弟真的犯下此案。主要原因就是阿強跑掉了。徐沛晴每個禮拜都會回家探望自己的父母,看著淚流成河的母親,以及總是瑟縮在一旁的父親,徐沛晴內心有如刀割。母親篤信自己兒子的清白,一直說要找出證據證明阿強沒有犯罪,徐沛晴只能以回家看看自己父母的方式,讓他們感到身邊還有人可以安慰照應,卻又完全幫不上忙。她即使很想相信自己的弟弟,卻又拿不出隻字片語反駁報上所寫的那些東西。阿強想以暫時躲避的方式為自己尋找生機,卻無端拖累了一家人,他們同時也是那個時候,全世界唯一還對阿強的清白,抱持著最後一點信心的人。
第一幕 火速破案
炎熱潮溼的泰國芭苔雅,臨海而立,風光旖旎,即使進入十二月最涼爽的月分,每日最高溫仍有達攝氏三十度以上的可能。此處市集車水馬龍,沿途海濱度假酒店林立,長年門庭若市,因而素有「東方夏威夷」之稱。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芭苔雅正值觀光熱季,遊客熙來攘往,徐徐海風讓人心曠神怡,卻有人無視這座城市綺麗多姿的景貌,心起殺機。一位名叫「張保羅」的男子,當月十六日即遭人縊死在下榻飯店的浴室內。
他的死狀奇慘,透露潛伏在案情裡的深仇大恨。飯店人員發現張保羅時,他的雙手、雙腳均受到綑綁,凶手同時再以床單撕成的繩子纏繞住他的頸部,最後張保羅整個人且被懸吊於浴室的氣窗前,仿若一場警告意味濃厚的私刑。一個人若欲尋短自盡,其實根本不必這麼大費周章。透過泰國警方蒐證資料顯示,現場不僅有兩人以上搏鬥跡象,張保羅的臀部還有清楚受人在地上拖行的紅腫傷痕。
就在飯店業者因為這起血腥凶案惴惴不安之時,泰國警方卻在張保羅的房間內發現一本中華民國護照。護照的照片和死者面容相符;但英文的署名和他登記住房的「張保羅」名字大有出入。泰國警方隨即將採集的指紋傳真到臺灣的刑事警察局請求協查其身分。經過刑事局指紋室比對,赫然發現張保羅竟是同年九月,犯下內湖房屋仲介商黃春樹綁架撕票案的主嫌之一—黃銘泉。
這項消息經臺灣媒體披露,原先似已真相大白的綁票案,進而再掀波瀾。主要因為這起案件,當時除已被逮獲、正關在看守所裡的兩名同夥,以及在泰國橫死的黃銘泉外,尚有一名綽號「阿強」的嫌犯在逃。警方因此懷疑,黃銘泉是和阿強一起潛逃泰國,之後因為彼此利益擺不平而起衝突,結果引來不測。如今非得將本名徐自強的阿強緝拿歸案,否則綁票案的來龍去脈何以水落石出。更何況,警方數月前宣告偵破這起綁架案時,甚至是以「主謀」身分對徐自強發出通緝。
兩嫌被逮,黃銘泉已逝(幕後原因迄今未明),新聞媒體大篇幅報導的汐止山區富商遭撕票案,自九月間發生數月後,徐自強仍不見蹤跡。他的下落不明,讓警方火速偵破的擄人勒贖事件徒留一條大尾巴。
擄人勒贖唯一死刑
內湖房屋仲介商黃春樹遭綁架撕票的年代,尚是臺灣擄人勒贖必處唯一死刑的年代。不過,極刑的威嚇性,好像也無法確保利慾薰心或被逼上絕路的普通人不會變成惡棍,年年還是有綁架案發生。一九八七年底,新竹市東區東門國小四年級學生陸正,自補習班下課後失蹤,從此音訊全無,此一早期幼童綁架案大舉震驚了臺灣社會;一九八八年,另有曾成山因積欠債務無力償還,綁架撕票表哥的三歲稚子;一九八九年,則有張木火、卓三貴共同犯下多起綁架案,並殺害肉票;一九九○年底,新光集團少東吳東亮被胡關寶犯罪集團綁票,歹徒一開口就是索討一億元贖金,名人效應加上天價贖金,使得此案益發喧騰;一九九一年,「反共義士」卓長仁綁架了當時的國泰醫院副院長王欲明之子王俊傑,勒贖五千萬,是為英雄人物最大的嘲諷;一九九二年,無業的郭金村、蕭素貞,被控共謀擄掠年僅三歲的韓小弟弟,而後向其家人勒贖且撕票;一九九三年,吳欽明、吳火土兄弟因經濟拮据,共同駕計程車綁架撕票乘客;一九九四年,王禎耀將三名債務人擄走,並活活燒死於車內……綁匪之中,有尚在獄中等待槍決者,有已遭槍決者,從舉國矚目的陸正案開始,前列歹徒的下場和遭遇,似乎沒有帶來必然的警醒作用。一九九五年九月,內湖房屋仲介商黃春樹也就因此難逃一劫。
第二天
清晨,電話鈴響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清晨四點鐘左右,富甲一方的黃健雲,於睡夢中被一通電話吵醒,對方連名帶姓指名要找他,卻不待黃健雲回神,就把電話給掛了。由於兒子黃春樹前一天上午離家後即不見人影,黃健雲直覺這通電話可能和兒子的行蹤有關,最不希望的事情難道發生了?隔了五、六分鐘,家裡同一支電話再度鈴聲大作,四下靜謐無聲的大清早,聒噪的電話聲格外讓人感到不安。
對方說話了。但一開口,吐出的就是一把利劍:「你兒子現在在我手上,趕快準備七千萬做贖金,不可以報警。」不待黃健雲問個究竟,對方立刻又掛斷電話。歹徒反覆來電,倉促結束通話,也許是害怕被警方監聽,或者擔心被家屬識破犯局的機靈反應,但也可能純粹是心虛,因為心神緊張的下意識表現。
九月初,盛夏未盡尾聲,兩通電話,卻足以讓黃健雲背脊發涼。二十年前,黃健雲放棄彰化家族世代承襲的農務,北上改經營汽車材料行。乘著當年房地產熱潮,黃健雲順勢將手頭積蓄投入臺北縣(今新北市)汐止一帶的土地,土地交易獲利遠勝過汽車材料買賣,愈加激勵他改為投身房地產生意。很快的,他從一介鄉下農夫,而後一名小小汽車材料商人,轉眼財富三級跳,最終成為一間知名建設公司的大老闆,在地方上已非泛泛之輩。只是,沒想到世間常理,果真禍福相倚,他的兒子黃春樹也是因此招致歹徒的覬覦。
通話結束,黃健雲拿起話筒,立刻轉撥電話給黃春樹的妻子黃玉燕,告知她的先生被人綁架了。黃玉燕原以為先生只是和平常一樣,偶爾在外應酬沒有回家,未感覺出反常跡象,這下才知道事態嚴重。
清晨五點半,歹徒再度來電。黃健雲早睡意全失,他必須振作精神,以應付接下來一連串和歹徒之間的糾纏。電話那頭,傳來的內容和前一通如出一轍,再也沒有任何僥倖的可能,黃健雲陷入的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擄人勒贖案。
自接到歹徒第一通電話後,黃健雲當天上午七點不到,立刻前往自家附近的警察局報案,他明快地要把營救兒子的行動交給警方。事後證明,黃健雲起初並未考慮私了,自行和歹徒周旋應對,確實是正確的選擇,如此警方才得以立即成立專案小組,短短二十八天就將嫌犯之一逮捕,再循線掌握同謀,一舉破案。不過,一個月內即可讓歹徒現形,某種程度,或者也要歸因歹徒作案手法未必縝密無失,甚至還處處留下讓警方得以布局收網的線索。
歹徒為了逃避追蹤,多次仿效電影情節,每每來電和家屬對話,都盡可能精簡通話過程,及至察覺所使用手機已被掌握,便改以公用電話聯繫,不過,此時警方早已全程守在黃家,逐一監聽每一通來電。
也就是在事發兩個多禮拜後,黃健雲在一次和歹徒的對話中,為判斷兒子的生死,要求歹徒說出黃春樹女兒的生日,結果對方支吾其詞,沒有給出答案,那麼,已遭撕票的機率為之大增。逝者已矣,縱然再抱一線生機,此時則以逮人為首要之務,至少錢不要再落入歹徒口袋。在敵暗我明下,黃家人持續和歹徒針對贖金討價還價,價碼一度從原本的七千萬降至一千五百萬,後因為歹徒認為黃家和警方合作,導致他們取贖難度增高,一氣之下,再把贖金提高至一億元。來來回回,最後是黃春樹的妻子黃玉燕苦苦哀求,雙方才以一千六百萬說定。
第三天
第四幕 大逃亡
埋伏在公用電話停附近的警察很快地就將黃春棋逮獲,過程似乎比警方原先的沙盤推演還要順利。不過當晚,就在電話亭附近,他們隱約察覺似乎另外有個人趁亂逃跑。根據警方掌握的監聽紀錄,他們懷疑同一時間跑掉的那個人,就是亦曾打電話向被害者家屬勒索贖金的陳憶隆。
事發隔天中午,阿強接到一通陳憶隆的來電。阿強直覺,因為賭博電玩生意屢屢被警方查扣的陳憶隆,這回八成又是要開口跟他借錢。阿強的太太卓嘉慧平常除了和阿強一起照顧檳榔攤的生意,之前還曾在陳憶隆的電玩店打工,阿強去店裡接太太下班時,偶爾會到店裡順便玩上兩把,因為多了層主雇關係,阿強進而結識太太的老闆—陳憶隆。阿強有時會邀請他到家裡玩牌,那段時間,他們的牌搭子就是黃銘泉和黃春棋。因為手頭經常短缺,經濟狀況相對穩定的阿強,便多次成為陳憶隆調頭寸的對象。
民國八○年代,賭博性電玩以其迷幻人心的誘惑力,吸光了多少人的青春和財富。遊藝場裡只要擺著幾臺賽馬機、水果盤、十三章麻將和吃角子老虎,天天都有人捧著大把鈔票上門。賭博性電玩的樂趣從來不只為了追求贏錢的快感,那是一種「癮頭」,讓人純粹沉溺在機率做主的靡想之中。即使一天下來浪擲千金,僅開了一次「役滿貫」(為日本麻將最高級的牌型,達成條件相當困難),還是有可能鼓舞你明天重返現場再接再厲。
當時賭博性電玩皆是非法營業,就像色情業者一樣,必須躲著陽光牟利。於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業者遭警方查扣的消息出現。一九九四年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曾雷厲風行掃蕩城裡的電玩業,一併阻斷了賭博性電玩的後路。此舉評價有好有壞,但營業場所總是龍蛇雜處,客人出入背景少有單純,因而在生活平實規矩的市民眼中,至少算得上是某種程度的德政。
陳憶隆即在賭博性電玩時興、尚有鑽營空間的年代,於桃園縣內屢仆屢起。一九九四年被以賭博罪判刑五個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隨即再犯,之後又被以賭博罪另外再判了五個月。直到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在參與綁架黃春樹之前,他再因賭博罪名,遭處有期徒刑七個月,是個不折不扣的累犯。每每被查扣賭博電玩機臺,陳憶隆就得再找門路籌措資金,好讓自己東山再起,因而前前後後向阿強借了數十萬元。阿強原本以為可以從中收取一些利息,誰知為了這點蠅頭小利,日後竟讓他付出無比慘痛的代價。
阿強直覺不對勁。陳憶隆那回除了再向他情商現金周轉外,還沒頭沒腦告訴他,警察早上曾經找上門,剛好他不在家,警察於是留話給他太太,說是要找他自己和阿強。難不成又是電玩店被查扣,要被判刑罰錢?陳憶隆已是前科累累,刑期說不定會更重。不過,警察找陳憶隆本來就不是什麼新鮮事,指名要找阿強,又是為了什麼?阿強追問緣由,陳憶隆卻始終支吾其詞,說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便把電話掛了。滿心狐疑的阿強之後回撥了一通電話給陳憶隆的太太,想問清楚到底警察找他做什麼,陳憶隆的太太又說警察根本沒提到他的名字,只拿走了家裡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電話簿。只是,那本電話簿裡阿強的名字剛好也在其中。
第四天
更加詭異的是,就在陳憶隆來電沒多久,而阿強拒絕再次拿錢出來幫忙應急後,輪到黃春棋打電話給他。電話那頭,黃春棋問阿強人在哪裡,阿強說自己正在檳榔攤。「喔,這樣啊,那我等一下去找你。」黃春棋話一說完就匆匆把電話掛斷。接連兩通讓人摸不著頭緒的來電,阿強其實心裡有數,這兩人一定惹出了什麼麻煩。當時已遭逮捕的黃春棋,顯然是受警方指示,被要求打電話給阿強,探一探阿強的動向,且謹慎小心不要打草驚蛇,讓這位黃春棋口中的「綁架撕票案主謀」不小心給跑了。
結束通話,阿強轉身離開檳榔攤,回到鄰近向岳母承租的公寓,愈想愈不對勁。約莫下午兩點鐘左右,租屋處的電話響起,這次是岳母打來的。岳母跟他說,「有一群人現在在檳榔攤外面,說是要找你。」阿強當時心想,黃春棋還沒來,檳榔攤外倒是圍著一群彪形大漢,會不會是他前不久曾出面替黃春棋租車,才讓自己惹上麻煩?如果找他的是警察,是不是因為黃春棋尚有別的案子通緝在案?如果找他的是黑道分子(那群彪形大漢其實是便衣警察),又是否是為了黃春棋欠下的賭債而來?從阿強的租屋處探頭往外看,數十公尺外,剛好可以撇見平常他們夫妻看顧的檳榔攤。看著好幾個來意不善的陌生男子,在檳榔攤前左顧右盼,阿強一陣背脊發涼,自覺在這節骨眼上,恐怕還是不要貿然露臉,否則真不知道會有什麼意外發生。接著,阿強小心翼翼不被那群人發現,躡手躡腳地離開租屋處,打算在搞清楚狀況前,先到臺北閃避風頭。之後阿強的媽媽曾和阿強通過電話,並問他,為什麼警察要到家裡找人。阿強說,「我就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啊。」
從避鋒頭變成逃亡
此時此刻要離開山腳村前去臺北,已不若二十多年前阿強媽媽那般躊躇不前。年代不同了,山腳村和臺北之間的差異,因為時空變化而拉近了不少距離。不久前,阿強才帶著太太去九份玩,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星期,這回索性在抵達臺北後,阿強立刻又轉乘客運,避走九份。
住在九份那一天,阿強和媽媽持續保持聯絡,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警察要找阿強?以及為什麼又會有一群「凶神惡煞」也在問阿強的下落?阿強的媽媽勸告阿強,不如就在外頭再待個幾天吧,總之先避一避。他們只是住在鄉下地方的平凡人,不可能和誰結下深仇大恨,阿強和太太每天都忙著檳榔攤生意,阿強的媽媽已改行從事家庭理髮,這樣的生活背景,實在沒道理替自己惹禍上身。
隔天,眼看什麼事也沒發生,一頭霧水的阿強傍晚又回到了桃園,返底家門,卻覺氣氛仍讓人不安,阿強的媽媽又一次勸告阿強去外頭待個幾天等情況明朗一點再回來。阿強這回乾脆帶著太太一起匆匆離開,夫妻兩人二十八日便決定搭乘夜車南下高雄。那時的心情也許還不至於帶有「逃亡」的感受,只覺得是不是因為黃春棋的關係,自己被莫名所以的事件拖下水。果真如此,也許外出避個一兩天,鋒頭一過,一切就可重回軌道。
黃春棋有案在身,麻煩不斷,還積欠人家賭債,難不成是債主找黃春棋討債不成,轉而要他這個表哥代償?阿強愈想愈心煩意亂,卻又理不出半點頭緒。到了高雄,已是九月二十九日清晨,才下車,他和太太疲累不堪,以致玩興全無,加上這趟旅程,總是夾雜著一股不安的情緒,哪有心思規劃玩樂的路徑。(南下高雄前,他們其實先去了一趟九份,隨即再又搭車南下。)剛從桃園到九份,再從九份搭夜車抵達高雄,兩人在不知作何是好下,立刻又買了火車票,準備前往花蓮。也或許確實有那麼一絲絲心神不寧,他們才會有如此反常的舉措出現。
第五天
那年阿強才二十六歲,太太卓嘉慧年紀更小,一對兩小無猜的年輕男女,先是未婚生子,及至登記結婚,阿強退伍回來,也幸好阿強的媽媽適時挺身而出,願意替他們照顧幼子,兩人才得以一起出外賺錢養家。因為孩子那時留在阿媽家中,生活瑣務有阿媽打點,阿強和太太這趟避鋒頭之旅,才能了無牽掛。
但這只是驚心動魄的逃亡前奏。他們益發感到事有蹊蹺,但又不知道自己應該為了什麼事情覺得不安。就在高雄火車站大廳,準備搜尋前往花蓮的車班時,阿強看到一旁書報攤販賣的報紙,隨手一翻,赫然驚見自己的照片被登在其上,而且還被指為是一起綁架撕票案的主謀,阿強立刻翻搜自己的口袋和行李,把身上任何可以證明自己身分的證件全部撕毀丟棄。他們被報上的新聞事件嚇傻了,卻不是因為其內容多麼驚悚恐怖、駭人聽聞,也許自己從小不喜歡唸書,沒有過什麼值得稱道的偉大事蹟,但也從來沒做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那麼,自己又有什麼樣天大的本事,可以和人共謀擄人、勒贖,最後還將之撕票?
整起綁架事件雖非縝密嚴謹而至萬無一失,阿強又有什麼自信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他不就是山腳村一間檳榔攤的老闆,之前頂多做過卡車司機,他沒混過幫派,不是與人打打殺殺的料,有什麼理由會讓自己如此手段凶殘,犯下殺人毀屍滅跡?缺錢嗎?他還有能力借錢給朋友、親戚。雖說狗急也會跳牆,阿強又沒什麼事情被逼急。若是利慾薰心,當初又怎麼會因為不願開每一趟都超載的砂石車,而把砂石車賣掉,轉做檳榔攤生意?被自己的表弟一口咬定涉案,實在是晴天霹靂。原來真正的逃亡才即將展開。至於若真的沒做那件事,阿強又為什麼要逃?
擔心警方「曉以大義」
「因為怕被警察打到招認做了這件事。」這是阿強之後所說決定「逃跑」的理由。當初,阿強的媽媽也是以此建議阿強暫時先不要出面。阿強的媽媽因為在自家從事家庭理髮,客人進進出出,因而聽聞不少街談巷議。有個店裡常客的工作是到警察局送飯菜,只要來洗頭髮,她都會對阿強的媽媽如實轉述個人在警察局裡看到的情景。包括老是有人被打,或者哪個嫌犯因遭到警察拳打腳踢,哭著躲到桌子底下求饒。新聞報導出來,阿強媽媽的朋友紛紛前來關心,他們多數不相信平日木訥寡言的阿強,會是個如此心狠手辣的傢伙。於是他們七嘴八舌勸說阿強的媽媽,要她轉告阿強,如果沒做就先不要出來,免得被抓進去後,讓警察打到承認自己有做。阿強的媽媽心想,如果阿強沒有參與這起綁架撕票案,那麼躲起來應該也不算是犯罪的行為才對。想起小時候,阿強因為幫忙家裡洗碗,隔天睡過頭,上學遲到被老師體罰,阿強的媽媽為自己那個總是遭人誤解又不善辯駁的兒子,感到一陣心酸不捨。
「因為怕被警察打到招認做了這件事」而決定逃跑,理由很牽強嗎?多年以後,尤伯祥律師成了阿強這起官司的辯護律師之後,便經常有人向他問及,如果當初阿強沒有犯罪,又為什麼要逃亡?言下之意,似乎「逃亡」就必然是屬於犯罪者的專利。尤伯祥律師坦言,雖然他自始至終相信阿強並沒有涉案,但「逃亡」這件事,確實為阿強帶來十分不利的觀感。不過經過多年律師工作磨練,他終於理解,在當時那樣的警界文化中,「刑求逼供」不僅時有所聞,甚至還相當普遍,因此以他個人出身中產階級的背景,理所當然會認為「逃跑」就是心虛,是畏罪潛逃;可是,對臺灣屬於中下階層的族群來說,警察的面目有時是很可怕的。在他們的世界裡,警察會打人也會索賄,然後抓到就是打,打到你承認為止。阿強之所以會選擇逃跑並非沒有道理。只是我們的社會新聞,從來不會如實寫下某人是受到刑求招供才願意說出真相,讓一切水落石出。多半情況下,他們只會採用制式的表述方式,以「在警方『曉以大義』下,嫌犯終於坦誠不諱」一語簡單帶過。
第六天
話說回來,黃春棋被捕的隔天,不就在警察局遭到刑求了。九月二十七日,改由檢察官負責偵訊時,黃春棋便改口否認自己涉案。檢察官問他,既然如此,為什麼之前會在警局坦誠犯行,黃春棋則回答,因為他受不了警察刑求他。根據檢察官偵訊筆錄上的記載,黃春棋曾說,「警方借提時,把我眼睛矇住,吊起來灌水,還捏我奶頭,用不知道何物夾我手指。」雖然黃春棋一度翻供,並未對案情帶來轉圜,但我們不難推論,阿強如果沒有逃跑,下場可能也難逃被毒打一頓。那個年代,警局裡經常上演那樣的劇情。
警方尚且握有黃春棋涉案的監聽錄音帶,使得就算有刑求事實存在,黃春棋也難自圓其說,即使如此還得受皮肉之苦。那麼,換作是阿強呢?在警方未能掌握他參與犯罪的任何證據前,他更有可能被打到認罪,且坐實了刑求之下,何謂百口莫辯。只是這一切終究沒有發生。阿強沒有因此遭到刑求招供,但也因為偕妻逃亡之舉,徒然讓自己在社會大眾的眼光中成了一名畏罪潛逃、罪無可恕的大壞蛋。
阿強和太太從高雄又回到九份,這次住了十天,手邊盤纏幾乎用罄。於是改而移至臺北市,尋找租金便宜的套房。背著在逃共犯的身分,被害者家屬還公開懸賞一百萬,夫妻兩人這才體會到什麼是亡命天涯,一度有共赴黃泉的念頭出現。阿強成天不敢出門,只能靠太太每天搭公車,到數公里外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回家報平安,阿強的太太還臨時接了些手工,以為逃亡籌措生活費。
主謀黃銘泉現形
逃亡的同時,阿強努力回想,黃春棋等人指控他參與犯案的九月一日,他究竟做了些什麼。就在阿強和太太藏匿於臺北市,約莫一個月後,因為陳憶隆的落網,這起事件再度成為熱門新聞話題。報上寫著:黃春樹撕票案,共犯陳憶隆落網,逃亡近一個月,栽在雲林,陳嫌供稱,主謀係黃春棋胞兄黃銘泉,目前二嫌(黃銘泉和阿強)在逃。
陳憶隆的供述迥異於黃春棋,雖然將主謀人選轉向黃春棋的哥哥黃銘泉,卻也沒有半點替阿強脫罪。根據警方提供給媒體的消息,警方曾在二十五日逮捕黃春棋後,立刻趕赴桃園圍捕阿強和陳憶隆,結果兩人先一步聞風逃逸。陳憶隆逃跑內情不得而知,倒是阿強這一方的理解,和警方認知略有出入。阿強認為當時自己並沒有逃跑的計畫,警方也沒有真正對其展開圍捕行動,純粹因為警方在檳榔攤「撲空」,才讓一切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經過警方初步偵訊,陳憶隆供出,黃銘泉才是策劃這次綁架案的主謀,並實際參與綁架且出手殺害人質。他自己則是因為經營電玩店不善倒閉,積欠債務,才接受黃春棋的提議參與作案。在著手綁架前,黃銘泉及黃春棋即計劃將黃春樹綁走後,隨即予以撕票,再向黃春樹家人勒贖。因此他們在綁架黃春樹的前兩、三天,就在黃春棋兩兄弟帶領下,前往臺北縣汐止山區棄屍地點,先一步挖好埋屍坑洞,待九月一日將黃春樹綁走,便直接將他帶到棄屍地點,逼問家裡電話後,就著手予以殺害。
陳憶隆所言,其實和黃春棋先前對案情的描述相去不遠。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原本黃春棋落網時,媒體曾根據他的說詞,把綁架案主謀的矛頭指向阿強,突然全部又轉而變成是黃銘泉所為。也就是說,陳憶隆若沒有說謊,那麼黃春棋就是把自己哥哥黃銘泉的犯行全部嫁禍到阿強身上,以此掩飾黃銘泉在這起案件中的角色。
第七天
事實上,黃春棋也把部分犯罪事實推到陳憶隆一方,這讓陳憶隆落網後,迭有怨言。陳憶隆其實也希望透過詳細交代案情,減輕自己的罪責。根據陳憶隆的說法,他是在八月中旬,於阿強家中,和黃銘泉、黃春棋兄弟,以及阿強一起謀劃綁架案,黃銘泉因為常到海外投資生意,同時也想幫自己弟弟還債,所以兩人就邀他入夥,他們兄弟都計劃好了,在人手不足下,且還缺一部車,才找上他幫忙,而他自己因為有資金周轉的需求,於是就爽快加入。阿強則因為是黃銘泉的表弟,也有車,聽到這件事也就參上一腳。
和黃春棋供詞出入之處,除了黃銘泉和阿強的角色之外,陳憶隆還說,阿強事先買了三瓶硫酸,準備滅屍;但黃春棋的說法是他們是以汽油燒毀屍體。但既然有硫酸的一段,則又更加證實這起犯罪是預謀殺人。阿強的角色儘管有黃銘泉頂替,卻也難逃擄人、殺人共犯之嫌。檢方於是再回頭訊問黃春棋,為什麼沒有老實供出黃銘泉,顯然是手足之情讓黃春棋扯了瞞天大謊。「之前我是為了保護我哥哥,怕我父母受不了,現在我想紙包不住火了。」在關於黃春棋的偵訊筆錄上,留有這樣一段文字。不過他還是緊咬著阿強不放,在同一份筆錄中,黃春棋說,「他(黃銘泉)告訴我他很後悔,就離開了(逃往泰國),他叫我不要打勒贖電話,但阿強(徐自強)說拿不到錢他不甘心。」這分明還是要把罪過加諸在阿強身上(根據陳憶隆的說法,黃銘泉殺害黃春樹之後,人都傻掉了,也許是因為害怕,才逃出國外)。
不過,黃春棋另外還補充說明,亦即因為阿強怕被害者家屬認出他來,所以從頭到尾都沒有出面打勒贖電話。此一說法,也吻合為什麼在警方掌握的監聽資料中,只有黃春棋、陳憶隆兩人和家屬之間的對話,從頭到尾都沒有阿強的聲音。看似言之成理,但在阿強投案之後,黃春棋這套說詞其實也不能說沒有破綻。
很快的,緊接陳憶隆落網,檢方一個月後,就對黃春棋、陳憶隆、黃銘泉和阿強四人求處死刑。檢察官認為,這起案件四名被告涉嫌預謀擄人勒贖鉅款,擄走被害人黃春樹當天即先滅口,再向家屬勒贖七千萬,贖金一度還增加到一億元,其手法相當殘酷,完全泯滅天良。四人正值青壯,觸犯重典,固令人惋惜,但因好逸惡勞,不思奮進,為謀不法之財,致人於死,本件犯行披露後,致人心惶惶,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罪無可逭,有與社會永久隔離的必要(指死刑)。
原本以為只要避避風頭,風波過了,夫妻兩人又可回到山腳村那處檳榔攤做生意,偶爾開車到城裡走走,又或者騎著摩托車買些小吃打打牙祭。沒想到,事情似是沒完沒了。他從一個砂石車司機,變成檳榔攤老闆,最後成了綁架撕票案的犯嫌,因而成了通緝犯,在被通緝的過程,因為他人的供述,一下又從主謀成為共犯,不過,卻又涉及了預謀殺人。
如果早知道等在臍帶纏繞、肺炎、車禍斷腿這些劫難後的人生是這樣,阿強自己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阿強的媽媽幾度將他從鬼門關救回,還曾為了阿強被罰半蹲,到學校跟老師理論,前一段人生的點滴,就只為了要把成年後的阿強送上刑臺?再逃下去,能躲到幾時?檢察官已經求處極刑,舉國民眾都確信阿強就是個十惡不赦、心狠手辣的歹徒。為逃避懲罰而四處藏匿,其心境不難理解。但是,自認根本沒有參與犯行,卻遭到警方鋪天蓋地的通緝,這一類的躲藏或許就少有人能夠體會了。
「心情沉澱下來後,你似乎也不認為那會是假的。」在阿強逃亡初期,和阿強夫妻、阿強父母同受煎熬的,還有阿強的姊姊。事過境遷,阿強的姊姊徐沛晴才終於敢在人前承認,自己當時確實一度以為自己的弟弟真的犯下此案。主要原因就是阿強跑掉了。徐沛晴每個禮拜都會回家探望自己的父母,看著淚流成河的母親,以及總是瑟縮在一旁的父親,徐沛晴內心有如刀割。母親篤信自己兒子的清白,一直說要找出證據證明阿強沒有犯罪,徐沛晴只能以回家看看自己父母的方式,讓他們感到身邊還有人可以安慰照應,卻又完全幫不上忙。她即使很想相信自己的弟弟,卻又拿不出隻字片語反駁報上所寫的那些東西。阿強想以暫時躲避的方式為自己尋找生機,卻無端拖累了一家人,他們同時也是那個時候,全世界唯一還對阿強的清白,抱持著最後一點信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