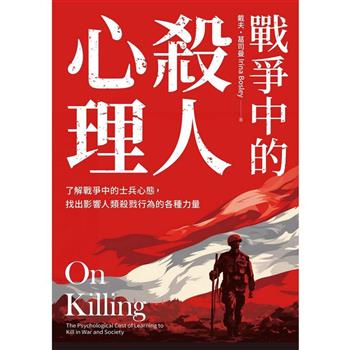第六章 恐懼統治
士兵作戰的時候,腦袋在想什麼?是哪些情緒反應讓大部分從長期作戰熬過來的士兵,最後卻滑落至瘋狂的深淵?這些情緒反應又是怎麼運作的?
讓我們以一個能夠呈現並整合恐懼、戰場疲憊、內疚、恐怖、仇恨、毅力與殺戮等因素的比喻性模型,作為了解與研究戰場精神創傷的參考架構。我在下面的章節中會逐一討論這些因素,以便更精確地了解士兵作戰時的心理與生理狀態。
第一個需要檢視的因素是恐懼。
以色列軍事心理學家班・夏立特進行的研究,是一一詢問剛從戰場撤下的士兵最害怕的事情。他本來以為士兵的反應會是:「死了」或「受傷,而且沒人管我死活」,沒想到士兵幾乎都強調,自己最害怕的事情是「同袍看不起我」,而不是受傷或戰死。
夏立特的另一個類似研究,是訪談一批沒有作戰經驗的瑞典維和部隊士兵。這次他得到的答案與他預期的一樣:士兵都說他們「作戰時最害怕的事情」是「死亡與受傷」。夏立特的結論是:作戰經驗能夠降低對死亡與受傷的恐懼感。
白庫與夏立特的研究都顯示,恐懼死亡與受傷並非造成戰場精神創傷的主因。事實上,夏立特發現,就算社會與文化灌輸士兵的訊息是作戰時該替自己著想、最應該害怕死亡與受傷,但等到他們上了戰場,最擔心的反而是無法完成壓在每一位士兵心頭的那個可怕責任。
「恐懼是導致作戰壓力出現的主因」,這個想法之所以為人普遍認可,原因之一是:這也是社會能夠接受的答案。電影與電視上難道不是經常說,只有笨蛋才不怕死、不怕受傷?然而,就算恐懼已經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我們仍然不願意正面檢討:到底我們恐懼的是什麼?是恐懼死與傷,還是擔心失敗與內疚?
恐懼研究一直就像是盲人摸象,有人以為摸到的是樹幹、牆壁,甚至有人認為摸到了一條蛇。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摸到的是整塊拼圖的一部分、摸到了一點真相。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覺得只能說出社會能夠接受的答案。我們比較會說出社會希望我們說的答案,比較不會說的是一開口就覺得不自在的答案。而社會告訴我們的、社會能夠接受的、社會覺得自在的那隻巨獸的名字,就是恐懼。
另一方面,一旦要面對內疚這個有強大影響力的因素時,很少人會覺得自在。恐懼是一種深埋每個人內心的具體情緒,而且來得快、去得也快。內疚的停留時間則多半為時甚長,而且可能是一種社會共有的集體情緒。捫心自問是個困難的工作,因為要面對許多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很容易因此迴避真相
士兵的兩難、恐懼的位置
恐懼死傷不是導致戰場精神創傷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當然,這並不是說,恐懼死傷導致精神創傷這種一般人普遍接受的觀點,沒有任何值得借鏡之處。而是說,真相的全貌其實更複雜。
我們也不應該就此認為,戰時發生的屠殺與死亡不那麼恐怖,害怕慘死與受傷也不會引發創傷。無論如何,單靠這些因素還不足以引發現代戰場大批出現精神傷員的現象。
還有其他諸多更深層的因素,讓士兵作戰時飽受精神創傷之苦。士兵排斥公然、積極地與敵人衝突,再加上害怕死傷,才是造成大部分戰場精神創傷與壓力的原因。因此,「恐懼統治」只是使士兵作戰時左右為難的一個因素而已。士兵墮入內疚與恐怖的深淵,而且掉落得那麼深,落入了俗稱「瘋狂」的領域,其原因除了恐懼外,還要加上戰場疲憊、恨、戰爭的恐怖等因素,以及士兵必須在這幾個因素與非得殺人間求取平衡的這個不可能任務。事實上,恐懼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因素。
第八章 內疚與恐怖的泥淖
感官的影響
除了恐懼與疲憊,還有一片恐怖之海圍繞著士兵,攻擊士兵的每一個感覺器官。
他們會聽到死傷者的悲喊,他們會聞到排泄物、血、焦屍與腐壞的餿味集合而成的屠宰場味道。
這些味道加起來,就是可怕的死亡味道。大地因為砲彈與炸彈無情肆虐而悲號時,他們會感覺到腳下的土地在顫抖。同袍在他們懷中死去時,他們則會感覺到生命顫抖著吐出最後一口氣、以及血液的最後溫度。他們與同袍相擁而泣時,會嚐到血與眼淚的鹹味,但是他們不知道、也不在乎是誰的淚。他們環顧四周,會看到:
滿地散落著一條條十五呎長的內臟,不小心就會絆到;橫腰而斷的屍身;手、腳、以及只剩脖子皮還連著的頭顱,最接近這顆腦袋的無頭屍在五十呎遠。夜色漸深,海灘上瀰漫著
燒焦的屍體惡臭。
——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黑暗,再見》(Goodbye Darkness)
奇怪的是,這些恐怖記憶似乎只對戰鬥員(實際作戰的士兵)衝擊最大,身在戰地的非戰鬥員、記者、平民、戰俘或觀察員,卻沒有出現這麼嚴重的影響。就像本書先前解釋過的,作戰士兵似乎會對於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產生深沈的責任感,甚至認為這些事情應該歸責於他個人,好像每一個戰死的敵人,都是他親手殺死的人;每一個死去的同袍都是他的責任。只要士兵在這兩種責任間擺盪一次,他的恐怖記憶中就會多添一層內疚。
理查・荷姆斯講過一位「勇敢、傑出」老兵的故事。戰爭結束已經快七十年了,這位老兵「一講到一位受士兵愛戴的軍官被砲彈碎片開腸破肚時,還是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年輕的時候,比較容易不去想這種事情,但是這些回憶會在老來時出現,夜晚時分縈繞在士兵身旁作祟。這位老兵告訴荷姆斯:「我以為我還蠻行的,不會去想當年那些可怕的事情。等到我老了,也不知道它們怎麼就從我當年把它們藏起來的地方出來。夜夜如此。」
即便如此、即便士兵周遭發生了這麼多事,但是這種恐怖只不過是合謀將士兵從痛苦大地驅離的諸多因素之一而已。
第十一章 殺人的重擔
抗拒在近距離殺戮同類的力道非常強。這種力道強到經常能夠擊敗自我保護本能日積月累的影響、領導階層的強制力、同儕的期待與保護同志性命的責任。
因此,士兵作戰時就會陷入這種左右兩難的悲慘情境。如果他克服了自己對殺戮的抗拒,並且在近距離作戰時殺了一名敵人,那麼,他的身上就會永遠背負著血腥內疚。如果他決定不殺敵人,那麼,同志戰死的血腥內疚、以及他的工作、國家、與志向蒙受的恥辱也會跟著他。他殺了人,該死;他不殺人,也該死。
殺,以及殺之後的內疚
威廉・曼徹斯特是二戰陸戰隊老兵,也是一位作者。他曾在近距離作戰時面對面殺了一名日軍,他感到悔恨與恥辱。他寫道:「自己傻傻地小聲說:『對不起』,然後吐了出來……吐得一身都是。我剛剛做的事情,背叛了我從小到大的教育。」其他有作戰經驗的老兵告訴我他們的近戰情緒反應,也在在附和曼徹斯特描述的恐怖反應。
暴力在媒體上呈現的方式,是告訴我們人可以很容易就丟掉終生的道德禁忌,或是任何其他既存的本能約束,毫不在意地殺人,作戰時也不會因此出現罪惡感。但是,曾經殺過人的人、或是願意聊起這件事的人,說法又不一樣。底下的引述段落,部分摘自基根與荷姆斯的書。這些段落也會出現在本書其他章節。我在此處引述這些文字的原因,是它們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士兵對殺人的情緒反應:
殺人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能做的最惡的事情。這種事情在任何地方都不應該出現。——一位以色列中尉
我竟然變成一個毀滅者,我相當自責。我覺得非常不安、無法形容的不安。我覺得自己與罪犯無異。——拿破崙時代的一位英國士兵
這是我第一次殺人。四周圍的人都散去以後,我走到那個我非常確定是我殺的德國人身邊、看著他。我還記得,當時我想著的是他年紀看起來有點大,應該已經成家生子了。我覺得很難過。——一次大戰英國老兵回憶第一次殺人後的反應
當時我沒有太多感覺,但我現在想起來:我屠殺了那些人,我謀殺了他們。——二戰德國老兵
我當場僵住了,因為那傢伙還是個孩子,大約十二到十四歲吧?當他轉過頭來看著我時,突然連身體都轉過來,手上拿著一把自動步槍對著我。我就這樣開火,對著那個孩子把一匣廿發子彈都打光了。然後,他就躺在那兒,我丟下我的槍、哭了出來。——美國特戰部隊軍官、越戰老兵
我又開了一槍,似乎打中了他的頭。血很多……我吐了出來,一直到其他人都來了才停。——以色列老兵回憶六日戰爭
那輛嶄新的標致汽車朝著我們開過來時,我們就對著它開火。裡面坐著一家人──有三個小孩。我哭了出來,但是我不能冒這個險……孩子、父親、母親,全在裡面,全都給殺了,但是我們就是不能冒這個險。——以色列老兵回憶入侵黎巴嫩作戰
我訪談保羅時,特別能感受到殺人引發的創傷有多嚴重。保羅是「海外作戰退伍軍人」的地區主管;二戰巴斯通戰役期間,他是一〇一空降師的士官。我問到他的戰時經歷與戰死同袍時,他毫不掩飾、侃侃而談。但我一問到他自己的殺人經驗時,他的回答是,戰場上通常不太能確定到底是誰殺了誰。說著說著他開始流下眼淚,久久之後他說,「但我記得有一次、我能夠確定……」,然後他開始啜泣,沒辦法講下去,老臉上出現痛苦的表情。我有點訝異,問他:「都這麼多年了,還很難過?」
他說,「對,都這麼多年了。」他就不願意繼續談下去了。
第二天他告訴我,「你知道嗎,你昨天問的問題,以後再問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不要因為問了那些問題傷了人。我沒事,你也看得出來,我可以面對,但是有些年輕點的,到現在還是傷得很重。沒必要又讓他們難過了。」這些回憶都是這些好心、善良的老兵身上,那些可怕、外人看不到的傷口的痂。
不殺,以及不殺之後的內疚
除了非常少數例外情形,每一位有作戰殺人經驗的人,內疚感都非常沈重。
士兵的內疚
許多研究都指出,一般來說,戰場上士兵的作戰動機不是仇恨或恐懼,而是團體壓力,以及下面四個因素的交互作用影響:一,在意同袍的看法。二,對部隊主管的尊敬。三,在意同袍與主管對自己名聲的看法。四,渴望對團體成就有所貢獻。
打過仗的士兵經常形容在戰場上弟兄們的關係,比夫妻關係還要緊密。約翰・鄂利(John Early)這位越戰老兵、也是羅德西亞戰爭的傭兵,是這樣對戴爾說的:
我這樣講,聽起來非常奇怪,但是作戰時會培養出一種愛情關係。原因是,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事,也就是你的生命,要靠你隔壁的人。如果他沒盡到責任,那麼你非死即殘。如果是你犯了錯誤,就換他非死即殘。所以你們之間的信任感一定要非常強才行。我敢說,除了親子關係外,這種信任感比任何事情都來得強,而且比夫妻關係強多了。你的生命在他手中,你把自己最珍重的東西委託給了那個人。
也因為這種形影不離的關係如此強烈,大部分作戰人員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表現會讓同袍失望。無數的社會學與心理學研究、老兵自述以及我進行的訪談,都清楚顯示士兵擔心對不起弟兄的力量。因為擔心無法盡全力幫助因為友誼與同袍之情而結合在一起的人,所引發的內疚與創傷會非常深刻。
但是,每一位士兵、每一名部隊幹部都曾經或多或少感受到這種內疚。對那些眼看朋友在身邊死去,自己卻沒有開槍的人來說,內疚可能非常深重。
幹部的內疚
領導幹部在作戰時擔負的責任也是一種棘手的兩難。他若是希望自己適才適所、表現優異,就必須愛他的屬下,靠著互依互存的責任感與情感建立深厚的關係。但是,到了最後,他卻沒有選擇,必須下達讓這些人可能因此陣亡的命令。
軍官與士兵、士官與二等兵之間的社會鴻溝,相當程度上讓上級得以安心派遣屬下赴難,若是屬下不幸戰死,這一道鴻溝又可以保護他們,讓那個不可避免的內疚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因為就算最優秀的領導幹部,也會犯下一些讓他們良心永遠不安的錯誤。一位好教練就算贏了比賽,也不忘分析自己的決策是否還有改進之處。一位好的作戰指揮官也是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會思考:如果他剛才換了個決定,那麼這些人、這些他視之如子、如兄弟的人,可能就不會陣亡。
但部隊領導幹部要能像下面這位老兵一樣反省,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該考慮的戰術我都考慮過了,該做的,我也都做了,但我們還是有幾個人陣亡。沒辦法。我們就是沒有辦法繞過那一片開闊地,只能直接穿越。所以,我的決定是錯誤的嗎?我不知道。(下一次)我是不是會做不一樣的決定?應該不會,因為我受訓所學就是這樣教的。我的決定是不是陣亡人數比較少的決定?沒有人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羅伯特・歐里少校、越戰老兵,引述自關恩・戴爾,《戰爭》
領導幹部腦袋裡出現這種想法,是危險的、是會致命的。部隊各層級幹部傳統上都能獲贈勳獎章或得到各種榮耀,這是一種對他們往後心理健康至為重要的作法。獲贈勳獎章、發布公報或其他表揚方式,代表這些領導幹部出身的社會強烈認可他們、告訴他們:他們表現很好,做了對的事情。他們在戰場上盡了責,雖然同袍因此喪命,但沒有人會因此怪他們。
否認與殺戮的沈重負擔
在殺人的責任與內疚間求取平衡,是出現戰場精神創傷的一個主要原因。哲學家暨心理學家彼得・馬林討論士兵的責任與內疚問題時說,士兵知道戰爭的代價是「死人不會活過來,成殘也就永遠成殘。別想否認自己的責任或過失,因為錯誤發生了就是發生了,永遠無可抵賴地寫在火焰中、寫在他人的殘肢斷臂上。」
是的,「錯誤發生了就是發生了,永遠無可抵賴地寫在火焰中、寫在他人的殘肢斷臂上。」錯誤導致的責任與過失,也許到了最後的確無可抵賴,然而,戰爭就像是一個大熔爐,要燒起熊熊爐火,靠的是許多名為否認的星星之火。殺人的負擔非常沈重,大部分士兵都不願意承認他們在戰場上殺過人。他們面對他人時會否認,面對自己時也會否認。丁特(E. Dinter)在他的著作中引述過一位鐵石心腸的老兵的話。這位老兵回答殺人的問題時刻意強調說:
現代戰爭中,殺人大部分都不是針對個人來的。有件事其實很少人明白,就是打仗時我們幾乎看不到德國人。將武器瞄準德國人射擊,然後看著他倒地,這種經驗很少人有,甚至步兵都很少有這種經驗。
甚至士兵們作戰時使用的語言,也在在否認自己犯下的惡行。大部分士兵不說自己殺人,而說敵人被擊倒、損耗、去除、掃蕩、清洗、摧毀。不承認敵人也是人,結果敵人變成一些有奇怪名字的動物。甚至武器也有暱稱。
我們的敵人在這種事情上也不遑多讓。麥特・布萊隆(Matt Brennan)說了一位派到他排裡的越南偵察兵的故事:
他過去一直是越共的死忠支持者,但在一班北越士兵錯殺他的老婆小孩以後,他就變了。
他現在很樂意跑在美國人前面獵殺北越士兵……他跟我們一樣,叫那些共產黨gook。有一晚我問他為什麼要叫北越兵gook ?
「昆,你也叫那些越共gook 或是dink,不會覺得奇怪嗎?」他聳聳肩說,「我沒差。總要叫他們什麼吧。你還真以為只有美國人會這樣?我自己的連、就是在叢林裡面打仗的那個連,叫你們『大毛猴』。我們會殺猴子,也……」這時他猶豫了一下,接著說:「也會吃猴子。」
士兵若是戰死,他的苦難也就一起被帶走了,但是殺死他的人,則會永遠和死者活在一起,最後死在一起。事情愈來愈清楚:戰爭就是殺人,而作戰時殺人,則會引發痛苦與內疚,這是人殺人的本質。戰爭的語言則可以幫助我們否認戰爭的真相,更嚥得下去戰爭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