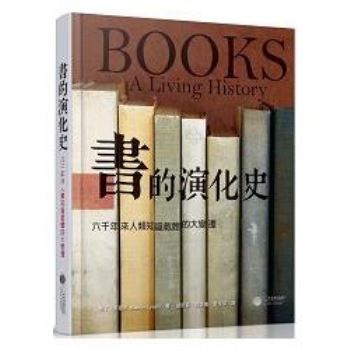書店興起
19世紀晚期,要買書有許多管道。傳統書店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商店則賣書兼賣食品雜貨、五金或服飾用品。在新英格蘭,雜貨店一般會有幾本《詩篇》選本和祈禱書出售。西班牙文讀者可以在街頭書報攤買到分冊出售的最新小說,還有像米蘭街頭稱為banchi的攤販銷售版畫、日曆、曆書與宗教小冊子給行人。流動小販在攜帶的一簍簍各色物品中也會放入幾本書。儘管如此,愈來愈多專門賣書的書店在小鎮與郊區出現,推廣了閱讀習慣,也將大眾整合為一個主流的大都會文化體。
賣書仍是受管制的行業。1848年以前,奧地利首相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試圖在德國與奧地利帝國施行審查制度,在此制度下,出版與販賣未經核准的文學作品都有招致罰鍰與入獄的風險。在法國,在拿破崙於1810年創立的制度下,想成為書籍銷售商的人必須申請執照(稱為brevet),提供四名由當地市長認證、可證實他品行端正的保證人,以及四份他具有執行這份工作所需專業能力的證言。如果申請通過,這名新的銷售商還必須宣誓效忠政府。政府必須知道新的書店不會成為散播顛覆性出版品的中心,也有足夠的資本能夠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執照制度一直到1870年才放寬。
在西方,書店密度穩定成長。以德國為例,1895年時,每1萬居民有一間零售書店,到了1910年,已經成為每8743名居民有一間書店。不意外的,最大城市的人均書店比鄉村和偏遠地區的多:1913年,每3700名柏林人就有一間書店,而萊比錫在1910年的人均書店更驚人,每1700人就有一間書店。書店數量的增加對於建立全國性的文學文化不可或缺。史上第一次,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買到同樣的流行書籍,從廣為人知的教義問答到《三劍客》(The Three Musketeers)這樣的小說皆然。
同樣在19世紀,鐵路書報攤將書本與報紙帶給了新的而且為數更多的消費者。W‧H‧史密斯(W. H. Smith,1825-91)於1848年在倫敦的尤斯敦車站(Euston Station)成立了第一個火車站書報攤。路易‧阿歇特(Louis Hachette)在1852年以鐵路圖書館(Bibliothèques des Chemins de Fer)跟進,並在法國政府同意下獨占火車站的書籍販售生意。今天,阿歇特仍擁有法國火車站的連鎖書報攤「赫雷」(Relais)兒童文學
最早專為兒童所出版的圖書都是教育讀本、行為指南和簡單的識字書,並且往往飾以動植物圖案和擬人化的字母。直到19世紀以前,英語國家的兒童往往都是從「角帖書」(horn-book)學識字的,這是一種小型帶短柄的木片,上面有一張紙,由一層透明的薄角片保護。紙上的內容通常是26個英文字母,基本的雙字母音節清單,以及一篇祈禱文,如〈主禱文〉。早期的識字讀本往往有一幅卷首插畫,描繪小男孩或小女孩坐在媽媽膝上學認字:直到19世紀晚期,兒童習得早期識字能力的環境通常都是家中,不是學校。
在19世紀,少數兒童讀物因為成為學校閱讀教材而享有盛名。其中包括伊索寓言與尚‧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95)的寓言故事,以及許多在19世紀初期演變為「童話故事」(fairy tale)的民間故事。另一個早期極具影響力的兒童故事集是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1697年的《鵝媽媽故事集》(Tales of Mother Goose),這本書被視為童話故事文類的奠基之作。
這些早期文集受到歡迎的程度,啟發了不少19世紀的兒童奇幻與童話故事,主題包括有魔法的物品和會說話的動物等等。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話故事集》(Fairy Tales)是一系列原創兒童故事,包括〈小美人魚〉與〈豌豆公主〉等已成現代經典的童話故事,於1835至45年間陸續出版,並逐漸蜚聲國際。1865年,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出版後旋即獲得好評;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的《木偶奇遇記》(Avventure di Pinocchio,1886)先是在義大利暢銷的連載作品,然後才以單行本形式風行全球。連阿思緹‧林格倫(Astrid Lindgren)在20世紀寫成的《長襪皮皮》,都有許多地方受到童話與民間故事文類的影響,書中滑稽而充滿奇想的故事以一名調皮的紅髮女孩為主角,她擁有超人的力氣與用不完的財富,得以超越一般瑞典小孩生活中的限制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初期出現了一批兒童小說,劇情寫實,無涉魔法,以年輕的主角為中心。在國際上獲得成功的作品包括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1883),L‧M‧蒙哥馬利(L. M. Montgomery)的《清秀佳人》(Ann of Green Gables,1908),與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婦人》(Little Women,1869),都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在1890到1930年之間,兒童文學成為圖書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版社開始有兒童文學編輯,公立圖書館也開設專供擺放童書的閱覽室。
童書是現代出版商重要且獲利豐厚的市場:20世紀的閱讀民調顯示,不論男女,閱讀的巔峰期都在大約12、13歲之時。在與其他媒體的競爭上,兒童圖書也特別成功,展現出在較為沉穩嚴肅的成人圖書出版世界中缺少的創意。立體書,有多種不同結局的書,以及提供聲音及觸感的書本都吸引了兒童讀者的興趣。不過,J‧K‧羅琳(J. K. Rowling)空前成功的哈利‧波特系列書籍(1997-2007)則顯示,較為傳統的兒童文學形式如奇幻/童話故事與校園故事文類的魅力不減。哈利‧波特七本系列書籍據說讓出版商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賣出超過4億本書,並且由時代華納拍成了賣座電影,讓作者羅琳在驚詫間於短短數年內成了億萬富翁。
兒童文學一直以來都吸引有創意的插畫家,他們的作品對刺激年輕讀者的想像力扮演了關鍵角色。以路易斯‧卡羅的愛麗絲系列書籍為例,它們與政治漫畫家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所繪的插畫之間就有著不可抹滅的連結。繪本書生產技術的進步,讓20世紀的插畫家得以創造出製作得美麗、多彩而豐富,有如藝術品的兒童書籍,從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感動人心的《野獸國》(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到波蘭繪者、同時是舞台設計師的詹‧平克斯(Jan Pienkowski)歡欣愉悅的《梅格與莫格》(Meg and Mog)系列。澳洲畫家陳志勇(Shaun Tan)畫筆下充滿奇想而讓人不安的世界,則不僅止於為印刷文字提供插畫,而是更進一步:他為《失物招領》(The Lost Thing,2000)與《別的國家都沒有》(Tales from Outer Suburbia,2008)所繪的插圖,即以言語溝通的不足為主題而發揮。
19世紀晚期,要買書有許多管道。傳統書店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商店則賣書兼賣食品雜貨、五金或服飾用品。在新英格蘭,雜貨店一般會有幾本《詩篇》選本和祈禱書出售。西班牙文讀者可以在街頭書報攤買到分冊出售的最新小說,還有像米蘭街頭稱為banchi的攤販銷售版畫、日曆、曆書與宗教小冊子給行人。流動小販在攜帶的一簍簍各色物品中也會放入幾本書。儘管如此,愈來愈多專門賣書的書店在小鎮與郊區出現,推廣了閱讀習慣,也將大眾整合為一個主流的大都會文化體。
賣書仍是受管制的行業。1848年以前,奧地利首相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試圖在德國與奧地利帝國施行審查制度,在此制度下,出版與販賣未經核准的文學作品都有招致罰鍰與入獄的風險。在法國,在拿破崙於1810年創立的制度下,想成為書籍銷售商的人必須申請執照(稱為brevet),提供四名由當地市長認證、可證實他品行端正的保證人,以及四份他具有執行這份工作所需專業能力的證言。如果申請通過,這名新的銷售商還必須宣誓效忠政府。政府必須知道新的書店不會成為散播顛覆性出版品的中心,也有足夠的資本能夠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執照制度一直到1870年才放寬。
在西方,書店密度穩定成長。以德國為例,1895年時,每1萬居民有一間零售書店,到了1910年,已經成為每8743名居民有一間書店。不意外的,最大城市的人均書店比鄉村和偏遠地區的多:1913年,每3700名柏林人就有一間書店,而萊比錫在1910年的人均書店更驚人,每1700人就有一間書店。書店數量的增加對於建立全國性的文學文化不可或缺。史上第一次,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買到同樣的流行書籍,從廣為人知的教義問答到《三劍客》(The Three Musketeers)這樣的小說皆然。
同樣在19世紀,鐵路書報攤將書本與報紙帶給了新的而且為數更多的消費者。W‧H‧史密斯(W. H. Smith,1825-91)於1848年在倫敦的尤斯敦車站(Euston Station)成立了第一個火車站書報攤。路易‧阿歇特(Louis Hachette)在1852年以鐵路圖書館(Bibliothèques des Chemins de Fer)跟進,並在法國政府同意下獨占火車站的書籍販售生意。今天,阿歇特仍擁有法國火車站的連鎖書報攤「赫雷」(Relais)兒童文學
最早專為兒童所出版的圖書都是教育讀本、行為指南和簡單的識字書,並且往往飾以動植物圖案和擬人化的字母。直到19世紀以前,英語國家的兒童往往都是從「角帖書」(horn-book)學識字的,這是一種小型帶短柄的木片,上面有一張紙,由一層透明的薄角片保護。紙上的內容通常是26個英文字母,基本的雙字母音節清單,以及一篇祈禱文,如〈主禱文〉。早期的識字讀本往往有一幅卷首插畫,描繪小男孩或小女孩坐在媽媽膝上學認字:直到19世紀晚期,兒童習得早期識字能力的環境通常都是家中,不是學校。
在19世紀,少數兒童讀物因為成為學校閱讀教材而享有盛名。其中包括伊索寓言與尚‧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95)的寓言故事,以及許多在19世紀初期演變為「童話故事」(fairy tale)的民間故事。另一個早期極具影響力的兒童故事集是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1697年的《鵝媽媽故事集》(Tales of Mother Goose),這本書被視為童話故事文類的奠基之作。
這些早期文集受到歡迎的程度,啟發了不少19世紀的兒童奇幻與童話故事,主題包括有魔法的物品和會說話的動物等等。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話故事集》(Fairy Tales)是一系列原創兒童故事,包括〈小美人魚〉與〈豌豆公主〉等已成現代經典的童話故事,於1835至45年間陸續出版,並逐漸蜚聲國際。1865年,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出版後旋即獲得好評;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的《木偶奇遇記》(Avventure di Pinocchio,1886)先是在義大利暢銷的連載作品,然後才以單行本形式風行全球。連阿思緹‧林格倫(Astrid Lindgren)在20世紀寫成的《長襪皮皮》,都有許多地方受到童話與民間故事文類的影響,書中滑稽而充滿奇想的故事以一名調皮的紅髮女孩為主角,她擁有超人的力氣與用不完的財富,得以超越一般瑞典小孩生活中的限制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初期出現了一批兒童小說,劇情寫實,無涉魔法,以年輕的主角為中心。在國際上獲得成功的作品包括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1883),L‧M‧蒙哥馬利(L. M. Montgomery)的《清秀佳人》(Ann of Green Gables,1908),與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婦人》(Little Women,1869),都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在1890到1930年之間,兒童文學成為圖書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版社開始有兒童文學編輯,公立圖書館也開設專供擺放童書的閱覽室。
童書是現代出版商重要且獲利豐厚的市場:20世紀的閱讀民調顯示,不論男女,閱讀的巔峰期都在大約12、13歲之時。在與其他媒體的競爭上,兒童圖書也特別成功,展現出在較為沉穩嚴肅的成人圖書出版世界中缺少的創意。立體書,有多種不同結局的書,以及提供聲音及觸感的書本都吸引了兒童讀者的興趣。不過,J‧K‧羅琳(J. K. Rowling)空前成功的哈利‧波特系列書籍(1997-2007)則顯示,較為傳統的兒童文學形式如奇幻/童話故事與校園故事文類的魅力不減。哈利‧波特七本系列書籍據說讓出版商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賣出超過4億本書,並且由時代華納拍成了賣座電影,讓作者羅琳在驚詫間於短短數年內成了億萬富翁。
兒童文學一直以來都吸引有創意的插畫家,他們的作品對刺激年輕讀者的想像力扮演了關鍵角色。以路易斯‧卡羅的愛麗絲系列書籍為例,它們與政治漫畫家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所繪的插畫之間就有著不可抹滅的連結。繪本書生產技術的進步,讓20世紀的插畫家得以創造出製作得美麗、多彩而豐富,有如藝術品的兒童書籍,從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感動人心的《野獸國》(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到波蘭繪者、同時是舞台設計師的詹‧平克斯(Jan Pienkowski)歡欣愉悅的《梅格與莫格》(Meg and Mog)系列。澳洲畫家陳志勇(Shaun Tan)畫筆下充滿奇想而讓人不安的世界,則不僅止於為印刷文字提供插畫,而是更進一步:他為《失物招領》(The Lost Thing,2000)與《別的國家都沒有》(Tales from Outer Suburbia,2008)所繪的插圖,即以言語溝通的不足為主題而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