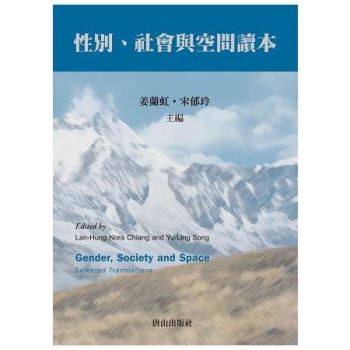節錄自〈台灣女性移民適應澳紐生活的過程:以澳紐的單棲媽媽為例〉
有關澳紐的台灣移民的研究結果
近十年來,台灣外移人數甚眾,每年有20,000至25,000名台灣人移居至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在1990年1月、1995年6月和2000年,移民往澳洲的台灣商業移民更達到了頂峰(Chiang,2001:700)。
作者利用澳洲1981至1996年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在雪梨、墨爾本以及布里斯本這些最多台灣移民居住的地區之中,有關他們的職業結構。我們發現,台灣移民的失業率在所有的移民族群體中是最高的。台灣男性在經濟上,如收入水平、職業地位和勞動力參與,都較女性成功。台灣出生的男性移民多數從事批發、零售、飯店及餐飲業,其次是商業、房地產和商業服務;而大多數女性則從事教育及社區服務。同時,前者多從事經理、行政和專業職位;後者則出任文職、銷售和服務性工作。在澳洲的台灣移民多數因為持有當地無效的海外學歷和資格證明,加上英文欠佳,又缺乏當地知識(local knowledge),還有因為其他制度性的歧視原因,導致出現向下社會流動的情況。儘管他們擁有中產階級的背景、高學歷及優秀的企業管理技能,但是因為英文程度欠佳,並且不願意接受比以前低下的工作,以致較難成立公司或者獲得工作(徐榮崇、姜蘭虹,2001;Chiang & Kuo,2000)。爾後研究又發現,他們在澳洲的經濟參與模式主要為自雇和受雇於台灣公司(姜蘭虹、宋郁玲,2001)。 就業不足和向下流動在近年移民群體中非常普遍,他們因此需要借助其他的收入來源,如儲蓄和在台灣工作。他們的流動模式創造了「太空人」現象,跨國家庭和回流移民、第二代移民的跨文化教育經驗,以及新的身分認同,這些問題無論在輸出地還是接收地,都需要深入地再進行研究。
儘管如此,大多數的台灣移民都有個人物業,而且大部分住在澳洲較富裕的市郊,如布里斯本的Mt. Omanney、Westlake、Cleveland和Eight Mile Plains;墨爾本的North Balwyn、Kew和Glen Waverly;雪梨的Chatswood、St. Ives和Killara(徐榮崇、姜蘭虹,2001)。對台灣移民遷居的田野調查(微觀)研究中,我們發現收入和住房預算、子女教育、居住地和工作場所與商店的距離,以及朋友的建議,均是他們選擇居所位置的考慮因素。而居住地的選擇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並且反映了個人的偏好與經驗,以及生活環境和房價的影響。近年,移民對擁有游泳池和庭院的別墅興趣漸減,這是由於他們沒有時間使用這些設施。故此,移民會遷居至其他地方。
移民研究大多針對經濟調適做宏觀的描述(Ip, Wu & Inglis,1998;Wu,2003),沒有深入分辨兩性的移民原因、定居經驗和適應過程。徐榮崇(2002)在研究移民對選擇居住地的決策過程中,以「需要」和「資本」作為討論移民流動的分析框架。但是,這項研究只關注家庭的選擇,忽略了那些因丈夫回台謀生,而留在異國獨自肩負養育孩子責任的妻子需要。
本文以女性作為研究主題,尤其是那些丈夫已經回台,或者成了「太空人」,而與孩子留在紐澳繼續移民生活的女性。當許多男性暫時回台以謀生計,而年輕移民也回台找工作,實在談不上所謂移民導致了台灣的「人才流失」。
有關澳紐的台灣移民的研究結果
近十年來,台灣外移人數甚眾,每年有20,000至25,000名台灣人移居至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在1990年1月、1995年6月和2000年,移民往澳洲的台灣商業移民更達到了頂峰(Chiang,2001:700)。
作者利用澳洲1981至1996年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在雪梨、墨爾本以及布里斯本這些最多台灣移民居住的地區之中,有關他們的職業結構。我們發現,台灣移民的失業率在所有的移民族群體中是最高的。台灣男性在經濟上,如收入水平、職業地位和勞動力參與,都較女性成功。台灣出生的男性移民多數從事批發、零售、飯店及餐飲業,其次是商業、房地產和商業服務;而大多數女性則從事教育及社區服務。同時,前者多從事經理、行政和專業職位;後者則出任文職、銷售和服務性工作。在澳洲的台灣移民多數因為持有當地無效的海外學歷和資格證明,加上英文欠佳,又缺乏當地知識(local knowledge),還有因為其他制度性的歧視原因,導致出現向下社會流動的情況。儘管他們擁有中產階級的背景、高學歷及優秀的企業管理技能,但是因為英文程度欠佳,並且不願意接受比以前低下的工作,以致較難成立公司或者獲得工作(徐榮崇、姜蘭虹,2001;Chiang & Kuo,2000)。爾後研究又發現,他們在澳洲的經濟參與模式主要為自雇和受雇於台灣公司(姜蘭虹、宋郁玲,2001)。 就業不足和向下流動在近年移民群體中非常普遍,他們因此需要借助其他的收入來源,如儲蓄和在台灣工作。他們的流動模式創造了「太空人」現象,跨國家庭和回流移民、第二代移民的跨文化教育經驗,以及新的身分認同,這些問題無論在輸出地還是接收地,都需要深入地再進行研究。
儘管如此,大多數的台灣移民都有個人物業,而且大部分住在澳洲較富裕的市郊,如布里斯本的Mt. Omanney、Westlake、Cleveland和Eight Mile Plains;墨爾本的North Balwyn、Kew和Glen Waverly;雪梨的Chatswood、St. Ives和Killara(徐榮崇、姜蘭虹,2001)。對台灣移民遷居的田野調查(微觀)研究中,我們發現收入和住房預算、子女教育、居住地和工作場所與商店的距離,以及朋友的建議,均是他們選擇居所位置的考慮因素。而居住地的選擇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並且反映了個人的偏好與經驗,以及生活環境和房價的影響。近年,移民對擁有游泳池和庭院的別墅興趣漸減,這是由於他們沒有時間使用這些設施。故此,移民會遷居至其他地方。
移民研究大多針對經濟調適做宏觀的描述(Ip, Wu & Inglis,1998;Wu,2003),沒有深入分辨兩性的移民原因、定居經驗和適應過程。徐榮崇(2002)在研究移民對選擇居住地的決策過程中,以「需要」和「資本」作為討論移民流動的分析框架。但是,這項研究只關注家庭的選擇,忽略了那些因丈夫回台謀生,而留在異國獨自肩負養育孩子責任的妻子需要。
本文以女性作為研究主題,尤其是那些丈夫已經回台,或者成了「太空人」,而與孩子留在紐澳繼續移民生活的女性。當許多男性暫時回台以謀生計,而年輕移民也回台找工作,實在談不上所謂移民導致了台灣的「人才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