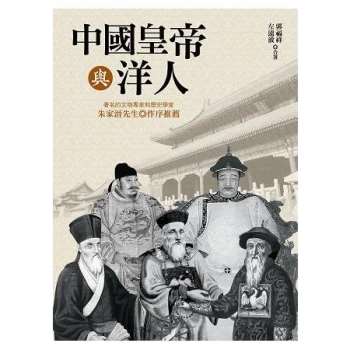第一章/
宋以前的帝王與外國人
帝王與外國人的接觸,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歷史源遠流長。據中國史籍記載,早在堯、舜、禹時代,就有西方的崑崙、渠搜、析支等國前來朝貢。「堯在位七年……有抵支之國,獻重明之鳥」。這種鳥「狀如雞,鳴似風,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博逐猛虎,使妖災不能為害」。(《太平廣記》卷四六○)而渠搜則於堯在位十六年來貢,所貢何物,史無明文。渠搜國即今塔吉克斯坦費爾干納一帶,朝貢之路漫長而艱辛,貢使能來到東土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中國方面,帝王主動與外國的交往,大約始自周穆王。據說穆王時犬戎勢力擴張,阻礙了周與西北方國部落的往來,於是穆王西征犬戎,打開了通往大西北的道路。穆王來到極西的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受到了西王母的隆重接待,於是「樂而忘歸」。但由於地理知識的缺乏,那時人們對本土以外的世界了解甚少,加之交通不便,像這樣的情況並不很多。
只有到了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打通以後,才真正使中外交流變得空前繁盛起來。通過與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的接觸,中國皇帝們臥居室而曉天下,不斷地吸取異域文化的精華,為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提供了依據。
綜觀宋以前帝王與外國人的關係,在以下幾個方面是比較突出的:一是佛教東來之後帝王與外國僧侶研討佛法,二是唐代日本遣唐使和唐朝皇帝的接觸,三是景教教徒和唐代宮廷的密切關係。
第一節 帝王與東來佛僧
佛教產生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印度。此後影響不斷擴大,成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
中國帝王與佛教的直接接觸,文獻記載秦始皇時即已有之。《廣弘明集》卷十一載:
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賫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
這種近乎傳奇色彩的敘述,多被視為荒誕無據,不為史家所取。延至漢明帝永平年間,遣使往西域求法,這是公認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始。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弘明集》)
這也是中國皇帝與佛教接觸之始。其事即民間傳說中的白馬馱經故事,所建佛寺即洛陽白馬寺。由於有皇帝的支持,加之又附於當時盛行的黃老之學,佛教在中土發展很快。東漢桓、靈帝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隨著佛教地位的確立,佛典翻譯變得格外需要,西域各國如印度、月氏、安息、康居高僧相繼東來,在洛陽與漢族佛徒合作從事佛經的翻譯,自漢迄宋,蔚為大觀。在東來佛僧中,不乏被皇帝延聘入宮從事佛教活動者。
漢代著名的東來譯經師主要有安清和支婁迦讖。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本來可以繼承王位,但他卻讓位於其叔,自己乃出家修道,深究經藏,並離開本土,來到京師洛陽。安清從漢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年)至靈帝建寧四年(一七一年)在洛陽譯經,歷時二十三年之久。文獻說他所譯經典「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是中國佛經翻譯的鼻祖。支婁迦讖,月氏人,漢桓帝末年至洛陽,靈帝光和、中和年間譯經很多,有《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經。他「博學淵妙,才思測微」,「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存文飾」。這些佛學經典的翻譯,為其後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興盛準備了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佛教最繁盛的時期。寺廟林立,塔剎櫛比,吃齋念佛成為一時的社會風尚。誦經陣陣,木魚聲聲,構成了這一時期特有的社會文化景觀。因此,這一時期帝王崇佛、敬佛者很多,許多外國僧侶悠遊於天子腳下,出入於帝王宮中,為弘揚佛法做出了貢獻。佛圖澄,西域人,佛學造詣很深。晉永嘉四年(三一○年)至洛陽,想在這裡建寺廟,但由於戰亂未成。不久,他看到後趙石勒殘暴異常,便立志用佛法勸化石勒。於是他單人持杖策來到石勒帳下,由大將郭黑勒引見給石勒,受到石勒、石虎的禮敬。石勒曾特頒詔書稱讚他的高風亮節: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東祿匪願,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少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可知佛圖澄在後趙宮廷享有極高的地位。
鳩摩羅什,本天竺人,家世國相,為當地望族。其父聰明有節,棄相位出家,來到龜茲,被龜茲王聘為國師,後娶龜茲王妹,生下鳩摩羅什。在其母指導下,鳩摩羅什潛修佛學,故年輕時便「道流西域,名被東國」。西元三五七年,苻堅在關中稱帝,建元永興。他在位期間,便對鳩摩羅什的聲名有所耳聞。建元十八年,苻堅派遣驍騎將軍呂光征龜茲,臨出發前在建章宮為呂光餞行,叮囑他說:
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用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若克龜茲,即馳驛送行。
呂光不久破龜茲,但苻堅卻於第二年被殺,呂光只好帶著鳩摩羅什到涼州。三八六年,呂光在此稱帝,建立後涼政權,鳩摩羅什便一直待在涼州。呂光及其後繼者不敬奉佛教徒,因而鳩摩羅什雖在後涼十七年,但並沒有大的作為。與此同時,姚萇在長安即皇帝位,建立後秦政權。他對鳩摩羅什早有所聞,便派人至後涼邀請鳩摩羅什到長安。後涼怕鳩摩羅什輔佐後秦,成為後患,便不許他東去。後來姚興即後秦帝位,於四○一年派碩德西伐後涼,後涼戰敗,涼主呂隆上表歸降,姚興才把鳩摩羅什接到長安。(《高僧傳》在長安,姚興拜鳩摩羅什為國師,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政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姚興親自到逍遙園澄玄堂聽鳩摩羅什講解佛經,並同他一起校對佛典,在宮中建立佛堂,對長安的佛教影響極大。「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晉書》)此後到中國譯經傳教的外國著名僧侶還有菩提流志、拘那羅陀、闍那崛多、那連提耶舍、達摩笈多等。其中闍那崛多來自犍陀羅,是和其同伴智賢等十餘人經于闐、吐谷渾、鄯州,於五五九年到達長安的。後被周明帝請入後園共論佛法,共翻譯佛經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之多。那連提耶舍,烏仗國人,五五六年來華,投靠齊文宣帝,所受禮遇甚隆。
隋朝建立後,他奉敕譯經。五八二年七月,奉隋文帝之命入京,充任外國僧主,住大興善寺。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原,建大興,特加敕在城中的靖善坊立寺,命名為大興善寺,規制與太廟相同。為弘揚佛法,文帝又命在大興善寺設立譯場,先後召請印度和中亞名僧達摩般若、那連提耶舍、達摩笈多、闍那崛多住在這裡從事譯經活動,對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影響極大。至唐代,屢派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佛經多由中國僧侶主譯,外國僧侶的影響漸少。及至宋代,雖屢有印度僧人向皇帝進獻梵經之事,但多已流於形式,翻譯的重要著作很少,外國僧人對中國皇帝的影響已經變得很小了。
第二節 東天皇與西皇帝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早在兩千多年前,雙方就有了彼此間的交往。一七八四年在日本福岡發現的漢代「漢倭奴國王」金印便是這種交往的明證。其後又經過幾個世紀,至隋唐時期,兩國交流進入了黃金時代。次數眾多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到來,使中國皇帝對這個東方島國的了解不斷深入。在隋朝短短的三十七年中,日本共派出了四次遣隋使,一方面是為了學習中國的文化制度,掌握復興後的中國佛教,為大化革新後的日本提供借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朝鮮半島。其中第一次是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六○○年),《隋書‧倭國傳》載:「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這次遣使在日本方面沒有明確記載。七年之後,即隋煬帝大業三年(六○七年),日本又派出了第二次遣隋使,使者為小野妹子,翻譯為歸化人鞍作福利。在其遞給隋煬帝的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之語。作為海外的一個小國,居然以天子自稱,把自己與中國皇帝完全等同起來,這種「傲慢」態度大大刺傷了隋煬帝的自尊心。據說隋煬帝看了國書後大為不悅,很不滿地對負責外交的鴻臚卿說:「蠻夷中遞交來的國書中,如有不懂禮貌的,不准再向我彙報。」隋煬帝沒有接受日本國書,但又不能打擊其遣使來朝的熱情,於是在小野妹子回國時,隋朝派出了裴世清作為宣諭使帶著隋煬帝的書信來到日本。信中說:「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知……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隋煬沒有用國書的形式答覆日本,令小野妹子空手而回,從而表示了他的不滿。同時他自己又派出了宣諭使,稱讚日本的朝貢,顯示了一個大國皇帝的寬容。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鑑,第二年當小野妹子為護送裴世清再一次訪問中國時,所帶來的國書不再是「日出處於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而是變成了「東天皇敬問西皇帝……」,用「天皇」和「皇帝」分別稱呼各自的最高統治者,將二者明確區別開來,這在中國方面是比較容易接受的。唐朝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時代,那時的中外友好交往盛況空前。「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正是這一歷史階段的真實寫照。在與唐朝交往的國家中,日本是其佼佼者。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同唐朝的交往,有唐一代,從唐太宗貞觀四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的二百六十四年的時間裡,日本共派遣了十六次遣唐使,其中包括送唐客使三次,迎入唐使一次。這些使團人數最多時達五六百人,少的也有一百多人。隨同遣唐使者而來的還有大批的入唐僧和留學生。他們在唐朝潛心學習中國文化,吸收其精華,將唐朝先進的制度文化帶回日本,為日本的發展提供了諸多借鑑。而唐朝對日本的外交使節也給予特別禮遇,「司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唐‧王維《送秘書晁鑒還日本國》序)其榮耀可知。
入唐的日本人中,不乏為官者。如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元正天皇靈龜二年(七一六年)被舉為遣唐留學生,參加了以多治比真人縣守為押使的第七次遣唐使。第二年出發,同行的還有玄昉、吉備真備和大和長岡等。當時唐朝正處於「開元之治」的輝煌時期,阿倍仲麻呂立刻被盛唐的氣魄所感染,不久即入太學學習,後參加了科舉考試,正式成為唐朝官吏,歷任左補闕、儀王友、秘書監、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兼安南節度使等官職。後來他曾試圖隨另一遣唐使回國,沒有成功,大曆五年(七七○年)正月在長安去世,在唐朝留居五十三年。
還有一個日本僧人空海,於中國文化造詣極高。他於八○四年到中國,除研習佛學外,還潛心書法藝術,其書藝受到唐順宗的喜愛。相傳空海在長安時,宮中帝御前有三間壁,上有王羲之書跡。一間不破,其餘兩間破損,王羲之的手跡泯滅,修理時無人敢下筆修補。唐順宗深愛空海書法,就命他補書。只見空海口咬一筆、兩手雙足各執一筆,五管齊下,須臾而成。唐順宗與在場的大臣們感嘆不已,見之目不暫捨。當寫到最後一個字時,空海又把剩餘的墨汁沃灌壁面,自然成字。唐順宗見此,低頭沉思片刻,贈給了他一個「五筆和尚」的美名。空海不久後回國,對日本書道產生了極大影響。開創盛唐局面的唐玄宗對日本的情況也非常關心,十分注意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對遣唐使的接待也是不遺餘力的。七三三年,日本派多治比廣成為遣唐大使、中臣名代為副使、平群廣成等為判官,分乘四船到中國,受到唐玄宗的接見。但不幸的是,多治比廣成回國才出長江口,便遇到了暴風襲擊。多治比廣成乘坐的第一船漂到多島,中臣名代乘坐的第二船漂到南海後返回中國,而平群廣成乘坐的第三船則漂到了崑崙國(今越南),有的被殺,有的被賣為奴,只有平群廣成等四人倖免逃回唐朝,第四船則下落不明。
唐玄宗得知這一情況後,採取果斷措施進行營救,急命安南都護與崑崙國交涉,要求放回第三船的倖存者。唐玄宗還命丞相張九齡代筆,以他的名義給日本聖武天皇寫了一封信,由中臣名代帶回。信中唐玄宗自稱「朕」,而稱聖武天皇為「卿」,講了自己如何關心遣唐使的安危,如何採取措施營救遇險的人,並讚揚日本為「禮儀之國」。在他的直接關懷下,剩下的人又安全返回日本。
七五三年,孝謙天皇派遣藤原清河為大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為副使的使團來到長安。唐玄宗在接見時,見到藤原清河高雅的舉止風度,禁不住稱讚說:「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真是禮儀君子之國啊!」隨後,他讓晁衡負責接待,帶領藤原清河等參觀了府庫及三教殿。為了表示友好,唐玄宗又命畫工畫了藤原清河的肖像,收藏於蕃藏中。第二年,藤原清河一行回國時,又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宴會。唐玄宗親自出席,並作詩送別: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駃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表達了祝他們一帆風順的心願,友好之情溢於言表。
八世紀中葉,由於中國內部的安史之亂,嚴重動搖了唐王朝的根基,日本向中國定期派遣使節的熱情明顯下降。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八九四年),管原道真上奏天皇請求停止遣唐使,得到批准,宣告中日文化交流黃金時代的結束。第三節 唐王與景教徒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派,此名初見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景教於西元五世紀產生於拜占庭,創始人為聶斯托里(Nestorius),所以也稱聶斯托里教派。聶斯托里原為敘利亞神甫,四二八至四三一年間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主張耶穌兼有人神二性的新說,與當時流行的基督教義不一致,引起眾多基督教信徒的反對,四三一年在以弗所(Ephese)宗教會議上被譴責為異端。聶斯托里本人遭到放逐,其教徒則逃亡波斯,此教遂由波斯傳播至中亞,並於唐貞觀九年由敘利亞人阿羅本傳入中國。就是在這個時候,唐朝皇帝開始接觸景教。
唐太宗時,唐朝聲威遠震中亞,西域諸國相率來朝。長安一城,萬國輻輳,波斯和阿拉伯諸國人,或使節,或商旅,或僧侶,紛紛經西域進入中國,其中也包括不少景教徒。西元六三五年,大秦國教士上德阿羅本攜帶大量景教經典,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長安,唐太宗聞訊,特命宰相房玄齡至西郊迎接並請入宮中。阿羅本先向唐太宗進呈了奏章,說明景教教義,奏章由房玄齡和魏徵譯成漢文。唐太宗對阿羅本待若上賓,經常讓他進宮講解有關教義,翻譯相關經典。隨著交往日深和對景教了解的增多,唐太宗越來越支持其教義。六三八年七月,他下令准許景教教士在國內傳教。唐太宗在詔書中說: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同時又命有關部門在長安義寧坊建造大秦寺院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後又讓畫工把他的肖像畫在寺內牆壁上,以表示對景教的重視。義寧坊大秦寺是史籍所載中國第一所正規的景教教堂。其後的唐高宗李治秉承前例,敕諭在各州建造景教堂,欽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在他的推動下,景教在中國迅速傳播,「法流十道,國富無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唐玄宗李隆基對景教更是極力鼓吹,親自為景教教堂題寫匾額。他不顧佛僧和道士對景教的攻擊,於開元初年讓其兄弟至教堂接受洗禮,建立壇場。天寶初,他又命大將軍高力士把太宗、高宗、睿宗、中宗及自己的寫真肖像拿到教堂安放,賜給教堂絹百匹。七一四年,大秦國教士佶和到長安朝見唐玄宗,玄宗讓他和教士羅含、普倫等十七人在興慶宮宣講景教法理,以擴大影響。另外,還有教士及烈曾兩次以朝貢的名義來到長安,都受到唐玄宗的接見。一次是七一三年,向唐玄宗進獻了許多奇器異巧之物,玄宗愛不釋手,為此侍御史柳澤還特意上書勸諫玄宗不要被這些譎怪淫巧之物迷惑。另一次是七三二年,進獻之物不詳,這一次玄宗特別賜給他紫袈裟一副、帛五十匹,以示褒獎。為了統一管理,減少麻煩,七四五年十月,特頒布詔書: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會要》卷四十九)
將全國景教教堂統改稱大秦寺,把景教在中國的發展推上了一個新台階。
唐肅宗李亨時又下詔在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這一時期著名的景教教士伊斯與肅宗過從甚密。伊斯「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開始在皇宮中為肅宗服務,深受倚重。後被授予軍職,在唐代名將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軍中充當謀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由於軍功,肅宗特賜以紫袈裟。他的能散祿賜、樂施好善在當時遠近聞名。其後的唐代宗李豫每逢生日,總要向景教教士賜天香,頒御饌,其待遇同佛教僧侶別無二致。
宋以前的帝王與外國人
帝王與外國人的接觸,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歷史源遠流長。據中國史籍記載,早在堯、舜、禹時代,就有西方的崑崙、渠搜、析支等國前來朝貢。「堯在位七年……有抵支之國,獻重明之鳥」。這種鳥「狀如雞,鳴似風,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博逐猛虎,使妖災不能為害」。(《太平廣記》卷四六○)而渠搜則於堯在位十六年來貢,所貢何物,史無明文。渠搜國即今塔吉克斯坦費爾干納一帶,朝貢之路漫長而艱辛,貢使能來到東土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中國方面,帝王主動與外國的交往,大約始自周穆王。據說穆王時犬戎勢力擴張,阻礙了周與西北方國部落的往來,於是穆王西征犬戎,打開了通往大西北的道路。穆王來到極西的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受到了西王母的隆重接待,於是「樂而忘歸」。但由於地理知識的缺乏,那時人們對本土以外的世界了解甚少,加之交通不便,像這樣的情況並不很多。
只有到了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打通以後,才真正使中外交流變得空前繁盛起來。通過與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的接觸,中國皇帝們臥居室而曉天下,不斷地吸取異域文化的精華,為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提供了依據。
綜觀宋以前帝王與外國人的關係,在以下幾個方面是比較突出的:一是佛教東來之後帝王與外國僧侶研討佛法,二是唐代日本遣唐使和唐朝皇帝的接觸,三是景教教徒和唐代宮廷的密切關係。
第一節 帝王與東來佛僧
佛教產生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印度。此後影響不斷擴大,成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
中國帝王與佛教的直接接觸,文獻記載秦始皇時即已有之。《廣弘明集》卷十一載:
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賫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
這種近乎傳奇色彩的敘述,多被視為荒誕無據,不為史家所取。延至漢明帝永平年間,遣使往西域求法,這是公認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始。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弘明集》)
這也是中國皇帝與佛教接觸之始。其事即民間傳說中的白馬馱經故事,所建佛寺即洛陽白馬寺。由於有皇帝的支持,加之又附於當時盛行的黃老之學,佛教在中土發展很快。東漢桓、靈帝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隨著佛教地位的確立,佛典翻譯變得格外需要,西域各國如印度、月氏、安息、康居高僧相繼東來,在洛陽與漢族佛徒合作從事佛經的翻譯,自漢迄宋,蔚為大觀。在東來佛僧中,不乏被皇帝延聘入宮從事佛教活動者。
漢代著名的東來譯經師主要有安清和支婁迦讖。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本來可以繼承王位,但他卻讓位於其叔,自己乃出家修道,深究經藏,並離開本土,來到京師洛陽。安清從漢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年)至靈帝建寧四年(一七一年)在洛陽譯經,歷時二十三年之久。文獻說他所譯經典「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是中國佛經翻譯的鼻祖。支婁迦讖,月氏人,漢桓帝末年至洛陽,靈帝光和、中和年間譯經很多,有《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經。他「博學淵妙,才思測微」,「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存文飾」。這些佛學經典的翻譯,為其後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興盛準備了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佛教最繁盛的時期。寺廟林立,塔剎櫛比,吃齋念佛成為一時的社會風尚。誦經陣陣,木魚聲聲,構成了這一時期特有的社會文化景觀。因此,這一時期帝王崇佛、敬佛者很多,許多外國僧侶悠遊於天子腳下,出入於帝王宮中,為弘揚佛法做出了貢獻。佛圖澄,西域人,佛學造詣很深。晉永嘉四年(三一○年)至洛陽,想在這裡建寺廟,但由於戰亂未成。不久,他看到後趙石勒殘暴異常,便立志用佛法勸化石勒。於是他單人持杖策來到石勒帳下,由大將郭黑勒引見給石勒,受到石勒、石虎的禮敬。石勒曾特頒詔書稱讚他的高風亮節: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東祿匪願,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少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可知佛圖澄在後趙宮廷享有極高的地位。
鳩摩羅什,本天竺人,家世國相,為當地望族。其父聰明有節,棄相位出家,來到龜茲,被龜茲王聘為國師,後娶龜茲王妹,生下鳩摩羅什。在其母指導下,鳩摩羅什潛修佛學,故年輕時便「道流西域,名被東國」。西元三五七年,苻堅在關中稱帝,建元永興。他在位期間,便對鳩摩羅什的聲名有所耳聞。建元十八年,苻堅派遣驍騎將軍呂光征龜茲,臨出發前在建章宮為呂光餞行,叮囑他說:
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用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若克龜茲,即馳驛送行。
呂光不久破龜茲,但苻堅卻於第二年被殺,呂光只好帶著鳩摩羅什到涼州。三八六年,呂光在此稱帝,建立後涼政權,鳩摩羅什便一直待在涼州。呂光及其後繼者不敬奉佛教徒,因而鳩摩羅什雖在後涼十七年,但並沒有大的作為。與此同時,姚萇在長安即皇帝位,建立後秦政權。他對鳩摩羅什早有所聞,便派人至後涼邀請鳩摩羅什到長安。後涼怕鳩摩羅什輔佐後秦,成為後患,便不許他東去。後來姚興即後秦帝位,於四○一年派碩德西伐後涼,後涼戰敗,涼主呂隆上表歸降,姚興才把鳩摩羅什接到長安。(《高僧傳》在長安,姚興拜鳩摩羅什為國師,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政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姚興親自到逍遙園澄玄堂聽鳩摩羅什講解佛經,並同他一起校對佛典,在宮中建立佛堂,對長安的佛教影響極大。「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晉書》)此後到中國譯經傳教的外國著名僧侶還有菩提流志、拘那羅陀、闍那崛多、那連提耶舍、達摩笈多等。其中闍那崛多來自犍陀羅,是和其同伴智賢等十餘人經于闐、吐谷渾、鄯州,於五五九年到達長安的。後被周明帝請入後園共論佛法,共翻譯佛經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之多。那連提耶舍,烏仗國人,五五六年來華,投靠齊文宣帝,所受禮遇甚隆。
隋朝建立後,他奉敕譯經。五八二年七月,奉隋文帝之命入京,充任外國僧主,住大興善寺。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原,建大興,特加敕在城中的靖善坊立寺,命名為大興善寺,規制與太廟相同。為弘揚佛法,文帝又命在大興善寺設立譯場,先後召請印度和中亞名僧達摩般若、那連提耶舍、達摩笈多、闍那崛多住在這裡從事譯經活動,對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影響極大。至唐代,屢派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佛經多由中國僧侶主譯,外國僧侶的影響漸少。及至宋代,雖屢有印度僧人向皇帝進獻梵經之事,但多已流於形式,翻譯的重要著作很少,外國僧人對中國皇帝的影響已經變得很小了。
第二節 東天皇與西皇帝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早在兩千多年前,雙方就有了彼此間的交往。一七八四年在日本福岡發現的漢代「漢倭奴國王」金印便是這種交往的明證。其後又經過幾個世紀,至隋唐時期,兩國交流進入了黃金時代。次數眾多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到來,使中國皇帝對這個東方島國的了解不斷深入。在隋朝短短的三十七年中,日本共派出了四次遣隋使,一方面是為了學習中國的文化制度,掌握復興後的中國佛教,為大化革新後的日本提供借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朝鮮半島。其中第一次是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六○○年),《隋書‧倭國傳》載:「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這次遣使在日本方面沒有明確記載。七年之後,即隋煬帝大業三年(六○七年),日本又派出了第二次遣隋使,使者為小野妹子,翻譯為歸化人鞍作福利。在其遞給隋煬帝的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之語。作為海外的一個小國,居然以天子自稱,把自己與中國皇帝完全等同起來,這種「傲慢」態度大大刺傷了隋煬帝的自尊心。據說隋煬帝看了國書後大為不悅,很不滿地對負責外交的鴻臚卿說:「蠻夷中遞交來的國書中,如有不懂禮貌的,不准再向我彙報。」隋煬帝沒有接受日本國書,但又不能打擊其遣使來朝的熱情,於是在小野妹子回國時,隋朝派出了裴世清作為宣諭使帶著隋煬帝的書信來到日本。信中說:「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知……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隋煬沒有用國書的形式答覆日本,令小野妹子空手而回,從而表示了他的不滿。同時他自己又派出了宣諭使,稱讚日本的朝貢,顯示了一個大國皇帝的寬容。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鑑,第二年當小野妹子為護送裴世清再一次訪問中國時,所帶來的國書不再是「日出處於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而是變成了「東天皇敬問西皇帝……」,用「天皇」和「皇帝」分別稱呼各自的最高統治者,將二者明確區別開來,這在中國方面是比較容易接受的。唐朝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時代,那時的中外友好交往盛況空前。「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正是這一歷史階段的真實寫照。在與唐朝交往的國家中,日本是其佼佼者。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同唐朝的交往,有唐一代,從唐太宗貞觀四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的二百六十四年的時間裡,日本共派遣了十六次遣唐使,其中包括送唐客使三次,迎入唐使一次。這些使團人數最多時達五六百人,少的也有一百多人。隨同遣唐使者而來的還有大批的入唐僧和留學生。他們在唐朝潛心學習中國文化,吸收其精華,將唐朝先進的制度文化帶回日本,為日本的發展提供了諸多借鑑。而唐朝對日本的外交使節也給予特別禮遇,「司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唐‧王維《送秘書晁鑒還日本國》序)其榮耀可知。
入唐的日本人中,不乏為官者。如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元正天皇靈龜二年(七一六年)被舉為遣唐留學生,參加了以多治比真人縣守為押使的第七次遣唐使。第二年出發,同行的還有玄昉、吉備真備和大和長岡等。當時唐朝正處於「開元之治」的輝煌時期,阿倍仲麻呂立刻被盛唐的氣魄所感染,不久即入太學學習,後參加了科舉考試,正式成為唐朝官吏,歷任左補闕、儀王友、秘書監、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兼安南節度使等官職。後來他曾試圖隨另一遣唐使回國,沒有成功,大曆五年(七七○年)正月在長安去世,在唐朝留居五十三年。
還有一個日本僧人空海,於中國文化造詣極高。他於八○四年到中國,除研習佛學外,還潛心書法藝術,其書藝受到唐順宗的喜愛。相傳空海在長安時,宮中帝御前有三間壁,上有王羲之書跡。一間不破,其餘兩間破損,王羲之的手跡泯滅,修理時無人敢下筆修補。唐順宗深愛空海書法,就命他補書。只見空海口咬一筆、兩手雙足各執一筆,五管齊下,須臾而成。唐順宗與在場的大臣們感嘆不已,見之目不暫捨。當寫到最後一個字時,空海又把剩餘的墨汁沃灌壁面,自然成字。唐順宗見此,低頭沉思片刻,贈給了他一個「五筆和尚」的美名。空海不久後回國,對日本書道產生了極大影響。開創盛唐局面的唐玄宗對日本的情況也非常關心,十分注意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對遣唐使的接待也是不遺餘力的。七三三年,日本派多治比廣成為遣唐大使、中臣名代為副使、平群廣成等為判官,分乘四船到中國,受到唐玄宗的接見。但不幸的是,多治比廣成回國才出長江口,便遇到了暴風襲擊。多治比廣成乘坐的第一船漂到多島,中臣名代乘坐的第二船漂到南海後返回中國,而平群廣成乘坐的第三船則漂到了崑崙國(今越南),有的被殺,有的被賣為奴,只有平群廣成等四人倖免逃回唐朝,第四船則下落不明。
唐玄宗得知這一情況後,採取果斷措施進行營救,急命安南都護與崑崙國交涉,要求放回第三船的倖存者。唐玄宗還命丞相張九齡代筆,以他的名義給日本聖武天皇寫了一封信,由中臣名代帶回。信中唐玄宗自稱「朕」,而稱聖武天皇為「卿」,講了自己如何關心遣唐使的安危,如何採取措施營救遇險的人,並讚揚日本為「禮儀之國」。在他的直接關懷下,剩下的人又安全返回日本。
七五三年,孝謙天皇派遣藤原清河為大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為副使的使團來到長安。唐玄宗在接見時,見到藤原清河高雅的舉止風度,禁不住稱讚說:「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真是禮儀君子之國啊!」隨後,他讓晁衡負責接待,帶領藤原清河等參觀了府庫及三教殿。為了表示友好,唐玄宗又命畫工畫了藤原清河的肖像,收藏於蕃藏中。第二年,藤原清河一行回國時,又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宴會。唐玄宗親自出席,並作詩送別: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駃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表達了祝他們一帆風順的心願,友好之情溢於言表。
八世紀中葉,由於中國內部的安史之亂,嚴重動搖了唐王朝的根基,日本向中國定期派遣使節的熱情明顯下降。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八九四年),管原道真上奏天皇請求停止遣唐使,得到批准,宣告中日文化交流黃金時代的結束。第三節 唐王與景教徒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派,此名初見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景教於西元五世紀產生於拜占庭,創始人為聶斯托里(Nestorius),所以也稱聶斯托里教派。聶斯托里原為敘利亞神甫,四二八至四三一年間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主張耶穌兼有人神二性的新說,與當時流行的基督教義不一致,引起眾多基督教信徒的反對,四三一年在以弗所(Ephese)宗教會議上被譴責為異端。聶斯托里本人遭到放逐,其教徒則逃亡波斯,此教遂由波斯傳播至中亞,並於唐貞觀九年由敘利亞人阿羅本傳入中國。就是在這個時候,唐朝皇帝開始接觸景教。
唐太宗時,唐朝聲威遠震中亞,西域諸國相率來朝。長安一城,萬國輻輳,波斯和阿拉伯諸國人,或使節,或商旅,或僧侶,紛紛經西域進入中國,其中也包括不少景教徒。西元六三五年,大秦國教士上德阿羅本攜帶大量景教經典,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長安,唐太宗聞訊,特命宰相房玄齡至西郊迎接並請入宮中。阿羅本先向唐太宗進呈了奏章,說明景教教義,奏章由房玄齡和魏徵譯成漢文。唐太宗對阿羅本待若上賓,經常讓他進宮講解有關教義,翻譯相關經典。隨著交往日深和對景教了解的增多,唐太宗越來越支持其教義。六三八年七月,他下令准許景教教士在國內傳教。唐太宗在詔書中說: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同時又命有關部門在長安義寧坊建造大秦寺院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後又讓畫工把他的肖像畫在寺內牆壁上,以表示對景教的重視。義寧坊大秦寺是史籍所載中國第一所正規的景教教堂。其後的唐高宗李治秉承前例,敕諭在各州建造景教堂,欽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在他的推動下,景教在中國迅速傳播,「法流十道,國富無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唐玄宗李隆基對景教更是極力鼓吹,親自為景教教堂題寫匾額。他不顧佛僧和道士對景教的攻擊,於開元初年讓其兄弟至教堂接受洗禮,建立壇場。天寶初,他又命大將軍高力士把太宗、高宗、睿宗、中宗及自己的寫真肖像拿到教堂安放,賜給教堂絹百匹。七一四年,大秦國教士佶和到長安朝見唐玄宗,玄宗讓他和教士羅含、普倫等十七人在興慶宮宣講景教法理,以擴大影響。另外,還有教士及烈曾兩次以朝貢的名義來到長安,都受到唐玄宗的接見。一次是七一三年,向唐玄宗進獻了許多奇器異巧之物,玄宗愛不釋手,為此侍御史柳澤還特意上書勸諫玄宗不要被這些譎怪淫巧之物迷惑。另一次是七三二年,進獻之物不詳,這一次玄宗特別賜給他紫袈裟一副、帛五十匹,以示褒獎。為了統一管理,減少麻煩,七四五年十月,特頒布詔書: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會要》卷四十九)
將全國景教教堂統改稱大秦寺,把景教在中國的發展推上了一個新台階。
唐肅宗李亨時又下詔在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這一時期著名的景教教士伊斯與肅宗過從甚密。伊斯「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開始在皇宮中為肅宗服務,深受倚重。後被授予軍職,在唐代名將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軍中充當謀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由於軍功,肅宗特賜以紫袈裟。他的能散祿賜、樂施好善在當時遠近聞名。其後的唐代宗李豫每逢生日,總要向景教教士賜天香,頒御饌,其待遇同佛教僧侶別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