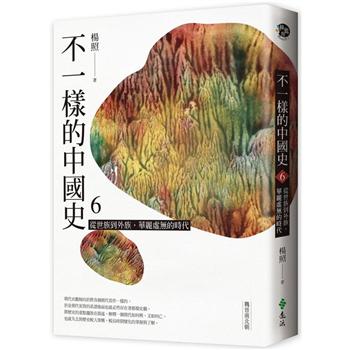從「四聲」探源,重大的文字設計實驗
從文體格式的角度看,駢文是中古時期出現的重大文字設計實驗。參與其中的六朝貴族,尤其是南朝文人,有意識地針對中國文字的特性,開展出特殊的設計方向。中國文字是「單字/單音」的,每個字都只有一個單一聲音,這是很早就確立下來、不會改變的。在這個時期,針對這樣的特性,出現了「對仗」和「協韻」的設計。
「對仗」和「協韻」的運用早就存在,比如《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在文義上是對仗的,而且也用到疊字所產生的聲音效果。不過到了六朝,當駢文的形式固定下來後,文人是有意識地尋找並建立「對仗」與「協韻」的規律,開發出過去光憑直覺不可能達到的嚴謹程度與眾多可能性。
後世對於聲韻的理解,例如一直使用到今天的「四聲」劃分——平、上、去、入,主要都是在六朝時形成的。六朝之前,中國特殊的「文、言分離」狀況下,文字不是表音符號,很明顯地使得中文的語音系統相對不發達。一直到南朝沈約、周顒之前,中國文字究竟應該發什麼樣的讀音,始終浮動不確定。最常用的是從音樂中借來的「宮、商、角、徵、羽」五聲分類,然而語言的音調和音樂的音調有很大的差距,很難真正配合得上。
要到南朝,借助印度語言傳入帶來的影響,中國才發展出更精確的標音工具。由巴利文或梵文這種印歐語言寫成的佛經進入中國,剛開始並沒有太多聲音上的問題,因為在「格義」階段,基本上是套用中國既有的語詞來翻譯佛經。不過格義方式能傳達的佛教概念很有限,到後來就開始改而採用直接音譯專有名詞的做法。如此一來,必然碰觸到多音語言如何對應中文的問題,還必然在外來語言的刺激下,引發對中國自身語音系統的省視。
於是佛經翻譯進入了新的階段,有更多的專門研究者出現,也有寺院組織推動佛經的解釋與推廣。
此外,佛教的傳揚不只包括對佛經的認識,還有像「梵唱」這樣的信仰儀式。佛教相信誦經可以累積功德,而所誦的經文並不是純粹中文的,因為都用中文的文本相對地沒有那種誦經儀式中所需要的流動音樂性。因而「梵唱」唱的,往往是介於梵文和中文之間的特別聲音,大量保留了像「南無阿彌陀佛」這樣模仿多音節語彙的聲音。梵文的Amitaba變成中文的「阿彌陀佛」,那聲音既非梵文、也非傳統的中文。
因為接觸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而那個系統中語言與文字間完全不一樣的關係,促使六朝時期的中國人重新省視自身的語、文關係,尤其是多音節語言的特性,刺激了對於既有語言的高度聲音意識。
陳寅恪先生早年寫過一篇論文,題目為〈四聲三問〉,即考據漢字「四聲」的來歷。依據他的整理,原本中國語言中最清楚的聲音是「入聲」,因為是短促向下的,最容易辨識,也最早有了標示的方法。至於另外三聲「平、上、去」,則是援用印度傳來的《聲明論》。藉由轉讀佛經的聲調,應用在美化中文上,於是使得「四聲」系統盛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齊武帝永明七年(西元四八九年)二月二十日,當時的竟陵王蕭子良聚集了大批的僧侶,「造經唄新聲」,有意識地創造誦唸佛經的新音調,在訂定文字讀音上是歷史性的大事件。從此確立了「四聲」,而周顒、沈約就是那時候新的「四聲」理論和規律的代表人物。
「四聲」確立後又經過一些重要變化。從古早的「四聲」到現代漢語的「四聲」,最大的變化發生在入聲字上。北方語言中入聲愈來愈不明顯,到後來和去聲混同了。不過發音的主流仍然維持「四聲」,取消了入聲,卻將平聲一分為二,有「陰平」和「陽平」之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語」裡的一聲、二聲。
「四聲」在六朝形成後,原本從音樂中挪用過來的「五聲」,相應就不再使用了。
* * *
* * *
要了解隋唐的制度,好好看看北朝
中國中古史研究有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也是一直到今天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不能不讀的著作,那就是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這本書的書名藏著幾個容易產生誤解的字。書名叫做「稿」,表示未完成,只是先拿出來給大家看的稿本,還要再修訂。這是陳寅恪的謙讓習慣,事實上這本書的內容非常完整,立論也很堅實,已經是定本。另外,「略論」二字也不算精確,因為書中已經網羅了與此題目相關的主要史料,進行詳密的探討,提出非常精彩的論證,一點都不疏略。
最重要的是,書名提的是「隋唐」,但實際處理的,主要不是隋代、唐代的歷史,而是要追索其「淵源」,也就是要將我們在隋代、唐代歷史資料上看到的種種制度,仔細追索其來歷。
這本書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貢獻,在於糾正了過去「正統史觀」的偏見,凸顯了北朝的重要性。傳統史學中雖然將這段歷史並稱「南北朝」,但在概念上畢竟還是重南輕北,也就是從「朝代史觀」的連貫性來說,排列順序是曹魏、西晉、東晉、宋、齊、梁、陳、隋、唐……。這樣的概念深入人心,很自然地就將北朝視為偏枝旁統,看待歷史變化時也經常忽略北朝的影響。
陳寅恪的著作指引了現代史學在南北考量上的重新調整,提醒大家隋代、唐代真正的來歷為何。隋代的開國皇帝楊堅和唐代的開國皇帝李淵,他們都來自北方,在建國之前經歷了北魏分裂的東魏、西魏被北齊、北周取代的一系列變化;相對地,他們和南方的南朝並沒有那麼密切的關係。先入為主的「正統史觀」從南朝的角度看隋代、唐代,就會有所偏差。陳寅恪以堅實的史證指出,要了解隋唐的制度,必須將眼光從南朝移開,好好看看北朝。
這本書絕對不是「稿」、不是「略論」,它比大部分的史著都更豐富、更有說服力,尤其建立了兩個明確的觀點。第一,陳寅恪要呈現的不只是隋唐和北朝的一般傳承關係,而是扎扎實實的「制度淵源」。過去對於隋唐與北朝的連結有些鬆散、普遍的說法,例如強調李家可能有外族血統,所以他們對家庭、家族的觀念和傳統漢族思想不一樣,以此解釋為什麼會發生屠殺兄弟的「玄武門之變」……
這不是陳寅恪要談的。他在書中顯示的是,北朝對隋唐最大、最深遠的影響是制度。北朝所構想、制定和實施的制度,決定了後來的隋唐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帝國。隋唐是中國的「第二帝國」,和之前的秦漢帝國大不相同,我們必須透過北朝,才能真正說清楚從秦漢帝國轉折走向隋唐帝國的過程。
第二個觀念是,所謂源自「北朝」,不能被簡化看作源自「外族」或源自「草原民族」。對隋唐產生關鍵影響的這些制度,不是直接從草原帶進中原的,而是在北方原有的漢人文化和新進來的外族生活、外族組織之間漫長的涵化結果。如此出現了一種既非漢人也非草原的新思考、新精神,如果沒有這套新思考、新精神,新的隋唐帝國便無從成立。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提示了中國歷史上不同民族文化互動涵化的過程,格外值得重視。不是粗枝大葉地談論草原民族如何接受漢化,或倒過來草原民族的習俗文化如何改變漢民族;我們需要做的,是細緻地追索某個特定的草原民族的某種習俗文化,以什麼樣的方式和漢人既有的政治或社會組織進行了怎樣的互動,以至於產生了什麼樣的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