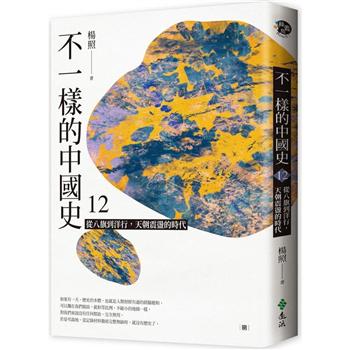「內聖」與「外王」在康熙身上混同了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各種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批注,有時用滿文寫,有時用漢文寫。
滿文才是他的母語,漢文是他後來學習的,所以在運用漢文時格外簡潔直白,不囉嗦、不廢話,更沒有什麼客套裝飾。不論是康熙皇帝親筆御批,或是別人幫他謄抄過的,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見。
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有一本奇特的著作,書名叫做 "Emperor of China",書中寫的中國皇帝就是康熙,而此書最奇特之處在於使用了第一人稱,從頭到尾都是「我」。
這個「我」是史景遷嗎?不是,是康熙皇帝。那麼這本書是小說嗎?不然怎麼能復活康熙皇帝,用他作第一人稱來寫?史景遷又不是康熙皇帝,從史學角度看,他怎麼能寫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稱敘述的書?
一般狀況下是不能的,但史景遷把握、凸顯了從史學和史料學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獨特之處。幾乎書中的每一段,都的的確確有著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稱留下來的史料作為根據,不是出於史景遷的臆測或想像虛構。史景遷所做的,是將這些龐雜豐富的史料,依照康熙的生活進行分類統整。
書的第一章是「遊」,主要講遊獵,在皇帝生活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要維持從東北來的民族風格,也和軍事訓練、軍事行動密切相關。第二章接著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實質進行統治, 和大臣如何具體互動。到最後一章,則探索並呈現他和諸多兒子之間的關係,也就聯繫到皇位與權力的繼承問題。
很難找到多少歷史人物,更不用說帝王,能夠如此用第一人稱來呈現,清楚顯示出康熙皇帝的相關史料多麼豐富。而如此貼近切入他的生活,更具說服力地讓我們看到,他對於知識具有真摯的熱忱,對於聖賢學問的興趣遠高於教他的那些儒生講官們。
這件事對清朝的統治很重要,擴大來看,對中國士人的傳統也很重要。自宋朝建立起來的近世政治觀念,核心精神是區分「政統」與「道統」,皇帝與王朝繼承「政統」,士人則擔負「道統」。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別的,就是「政統」承認需要有「道統」的支撐與協助,才能構成合法、完整的統治機制。
然而到了明朝,「政統」與「道統」之間陷入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士節」的價值觀仍在, 士人普遍有著「道統」的信念,然而皇帝那邊的「政統」卻不只輕忽「道統」,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將「政統」抬得高高在上,「道統」地位相對低落。於是原本認定應該由「道統」來輔佐、甚至指引「政統」的信念便無法落實。
到了康熙朝,產生了「道統」和「政統」間的進一步扭曲──「內聖」與「外王」的兩個範疇在康熙皇帝身上混同了。原本應藉由掌握聖賢知識以代表「道統」,可以在「內聖」範疇中超越皇帝、指導皇帝的讀書人,卻在康熙皇帝面前明顯被比了下去。
在「政統」的權力面,他們當然比不上皇帝;而現在麻煩的是,連在「道統」的知識與實踐上,他們也不如皇帝。皇帝對於聖賢知識的看重程度高於這些士人,進而皇帝對於這些聖賢知識的理解,也高於本來該當他老師的人。皇帝解說朱注,講官只能靜默聆聽,不能置一詞,師生關係明顯逆轉,變成「政統」和「道統」的領導權都掌握在皇帝那裡。(摘自第二講「康熙:統治合法性的確立」)
科舉中人充滿私欲欺瞞的虛偽人生
究竟是哪些因素動搖了科舉制度呢?
首先是考據學的興起,使得舉業不只不再是士人的唯一選擇,而且拉低了原本在明朝舉業成就的地位。《儒林外史》以元朝末年王冕的故事開端,吳敬梓更以王冕拒絕科舉的態度自況,將王冕刻劃為不只是瀟灑,還有著比一般士人更真切的道德自我,應該得到更高的尊崇。
和王冕的故事同等深入人心的,還有「范進中舉」(第三回)。吳敬梓能將這場鬧劇寫得如此精彩,一方面固然靠他的文學之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社會上對於「中舉」這件事的準備、期待到對待反應方式,真的已經扭曲到極度不正常的地步。科舉制度的高度不確定性,對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激烈翻轉程度,使得牽涉在其中的人都有著精神疾病的症狀。整個科舉的放榜場面,就是一連串的昏亂攪擾,讓所有的人都忽忽如狂。
《儒林外史》寫科舉,同時寫和科舉相關的這些士人、官員們的不正常生活。要過那樣的生活,當然不可能遵照他們所讀的聖賢書裡給予的道德訓令與指示,於是更根本的弊病就在於這些人都無法、也不可能過一種誠實的生活,終日在虛偽與自我欺瞞中混日子。
《儒林外史》並不是像《三國演義》或《水滸傳》那樣來自說書的傳統,是說書人一代又一代累積出來的故事集,也不是像西方長篇小說要寫一個有頭有尾有中腰的完整故事,而是一個看透了舉業的人,幫我們從內在呈現戴上舉業眼鏡所看到的歪七扭八世界。
書名叫做《儒林外史》,這「外」字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謙卑地表示這是對於「儒林」的非正式記錄,選擇這些人是跟隨著正史中有「儒林傳」的標準,不過自己寫的當然不能入歷史之法眼,只能是「外史」。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所記錄的事跡在常理之外,不是我們一般人、一般正常生活中會有,能夠用日常之理去理解的,那是圍繞著舉業而產生的各種光怪陸離現象。
從結構上看,《儒林外史》很混亂,沒有貫串的主角,也沒有明確的敘事主軸。勉強只能說採用了一種「打彈子」的方式來安排小說敘事,從一個人引出另一個人,轉而說另外這個人的故事,等到他又遇到了別人,故事又再轉去那個人身上。這樣的方式使得讀者讀了後面就很難記得前面寫過什麼,而且小說要寫誰、不寫誰,總共要寫多少人的故事,都沒有必然性。不過如果我們將吳敬梓所寫的看作是一連串的社會評論,那麼這樣的敘述結構自有其合理性。
他用不同的人物引出不同的社會問題,面面環繞著一個不變的中心,那就是科舉中人如何背離所讀所學的道理,過他們充滿私欲與欺瞞的虛偽人生。
雖然寫的是小說,但吳敬梓的態度反而最接近顏元或戴震他們所提倡的「實學」。他是在做具體的社會調查,在進行詳細的社會記錄。顏元或戴震這些人沉浸在大傳統中,無從獲得、甚至無從尋覓思想資源,讓他們接近具體的人事,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社會」,所以他們的「實學」觀念最終只能退回到書本裡進行。
吳敬梓走了另一條很不一樣的路,從原本大傳統的邊緣地帶,採取雖然使用文字但被視為不正統、不入流的小說形式。吳敬梓再將小說文人化,比描述富商淫亂生活的《金瓶梅》更文人, 直接以文人為小說處理的對象。
以此,吳敬梓得到了開創性的突破成績,細膩且忠實地刻劃了文人與舉業之間不見得那麼堂皇光明的關係。可惜《儒林外史》的開創性並沒有能號召後續者,一來是自身小說形式不成熟, 二來是缺乏一種討論集體現象的方法,只能停留於個別人物的跳躍式呈現。吳敬梓的小說變成了曇花一現的孤例,要等到清末最後十年,才有「譴責小說」隔代傳承、開展其形式與內容。(摘自第四講「變化中的滿漢文化互動」)
「全權代表」與絕對皇權的牴觸
東方和西方在十七世紀的發展,產生了對比的差異。歐洲在一六四八年之後,邦國的平等主權制度確立,形成西方外交活動的根柢;另一邊則是清朝承襲甚至加強了中國中心觀念,使得這兩者之間幾乎無法溝通。
從西方列國外交的角度看,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那就是中國一直頑拒派任全權代表。「全權代表」是從法文pleins pouvoirs 翻譯過來的,意思是確認這個人得到充分授權,可以在談判時進退折衷,以便和對方達成協議。當重大事務進行談判時,歐洲國家已經習慣要求有「全權代表」,要有人說話可以算數,會議談判才有意義。如果無法定案,那就只能來來回回、浪費時間罷了。
可是中國絕對皇權觀念下,只能有「欽差大臣」,意思是由皇帝派任去執行特殊任務,執行該任務時具備等同於皇帝的權力。但「欽差大臣」做的決定,皇帝還是可以否定,皇權最終仍然在皇帝身上,不會交付給任何「全權代表」。皇帝與大臣之間的絕對距離,使得任何大臣不可能得到這種外交談判所需要的信任。
林則徐奉命查辦和鴉片相關的「海口事件」,獲得了欽差大臣的身分,他也將規劃的處理方式對皇帝上奏,還得到皇帝的讚許。然而雷厲的禁菸行動最終引發英國大軍壓境,皇帝可就反悔了,他痛責林則徐,別說兩廣總督身分不保,幾乎連命都沒有了。
鴉片戰爭打輸了,必須向英國求和,英國提出的條件是要有「全權代表」來進行談判,才願意停止軍事行動。當時道光皇帝知道後,御批簡單四個字:「可惡之至」。後來英法聯軍侵襲,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時,譚廷襄以直隸總督身分到大沽口談判。英、法方首先要確認的就是:來者是「全權代表」嗎?譚廷襄無奈地表示:我不可能是「全權代表」,沒有任何人可能是,因為在中國只有一個人能具備「全權」,那就是皇帝。
西方產生「全權代表」觀念,是在西發里亞條約後的列國制度中多次試驗得到的教訓。雙方在可能爆發戰爭的緊張狀態,或試圖要結束戰爭時,必須要由真正能拍板定案的人坐下來談判, 你來我往,有攻有防,有進有退。如果無法有效談判,談判時無法確認對方有多大的決定權限,雙方很容易誤判,而造成意外的重大傷害或損失。
在過程中,西方國家發展出內外機制,確保「全權代表」取得君主與政府的信任,也知道如何防範談判中的越權主張與行為。
然而中國沒有經歷過這種過程,皇帝和他所派去的代表之間,沒有這種信任管轄機制。更重要的,皇權本來就是可以後悔改變的,皇帝甚至不受自己過去所做的決定約束,這是絕對皇權的一部分。
絕對皇權的關鍵之一,就是皇帝的主觀意志高於制度,皇帝必須保有反覆變更的權利,才不會變成制度或慣例的傀儡。皇帝要能推翻制度,也要能推翻自己過去的意見與主張。(摘自第五講「東方帝國與西方帝國的根本差異」)
中國共產黨和太平天國崛起的相似性
太平天國訴諸於中國歷史「小傳統」伏流中一直存在的素樸平等信念。為什麼有人窮、有人富?更奇怪的,為什麼富人那麼富、窮人那麼窮?同樣都是人,卻在財富上有這麼大的差異,怎麼來的?
富人容易將自己的財富與享受視為理所當然,不會問也不需要問這種問題;但相對地,窮人常常會在羨慕或忌妒的心情中生出這樣的疑問,並對現實中的分配狀況感到不公平。每個社會都有這種素樸的平等訴求,在中國也往往成為刺激底層騷亂的一大力量。當農民受到荒欠或戰爭影響,幾乎要活不下去,卻同時看到富人仍能吃飽穿好,相對被剝奪感升高到一定程度,就寧可訴諸賣命、賭命的方式予以宣洩。
這種情緒存在上千年,曾經鼓動幾千次的騷亂事件,不過太平天國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給素樸的信念一套外來的真理包裝。用一種不是傳統大家所熟悉的說法,卻正因為是外來的,帶有陌生性質,聽起來更有道理。這種訴求、這種狀況,在太平天國滅亡半個多世紀後,又在中國以另一種更為波瀾壯闊的方式複製出現,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
從一九二○年代快速崛起,到一九四九年取得全中國的政權,開始了長期的統治,除了外緣如中日戰爭的因素外,在內緣、根柢上,中國共產黨憑藉的就是創造出能夠將農民和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思想與組織。
這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完全沒有前例。我們可以用明末的情況做個明顯的對比:以農民組成的「流寇」得不到士人的支持,李自成的組織裡吸引不了什麼士人,無法建立一個像樣的政府;而由士人組構的幾個南明政權又得不到民心,在基層社會的建造上徹底失敗。
能鼓動人民的,是革命推翻既有秩序,但這是士人最害怕的;而士人所支持的既有秩序、恢復舊秩序,又明顯違背了農民要翻身的強烈情緒,怎麼可能吸引農民呢?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崛起過程中,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發揮了前所未見、巨大的社會階層團結作用,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重要關鍵。
一端是農民,他們被素樸的「共產」平等觀念所號召、動員;另一端是知識分子,他們嚮往馬克思主義的外來先進學說,尤其是背後的科學理論保證。如此中國共產黨完成了歷史性的社會連結,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迸發出驚人的力量,從知識到組織到武裝戰鬥,都遠遠超過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中國當時其他政治勢力。
以這種方式崛起的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後重新整理歷史,不會沒注意到類似的模式出現在太平天國。名字叫「太平天國」,強調的不是「和平」而是「平等」;而且在凸顯「平等」重要性時,洪秀全引用了外來基督教作為權威,創造了一個奇特的「拜上帝教」。披著外來宗教真理訴求的偽裝,使得太平天國和之前的地下會黨,以及五斗米教以降到白蓮教的各式團體,都顯得不一樣。過去地下團體的信仰基礎都入不了士人的法眼,是被士人剝奪其地位與合法性的邊緣思想,於是在動員上有極大的先天限制。
太平天國的全新信仰直接聯繫上從鴉片戰爭到南京條約,大幅衝擊士人文化的西洋思想,再和底層的農民組織綁在一起,讓朝廷和士人們不知該如何應對。更重要的,如同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參與其中的人感受到一份理想與希望的鼓舞。集體行動不只是為了替自己找到溫飽,而是為了在現實中建造「天國」。
接受信仰動員、改造的農民,因而展現了一種特殊的紀律,讓太平天國可以創建政治與財政組織,才能夠將政權延續那麼久。(摘自第八講「絕不太平的「太平天國」」)